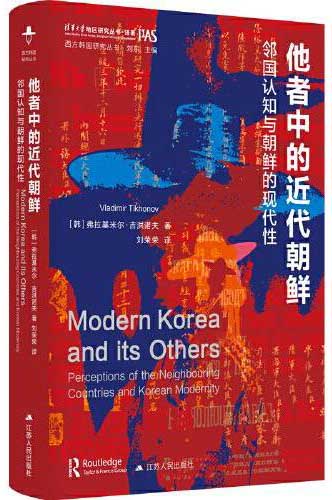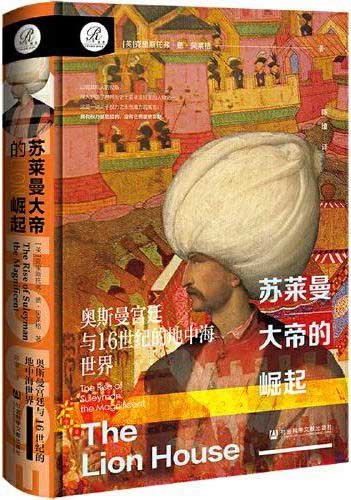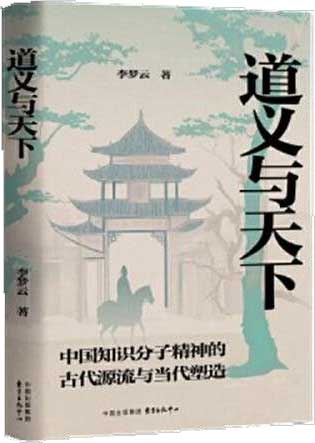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他者中的近代朝鲜(西方韩国研究丛书)
》 售價:NT$
398.0
《
索恩丛书·苏莱曼大帝的崛起:奥斯曼宫廷与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
》 售價:NT$
403.0
《
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宋代将门百年兴衰史
》 售價:NT$
454.0
《
金钱的力量:财富流动、债务、与经济繁荣
》 售價:NT$
454.0
《
超越想象的ChatGPT教育: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教育 (土耳其)卡罗琳·费尔·库班 穆罕默德·萨欣
》 售價:NT$
352.0
《
应对百年变局Ⅲ:全球治理视野下的新发展格局
》 售價:NT$
398.0
《
前端工程化——体系架构与基础建设(微课视频版)
》 售價:NT$
454.0
《
道义与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古代源流与当代塑造
》 售價:NT$
407.0
編輯推薦:
日本国宝级摄影师,亚洲当代摄影拍卖纪录保持者,杉本博司文字代表作。将最亘古永恒的事物用最崭新的方式呈现。以生命、时间、历史为核心,书写个人对文明兴衰的解读与想象,探讨这世间的刹那与永恒,蕴含深刻的思考和智识。
內容簡介:
本书是日本国宝级摄影师杉本博司唯一一本摄影评论集,书名“直到长出青苔”取自素有“日本诗经”之称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书中收录了杉本博司自1974年以来所有的代表作品,包括“海景系列”、“肖像系列”、“剧场系列”、“建筑系列”、“博物馆系列”、“布景系列”等。文章分为十六章,每章以一幅杉本的摄影作品和一段问答起兴,延引出艺术家本人通过摄影的方式与历史、哲学、时间、记忆、梦境等主题的互动所获得的洞见,并以及其诗意而禅意的方式娓娓道来,充满东方意境。
關於作者:
杉本博司
目錄
作者中文版序
內容試閱
人究竟需要多少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