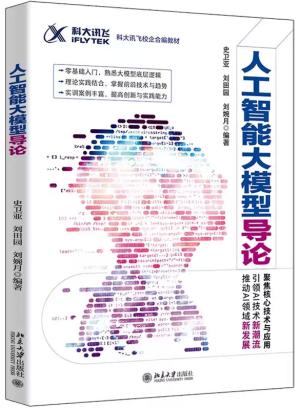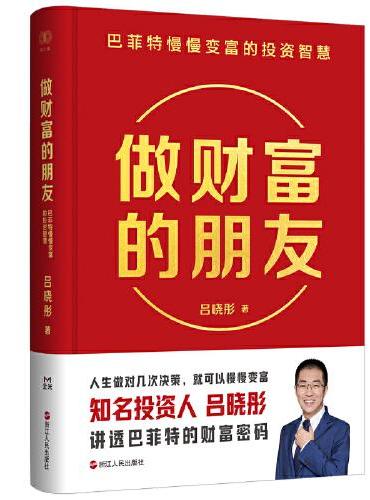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NT$
454.0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NT$
347.0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NT$
352.0

《
纸上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破译古老文明的密码,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150+资料图片)
》
售價:NT$
398.0

《
米塞斯的经济学课:讲座与演讲精选集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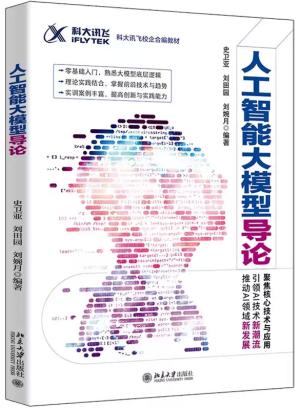
《
人工智能大模型导论 科大讯飞校企合编教材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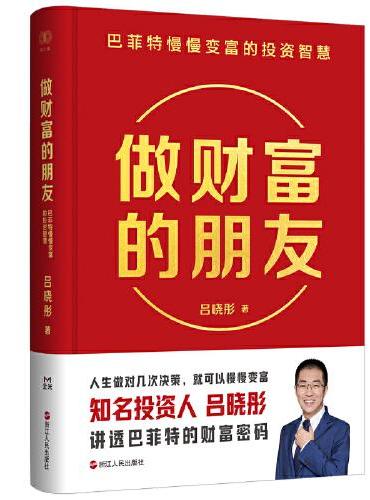
《
做财富的朋友:巴菲特慢慢变富的投资智慧
》
售價:NT$
383.0

《
一群数学家分蛋糕:提升逻辑力的100道谜题
》
售價:NT$
281.0
|
| 內容簡介: |
当年轻貌美的珍妮遇上相貌堂堂的白兰德,悲剧的序幕已然拉开。
天真懵懂的珍妮轻率献出了宝贵的贞操,谁料到才52岁的白兰德会英年早逝呢,他倒是许诺要和珍妮结婚的。
这场于珍妮而言新奇而短暂的人生插曲给她留下了可爱的女儿,也让她从此失去了正常嫁人的机会。
悲
剧继续延续,珍妮又遇上了英俊富有的雷斯脱。如果说白兰德还算谦谦君子的话,那么这个雷斯脱绝对是霸道强悍的。温柔善良的珍妮又一次在命运的捉弄下不由自
主委身于雷,倒也过了几年稳定舒适的生活。直至雷为了遗产抛弃她,女儿也因病死去,珍妮终于孑然一身,悲剧已达顶峰,而故事也就此结束了。“在她面前,她
只凝视着一个寂寞余年的长杳视景”。
一部哀婉凄恻的情史,一曲悲天悯人的恸歌。德裔贫民戈哈特的大女儿珍妮为人帮佣,与参议员白郎特相爱。不久,白朗特不期病故,留下一遗腹女。之后富家子瑞斯特爱上珍妮并与之同居,但在婚事上一直下不了决心,其后因兄弟姐妹的阻拦和反对而苦恼,并在家族的压力下与珍妮分手,重归上流社会,最后,和洛蒂。贝丝结婚。两情缱绻而劳燕分飞,珍妮孤独的过完了中年,瑞斯临终前对她亲吐心腹之言后,痛苦的死在了她的怀中。
|
| 關於作者: |
西奥多·德莱塞
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和代表作家,被认为是同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的美国现代小说的三巨头之一。在当时那个时代里,德莱塞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形象。这不仅仅因为他在1925年出版了让人读后悲伤至极的《美国的悲剧》,也是由于他的个性化的个人生活,对女性的渴望使他卷入种种风流韵事。代表作有《嘉丽妹妹》《珍尼姑娘》等
。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一八八○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一位中年妇女,由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姑娘陪着,走进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家大旅馆,来到账房的台子跟前,打听那里有没有她能做的工作。她身子虚胖无力,面容坦率开朗,言谈举止却显得天真羞怯。她那双善于忍耐的大眼睛里,饱含着这么一点忧愁,只有满怀同情地端详过孤苦无告、心烦意乱的穷人面容的人方能理解。谁都看得出来,跟在她后面的女儿怎么会有一种羞涩、胆怯之感,使她躲缩在背后,两眼若无其事地望着别处。要知道,她母亲虽说没有受过教育,但她富有诗意的心灵里,却充满了幻想、感情,以及与生俱有的慈爱。她父亲则具有一种稳重沉着的性格,而这些性格在她身上都兼容并包了。此刻正是贫困把她们赶到这里来的。她们母女俩赤贫如洗的境况是那样富有感染力,甚至连那个账房都被感动了。
“你乐意干什么样的工作?”他问。
“也许你们这里有一些洗洗擦擦的活儿,”她胆怯地回答,“我会擦地板。”
她的女儿一听见这句话,就怪别扭地把脸孔侧转过去,这倒不是因为她不乐意干活,而是因为她不愿让人家一眼就看出她们穷得非出来干活不可。那个账房倒是颇有侠义心肠的,见到这样的美人儿落了难,不免有些于心不忍。从那个女儿真的百般无奈的神情,一望可知她们的遭遇确实是苦不堪言。
“请稍等一会儿。”那个账房说了,就走进后面办公室去叫女茶房的领班出来。
旅馆里果然有的是工作。经常来擦地板的那个女工走了以后,大楼梯和大客厅就没有人打扫了。
“跟着她的是她的女儿吗?”女茶房的领班问,因为从她站着的地方就看得到她们。
“是的,依我看大概是吧。”
“她要是想来的话,今儿个下午就可以来。我想,那女孩子也会给她帮帮手吧?”
“你就去找女茶房的领班,”那账房回到办公桌跟前高兴地说,“就打那儿过去,”他指着附近一道门,“她会关照你的。”
原来,吹制玻璃的工人威廉·格哈特本人和他全家屡遭不幸,以短小的一幕,不妨可以说,就是这出悲剧的顶点。威廉·格哈特碰到的正是下层社会里司空见惯的厄运,他每天都得看着他的妻子,他的六个孩子,还有他自己,就靠哪一天赶上运气好,赐给他的一点儿东西勉强过活。他自己正病倒在床上。他的大儿子塞巴斯蒂安——他的同伴们管他叫巴斯——现在本地一家制造货车厂商那里当艺徒,每周收入只有四块钱。大女儿珍妮维芙,虽然十八岁多了,至今还没有学过任何手艺。剩下的孩子是,乔治十四岁,玛莎十二岁,威廉十岁,维罗尼加八岁,他们年纪还都太小,什么事都不会干,只是给全家生活徒增困难罢了。他们生活上唯一的依靠,就是那所房子,尽管用房子来抵押只借得了六百块钱,毕竟还是属于格哈特的财产。当时他之所以要筹借这笔钱,是因为买下这所房子,已把他全部积蓄都花完了,但他还想在旁边另搭三个房间和一条门廊,这样一家人方才全能住下。虽然离抵押期限还有好几年,但因为他日子过得越来越紧,不但把平日攒下来准备还本的那一点儿钱动用了,就连偿付年息的钱也都花完了。格哈特求告无门,自己知道日子难过,——医生索取诊金的账单,房子抵押后的按期付息,不用说,还有向肉铺子、面包房的赊欠,尽管店主们知道他的确诚实可靠,随他拖欠不还,可是到头来还是信不过他了,——以上种种烦恼沉重地压在他心上,使他寝食不安,他的病也就迟迟好不了。
格哈特太太可不是一个弱女子。她一直替人家洗衣服,反正有多少洗多少,其余的时间就得给孩子们穿衣、做饭,打发他们去上学,还要给他们缝补衣服,侍候卧病的丈夫,偶尔她也会暗自落泪。每当杂货铺不肯赊欠东西时,她又得常常亲自出去,寻找一家远一点的新杂货铺,先拿一点儿现钱开个户头,以后记账赊欠,直到有人警告那位好心的铺子老板切莫上当、不再让她赊欠的时候,她只好越走越远,另找新的铺子去。那年月,玉米最便宜。有时她就煮上一锅加碱玉米糁,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吃上整整一个星期。玉米粉调成粥,也总比没东西吃强些,不过里面要是加上一点儿牛奶,那就算得上吃酒席了。炸土豆在他们看来几乎就像一种佳馔,咖啡则是难得喝上的珍品。煤块是他们提着篮子、木桶,沿着附近铁路车场的岔道两旁捡来的。劈柴同样也是从附近木栈那里拾来的。他们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熬着日子,无时无刻不在巴望父亲的病好起来,玻璃厂早点开工。无奈冬天转眼就到,格哈特开始感到绝望了。
“我恨不得马上摆脱掉窘境才好。”——这是那个倔强的德国人嘴上常说的一句口头禅,不过,他说话时那种有气无力的声音,还是表达不出他内心的焦灼不安。
真是祸不单行,偏巧小维罗尼加又出了麻疹,一连好几天,大家都认为她八成儿活不成了。她的母亲什么事都顾不上了,只是守在她身旁,一个劲儿替她祈祷神佑。埃尔旺格大夫纯粹出于人类的同情,每天都过来给那个孩子认真诊治。路德宗教会里的旺特牧师,也以教会的名义前来表示慰问。他们两个人都把一种阴森森的宗教气氛带到了格哈特家里。他们是身穿黑袍、由至高无上的主派来的神圣使者。格哈特太太好像以为马上就要失掉自己的孩子,忧心忡忡地守在那小床旁边。三天以后,危险好歹过去了,可家里连一块面包都没有了。塞巴斯蒂安挣来的工钱,都拿去买药了。只有煤块还可以随便去捡,可是,孩子们已有好几回从铁路车场被撵了回来。格哈特太太把她可以求职的地方通通想过了,正在绝望之中才想起了这家大旅馆。现在她真像奇迹一般,时来运转了。
“你要多少工钱?”女茶房问她。
格哈特太太没承想到人家会征求她的意见,可是她为饥寒所迫,就壮了壮胆回答说:
“一天一块钱,不算太多吧?”
“不太多,”女茶房说,“这里每星期大概只有三天的活儿。你只要每天下午来一趟,就干完了。”
“好极了,”格哈特太太说,“打今天就开始?”
“好的。你跟我来,我指给你看打扫的工具在哪儿。”
她们就这样即刻被领进的地方,是当地一家以豪华著称的大旅馆。
作为俄亥俄州首府的哥伦布,人口有五万,过往旅客络绎不绝,确是经营旅馆业的理想场所,事实上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机会,至少当地居民对此颇感得意。这家旅馆是一座气势宏伟的五层楼的建筑物,坐落在本城中央广场的一隅,广场那里则是州议会大厦和各大商店。旅馆大厅很宽敞,不久前还重新装饰过。白色大理石地坪和墙裙,因为经常细心揩擦,总是闪闪发亮。富丽堂皇的楼梯两侧是胡桃木扶手,每个踏级上都嵌着黄铜横条。大厅的一隅,有一个专卖报纸和香烟的柜台,十分惹人注目。账房间和经理部各办公室,就设在楼梯拐弯处底下,全用上等硬木板壁隔开,都安上了当时最新款式的煤气装置。站在大厅尽头的一个门口,就可以望见旅馆附设的理发厅,里面摆着一排排理发椅和刮脸用的水杯。旅馆门前经常有两三辆接送客人的汽车,按照火车开行的时刻一会儿开来,一会儿又开走。
这个大旅馆是本州政界冠盖云集之处。有好几个州长,在他们任期内都把这里当作常驻的寓所。还有两个美国参议员,只要到哥伦布来办事,少不了住到这家旅馆里带有客厅的房间。里头有一位就是参议员布兰德,差不多被旅馆老板看成是个长住的客人,因为布兰德不仅是本城居民,而且还是个单身汉,除了旅馆以外,城里已是无家可去了。在其他来去匆匆的客人里头,包括众议员、本州议员,以及院外游说的政客、商人、自由职业者,总之,各色人等,应有尽有,他们来来往往,使得这个有如万花筒一般的世界越发眼花缭乱、喧声鼎沸。
她们母女俩突然被抛入这个光艳夺目的小天地,不由得感到无限惊骇。她们总是小心翼翼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去碰。生怕得罪人家。她们负责打扫的那个铺着红地毯的大门厅,在她们看来简直如同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她们总是连眼睛都不敢抬起来,说话时也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后来去刷洗楼梯踏级,揩擦漂亮的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她们俩可得要鼓起一点儿勇气来才行,因为这时母亲心里不免有些胆怯,而女儿觉得自己就这样出现在大庭广众之前,哪能不害臊呢。客人们就在楼梯下壮丽宏伟的休息厅里闲坐、抽烟,而且还不断有人进进出出,谁都看得见她们母女两个。
“这儿不是挺美吗?”珍妮维芙喃喃自语道,但一听见自己的声音,心里就感到紧张不安。
“是啊。”她母亲回答说,这时正跪在地上,用她那双笨拙的手使劲在拧揩布。
“住在这儿一定花很多的钱吧,你说是不是?”
“是啊,”她母亲说,“小小的旮旮旯旯里,可别忘了擦。看这儿,你就漏掉了。”
珍妮听了妈这么说,心里很憋气,但她还是认真地干活,使劲地揩呀擦呀,再也不敢抬头东张西望了。
母女俩就这样胼手胝足地从楼上沿着楼梯揩擦下来,一直忙活到五点钟光景。外面天黑了,整个大厅却灯火辉煌。她们眼看着怏要擦到楼梯底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