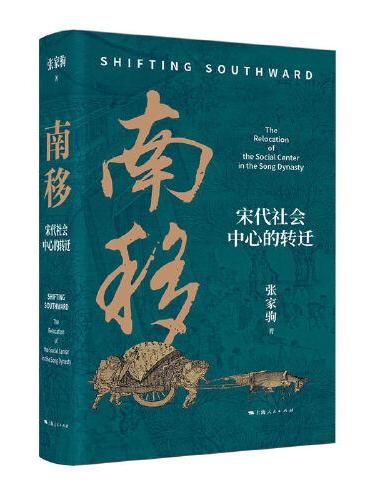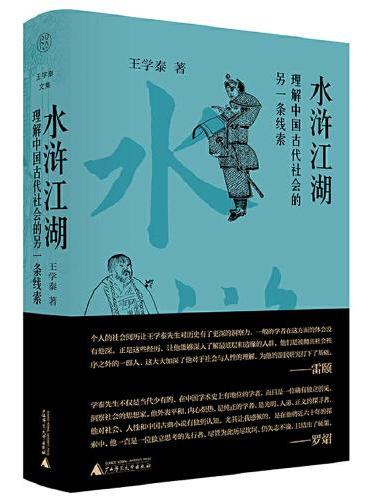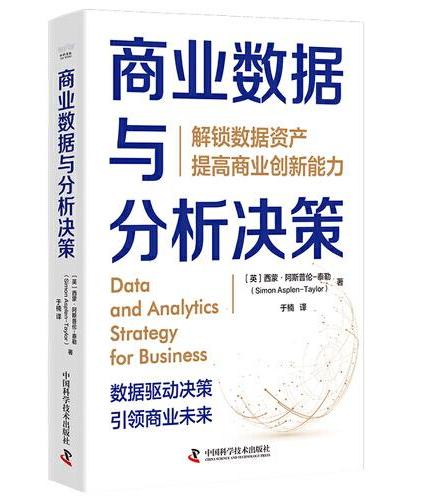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慢性胃炎的中医研究 胃
》
售價:NT$
30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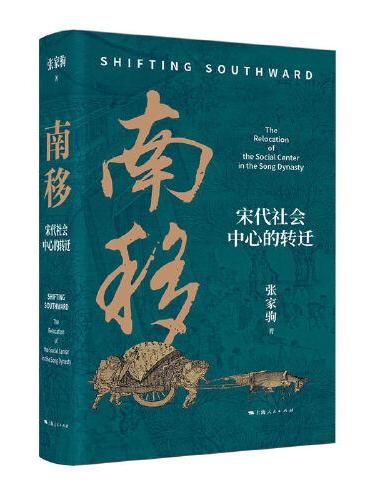
《
南移:宋代社会中心的转迁
》
售價:NT$
7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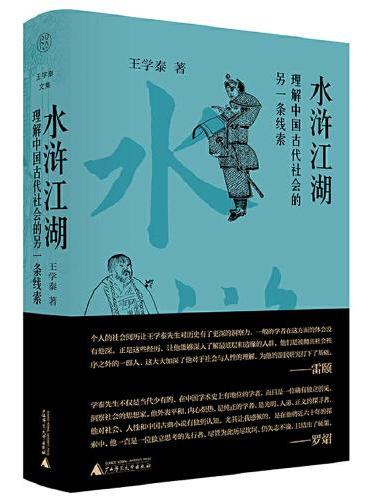
《
纯粹·水浒江湖: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另一条线索
》
售價:NT$
469.0

《
肌骨复健实践指南:运动损伤与慢性疼痛
》
售價:NT$
1367.0

《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MySQL版)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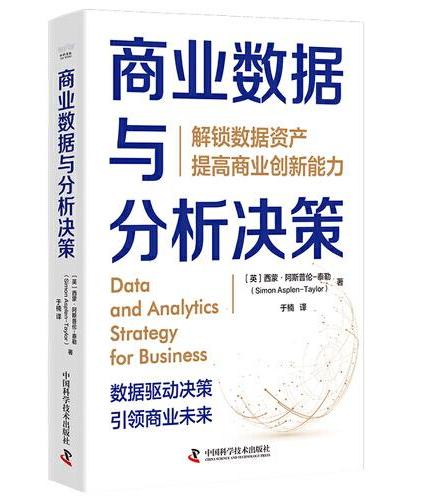
《
商业数据与分析决策:解锁数据资产,提高商业创新能力
》
售價:NT$
367.0

《
倾盖如故:人物研究视角下的近世东亚海域史
》
售價:NT$
357.0

《
史学视角下的跨文化研究(一): 追踪谱系、轨迹与多样性
》
售價:NT$
485.0
|
| 編輯推薦: |
★当村上春树谈奥运时,他谈些什么?
★你以为只看电视,就能看透奥林匹克的一切?
以悉尼奥运为切入点,村上春树坦诚表达对奥运、对竞技体育的反思,以及对澳洲人文的考察
★温和的村上,第一次犀利批判!
体育是残酷的东西。而要对抗这残酷的体育,只能反过来残酷地对待体育。挨了揍立即还以老拳!
★30岁以前,我觉得写文章是很难的工作,有许多题材写不出来。但在《悉尼!》以后,已经没有了那种顾忌。现在我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写作变成一件轻松的事。
——村上春树
|
| 內容簡介: |
因酷爱跑马拉松,2000年,村上春树应《Number》杂志邀请赴悉尼采访奥运会。
本书以悉尼奥运为切入点,坦诚地表达了村上对奥运会、对竞技体育的反思,并幽默地写下对澳洲人文的考察、对考拉和袋熊的趣味观察:
体育是残酷的东西。而要对抗这残酷的体育,只能反过来残酷地对待体育。挨了揍立即还以老拳。
主办方对这些竞技者几乎全无体谅之心,满脑子想着自家那哗众取宠的演出。如此一来,哪里是什么体育盛典,无非是国家与巨型企业出于同一目的携手组织的活动,其原理就是投资与回报。而体育说来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欣赏与赞美这种肉体的辉煌。少数幸运的选手由于辉煌的成功,他们的姓名将长久地为人们记忆。然而绝大多数的选手,不久便会静静埋没于无名而茫漠的黑暗中。
但有一样东西不得不承认。那就是某种纯粹的感动,恰恰是在无穷无尽的无聊之中才会产生……我大概会久久地记住当时空气的味道、光线的状况、人们的呼喊。那是一种特别的东西。
……
|
| 關於作者: |
村上春树
日本著名作家。
生于1949年。29岁开始写作,处女作《且听风吟》获日本群像新人奖,1987年问世的《挪威的森林》轰动全球,日文版销量已突破1000万册。
1982年秋,开始职业作家生涯,同时开始长跑。30年来,长跑足迹遍及夏威夷考爱岛、马萨诸塞剑桥、希腊马拉松古道。因酷爱跑马拉松,2000年,应日本《Number》杂志邀请赴悉尼采访奥运会。
《悉尼!》以悉尼奥运会为切入点,坦诚地表达了他对奥运会、对竞技体育的反思,并幽默地写下对澳洲人文的考察、对考拉和袋熊的趣味观察。
|
| 內容試閱:
|
9月11日(星期一)
抵达悉尼
巨人与养乐多的对阵一直看到第七局下半,此时养乐多领先两分,我才百般不舍地(这么说稍稍有些夸张,因为巨人夺冠几乎已成定局)坐进了日航JAL771航班。由于是飞往奥运会举办地悉尼的,自然座无虚席。代表团和官员将机舱挤得密不透风。一踏进机舱,就已然进入奥运状态了,甚至荡漾着类似激情的东西。连舱内广播也传来了“预祝搭乘本次航班的诸位选手大显身手……”的祝词。
在座位上刚坐下,睡意便立时袭来。不久晚餐送来,并不太饿,只扒拉了一半,其余的都剩下了。吃着吃着困意难禁,几乎是手中还拿着餐刀和叉子便睡着了。待醒来时,托盘已经撤走,咖啡也没喝到。就是如此困倦。横躺下来一直熟睡到早上四点。好像在东京期间积累了相当多的疲劳。
醒来后睁眼往舷窗外望去,只见眼前展现出澳洲大地,万里无云,唯有初升的新太阳高悬在空中。一万米的下方清晰地映出飞机的投影。
就像是裸露无遗的自我,与迄今见过的任何地方都风景迥异。至于何处相异、如何相异,颇难言喻,却迥然相异。既像在制作过程中失手做坏了的景观,又像是梦境之中意识之下扭曲了的风物。
我记得昨夜乘上了飞往悉尼的飞机,所以心下明白“这是澳大利亚风光”。若非如此,而是没头没脑地陡然将这风景塞在眼前的话,我只怕要懵懵懂懂不知自己身处何地,会迷惶困惑,还会忐忑不安。弄不好竟会以为被带到了别的行星。
从飞机上俯瞰西伯利亚冻土带的景象或阿拉伯沙漠的风光,也每每有野性而超现实之处,但长时间聚精会神地观察之后,总能有所解悟:“这儿就是这样的风土,因而使得景物如此吧。”但是澳大利亚的风景不同,总体而言是古怪之极。那种古怪一望便知。同时那古怪的盖然性却难以提取。凝神细看时,竟会生出奇妙的落魄感来,觉得自己仿佛被拽进了别的(错谬的)时空之中。好似蒂姆·伯顿的电影场景。
澳大利亚是一块在深深的孤立状态中送走了悠久时光、拥有独特发展历程的大陆。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平坦、最炎热的国家。由于雨水最少,大河也少,几乎不见所谓侵蚀的痕迹。也没有值得一谈的火山,没有山脉。而世界上为数最多的有毒动物却一一在此开张营业,譬如说十大毒性最强的毒蛇的名录,几乎悉数被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蛇占据。
澳大利亚栖息有大约二百三十种哺乳类动物,它们认识到澳洲大陆作为生存环境(尤其是对幼仔而言)过于严酷,半数在进化过程中选择了变为有袋类动物。如此一来,这块大陆与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交流,约有六万年之久是在日晒与孤绝中度过的。
就是这样一片土地。仅仅是从飞机上鸟瞰,也能强烈地切身感受这种类似“不可思议”的东西。
但景色的确秀美。有沙漠那般荒凉的土地,周匝绵延着平缓的丘陵,原生艺术般的清晰阴影一望无际。其中大概流淌着与远古一无变易的平缓的时间推移。永看不厌。
话虽如此,可这光景也太离奇了。
飞机终于飞出海上,大大地盘旋一周后,降落在悉尼国际机场。在机场的特设柜台领取了贴有相片的采访证,装在塑料套里,挂在脖子上。没有它就进不了比赛场馆。身穿蓝白两色统一服装的红脸膛善男信女(都是志愿者)守候在机场,为抵达的相关人士引路。“顾达矣。”不知何故,澳大利亚的志愿者都长着红脸膛。
乘出租车赴宾馆。那里叫作帝苑酒店。不大,也不算富丽堂皇。打个比方的话,令人想起一个本本分分兢兢业业、眼见步入中年后半期的人。但这样可能反而轻松些,不是那种不管跟谁四目相对都得掏腰包付小费的酒店。
房间阳光也充沛。洗了澡(幸运得很,热水供应正常),在桌上安好电脑,接上电话线,上网发邮件都不成问题。行啦,这一来工作场所就算搞定啦。有一个热水供应正常的浴缸,再有一张能干活的桌子,其余的事就无关紧要啦(然而这样的平静未能长久,不过是后话)。
在附近散步。天气既不热,也不冷,一件长袖衬衣正好。走进近旁的银行兑换一笔数目可观的日元。澳元最近持续急剧下跌,一澳元等于六十日元。记得几年前曾经接近一百日元(下文中出现的商品价格均为澳元)。
在大约两条街开外,找到一家专门出售降价书的书店,买了一批澳大利亚作家的小说。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在日本很难买到,在美国也一样,趁着逗留此地期间进一批货,尽管不知是否有趣,只能信手拈来,酌情选购。降价书店果然名副其实,价格便宜得惊人,三本十澳元。不过一澳元只相当于六十日元,这样的评价似乎有些过低。实际应该值八十日元。诚然,澳元贬值对我们旅行者来说无疑值得庆幸。
与先期抵达当地的《Number》编辑部的谷君(这是化名)及川多女士一道,去近处吃午饭。领到奥运期间租用的手机,那是奥运组委会出借的小型三星预付卡手机。三星是本届奥运会官方指定的手机,有了它便可以使用专用线路,据说要比普通手机容易接通。我不太喜欢手机,但要是没有它,此次采访可能就会手足无措。因为赛场太大,得东奔西跑,无法联络。三星对此次悉尼奥运会似乎很下了一番力气,花了不少钱。或者应说投入了巨额资金。三星的总经理为了营销甚至亲自赶来悉尼的新闻曾见诸报端。
在唐人街购物中心的意式餐馆,一边喝啤酒吃比萨,一边商谈采访事宜。我是初来乍到,诸事都摸不着头脑。但离开幕式还有几天,我们商定赶在之前调整好状态。我基本单独自由行动,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一如平素。
与他们分手后,我独自一人散步至达令港,去著名的悉尼水族馆。一旦奥运会鸣枪开赛,势必每天都将手忙脚乱,还是赶在之前一个人各处跑跑,把想看的东西先看了再说。水族馆非常大,按照参观路线一圈看下来花了近两小时,不过非常非常有趣。假如有《米其林水族馆指南》之类的话,毫无疑问会得满分。我去过许多国家的水族馆,而此处以澳大利亚独有的鱼类及海洋生物为主,展出内容十分特别。
一开始是鸭嘴兽。与澳大利亚其他哺乳类相同,总显得有些木头木脑,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仿佛困意未消却被强行唤醒的人,又像被迫套上不合趣味的衣裳被拽出门的人。
鸭嘴兽是害羞的动物,大多潜伏在水中生活。下面这个事实鲜为人知:雄性鸭嘴兽的后爪会分泌毒液,遭遇外敌时便会使用这招。并不会主动出击,而是“没办法呀,算了吧”,如此迫不得已时才使出此招。但毒性相当强,人类姑且不论,狗儿之类据说足以致命。
鸭嘴兽在水中时,眼睛、鼻孔和嘴巴都会紧闭密合。于是喙便成了唯一的感觉器官,全凭它觅食。怪物一个。本来已生蛋孵化,却还要再哺乳,为何非得多此一举呢?据说一七九八年,当第一具鸭嘴兽剥制标本被送往英国皇家科学院时,学者们惶乱不已,纷纷认为“这准是恶作剧,要不就是骗局”,拒之门外。他们以为这是用数种动物的部分躯体拼缀而成,胡乱捏造的标本。其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还有巨大的鳄鱼。澳大利亚有栖息于海水中的“咸水鳄”和栖息于淡水中的“淡水鳄”两类,而无论何事都爱从简的澳大利亚人便将前者呼为“小咸”,后者喊作“小淡”。如此称呼让人误以为它们很可爱,其实毫无可爱之处。小咸每每单独行动,小淡则爱结队成群。小淡只将两眼浮出水面,待动物夜间来喝水便一口咬住。袋鼠之类也常常被吞噬,但小淡多数不袭击人类。
据说从前有一只巨大的小淡很出名,专门袭击摩托艇的悬挂式马达。这家伙对噪音轰鸣的悬挂式马达深恶痛绝,无论何等忙碌,只要一听见那声音,便猛扑过去咬住小艇,嚼成齑粉(完全可以理解它的心情)。尽管如此,它却从不袭击人类。
然而小咸君只要一看见人,百分之百就要条件反射般奔袭过来。这种对人类而言本质上危险且致命的动物,找遍全世界也不多见。没遇到挑衅也要袭击人类的动物,据说包括这家伙在内,地球上只有两种。(另一种是什么?我渴望知道,然而书上却没写。)
尾巴扁平呈刮刀状,它摇摇摆摆地甩动这尾巴,在海里游来游去。全长达三四米,有的年龄竟高达百岁,真够长寿的。用锋利的牙齿牢牢咬住猎物,一口吞进喉咙深处,然后再优哉游哉地慢慢消化。牙齿的作用只是为了不让猎物逃脱,而不是用来咀嚼的。被这种家伙活生生地一口吞下去,一定不是快事。一旦吞下肚去,恐怕是不会简简单单就放出来的。
鲨鱼也为数众多。全长达三米的沙锥齿鲨沿着玻璃回廊悠闲地游来游去。外表看去简直是大白鲨直接从银幕上游了出来,好不吓人,其实这种鲨鱼并不袭击人类。但因为形象狰狞可怖,直至不久前在澳大利亚还被视为危险物种。
在澳大利亚,如果杀死沙锥齿鲨,将被课以巨额罚金。但形象如此可怖的鲨鱼一旦落入渔网,想杀之以除害恐怕是人之常情。在澳大利亚,死于交通事故者每年为五千人,但遭遇鲨鱼袭击丧生者平均每年一人。一般所知的三百七十五种鲨鱼中,袭击人类的仅有五种。然而,尽管被告知不必如此惊恐,可游泳时遭遇巨大鲨鱼还能镇定自若,准确作出判断“没关系,这家伙不属于那五种”的人,只怕寥寥无几。一般人更会由于过度恐惧导致心脏病发作吧。
鲨鱼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食欲旺盛。只需两天喂食一次即可。因此在悉尼水族馆,为了确保每只鲨鱼都吃到了食物,潜水员每次都亲手喂它们鱼吃。
鲨鱼的尾鳍后方并排长着两个生殖器(看去很像后腿),交尾时使用其中的一个。到底依据什么基准进行选择呢?今天该是右边啦,因为上次是左边,莫非是这样么?假如我是鲨鱼,只怕会忘记上次用的是哪一边。
水族馆透明的圆筒状回廊直通达令港海底。外面的大海货真价实,并非人工仿造(当然是隔开来的),因此相当真实,震撼人心。
尽管不会被水母吞噬,可它仍然令人生畏。虽没有实物,却以照片形式展示了它给人的皮肤留下伤痕的实例,实在触目惊心。我在热海的海面游泳时也曾被水母螫过,奇痛无比。而这些照片上伤痕的惊人程度远非日本的水母可比。皮肤竟至变形!
可对人造成严重伤害的水母,在澳大利亚共有四种:
1.箱型水母
2.远洋水母
3.发水母
4.僧帽水母
如果只是听听名字发音,倒也感觉不错,其实没有一种可亲可爱。一旦被这些家伙螫着,再遭遇小咸君袭击的话,可就惨不忍睹了。
而且,澳大利亚的海胆也异常凶猛,若被刺着一回(那刺儿还来得个粗),再断在里面,便极不易挑出来,挑出之后据说也会留下严重的伤痕。十分吓人。此外更有众多凶暴的毒蛇栖息在海中。
不吓人的,则有青蛙君,十分好玩。有一种绿蛙很可爱。
总而言之水族馆很大,光走路就走得疲惫不堪。应当分成两天来看才好。
归途乘坐单轨电车返回宾馆附近。单轨电车恰好在约两层楼的高度行驶,可以从窗口窥见建筑上层的房间。有英式小酒馆,有美容院,有普通办公室。这颇为有趣。其间可见不同于在街道上行走时所见的都市风景。跟其他交通工具相比,单轨电车票价稍贵,然而颇有些《银翼杀手》的感觉,饶有兴味。
晚上和谷君坐出租车赴市内一家叫“某某俱乐部”的餐馆吃日本料理。虽然来澳大利亚第一天就吃日本料理未免有点怪,但姑且不计较。该店据称是朋友的朋友开的。我吃寿司。这家日本料理店里还放了台吃角子老虎机。在澳大利亚,但凡冠以“某某俱乐部”的餐馆,大多放有赌博机,似乎是法定如此。名目上是会员制,但实际上有名无实,大家都以“嘉宾”身份入内。
我喝澳洲葡萄酒,要的是赤霞珠红酒,禾富庄园一九九七年份。美味异常,后来我还去过酒铺,打算买同样的酒,二十澳元,但是高一档次的禾富庄园赤霞珠红酒(一九九六年份灰牌)也才四十澳元,我便试着买了这种。带回日本喝去(如果没在路上喝光的话)。
回到宾馆房间,立即钻进被窝睡觉。可是空调过猛,冷。我裹紧被子,一边发抖一边睡。找遍房间也没发现设定空调温度的开关。明天得投诉去,今天已经无心再做任何事情了。
……
9月22日(星期五)
令人愉快的铅球比赛
六点前起床。正打算写稿子,却发现好像把电源转换器忘在了布里斯班的宾馆里,(啊呀呀,为什么总是丢三落四的!)无法使用电脑。打算待会儿借谷君的,不过昨夜弄得太晚,他肯定还没起床。没办法,姑且先整理剪下的报纸。报纸真是新闻的宝库(废话一句)!
早晨去一直叨扰的那家咖啡馆喝咖啡,吃三明治。三明治太大,吃不完,剩下一半带回来留作午餐吃。长期旅行时每每如此,胃口会一天天地小下来,变成一天仅吃两餐即可。
向澳大利亚人道谢说“Thank you”,他们往往不回答“不用谢”,而是答以“Thank
you”。起初我也没太在意,可渐渐疑惑起来。有的人还会说“No worry”。然而从没有人说“You are
welcome”。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了“You are
welcome”,对方便会以为“臭小子竟敢耍我”,劈头盖脸打过来么?
慢跑了四十五分钟。昨日坐了整整一天的车,身体僵硬,不过跑着跑着得到缓解,劲头涌出来了。回到房间,洗澡洗衣。每天去奥林匹克公园看比赛,在售货亭吃热狗,到对面的小酒馆喝啤酒,得空便写稿子,入浴时洗身子顺带洗内衣内裤和运动衣,于是一天便似乎匆匆过去了。哎哟,好忙。
下午,乘电车去奥林匹克公园。上车后,心想“在赛些什么啊”,便摊开报纸查找。在赛棒球,澳大利亚对阵古巴。我打算去观看这场比赛,一边在记者席上写稿子。我得把这次旅行写下来。记者席上备有带电源插座的桌子,可以一面吹着来自海湾的清凉的风,一面在蓝天下心情舒畅地写稿。当然喽,得空还要瞟上几眼棒球。
澳大利亚面对夺标最大热门古巴队,拼得相当不错。比赛最后以一比零告终,古巴险胜。就过程而言,取胜也是顺理成章。古巴投手没让澳大利亚攻击阵容打出连续安打,无须换人便毫不费力地投完整场比赛。球速始终超过每小时一百五十公里。澳大利亚教练对此惊叹不已:“那样的投球可是美国职业棒球甲级联赛王牌选手的水平呀!”澳大利亚总共只打出三个安打。
然而澳大利亚防守稳健,古巴击球手的击球也难以突破对方防线。尽管开场便先声夺人攻陷一城,后来却怎么也无法再接再厉。随着比赛的推移,古巴击球手愈加焦躁,就连我们都有所感受。场上洋溢着“不该是这个样子!”的气氛。被压制的澳大利亚队反倒更有活力。澳大利亚的击球手中,在美国密尔沃基酿酒人队与野茂英雄组成投接搭档的接手尼尔森(中日龙队的“澳洲野犬”)打出了两个安打,引人注目。
球场满座(到场观众为一万四千)。不必说,占绝大多数的是澳大利亚人,助威声势也盛大热烈,场内的狂热劲头也堪称炉火纯青。假如被蒙着眼带进来,估计根本不知道这里竟是澳大利亚。但与观众的兴奋相比,记者席却空空如也。托其福我倒可以不慌不忙地干活。虽说是万里晴空,但躲入背阴处便是凉风习习。我穿了条短裤出来,结果两腿觉得冷。体感温度与昨日之前迥然不同。
古巴队的红色球衣,在日间赛场那鲜艳的绿茵上格外醒目。醒目得简直不妨说是“杂乱无章”、“野蛮之至”。尽管如此鲜艳夺目,此次的古巴国家队却不见一贯的压倒性的强大。澳大利亚队诚然输了球,但肯定会有这样的感触:对方绝非不可战胜的敌手。就像惜败于巴西脚下的日本足球队一样。
看完棒球,顺便去了趟新闻中心,想了解田径赛的开赛时间。不料竟与有森裕子不期而遇。她和电视台的人在一起,面庞清瘦,晒得黝黑,比之前更加精悍。看来训练得相当刻苦。
在新闻中心的电脑上确认田径比赛日程安排。女子五千米六点钟、男子一万米九点半鸣枪开赛。之间夹着女子四百米预赛,那位圣火接力手凯西·弗里曼也将出场。还有男子一百米和女子一百米预赛。我决定一边干活,一边从头到尾慢慢地观看径赛。
在新闻中心伏案工作至六点。一到六点,移到主体育场,一面继续写稿,一面欣赏感兴趣的比赛。首先是女子五千米预赛。我自然为三位日本选手加油,可惜全军覆没。脚力根本不及非洲和中美洲选手。这样的距离无疑是全仗才能比拼的世界,对日本选手而言恐怕过于苛刻。
男子一百米,伊东浩司奋力拼搏,通过了预赛。虽然是勉勉强强过线,但毕竟十分了得。成绩是十秒二五。后面还有半决赛,不过到了这一步,只怕前途不易吧(注:结果终于没戏)。
女子四百米预赛。弗里曼跑得毫不费力,从容地撞过终点线。她跑姿优雅,仿佛在说:预赛嘛,哪里用得着那么拼命。尽管这样,她却依然比谁都快,第一名通过预赛。但她并没有特别高兴,没有笑脸,连手也不挥。观众席上的加油声排山倒海,无数的闪光灯在看台上闪烁。她跑完比赛后,许多观众便离席而去。即便还是预赛,她的出场照样是这一日的精华场面。自不待言,到了决赛人气一定会更加升温吧。
但并非人人都支持弗里曼。她是原住民,却被破格提拔为代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棒圣火接力手,不少人对此怒不可遏:这岂不是政治交易吗?!大量的攻击性邮件寄到媒体。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事,凯西·弗里曼似乎变得相当神经质。巨大的重负落在她的肩头。这分明不能归罪于她,不是她的责任。
她不多说话,在态度上也没有表现。然而从她的举止中,却不能不感受到类似冰冷的火焰般的东西。站在跑道上,接受着支持者的热烈声援,她却显得异常孤独。澳洲运动员们因为奖牌大丰收欢天喜地,她置身其中更是显得孤独。
“今天的比赛结果您满意么?”对于新闻记者这样的提问,她一言不发,只是点了点头便匆匆离去。一如平素,新闻稿里写道。决赛夺得冠军时,她会不会破颜一笑?哪怕只是为了亲眼目睹这个镜头,我也希望她能夺取金牌。
我是为了观看女子五千米和男子一万米预赛才来主体育场的,但此话先不谈,出人意料的是铅球比赛十分有趣。只见长得五大三粗的大叔齐聚一堂,像飙车一族“地狱天使”的集会一般。或是ZZ
Top的歌迷会。这些大叔虽然外表吓人,其实相当可爱。朝着大屏幕的摄像机乱做鬼脸。铅球没扔出去反倒掉到地上,也嘻嘻哈哈,仿佛在说:啊哟,好危险。还神气活现地大做V字手势。喂喂,我说你们严肃点儿好不好!
不过,望着这样的场面,你会觉得这不太像奥运比赛,非常愉快。那气氛就像是星期六晚上,一群炫耀力气的大叔在街头的酒吧里喝着啤酒比试力气。其中最具震撼力的大叔是芬兰人,浑身洋溢着一种强烈的“临场感”,仿佛刚才还在森林里一面吓退附近的狗熊一面砍伐木头来着。体格雄伟,似乎能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整桶啤酒。我喜欢上了这位大叔的长相,便一直为他加油,总算奏效(不知是否如此),他成功夺得金牌。两位美国人分获银牌和铜牌。颁奖仪式上演奏芬兰国歌,这好像是ZZ
Top,哦不不,西贝柳斯的曲子,太好了。我也起立鼓掌。大叔,干得好啊!不妨向故乡的人们炫耀一番吧。今晚的啤酒肯定味道好极了。
这边在投掷铅球,旁边在比赛跳高。田径赛中的田赛是许多项目同时进行的,看得人眼花乱。说必然倒也是必然:铅球选手与跳高选手的体形,对比未免也太过鲜明。而且跳高选手即使试跳失败,也不会做出V字手势来遮羞。不仅是身材,在精神上也迥然相异。如果让他们对换角色,进行对方的比赛,恐怕就得天下大乱了。
然而体育场里飞蛾奇多。我一面挥手击退频频来袭的飞蛾,一面写着原稿。田赛场上也满是飞蛾,抬头望去,只见密密麻麻的飞蛾遮蔽了天空。大概有好几万只吧。似乎是辉煌的照明将整个霍姆布什的飞蛾都吸引过来了。该不会有古怪的飞蛾吧。要是被它们在耳朵里产了卵,可就惨不忍睹啦。
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男子一万米预赛。我很钟情一万米这个项目,看起来总是目不转睛。当然马拉松我也很钟情,不过一万米有一万米独有的兴奋。如果说马拉松是重油浓酱的串烤鳗鱼盖浇饭,一万米就好比是清淡爽口的什锦天妇罗荞麦面(这个比喻也许不大好懂)。然而好慢哪,时钟已经指向了晚间十点,接近深夜了。就不能早点开始比赛么?早睡早起的人便看不成田径比赛,这也真叫怪事。
首先第一组,嘉娜宝的高冈寿成奋力拼搏,顺利闯入决赛。中盘被非洲选手为主的第一梯队的四位选手甩下,可是在最后三圈又独自从第二梯队冲出,积极地向前追赶。赛风积极进取。虽然由于差距拉得过大未能追上,但独自远远跑在第二梯队前面,第五个冲过终点。二十七分五十九秒。第一梯队四人成绩都在二十七分五十秒左右。
第二组中有SB的花田胜彦出场。照例带着鲜艳耀眼的橙黄色太阳镜。比赛的发展与高冈寿成那一组几乎相同。在最后三圈猛追以非洲选手为主的第一梯队四人,到了最后的直道终于赶上,就势硬挤进去,夺得第三。创个人最好成绩,二十七分四十五秒一三。跑得相当好。花田给人的印象是每每以毫厘之差功败垂成,今天可算做到了坚韧不拔,很好。
我还是平生第一次亲临现场仔细观看田径比赛。平常总是通过电视画面观战。看电视的话,毕竟只能看到适合电视播映的那一部分。以大抵相同的角度,播放大抵相同的图像。播音员和解说人的话也大抵沿袭相同的模式。所以胜负情形、技巧如何虽然可以了解得细致入微,却很难感同身受地把握整体的推移。
而来到体育场一看,便可以清晰地知道,一种竞技项目并非孤零零的独立存在,而是拥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这是一个新发现。在之前漫长的沉默和之后漫长的沉默间,方才有它存在。我们观众也和选手们一样,从漫长的沉默中浮起,深入这种竞技项目之中,然后再度沉入漫长的沉默中去。而这种沉默,理所当然地,在电视转播中完全被切掉了。
体育场这个所在,走来亲眼一看才会知道,其实相当杂乱。田赛场上和径赛场上,各种比赛项目同时展开,而且每个项目都在默默进行。如果不集中精力仔细观看,你就会不辨东西南北。没有评价,没有说明。遇到不明之处,只能自己调出资料,查找讯息。然而只要眼睛习惯了这种杂乱,就能渐渐学会只截取自己需要的讯息,学会自己动脑判断,自己睁眼观察。于是,在场的一个个选手身体反应的速度,其毅力其呼吸,紧迫感,注意力,恐惧感,所有这一切(尽管相距很远)都会活生生地、畅通无阻地传递过来。
赛场上,众多的一流运动员各各在殊死拼搏。有人拥有压倒性的才华,有人拥有马马虎虎的才华,也有人只有难以称为才华的才华。然而不论是何等优秀的角色,其才华的巅峰状态恐怕也只能维持短短数年。肉体会在形形色色的角落撞上极限,慢慢走上衰落之道。换言之,肉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恰与遮蔽了体育场上空、飞来舞去的群群飞蛾相同。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欣赏与赞美这种肉体的辉煌。少数幸运的选手由于辉煌的成功,他们的姓名将长久地为人们记忆。然而绝大多数的选手,不久便会静静埋没于无名而茫漠的黑暗中。我望着在赛场上专注于各项竞技的年轻人的身影,一边在心中如此思索。忽然,我想到了远古时,希腊市民在圆形露天竞技场里眺望着赤身裸体的运动员们,或许也思考过同样的问题。肯定思考过吧。一则希腊人就是喜欢思考这类事情的民族,再者肉体不可避免地会衰弱消亡,乃是自古以来永恒不变的事实。
所有的径赛项目全部结束,是在十点四十分左右,之后大家络绎不绝地朝着车站走去。于是通向车站的路上排起了一条长龙,怎么也走不到开往市内的电车站台。我在这长龙中等了差不多三十分钟,队伍只向前挪动了一点点。
照这样下去的话,等坐上电车起码得花一个小时(这里我来过多次,感觉应当是准确的),于是我毅然改乘相反方向的西去列车,先到立德寇姆,在那里换乘开往市内的电车。即是说不乘坐奥运专列,而是去坐普通的通勤电车。上次我去过帕拉玛塔,大致知道换车的诀窍。
结果这是正确答案,我得以乘坐毫不拥挤的电车回到了中央车站。话虽如此,这次奥运会的旅客运输的确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平时还算好,到了高峰期简直手足无措。甚至得排一个小时的队。而且,一旦电车运行上出现麻烦(比如说事故或车辆故障之类),数十万人将被抛掷在有如陆上荒岛的地方。只是设想一下便令人不寒而栗。所幸的是迄今为止,这样的情况连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饥肠难耐,打算一回到市内就去宾馆旁边的小酒馆吃顿便餐,然而是周五之夜,各家小酒馆都人满为患。甚至有客人走到酒馆外面喝啤酒。每个周末都像大年夜一般喧噪不已。无奈,只得回到房间里,独自一人喝罐装啤酒,吃着从附近便利店买来的仙贝。宾馆周围是华人聚居的地域,华裔青年成群结队地涌到街头,欢度周末之夜。几个男孩在邀约几个女孩,好像很快乐。我如果精力尚存的话,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然而我有些疲倦。年纪也大了。又不会说中国话。
如此这般,待上床时已是凌晨一点了。就不能早一点结束比赛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