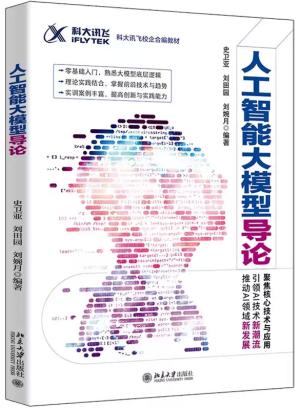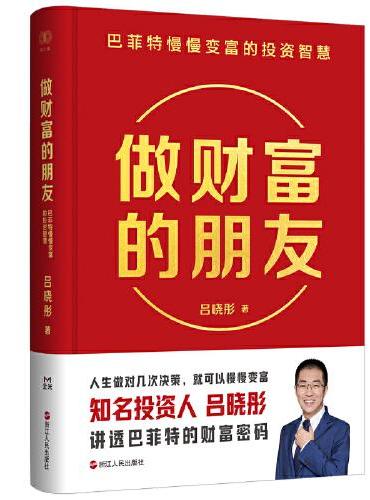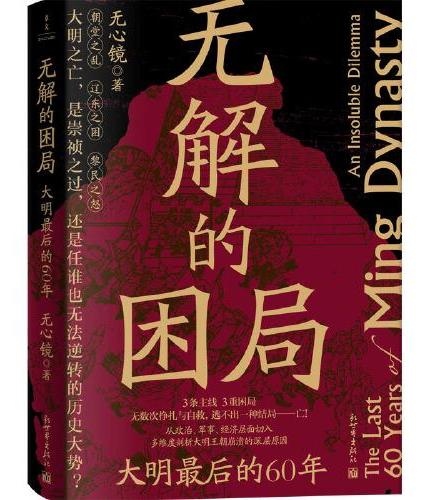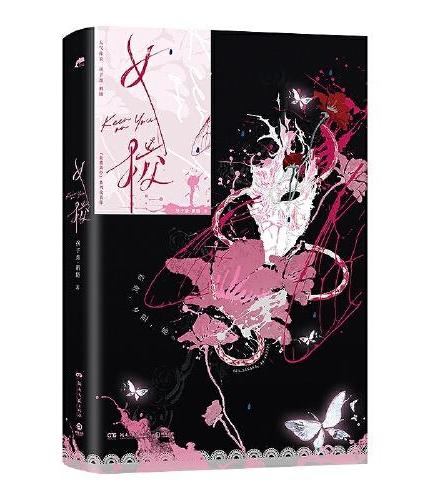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NT$
352.0

《
纸上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破译古老文明的密码,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150+资料图片)
》
售價:NT$
398.0

《
米塞斯的经济学课:讲座与演讲精选集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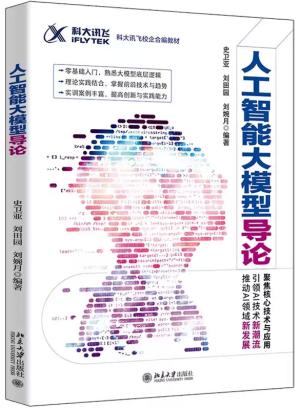
《
人工智能大模型导论 科大讯飞校企合编教材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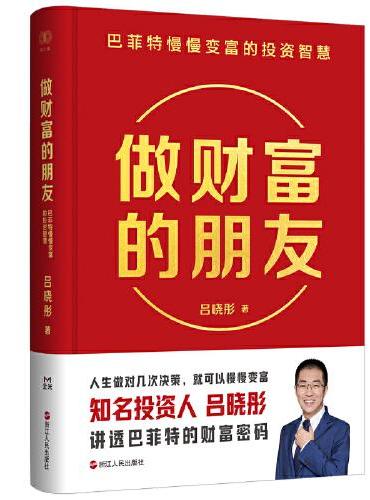
《
做财富的朋友:巴菲特慢慢变富的投资智慧
》
售價:NT$
383.0

《
一群数学家分蛋糕:提升逻辑力的100道谜题
》
售價:NT$
2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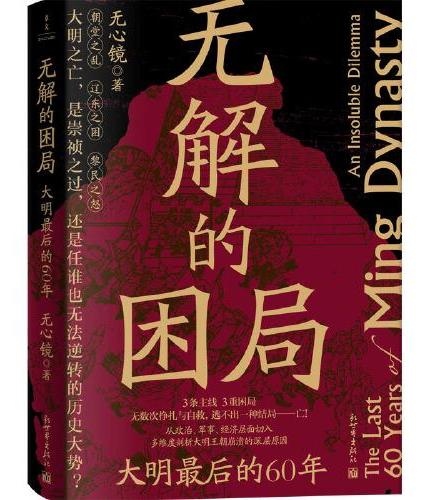
《
无解的困局:大明最后的60年
》
售價:NT$
3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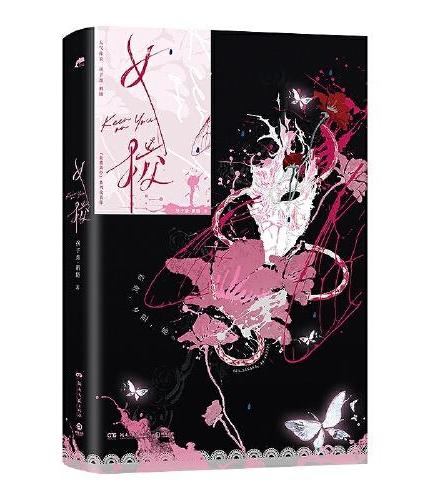
《
女校(人气作家孩子帮·鹅随“北番高中”系列代表作!)
》
售價:NT$
281.0
|
| 編輯推薦: |
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大师奖得主、三获爱伦?坡奖
入选侦探小说百大榜单
被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搬上荧幕的经典作品
在这个由盲作家写下的故事里,在她流光溢彩的幻想世界中,有最惊悚的谋杀和最动人的情话
|
| 內容簡介: |
|
孤僻富有的克拉沃小姐接到了一通骚扰电话,电话里的声音神秘而魅惑。随后,电话中的诅咒竟然一个接一个地变成了现实。克拉沃小姐委托她的股票经纪人布莱克希尔调查打骚扰电话的人,更多的受害者浮出水面。最可怕的是:那个打电话的人没有制造任何新的恐惧,只是利用了她们已有的恐惧……
|
| 關於作者: |
玛格丽特·米勒 Margaret Millar,1915—1994
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婚后移居美国,成为美国公民。高中时期开始写作,一九四一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后因罹患眼疾而采用口述录音的方法创作。凭借《眼中的猎物》、《怪物的疆域》、《邪魔》三获爱伦·坡奖。曾任美国推理作家协会主席,一九八三年被该协会授予大师奖。一九八七年,《眼中的猎物》入选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评选的“一百部最佳侦探小说”。
玛格丽特·米勒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文笔简洁而富有表现力,长于使用比喻,常常通过营造不安和恐怖气氛推动人物冲突和情节发展。她关注社会阶级差异、性自由问题和处于道德困境中的社会边缘人物,善于刻画孤独偏执的人性。在她的笔下,精神病人的幻想世界令人既毛骨悚然又心醉神迷。
她的丈夫肯尼思·米勒(笔名罗斯·麦克唐纳)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两人上高中时相识相恋。婚后,肯尼思在妻子的影响下开始创作侦探小说,成为硬汉派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同妻子一样,他也擅长运用心理暗示和比喻,同样三获爱伦·坡奖,并先于妻子获得大师奖。
|
| 內容試閱:
|
1
一个轻轻的、带着笑意的声音:“是克拉沃小姐吗?”
“我是。”
“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一个朋友。”
“我有很多朋友。”克拉沃小姐撒了个谎。
电话桌上方挂着一面镜子,她看到自己的口型正在重复这个谎言,似乎很享受。接着又看到自己点了点头,表示肯定——这个谎言是真的,是的,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谎言。只有眼睛拒绝被说服,尴尬地眨了眨,目光从镜子里移开了。
“我们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那个女孩说,“但我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搜集你的消息,我有一个水晶球。”
“我……请你再说一遍?”
“我有一个可以预知未来的水晶球,所有的老朋友都会不定时地在里面出现,今天晚上出现的是你。”
“我?”海伦?克拉沃的目光又转向镜子。镜子是圆的,像一个水晶球。她的脸闪现出来,像一个老朋友,一个熟悉却不亲密的朋友。她薄薄的嘴唇紧紧抿着,皮肤紧贴着颌骨。黑色的头发剪得像男人的一样短,耳朵都露了出来。她的耳朵总是像被冻坏了一样带着一抹紫红色。眼睫毛和眉毛的颜色太浅了,以至于眼睛周围看起来一片空白,这有点儿可怕。水晶球里有一个老朋友。
她很小心地说:“请问你是哪位?”
“伊夫琳,记得吗?伊夫琳?梅里克。”
“哦,当然。”
“现在想起来了?”
“是的。”她又撒了一个谎,比前一个还容易。这个名字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个分辨不出来的声音,就像三层楼下、车流嘈杂的大道上的一辆车和另一辆车的噪声一样难以分辨。它们听起来都很像:福特、奥斯汀、凯迪拉克和伊夫琳?梅里克。
“还在吗,克拉沃小姐?”
“在。”
“听说你老爸死了。”
“对。”
“听说他给你留下一大笔钱。”
“那是我的事。”
“这么多钱可不容易处理。也许我能帮你。”
“谢谢,不需要。”
“也许你很快就会需要了。”
“我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不认识的人帮忙。”
“不认识的人?”语气很刺耳,好像被激怒了。“你说你记得我。”
“只是出于礼貌而已。”
“礼貌,你总是表现得像个淑女,是吗,克拉沃?或者装作是。总有一天你会记住我的,总有一天我会出名。我的身体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艺术博物馆里,每一个人都会看到我。嫉妒吧,克拉沃?”
“我觉得你……疯了。”
“疯了?哦,不是,疯的不是我,是你。你才是那个什么都记不住的人。我知道你为什么记不住,因为你嫉妒我,太嫉妒了,所以你把我从记忆中抹去了。”
“才不是呢,”克拉沃尖着嗓子喊,“我不认识你,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你弄错了。”
“我可没弄错。克拉沃,你需要一个水晶球,这样就能记得你的老朋友了。我应该把我的水晶球给你,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自己了。喜欢吗?还是害怕了?你一直是个胆小鬼,我的水晶球会吓得你灵魂出窍。我正看着它呢,你想听一听我看到什么了吗?”
“不,不要说了。”
“我看到你了,克拉沃。”
“不——”
“你的脸就在我面前,清清楚楚。但有点儿不对劲儿,哦,我看到了,你出事了、受伤了,你的前额撞开了,你的嘴在流血,血,到处都是血,到处都是……”
克拉沃小姐伸手把电话从桌子上扫了下来。电话翻倒在地板上,没有摔坏,还在嘟嘟地响。
她坐下来,吓呆了。在水晶球一样的镜子里,她的脸没有变、没有受伤。额头是平滑的,嘴唇是整洁的,皮肤却像纸一样白,似乎已经没有血可以流了。克拉沃小姐的血已经流尽了,这么多年来,默默地,在心里流尽了。
震惊逐渐消退以后,她俯身捡起电话,放回桌子上。
听筒里传来了接线员的声音,“请告诉我号码。我是接线员,请告诉我号码。你想打电话吗?请告诉我号码,好吗?”
她想说,给我接警察局。就像戏剧里的人那样轻松随意,就像她们已经习惯了每周给警察局打两三次电话一样。克拉沃小姐从来没有报过警,一次也没有。在她三十多年的生活中,她甚至都没跟警察说过话。她不害怕警察,只是没有和他们打交道的机会。她没犯过罪,和罪犯没有过任何干系,也没有人对她犯下过任何罪行。
“请问你要的号码?”
“是……是琼吗?”
“什么?是的,克拉沃小姐。哦,你不出声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晕过去了,或者出了什么别的事呢。”
“我从来没有晕倒过。”第三个谎言。说谎已经变成了习惯,变成了爱好,像串成一串的珠子,由谎言做成的项链。“几点了,琼?”
“九点半左右。”
“你很忙吗?”
“现在总机只有我一个人,朵拉感冒了,我也差一点儿。”
含混不清的话语里透着自怜,克拉沃怀疑琼并没有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差点儿感冒,估计琼的上司也不信。
“你快下班了吧?”
“还有半个小时。”
“你能不能……我希望你能在回家前到我的房间来一趟。”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克拉沃小姐?”
“是的。”
“哎呀,我什么也没——”
“十点以后见,琼。”
“啊,好吧,可我还是不明白我——”
克拉沃小姐挂断了电话。她知道怎么对付像琼这样的人:挂断电话,断绝联系。克拉沃小姐没有意识到,她一生中断绝联系的人已经太多了,她太频繁、太轻易地挂断了太多人的电话。现在,她三十岁了,孤身一人。电话再也没有响过,敲门的只有送饭的服务员、理发的女美容师,或是送晨报的门童。再也没有谁的电话可以挂断了,除了一个在她父亲办公室工作过的接线员和一个疯疯癫癫的陌生人,拿着水晶球的陌生人。
她挂断了那个陌生人的电话,但挂断得太迟了。似乎是孤独感迫使她去聆听,即使邪恶的语言也胜过寂静无声。
她穿过客厅,推开小阳台的法式玻璃门。阳台上只能放下一把椅子,克拉沃小姐坐了下来,望着三层楼下的马路。马路上车流滚滚,灯光闪烁。人行道上挤满了人,夜色中充满了嘈杂的生活气息。噪声敲击着克拉沃小姐的耳膜,听起来真奇怪,好像是来自另一颗星球的声音。
一颗星星在天空中升起。第一颗星星是用来许愿的,但克拉沃小姐什么愿望都没有。她和马路上的行人只隔着三层楼的楼梯,却像到星星的距离一样遥远。
琼来晚了,她绕道去了酒吧,从后门的楼梯爬到了克拉沃小姐的厨房门口。克拉沃小姐有时也走后楼梯,琼经常看见她偷偷摸摸地进进出出,像一个瘦弱的、胆战心惊的鬼魂在躲避活人。
厨房的门上了锁。克拉沃小姐的所有东西都上了锁。旅馆里有一个传言,说她在房间里藏了一大笔钱,因为她不信任银行。这样的传言太普遍了,一般都是门童传开的。没钱赌马的时候,这些孩子就以幻想能偷到钱为乐。
琼不相信这个传言。克拉沃小姐把东西锁起来,因为她就是一个习惯了上锁的人,无论东西是否值钱。
琼敲了敲门,等着克拉沃小姐来开。她微微摇晃着,因为喝了双份的马提尼,楼下的收音机正在放华尔兹,华尔兹总是让她跟着晃,骨瘦如柴的身体在那件廉价的花格呢大衣里前后摇晃。
“谁呀?”克拉沃小姐的声音打断了音乐,像一把刀切断了黄油。
琼把手放在门框上,稳住了身体。“是我,琼。”
门链被取了下来,门锁开了。“你来晚了。”
“我来之前有些事要做。”
“我明白。”克拉沃小姐知道是什么事,厨房里都能闻到了。“进来吧,去另一个房间。”
“我得马上走。我姨妈会——”
“你为什么走后门的楼梯?”
“我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让我上来,如果是我做错了什么,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来这里,他们会大惊小怪的。”
“你什么也没做错,琼。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克拉沃小姐微笑着,态度很和善。她知道怎么对付像琼这样的人。微笑,即使是被恐惧和不安造成的极度痛苦折磨着,她也对她们微笑。
“你来过我的房间吗?琼?”
“没有。”
“从来没有?”
“我怎么可能来过呢?你从没有让我上来过,我是在你搬进来以后才找到这份工作的。”
“你想先参观一下吗?”
“不,不,谢谢,克拉沃小姐。我得马上走。”
“那就喝点儿什么吧,你想喝什么?”微笑,说些好听的话,准备各种饮料,她不惜一切代价逃避孤独,期待电话铃再次响起。“我有一些上好的雪利酒,存了很久了——为了招待客人用的。”
“一丁点儿雪利酒应该不至于让我喝醉,”琼知趣地说,“尤其是我快要感冒的时候。”
克拉沃小姐在前面带路,穿过走廊走到了客厅。她转过身以后,琼好奇地四处打量着,但实在没什么可看的。走廊里的门都关着,根本看不到门后藏着什么,储藏室、卧室或是浴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