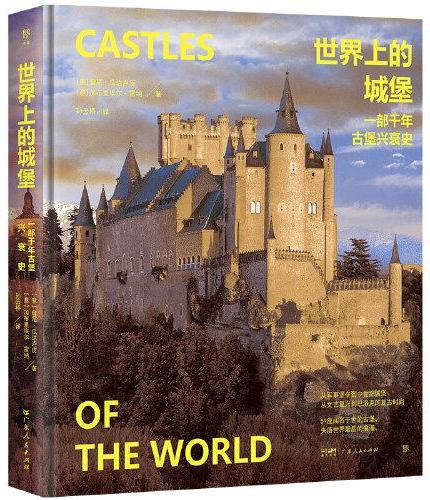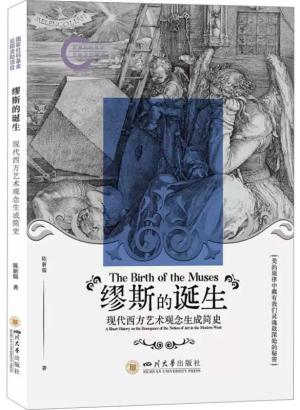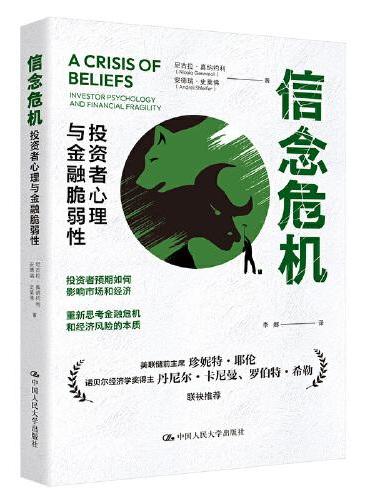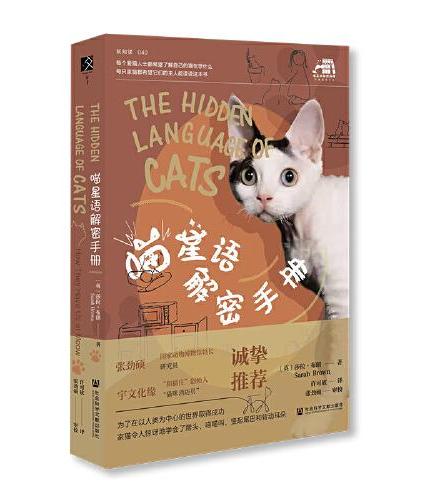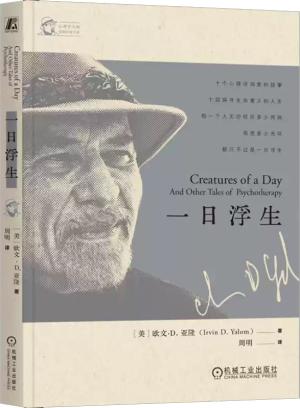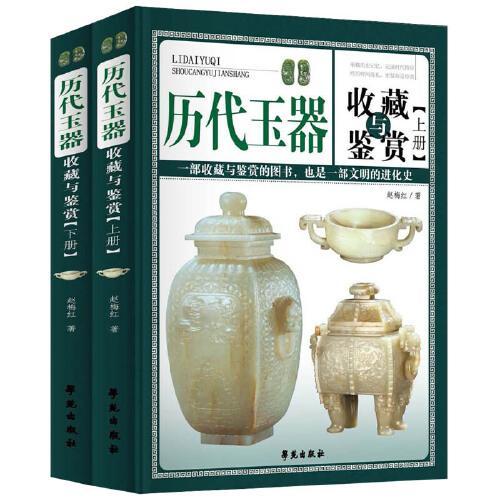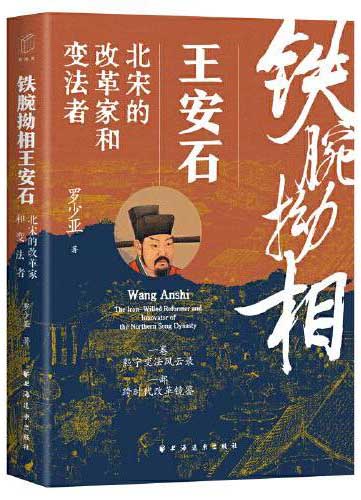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世界上的城堡:一部千年古堡兴衰史(从军事建筑到中世纪城堡,59座经典古堡,高清全彩图文,精装收藏品质)
》 售價:NT$
1214.0
《
缪斯的诞生 现代西方艺术观念生成简史
》 售價:NT$
398.0
《
信念危机:投资者心理与金融脆弱性
》 售價:NT$
347.0
《
喵星语解密手册
》 售價:NT$
403.0
《
新型戏剧编剧技巧初探
》 售價:NT$
383.0
《
一日浮生
》 售價:NT$
367.0
《
历代玉器收藏与鉴赏
》 售價:NT$
1836.0
《
铁腕拗相王安石:北宋的改革家和变法者
》 售價:NT$
500.0
內容簡介:
本书收录了著名女作家虹影多年来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精品,如《环形玫瑰》《地铁站台》《逃出爱的罗网》《一镑钱的考验》《那年的田野》《红蜻蜓》《带鞍之鹿》《白色的蓝鸟》《大师,听小女子说》《逃出纽约》等。这些小说,题材涉及爱情、信仰、宗教、异域生活等,其中故事多以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性大都市的生活为背景,塑造的主人公却多为东方人,反映的则多是东西方文化深层次的碰撞与融合,具有强烈的跨地域性风格。
關於作者:
虹影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美食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代表作有长篇《好儿女花》《饥饿的女儿》《K――英国情人》《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等,诗集《沉静的老虎》、散文集《小小姑娘》等。现居北京。六部长篇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出版。她的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曾获纽约《特尔菲卡》杂志“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曾获台湾19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
目錄
环形玫瑰
內容試閱
虹影答赵黎明问问:我觉得你的小说也好,人生也好,具有一种“天然”的边缘特质?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答:从未想过此问题。要认真想,该是从母亲那儿继续的血,她是这样一个人,认定的事,就把一切顾虑抛开做了,即使碰得头破血流。问:“边缘”是不是你走向“中心”的道路?你为什么那么执著地写边缘人物?边缘人性?答:不会从边缘走向中心,因为到了那儿,就无回头路可走了。因为我能呼吸到那儿的气息,听懂那儿的人的声音。他们很微小,很无辜,凭着直觉,不遵循世俗和传统地生活。边缘人性,都有点扭曲,不太常人化,多易受伤,敏感,性格都有些过分直拗。问:还是从开头说起吧,童年记忆与创作的关系。发现你的小说有一个母本:那就是《饥饿的女儿》,后来很多小说的主题可以说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童年记忆”在你心中、在你一生中真的那么重要吗?它对一个作家真的那么重要吗?能否走出这个“阴影”?答:我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那过程,也是我写作的源泉。童年记忆对我而言,是解开我所有作品的钥匙。我从小就看到人自杀,我们住的院子里就有不少人自杀。我看过各种各样的尸体,甚至亲眼目睹了五官流血的死。记得有一回,院子里有个姨太太自杀了。她死后还常常穿了一身白,轻飘飘地爬上我家的楼梯,到了阁楼屋顶就不见了。每回看见她,我都不害怕。我到如今还时常回忆这些往事。至于这些年来,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是怎么走出死城的,我到现在还感到奇怪。每次开始一个新的小说,我都无法控制自己回到童年,那些阴影那些可怕的记忆,并未因时间的消逝而过去,也许一年比一年淡了,可是一旦有相关的事发生,那些记忆便扑面而来。问:你好像说过你的文学总是与长江有关,详细谈谈,长江对于你的创作给予了怎么样的影响?她对于你在人生也好、文学品格也好,具有怎样特别的意义?答:我生长在长江边上,我的父亲是长江上的一个水手,我的母亲就在长江边干苦力。我的《好儿女花》,谈到母亲,也说到这条江在我命运中的重要,母亲模型对我的重要。没有她,也就没有我,包括我的语言,也是承继了她的风格,朴素简洁,别致,我还少一点她的幽默。几乎我的每一部小说都发生在河流上面。无论后来我到哪里,全国跑全球跑,我依然是长江的女儿,我始终感觉自己站在河流边上,永远是那个在江边奔跑的五岁的小女孩,希望有一个人来救我,把命运彻底地改变,我发现来救我的人,只能是我自己。问: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你的小说关注了长江上下游两个滨江城市,重庆与上海,再说说这两个城市对于你写作的特别意义?答:我生长在长江边,是长江的女儿,我睁开眼,看见的地方,也是记忆开始的地方。我大多数小说都是关于这条江的,《饥饿的女儿》和《孔雀的叫喊》是写长江上游的重庆包括三峡地区,《K-英国情人》是写长江中游的武汉,《上海三部曲》是写长江下游的上海。长江上游,有非常多的巫术,小时老百姓看病一般不太爱到正规的医院去,都是请巫婆来唱念,或者是玩魔术,或者是人死了做道场,我从小的环境就是带有巫术色彩的。看到很多流浪艺人演出,像春节,家里面人也会做些魔术。我觉得魔术是一个非常让我着迷的事。长江就是一条魔江,你会发现突然它不高兴,会把一条条船吞下去全部埋葬。它如果要让你活,你怎么想死都死不了。像我的三哥他在长江里游来游去,不管多么涨大水,别人一跳下去可能就没人影了,可河水就是爱他,不会把他吞掉。因为我们在南岸,附近都是一些山,比如三块石,那里埋了死掉的人,你走进山里,会发现很多奇怪的现象,比如树跟你说话,花在你眼前一瞬间就开了,这是你心情很好。比如你心情不好,它们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叫声。这些都跟我曾经的生活环境有关。我写重庆和上海,是因为这两座城市变幻多端,充满魔幻,像一个巨大的舞台,各种人上台表演,我只记录那最打动我的演员和演技。问:觉得你写上海总是把你的父亲母亲扯上,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答:母亲有第一个丈夫是袍哥头子。我写上海王里筱月桂,想到母亲,她是乡下姑娘,到了一个大城市,她把所有的希望寄寓到这大城市。她的命运起伏多变,一波三折。我父亲呢,故事就长了,父亲是抗战时被抓壮丁来到重庆的,重庆人叫他“下江人”。我父亲一辈子没学会说哪怕勉强过得去的重庆话,幸亏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不得不开口时才开口。开口说的是天台宁波口音,很像上海话,与重庆话就隔了千里万里。只有我能听懂父亲的话,所以做了义务翻译,由此拣了几句半通不通的上海话。父亲生前有个愿望,希望骨灰回家乡。母亲和哥姐都不肯,怕父亲的魂回了老家就回不到重庆。所以那年我从伦敦回来,兄弟姐妹一起选择了面临长江的山坡上,让他的坟朝向江水,以便他的灵魂可顺着江水去家乡探望,再顺江水回来。但是父亲的愿,我必须还。作为小说家,我却有一个多年修炼得来的移魂术:我能让我的主人公替我还父亲的愿:在上海长大——冒险上海,征服上海,败绩上海。冥冥之中,我觉得父亲会喜欢这个故事,让我代他生活在上海。问:你的小说总是有一种“纪实”的意味,比如说前期的《饥饿的女儿》,后期的上海系列小说,但其实你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在选材上,你为什么执著于此呢?你有无其他“虚构”小说的打算?或是否准备创作“转型”?答:我想借用评论者朱大可的文章来回答你这个问题:《K-英国情人》不是流氓主义小说,它只是一种有关性爱和情欲的诗意回忆,这场司法噩梦,对虹影而言是一种严重的打击。作为对《K》事件的一种应激性反应,才华横溢的虹影在2003年开始写作《上海王》,其风格发生了戏剧性的锐变。该小说是《K-英国情人》的一次反题性书写,它旨在重塑江湖女艺人“筱月桂”的坚硬形象,她出身妓院的底层丫鬟,最终却由于性感的姿色、优美的才艺和狠辣的手腕,成为掌控庞大的上海洪门帮会的“教母”。整部小说隐含着一种文学史上罕见的“母权主义”的古老信念,那就是以女人的性别身份去超越寻常意义的情色操作,征服流氓横行的险恶江湖,从而实现对男权世界的最高统治。这部小说是虹影小说走向流氓主义美学的标记。她的新偶像“筱月桂”最终成了她自身的生命“镜像”。她在“自序”中所流露的无畏表情,正是她和那“镜像”合二为一的微妙征兆。问:你的小说与中外作家的关系问题。你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有哪些?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有哪些?他们分别给予你怎么样的影响?答:从小到大谁的作品好我就接受谁,我不看这人是不是大作家,甚至某一个字、某一句话,在街上听到老百姓说的一个很生动的词,我都会学习。我从小就喜欢看翻译小说,从六七岁起就开始读雨果等人的小说。我的记性特好,而且五官的感受力也强,所以我通常能把故事的剧情牢牢记在心里。另一方面我也特别用功,我一切都是自学的。例如,我小时候对高尔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及其人其事很着迷,就曾经把高尔基的精彩句子一一抄在笔记本上,甚至把整部《巴尔扎克传》全抄了下来。后来我广泛阅读西方小说,尤其欣赏英国19世纪女作家布朗特的小说《咆哮山庄》(即《呼啸山庄》),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很像书中的男主角,有些复杂,有些疯狂,有些难以形容。我想,在写小说的技巧方面,我受《咆哮山庄》的启发最深。至于中国古典小说,我最喜欢《老残游记》,在某程度上,也受了该书的影响。问:可能由于早年诗歌创作的潜在影响,我发现你的小说中具有比较浓厚的诗的味道,比如说跳跃性很强,“哲理性”很强,等等,说说你如何把小说与所谓“诗意”结合起来的?答:我现在也写诗,只是在国内没有出版而已,不过在台湾去年出版新诗集《沉静的老虎》。诗一直是我的生命,不可缺少。想起来,有诗性的语言,热衷想象,绝对与我的童年有关系。我家的堂屋,那些在夜里神出鬼没的蝙蝠,据父亲说,是医治不治之症的偏方。尤其是用电筒搭着木梯捉蝙蝠,那些月光与乌云比赛漫过天井,我父亲眼盲,他却站在黑暗中,而瓦片上有奇怪的脚步声。再看那堂屋的墙,黑暗中全是天书般的文字,写着一个个人的过去和未来,我在这种企图读懂的过程中明白了文字的力量。问:你追求的小说的最高境界是什么?看得出来,在文体上你有一种纪实与虚构的自觉努力?你今后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答:在这儿我想说一个故事,多年前,我曾读过一首波斯长诗《鸟儿的故事》,里面有一群鸟儿历经千难万苦想寻找鸟王西姆格,一路上很多的鸟放弃了,有的开了小差,有的出了意外,有的吃不了苦,停止不前,大多数鸟都死去了,终于有三十只鸟经历艰险和苦难达到西姆格国王所在的一座山上,见到了鸟王。鸟儿最后发现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想寻找的鸟王,而且西姆格就是他们中的一只,或者就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或全体。问:文学与性的问题:小说《K-英国情人》中,对于中国道家“瑰宝”房中术,你有着出神入化的描写?你对此好像有蛮深的研究。你对于性的描写重要性、它与小说审美的关系,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说明吗?答:欲望确实是我作品中的主题。但我所写的欲望是以女性为主体的。首先,我以为性的欲望一直是可以粉碎世界的。如果强烈的欲望最终不求解脱,一定会产生灾难。在我的那本《K》的小说中,“性”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我以为“情人”的身份最能表达女性的本性。女人一旦为爱而受苦,而牺牲,内心的世界也就变得特别丰富。在小说里,我尽量把女性欲望写成抒情的、道家的,但其重点仍是如何从欲望解脱出来的问题。问:女权主义问题。你说过你没有刻意用女人眼光口气去写小说。但是你的小说还是有一种女性主义小说的气味。比如女性孤独,比如为“伟女人”上海王立传等,这些小说多少也可以看着你的“自叙传”,也就是说,你还是有一种“小女人”的气质,对于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待?答:我不同意你的话。我也不认为应该把我归为小女人或大女人类。我是女儿身男儿心。这男儿心也并非看不起女性,而是说性别在我身上不能说明什么,一句话,我的写作该是超性别写作。我的成长过程,没有受到一个女孩子应得的呵护,我必须比男孩子更加坚强,面对许许多多人生难题。这样好。这样我一生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女人。我是说,女人应当有权享受软弱,享受手足无措,享受被人原谅“见识短”。没有这事,我从来不期望这种奢侈。如果你把我这种人生态度,称作女权主义,那就不太妙:因为没有多少女知识分子有过那样的成长经历。而现在的女权主义,过于知识分子气。我可以说是一种前理论的女权主义者,命运预设的女权主义者,行动的女权主义者。我正在杀青的一部新长篇,就是写一个女人如何征服了男人的天下,一百年前的上海。问:关于你自己的作品,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凡小说出来后,你总是要为读者做一番“主题思想”的解释,这和许多作家很不一样。你这样做我觉得是不是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怕读者读不懂你的大作?第二,你有一种不被理解不被重视的“焦虑”?答:总被误读,才会想到写一点心得。也只有《上海魔术师》做了这工作,并非每本书如此吧。问:雅俗问题。你的小说在做一种自觉的努力,在雅俗之间寻找一种中间道路。你如何看待所谓雅与所谓俗的?你如何调和二者关系,达到一种最佳平衡点?答:台湾作家朱西宁先生生前说到我的小说,认为是雅俗共赏。我认为他在鼓励我。我还未真正做到这点。如何雅,如何俗,这分界线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不小心可能就滑到俗里了,稍走偏一点,就掉进了前卫中。就两者,没办法时,情愿是前卫到踩地雷死了,也不肯俗到自己看不起。问:在写扭曲人性方面,我发现你和张爱玲有得一拼,你如何看待张爱玲及其小说?答: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作家有她那么下得狠心写小说。我曾说她的写作是无心肠写作。好作家就该如此。问:回到“专业化”小说的问题:就小说的起源来看,小说必须满足社会上有闲市民的阅读兴趣,因此小说首先必须好看,要“好看”就必须迎合,而迎合则不可避免地会有损“启蒙”,你如何在好看与启蒙之间寻找平衡的?答:读者有权力读到一个故事好又有艺术性的小说。大俗大雅是一个境界。我一直在为此目的试验。问:你对你在当代作家中的“位次”怎么看?你对当今评论界对于你的“待遇”怎么看?答:中国评论界问题大,并非对我一个人如此。我以前也参加过一些作家和作品研讨会,基本上是赞歌式批评、小圈子批评,还有就是一棍子打死的批评、不读作品的评论,可以安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的套话。一句话,“伪批评”或“缺席批评”。在给文学评奖时就更出格,始终是暗箱作业。都说海内外华人文学是一家,轮到文学奖时,却说,这人不是咱们的作家,不在评选之列。难道至今华夷有别?这样坐地画圈的奖,能超越诺贝尔奖?问:你的作品在海外获得很多读者,也获得不少国外大奖。对于“外面的世界”我所知有限。就你所知,海外、台湾对于你作品的重视之主要原因在哪些方面?答:国外的文学奖在评选标准上,对艺术性和探索性很看重。以英国布克文学奖为例,关于其评选标准,我记得最近报纸上有篇文章用半讽刺半认真的口吻说,一本书有可能得奖必须具备三点:第一,如果书出版之后媒体发表了很怪的书评,记者读不懂;第二,如果读者发现书里面有很怪的词语,读不懂,需要去查词典;第三,如果书里面有大段的与故事无关的描写,让读者读得云雾里,读不懂。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样的标准难道不是在鼓励作家在艺术上作出大胆的探索吗?他们对我的作品重视,我想作品本身有其魅力,在艺术上、结构上有它的特质,敢打破一切陈旧。更何况没有人为的那些背后操作的原因。问:你的读书与创作关系如何处理?如何培养后劲?答:我是读一批书,走一些新地方,选定一个题目,做研究,再沉下心来写作。写不下去,就回到长江南岸边上,走一走,看江水流逝,灵感就来了。问:你今后创作的发展方向?答:正在写一部儿童成长的长篇小说,还会写一些儿童故事给我的女儿。也许会画画吧,但会一直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