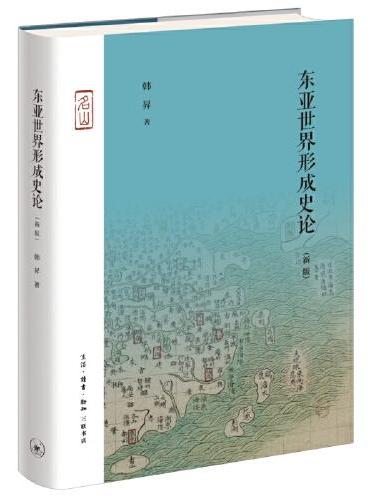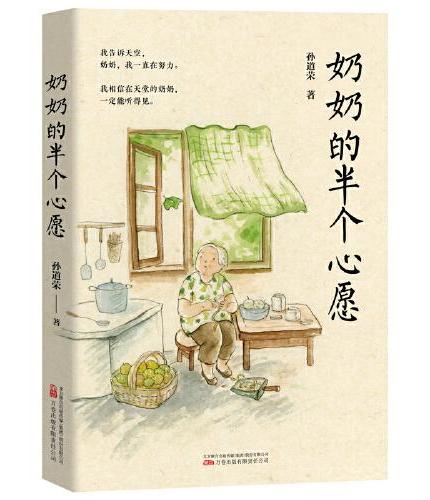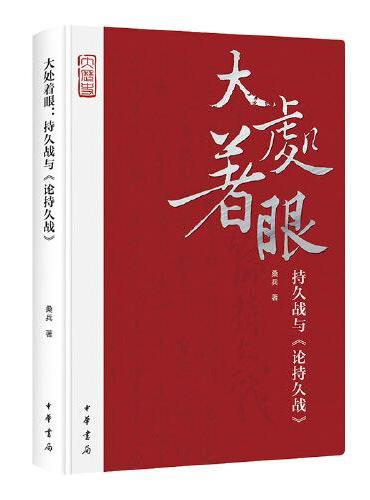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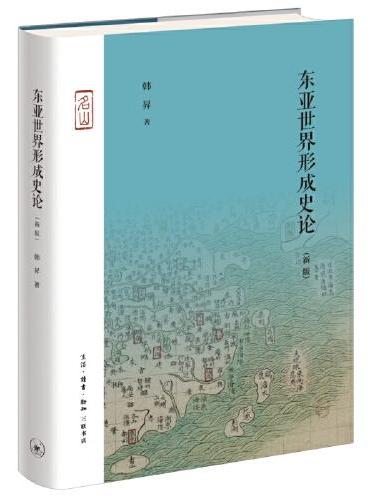
《
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新版)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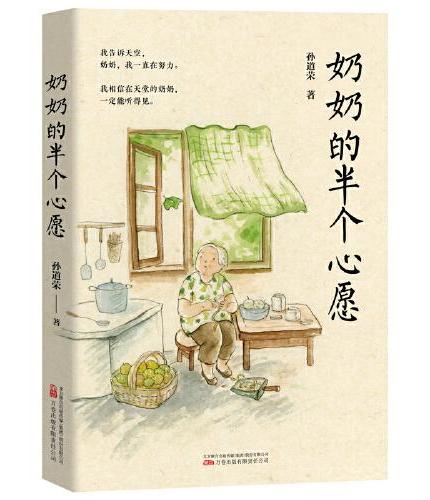
《
奶奶的半个心愿 “课本里的作家” 中考热点作家孙道荣2024年全新散文集
》
售價:NT$
190.0

《
天生坏种:罪犯与犯罪心理分析
》
售價:NT$
445.0

《
新能源材料
》
售價:NT$
290.0

《
传统文化有意思:古代发明了不起
》
售價:NT$
199.0

《
无法从容的人生:路遥传
》
售價:NT$
340.0

《
亚述: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的兴衰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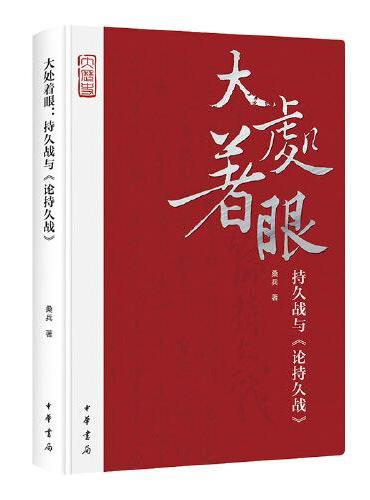
《
大处着眼:持久战与《论持久战》
》
售價:NT$
390.0
|
| 編輯推薦: |
《大河》与村上春树、奥尔罕帕慕克共同入围“小诺贝尔奖文学奖”——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入围作品。
《大河》一举攻占12个国家和地区小说畅销榜的经典之作。
《大河》深入爱与宽恕等主题,以独特的视角关注了一个特殊人群——到加拿大避难的美国反越战者。
广阔山林,越橘飘香,《大河》以诗一般的语言展现了加拿大边陲小镇的独特风貌,以及小镇居民的道德观念与社会风气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巨变的过程。
|
| 內容簡介: |
《大河》讲述有时, 那些颠覆我们生活的事件并非一开始就如大难降临,
相反,它们让人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美加边境的一处农场,狭长的山谷和宁静的小镇,曾经是加拿大15岁女孩娜塔莉的完美生活背景。那时,她对家人会永远生活在一起的信念坚定不移,但是一场战乱,一个美国男子的到来,一切都发生了难以遏制的改变……
一个悲凉不安的家族秘密,爱恨纠葛,故事如此残酷而又充满柔情,作者诉说了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
| 關於作者: |
多娜?米尔纳(Donna Milner)
加拿大作家。《大河》是她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已经在12个国家和地区热销,并被翻译成6种语言,并且入围世界上奖金最高的单一文学奖——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
米尔纳从事房地产工作25年,直到退休才开始追求埋藏心中多年的写作梦想。她的很多富有新意的非小说作品刊登在地方期刊、《读者文摘》等刊物上。
她有四个孩子,目前与丈夫生活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州。
|
| 內容試閱:
|
仿佛热浪中蒸腾而起的一个幻象,他沿着我家门外那条蜿蜒的土路, 徒步而来。我在门廊背阴的地方注视着。
一九六六年七月那个炎热的夏日,我十四岁,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十五岁了。身后绞衣机里的水就快排完了,我倚在门廊边上,在太阳下眯缝着双眼。外面院子里,刚洗好的衣物纹丝不动地耷拉在横跨整个院子的三条晒衣绳上。床单在强烈的太阳光下白得刺眼,倒给我家一溜儿整齐晾挂在那儿的各色衣物当了背景。妈妈嘴里满是衣夹,背对门口站在木制的防水台上。她俯身从柳条洗衣篮里拉出一件斜纹粗布衬衫,哗的一声,用力将湿漉漉的衣服抖开,然后夹在晒衣绳上。
那天,妈妈看起来与往常不太一样。在洗衣日里,她通常是用一块方巾拢住头发,然后在额头处打个结。那天下午,她却用发卡和梳子绾住秀发,顽皮的金色发卷和细碎的发丝散落在脸庞和颈项上。当然还不止这些。她那天看起来心神不宁,甚至脸颊绯红。我肯定她在脸上抹了些雅芳胭脂。早些时候,她把哥哥们的牛仔裤丢进绞衣机里洗时,发现我在偷偷打量她。
“唉,这天真够热的。”她说道,接着向后拢了拢头发,把它们夹在耳后。
妈妈正忙着把最后一批洗好的衣物晾起来,无暇顾及外面路上的情况,所以是我先看到了他。他从牧场边的弯道上绕出来,跨过护牛栏,穿过影影绰绰的白杨林荫,然后又走到白花花的日光下。他一边肩上挎着粗呢大包,另一边挂着个黑色的东西。等他走近了,我才看清那是个吉他盒。随着他不紧不慢的步伐,盒子在他身后晃荡着。
“嬉皮士”在我的词汇表里可是个新词,一个外国词。它指的是那群奇装异服、高举“做爱不作战”和平标语游行的美国人;一群把花朵插在防暴警察枪管里的反越战示威者;它还意味着一群逃兵役的家伙。我们农场南边是绵延一英里半的边境线。有传言说,他们中有些人从那越境跑到加拿大来。谣传而已。于我来说,除了这些谣传,他们不过是山谷地区信号时断时续的电视里出现的模糊图像。现实生活中,我还从未见过一个真的嬉皮士,直到此时此刻。
“怎么了?”妈妈的声音将我从恍惚中惊醒。她从洗衣台那边走进来,把空的洗衣篮递给我。我还没吭声,她就转身看向大路。这时,我们的牧犬巴迪昂着头,嗖地一下从平时午后打盹的门廊台阶下冲了出去,宛如一团模糊不清黑白相间的影子。这只边境牧犬越过尖桩篱笆,飞奔至牲口棚那边,发出一声已然迟了的警告。
“巴迪!”妈妈冲着它喊了一声。而那个长发的陌生人已经屈膝跪在路边,轻声地安抚着对他咆哮的牧犬。不一会儿,他站起身,跟巴迪一起继续往院子这边走来。他在围栏外对我们微笑,任由我们的狗舔他的手掌。妈妈也对他笑了笑,抚平有些潮湿的围裙,下台阶朝他走去。我迟疑了一下就放下洗衣篮,也跟了上去。我在门口见到了他。
妈妈在等他。
她没料到的是,她等来的是如冷风般的一段辛酸。
2
我本该知道的。
这些年来大家讳莫如深。可每个人的眼里都存有疑问。我怎么会一直没有察觉呢?三十四年过去了,我仍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
我时常沉浸于对过往的回忆,回到童年“以前”,物是人非以前的那段日子。那时,“家人不可能永远在一起”这个念头在我看来是难以想象的。那时,我全部的世界就是我们家的农场。它坐落在英属哥伦比亚省卡什柯德山区深处一条狭长的山谷里,那是一片绵延四百多英亩的土地。其余的一切——农场北边三英里外的埃特伍镇,包括镇里的两千五百位居民——不过是我们完美生活的背景。或者说这一切,仿佛就是我生活的全部,直到快十五岁时。
那是我所有“后来”记忆的出发点。
有时,我能将记忆冻结——那些关于“后来”的记忆。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我可以假装一切从未发生。我有时甚至相信事实真的如此。
然而,一九六六年那个夏日是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那天是我人生的分水岭,从拥有一个完整美好的家,到生活中的一切被彻底颠覆。
那些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事件并非一开始就如大难降临,惊天动地。有一阵子,它们甚至显得那么美好。
后来,妈妈总是责骂那些慢慢蚕食了我们这个小农场的一切变化。
高速路兴建起来,其中一条连通了我们镇和加拿大一号公路。在东库坦尼亚斯,河谷地区被洪水吞没,人们在那建起水坝发电,将电力输送到正在蓬勃发展的省城以及我爸爸说的“南边那个闹电荒的邻居”。
“现在到处都是工作机会。”晚饭时,妈妈忧心忡忡地说。那天,从我记事起就在农场工作的雇工杰克没打招呼就离开了。“谁会有兴趣到一个犄角旮旯里的奶牛场工作呢?”“我们会有办法的。”爸爸嚼着嘴里的饭说,“摩根和卡尔可以先帮着搭把手,娜塔莉可以在乳品间帮忙,我们会挺过去的。”他俯身过去拍拍她的手。
“不行,”妈妈抽回手,站起来去拿咖啡壶,“你的牲口越养越多,我的儿子相继辍学。起码得让一个儿子读完高中吧。”她没再往下说“然后去上大学”。她没法再说出这个梦想了。卡尔是她最后的希望。
妈妈在《埃特伍周报》上刊登了一条两行字的招聘广告,然后就雇用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应聘的人。“他的声音很好听。”七月的那个早晨,宣布了雇人的消息后,她说了这么一句。早餐后,她开始收拾盘子,仿佛不经意般地又冒出一句:“他是个美国人。”我瞥了父亲一眼。他浓眉上挑,正消化着她这番话。我知道他们对逃兵役到加拿大避难的美国年轻人看法相左。我寻思着会不会有机会看到他们第一次真正吵起来。爸爸很少跟妈妈争吵,可那会儿他不满的是妈妈事先没跟他商量就自作主张,而且还是在这件他一贯态度鲜明的事情上。他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抓过挂在门上的宽边礼帽——他送奶时才戴的帽子,刷地一下扣在脑袋上。我知道他很不高兴。
“呃,”爸爸和卡尔关门出去后,妈妈说,“我想,这事儿挺顺利的。
嗯,娜塔莉?”她手里攥着橡胶手套,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我不会再把一个儿子白白搭在农场上。”从提得动奶桶开始,我那三个哥哥的生活就完全服从于挤奶时间表了。每天清晨,他们天不亮就起床,站在楼上卧室总是冰冷的地板上穿好工作服。我甚至觉得博伊尔是穿着衣服睡觉的。
博伊尔,家里的老大,自己在阁楼那有个壁橱般大小的房间。十二岁时他就不愿再与摩根、卡尔共用一个卧室。他在楼上两个卧室之间的横梁处给自己搭建了个窝。客厅天花板那有个口子,他就钉了个简陋的木梯,从那儿爬上去。十四岁时,他在那儿做了个真正的楼梯。
冬天,那小小的阁楼间有时冷到你可以看到自己呼出的白烟。夏天,即使打开窗户也无法驱散房间里的闷热。可是博伊尔从不抱怨。这个房间是他的圣殿,房间里的每一寸空间都堆满了书,凡有幸受他之邀去那儿玩,或者可以去阅读那些书籍的人,无不嫉妒他在这所祖父于世纪之初就亲手修建好的农舍里缔造出来的一方天地。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所以有一间自己的卧室。这个房间原来是博伊尔的,我出生后就把他挤了出去。哪怕博伊尔因此恨过我,他也从来没表现出来。我倒是很愿意跟他分享一个卧室的。可我那时太小,根本不明白他需要的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过了很久,我还喋喋不休地追问为什么他得跟男孩们睡一个房间,又为什么要搬到阁楼上去。
每天早晨,博伊尔总是第一个下楼到厨房的人。他捅开炉灰,添上柴火,给妈妈把那个笨重的铁炉子重新点上后,才出门去牲口棚。直到一九五九年我们家用上了电炉,他起床下楼才直接到前院,在那儿换上齐膝高的胶鞋去干活,无论冬夏。每天凌晨四点五十分整,博伊尔都会砰地摔上厨房门,让屋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干活去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和住在挤奶棚楼上的雇工杰克一起,把牧场里的奶牛赶进挤奶棚里。
摩根和卡尔从不着急起床干活。爸爸常常一大早就大呼小叫,用冰水吓唬他的两个小儿子起床。 “穆特和杰夫。”
他这样叫他俩。摩根比卡尔大两岁,可是从小卡尔的个子就高一截。两人从来都是孟不离焦、形影相随的。一看到摩根揉着睡眼沿楼梯蹒跚而下,我们就知道卡尔肯定也在后面跟着。摩根的厚羊毛袜前半截总在脚丫子前呼扇着,像脚丫上多长了一截东西。妈妈一看到就教训他,要他把袜子拉起来。我们都觉得奇怪,他这样居然不摔跤,尤其是楼道那儿黑糊糊的,可这截耷拉着的袜子就跟天生长在他脚丫上一样。
哥哥们的这番晨练出操就跟妈妈做祈祷一样规律。
妈妈什么时候都做祷告。小时候,她要求我们严格遵守这个习惯。
每餐动刀叉前,我们须得低头祈祷。每天晚上挤完牛奶,她都手拿念珠,领着我们在客厅里,对着壁炉架上的玛利亚和基督画像祷告:“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尔偕焉。”她诵这《玫瑰经》时,我和哥哥们跪在满是划痕、有着粉灰色花纹图案的油布地毯上,努力克制自己的烦躁不安。妈妈笃信这样一句话“一起祈祷的家人能永远相伴”。
年幼时,我会抬头偷看妈妈低着头、手里滑动念珠、双唇低诵经文的样子,心里想着如果祈祷能让人如此美丽,我愿意老老实实去做祈祷。
妈妈原是个基督新教徒,和爸爸结婚后皈依了天主教,从此满怀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第一次和你父亲步入圣安东尼教堂时,我就有种归属感,”她曾经这样告诉我。“这种感觉,”她说,“是永恒。那教堂、那些雕塑、图画和肖像仿佛早已存在于此——并且会——永存于此。从教堂彩色玻璃窗外流泻而进的阳光、那些仪式、那永远燃烧的蜡烛、那芳香,”她喃喃低语,仿佛在自说自话,“所有的一切感觉是那么自然,甚至是契合。”念珠就是她的安慰,一种真实,一种她能牢牢抓住的依靠。它们在她指间滑动,犹如呼吸般自然。“皈依,”她说,“犹如踏上归途。”她本来希望所有的孩子都皈依天主教。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孩子——也许博伊尔除外——像她那般虔诚。甚至连一出生就是天主教徒的爸爸也不如她那般虔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