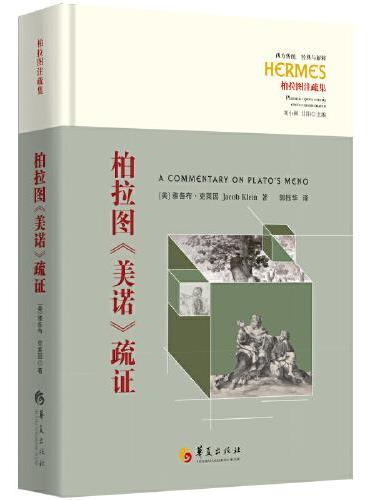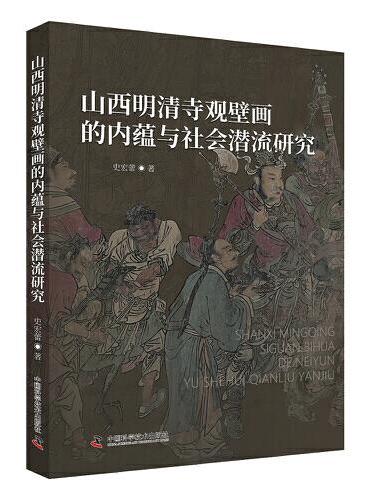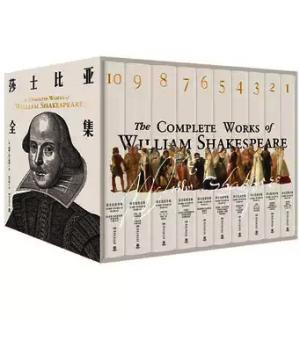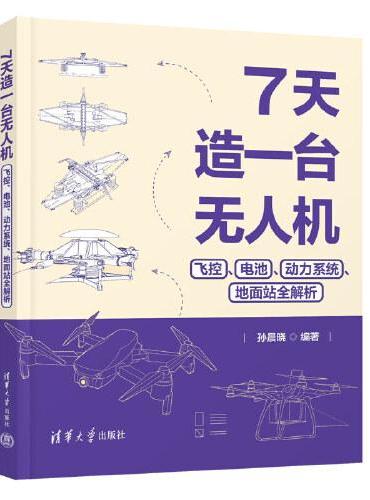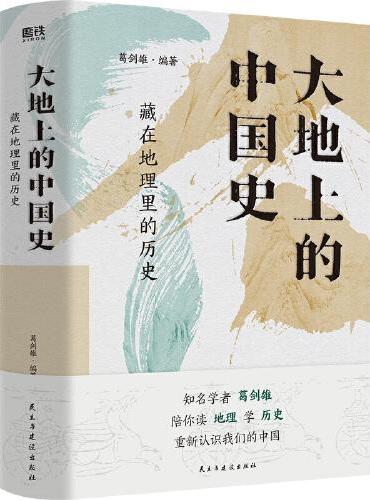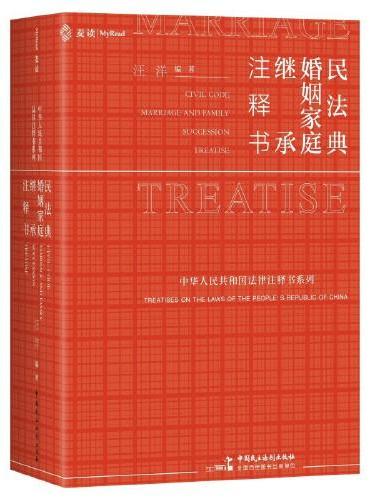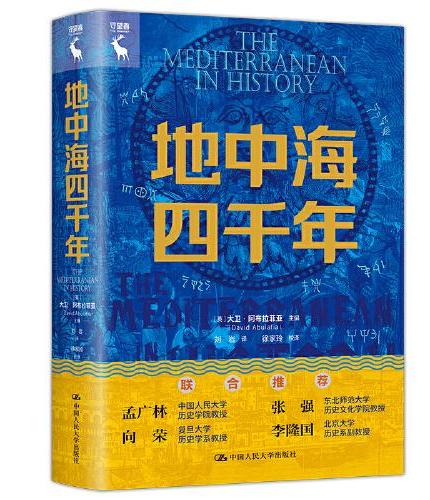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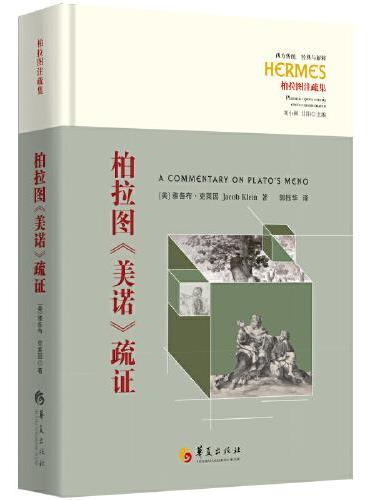
《
柏拉图《美诺》疏证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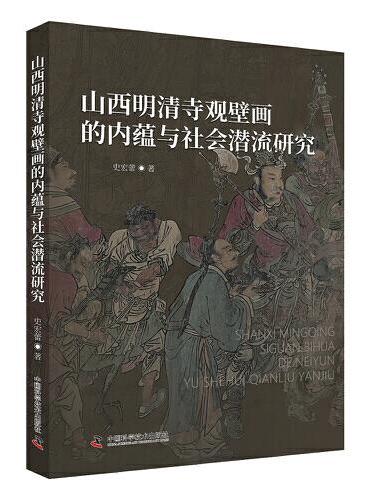
《
山西明清寺观壁画的内蕴与社会潜流研究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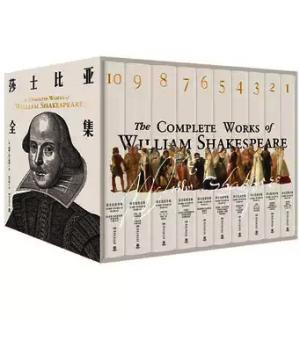
《
莎士比亚全集十卷
》
售價:NT$
27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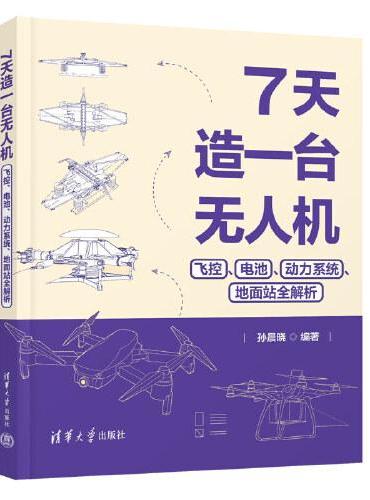
《
7天造一台无人机:飞控、电池、动力系统、地面站全解析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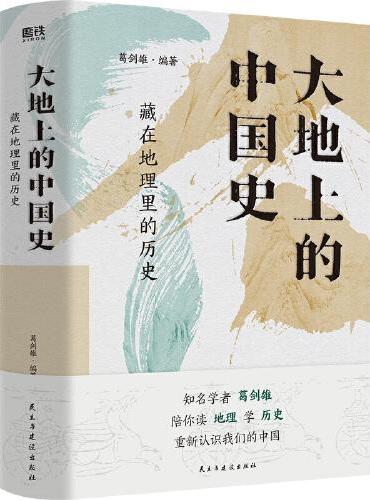
《
大地上的中国史:藏在地理里的历史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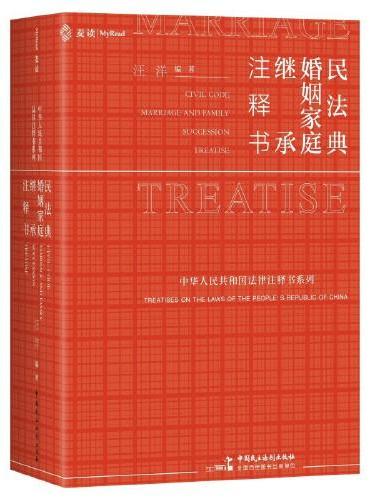
《
《民法典·婚姻家庭继承注释书》(家事法专用小红书,一书尽揽现行有效办案依据:条文释义+相关立法+行政法规+地方立法+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地方法院规范+权威案例,麦读法律54)
》
售價:NT$
6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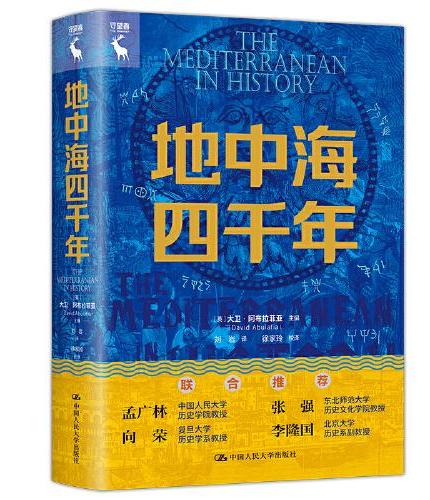
《
地中海四千年
》
售價:NT$
857.0

《
君子至交:丁聪、萧乾、茅盾等与荒芜通信札记
》
售價:NT$
316.0
|
| 編輯推薦: |
被J. K. 罗琳誉为“最有魅力的作品”
《我的秘密城堡》是我读过的最有魅力的作品。——J. K. 罗琳
入选BBC“100部英国人最喜欢的书”
入选《卫报》“一生必读的1000本书”
全球销量超过100万册
年轻人的忧伤令人沉迷
像上午刚写成的一样新鲜,像简·奥斯丁一样经典。——唐纳德?韦斯特莱克美国著名作家
|
| 內容簡介: |
这一刻,我在写作,就坐在厨房的水池里。水滴顺着房檐落进门边的集雨桶。
我和姐姐罗斯,两个女孩子,住在这么一幢始建于查尔斯二世、孤单奇异的宅子里,处境相当浪漫。但罗斯却不这么认为:深锁在衰败的废屋里,四周泥沼重围,哪里有什么浪漫可言?的确,我们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睡衣穿。
罗斯决定像浮士德一样,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条件是趁青春仍在时好好享受它。
就在那天夜里,两个年轻的美国人闯入古堡,惊起一片涟漪……
|
| 關於作者: |
多迪·史密斯(Dodie
Smith,1896—1990),英国家喻户晓的女作家、好莱坞编剧,电影作品有《不速之客》《风流种子》《我的秘密城堡》《101只斑点狗》等。这位女作家有童话般的一生。本书销量至今已逾百万册。
|
| 內容試閱:
|
这一刻,我在写作,就坐在厨房的水池里。那情形是:我双脚在池中,身子则在滴水板上。事先我垫好了宠物用的毯子和茶壶套。也不能说这样就实在很舒服了,何况那里还有一股碳酸皂的呛人气味。不过,整个厨房只有这一处晒得到些许日光。我发现,坐在一处从未坐过的地方可以启迪文思——我坐在鸡舍里写过本人的最佳诗作,即便如此,那诗也实在算不得很好。于是我认定,我是写不好诗歌的,不该为它们再费半点笔墨。
水滴顺着房檐落进门边的集雨桶。水池上方,窗外的风景格外阴郁。潮湿的花园外,庭园的周围,是残破的墙挨着城壕的岸边。城壕外,犁过的农田犹如泥沼,一路延伸到铅灰色的天边。我告诉自己,我们这里一向承受的所有雨水都对自然界有益无害,而且不知什么时候,春天就会奔放地涌向我们。我刻意在树上找寻叶子,臆想着庭园里充满阳光。很不幸,心眼看到的绿叶金光越多,肉眼看到的黄昏色调就越显枯瑟。
我把目光从窗外移开,望向厨房的炉火,这感觉舒服多了。就在炉火的左边,我的姐姐罗斯正在熨衣服
—尽管她显然眼神不太灵,而且如果烫坏了她唯一的睡袍,会很可惜的。(我有两件,不过有一件没有后背。)罗斯在炉火边尤为动人,炉火的光为她镀上金粉色的光晕,令她越发显得轻盈柔婉。她已近二十一岁,对生活怀着尤怨之心。我十七岁,容貌比年纪轻,心绪比年纪老。我不是个美女,面容倒还修洁齐整。
我曾经和罗斯谈论过,我们的处境是相当浪漫的:两个女孩子,住在这么一幢孤单奇异的宅子里。她的回答是,深锁在衰败的废屋,四周泥沼重围,哪有什么浪漫而言?我必须承认,我们的家,算不上一处理想的居所。可是我喜欢它。这房子始建于查尔斯二世,又毁于克伦威尔当政时期。我们的整面东墙都是城堡的一部分,城堡中还竖着两座圆塔。城堡的箭楼依然完好,有一带未受缺损的城垣把它与主建筑联结在一起。而贝尔摩德塔楼则是更古老的一部分城堡的残余,它依然矗立在旁边的基筑上。不过此刻,我是没有心情周详地描绘我的家园了,除非将来哪一天,比眼下有更多的时间。
我写这篇札记,一部分原因是想练习新近所学的速记法,再者,我也想自己学着写小说
——我想设计好所有的人物,用对话的形式把他们表现出来。我依着自己固有的风格:不假思索,信笔疾书,按理应该是不错的,然而到目前为止,我的文字仍然僵板生涩。唯一的一次,父亲赏脸,读了我的一篇习作。他说我的文字搔首弄姿,竭力搞笑,却又蕴藏着庄重的格调。他要求我放松精神,让字句从心灵中流淌出来。
我倒是希望能有什么办法,让字句从父亲的心灵中流淌出来。许多年前,他写了一本非同小可的书《雅各布角力》,其中融合了小说、哲学、诗歌。此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在美国
——父亲在那里举办讲座,解读他的大作,也因此赚了很多钱,似乎转眼间就要成为不折不扣的大作家了。然而从那以后,父亲却停止了写作。母亲认定这是在我五岁时发生的一桩变故造成的。
当时我们住在一幢海边的小宅子里。父亲刚刚结束了第二次在美国的讲学,回到家中与我们团聚。一天下午,我们在园中用茶点,父亲对母亲发起火来,大声地叫嚷着。那时他正在切蛋糕,顺手便向我母亲挥舞起手里的刀。父亲的架势相当凶恶,竟然惊动了一位见义勇为的邻居。他越过篱笆前来劝阻,自己却被揍了。后来父亲在法庭上辩称,用一把切蛋糕的银质餐刀杀害一名妇人,必定会漫长而难熬,恐怕要一寸一寸地拉锯,才能把人杀死;他丝毫没有杀害我母亲的动机,这一点确定无疑。整个诉讼显得相当滑稽,除了正义的邻居,其他人都十分搞笑。不过父亲的搞笑过了头,竟盖过了法官的风头,再加上他的确让邻居伤得不轻,于是被判入狱三个月。
他出狱以后,变得温良和善,无以复加,简直是男人可以做到的极致了。那是因为,他的坏脾气改掉了很多。除了这一条,他在我眼里似乎没有任何改变。然而罗斯却记得父亲已经开始落落寡合。就在那前后,他签了一份为期四十年的租约,租下了这座城堡。这个居所,对于遁世寡合之辈,的确值得艳羡。我们在这里住下。那时,他照计划应当动笔撰写新书,不过时光流去,却全然没了写作的下文。最后我们发现,他已彻底放弃了著书的念头。到如今多年过去,他一直拒绝讨论继续写作的事。他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大门旁的墙顶小屋里流连。那个地方冬天冰冷,而且没有壁炉,他只能偎着油炉取暖。据我们所知,他所做的唯一一件事便是阅读从镇上图书馆借来的侦探小说。镇上小学图书管理员兼校长玛希小姐把这些书带给父亲。她十分崇拜他,而且常说:“他的灵魂里铸进了铁。”
我个人以为,区区三个月牢狱生活不至于让一个男人的灵魂生硬如铁,最起码,对于像我父亲这样活力满满的人不至于。说到活力满满,他刚出狱的时候似乎的确如此,不过现在却消逝了——他的落落寡合几乎发展成了病态。我常常觉得他根本不喜欢和家人打照面。他以往那种天真的愉快情绪无影无踪了。有时候他强作欢笑,越发让我尴尬无措。不过通常情况下,他并不郁闷或者恼怒。我认为比起他过去的坏脾气,我应当对现状感到庆幸。唉,可怜的父亲,的确相当落魄了。不过他至少还能在园子里多少干些活儿。我知道如此描绘父亲有失公允,今后我一定要用心观察。
八年前母亲故去了,死因则完全属于自然规律。我认为她一定是个内向的人,因为我对她的记忆极为模糊,而对于其他事物,偏又有绝佳的记忆力。(狂舞餐刀的事件,我记得一清二楚——我当时还用小木铲去揍那位跌倒在地的正义邻居,父亲一直说这个情节累得他多判了一个月。)
三年前(或许是四年前吧?我知道父亲那一阵心血来潮,热衷起社交活动,那一年是一九三一年),一位继母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当真为此惊讶了。她是一名著名的艺术模特,自称其教名为陶珮兹。就算它真的是洗礼的时候取的,作为一个女人,难道非要坚持用这样的名字?她非常美丽,面色格外苍白,一头浓密的金发,发出近乎白色的光芒。她不用化妆品,连粉底也不用。在泰特美术馆有两幅以她为模特的画作:一幅是麦克摩里斯所作,名为《佩玉的陶珮兹》,画中的她戴着一件极美的翠玉项链;另一幅是阿拉迪的作品,画中的她裸体倚在旧式的马鬃套沙发上,据她说那面料刺得她非常痒。这便是所谓的“组合创作”。不过由于阿拉迪把她画得比她本人更加苍白,似乎称为“分解创作”更为贴切。其实,陶珮兹的苍白并非不健康的那种,只不过,如此肤色使得她看起来似乎属于某个奇异的族群。她的嗓音非常沉厚,其实那是她刻意装出来的,一如她在绘画和鲁特琴演奏中的装腔作势。然而她的善良,却和她的上乘厨艺一样,绝对真实,我非常非常喜欢。写完这段时,她恰好出现在厨房的台阶上,多美好的巧合。她穿着古色古香的橙色茶会礼服,一头笔直而泛白的金发飞泻到腰部。她在最高一级台阶上站定,说:“啊,姑娘们……”半句话里有三个变调,音质丝般柔滑。
此刻,她坐在钢质三脚架上,拨弄着炉火。粉红色的火光映得她更显平和,然而十分漂亮。她二十九岁,在父亲之前还有过两任丈夫(关于他们的事,她从不和我们谈论太多),却依然年轻。这一点或许得益于她寡淡的表情。
此时的厨房看起来分外美好。火光烁烁,从炉灶围栏间沉稳地漫出来,从盖子掀开的炉顶漫出来。刷了白浆的四壁染成了玫瑰色,连黑暗的房梁也变成了金黑色。最高一根横梁距离地面超过三十英尺。罗斯和陶珮兹就像火光闪耀的巨大山洞里的两个小矮人。罗斯正坐在靠垫上,预热着熨斗。她带着不满的表情盯着陶珮兹。我常常能猜透罗斯的心思,我打赌她此刻必定是在艳羡那件橙色茶会礼服,嫌弃自己寒酸的旧衣裙。可怜的罗斯几乎嫌弃自己拥有的一切,而对自己没有的东西,她多半是要艳羡的。其实,我也一样心存不满,只不过我似乎不大为此纠结。这一刻,我望着她们两个,无端地觉得开心:虽然依旧坐在冰冷的滴水板上,我却知道随时可以凑过去,同她们一道分享温暖。
哦,天哪,那光景真的有些无聊!罗斯提议陶珮兹去伦敦赚些钱回来。陶珮兹说她觉得那样不值,因为在伦敦生活的开销太大。就算她能省下几个钱,也一定用来给我们买礼物了
——她真的非常慷慨。
“用我做模特的两位画家现在都在国外,”她接着说,“而且我不喜欢为麦克摩里斯做事。 ”
“为什么不喜欢?”罗斯问道,“他比其他人付的价钱高,不是吗?”
“那是他应当的,你要想想他多么有钱。”陶珮兹说,“可是我不喜欢给他当模特,因为他只画我的头。你们的父亲说过,画我裸体的男人会专注于他们的作品,而这位麦克摩里斯手上只画我的头,心里却专注于我的身体。他说得绝对没错。我和他之间的麻烦太多,已经不得不瞒着你们的父亲了。
”
罗斯说:“我倒觉得要是能赚点大钱,摊上些小麻烦也值得了。 ”
“如果是那样,你可就真的麻烦了。”陶珮兹说。
罗斯一定会感到很气恼的,因为她自己从没遇到过这类麻烦,从来没有。
她突然夸张地扭过头说:“我绝对愿意惹点麻烦。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或许会觉得有意思:我考虑出卖自己,已经想了有一阵子了。要是有必要,我甚至觉得不妨站在街上卖笑。”
我告诉她在萨福克郡的腹地,她根本不可能站街卖笑。
“不过如果陶珮兹乐意好心借给我去伦敦的路费,再教我几招……”
陶珮兹说她从来没有当街卖笑的经历,而且深以为憾事:“人要想精进升华,就必须先泥足深陷。”这就是陶珮兹的做人理念,你必须有巨大温情,方能包容得下。
“而且不管怎么说,”她告诉罗斯,“你就算真想做个努力赚钱、努力堕落的女孩,也只能排在最后一名了。如果你决心要出卖自己,最好选定一个有钱人,体面地嫁给他。”
这个主意,罗斯当然也是想到过的,然而她总盼着这个富有的男人还能够英俊、浪漫。她始终没有遇上一个可以谈婚论嫁的男人,哪怕丑一点的、穷困潦倒的也不曾有过。我觉得她一定是因为想到此处,这才失望至极,竟然流下泪来。她一年才哭这么一次,所以实在应该上前安慰才对,然而我宁可安坐在水槽里不动。我开始意识到,身为作家就难免变得麻木无情。
所幸,陶珮兹安慰人的本事远远胜过我,因为我向来不会把别人紧紧揽在怀里。而她却母性泛滥,任由罗斯的鼻涕眼泪沾满了她的橙色丝绒礼服,好在这件衣服已遭受过许多种不同的沾污了。
此后,罗斯一定会对自己的表现大为恼怒,因为她对陶珮兹怀有一种恶意的蔑视。然而此刻,她们彼此却温情脉脉。罗斯把熨烫的活儿放在一边,渐渐止住哭泣,而陶珮兹一边为茶点铺排桌面,一边漫无边际地谈着赚钱计划,比如在镇上举办一场鲁特琴演奏会或是分期付款买一头猪。
我写累了就放下笔一道聊两句,不过没说过什么切中要害的话。
雨又要下起来了。斯蒂芬穿过庭园向我们走来。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他的母亲当年是我们的女佣,她死后,儿子便没了去处。他为我们种菜、养鸡,还要干数不清的奇怪活计——我想不出要是没了他我们怎么生活。如今他十八岁了,生得十分健壮俊美,然而外表之下,他的谈吐却生涩迟钝。他对我一向十分殷勤卖力,父亲称他是我的乡村情郎。他很接近我想象中《皆大欢喜》里的牧羊人西尔维厄斯,不过我却一点也不像那个菲比。
此时斯蒂芬已来到近前。他点燃一支蜡烛,把它插进我身边的窗前烛槽里,说:“您这样会看坏了眼睛的,卡桑德拉小姐。”接着他在我的札记簿上丢下一小块紧紧折叠的纸。我心头一紧,因为这里面很可能是一首诗,我想是他在谷仓里写的。他的笔迹严谨而漂亮,抬头写的是“斯蒂芬?考利致卡桑德拉小姐”,内容的确是一首动人的诗歌——是罗伯特?赫里克的作品。
我该如何面对斯蒂芬呢?父亲说,他那自我表现的欲望是不足道的,然而我觉得他的根本欲望是令我欢喜
——他知道我对诗歌的钟爱。我应当告诉他,我知道他不过是照抄原作,整个冬天他一直如此,大约一周一次。然而我实在狠不下心去伤害他。
或许开春以后,我可以带他散散步,顺便用一种婉转勉励的语气揭穿他。这一次,我没有说些伪善的赞美之词,而是代之以一个微笑,示意他可以去忙别的了。于是他穿过厨房,汲水灌入蓄水池里,面色十分愉悦。水井就在厨房的地面以下,从城堡建成之初它就在那里,六百年来一直承担着供水的职责,据说从来没有干涸过。当然,它必定见证过无数台水泵,而眼下的这一台买来的时候,据说维多利亚热水系统就要引进了。
我的写作一再被人打断。陶珮兹刚刚过来灌水壶,却溅湿了我的腿,而我的弟弟托马斯又从距我们最近的镇上的“王家地穴”学校放学回来了。他是个毛手毛脚的十五岁愣小子,有一头丛生的乱发,梳理都很困难,颜色也和我头上的一样,像老鼠毛。不过,我的头发可服帖得多了。
托马斯一进来,立刻让我想起了当初自己是怎么放学回家的——那是数月之前日复一日的经历。一闪念间,我仿佛又坐上了缓缓蠕动的小火车,漫漫十英里后,再从斯考特尼车站改骑自行车,再跋涉五英里!冬天的时候我简直恨透了这趟路程。不过,去学校读书也有我喜欢的事情,比如,电影院经理的女儿也在同一所学校,她隔三岔五会带我看免费电影,这一点我很怀念。对学校本身,我也相当留恋:在如此安静的小镇,有这么好的一所学校,的确令人惊讶。同托马斯一样,我当初在自己的学校里也获得了奖学金,我们的聪明伶俐,还算说得过去。
此时大雨猛烈地敲打着窗户。我身边的烛火令户外更显昏暗。厨房的另一端此时也暗了一些,因为水壶盖住了炉灶的火光。她们两个坐在地上,用架子烤着吐司。每个人的头上都镀了一道闪亮的金边,那是火光漫过各人的头发。
斯蒂芬已经汲过了水,正在给炉子添料——这是一座旧式的砖砌炉,它可以给厨房供暖,还可以提供额外的热水。有了炉火加上灶火,厨房成了整座宅子里最温暖的地方,因此我们一向最喜欢坐在这里。纵然到了夏天,我们照样在此用餐,因为餐厅的家具一年前就卖掉了。
天哪,陶珮兹煮上鸡蛋了。母鸡感念我们的祈祷竟产下蛋来,居然也没人告诉我。哦,英雄的母鸡!我原指望茶点只能吃些面包涂植物黄油,我早已吃厌了植物黄油。谢天谢地,我们的面包已经不能再廉价了。
多么奇怪:我们居然还依稀记得,“茶点”就是休息室里的小蛋糕和薄片面包涂黄油。如今它成了一顿干瘪的简餐,而我们还是得应付着吃下,因为必须熬到次日的早餐才能再次进食。这一“餐”,我们通常等托马斯放学后一起吃。
斯蒂芬在点灯了。玫瑰色的炉火光芒马上就要在厨房退去,不过,灯光也是很美的。
灯火燃起。斯蒂芬把灯端上桌子。父亲来到了台阶前,肩上裹着一条旧格子花呢旅行毯。他刚从城堡墙顶上的门房走下来。他嘟囔着:“茶点,茶点,玛希小姐有没有带书来?”她没有。然后他说他的手冻得麻木了,不是在抱怨,倒像是一种带着少许惊讶的口气。不过,我很难相信城堡里的人会因为冬天冻僵了身子而觉得惊讶——不管是身体的什么部位。他走下楼梯,甩掉头上的雨水,此时我突然觉得我好喜欢他。如果不能时常抱有这种感觉,我会害怕的。
他依旧是位仪表出众的男人,尽管他精致的五官因为多余的脂肪而少了些光彩,而肤色也较以往暗淡了。曾经,他的皮肤和罗斯的一样光润。此时,他和陶珮兹聊起来。我不无遗憾地注意到,他此刻又在伪装心情愉快了——尽管我相信这些日子以来陶珮兹会为他的强颜欢笑而存有感激之心。她崇拜他,而他似乎对她兴趣不大。
我必须从滴水板上站起来了——陶珮兹要用茶壶套了,而我们的爱犬海洛薇兹也晃了进来,看到我借用了她的毯子。她是一只牛头梗。除了尾巴上露出的奶糖般的粉色皮肤,她通体雪白。
好吧,海洛薇兹,亲爱的,拿回你的毯子吧。她盯着我,眼里充满爱意、责备、自信和幽默——她只有一双很小的、长歪的眼睛,为何能如此丰富地表情达意呢?
我坐在台阶上写完了这一则。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尽管父亲伤怀,罗斯抱憾,斯蒂芬的诗歌令我窘迫,我的家庭前景也不见得有多少希望。或许这仅仅是因为我满足于自己的创作冲动,又或许是因为想到了茶点时的鸡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