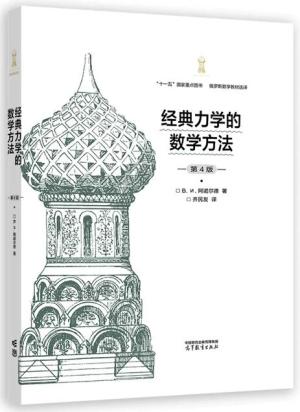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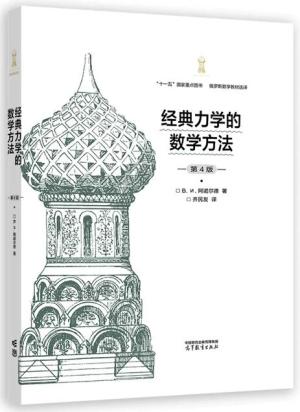
《
经典力学的数学方法(第4版)
》
售價:NT$
403.0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跟随历史的足迹 见证一个民族的觉醒与抗争
》
售價:NT$
305.0

《
功名诀:左宗棠镜像
》
售價:NT$
908.0

《
布克哈特书信选
》
售價:NT$
439.0

《
DK园艺的科学(100+个与园艺有关的真相,让你读懂你的植物,打造理想花园。)
》
售價:NT$
500.0

《
牛津呼吸护理指南(原书第2版) 国际经典护理学译著
》
售價:NT$
959.0

《
窥夜:全二册
》
售價:NT$
407.0

《
有底气(冯唐半生成事精华,写给所有人的底气心法,一个人内核越强,越有底气!)
》
售價:NT$
347.0
|
| 內容簡介: |
19世纪50年代的得克萨斯与墨西哥边境,一个十四岁的得克萨斯男孩无意中误入了一个噩梦般的世界。在这里,印第安人被肆意杀戮,而对其头皮的贩卖生意欣欣向荣。
大体说来,小说的情节是一个人的历程,盗用书中原话表达,就是没完没了的“他继续骑行”。主人公无名无姓,大字不识,全书在其不同年龄段分别称其为“孩子(thechild)”、“少年(thekid)”和“男人(theman)”。故事重心是主人公少年时的经历。他生来丧母,十四岁时离家游荡,常与人打架斗殴。后来被拉去加入美国的军事阻挠队伍,前往墨西哥,出师不久,便遭到了印第安人的致命打击。而后因为偶然,他又加入受雇于奇瓦瓦州州长的头皮猎人队伍。该队伍由罪犯、老兵和印第安人组成,头目是美墨战争老兵格兰顿,而实际的灵魂人物是霍尔顿法官。在此二人的带领下,队伍与奇瓦瓦州州长达成协议,专门不加区分地屠杀各种印第安人(包括好战的阿帕契人和热爱和平的踢格人等)和墨西哥人,以遇害者的头皮为收据换取黄金。队伍在墨西哥境内四处游荡、大肆屠杀,老幼妇孺均不放过。最后协议终止,队伍在占领尤马渡口期间,遭到曾加害过的尤马人的报复,几乎全军覆没,成员或死或逃,少年逃脱后也离开队伍。小说的主要情节便是他们在荒漠、村庄、山间、城镇的各种暴行。小说最后跨越到二十八年后,已成为男人的主人公在格里芬的蜂巢酒馆遭遇法官,被其杀害,队伍成员至此全部牺牲,而小说也在法官的舞蹈中结束。
作为麦卡锡的代表作之一,《血色子午线》是麦卡锡写作风格的转折之作,为其奠定了现代美国文坛的大师地位。
|
| 關於作者: |
|
科马克·麦卡锡,当代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代表作有《血色子午线》、《边境三部曲》、《老无所依》、《路》等。
|
| 內容試閱:
|
你们的想法令人生畏,你们的内心软弱无力。你们的行为充满怜悯而又残酷,让人感到荒诞不经,行事之时心浮气躁,仿佛难以抗拒。最终,你们愈发畏惧鲜血,鲜血与时间。
切勿以为,黑暗之物的生命会沉没在苦痛之中,犹如迷失于悲伤。悲伤之感并不存在。因为悲伤是完全被吞没到死亡中的事物,而死亡和垂死正是黑暗之物的生命。
去年率领远征队前往埃塞俄比亚北部阿尔法地区的克拉克,连同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同事蒂姆·D.怀特一起声称,通过对该地区发现的距今30万年的化石头骨进行重新考察,他们发现,割头皮的做法自古有之。
《尤马太阳日报》,1982年6月13日
田纳西州的童年——出走——新奥尔良——打架——中弹——去加尔维斯顿——纳科多奇斯——格林牧师——霍尔顿法官——打架——托德文——烧旅店——逃跑
看这孩子。他苍白瘦削,身着单薄破烂的亚麻衬衫。他在往洗碗间的灶里添柴。屋外是翻耕过的深色田地,地上残雪斑驳,远处更暗的森林里还藏有几匹余狼。人们以为此处均是劈柴挑水[出自《圣经·约书亚记》9∶21。原句为“于是他们为全会众作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的穷人,但他的父亲其实是教师。他醉倒在地,吐着无名诗人的句子。男孩蹲在火旁,注视着他。
你降生那夜,一八三三年。狮子座流星雨。众星纷坠,何其壮观!我仰望天空,寻找诸天黑色的洞口。北斗破漏。
十四年前,母亲怀下此物,却因他丧命。父亲从不提她名字,孩子也不知道。他在世上尚有一姊,但却无望再见。他注视着,苍白而蓬头垢面。他不会读写,骨子里早已养成对盲目暴力的嗜好。所有故事都在那张面孔上,三岁看老。
十四岁时他离开家。他再也不用见到黎明前黑夜中的冰冷厨房。还有柴禾、盆盆罐罐。他向西游荡,一直抵达孟菲斯,如平坦田园上的孤旅人。黑人在田间劳作,瘦削而佝偻,棉花蒴果中的手指如同蛛爪。园里阴影笼罩的痛苦。
一些身影迎着下沉的夕阳,走在沉缓的黄昏中,穿过纸一样的地平线。一名孤单的黑人农夫独自赶着骡子拖着耙,沿着雨打过的洼地步入夜色。
一年后他到了圣路易斯。坐上去新奥尔良的平底船。四十二天的水路。夜晚时分,汽艇顺着深黑的水面喧嚷迟行,灯火通明如漂流的城市。他们把浮船拆散,卖掉木材,然后他走到街上,听见陌生的口音。他住在酒馆后院上方的屋里,每到夜晚就像童话里的野兽一般溜出去,跟水手打架。他个头虽小,但腕粗掌大,肩膀结实。说来也怪,这孩子脸上虽有疤,但面容却似未改变,眼神出奇地天真。他们打架时动拳脚,也抡瓶子使刀子。不论种族,不论出身。有些人说话像猿猴在低吼。有些人来自遥远的异乡,居高临下地看他们在烂泥里流血,他感到自己维护了人类的力量。
某天晚上,一名马耳他水手长用小手枪朝他后背开了一枪。他转身要与其拼命时,心脏正下方又中一枪。那人逃跑了,他倚着吧台,血透过衬衫向外涌出。其他人转过头去。过了一会儿,他瘫坐在地。
他在楼上房间的小床上躺了两周,由酒馆老板娘照料。她给他送饭,端屎尿。她身强体壮,像男人一样瘦长结实。伤愈之后,他没钱给她,便趁夜离开,睡在河边,最后找到一艘可以载他的船。这船要去得克萨斯。
直到此时这孩子才终于摆脱自己的过去。身世和宿命渐行渐远,无论世界如何转变,也不会有如此荒蛮之境,来检验创世之质料能否任人塑造,自己的心是否并非另一种泥土。乘客都是些胆怯冷漠的人。他们锁闭双眼,没人问彼此出行的目的。他睡在甲板上,和其他旅人一起。他注视着微暗的水岸起起伏伏。灰色的海鸟呆立而视。鹈鹕沿着水岸,滑翔在灰色的水波上空。
他们从驳船登岸,移民带着奴隶,打量着低矮的海岸线、薄沙覆盖的海湾和薄雾中出没的矮松。
他穿过港口的窄街。空气里飘着咸味和新锯木头的味道。夜晚,妓女似饥渴的灵魂在暗处喊他。一周后,他再度动身,兜里装着挣来的几块钱,夜里独自走在南边的沙路上,双手拳在廉价外套的棉袋里。横穿沼泽地的泥堤。成群的白鹭宛如藓沼中的白色蜡烛。风的刀口阴冷,在路边的树叶中大步跳跃,然后在夜间的田野上继续匆忙前行。他往北穿过一些小村落和农场,干一天活挣一天钱,包吃包住。他看见一个弑亲者被绞死在十字路口旁的村落里,这人的朋友们往前跑,拉着他的腿,他吊死在绞索上,裤裆尿湿了一大片。
他或在锯木厂工作,或在白喉疫区工作。一位农场主用一头老骡子抵他工钱,一八四九年的春天,他骑着骡子穿过先前的弗雷多尼亚共和国,进入纳科多奇斯镇。
自雨落那天起,格林牧师就每天向满屋的人布道,而这场雨已经下了两周多。少年猫着腰进入这个破烂的帆布帐篷时,只有墙边剩下可容一二人站立的地方,潮湿和久未洗澡的恶臭挥之不去,使得这些人不时地猛冲到倾盆大雨中呼吸新鲜空气,直到实在受不了大雨浇头才返回。他和其他躲雨的人沿着后墙站定。唯一能将他和人群区分开的,也许就是他没有武器。
乡亲们,牧师说道,这里是地狱,地狱,人间地狱啊,就这儿,纳科多奇斯,他不能袖手旁观。我跟他说,我说:你要把上帝之子带到这儿来?然后他说:噢不,不,我不带。然后我说:难道你不知道,他说过我会永远与你同在,直到无路可走?
这个嘛,他说,我又没叫谁去啥地方。然后我说:乡亲们,你不用请他。管你有没有请,你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我说:乡亲们,你甩不掉他。好。你还要拖着他,就是他,去那头的地狱么?
你见过雨这样下个没完的地方没?
少年之前一直注视着牧师。他扭头去看说话的男人。这人留着典型的马夫式的长八字须,头戴帽顶又圆又矮的宽檐帽。他眼睛有点斜视,认真地注视着少年,仿佛想知道他对这雨有什么看法。
我刚到这儿,少年说。
我可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少年点点头。一个披着油布雨衣的高大男子进了帐篷,脱下帽子。他头如秃石,无须无眉也无睫毛。他身长近七尺,即使站在这个流动的上帝之舍里也还抽着雪茄,脱帽似乎只是为了甩掉上面的雨水,因为他又戴上了帽子。
牧师的布道戛然停止,帐篷里杳然无声,所有人都注视着此人。他理了理帽子,挤到牧师所站的板条讲坛前,转过身来,对牧师的教众讲话。他面色平静,长着一张孩子的脸,甚是奇异。他举起双手,双手不大。
女士们、先生们,我觉得有义务告诉诸位,这位主持此次奋兴布道会的人是个骗子。他没有任何认证机构承认或临时提供的神学证明。他完全不符合被他篡夺之职责的最基本要求,而只是背下了《圣经》中的几个段落,从而给他的欺骗性的布道增添一丝丝他鄙夷的虔诚色彩。事实上,这位站在你们面前假装主之牧师的先生除了大字不识,还在田纳西、肯塔基、密西西比和阿肯色州遭到了通缉。
天哪,牧师叫喊道,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他激动地读起打开的《圣经》。
在众多指控中,最近的一条牵扯了一名托管给他的十一岁女孩——注意,是十一岁——他震惊地发现在强暴她时,他自己竟然穿着上帝的制服。
人群中哀叹四起。一位女士跪倒在地。
是他,牧师呜咽地叫道,是他。魔鬼。就站在这儿。
吊死这个恶棍,一个丑陋的暴徒从后面的走廊里喊道。
不到三周以前,他因为与一头山羊性交,从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被驱逐了出来。是的,这位女士,我说的是:山羊。
不毙了这狗日的,就瞎了我的眼,一个男人从帐篷远处站起来,从靴子里拔出一支手枪,瞄准,开火。
年轻的马夫当即从衣服里取出一把刀,划开帐篷,跨入雨中。少年紧随其后。他们弓着腰,越过泥泞奔往旅店。帐篷内早已枪声四起,帆布墙四周被砍开了十几道口子,人们纷纷拥出,女人尖叫,众人跌跌撞撞,还有人被脚跺倒在泥里。少年和他的朋友到了旅店的走廊后,抹了抹眼睛上方的水,扭头回看。正当此时,帐篷倾斜起来、起皱,像受伤的巨大水母缓缓落在地上,满地拖着撕碎的帆布墙和毁坏的拉绳。
他们进去时,秃头男人已在吧台。
他前面亮锃锃的木头吧台上放着两顶帽子和两大把钱币。他举起酒杯,但并非向他们致意。他们倚着吧台,点了威士忌,少年放下酒钱,但酒保用大拇指把钱推了回去,点点头。
法官请了,他说。
他们把酒喝掉。马夫放下酒杯,瞅了瞅少年,或者说看似如此,他的眼神令人吃不准。少年顺着吧台望向站着的法官。吧台很高,并非人人都能把肘放在上面,但却只齐法官的腰,他站在那里,双手平放在木头吧台上,身子微倾,似乎又要发表一通演讲。此时门口走进一堆一堆的人,身上又是血又是泥的,骂骂咧咧。他们聚拢在法官四周。已有人调集民兵团,去缉拿牧师。
法官,你咋会知道那个冒牌货的罪行的?
罪行?法官问道。
你啥时候去的史密斯堡?
史密斯堡?
你咋知道他犯的那些事儿的?
你是说格林牧师?
是的,先生。我估摸你来这旮旯前在史密斯堡吧。
我这辈子都没去过史密斯堡。估计他也没去过。
他们面面相觑。
那你在哪儿见过他?
我今天第一次见到此人。从来就没听说过他。
他举起杯子,喝了一口。
屋子里安静得出奇。这些人看上去就像泥塑。终于有人大笑起来。然后另一个。很快他们所有人都大笑起来。有人请法官喝了一杯。
在他遇见托德文之前,已经连续下了十六天雨,而后仍然未停。他仍然站在同样的酒馆里,喝得身上只剩两块钱了。马夫已经离开,屋子差不多也空了。房门敞开,能看见旅店后面的空地里有雨水落下。他喝光杯里的酒,走了出去。一些木板横在泥里,他沿着门灯渐远渐暗的光带,向空地末端的木板厕所走去。另一人从厕所那边走回来,二人在狭窄的厚木板中央相遇。那人身子微晃。湿漉漉的帽檐耷在两肩,前面的帽檐用针往后别住。他用一只手拎着一个瓶子。给我闪开,他说。
少年并不打算让路,也觉得没有必要跟他理论。他一脚踢向这人下巴。这人倒下,然后又爬了起来。他说:老子弄死你。
他挥着瓶子过来,少年一躲,然后他又一挥,少年后退。少年朝他出击时,这人拿瓶子往他脑侧一挥,当即打碎。少年离开木板,掉进泥中,男人冲着跟上来,握着参差不齐的瓶颈,想刺少年的眼睛。少年用双手挡住,手上沾了一层滑溜溜的血。他一直试图伸手入靴取出刀子。
干死你,男人说。他们在阴暗的空地中吃力地走来走去,鞋都甩掉了。少年已经拿到了刀子,他们面对面绕着圈,男人向他晃过来时,他割开了男人的衬衫。男人扔掉瓶颈,从颈后拔出一把巨大的博伊刀。他的帽子已经掉了,黏黑的头发绕着头部悬摆,疯子一样嘴里不停喊着杀,以示威胁。
那小子要挨刀了,站在走道上的一名旁观者说。
杀、杀,男人语无伦次地说,一边费力向前。
但又有一人走进空地,像母牛一样发出沉稳的哼哧声。他扛着一根巨型的橡木棍。他先来到少年身边,挥动木棒,少年脸朝下一头栽在泥里。如果当时没人把他翻过来,他就没命了。
醒来已天明,雨也停了,他向上看到一张男人的脸,长长的头发,浑身是泥。男人在跟他说什么。
啥?少年问道。
我说,咱俩是不是扯平了?
扯平了?
扯平了。如果你他妈还想挨揍,可以。
他瞅了瞅天空。高空中,很小一个点,一只兀鹰。他又瞅了瞅男人。我脖子断了?他问。
男人越过空地往外望,啐了一口,又瞅了瞅少年。你起不来了?
不知道。我没试。
我没打算弄断你脖子。
嗯。
我是打算宰了你。
还没人做到。他用手撑着泥地,站了起来。那人坐在木板上,靴子放在一边。你没做错啥,他说。
少年不自然地四处张望。我靴子呢?他问。
男人乜斜着眼瞅着他。片片干泥从脸上往下掉。
哪个狗日的要是拿了我靴子,非宰了他不可。
那儿好像有一只。
少年吃力地穿过泥地,拿回这只鞋。他在院子里四处走动,步履沉重,用脚感觉可能是鞋子的硬块。
这是你的刀?他问。
男人斜了他一眼。好像是,他说。
少年将这刀扔过去,他弯腰捡起来,在裤腿上擦了擦巨大的刀刃。还以为你被谁偷走了,他对刀说。
少年找到了另一只鞋,走过去坐在木板上。他的手上糊着大块的泥,他用一只手蹭了下膝盖,又把手放下。
他们并排坐着,越过不毛的空地向外眺望。空地边缘是尖木桩围栏,围栏之外,一个男孩在井边取水,那边的院子里还有几只鸡。一人从酒吧的门口那边经木板走向户外厕所。经过坐着的他们时,他止步瞧了几眼,然后离开踩进泥里。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又踩进泥里,绕过他们,回到步道上。
少年瞅了瞅这人。他的脑袋窄得出奇,头发抹着一层泥,造型怪异而原始。前额烙着字母H和T,下面接近双目之间的地方烙着F,这些字母刺眼地向外张开,仿佛烙铁在他脸上放了太久。他回头看少年时,少年发现,他没有耳朵。男人起身,将刀子入鞘,提起鞋子沿着木板就往前走,少年也起身跟着。去旅店的半途,男人止步,望向外面的泥地,然后坐在木板上,连泥带鞋一起穿上。然后他起身,吃力地穿过空地,捡起什么东西来。
你过来瞧瞧,他说,瞧我这破帽子。
你看不出来是啥,像啥死了的玩意儿。他拍了拍帽子,戴在头上,继续往前走,少年跟着。
酒馆是一道狭长的走廊,两边是涂了亮漆的墙板。墙边靠着桌子,地板上放着痰盂。暂时无人光顾。他们进去时,酒保抬头瞅了一眼,正在扫地的黑鬼将扫帚靠墙立起,走了出去。
希尼呢?身披泥衣的男人问。
估计在睡觉。
他们往里走。
托德文,酒保叫道。
男孩回头。
酒保已从吧台后面走出,望着他们的背影。他们从门口走过去,穿过旅店的门厅,径直走上楼梯,在地板上留下各种形状的泥印。他们踏上楼梯后,桌后的店员探出身来喊他们。
托德文。
他止步,回头。
他会一枪毙了你。
希尼那小子?
希尼那小子。
他们继续往楼梯上走。
楼梯顶部是一个长厅,长厅末端有一块窗玻璃。墙上有涂了漆的门,挨得很近,看上去像一个个小橱子。托德文继续前行,一直走到长厅底端。他听了听最后一扇门的动静,给少年使了个眼色。
有没有火柴?
少年掏了掏口袋,拿出一个脏兮兮、压扁了的木盒子。
男人接过去。需要一点火种,他说。他弄碎盒子,把碎渣对着门堆起来。他擦了一根火柴,将碎渣点燃。他把这一小堆燃烧的木头推到门下面,继续加火柴。
他在里面?少年问。
等着瞧。
一股黑烟盘旋而起,点燃的油漆冒出蓝色火焰。他们蹲在门厅,注视着火。微弱的火焰开始沿着板条向上蔓延,然后又猛地缩回去。他们二人看上去就像沼泽地里挖出的东西。
快,敲门,托德文说。
少年起身。托德文站起来等着。他们能听见火焰在屋里噼噼啪啪地响。少年敲门。
你使点劲儿。那小子喝了点酒。
他握紧拳头,狠狠地敲了五下。
妈的,火,一个声音说。
来了。
他们等着。
他妈的热死老子了,那声音骂道。然后门把转了转,门开了。
他穿着内裤,手里捏着一块扭门把的毛巾。看见他们后,他又转身回屋,但托德文一把擒住他的脖子,将他骑压在地,抓住头发,用大拇指掏着他的一只眼球。那人逮着他的手腕就咬。
踢他狗嘴,托德文叫道,快踢。
少年绕过他们,走进房间,回身一脚踢到那人脸上。托德文拽着他的头发往后拉。
踢他,他喊道。好,踢他,踢得好。
他又踢了一脚。
托德文将这个满脸是血的头转了过来,瞅了瞅,把它扔到地上,然后站起来,自己又踢了几脚。两个旁观者正站在门厅里。门整个烧着了,墙和天花板的一部分也着了火。他们走到门外,顺着走廊离开。店员一步两级地赶上来。
托德文你个狗日的,他说。
托德文站在他上面四级台阶的位置,他一脚踢中店员的喉咙。店员坐倒在楼梯上。少年经过他时,朝他脑侧一击,店员翻向一边,滑到楼梯底部。少年跨过他进入走廊,穿过前门走了出去。
托德文沿着街跑,疯了似的在头上挥舞拳头,哈哈大笑。他看上去就像被赋予生命的巨大泥塑伏都教人偶,少年也差不多。在他们身后,火焰正舔舐着旅店的最上角,黑色烟云在得克萨斯温暖的清晨中升起。
他之前骡子留在了镇边一个专门收容动物的墨西哥家庭,到那儿时他一脸慌乱,上气不接下气。女人开了门,瞅了他一眼。
我的骡子,他喘息着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