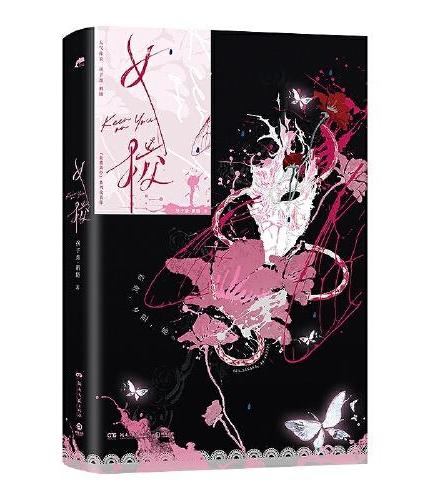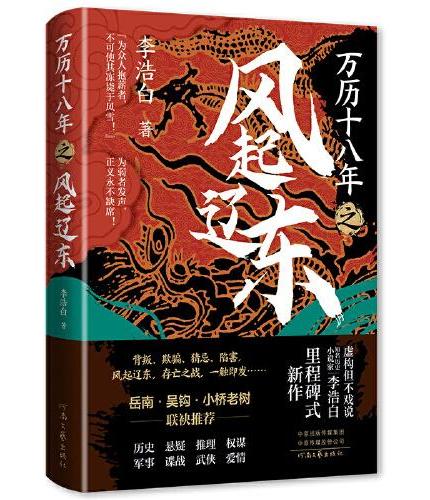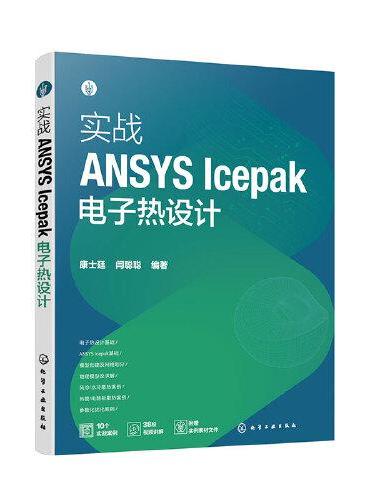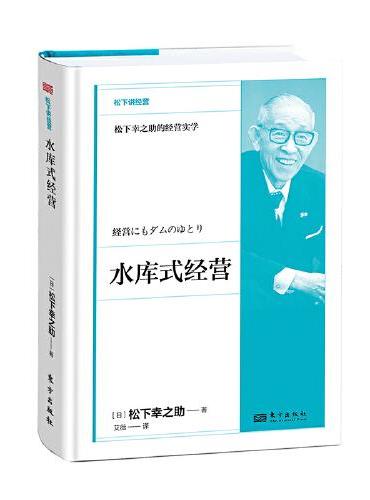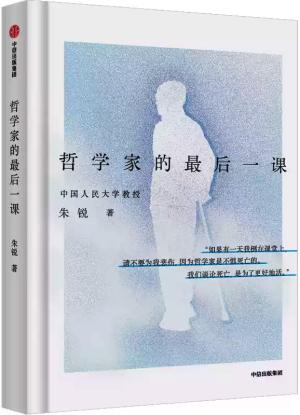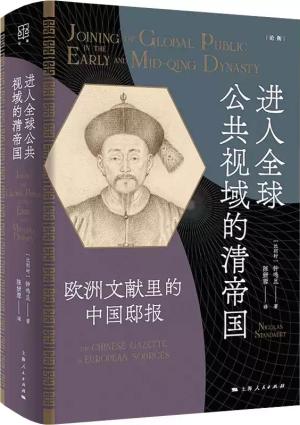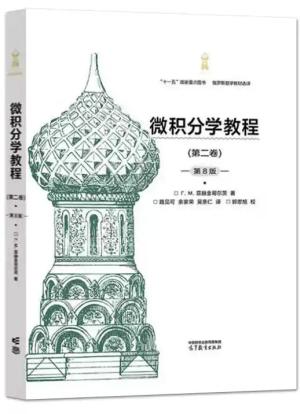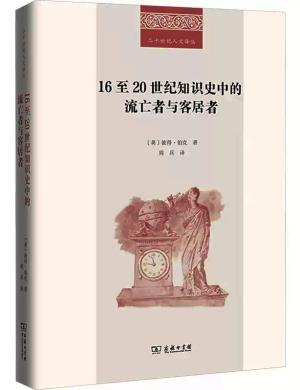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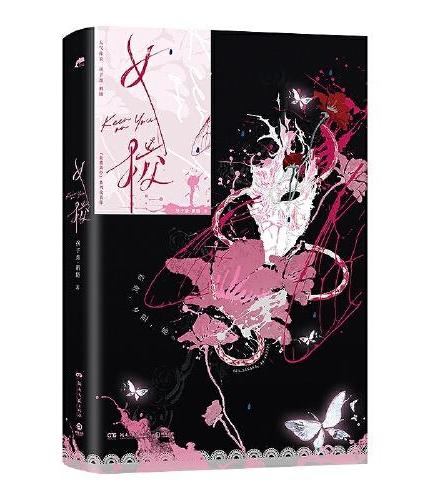
《
女校(人气作家孩子帮·鹅随“北番高中”系列代表作!)
》
售價:NT$
2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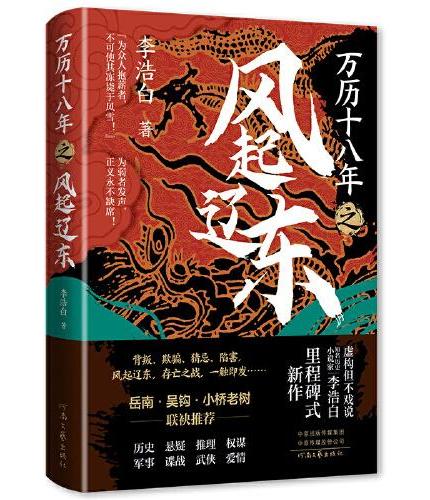
《
万历十八年之风起辽东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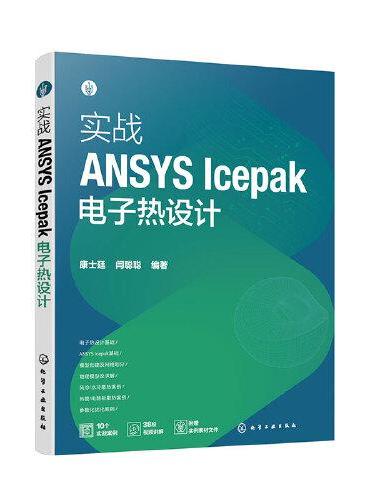
《
实战ANSYS Icepak电子热设计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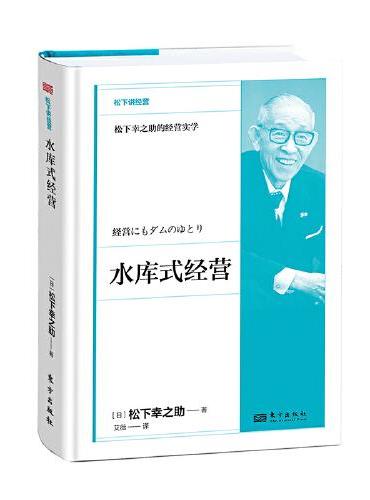
《
水库式经营
》
售價:NT$
2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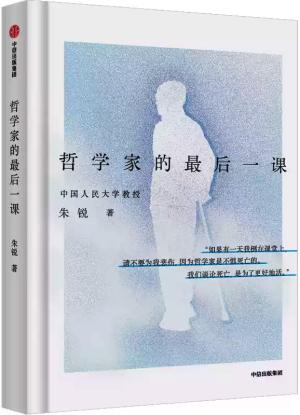
《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
售價:NT$
2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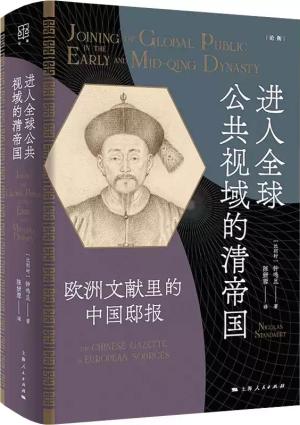
《
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
》
售價:NT$
6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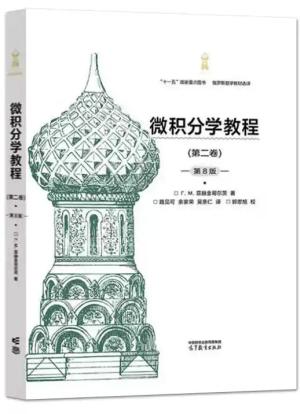
《
微积分学教程(第二卷)(第8版)
》
售價:NT$
5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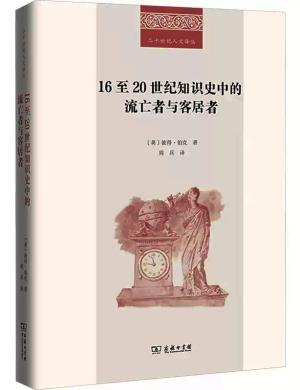
《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
》
售價:NT$
484.0
|
| 編輯推薦: |
★澳大利亚史上最畅销的书
★男孩成长百科全书!
★一,它最小,但最大,拥有最大的力量。
★囊括一切动人元素:悬疑、异国风情与火爆动作场面;神秘、心理与魔法;
融少年成长探索与拳击对决的戏剧张力于一身。——《纽约时报》
★一部极为迷人的小说,叙述一名非凡男孩的蜕变过程,以及他对周遭人物心灵上的影响力。
主角并非英雄式人物,但具备幽默感与清新朴实的特质;探险过程也非常扣人心弦。——《洛杉矶时报》
|
| 內容簡介: |
《一的力量》内容简介:他出生在南非,他既不是黑人,也不是南非人,而是南非人的仇人——“红脖子”英国人,因此处处受到歧视。5岁时进入寄宿学校,得到的第一个名字叫“尿尿鬼”,任何人都可以踩他一脚。
暴力与歧视在学校唯一学到的东西,但他靠着聪明与机智,还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艰难地活了下来。在离开学校的归途火车上,他结识了生平的第一个朋友哈皮,一名列车车长兼业余拳击手。哈皮让小男孩明白:只要用脑子、用心,小也可博大,弱者也能具有震撼众人的能力!从此,小男孩拥有了新的名字:皮凯,同时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告别了哈皮之后,皮凯的人生中陆续遇到很多教他成长的贵人,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一的力量”:一,它最小,但最大,拥有最大的力量。如果不是年龄提示,很难想象这些震撼人心的故事竟都发生在一个孩子幼年时期。从5岁到15岁整整十年,一个小男孩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书写了一部关于“一的力量”的传奇。
|
| 關於作者: |
布莱斯·考特尼(Bryce
Courtenay),真实经历有如传奇的澳大利亚头号国民作家。祖籍英国,生于南非,在澳大利亚从事广告业,直到55岁才动笔写下第一本小说《一的力量》,结果这部带有半自传色彩的历史成长小说马上成了天王级畅销书。考特尼是澳大利亚作家中的销售记录保持人,至今无人能超越。
|
| 內容試閱:
|
事情是这样的。
在我的人生正式开始之前,我也一样啼哭吃奶,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发生在一对大而柔软的黝黑乳房上。依着非洲传统,我持续吃了头两年半的奶水,之后我的祖鲁乳母成了我的保母。她是个充满欢笑、温暖又柔和的人,她会将我搂在胸前,用手顺着我的金色卷发。她的手很大,手掌几乎可以包住我整个脑袋。她唱着能抚平我伤痛的歌,歌词是关于一个勇敢的年轻战士去猎狮子;还有一首女人的歌,说她们去河边的大石上洗衣服,日落时分,狒狒们会从山里跑出来喝水。
我正式的生活从五岁开始。母亲精神崩溃,我被迫离开可爱的黑保母与她又大又白的微笑,进入寄宿学校。
然后便是一段充满黄色南瓜瓣的日子。南瓜片总是烧焦,边缘尝起来苦涩。马铃薯泥里混着透明的块状物,带软骨的肉浸在灰白色肉汁中,加上胡萝卜粒、温润虚烂的高丽菜叶、早晨醒来已湿答答的床单,还有一种名为“寂寞”的全新感受。
头两年的时间,我是全校年纪最小的孩子,而且我只会说英语──一种仿佛黑死病一样扩散到神圣大陆的传染病语言,污染了阿非利堪人纯洁甜美的水源。
波尔战争让大家对英国人怀有强烈的憎恶感,他们叫英国人“红脖子的”。那股仇恨流进了阿非利堪人的血液,囤积在下一代的内心与想法中。对学校的男孩子而言,我可说是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他们了解自己天生对我这族类所抱持的仇恨。
我说的语言曾经吐出一些句子,那些话杀掉了他们的祖父,并将他们的祖母送进世界上第一个集中营。她们在那里如苍蝇一般死于痢疾、疟疾与黑尿热。对严厉的卡尔文教派农人来说,父债子还,至第三代方休。于是,我被传染了。
当时完全没有人警告我,说我将被视为邪恶的人种,因此事情发生时,就像是一场恐怖的意外。我在幼童宿舍里暗自抽噎啜泣,突然间来了两个十一岁的男孩子,把我从充满可怕樟脑味道的被单里拉出来,带到高年级宿舍,在战争委员会面前接受审判。
当然,我的审判是场公理正义的闹剧。但当时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在敌军的腹地被掳获,而每个人,即便是五岁小孩,都知道那代表死刑。我站在那儿支支吾吾,不了解那个声音宏亮的十二岁法官说些什么,也不了解为何当他宣判时,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但我猜想,情况是糟到不能再糟。
当时我不太知道死亡是什么。我知道“死”是农庄的屠宰场对小猪、小羊,有时候则是对小母牛所做的事。猪仔的惨叫太凄厉了,我想就算对猪仔来说,那经验也绝对不怎么美妙。
我当然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我知道死不如生好。而现在,在我能真正领受生之甜美前,死亡就要降临在我头上了。被拖出去的时候,我强忍着泪水。
那晚一定是月圆夜,因为蓝色的光芒笼罩整个盥洗室。厚实花岗岩砌成的浴室隔间棱角分明,矗立在湿漉漉的水泥地板上。之前我从未来过淋浴室,这地方像极了农庄的屠宰场,甚至闻起来也一样,充满了尿与药皂的味道。于是我猜这就是我的葬身之地。
我的眼睛哭得有点肿,但仍看得见那些挂有肉钩子的地方。每一片花岗岩板都有一根从后面墙上伸出来的管子,管子末端有个把手。他们会把我吊在那东西上面,然后我就会死,跟那些猪仔一样。
他们叫我脱掉睡衣,跪在其中一个淋浴间里,面向墙壁。我瞪着地板上的洞,所有的血都会从那里流掉。
我闭上眼睛,呜咽无声地祈祷。我不是对神祷告,而是对我的保母。我觉得那是一件更迫切该做的事情。当她无法解决我的问题时,她会说:“我们必须向无上无上之神祷告,他是伟大的巫医,会知道该怎么做。”虽然我们从来不曾真的召唤大神作法,但那不重要,光是知道你需要他时他便存在,这一点即让人安心。
但是当时才要藉保母得到指示已经太迟了,要她帮忙传递信息也来不及了。我感到水溅到脖子上,以为是温热的血液从我颤抖赤裸的身体流下来,经过水泥地板流进排水管。很好笑,我不觉得自己死了,但是你知道,谁会了解死亡感觉起来是怎么一回事?
那法官与他的战争委员会成员们在我身上撒完尿之后便离开了。没多久,世界变得非常安静,只有头上某处传来答、答、答的滴水声,以及我吸鼻子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另一个地方传来的。
因为我从来没看过淋浴间,所以不知道要怎么转开莲蓬头,也不知如何冲洗身体。从前保母总是在厨房炉子前的锡盆里帮我沐浴,我会站起来让她在我身上涂满香皂。她在我的小鸡鸡上抹香皂时,那一对在厨房工作的双胞胎女仆,迪与达,就在背地里偷笑。有时候小鸡鸡会自己站起来,每个人于是咯咯笑得更开心。因此,我知道小鸡鸡很特别。至于有多特别,我很快就明白了。
我试着用睡衣擦干身体,衣服因为掉在地上,所以湿了好一大块。然后我穿回睡衣。我没有费心去扣扣子,因为双手仍抖得厉害。我在那个又空旷又黑暗的地方游荡,直到找到幼童宿舍,爬进毯子里,结束了正式生活的第一天。
我没办法告诉你,正式生活的第二天比第一天要好一点。从我醒来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不对劲了。许多小孩子围在我的床边,捏着鼻子喷气,大声抱怨。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他们能抱怨的事情可多了。我闻起来比卡菲尔尿桶还糟,比家里的猪仔还糟。甚至比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还糟。
一个唇上方有一小撮黑毛的大人走进来,所有的小孩一哄而散。那是前一天晚上带我来寝室的女士。“早安,梅富!”小孩子齐声大喊,而且都在自己的床边立正站好。
那身材高大名叫“梅富”的人瞪着我。“来!”她口气很凶,抓着我的耳朵一扭,把我拖出臭得要命的床铺,回到屠宰场。她光用一只手就脱掉我没扣扣子的睡衣,把我的裤子拉至脚踝。“跨出来。”她大吼。
我绝望地想着,这人甚至比保母还要高壮。如果她也尿在我身上,我一定会淹死。我跨出睡裤,然后她放开我的耳朵,把我推进一个淋浴间。突然间,出现一道嘶嘶声,然后冰水像针一样刺进我的身体。
如果你从来不曾淋过浴,或从未出其不意浸入冰水里,你会很容易相信这就是死亡了。我双眼紧闭,冰雹般的水柱源源不断,一千枝冰锥同时钻进我皮肤。怎么有人可以一次尿那么多?
死亡冷如冰霜。地狱应该是充满火焰与硫磺才对,但是在这里我却冷得要死。那感觉很可怕,然而就如同之前种种一样,事情与我所期待、所相信的都大相径庭。
“到了寄宿学校,你会跟一大群小朋友一起睡在大房间里,你再也不必怕黑了。”这一切听起来多么令人兴奋啊。
猛烈的嘘嘘声与山洪般的冰尿突然停了。我睁开眼,没看到梅富;反而看到那个法官站在我面前,他的睡衣袖子卷起,伸过来关掉莲蓬头的手臂湿淋淋的。陪审团与一堆跟我同宿舍的小孩站在他身后。
等我脸上与眼睛上的水滴干净后,我试着微笑,那法官湿答答的手臂突然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出那间大理石淋浴间。陪审团围着我,我害怕地站在原地,用手护住蛋蛋,牙齿不由自主打颤,我甚至可以听见脑袋里那怪异清脆的切分颤音。法官又抓住我,用一只大手抓住我两手腕,拉开我的手,然后指着我的小鸡鸡说:“你为什么尿在床上,红脖子的?”
“嘿,瞧,他的小蛇上没有帽子!”有人大叫。他们都挤过来,很高兴发现这个天大的秘密。
“尿床的!尿床的!”有个小孩子大喊,一下子所有的小孩都一起大喊。
“给我听好,你这个尿尿鬼,”那法官说:“是谁把你那条小蛇上的帽子剪掉啦,尿床的?”
我低头看着他指的地方,此时打颤的牙齿已经转成比较安静的定音鼓了。在我看来,一切都非常正常,鸡鸡顶端带着一点亮蓝色,几乎隐没在周围完好的皮圈中。我困惑地抬头看着法官。
法官放开我的臂膀,用双手拉开他睡裤。他的“小蛇”根本跟怪物一样大,悬在那儿与我的眼睛平行,看起来像是用连在一起的护套做成,粗粗的皮一直延伸到最下方。底部有一小撮毛发。我必须说实话,那东西并不怎么好看。
当然,有更多大麻烦正等着我。我是“红脖子的”,也是“尿床的”;我说的是错误的语言;然后现在显然我的构造也与他们不同。但是我还活着,而在我的书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将自己受欺负的时间降至一天不到一小时。我几乎已经把求生的艺术练到滚瓜烂熟,只除了一件事:我成了习惯尿床的人。
如果你每天早上都在床上留下一滩湿印,你是不可能完全融入环境的。我的一天通常从尿床然后挨梅富一顿揍开始,之后我得独自到那可恨的淋浴间去洗我的橡胶床垫。当我拿出那把他们叫我使用的大木刷,用力把药皂抹上硬梆梆的刷毛时,刺痛的肥皂沫总会猛地喷进我眼睛。但很快我便发现不必得照梅富说的那样用药皂,只要让床垫在水柱下好好冲一冲就可以了。
我的早晨惯例其实有些用处。我学会“哭泣”是件很奢侈的事,一个适应良好的家伙应该放弃流泪。我很快便成了学校里最常被揍的人,法官说我创了纪录。就适应新生活而言,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拥有一个还不算缺陷的头衔,我并不只是可恨的“红脖子的”与“尿床的”,我还是纪录保持人。告诉你,那感觉可棒了。
法官下令每一次只能揍我一下下,这里一拳,那里一巴掌。如果我不再是“尿床的”,他甚至可以连那一下下都不揍。不过他补充说,因为我是“红脖子的”,这点就不能不揍了。我得承认我还满赞同的。我私下决心不要尿床,甚至对保母祈祷或对神祈祷,但看来都没有什么效果。
也许这一切与我不完美的小鸡鸡有关?我在裤子两边口袋内里挖了一个可让拇指与食指穿过的小洞,偷偷拉着我的鸡鸡皮,尽我所能想把它拉到最前面,希望它丧失弹性,让我变正常。唉唉,除了小鸡鸡痛得要命之外,什么也没有。我这一辈子注定要当个尿尿鬼了。
第一个学期终于结束。我回老家去过五月假期。我将回到保母身边,她会听我说我的悲惨故事,然后睡在我床脚的垫子上,这么一来鬼就不会来抓我了。我也要问问我母亲是否已经不崩溃了,那么我便可以留在家里。
我坐在翰尼.波什夫大夫闪亮崭新的雪佛兰跑车后座,高兴地启程回家。翰尼大夫是我们的小区医生,也是我们那地方的英雄,他在北特兰斯瓦的橄榄球队里担任传锋的位置。法官看见他来接我的时候,还与我握手,保证下个学期所有事情都会好转。
第一个向我提及崩溃一事的人就是翰尼大夫,而现在他肯定地告诉我,我母亲“恢复良好”,但仍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目前还不可能回家。
很不幸,那表示我无法留在家里。除非我变得跟我爷爷一样老,或甚至更老,否则不必离开的机会是微乎其微。
我坐在后座享受凉风与阳光,随着车子前行,我不再是“红脖子的”与“尿床的”,而是了不起的老板。我们经过非洲村落,鸡只嘎嘎叫,死命拍打翅膀逃离马路,卡菲尔狗也吠个不停。那些狗肋骨突出,脸瘦得只看见嘴,身上都是斑点,正追着鸡跑──当然是在我们轰轰加速的宝座安全通过之后。身为一个伟大的老板,这些事对我来说自然平淡无奇。生活真美好。我可以肯定告诉你,生活非常美好。
保母哭得很厉害,豆大的泪珠滚落脸颊,溅在巨大温暖的胸部上。她不断用黑色的巨手摸我剃过发的头,一面抱紧我一面呜咽低吟。我本来想等回家时要好好哭个痛快,但跟她一比真是输了。
时近夏末,日子充满农妇采收棉花时的歌声。她们沿着长条状的田地工作,一边聊天唱歌,声音美妙和谐,一边从晒黑的棉花荚中挽下蓬松的白色纤维。
保母传了信息给无上无上之神,让他知道我们因为小孩晚上尿床的问题,急需见他。我们把信息放在鼓上,两天后便听说约在这两个礼拜,伟大的巫医会在去拜访伟大的雨后莫迪亚吉途中现身。
保母一谈到伟大的无上无上之神,总是翻着白眼,双颊涨红。“他会扔一只白色大公牛的胫腿骨来替你清干床铺。”她保证。
“那他也会让我的小鸡鸡长出皮来吗?”我想知道。她紧紧把我抓到胸前,笑得咯咯颤颤,答案则掉进了她不停起伏的肚皮里。
在田里工作的妇人们热烈讨论我晚上尿床的问题,她们想了很久,怀疑就这么一件小事能请到伟大的巫医吗?“草编的睡毡在早上的阳光下晒晒就干了,这种小事不适合请非洲最伟大的巫医来操心。”
对她们来说当然没关系,她们不必回到法官与梅富那儿。
约莫在我们发出信息的两个礼拜左右,无上无上之神搭着他的大别克轿车来了。那辆轿车是他强大权力与财富的象征,甚至那些把他看成邪灵转世的波尔人也怕他,就像所有无知畏神的人一样。没有人预备拿荷兰归正会的教义来与这个古老的黑妖怪对抗。
一整天都有农妇带食品礼物来。到下午三、四点,屠宰场旁边的酪梨树下多了一座由卡菲尔玉米、各种南瓜、当地菠菜与西瓜堆起的小山。旁边有一捆捆干烟草,而在分开的两张大草席上躺着六只瘦巴巴的卡菲尔种鸡。它们大多是老公鸡了,像蒸煮了四小时那么老。它们侧躺着,鸡爪用绳子缚着,翅膀剪掉,瘦而无毛的颈子与秃顶都沾满泥土。如果不是偶尔踢个腿,也只有不时一声:“嘎!”及猛然一睁的圆珠眼能透露它们还活着的讯息。
其中有只特别瘦弱的灰毛老公鸡在我看来像极了爷爷。我爷爷的眼睛是浅蓝色的,湿润湿润的,那是一双注定要注视着柔软英国风景的眼睛。不过,这只老公鸡的眼睛像红珠灯串一样尖锐。
我爷爷下了台阶,往黑色别克大轿车走去。他停下来踢了其中一只公鸡一脚,他恨那些卡菲尔鸡的程度简直就跟他恨申刚族人一样。只有他那百来只奥屏顿黑鸡和六只巨大的公鸡能让他感到又骄傲又快乐。农场里的几只卡菲尔鸡,就算绑成一捆又剪掉翅膀,也只像是让半打脏兮兮的老男人出现在芭蕾舞课里一样多余。
他力赞无上无上之神,那巫医曾经治好他的胆结石。“我吃了他臭臭的绿药丸,然后,天吶,那结石就像猎鹿的大号铅弹一样在我身体里爆炸消失了!从此我再没看过一颗结石。如果你问我,我会说那只老猴子是整个低草原地区最他妈厉害的大夫。”
我们等着无上无上之神从别克轿车里出来,这个老巫医跟保母一样,是祖鲁族人。传说他是伟大的祖鲁国王丁冈的最后一个儿子,丁冈曾经对抗波尔人与英国人直到最后一刻。经过了两个世代,波尔人终于在“血河之战”中打败了他的战士,而他们至今仍十分敬畏他。
那一战过后二年,丁冈逃离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莫庞德与波尔人的联合军队,到大列朋波山脉请求当地的鸟沃人给予庇护。那一晚在他被鸟沃族叛徒暗杀前,他们带了一个处女到他面前,于是这个有史以来第二伟大的国王的战士之种便留在女孩十四岁的子宫里。
“我选择了血战,但我这么儿将会选择智慧。你们将叫他‘无上无上之神’,他会是全非洲最伟大的人。”丁冈曾如此对那个吓坏的鸟沃少女说。
就这样,这个受人搀扶从别克轿车后方步出的矮黑干瘪男人,今年已经一百岁了。
无上无上之神穿着一套不相称的西装,棕色外套旧得发亮,长裤则是蓝色细条纹布制成。上身是得装上可拆式浆领的白色衬衫,却没装领子,改用一颗象牙金色的大领扣固定在脖子上。他肩膀上披了一条看起来很脏的豹皮斗篷。一如这里的习俗,他没穿鞋,他脚底扁平,边缘龟裂。他的右手拿着一支带有美丽编珠的拂杖,那是首领的权力象征。
我从来没看过那么老的男人。干胡椒似的头发比干棉花还白,一小撮一小撮的白胡子从脸颊上冒出来,嘴里只剩三颗黄牙。他注视我们,眼睛一亮,锐利而清晰,仿佛那只老公鸡的眼睛。
许多女人开始哭号,老人实时出言叱喝她们。“愚蠢的印法西!死神没有跟我一起坐大车来。难道你们没听见它大肚子里的吼声吗?”
我祖父走过去,四周安静下来。他简单地欢迎无上无上之神,应允他今晚可以在农场里过夜。老人点点头,完全没有一点意料中卡菲尔人惯有的谄媚举止,我祖父也似乎不期待他那么做。他只是把老人骨瘦如柴的手爪一握,然后回到门廊前的椅子上。
跟其他女人一样,将泥土涂在额头上的保母最后终于说话了。“我的主人,女人准备了食物,我们也有鲜酿的啤酒。”
无上无上之神看也不看她一眼(我觉得这举止很勇敢),指示其中一个妇女去解开那些瘦弱的公鸡。两名妇女跑过去,很快将鸡只松绑。鸡还是躺在那里,丝毫未察觉自己已重获自由,直到老人举起他的拂杖对它们挥舞。鸡群突然嘎嘎大叫,拍打发育不良的翅膀,起身窜逃冲奔。它们往空地跑,长脚举得高高的,只有一只除外──那只长得像祖父的公鸡慢慢站起来,伸展颈子,拍打它所剩无几的翅膀,头忽左忽右疾动,微微昂起头仿佛正专心聆听。然后,说多冷静就有多冷静,它竟走到玉米堆那儿啄食起来了。
“抓住那些披着羽毛的恶魔,”无上无上之神突然指示道,“给老人抓来今晚的晚餐。”
女人们兴冲冲地尖叫一声又围住那些鸡。紧张的气氛松缓下来,五个女人各倒抓着一只鸡,等待老人指示。无上无上之神蹲下来,用手指在沙地上画了一个直径两呎的圆,像只老黑猩猩一样跳来跳去,又完成了五个差不多大小的圆,一边画一边喃喃自语。
当咒语告一段落,他指示其中一个妇女拿来一只公鸡,他抓着老鸡瘦长的颈子与双脚,沿着地上的圆圈再画一次,这次是以鸡喙做笔。然后他将公鸡放在圆圈里,鸡躺在那儿动也不动,双眼紧闭,从两边翅膀底下各伸出一只脚。他继续重复了五次,让另外五只鸡在众目睽睽下各躺在一个圆圈里。鸡一躺下来休息,妇人们便惊异地倒抽一口气。那只是初级的魔法,不过倒足以让事情顺利进行。
无上无上之神移过去一点儿,盘腿蹲坐在印答巴毯中间,举手示意我过去跟他一起。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存在,我害怕地紧紧抓着保母的裙子。她将我轻轻推向他,悄声而清楚地对我说:“你一定得去,这是无比的荣幸。只有首领才能跟首领一起坐在会毯上。”
老人身上带有非洲汗水特有强烈而甜美的味道,混合着烟草以及非常老的老人味。那味道还不算太坏,毕竟就臭味来说我见过的世面还不少。我也盘腿坐在他旁边,眼睛直直盯着前方地面。
无上无上之神靠过来,以祖鲁话对我说:“明天我会把刚才公鸡的把戏告诉你,那不是魔法,你知道,这些愚蠢的申刚族人以为是,他们不配知道太多。”
“谢谢你,先生。”我轻声说。就算那只是个把戏,也聪明得要命。如果我可以在学校里找到一只迷途的鸡,也许就可以让法官跟那些陪审团员感到百思不解而害怕。当场我对他的能力信心满满,他将改变我“尿尿鬼”的地位。
无上无上之神嘱咐保母开始张罗“夜水”事宜,很快两个女人便受托升起炊火,其余妇女则小心翼翼围着印答巴毯坐着,连一点点儿边也不敢碰到。
非洲的故事总是非常长,珍惜收拢每个细节,以便让人重述一千次。对保母而言,独自站在即将隐灭的火光中说着故事,是很了不起的一刻。她以申刚语说着,这样一来所有人都听得懂,并且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瞪大眼、哼气、点头或叹息。
她们觉得高壮的梅富与她唇上的胡子很怪异,倒不太惊讶法官与陪审团不公的行径,因为她们都明白,白人所作的判决与实际发生的事经常毫无关联。法官与陪审团在我身上尿尿这件事让她们双手掩耳,摇晃身体并哀叹呻吟。难道这比那些白人所做的事更侮辱人?
突然间天色便暗了,这是非洲特有的日落。火堆里的绿木裂开,发出尖锐的哔剥声,冒出一阵火花。跳跃的火光照亮保母的脸庞,听众没有忘记她娓娓道来的故事是多么悲惨不幸。当保母说到最后死亡将临,长了胡子的巨大死亡天使两腿间喷出冷尿淋了我满头满脸时,许多人哭了起来。
我得承认保母的表现让我印象深刻,但是当她说到我的小蛇没有帽子──在我看来这可是整件事的重点──她们却睁着泪眼,手摀住嘴咯咯笑了。
保母最后做出结论,她认为“夜水”是那个长了男人胡子,双腿间像瀑布一样的死亡天使加在我身上的邪恶诅咒,这么一来她才能每天早上都出现,拿皮鞭在我虚弱的幼小身躯上施以一顿好打。而只有伟大如无上无上之神的巫医才能打败那邪恶的诅咒。
最后啜泣不已的保母坐下,那些女人吃惊的脸庞在柴火照耀下一清二楚。她们知道从未有人说过这样的故事,这故事很可能会流传下去,辗转成为一则申刚传说。
我可以告诉你,任何人,特别是我自己,能够熬过那些折磨,都让我极为惊讶。
无上无上之神站起来,抓抓屁股,打了个大呵欠,用拂杖柄戳戳正在啜泣的保母,命令道:“女人,给我拿些卡菲尔啤酒来。”
厨房里那对双胞胎女仆迪与达送来我的晚餐,保母则负责打点那个瘦巴巴老巫师要喝的,以及他需要的东西。那两个小女孩瞪大眼,兴奋异常地告诉我,我是她们见过最勇敢的人了。
睡前,保母一如往常陪在我身边。她带来一个大甜薯,从中剖开,上头插着汤匙。甜薯冒着微微蒸腾的热气,在汤匙把手上凝成了水珠。传说人哀伤时甜薯可振作精神,高兴时可作为庆祝。带皮的烤甜薯本身便有舒缓疗愈的能力。
保母仍很亢奋。她抓着我,将我紧搂在她宽阔的胸脯里,笑着告诉我,我能让那只老猴来访对她来说是何等恩泽,毕竟他是全非洲最伟大的巫医。她告诉我,她能讲述那个夜水的故事,表示祖鲁女人也能说故事,即便跟一个口才顶尖的申刚人所说最好的故事相比,各方面也皆毫不逊色。
我指出她完全忘记提到我是学校最常被揍的纪录保持人,突然一颗豆大的泪珠滑落她脸颊。“白人给的惩罚早让黑人了解,一顿皮鞭可以损坏我们的身体,但绝对无法伤害我们的灵魂。我们就是大地,所以我们长成了大地的颜色。最后胜利会属于土地,每个非洲人都了解这一点。”
无论那些话是什么意思,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离开之前,保母先点了石蜡灯并将灯转暗,但没有暗到当怪物想偷偷溜进我房间时,我会认不出来的程度。
“今晚无上无上之神会入梦拜访你,替你的‘夜水’找到出路。”她说,替我盖好被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