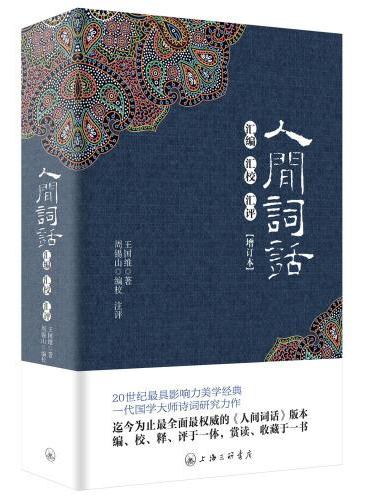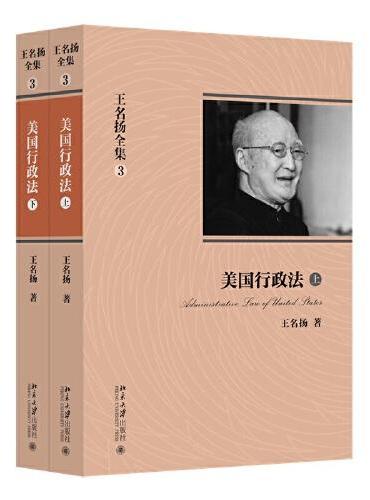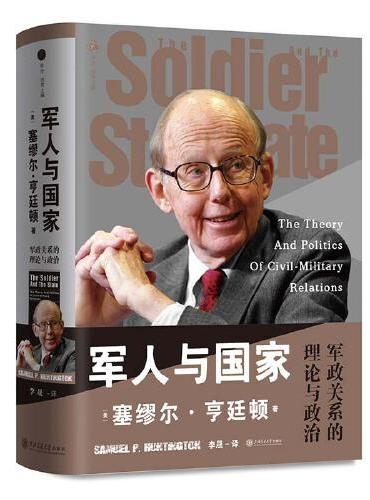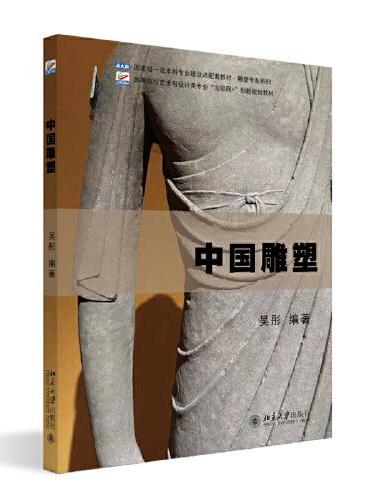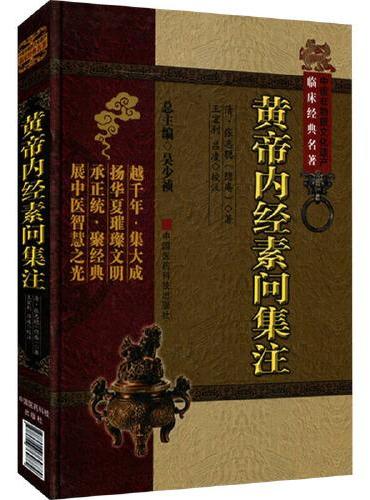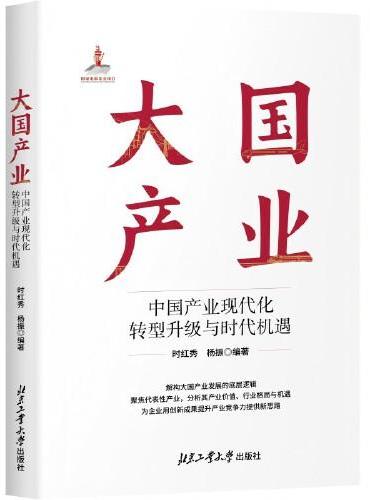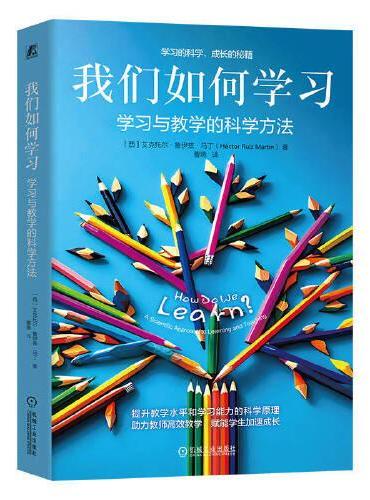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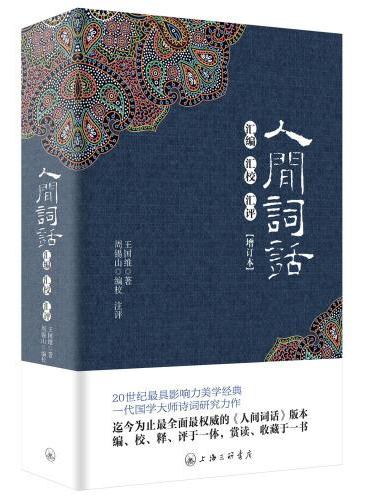
《
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新)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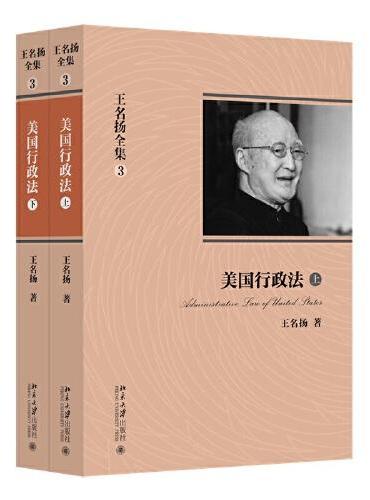
《
王名扬全集:美国行政法(上下) 王名扬老先生行政法三部曲之一
》
售價:NT$
8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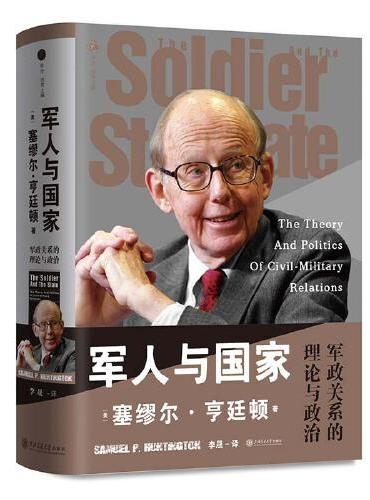
《
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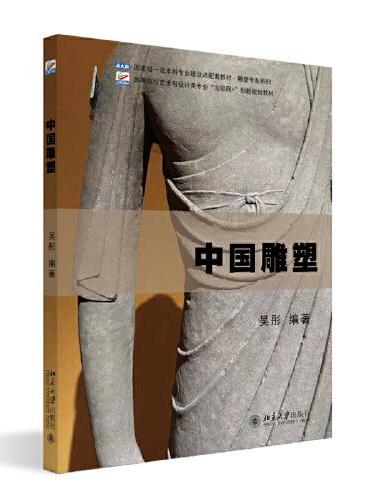
《
中国雕塑 高等院校艺术与设计类专业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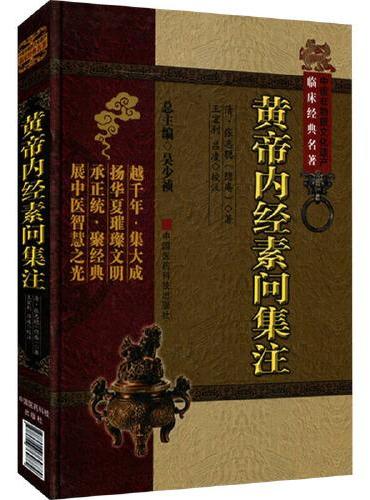
《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
》
售價:NT$
3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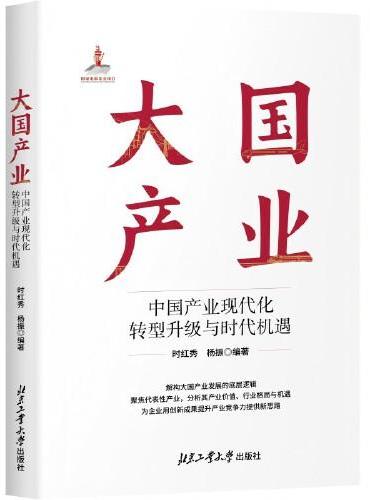
《
大国产业—中国产业现代化转型升级与时代机遇
》
售價:NT$
403.0

《
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咨询
》
售價:NT$
7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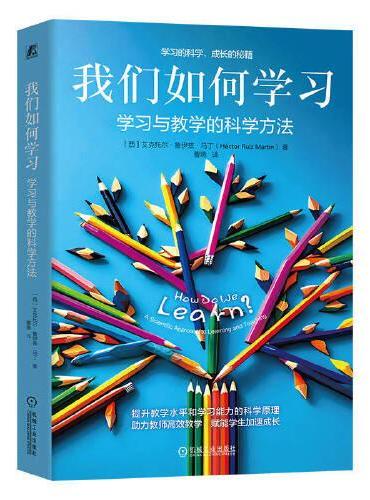
《
我们如何学习:学习与教学的科学方法 (西班牙)艾克托尔·鲁伊兹·马丁
》
售價:NT$
403.0
|
| 編輯推薦: |
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左邻右舍,还有远方的人。
他们按照自然的节奏生活,他们生命的律动融入自然的节奏中。
在被雪山环绕、蕴涵着轶事的牧场上,牧人的世界之所以动人心弦,是因为他的四周荡漾着万事万物的气息,如同日月一般古老而新鲜——
那个时候,草原的传统就是自由,没有边界。
牧人可以朝着任何一块牧地行进,感觉哪里好就躺在哪里,一切牛羊的方向就是他的方向。牧场上有他的道路,他的时间,他的床铺,他的家……
在这里,牧人触摸到的不是时光的流逝,而是时光温暖的给予。
草原千年的时光缓慢悠长,牧人、羊群,一起走在回家的温暖之途,也许,世间并无隐逸之路而只有生活。
谨以此书献给那片草原、那些牧人,以及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你。
愿这本书牵出潜藏在你我心底的“游牧”情结……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对边疆游牧生活挽歌式的实录,记录了新疆和甘肃的草原游牧民族生存景观。草原民族在从游牧到定居的生活转变过程中,当那些淳朴自由的民俗渐渐消失、游牧时代进入历史的尾声,既有对古老生活方式的回望和挽留,更有对新生活的迎接。
本书所讲述的这些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关乎历史,关乎他人,更关乎我们自己。我们对自由在内心的追逐。
|
| 關於作者: |
|
南子:诗人,作家。1972年生于新疆,现居乌鲁木齐。2012年获第三届“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出版诗集《走散的人》,散文集《奎依巴格记忆》,历史人文随笔集《洪荒之花》及《西域的美人时代》,长篇历史小说《楼兰》,长篇风俗小说《惊玉记》。
|
| 目錄:
|
上篇:游牧?草原
奥塔尔牧道秋季转场
沙吾尔冬牧场
沙漠中的牧驼家族
路上的阿肯
萨满铃鼓
中篇:牧歌?毡房
马影远去
在羊毛线里游移的手指
那拉提的两面
遥远的“杨哥家”
下篇:定居?村庄
迷失的部落
我目睹了美感从一个村庄消失
失落的牧鞭
游牧者的归途
后记
|
| 內容試閱:
|
奥塔尔牧道
留恋着稀疏枯黄牧草的大尾羊被赶回来了;
被羊粪熏得黑乎乎的烟筒拔了下来;
骑马人的鞍子上挂着备用马鞍和皮绊;
鼓胀的风干羊肚子里塞满了羊肉;
“霍斯(毡房)”尖顶上的毡子卸掉了,圆圆的网笼里一下子变得透亮;
积了一个夏天厚厚尘土的被褥、花毡卷起来,静静搁置一旁。
女人的衣服、绣针和一团团羊毛线,男人厚重的羊皮裤子和旧靴子,熬奶茶的铜壶,刷着蓝漆的木摇床,还有绣了整整一个夏天的花毡……所有的东西就要牢牢地绑在骆驼身上了。几峰高大的骆驼在一旁半卧着,一边静静地反刍,一边等着主人的召唤。它们的身体在清晨与日暮时分,呈现出古铜色的光泽……
九月的暑气刚过,哈萨克族牧人向着冬牧场的迁徙就这样开始了。
在我的前面,走着一群行色匆匆、沉默不语的牧人。他们的身上有一种草原上特有的气味,这气味混合了风沙、秋草、毛毡、酥油和羊膻味儿。一路上,我闻着这种气味,跟着他们。有的男人裹着破旧的灰黑色西服,腰间捆了根皮绳;有的则套了件褪了色的军用棉服,头顶皮毡帽。而女的则一律长裙子里面套着肥大的裤子,她们的头发总是乱糟糟的,好像一把秋天的干草,但眼神黑黑亮亮的,脸上也黑里透红,健康、自然,是阳光的杰作。
他们一长排地跟着牛羊群默默地走,其中一个男人古铜色的胳膊上爬着一只黑壳虫子,静止不动——显然,它把他当成是大地的一部分了。
除了人的脚步声,我的周围还充满另一种重重的脚步声,那是千百头牛和羊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到一起,用细小的蹄子踏出的轰响声。我的脚在机械地动着,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到了一座山坡上,我的左面都是连绵的黑色石头的山脊,眼前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牛羊。我最先跟着的那些牧人早已走远,但是,同样的气味又成了我的向导。我不知道是谁在领着我,只知道是一种草原上特有的气味。
这些牧人的脚步和牛羊的蹄踏,使整条道路烟尘腾起,混乱杂沓中洋溢着勃勃生机。
这是2006 年9
月我的一次经历。当时,我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随着杜热乡的老牧人阔加拜一家,从夏牧场转往冬牧场。
新疆属山地牧区,随山地海拔的变化,从低处的荒漠到高山草地,形成垂直分布的不同牧场。这些牧场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草的种类也明显不同。牧人们从长期的游牧生活中总结出经验,根据气候的冷暖、地形的坡度和牧草的长势,在一定区域内转季放牧,并把由夏牧场转移至冬牧场或由冬牧场转移至夏牧场的做法称为“转场”。转场,在哈萨克语中叫“阔什霍恩”,“阔什”是“搬家”的意思,而“霍恩”是“居住”的意思。
一般的牧人家庭,都要养一百只以上的牛羊来维持基本生存,而一个草场能够承载的牛羊数量是有限的,牧人们很遵守自然法则,出于在草原上生存的长远考虑,不会等到周围的草都被吃光了才迁徙。所以,牧人转场主要是为了草场的良性循环,也为了他们的牛羊能够吃到新鲜的牧草,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比如遇到雪崩、狼群袭击和龙卷风等突发事件。
牧人在转场前,要先考查目的地的水草状况等,并与亲戚、邻居和朋友事先商定转场的时间、路线,约定途中宿营的地点,盘算途中的每一个细节及可能遇到的问题,如有没有将要出生的牲畜,如何安置老弱牲畜,等等。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之后,牧人就可以带上所有的家当和牲畜出发了。
在哈萨克族牧区,通常在各类草场之间都有固定的、大小不等的、滩险各异的道路相通。这些道路被称为牧道,是由牧人和成群结队的牛、羊、马、骆驼等牲畜,在茫茫大草原上和高山河谷中,天长日久踩踏出来的路。牧人们在山区转场,必须按牧道行走,这样既能保证人畜的安全,防止牲畜肆意践踏牧草、破坏草原,还可以避免因践踏他人草场而引起的纠纷。
哈萨克族牧人所选择的转场牧道都是经过很多年,由好几代人实践、选择并留传下来的传统牧道。一般说来,那些牧道都有自己的名字。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牧区共有两条主要的牧道:吐尔洪牧道与杜热牧道。这两条牧道的长度差不多,都在450
公里左右。我的这次转场走的就是杜热牧道的一个分支——奥塔尔牧道。
奥塔尔牧道长180
多公里,道路狭窄、艰险,到处都是尖利的砾石,是转场时必经的一条老路。有的地方还有暴突的岩石阻挡前进的路。在20 世纪80
年代,这条牧道的险要处都是用石子铺垫而成,路面很窄,有的路段曾经不足15
厘米宽,只能让一个人勉强通过。牧道与山谷交叉,常常延伸到谷底之后又爬上来。牧人通过这条牧道转场,每季需15
天时间。可想而知,当年那些牧人赶着大量的牲畜从这里经过时,会是怎样的一番艰辛景象。
头羊
羊群在我们前面走着,踩得沙子发出细碎的声响。羊群很密集,但却不乱,从后面看,它们走动着的身子犹如涌动的一层层波浪。我注意到,一只羊始终走在羊群之前,遇坡它先爬坡,遇河它先过河。羊群始终跟着它行走,它也始终在判断着前面的方向和道路的情况。
阔加拜说,它是一只头羊,正是因为有了它对羊群的引领,走在后面的牧人也就不用再操心了。细看这只头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和羊群中的任何一只都一模一样。于是我问阔加拜:“什么样的羊才能当头羊?”
他笑了笑说:“任何一只羊都可以当头羊,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过了一会儿,那只头羊有了变化,它先是显得有些气力不支,继而放慢了脚步,羊群随着它的变化也有了变化,显得散乱起来。这时候,羊群中走出一只羊及时接替了它。那只羊接掌了头羊的重任,领着羊群又往前走去。
要过河了,仍然是头羊先下水。它边探边走,试出一条有石头的过河路。羊群站在河边,等着它探出一条河中路。头羊走到中间时突然一下子踩入深水中,水淹至它的头部,它扑腾几下游了出来,但已没有力气再向前,只好返回。另一只羊马上进入河中,它巧妙地躲过了刚才的深水,但没走几步,又在一块石头上滑倒了,不得不返回。第三只羊及时踏入河中,躲过前面两只羊陷入过的危险区,又向前走了几米,但它还是滑倒了,被冲出很远才爬上岸。第四只羊像是憋着一股劲儿似的,“扑腾”一声跳进河中,绕过前面几只羊失蹄的地方,顺利地上了岸。后面的羊们都已看得明明白白,沿着它探出的路一一过了河。四只羊前赴后继,用头羊的精神探出了一条过河的路。当所有的羊上岸后,最后一次探路成功的羊当仁不让地当起了头羊。
至此,我才明白,头羊因为要观察路线和方向,还要带领羊群前行,所以比别的羊要多耗去些力气。当一只头羊累了的时候,总会有另一只羊及时补上,羊群因此才会一直走向牧场,而走在最前面带路的,总是一只和任何一只羊没什么两样的头羊。
赛力克家的地窝子
每年的8 月至9
月,是牧人们上山给家畜们打草储备冬料的季节。之后不久,严冬就到来了。在阿勒泰远冬牧区,一年中有一大半时间是严寒的冬季。从沙吾尔山走上几公里,也看不到一个人和一座毡包。
但在这样的严寒天气,牧人们的放牧却照样持续。山上没有电,牧人们习惯早睡早起。每天清晨,他们早早起来,一推开毡帘,看到的是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羊圈的木围栏,嘴里含混着像魔咒一样的特别用语。羊群听懂了呼唤,奔出围栏。自由、清凉的晨风将它们身上的毛吹得蓬松,看上去就像一串棉毛球一样滚动。稀疏的灌木丛在风中摇动,在雪中挺立着尖利的根茎。羊群此起彼伏的咩咩声已飘得很远,留下的蹄印似乎是永远擦不掉的东西,给寂寞和荒凉的冬牧场增添了几分生机。
牧人们一大早就穿上厚厚的羊皮大衣、羊皮裤子,戴上羊皮帽子,开始了一天的放牧生活。晚上,他们哈着一嘴白气从毡房外进来,肩上落了一层晶莹的雪粒,笑容是那样的纯朴。在这片遥远、苍茫的雪原中,牧人的身姿并不显得渺小。相反,雪原因了牧人和羊群的嵌入而有了些许人间气息。
在一个牧人的“地窝子”门口,一只牧羊犬围着我狂吠。它变着花样儿吠叫,把自己叫成一群狗的阵势。等我们从屋子里出来时,它却已经无影无踪。天色将暮,毡房外,无尽雪原的风飒飒作响,周围是狗、羊、马的粪便。这一切在夕阳的映衬下,都彰显出一种自然和谐的勃勃生机。
这是牧人赛力克家的地窝子。像别的哈萨克族牧人家庭一样,赛力克与妻子帕娜尔把老人们留在温暖的瓦房里过冬,自己则赶着羊群从300
公里外的苏木凯木夏牧场来到了沙吾尔冬牧场,也就是冬窝子。在这片平坦的阿勒泰南部地区,他们将度过整整大半年的寂寞时光。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赛力克与帕娜尔身边多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阿尔曼,一个面目清秀的男孩,刚刚5 个月大。
阿尔曼出生在到处绿油油的苏木凯木夏牧场。夏牧场青草茂盛,牛羊肥壮,牧人们住得安稳,消磨着悠闲的盛夏时光。很快,去沙吾尔冬牧场的时间到了。通常,从苏木凯木夏牧场向沙吾尔冬牧场靠拢,要赶着羊群沿途颠簸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搬24
次家才能到达。出发时,牧道上羊群欢鸣,烟尘腾起;渐渐地,寒潮逼近,四野茫茫的冰雪世界出现在眼前。
这一次在转场前,赛力克家的母牛生下了一只可爱的小牛犊。当他们走出夏牧场时,这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牛犊走不动路,蜷伏在路边。帕娜尔只好把它背在背上,但是走了一会儿,发现路太难走了,于是她把小牛犊放进一峰骆驼背上的筐子里,而另一个筐子里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阿尔曼。驮着婴儿的骆驼,背着小牛犊或小羊羔的哈萨克族妇人,这种奇妙场景在转场途中是常见的。只不过,赛力克家这次转场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骆驼的背上既有小牛犊,又有小婴儿。小牛犊一脸神秘的神情,与婴儿阿尔曼不时地对望,并各自伸出头东张西望地看着路边的景色。
筐子在骆驼背上摇晃,母牛跟在骆驼身边不肯离去,常常在骆驼趴下休息的间隙凑上去舔小牛犊的脸。
为了迎接阿尔曼的到来,赛力克与哥哥用了4
天时间在冬牧场挖了一个地窝子——这埋入冻土下的土房子拙朴的模样快要被外界遗忘了,却出奇地结实、御寒。
一扇窄窄的木门被钉上了厚实的毛毡,粗糙的木桩支撑着低矮的泥面屋宇,柔和的光束穿过一片巴掌大的窗玻璃斜射在泥墙上,光线中有粗大的颗粒在移动。泥屋子里充满了羊肉、泥土、薄雪、柴火、婴儿的奶香等气息,温暖而又炽烈。
木门的开合间,升腾起一股浓重的水汽。女主人低下身子,往炉膛里塞入刚打好的梭梭柴,晶莹的冰粒碎屑还停留在灰黑的枝杆上。炉子里飘着淡蓝色的火焰,长长的铁皮烟筒一端伸向炉口,另一端拐弯伸向窗外,烟雾已经将屋檐熏得发黑。
她轻盈地弯下腰,端去铝锅,用木棍从炉子里拨出了就要燃尽的木柴。午后的空气中一点点散发出某种细碎的甜蜜,越来越浓,是久违的底层生活的味道。
在这个拥有婴儿哭笑声的地窝子里,有着生活的真实和温暖。生活,哪怕再艰辛、再清贫,都充满简单的幸福。这对年轻夫妇在这不为人知的小角落里过着平凡的生活,他们的幸福你羡慕吗?
从去年9
月到现在,地窝子里没有什么客人造访。看得出来,女主人帕娜尔对我的到来显得很激动。她摊开布单,“哗啦”一下魔术般地摊开一大堆用羊油炸好的包尔撒克(油炸面果子)。
“帕娜尔”在哈萨克语里是“马灯”的意思。帕娜尔家的毡包与赛力克家的毡包相隔20
多公里,但用他们的话说,却可以算是“邻居”。而帕娜尔与赛力克初中毕业后都没能继续上学,他们各自放牧和转场,经常在放牧和转场的途中相遇,于是,两个青春萌动的年轻人“好”上了。后来,他们干脆把两家的羊群合在一起——结婚了。
婴儿降生,羊只增多,平凡而温暖的生活就这样持续了下来。赛力克对新盖好的地窝子感到很满意。“这也算是正式在冬牧场‘定居’了吧。”赛力克特意强调“定居”这两个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