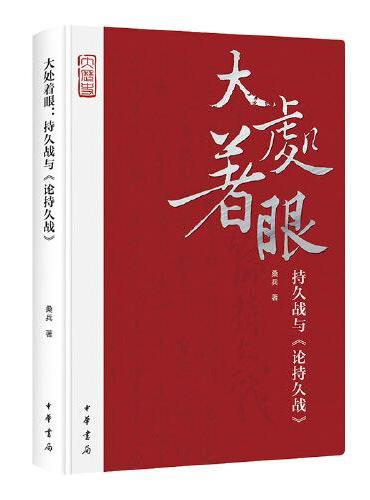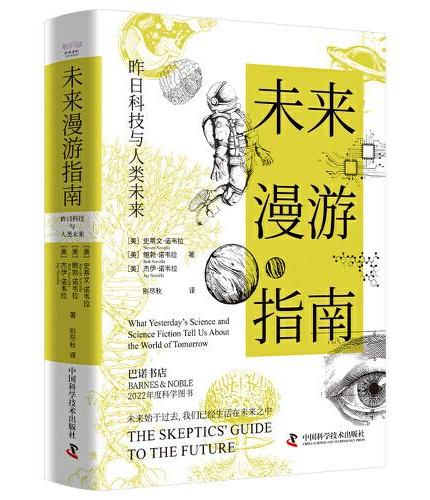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传统文化有意思:古代发明了不起
》
售價:NT$
199.0

《
无法从容的人生:路遥传
》
售價:NT$
340.0

《
亚述: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的兴衰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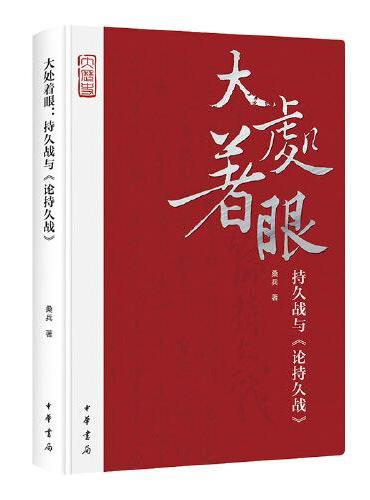
《
大处着眼:持久战与《论持久战》
》
售價:NT$
390.0

《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采煤机智能制造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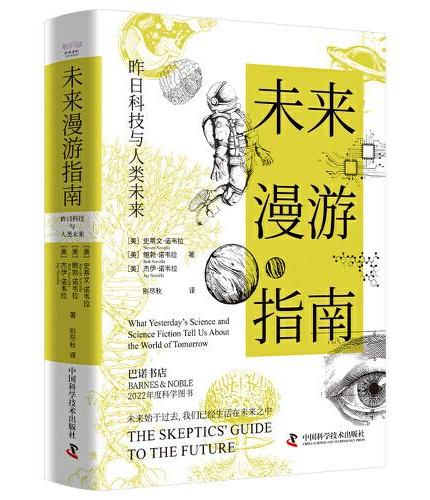
《
未来漫游指南:昨日科技与人类未来
》
售價:NT$
445.0

《
新民说·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上下册)
》
售價:NT$
790.0

《
我从何来:自我的心理学探问
》
售價:NT$
545.0
|
| 編輯推薦: |
|
《詹姆斯·M·凯恩作品:幻世浮生》与《邮差总按两遍铃》一样,《詹姆斯·M·凯恩作品:幻世浮生》也是美国出版史上的超级畅销书,对于美国“黑色文学电影”的传统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而在这种类型中,也很难找到真正超越它们的作品。根据《詹姆斯·M·凯恩作品:幻世浮生》改编的电影获1945年奥斯卡奖六项提名,由琼·克劳馥摘取最佳女主角奖,张爱玲的《小团圆》中也提到过这部当时引起轰动的电影。根据《詹姆斯·M·凯恩作品:幻世浮生》改编的电视剧获2011年艾美奖二十一项提名,由凯特?温丝莱特摘取最佳女主角奖。
|
| 內容簡介: |
|
故事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开始。中产主妇米尔德里德与丈夫伯特之间的婚姻危机因为经济形势的陡然紧张而加剧,不得不黯然分手。米尔德里德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屡次因为失业而几乎山穷水尽。支撑着她的动力是大女儿维妲漂亮聪颖的天资、过人的音乐才华和某种似乎超越她现有阶层的傲人气质。为了维妲,米尔德里德点燃了自己所有的能量——无论是当侍应还是开店,抑或利用自己的美貌勾引男人,最终都是为了成全维妲的野心。然而,米尔德里德渐渐发现自己一步步走进了自挖的陷阱。维妲究竟是亟需一双翅膀的天使,还是回过头就会咬恩人一口的毒蛇?抑或,她两者都是?
|
| 關於作者: |
詹姆斯·M·凯恩,1892年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写作生涯从记者开始,历任《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报道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驻法国的战地记者,《纽约世界报》编辑,以及《纽约客》执行主编,此后一度在好莱坞担任编剧。在编剧合同到期,开车逛遍了南加州,并写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惊悚短篇之后,在著名出版人诺普夫的鼓励下,他开始写那本即将改变他一生的小说。
无论用什么语言来形容《邮差总按两遍铃》在当时获得的成功以及此后长销不衰的状况,都不算过分。文学史家认为它“或许是美国出版史上第一部超级畅销书”,而且是当之无愧的“黑色文学电影”的开山鼻祖——而在这种类型中,也很难找到真正超越《邮差》的作品。这部短短的小说位列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曾被四次搬上银幕。《邮差》之后,凯恩又创作了两部风格相近的黑色小说《双重赔偿》和《幻世浮生》(又译作《欲海情魔》),根据这两部小说的电影都成为影史经典。1977年,凯恩以85岁高龄逝世。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这是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在加利福尼亚州格兰岱尔市的一片草坪上,一个男人正在加固树木。这是个让人厌烦的活儿,他先得剪掉枯枝,再用帆布条裹住细弱的树枝,然后把绳套缠在布条上,和树干捆在一起,这样等到秋天鳄梨成熟的时候就能承受果实的重量了。虽然这是个炎热的下午,可他仍然不慌不忙,活儿干得一丝不苟,还吹着口哨。他有三十四五岁,个子不高,那条裤子虽然有些污渍,但穿在他身上却别有一种自然风度。他的名字叫赫伯特?皮尔斯。他收拾好了那些树,又把枝枝叉叉还有枯死的树枝耙成一堆,抱回到车库,丢进一个盛柴火的箱子里。接着,他拿出割草机开始修剪草坪。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地区,有成千上万处这样的草坪:一片草地上栽种着鳄梨、柠檬和含羞草,树木周围用铁锨围起一圈圈的土。房子的样式也司空见惯,是西班牙式的平房,白色墙壁配以红瓦屋顶。现在,西班牙式的房子有点儿过时了,但在当时看来却很是高雅漂亮,这座房子和它后面的一座不相上下,也许还要好上那么一点点。
他割完草,又拿出一卷软管,固定在一个水龙头上,开始浇水。这活儿他也做得很精心,把水喷洒到树上、培成一圈的泥土上,还有铺上地砖的小路上,最后还浇灌了草坪。等到整片地方湿漉漉的,散发出一股雨水的气息,他这才关上水龙头,把软管从手里一点点拽过来,让水流出去,然后盘起软管,放进车库。他又绕到前面看了看那些树,确信浇上的水没有让布条绷得太紧,就进了屋。
他走进的客厅正对着草坪,看上去真像是商场里摆设的那种为西班牙风格的房子量身定做的客厅样板间:深红色天鹅绒制成的盾形纹章陈列在墙上,深红色天鹅绒窗帘挂在铁艺杆上;深红色的小地毯镶有富丽的花边;壁炉前摆放着一张有靠背的长椅,两侧各有一把椅子,都带着笔直的靠背和串珠椅垫;一张长长的橡木桌子上有盏台灯,罩着彩色玻璃灯罩;另外两盏铁艺落地灯和上方的铁艺窗帘杆倒是很相衬,灯上罩着深红色的丝绸灯罩;房间的一角有张桌子,样式颇有大急流城
的风格,桌上有一台贝克莱特式收音机
。漆成浅色的墙上,除了那个盾形纹章以外,还有三幅画:一幅是落日余晖中的孤峰,突出的前景是几个牛骨架;另一幅是一个牛仔赶着牛群穿过雪地,还有一幅是一列车厢带顶篷的火车艰难地驶过盐碱滩。长条桌案上有一本烫金封面的《实用知识百科全书》,斜放在那儿很引人注目。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客厅既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又有窒闷的气息,二者的结合堪称一绝,住在里面会非常压抑。但这位男主人还隐隐有点儿引以为豪的意思,特别是那些油画,他自己确信称得上“相当不错”。至于住在里面的感觉,他倒从来没有想过。
今天,他看也没看一眼,也压根儿没去想,就匆匆忙忙穿过客厅,一路吹着口哨回到卧室。卧室里满满当当地摆放着一套明亮的绿色七件套组合家具,显出一派柔和的女性格调。他把工作服脱下来,挂进一个壁橱,然后赤裸着身子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冲了个淋浴。这里再次映射出他所生活的文明世界,但却有一种强烈的反差。因为,尽管这个文明世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草坪、客厅、油画和其他具有审美情趣的物件上都表现得有些幼稚,但就实用性而言,它本身就代表一种天才智慧,它所遗忘的比其他所有文明世界一直以来所了解的还要多。此时,他正在浴室里吹着口哨,这浴室本身就是一件有实用价值的珍品:它是用绿色和白色相间的瓷砖镶拼而成,简直跟手术室一样洁净,里面的一切都井然有序,而且都在正常运转。他拧上水龙头,过了二十秒,又跨进浴缸,水温正合他意。他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拧开排水管,跨出浴缸,用一块干净毛巾擦干全身,又回到卧室里,这段时间他一直吹着口哨,曲调没有一点儿间断,他完全是漫不经心,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梳好头发,开始穿衣服。这次他没有穿宽松的便裤,而是一条灰色的法兰绒裤子:他新换了一条,配上一件开领短袖衬衫,还有一件样式很随意的外套。然后,他溜溜达达地回到厨房里,厨房正对着浴室,他太太正在那儿给一只蛋糕涂糖霜。那是个身材娇小的女人,看样子比他年轻许多;不过,这时候她的脸颊沾上了巧克力,身上穿一件宽松的绿色罩衫,很难看得出来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只能看见罩衫和鞋子之间露出两条非常性感的腿。她正在研究一本蛋糕设计书里的某一款图案,是一只鸟儿嘴里叼着卷轴,眼下她正试着用铅笔在便签纸上仿照着画下来。他瞧了一会儿,瞟了一眼那个蛋糕,说了声看起来棒极了。这话大概只能算是轻描淡写,因为那个蛋糕实在是太大了,直径有十八英寸,四层高,笼罩着丝绸一般的光泽。不过,发表完评论之后,他打了个哈欠说:“嗳——我看这儿也没什么我能做的。那我就到街上走走了。”
“你回家吃晚饭吗?”
“我尽量赶上,不过,要是我六点以前没回来,就别等我了。我也许会被什么事儿绊住。”
“我想知道。”
“我告诉你了,要是我六点以前没回来……”
“这对我来说等于什么也没说。我现在正在给惠特利太太做蛋糕,为这个她会付给我三美元。要是你在家,我还得把其中一部分钱花在你晚餐吃的羊排上。要是你不在家,我就能买些孩子们更喜欢的东西。”
“那就别把我算进去了。”
“我就想知道这个。”
此情此景有一种阴冷的调子,显然和他的心情不合拍。他犹犹豫豫地闲站在那儿,试图得到几句夸奖。“我把树都加固了。捆得结结实实,这样等鳄梨长大的时候就不会把树枝压弯,就跟去年一样。我还修剪了草坪。外面看起来相当不错呢。”
“你打算给草坪浇水吗?”
“我已经浇过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带着点儿洋洋得意的味道,因为他给她设下了一个小小的陷阱,她恰恰掉了进去。不过接下来的沉默是个有点儿不大好的征兆,就像是他自己跌进了一个陷阱,还浑然不觉。他局促不安地加了一句:“浇得透透的。”
“这会儿给草坪浇水早了点儿吧,难道不是吗?”
“哦,什么时候浇水都差不多吧。”
“大多数人都是等到晚些时候,太阳不那么热了,才给草坪浇水,这么做大有好处,不会把好端端的水给浪费掉,那可是别人要花钱的。”
“比方说谁?”
“我看在这个家里除了我没谁在干活儿。”
“你见过有什么活儿我本来能干可就是不干吗?”
“这么说你及早就把活儿干完了。”
“说吧,米尔德里德,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正等着你呢,赶快去吧。”
“谁在等我?”
“你看你自己心里清楚。”
“如果你说的是玛姬?比德霍夫,我都有一个星期没见过她了,她对我来说,不过我没别的事儿可干的时候一块儿打打拉米纸牌
的玩伴,如此而已,没别的。”
“那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时间,要是你问我的话。”
“我压根儿就没问你啊。”
“你都和她干些什么?跟她玩儿一会儿拉米纸牌,然后就解开她老是连胸罩也不穿在里面的那条红裙子,把她抛到床上?接着呢,你自己美美地睡上一觉,然后起身看看她的冰箱里有没有冷鸡肉,接着呢,再玩儿一会拉米纸牌,然后再把她抛到床上?嘿,那一定爽得很吧。我简直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那更来劲的事儿了。”
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看得出来,他的火正直往上冒,他张了张嘴要说什么,却又改了主意。过了一会儿,他做出一副甘拜下风的高姿态,说:“噢,好吧。”然后就开始往厨房外面走。
“你不要给她带点儿什么吗?”
“给她带……?你这是什么意思?”
“哦,还剩了点儿面糊,我就做了几个小蛋糕留给孩子们吃。她长得那么胖,一定喜欢吃甜的,好了——就在这儿呢,我来给她包起来。”
“见你的鬼去吧。”
她把那张描画着鸟儿的草图放到一边,直视着他。关于爱情、忠实,还有道德,她已经无话可说。她说的是钱,还有他找不到工作的事儿;当她提到他找的那个女人,并不是把她当作一个妖妇,窃取了他的爱情,而是作为造成他最近游手好闲的原因。他不断插嘴为自己辩解,一个劲儿地说根本没有工作可找,还忿忿不平地硬是说,要是比德霍夫太太和他一起生活,他起码会得到片刻安宁,而不是为一些他根本无法掌控的事情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他们的语速都很快,仿佛说出的话烫嘴似的,得赶紧吐出去好让嘴巴冷却下来。说真的,这种丑陋的情景由来已久,堪称经典,他们这种互相指责自从有婚姻以来就一直不断上演,而且他们的争吵毫无新意,更没有任何美感可言。过了一会儿,他们停了下来,他又要往厨房外面走,却被她叫住了,“你要到哪儿去?”
“我要告诉你吗?”
“你是不是要去玛姬?比德霍夫那儿?”
“就算我要去那儿又怎么样?”
“那你干脆还是马上收拾东西走人吧,永远也别再回来,因为如果你出了这个门,我就不让你再回来。要是你逼得我非得用这把切肉刀对着你,你就别想再回到这个房子里来。”
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那把切肉刀,举起来,又放了回去,他在一旁看着,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接着来啊,米尔德里德,尽管接着来。你要是不当心点儿,说不定哪天我会骂你一通。我才不在乎离开你呢,我马上就走。”
“你别想骂我,我骂你还差不多。今天下午你要是去找她,这就是你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家。”
“老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那就收拾东西吧,伯特。”
他脸色变得煞白,两个人对视了很久。“那好吧,我走。”
“你最好现在就走。越快越好。”
“好……好吧。”
他昂首阔步走出厨房。她往一个锥形纸袋里装满糖霜,咔嚓一声用剪子剪下底端,开始往蛋糕上涂画那只鸟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