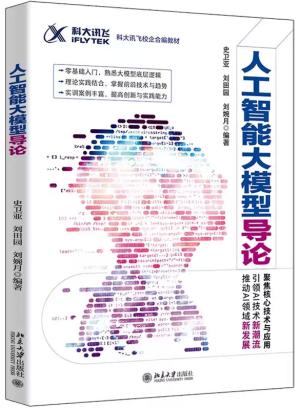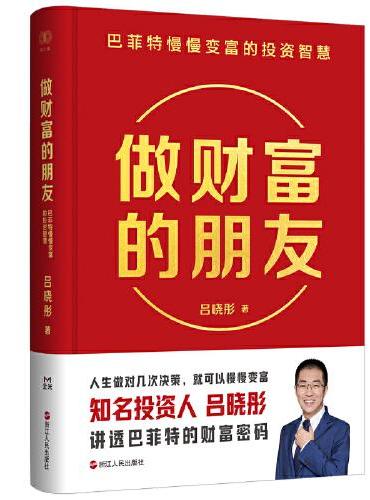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NT$
454.0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NT$
347.0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NT$
352.0
《
纸上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破译古老文明的密码,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150+资料图片)
》 售價:NT$
398.0
《
米塞斯的经济学课:讲座与演讲精选集
》 售價:NT$
347.0
《
人工智能大模型导论 科大讯飞校企合编教材
》 售價:NT$
352.0
《
做财富的朋友:巴菲特慢慢变富的投资智慧
》 售價:NT$
383.0
《
一群数学家分蛋糕:提升逻辑力的100道谜题
》 售價:NT$
281.0
內容簡介: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很多当今的中国人来说,1978
關於作者:
刘香成,1951年生于香港,1975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人文和政治科学系,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內容試閱
刘香成的中国摄影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