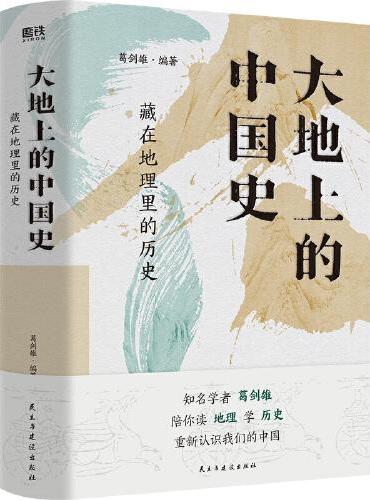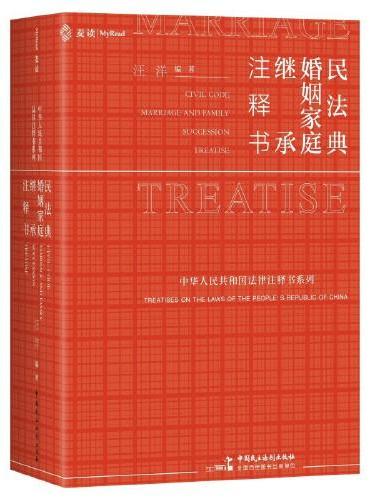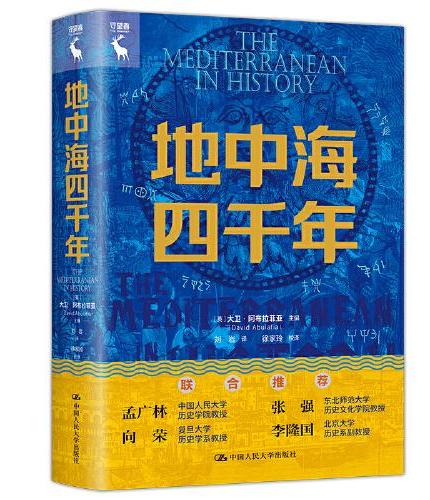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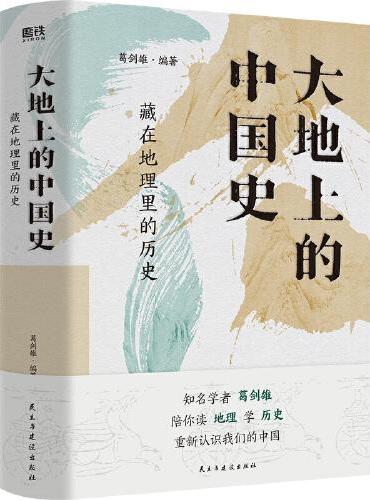
《
大地上的中国史:藏在地理里的历史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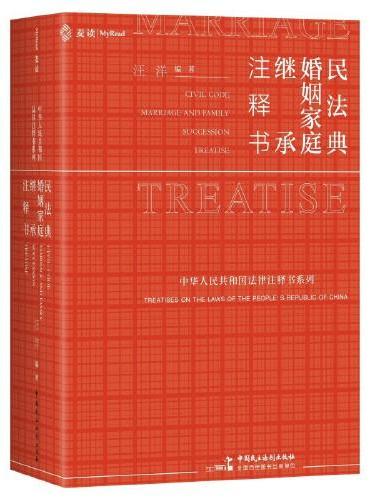
《
《民法典·婚姻家庭继承注释书》(家事法专用小红书,一书尽揽现行有效办案依据:条文释义+相关立法+行政法规+地方立法+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地方法院规范+权威案例,麦读法律54)
》
售價:NT$
6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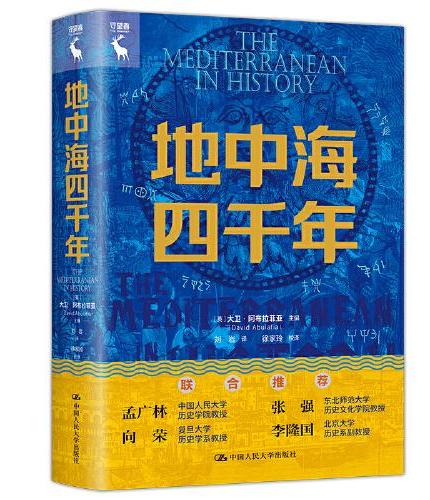
《
地中海四千年
》
售價:NT$
857.0

《
君子至交:丁聪、萧乾、茅盾等与荒芜通信札记
》
售價:NT$
316.0

《
日和·缝纫机与金鱼
》
售價:NT$
194.0

《
金手铐(讲述海外留学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挣扎、收获与失去)
》
售價:NT$
347.0

《
五谷杂粮养全家 正版书籍养生配方大全饮食健康营养食品药膳食谱养生食疗杂粮搭配减糖饮食书百病食疗家庭中医养生药膳入门书籍
》
售價:NT$
254.0

《
七种模式成就卓越班组:升级版
》
售價:NT$
296.0
|
| 編輯推薦: |
★ 可是我对这本小书(《小坡的生日》)仍然最满意,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深喜自己还未全失赤子之心。
最使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简明浅确。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真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敢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
希望还能再写一两本这样的小书,写这样的书使我觉得年轻,使我快活: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
——老舍
老舍是中国现代优秀的作家,《骆驼祥子》、《茶馆》、《二马》……一部部耳熟能详的作品都出自他之手。可是或许很多人并不了解,在中国儿童文学兴起之初,老舍也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童话作品和儿童题材小说,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殿堂涂上了不一样的颜色。这些作品生动有趣,深入浅出,诙谐幽默,充满童真童趣,具有老舍文学作品的一贯水准,也更适合孩子的阅读。阅读这些作品,帮你了解一个《骆驼祥子》之外另一个老舍,
★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对老舍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梳理和展示,了解《骆驼祥子》之外别一个老舍;
★还是那个老舍,同样的幽默,同样的风趣,一片赤诚之心,深入浅出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最适合孩子的阅读;
★听“孩子头儿”老舍给你讲故事,奇妙的童年乐
|
| 內容簡介: |
|
《小坡的生日》是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对老舍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梳理和展示,帮你了解《骆驼祥子》之外别一个老舍。全书分为“童话”和“小说”两辑,收入了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短篇童话《小木头儿》,儿童小说《小坡的生日》三部作品,除了具有老舍作品一贯的温情和幽默,更具有强烈的童真童趣,让人忍俊不禁,不忍掩卷。
|
| 關於作者: |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曾荣获“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被誉为“语言大师”。
老舍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二马》、《猫城记》、《离婚》,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剧作《茶馆》、《龙须沟》等,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构佳作。他的作品多取材于市民生活,幽默风趣,形象生动,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生活情趣,被誉为“深度、激情和幽默都是世界性的、超越国界的”。
老舍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小坡的生日》、《小木头人》、《小铃儿》等,具有老舍作品惯有的机智幽默、温情诙谐的特点,又充满童真童趣,读来让人爱不释手、回味无尽。
|
| 目錄:
|
童话
《小坡的生日》
《小木头人》
小说
《小铃儿》
|
| 內容試閱:
|
小铃儿
京城北郊王家镇小学校里,校长、教员、夫役,凑齐也有十来个人,没有一个不说小铃儿是聪明可爱的。每到学期开始,同级的学友多半是举他做级长的。
别的孩子入学后,先生总喊他的学名,惟独小铃儿的名字——德森——仿佛是虚设的。校长时常地说:“小铃儿真像个小铜铃,一碰就响的!”
下了课后,先生总拉着小铃儿说长道短,直到别的孩子都走净,才放他走。那一天师生说闲话,先生顺便地问道:“小铃儿,你父亲得什么病死的?你还记得他的模样吗?”
“不记得,等我回家问我娘去。”小铃儿哭丧着脸,说话的时候,眼睛不住地往别处看。
“小铃儿,看这张画片多么好,送给你吧!”先生看见小铃儿可怜的样子,赶快从书架上拿了一张画片给了他。
“先生!谢谢你——这个人是谁?”
“这不是咱们常说的那个李鸿章吗!”
“就是他呀!呸!跟日本讲和的!”小铃儿两只明汪汪的眼睛,看看画片,又看先生。
“拿去吧!昨天咱们讲的国耻历史忘了没有?长大成人打日本去,别跟李鸿章一样!”
“跟他一样?把脑袋打掉了,也不能讲和!”小铃儿停顿一会儿,又继续着说:“明天讲演会我就说这个题目,先生!我讲演的时候,怎么脸上总发烧呢?”
“慢慢练就不红脸啦。铃儿该回去啦!好,明天早早来!”先生顺口搭音地躺在床上。
“先生明天见吧!”小铃儿背起书包,唱着小山羊歌走出校来。
小铃儿每天下学,总是一直唱到家门,他母亲听见歌声,就出来开门。今天忽然变了:
“娘啊!开门来!”很急躁地用小拳头叩着门。
“今天怎么这样晚才回来?刚才你大舅来了!”小铃儿的母亲,把手里的针线扦在头上,给他开门。
“在哪儿呢?大舅!大舅!你怎么老不来啦?”小铃儿紧紧地往屋里跑。
“你倒是听完了!你大舅等你半天,等的不耐烦,就走啦;一半天还来呢!”他母亲一边笑一边说。
“真是!今天怎么竟是这样的事!跟大舅说说李鸿章的事也好哇!”
“哟,你又跟人家拌嘴啦?谁?跟李鸿章?”
“娘啊,你要上学,可真不行!李鸿章早死啦!”从书包里拿出画片,给他母亲看,“这不是他,不是跟日本讲和的奸细吗!”
“你这孩子!一点儿规矩都不懂啦!等你舅舅来,还是求他带你学手艺去,我知道李鸿章干吗?”
“学手艺,我可不干!我现在当级长,慢慢地往上升,横是有做校长的那一天!多么好!”他摇晃着脑袋,向他母亲说。
“别美啦!给我买线去!青的白的两样一个铜子的!”
吃过晚饭,小铃儿陪着母亲,坐在灯底下念书。他母亲替人家作些针黹。念乏了,就同他母亲说些闲话。
“娘啊,我父亲脸上有麻子没有?”
“这是打哪儿提起,他脸上甭提多么干净啦!”
“我父亲爱我不爱?给我买过吃食没有?”
“你都忘了?哪一天从外边回来不是先去抱你,你姑母常常地说他:‘这可真是你的金蛋,抱着吧!将来真许作大官增光耀祖呢!’你父亲就眯睎眯睎地傻笑,搬起你的小脚指头,放在嘴边香香地亲着,气得你姑母又是恼又是笑。——那时你真是又白又胖,着实的爱人。”
小铃儿不错眼珠地听他母亲说,仿佛听笑话似的,待了半天又问道:
“我姑母打过我没有?”
“没有!别看她待我厉害,待你可是真爱。那一年你长口疮,半夜里啼哭,她还起来背着你,满屋子走,一边走一边说:‘金蛋!金蛋!好孩子!别哭!你父亲一定还回来呢!回来给你带柿霜糖,多么好吃!好孩子!别哭啦!’”
“我父亲那一年就死啦?怎么死的?”
“可不是后半年!你姑母也跟了他去,要不是为你,我还干什么活着?”小铃儿的母亲放下针线叹了一口气,那眼泪断了线的珠子般流下来!
“你父亲不是打南京阵亡了吗?哼,尸骨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呢!”
小铃儿听完,蹦下炕去,拿小拳头向南北画着,大声地说:“不用忙!我长大了给父亲报仇!先打日本后打南京!”
“你要怎样?快给我倒碗水吧!不用想那个,长大成人好好地养活我,那才算孝子。倒完水该睡了,明天好早起!”
他母亲依旧作她的活计,小铃儿躺在被窝里,把头钻出来钻进去,一直到二更多天才睡熟。
“快跑!快跑!开枪!打!”小铃儿一拳打在他母亲的腿上。
“哟,怎么啦?这孩子又吃多啦!瞧!被子踹在一边去了,铃儿,快醒醒!盖好了再睡!”
“娘啊,好痛快!他们败啦!”小铃儿睁了睁眼睛,又睡着了。
第二天小铃儿起来得很早,一直地跑到学校,不去给先生鞠躬,先找他的学伴。凑了几个身体强壮的,大家蹲在体操场的犄角上。
小铃儿说:“我打算弄一个会,不要旁人,只要咱们几个。每天早来晚走,咱们大家练身体,互相地打,打疼了,也不准急,练这么几年,管保能打日本去;我还多一层,打完日本再打南京。”
“好!好!就这么办!就举你做头目。咱们都起个名儿,让别人听不懂,好不好?”一个十四五岁、头上长着疙瘩、名叫张纯的说。
“我叫‘一只虎’,”李进才说,“他们都叫我李大嘴,我的嘴真要跟老虎一样,非吃他们不可!”
“我,我叫‘花孔雀’!”一个鸟贩子的儿子,名叫王凤起的说。
“我叫什么呢?我可不要什么狼和虎。”小铃儿说。
“越厉害越好啊!你说虎不好,我不跟你好啦!”李进才撇着嘴说。
“要不你叫‘卷毛狮子’,先生不是说过:‘狮子是百兽的王’吗?”王凤起说。
“不行!不行!我力气大,我叫狮子!德森叫‘金钱豹’吧!”张纯把别人推开,拍着小铃儿的肩膀说。
正说得高兴,先生从那边嚷着说:“你们不上教室温课去,蹲在那块儿干什么?”一眼看见小铃儿声音稍微缓和些,“小铃儿,你怎么也蹲在那块儿?快上教室里去!”
大家慢腾腾地溜开,等先生进屋去,又凑在一块商议他们的事。
不到半个月,学校里竟自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永不招惹人的小铃儿会有人给他告诉 :“先生,小铃儿打我一拳!”
“胡说!小铃儿哪会打人?不要欺侮他老实!”先生很决断地说,“叫小铃儿来!”
小铃儿一边擦头上的汗一边说:“先生!真是我打了他一下,我试着玩来着,我不敢再……”
“去吧!没什么要紧!以后不准这样。这么点儿事,值得告诉?真是!”先生说完,小铃儿同那委委屈屈的小孩子都走出来。
“先生,小铃儿看着我们值日,他竟说我们没力气,不配当,他又管我们叫小日本,拿着教鞭当枪,比着我们。”几个小女孩子,都用那炭条似的小手,抹着眼泪。
“这样子?可真是学坏了!叫他来,我问他!”先生很不高兴地说。
“先生,她们值日,老不痛痛快快的吗,三个人搬一把椅子。——再说我也没拿枪比画她们。”小铃儿恶狠狠地瞪着她们。
“我看你这几天是跟张纯学坏了,顶好的孩子,怎么跟他学呢!”
“谁跟‘卷毛狮’……张纯……”小铃儿背过脸去吐了吐舌头。
“你说什么?”
“谁跟张纯在一块儿来着!”
“我也不好意罚你,你帮着她们扫地去,扫完了,快画那张国耻地图。不然我可真要……”先生头也不抬,只顾改缀法的成绩。
“先生,我不用扫地了,先画地图吧!开展览会的时候,好让大家看哪!你不是说,咱们国的人,都不知道爱国吗?”
“也好,去画吧!你们也都别哭了!还不快扫地去,扫完了好回家!”
小铃儿同着她们一齐走出来,走不远,就看见那几个淘气的男孩子,在墙根站着,向小铃儿招手,低声地叫着:“豹!豹!快来呀!我们都等急啦!”
“先生还让我画地图哪!”
“什么地图,不来不行!”说话时一齐蜂拥上来,拉着小铃儿向体操场去,他嘴直嚷:
“不行!不行!先生要责备我呢!”
“练身体不是为挨打吗?你没听过先生说吗?什么来着?对了:‘斯巴达
的小孩,把小猫藏在裤子里,还不怕呢!’挨打是明天的事,先走吧!走!”张纯一边比方着,一边说。
小铃儿皱着眉,同大家来到操场犄角说道:
“说吧!今天干什么?”
“今天可好啦!我探明白了!一个小鬼子,每天骑着小自行车,从咱们学校北墙外边过,咱们想法子打他好不好?”张纯说。
李进才抢着说:“我也知道,他是北街洋教堂的孩子。”
“别粗心咧!咱们都带着学校的徽章,穿着制服,打他的时候,他还认不出来吗?”小铃儿说。
“好怯家伙!大丈夫敢作敢当,再说先生责罚咱们,不会问他,你不是说雪国耻得打洋人吗?”李进才指教员室那边说。
“对!——可是倘若把衣裳撕了,我母亲不打我吗?”小铃儿站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
“你简直地不用去啦!这么怯,将来还打日本哪?”王凤起指着小铃儿的脸说。
“干哪!听你们的!走……”小铃儿红了脸,同着大众顺着墙根溜出去,也没顾拿书包。
第二天早晨,校长显着极懊恼的神气,在礼堂外边挂了一块白牌,上面写着:
德森张纯……不遵校规,纠众群殴,……照章斥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