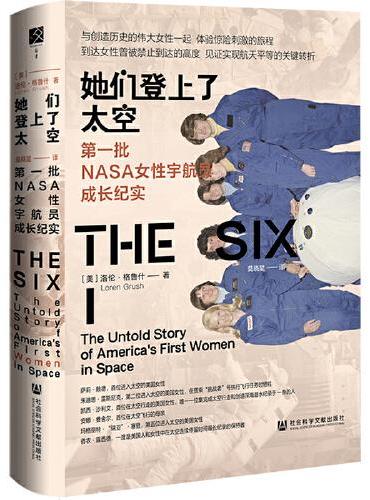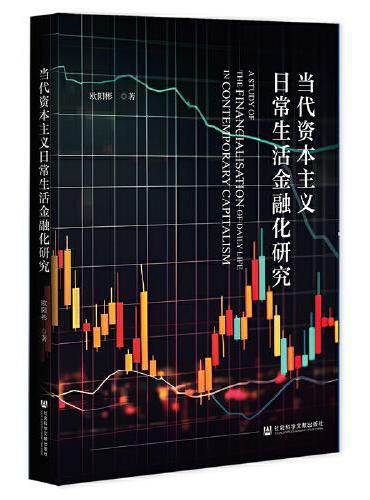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倾盖如故:人物研究视角下的近世东亚海域史
》 售價:NT$
357.0
《
史学视角下的跨文化研究(一): 追踪谱系、轨迹与多样性
》 售價:NT$
485.0
《
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论衡系列)
》 售價:NT$
551.0
《
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革命不是新制度推翻旧制度,而是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殊死斗争!屡获大奖,了解光荣革命可以只看这一本)
》 售價:NT$
1010.0
《
东方小熊日本幼儿园思维训练 听力专注力(4册)
》 售價:NT$
408.0
《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 售價:NT$
500.0
《
她们登上了太空:第一批NASA女性宇航员成长纪实
》 售價:NT$
500.0
《
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金融化研究
》 售價:NT$
653.0
編輯推薦:
某些读者以为加缪的哲学代表了悲观与绝望,那只是肤浅的见解。其实,它充满信念,企图唤醒人类对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们的时代回复了加缪的呼吁,1957年推举他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此实不足为奇。
內容簡介:
傅佩荣教授集中于加缪的核心思想展开讨论,分析此一核心思想在加缪整个思想历程中的发展和成熟过程。这一核心思想就是“生命是荒谬的”。
關於作者: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比利时鲁汶大学、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
目錄
第一篇
內容試閱
1960年1月4日,阿尔伯?加缪(Alb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