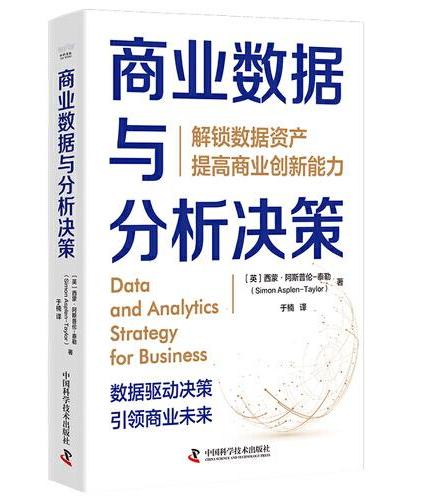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MySQL版)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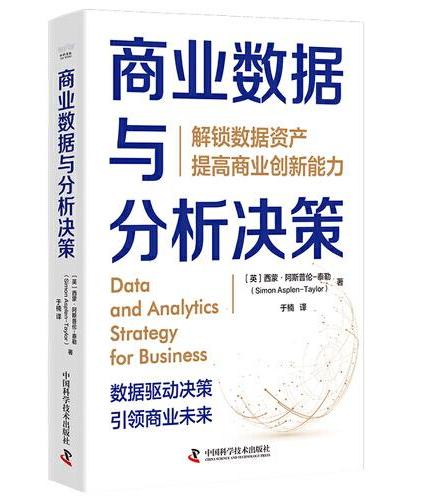
《
商业数据与分析决策:解锁数据资产,提高商业创新能力
》
售價:NT$
367.0

《
倾盖如故:人物研究视角下的近世东亚海域史
》
售價:NT$
357.0

《
史学视角下的跨文化研究(一): 追踪谱系、轨迹与多样性
》
售價:NT$
485.0

《
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论衡系列)
》
售價:NT$
551.0

《
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革命不是新制度推翻旧制度,而是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殊死斗争!屡获大奖,了解光荣革命可以只看这一本)
》
售價:NT$
1010.0

《
东方小熊日本幼儿园思维训练 听力专注力(4册)
》
售價:NT$
408.0

《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
售價:NT$
500.0
|
| 編輯推薦: |
|
《大卫·科波菲尔》是文学大师狄更斯自传性经典,充满了温情的杰出的成长小说。启示我们在残酷的现实之下,如何认识自己,努力向上,获得幸福和真爱。原版插图本,非常吸引人。
|
| 內容簡介: |
|
《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自传性的经典作品。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是个身世不幸的遗腹子,年轻柔弱的母亲改嫁,大卫的继父对他们进行了虐待,不久,母亲和刚出生的婴儿死去,而大卫沦为孤儿,被送去当童工,早早丢失了童年,饱尝人世的艰辛。他决定投奔姨奶奶,开始新的生活。经历了种种世事变迁、悲欢离合,大卫?科波菲尔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并获得真爱和幸福。《大卫·科波菲尔》这部杰出的成长小说始终贯穿着友爱、善良、坚强,甚为感动人心,是优秀的人生教科书,生命力永恒。
|
| 關於作者: |
[英]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伟大小说家。他的作品生动有力,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至今畅销不衰。代表作有《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双城记》《远大前程》《雾都孤儿》等。
|
| 目錄:
|
第一章 我降生人世
第二章 我初识人世
第三章 我换了个环境
第四章 我陷于屈辱境地
第五章 我被送出家门
第六章 我扩大了交往圈
第七章 我在萨伦学校的“第一学期”
第八章 我的假期,尤其是一个快乐的下午
第九章 我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第十章 我遭受遗弃,但有了另一种安排
第十一章 我开始独自谋生,但并不喜欢
第十二章 我仍然不喜欢独自谋生,于是下了大决心
第十三章 我下了决心之后的遭遇
第十四章 姨奶奶就我的事情做出了决定
第十五章 我从头再来
第十六章 我在很多方面成了新生
第十七章 又见故人
第十八章 回顾一段往事
第十九章 我环顾四周,结果有所发现
第二十章 斯蒂尔福思的家
第二十一章 小埃米莉
第二十二章 故地新人,物是人非
第二十三章 我支持迪克先生的看法,并且选择了职业
第二十四章 我最初的放纵行为
第二十五章 天使与魔鬼
第二十六章 我坠入情网
第二十七章 汤米·特拉德尔
第二十八章 米考伯先生发出挑战
第二十九章 重访斯蒂尔福思家
第三十章 损失——巴吉斯离世了
第三十一章 更大的损失——埃米莉出走了
第三十二章 踏上漫漫旅途
第三十三章 享受快乐时光
第三十四章 姨奶奶把我吓了一大跳
第三十五章 意志消沉
第三十六章 热情洋溢
第三十七章 一点儿凉水
第三十八章 合作关系解体
第三十九章 威克菲尔德与希普
第四十章 浪迹天涯
第四十一章 多拉的两位姑妈
第四十二章 挑拨离间
第四十三章 再回顾一段往事
第四十四章 我们料理家务
第四十五章 迪克先生践行了姨奶奶的预言
第四十六章 消息
第四十七章 玛莎
第四十八章 料理家务
第四十九章 我如堕五里雾中
第五十章 佩戈蒂先生梦想成真
第五十一章 踏上更加漫长的旅程
第五十二章 我为一次大爆发推波助澜
第五十三章 还要回顾一段往事
第五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交易
第五十五章 暴风骤雨
第五十六章 新伤旧痕
第五十七章 移居国外的人
第五十八章 离家远行
第五十九章 远行归来
第六十章 阿格尼斯
第六十一章 我面对两个有趣的悔罪者
第六十二章 一盏明灯照亮我的人生之路
第六十三章 故人登门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
| 內容試閱:
|
"第三章
我换了个环境
我猜想啊,车夫的那匹马是世界上最懒散的,一路上低着头,磨磨蹭蹭,似乎存心要让那些收接邮件的人久久等待。我还真就有这么一种感觉,马有时候会因为自己的这个意愿而笑出声来,但车夫说,马只是患了咳嗽的毛病。
车夫也像他的马一样,低垂着头,两只胳膊一边一只搁在膝盖上,边赶车边露着一副睡眼蒙眬的样子。我说的是“赶车”,实际上我觉得,没有他在,马车也照样能到达雅茅斯,因为所有的活儿马全包了。至于说到交谈,他压根儿没有这个兴致,只会吹吹口哨。
佩戈蒂捧了一篮点心放在膝盖上。即便我们乘着这辆马车要到伦敦去,路上的食物也够我们吃的。我们吃了很久,也睡了很多。佩戈蒂老是把下巴颏支在食物篮的提手上面睡觉,但她抓得牢牢的,没有松开过手。要不是亲耳听到,我简直不会相信,一个孤弱无助的女人鼾声竟然打得这么响亮。
我们途中拐进了好多回小路,给一家酒馆送了一副床架占去了很长时间,还去了另外几个地方,弄得我都厌烦了,后来很高兴终于到达了雅茅斯。我朝河对岸那一片广袤的荒滩地看过去,感觉那地方像海绵一样,相当松软潮湿。我不禁感到惊奇,如果世界真的如同我的地理书上所描述的那样是圆形的,那为什么有些地方这么平坦呢?但是,我又想到,雅茅斯或许是处在两极之间,这样就解释得通了。
我们到了更近处,看到四周的景致形成一条低垂的直线,置于天空之下。我给佩戈蒂提示说,要是有一处小山丘什么的,景致或许就会改观了。而如果这片土地与大海相隔得更远一些,城镇和海潮不像是水浸面包似的混到一起,那景致也会更加壮观。可佩戈蒂说,语气比平常还要重,我们应当入乡随俗,而在她的心目中,她为把自己称作“雅茅斯熏鱼”而自豪。
我们到了街上(我对那儿的一切都很陌生),闻到了种种味道,有鱼的、沥青的、填絮的和焦油的。看到了水手到处走动着,还有马车在石板地上来回辘辘前行,这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刚才对这样一个繁忙的地方评价有失公允。于是,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佩戈蒂,她听了非常高兴,异常得意,并且告诉我,众所周知(我想是对那些有幸生来就被称为“雅茅斯熏鱼”的人而言),总的说来,雅茅斯是天底下最美的地方。
“看,我们家阿姆!”佩戈蒂大叫了起来,“长得都认不出来啦!”
哈姆在酒馆门口等我们,像个老相识一样对我嘘寒问暖。刚一开始,我对他的感觉不像他对我那样熟悉,因为自从我降生的那个夜晚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到过我们家,所以我自然没有他那种感觉。不过,他背着我往家里走,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密切了起来。他身高六英尺,体形硕大,身体强壮,肩宽腰圆,但长着一张孩子脸,堆满了憨笑,一头淡色鬈发看上去像只绵羊。他身穿帆布外套、一条硬邦邦的裤子,即使不把腿伸进去,也可以立得住。说他戴了帽子并不确切,倒是应该说像一座老房子上盖着个漆黑的屋顶。
哈姆背着我,胳膊下还夹着我们的一只小箱子,佩戈蒂提着我们的另一只小箱子。我们穿过了几条巷子,到处有碎木片和小沙堆。途经了很多地方,如煤气厂、制缆厂、小船厂、大船厂、拆船厂、堵船缝厂、配件厂、铁匠铺,等等。最后,终于来到了那片我在远处就已经看到的荒滩。哈姆这时候说:
“大卫少爷,那就是我们家!”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极目远眺了荒野,看到了远处的大海、远处的河流,但就是没有看到房屋。不远处,倒是有一艘漆黑的驳船,或者是另一种什么废置的旧船,高高地搁置在干燥的地面上,一节像铁漏斗一样的东西向上突出,当作烟囱,正冒着热烘烘的烟。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可以住人的地方。
“你说的是那个吗?”我说,“那个像船一样的东西?”
“没有错,大卫少爷。”哈姆回答。
住在船里面这种想法充满了浪漫色彩,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即使是阿拉丁的宫殿、神鹰之蛋什么的,也不可能使我如此着迷。船的一侧开了一扇很有趣的门,还加了个屋顶,上面还开着几扇小窗户。但是令人着迷而又惊奇的是,它是一条真正的船,毫无疑问,出海过无数次,压根儿就没想到过要把它搁置在地面上供人居住。这就是它令我如痴如醉的地方。如果是人家本来就打算用来居住的,我可能就会觉得船的空间小了,不方便,寂静冷清。但是,既然压根儿没打算派上这个用场,那就是一处再理想不过的住所了。
里面收拾得整洁干净、气氛雅致。摆了一张桌子,一具荷兰钟,一个五斗柜,柜上放着茶盘,上面画了一个撑着阳伞的女士,女士领着个童子军模样的孩子在漫步,孩子在滚铁环。茶盘被一本《圣经》挡着,免得掉下来。不过,我想万一那茶盘掉下来,就会把《圣经》周围的那些茶杯、碟子和茶壶都砸碎。墙上挂了几幅加了镶框的普通彩色画,画的是《圣经》中的故事。所以,打那以后,我每次一看到小商贩手上拿着的这种画时,眼前就会再一次呈现出佩戈蒂哥哥家室内的陈设。图画中印象最深的有两幅:一幅是身着红衣的亚伯拉罕要用身着蓝衣的以撒献祭。另一幅是身着黄衣的但以理被扔进了绿色狮子洞穴中。在小壁炉架的上方,挂了一幅画,画的是一艘在森德兰造的名叫“莎拉?简”号的斜桁四角帆船,船艉还是用真正的木片贴上去的,这是一件同时体现了美术创作和木工技术的艺术品。我认为,有了这样一件藏品,会受世人羡慕的。天花板下的横梁上钉了些钩子,我当时猜不透是做什么用的。室内还有一些柜子和箱子一类的东西,它们被用来当座位,聊做椅子。
所有这一切,我一跨进门槛第一眼就看到了——按照我的观点,这是孩子的特点。然后,佩戈蒂打开了一扇小门,让我看了看我的卧室。这是我所见过的卧室中最完美无缺和最赏心悦目的一个——坐落在船的尾部,有一扇小窗户,这儿原本是船舵伸出的地方,墙上挂了面小镜子,高度正好适合我,镜框上镶嵌了牡蛎壳。一张小床,正好容得下我。桌上放着一只蓝色的大杯子,里面插了一束海草。墙壁刷得像牛奶一样洁白,用各种碎布拼成的床单五颜六色,弄得我眼花缭乱。在这个充满了乐趣的房间里,有种味道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鱼腥味。这种味道无孔不入,所以当我掏出手帕擦鼻子时,发现手帕上的气味就像包了海虾后留下的。我把这个情况悄悄地告诉了佩戈蒂,结果她对我说,她哥哥经营的就是海虾、螃蟹和龙虾。我后来发现,外面那间专门放盆和桶的小木屋里常常看到一大堆这样的东西,它们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而且一旦咬住了什么,就再也不会松开。
一个围着白色围裙的女人礼貌周到地欢迎我们。我还在哈姆背上,离那个家还有四分之一英里远,这时候就看到她在门口行屈膝礼。一同欢迎我们的还有一个长得顶漂亮的小女孩(或许我感觉她如此),脖子上戴了一串蓝色珠子项圈,我有要亲亲她的意思,但她不肯,跑开躲了起来。随后,我们开始用正餐,放开了量吃,有清炖比目鱼、黄油酱和土豆,他们还专门给我做了一份排骨。这时候,一个毛发浓密、面目和善的男子进了屋。由于他管佩戈蒂叫“小姑娘”,还亲切地给了她脸上一个响吻,而我知道她平常的行为举止持重有度,所以我肯定,这便是她哥哥无疑了。他果然就是——佩戈蒂立刻向我介绍说,这是佩戈蒂先生,这个家的主人。
“很高兴见到您,少爷,”佩戈蒂先生说,“您会发现我们很粗俗,少爷,但您会觉得我们心眼儿实。”
我向他表示了感谢,并且回答,在这样一个生气盎然的地方,一定会过得开心愉快的。
“您妈妈好吗,少爷?”佩戈蒂先生问,“您离开时,她高兴吗?”
我告诉佩戈蒂先生说,她高兴极了,还表达了她的问候——这是我编造的一句客套话。
“说真格的,我太谢谢她啦,”佩戈蒂先生说,“对啦,少爷,您要是同她在此待上两个礼拜,”他朝他妹妹点了点头,“还有哈姆,还有小埃米莉,那可是我们家的荣幸啊。”
佩戈蒂先生热情友好,表达了主人的好客之情,然后到外面用一壶热水洗一洗,嘴里说着:“冷水根本洗不尽我这身上的脏东西。”不一会儿,他又进屋了,比刚才看上去清爽多了,不过脸很红,所以我不禁觉得,他的脸在这一点上和海虾、螃蟹、龙虾相同——进热水前黑黝黝的,出了热水后红彤彤的。
用过茶点,关上了房门,一切都安排得温馨舒适(这时候黑夜中透着寒气和雾霾),我觉得,就人们的想象力所及,这似乎是最惬意怡人的隐居之地了。倾听大风从海上刮来,知道室外雾气弥漫在荒凉平坦的滩地,目睹壁炉中燃烧的火焰,想到这儿除了这个住所没有任何别的,而这一处还是一艘船,这一切就像是施了魔法。小埃米莉不再感到羞涩腼腆了,和我一同并排坐在一个最矮和最小的柜子上,这个柜子正好够我们两个人坐,正好搁置在烟囱边的那个角落里。佩戈蒂太太围着白色围裙,正对着炉火坐着,手里做着编织活儿。佩戈蒂做着针线活儿,就像是在家里,身边摆着绘了圣保罗教堂的针线盒和那一小块蜡,好像这些东西压根儿就没有被拿到过别家。哈姆刚才一直在对我进行四门奖的启蒙,这会儿又试着用那副肮脏的牌回忆算命的游戏,翻牌时把大拇指上的鱼腥味都沾到上面了。佩戈蒂先生抽着烟斗。我感觉,这是聊聊天说心里话的时候。
“佩戈蒂先生!”我说。
“少爷。”他说。
“给儿子取名哈姆,是因为你们也住在像方舟一样的船上吗?”
佩戈蒂先生似乎觉得这是个挺深奥的问题,但还是回答:
“不是的,少爷。我就压根儿没给他取过名。”
“那么名字是谁给取的呢?”我用《教义问答》手册中第二个问题问佩戈蒂先生。
“呃,少爷,他父亲给取的。”佩戈蒂先生说。
“我还以为你是他父亲呢!”
“我弟弟乔才是他父亲。”佩戈蒂先生说。
“他不在人世了吗,佩戈蒂先生?”我礼貌性地停顿了一会儿后试探着问。
“是淹死的。”佩戈蒂先生说。
我感到很惊诧,佩戈蒂先生竟然不是哈姆的父亲。于是,我开始纳闷,是不是把他同这儿任何人的关系都弄错了啊。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于是打定主意要向佩戈蒂先生打听个清楚明白。
“小埃米莉,”我瞥了她一眼说,“她是你女儿,对不对,佩戈蒂先生?”
“不是,少爷。我妹夫汤姆才是她父亲。”
我没有办法了。“也不在人世了吗,佩戈蒂先生?”我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还是礼貌地问。
“是淹死的。”佩戈蒂先生说。
我感觉这个话题很难再继续下去了,但还是没有弄个水落石出,无论如何得弄个清楚明白啊。于是,我开口问:
“你难道就没有孩子吗,佩戈蒂先生?”
“没有啊,少爷,”他回答,勉强地笑了一下,“我单身汉一个。”
“单身汉!”我说了一声,惊诧不已,“啊,那个是谁,佩戈蒂先生?”我指着围了白围裙在做编织活儿的女人。
“那是格米治太太。”佩戈蒂先生说。
“格米治,佩戈蒂先生?”
但是,说到这儿,佩戈蒂——我是说我自己的那个佩戈蒂——夸张地向我示意,意思是我不要再问下去了。所以我只是坐着,看着默默无语的一伙人,直到后来要去上床睡觉了。后来,我到了属于我的那个私密小天地里,佩戈蒂才告诉我说,哈姆是佩戈蒂先生的侄子,小埃米莉是外甥女,他们都是孤儿,无依无靠,佩戈蒂先生先后收养了他们。格米治太太是个寡妇,丈夫曾经是和佩戈蒂先生一道跑船的,死的时候生活贫穷。佩戈蒂说,佩戈蒂先生本人也是个穷人,可是他品德高尚、为人真诚,就像是黄金和钢铁——这就是她用的比喻。佩戈蒂还告诉我说,他唯有一件事情会吹胡子瞪眼,骂天咒地,那就是听到有人提他的侠肝义胆行为。他们当中若是有人提到了,他就会右手往桌子上使劲一拍(有一次把桌子都拍裂了),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再听到有人提这事,他若不赶紧离开一去不回,那就该“被玷污脏身”。我再三询问这个难听的被动词的来历,但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一丁点儿。不过,他们都认为这是个最严厉的赌咒词。
我完全了解了这家主人的高尚品德。女人们的小卧室在船的另一端,和我的一样,我听见她们进那儿去了。还听到了佩戈蒂先生和哈姆也去睡觉了,他们在我先前注意到的屋顶钩子上替自己挂起了两张吊床,至此,我心满意足,睡意便浓了起来。睡意慢慢地向我袭来,这时候,我听见海风呼啸,猛烈强劲地吹过平坦的滩地,我睡意蒙眬,心里担心着夜间大海要涨潮。但仔细一想,我毕竟在船上,即便发生了什么事,有佩戈蒂先生这样的人在也不必担心。
不过,直到清晨来临,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晨曦刚一爬上我房内镶有牡蛎壳的镜框上,我就起床了,跟小埃米莉一同外出,在海滩上捡小石子玩。
“我看你是个出色的水手吧?”我对埃米莉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心里觉得礼貌的做法是得说点儿什么。而且就在这时,有一条船向我们靠近,那亮丽的船帆在她那亮晶晶的眼中显现出一个美丽的小影像,所以我心里突然想到了要这么说。
“不,”埃米莉摇了摇头说,“我害怕大海。”
“害怕!”我说,态度勇敢而得体,对着浩瀚的大海摆出一副架势,“我不害怕!”
“啊!可大海残酷无情啊,”埃米莉说,“我看见过它对着我们的亲人残酷无情,看见过它摧毁了一条同我们的住房一样大的船,把它撕成了碎片。”
“我希望那船不是……”
“我父亲溺水身亡的那条?”埃米莉说,“不,不是那条。我从没有见过那条船。”
“你从未见过你父亲他人吗?”我问她。
小埃米莉摇了摇头说:“不记得了!”
这纯属巧合!我立刻向她解释说,我也从未见过我父亲。我和母亲如何相依为命,生活过得幸福无比,而且会继续下去,我的意思是说还会一如既往地幸福下去。父亲被埋葬在我家旁边的墓地里,树木掩映,多少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漫步在树枝下面,倾听着鸟儿鸣唱。但是,看起来,我的孤儿状况同埃米莉的有些不同。她失去父亲之前母亲已不在人世了,她父亲的坟墓在哪儿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在大海深处的某个地方。
“除此之外,”埃米莉一边说,一边低头四下里找着贝壳和小石子,“你父亲是个绅士,母亲是个有身份的夫人,而我父亲是个渔夫,母亲是个渔夫的女儿,我舅舅丹也是个渔夫。”
“丹就是佩戈蒂先生,对不对?”我问。
“丹舅舅——在那儿。”埃米莉回答,对着船屋点了点头。
“对,我说的是他。我想,他一定心地非常善良吧?”
“善良?”埃米莉说,“我要是有朝一日做了有身份的夫人,就要送给他一件有钻石纽扣的天蓝色外套、一条淡黄色的裤子、一件红色的天鹅绒背心、一顶帽檐向上卷起的三角帽、一块大金表,一个银烟斗,还有一箱子钱。”
我说,我毫不怀疑,佩戈蒂先生很配得到这些宝贝儿。但我得承认,他的这位小外甥女知恩图报。对于她提出要送给他的这些衣着服饰,我敢说,他穿在身上后很难觉得舒适自如,我尤其怀疑那顶三角帽,不过,只是心里这么想来着,并没有表露出来。
小埃米莉罗列着这些宝贝儿的时候,停下了脚步,仰望着天空,仿佛那些东西是一幅光彩夺目的幻象。我们继续向前,捡着贝壳和小石子。
“你想做个有身份的夫人吗?”我问。
埃米莉看了看我,笑着点了点头说:“想做。”
“我很想做个有身份的夫人。到那时,我们就全都是体面人啦。我、舅舅、哈姆、还有格米治太太。遇上了暴风雨天气,我们也就不用担惊受怕了——我的意思不是替自己担惊受怕。毫无疑问,我们为的是穷苦的渔夫们。他们若是遇上什么伤害,我们可以出钱帮助他们。”
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前景令人心满意足,而且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表达了自己的欣喜之情,小埃米莉受到了鼓励,就怯生生地说:
“现在你还觉得自己不害怕大海吗?”
大海平静了下来,足以令我放心了。但是,毫无疑问,如果看到大的浪头涌入,想到她那些淹死的亲戚的可怕情形时,我一定会撒腿就跑。然而,我还是说了声:“不害怕,”接着又补充说,“你虽然口头上害怕,但实际上你也不害怕。”因为我们刚才走在一条陈旧的防波堤或木质堤道上,她都走得靠近边沿上了,我都担心她会掉下去。
“这样走我不害怕,”小埃米莉说,“但是,夜间海风刮起的时候,我就会醒过来。想到丹舅舅和哈姆,就会浑身颤抖,觉得自己听到了他们喊救命的声音,所以,我才想要做个有身份的夫人。但这样走我并不害怕。一点儿也不,你看!”
我们站立的地方一块凹凸不平的木板突出去,高悬在水面上,毫无防护措施。埃米莉突然离开我身边,顺木板跑着。我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所以,我敢说,自己若是个画家,一定能够把那天的情形清楚地画出来。小埃米莉的神态我永志难忘,她就像朝着死亡奔去(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冲向大海。
埃米莉娇小的身躯轻盈活泼、无拘无束,转身便安然无恙地飘然而至,回到了我身边。我很快就因为自己刚才又是担心又是惊叫的状态而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大呼小叫毫无用处,附近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可是,在从那以后的成人岁月中,我有多少次曾想过,小姑娘突然有了鲁莽行为,热切张狂的目光望着远处,除了可能存在的别的种种隐秘事物之外,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有某种令她神往的东西,吸引着她走向危险,并经她父亲的允诺,诱使她向着他靠近,所以她可能在那一天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从那以后有一段时期,我纳闷着,如果她未来的生活能够展现在我的面前,按照一个孩子对生活的理解而充分加以展示,如果保护她免遭危险是我的举手之功,我会不会伸出手去拯救她?从那之后有一段时期——我并不说那是很长的一段时期,但确实有那么一段,我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那天早晨,如果小埃米莉当着我的面被水淹没了头,是不是会更好些?我的回答是,是的,是更好些。
这可能言之过早了,我也许还不到叙述这事的时候。不过,就顺其自然吧。
我们漫步了很远的距离,见了一大堆我们认为很稀奇的东西,还小心翼翼地把一些搁浅的海星放回到水中——直到现在,我还不甚了解那种鱼,不知道它们是应该感谢我们,还是相反,然后,返回佩戈蒂先生的住所。走到外面放龙虾的棚屋下时,我们两小无猜地相互亲吻了一下,然后满心欢喜地进屋用早餐了。
“就像一对小花美。”佩戈蒂先生说,他说的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就像一对小画眉鸟。我还以为是夸奖的话呢。
我当然爱上了小埃米莉。我肯定自己爱上了那个小妞,尽管后来的爱情也崇高圣洁,但这次的爱与之相比,同样充满了真情实意,同样表现得温柔缠绵,而且更加纯洁无瑕,更加无私无畏。我相信自己的想象中出现了某种东西,弥漫在那个蓝眼睛小妞的周围,使她飘然欲仙,成了个天使。要是在某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她展开一对小小的翅膀从我的眼前飞走,我想,我有理由做好这种思想准备,不会感到很突然的。
我们一向亲亲热热,一小时接一小时地漫步在雅茅斯苍茫古老的滩地上。日子在我们的嬉戏游玩中过去,好像时光还没有长大,也还是个孩子,成天就是玩耍。我告诉埃米莉,我非常喜爱她,还说除非她也表白喜爱我,否则我只能举刃自刎。她说她喜爱我,我毫不怀疑她的确如此。
至于意识到地位悬殊,或者青春年少,或者我们面临的其他阻碍,我和埃米莉都没有去费这个心思,因为我们的心中根本没有想到过未来。如同我们不会为自己越来越年轻做着准备一样,我们没有为自己长大做着准备。我们备受格米治太太和佩戈蒂的羡慕,因为我们夜间也往往会并排坐在我们的小矮柜上,窃窃私语、爱意绵绵。“上帝啊!多美的状态!”佩戈蒂先生嘴里叼着烟斗,朝我们微笑着说。哈姆什么也没干,整个夜晚就是咧着嘴笑。我觉得,他们从我们的身上感受到了快乐,就和从一个精致的玩具或一个古罗马圆形剧场的袖珍模型上面感到的快乐一样。
我很快就发现,格米治太太虽然寄住在佩戈蒂先生家,但是她并不总像大家期待的那样表现得友好随和。她心情烦躁,在这样一个小家庭当中,有时候会怨天尤人,搞得别人不舒服。我很替她感到难过。但是,我认为,如果格米治太太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间可以待一待,一直待到心情好转了,那倒是会有令人觉得亲切随和的时候。
佩戈蒂先生时不时地会上一家名叫“心悦楼”的酒馆。我到了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他就出去了。八点多的时候,格米治太太抬头看了看那具荷兰钟,并说他到那儿去了,还有就是,她上午就知道他会去那儿,这时候我才知道了这事。
那天,格米治太太整天都神情沮丧。早上炉火光冒烟的时候,她便哭了起来。“我真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啊,”格米治太太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就会这么说,“一切的一切都和我对着来。”
“哦,烟很快就会散掉的,”佩戈蒂说——我指的还是我们那个佩戈蒂,“再说,也不就是唯独你一个人不好受,我们大家都一样啊。”
“我就是觉得我更不好过。”格米治太太说。
那天天气寒冷,寒风刺骨。在我看来,火炉旁边那个专属于格米治太太的角落是整个家中最温暖舒适的地方,而她坐的那把椅子毫无疑问也是最舒适的,可她那天还是不自在。她不停地抱怨,说天气冷,冷风钻进了她的脊背,她称为“像讨厌的东西爬进去了”。最后,她说到这事就又哭了起来,嘴里又念叨着:“我真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啊,一切的一切都和我对着来。”
“天气确实很冷,”佩戈蒂说,“大家的感觉都是这样。”
“我比别人更觉得冷。”格米治太太说。
到了吃饭的时候,她还是如此。因为我是贵客,便享受到了优待,而我之后就是格米治太太享受了。那天吃的鱼很小,刺又多,土豆也有点儿烧焦了。我们大家都承认,这顿饭吃得不怎么痛快,但格米治太太说,她比我们大家的感觉更甚,又流起了眼泪,还是满腹委屈,重复了先前说过的话。
因此,等到九点左右佩戈蒂先生回到家时,苦命的格米治太太坐在属于她的那个角落里干着编织活儿,神情凄惨,痛苦不堪。佩戈蒂则兴致勃勃地做着事。哈姆在补一双下水穿的大靴子。我呢,就和小埃米莉坐在一起,念书给她听。格米治太太除了叹气,就不会发出点别的声音,喝过茶之后,眼睛就再也没有抬起来过。
“对啦!伙计们,”佩戈蒂先生说着,坐了下来,“你们大家可好啊?”
我们打着招呼,看看什么东西(表示一种眼色),表示欢迎他回家,只有格米治太太除外,她只是一边编织东西,一边摇头。
“哪儿又不对劲啦,”佩戈蒂先生拍了拍手说,“高兴高兴吧,老妞儿!”(佩戈蒂先生的意思是说“老姑娘”)
格米治太太似乎没办法高兴起来,她掏出一条旧黑丝绸手帕,擦了擦眼睛,但是,没有把手帕放进口袋里,而是拿在手上,又擦了起来,然后还是拿着,准备随时使用。
“哪儿不对劲啦,老妞儿!”佩戈蒂先生说。
“没什么,”格米治太太回答,“你又去‘心悦楼’了吧,丹尔?”
“是啊,没错,我今晚在‘心悦楼’待了一会儿。”佩戈蒂先生说。
“我很抱歉,竟然把你逼到那儿去了。”格米治太太说。
“逼去!我可不要人家逼啊,”佩戈蒂先生说着,爽朗地笑了起来,“我是心甘情愿去的啊。”
“心甘情愿,”格米治太太说着,摇了摇头,擦了擦眼睛,“是啊,是啊,心甘情愿。我很难过,正是因为我,你才心甘情愿地去呢。”
“因为你?才不是因为你呢!”佩戈蒂先生说,“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是啊,是啊,是因为我,”格米治太太哭着说,“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我知道自己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不单单是一切的一切和我对着来,我也和所有人对着来呢。是啊,是啊。我比别人的感受更深,表现得也更明显。都是因为我命苦。”
我坐在那儿耳闻目睹这一切,心里不禁想到,除了格米治太太之外,不幸的命运也降临到了这个家庭中其他人的头上。但佩戈蒂先生并没有这样反驳她,只是用另一种请求作为回答,请求格米治太太高兴起来。
“我也不希望自己这样,”格米治太太说,“我做不到啊,我知道自己的情况。我烦心的事不断。我觉得心里烦,老是不顺心。我希望自己忘记烦恼,可就是没办法。我希望自己能够狠心应对,可就是做不到。我把这个家庭弄得很别扭,这我不奇怪。我把你妹妹和大卫少爷搞得成天不舒服。”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突然一下就软了,然后大声地说:“不,没有的事,格米治太太。”我心里难过极了。
“我做得太差劲了,”格米治太太说,“我不应该这样来报答你。我最好是去济贫院等死算了。我真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啊,最好不要在这儿碍手碍脚的。要是事情同我对着来,我自己就会闹别扭,那就让我回济贫院去闹别扭算了,丹尔,我最好到济贫院去,死在那儿,免得在这儿连累别人!”
格米治太太说完这番话之后,便起身睡觉去了。等她离开后,佩戈蒂先生除了表露出深深的同情之外,别无其他表情。他环顾我们大家,摇了摇头,脸上挂满了同情,低声说:
“她还在一直想着她老头儿呢!”
我当时还不太明白,格米治太太心里一直惦记着的老头儿是谁,直到后来佩戈蒂安顿我上床睡觉时,向我解释说,那指的是已故的格米治先生。她的哥哥每每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总用这个理由来解释,而且总会令他感慨不已。那天夜里他上了吊床之后,我亲耳听见他对哈姆反复说:“可怜的人啊!她还一直想着她老头儿呢!”在我们待在那里的剩下时间里,每当格米治太太从这样一种状态中恢复过来之后(其间又发生了几次),他都会说着同样的话,以此来冲淡气氛,而且总是洋溢着深深的同情。
两个星期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其间没有任何变化,只有潮起潮落,因为这样改变了佩戈蒂先生外出和回家的时间,也改变了哈姆干活儿的时间。当后者闲着没事时,有时候会陪着我们走走,带我们去见识一下大小船只,还带我们去划过一两次船。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往往会同某个地方,比同别的地方有更加特殊的联系,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感觉,尤其是涉及童年时代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每当我听人说起或者在书报上看到雅茅斯这个名字的时候,总会想起海滩上的某个礼拜日,召唤人们去做礼拜的钟声,小埃米莉倚靠在我肩膀上,哈姆懒洋洋地向水里扔石子,远处海面上,初升的太阳喷薄而出,冲破重重迷雾,显露出影子似的船只。
最后,回家的日子到了。我忍受住了同佩戈蒂先生和格米治太太的离别,但是,离开小埃米莉给我的心中带来的痛苦是透心彻骨。我们手挽着手一同走到车夫歇脚的酒馆前,我在路上就向她承诺要写信给她(我后来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过那字写得比手写的房屋招租广告还要大)。我们分别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悲伤,如果在我这一生中心里有过空落落的感觉的话,那一天的情形就是。
唉,我客居在外的整个时间里,又一次对不起自己的家,因为我极少甚至根本就没有想过家。但我刚一转身朝家里去,幼小的内心就充满了自责感,它似乎用一根坚定的手指指向那个方向。我的情绪越发低落,心里觉得,家是我的窝,母亲是我得安慰的人,是我的朋友。
我们越往家的方向走,我的这种感觉越强烈。离家越近,沿途的景物越熟悉,我也就越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家,扑向母亲的怀抱。可是佩戈蒂没有表露出激动的情绪,而是极力克制着(虽然态度上很和蔼),看上去局促不安、心情不佳。
尽管佩戈蒂表现出这样的一种状态,但只要车夫的马匹乐意,总归要回到布兰德斯通的乌鸦巢——而且实现了。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多么清楚啊,那天下午,阴沉寒冷,天色昏暗,像是要下雨了。
门开了,我兴高采烈,心情激动,半是笑半是哭地等着见我的母亲,可等到的不是她,而是个陌生的仆人。
“怎么回事,佩戈蒂!”我神情沮丧地说,“她没回家吗?”
“不,不,大卫少爷,”佩戈蒂说,“她回来了。您等一会儿,大卫少爷,我要——我要告诉您一点儿事。”
佩戈蒂下车时,情绪激动,加上天生笨拙,所以显得像个最最非同寻常的大彩球,不过我当时心里一片茫然,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没有对她说这个。她下车后,拉着我的手,把我带进厨房,然后关上了门,弄得我如堕五里中里。
“佩戈蒂!”我惶恐地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事,愿上帝保佑您,宝贝大卫少爷!”她回答,故意表现出轻松自如的样子。
“我敢肯定出了什么事,妈妈在哪儿?”
“妈妈在哪儿,大卫少爷?”佩戈蒂重复了一声。
“对呀。她为何不到大门口来接我,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哦,佩戈蒂!”我两眼噙满了泪水,感觉自己好像要晕倒了。
“哎呀,心肝宝贝儿啊!”佩戈蒂大声说着,一把抱住了我,“怎么回事?说话,心肝宝贝儿!”
“别是她也死了吧!哦,她没死吧,佩戈蒂?”
佩戈蒂大声喊了句“没有”,声音大得惊人。然后坐了下来,开始直喘粗气,说我把她吓了一跳。
我抱住了她,让她压压惊,或者说让她恢复正常,然后,站立在她面前,用急切和探询的目光看着她。
“你看,宝贝儿,我应该之前就告诉您的,”佩戈蒂说,“可我没找到机会。我或许应该创造一个机会的,但我且实没能,”佩戈蒂紧急情况下调用的词语中,总是用“且实”代替“确实”,“打定主意。”
“接着说吧,佩戈蒂!”我说,比刚才更加惶恐了。
“大卫少爷,”佩戈蒂说着,用一只手颤抖地解开帽子,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您心里是怎么想的?您有爸爸了!”
我浑身颤抖,脸色苍白。有种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或怎么会——与墓地中的坟墓有关,与死者复活有关,像是一股难闻的风向我袭来。
“一个新的。”佩戈蒂说。
“一个新的?”我重复了一遍。
佩戈蒂喘了一口粗气,像是要咽下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伸出手说:
“来吧,去见见他。”
“我不想见他。”
“还有您妈妈呢。”佩戈蒂说。
我不再退缩了,我们便径直到了那间更为豪华的客厅。到那儿后,她就走了。母亲坐在炉火的一边,默德斯通先生坐在另一边。母亲放下手上的活儿,急急忙忙站起身来,但我觉得她战战兢兢。
“行啦,克拉拉,亲爱的,”默德斯通先生说,“冷静点儿!要克制住自己,永远要克制住自己!大卫,孩子,你好吗?”
我把手伸向了他。愣了一会儿之后,这才走向母亲,吻她。她吻了我,还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坐下来接着干手上的活儿。我不能看着她,也不能看着他,心里很清楚,他在看着我们两个人,于是,我走到窗户边,干脆站在那儿看着外面,看着一些在寒冷中垂着枝条的灌木。
我一能够悄悄地离去,便溜到楼上去了,先前心爱的卧室有了变化,我得睡到远离这儿的地方。我又溜回到楼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保持原状。一切都似乎大变样了,我又漫步到院子里,但一下子退缩了回去,因为空荡荡的狗舍里有了一条大狗——像他一样,声音低沉,皮毛黝黑,狗一看见我,便大发雷霆,蹿了出来扑向我。
第四章
我陷于屈辱境地
我的床被搬进了这么一个房间,如果这个房间有知觉,能够提供证据,那我今天兴许会请求它——现在谁睡在那儿,我真想知道啊!请求它替我作证,我那天到那儿的时候,怀着的是怎样一种沉重心情。我朝楼上的那间屋子走去,上楼梯时,只听见身后院子里狗的狂吠声,我打量着屋子,一片茫然,莫名其妙,屋子同样也打量着我。我两只小手相交叉坐了下来,陷入了沉思。
我想到了最最奇怪的事情。想着那屋子的形状,想着那天花板上的裂纹,想着那墙上糊着的纸,想着那窗玻璃上的裂纹,景致形成了一道道波纹和一个个涟漪,想着那脸盆架,支在三条腿上摇摇欲坠,一副满腹牢骚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思念老头儿的格米治太太。我一直痛哭着,但是,除了意识到浑身寒冷和内心沮丧之外,我肯定,压根儿就没想过自己为何要哭。最后,我在孤单寂寞之中开始想到,自己深深地爱上了小埃米莉,而强忍着痛苦离开了她,来到了这儿,没有人像她那样需要我和在乎我。想到这儿,我痛苦万分,就用被子的一角裹住自己,哭着哭着便睡着了。
有人说“他在这儿呢”,并把被子从我热乎乎的头上掀开,我给弄醒了。母亲和佩戈蒂来找我了,是她们中的一位把我弄醒的。
“大卫,”母亲说,“你怎么啦?”
我觉得莫名其妙,她居然问起我来了,于是回答:“没事。”我记得,自己把脸转了过去,不让她看见我颤抖的嘴唇,因为这才是对她更为真实的回答。
“大卫,”母亲说,“大卫,我的孩子啊。”
我可以肯定,她当时说的话没有哪一句像把我称作她的孩子这一句更使我感动不已。我用被子蒙住,不让她看到眼泪,当她要抱我起来时,我的手使劲地推开她。
“这是你干的好事,佩戈蒂,你个残忍的东西!”母亲说,“我对这事毫不怀疑。我不知道,你居然煽动我的孩子与我对着干,或者与任何同我相亲相爱的人对着干,你的良心如何得到安宁?你这是何用心,佩戈蒂?”
可怜的佩戈蒂举起双手,抬起了眼睛,只能用我在饭后祈祷时说的话来回答:“愿上帝宽恕您啊,科波菲尔太太,但愿您永远不会为自己现在说的话后悔!”
“真把我气糊涂了,”母亲大声说,“我还在度着蜜月呢。这个时候,就算是对我怀有宿怨的仇敌,也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不至于嫉妒我过上一段内心平静、幸福快乐的日子。大卫啊,你个淘气孩子!佩戈蒂,你个狠毒的东西!哦,天哪!”母亲大声说着,脸从我们一个转向另一个,气急败坏,态度固执,“这是个多么艰难的世界啊,本来还以为可以生活得尽可能开心愉快些的!”
我感到有一只手触到了我,知道那既不是母亲的也不是佩戈蒂的,于是从床上滑了下来,站在床边。那是默德斯通先生的手,他一边抓住我的胳膊一边说:
“怎么回事?克拉拉,亲爱的,你难道忘了吗?要坚定沉着,亲爱的。”
“很对不起,爱德华,”母亲说,“我是想好好表现来着,可我忐忑不安。”
“可不是嘛!”他回答,“这么快就听到这么糟糕的事,克拉拉。”
“我现在被弄成这个样子,真是太难堪了,”母亲噘着嘴说,“真是——太难堪——对不对?”
他把母亲拉到自己身边,对着她的耳朵轻声说着,还吻了她。我看到母亲的头倚在他的肩膀上,胳膊贴近他的脖子,这时候,我清楚地知道——清楚地知道,他能够把她温柔娴雅的性格塑造成他心目中想要看到的样子。正如我现在明白的,他这样做了。
“你下楼去吧,亲爱的,”默德斯通先生说,“我待会儿同大卫一起下楼。我的朋友啊,”他朝母亲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看着她离开,之后便黑着脸朝着佩戈蒂,“你知道你们太太的姓氏了吗?”
“我服侍太太很长时间了,先生,”佩戈蒂回答,“应该知道的。”
“是这么回事,”他回答,“但是,我想,我上楼时听到你对她说话,用的不是她的姓。你知道她已经随我姓了。你要记住,听见了吗?”
佩戈蒂神情不安地瞥了我几眼,一声不吭地行了个屈膝礼便出去了。我觉得,她看出人家希望她离开,况且也没有待着不走的理由。房间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关上门,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拉我站在他跟前,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的眼睛。我觉得自己丝毫不亚于他,目光被他吸引着,也盯住他。我现在回忆起我们当时对视的情形,仿佛又一次听到了自己的心急速剧烈地跳动着。
“大卫,”他抿着嘴说,嘴唇抿得薄薄的,“如果我要对付一匹犟马或一只凶狗,你认为我会怎么做?”
“不知道。”
“我揍它。”
我先前低声回答问题时气喘吁吁,但我觉得,这时缄口不言呼吸更加急促。
“我要让它害怕退缩、感到难受。我心里会想着:‘我要征服这家伙,’即便那样要了它的命,我也得这么办。你脸上是什么?”
“是污垢。”我回答。
他和我一样清楚,那是泪痕。但是,如果问上二十遍,每问一次都要扇上二十个耳刮子,我相信,自己幼小的心被撕裂了也不会这样告诉他。
“你人虽小心眼儿可大,”他说着,脸上露出了他特有的冷峻微笑,“你清楚我的意思,我要看着你把脸洗了,先生,同我一道下楼吧。”
他指着那个被我比作格米治太太的神态的脸盆架,并向我点头示意,要按照他的“旨意”行事。我当时毫不怀疑,现在更加不怀疑,如果我犹豫磨蹭片刻,他会毫无顾忌地把我打倒在地。
“克拉拉,亲爱的,”他说着。我按照他的吩咐行事之后,他把我拉到客厅里,手抓住我的胳膊不放,“我希望你不会再忐忑不安了。我们很快就会改善我们这孩子的脾气。”
我的天哪!如果当时有人说句友好的话,我或许今生今世就有长进了,或许今生今世变成了另一种人。一句鼓励和解释的话,一句同情怜悯我年幼无知的话,一句欢迎我回家的话,一句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到确实是到了家里的话,这样的话,或许会使我从那以后打心眼儿里恭顺孝敬他,而不致表面上虚情假意地迎合他;会使我尊重敬仰他,而不致怨恨仇视他。我认为,母亲看到我站在房间里诚惶诚恐局促不安,心里会很难过,所以,一会儿之后,当我悄悄地坐到一把椅子边时,她的目光追随着我,表情更加忧伤——也许是因为没有见到我孩子气的步态中自由自在的样子。可是,这样的话没有说出,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单独用餐。默德斯通先生似乎很爱我母亲——但我恐怕并不至于因此便更加喜爱他,而母亲也很爱他。我从他们说的话中知道,他有个姐姐马上就要来同他们一起住,当晚就会来。我不能确定,我是当时就发现了,还是后来才发现的,默德斯通先生本人并不亲自经营什么,但他在伦敦的一家酒行里持有股份,或者说每年都可以从那儿得到一些红利,这个经营模式打从他曾祖时代起就有了。他姐姐也一样,在那家酒行中有利益关系。但是,不管情况是否如此,我都可以在此把这事提一提。
用餐过后,我们坐在炉火边,我的心里在思忖着设法逃离到佩戈蒂那儿去,而又不至于显得胆大妄为地溜走,以免激怒这个家里的主人。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马车停在我们家花园的栅栏门前,他起身出去迎接来客,母亲跟在他后面。我提心吊胆地跟在她后面。到达客厅门口时,幽暗中,她转过身来,像平常那样抱住我,轻轻地嘱咐我,要我爱我的新父亲,听他的话。她这样做的时候慌里慌张、偷偷摸摸,好像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态度温柔亲切。她把一只手伸到自己身后,握住我的,直到到了花园里离他站的地方很近时,她才放开了我的手,用手挽住他的胳膊。"第三章
我换了个环境
我猜想啊,车夫的那匹马是世界上最懒散的,一路上低着头,磨磨蹭蹭,似乎存心要让那些收接邮件的人久久等待。我还真就有这么一种感觉,马有时候会因为自己的这个意愿而笑出声来,但车夫说,马只是患了咳嗽的毛病。
车夫也像他的马一样,低垂着头,两只胳膊一边一只搁在膝盖上,边赶车边露着一副睡眼蒙眬的样子。我说的是“赶车”,实际上我觉得,没有他在,马车也照样能到达雅茅斯,因为所有的活儿马全包了。至于说到交谈,他压根儿没有这个兴致,只会吹吹口哨。
佩戈蒂捧了一篮点心放在膝盖上。即便我们乘着这辆马车要到伦敦去,路上的食物也够我们吃的。我们吃了很久,也睡了很多。佩戈蒂老是把下巴颏支在食物篮的提手上面睡觉,但她抓得牢牢的,没有松开过手。要不是亲耳听到,我简直不会相信,一个孤弱无助的女人鼾声竟然打得这么响亮。
我们途中拐进了好多回小路,给一家酒馆送了一副床架占去了很长时间,还去了另外几个地方,弄得我都厌烦了,后来很高兴终于到达了雅茅斯。我朝河对岸那一片广袤的荒滩地看过去,感觉那地方像海绵一样,相当松软潮湿。我不禁感到惊奇,如果世界真的如同我的地理书上所描述的那样是圆形的,那为什么有些地方这么平坦呢?但是,我又想到,雅茅斯或许是处在两极之间,这样就解释得通了。
我们到了更近处,看到四周的景致形成一条低垂的直线,置于天空之下。我给佩戈蒂提示说,要是有一处小山丘什么的,景致或许就会改观了。而如果这片土地与大海相隔得更远一些,城镇和海潮不像是水浸面包似的混到一起,那景致也会更加壮观。可佩戈蒂说,语气比平常还要重,我们应当入乡随俗,而在她的心目中,她为把自己称作“雅茅斯熏鱼”而自豪。
我们到了街上(我对那儿的一切都很陌生),闻到了种种味道,有鱼的、沥青的、填絮的和焦油的。看到了水手到处走动着,还有马车在石板地上来回辘辘前行,这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刚才对这样一个繁忙的地方评价有失公允。于是,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佩戈蒂,她听了非常高兴,异常得意,并且告诉我,众所周知(我想是对那些有幸生来就被称为“雅茅斯熏鱼”的人而言),总的说来,雅茅斯是天底下最美的地方。
“看,我们家阿姆!”佩戈蒂大叫了起来,“长得都认不出来啦!”
哈姆在酒馆门口等我们,像个老相识一样对我嘘寒问暖。刚一开始,我对他的感觉不像他对我那样熟悉,因为自从我降生的那个夜晚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到过我们家,所以我自然没有他那种感觉。不过,他背着我往家里走,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密切了起来。他身高六英尺,体形硕大,身体强壮,肩宽腰圆,但长着一张孩子脸,堆满了憨笑,一头淡色鬈发看上去像只绵羊。他身穿帆布外套、一条硬邦邦的裤子,即使不把腿伸进去,也可以立得住。说他戴了帽子并不确切,倒是应该说像一座老房子上盖着个漆黑的屋顶。
哈姆背着我,胳膊下还夹着我们的一只小箱子,佩戈蒂提着我们的另一只小箱子。我们穿过了几条巷子,到处有碎木片和小沙堆。途经了很多地方,如煤气厂、制缆厂、小船厂、大船厂、拆船厂、堵船缝厂、配件厂、铁匠铺,等等。最后,终于来到了那片我在远处就已经看到的荒滩。哈姆这时候说:
“大卫少爷,那就是我们家!”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极目远眺了荒野,看到了远处的大海、远处的河流,但就是没有看到房屋。不远处,倒是有一艘漆黑的驳船,或者是另一种什么废置的旧船,高高地搁置在干燥的地面上,一节像铁漏斗一样的东西向上突出,当作烟囱,正冒着热烘烘的烟。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可以住人的地方。
“你说的是那个吗?”我说,“那个像船一样的东西?”
“没有错,大卫少爷。”哈姆回答。
住在船里面这种想法充满了浪漫色彩,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即使是阿拉丁的宫殿、神鹰之蛋什么的,也不可能使我如此着迷。船的一侧开了一扇很有趣的门,还加了个屋顶,上面还开着几扇小窗户。但是令人着迷而又惊奇的是,它是一条真正的船,毫无疑问,出海过无数次,压根儿就没想到过要把它搁置在地面上供人居住。这就是它令我如痴如醉的地方。如果是人家本来就打算用来居住的,我可能就会觉得船的空间小了,不方便,寂静冷清。但是,既然压根儿没打算派上这个用场,那就是一处再理想不过的住所了。
里面收拾得整洁干净、气氛雅致。摆了一张桌子,一具荷兰钟,一个五斗柜,柜上放着茶盘,上面画了一个撑着阳伞的女士,女士领着个童子军模样的孩子在漫步,孩子在滚铁环。茶盘被一本《圣经》挡着,免得掉下来。不过,我想万一那茶盘掉下来,就会把《圣经》周围的那些茶杯、碟子和茶壶都砸碎。墙上挂了几幅加了镶框的普通彩色画,画的是《圣经》中的故事。所以,打那以后,我每次一看到小商贩手上拿着的这种画时,眼前就会再一次呈现出佩戈蒂哥哥家室内的陈设。图画中印象最深的有两幅:一幅是身着红衣的亚伯拉罕要用身着蓝衣的以撒献祭。另一幅是身着黄衣的但以理被扔进了绿色狮子洞穴中。在小壁炉架的上方,挂了一幅画,画的是一艘在森德兰造的名叫“莎拉?简”号的斜桁四角帆船,船艉还是用真正的木片贴上去的,这是一件同时体现了美术创作和木工技术的艺术品。我认为,有了这样一件藏品,会受世人羡慕的。天花板下的横梁上钉了些钩子,我当时猜不透是做什么用的。室内还有一些柜子和箱子一类的东西,它们被用来当座位,聊做椅子。
所有这一切,我一跨进门槛第一眼就看到了——按照我的观点,这是孩子的特点。然后,佩戈蒂打开了一扇小门,让我看了看我的卧室。这是我所见过的卧室中最完美无缺和最赏心悦目的一个——坐落在船的尾部,有一扇小窗户,这儿原本是船舵伸出的地方,墙上挂了面小镜子,高度正好适合我,镜框上镶嵌了牡蛎壳。一张小床,正好容得下我。桌上放着一只蓝色的大杯子,里面插了一束海草。墙壁刷得像牛奶一样洁白,用各种碎布拼成的床单五颜六色,弄得我眼花缭乱。在这个充满了乐趣的房间里,有种味道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鱼腥味。这种味道无孔不入,所以当我掏出手帕擦鼻子时,发现手帕上的气味就像包了海虾后留下的。我把这个情况悄悄地告诉了佩戈蒂,结果她对我说,她哥哥经营的就是海虾、螃蟹和龙虾。我后来发现,外面那间专门放盆和桶的小木屋里常常看到一大堆这样的东西,它们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而且一旦咬住了什么,就再也不会松开。
一个围着白色围裙的女人礼貌周到地欢迎我们。我还在哈姆背上,离那个家还有四分之一英里远,这时候就看到她在门口行屈膝礼。一同欢迎我们的还有一个长得顶漂亮的小女孩(或许我感觉她如此),脖子上戴了一串蓝色珠子项圈,我有要亲亲她的意思,但她不肯,跑开躲了起来。随后,我们开始用正餐,放开了量吃,有清炖比目鱼、黄油酱和土豆,他们还专门给我做了一份排骨。这时候,一个毛发浓密、面目和善的男子进了屋。由于他管佩戈蒂叫“小姑娘”,还亲切地给了她脸上一个响吻,而我知道她平常的行为举止持重有度,所以我肯定,这便是她哥哥无疑了。他果然就是——佩戈蒂立刻向我介绍说,这是佩戈蒂先生,这个家的主人。
“很高兴见到您,少爷,”佩戈蒂先生说,“您会发现我们很粗俗,少爷,但您会觉得我们心眼儿实。”
我向他表示了感谢,并且回答,在这样一个生气盎然的地方,一定会过得开心愉快的。
“您妈妈好吗,少爷?”佩戈蒂先生问,“您离开时,她高兴吗?”
我告诉佩戈蒂先生说,她高兴极了,还表达了她的问候——这是我编造的一句客套话。
“说真格的,我太谢谢她啦,”佩戈蒂先生说,“对啦,少爷,您要是同她在此待上两个礼拜,”他朝他妹妹点了点头,“还有哈姆,还有小埃米莉,那可是我们家的荣幸啊。”
佩戈蒂先生热情友好,表达了主人的好客之情,然后到外面用一壶热水洗一洗,嘴里说着:“冷水根本洗不尽我这身上的脏东西。”不一会儿,他又进屋了,比刚才看上去清爽多了,不过脸很红,所以我不禁觉得,他的脸在这一点上和海虾、螃蟹、龙虾相同——进热水前黑黝黝的,出了热水后红彤彤的。
用过茶点,关上了房门,一切都安排得温馨舒适(这时候黑夜中透着寒气和雾霾),我觉得,就人们的想象力所及,这似乎是最惬意怡人的隐居之地了。倾听大风从海上刮来,知道室外雾气弥漫在荒凉平坦的滩地,目睹壁炉中燃烧的火焰,想到这儿除了这个住所没有任何别的,而这一处还是一艘船,这一切就像是施了魔法。小埃米莉不再感到羞涩腼腆了,和我一同并排坐在一个最矮和最小的柜子上,这个柜子正好够我们两个人坐,正好搁置在烟囱边的那个角落里。佩戈蒂太太围着白色围裙,正对着炉火坐着,手里做着编织活儿。佩戈蒂做着针线活儿,就像是在家里,身边摆着绘了圣保罗教堂的针线盒和那一小块蜡,好像这些东西压根儿就没有被拿到过别家。哈姆刚才一直在对我进行四门奖的启蒙,这会儿又试着用那副肮脏的牌回忆算命的游戏,翻牌时把大拇指上的鱼腥味都沾到上面了。佩戈蒂先生抽着烟斗。我感觉,这是聊聊天说心里话的时候。
“佩戈蒂先生!”我说。
“少爷。”他说。
“给儿子取名哈姆,是因为你们也住在像方舟一样的船上吗?”
佩戈蒂先生似乎觉得这是个挺深奥的问题,但还是回答:
“不是的,少爷。我就压根儿没给他取过名。”
“那么名字是谁给取的呢?”我用《教义问答》手册中第二个问题问佩戈蒂先生。
“呃,少爷,他父亲给取的。”佩戈蒂先生说。
“我还以为你是他父亲呢!”
“我弟弟乔才是他父亲。”佩戈蒂先生说。
“他不在人世了吗,佩戈蒂先生?”我礼貌性地停顿了一会儿后试探着问。
“是淹死的。”佩戈蒂先生说。
我感到很惊诧,佩戈蒂先生竟然不是哈姆的父亲。于是,我开始纳闷,是不是把他同这儿任何人的关系都弄错了啊。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于是打定主意要向佩戈蒂先生打听个清楚明白。
“小埃米莉,”我瞥了她一眼说,“她是你女儿,对不对,佩戈蒂先生?”
“不是,少爷。我妹夫汤姆才是她父亲。”
我没有办法了。“也不在人世了吗,佩戈蒂先生?”我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还是礼貌地问。
“是淹死的。”佩戈蒂先生说。
我感觉这个话题很难再继续下去了,但还是没有弄个水落石出,无论如何得弄个清楚明白啊。于是,我开口问:
“你难道就没有孩子吗,佩戈蒂先生?”
“没有啊,少爷,”他回答,勉强地笑了一下,“我单身汉一个。”
“单身汉!”我说了一声,惊诧不已,“啊,那个是谁,佩戈蒂先生?”我指着围了白围裙在做编织活儿的女人。
“那是格米治太太。”佩戈蒂先生说。
“格米治,佩戈蒂先生?”
但是,说到这儿,佩戈蒂——我是说我自己的那个佩戈蒂——夸张地向我示意,意思是我不要再问下去了。所以我只是坐着,看着默默无语的一伙人,直到后来要去上床睡觉了。后来,我到了属于我的那个私密小天地里,佩戈蒂才告诉我说,哈姆是佩戈蒂先生的侄子,小埃米莉是外甥女,他们都是孤儿,无依无靠,佩戈蒂先生先后收养了他们。格米治太太是个寡妇,丈夫曾经是和佩戈蒂先生一道跑船的,死的时候生活贫穷。佩戈蒂说,佩戈蒂先生本人也是个穷人,可是他品德高尚、为人真诚,就像是黄金和钢铁——这就是她用的比喻。佩戈蒂还告诉我说,他唯有一件事情会吹胡子瞪眼,骂天咒地,那就是听到有人提他的侠肝义胆行为。他们当中若是有人提到了,他就会右手往桌子上使劲一拍(有一次把桌子都拍裂了),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再听到有人提这事,他若不赶紧离开一去不回,那就该“被玷污脏身”。我再三询问这个难听的被动词的来历,但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一丁点儿。不过,他们都认为这是个最严厉的赌咒词。
我完全了解了这家主人的高尚品德。女人们的小卧室在船的另一端,和我的一样,我听见她们进那儿去了。还听到了佩戈蒂先生和哈姆也去睡觉了,他们在我先前注意到的屋顶钩子上替自己挂起了两张吊床,至此,我心满意足,睡意便浓了起来。睡意慢慢地向我袭来,这时候,我听见海风呼啸,猛烈强劲地吹过平坦的滩地,我睡意蒙眬,心里担心着夜间大海要涨潮。但仔细一想,我毕竟在船上,即便发生了什么事,有佩戈蒂先生这样的人在也不必担心。
不过,直到清晨来临,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晨曦刚一爬上我房内镶有牡蛎壳的镜框上,我就起床了,跟小埃米莉一同外出,在海滩上捡小石子玩。
“我看你是个出色的水手吧?”我对埃米莉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心里觉得礼貌的做法是得说点儿什么。而且就在这时,有一条船向我们靠近,那亮丽的船帆在她那亮晶晶的眼中显现出一个美丽的小影像,所以我心里突然想到了要这么说。
“不,”埃米莉摇了摇头说,“我害怕大海。”
“害怕!”我说,态度勇敢而得体,对着浩瀚的大海摆出一副架势,“我不害怕!”
“啊!可大海残酷无情啊,”埃米莉说,“我看见过它对着我们的亲人残酷无情,看见过它摧毁了一条同我们的住房一样大的船,把它撕成了碎片。”
“我希望那船不是……”
“我父亲溺水身亡的那条?”埃米莉说,“不,不是那条。我从没有见过那条船。”
“你从未见过你父亲他人吗?”我问她。
小埃米莉摇了摇头说:“不记得了!”
这纯属巧合!我立刻向她解释说,我也从未见过我父亲。我和母亲如何相依为命,生活过得幸福无比,而且会继续下去,我的意思是说还会一如既往地幸福下去。父亲被埋葬在我家旁边的墓地里,树木掩映,多少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漫步在树枝下面,倾听着鸟儿鸣唱。但是,看起来,我的孤儿状况同埃米莉的有些不同。她失去父亲之前母亲已不在人世了,她父亲的坟墓在哪儿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在大海深处的某个地方。
“除此之外,”埃米莉一边说,一边低头四下里找着贝壳和小石子,“你父亲是个绅士,母亲是个有身份的夫人,而我父亲是个渔夫,母亲是个渔夫的女儿,我舅舅丹也是个渔夫。”
“丹就是佩戈蒂先生,对不对?”我问。
“丹舅舅——在那儿。”埃米莉回答,对着船屋点了点头。
“对,我说的是他。我想,他一定心地非常善良吧?”
“善良?”埃米莉说,“我要是有朝一日做了有身份的夫人,就要送给他一件有钻石纽扣的天蓝色外套、一条淡黄色的裤子、一件红色的天鹅绒背心、一顶帽檐向上卷起的三角帽、一块大金表,一个银烟斗,还有一箱子钱。”
我说,我毫不怀疑,佩戈蒂先生很配得到这些宝贝儿。但我得承认,他的这位小外甥女知恩图报。对于她提出要送给他的这些衣着服饰,我敢说,他穿在身上后很难觉得舒适自如,我尤其怀疑那顶三角帽,不过,只是心里这么想来着,并没有表露出来。
小埃米莉罗列着这些宝贝儿的时候,停下了脚步,仰望着天空,仿佛那些东西是一幅光彩夺目的幻象。我们继续向前,捡着贝壳和小石子。
“你想做个有身份的夫人吗?”我问。
埃米莉看了看我,笑着点了点头说:“想做。”
“我很想做个有身份的夫人。到那时,我们就全都是体面人啦。我、舅舅、哈姆、还有格米治太太。遇上了暴风雨天气,我们也就不用担惊受怕了——我的意思不是替自己担惊受怕。毫无疑问,我们为的是穷苦的渔夫们。他们若是遇上什么伤害,我们可以出钱帮助他们。”
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前景令人心满意足,而且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表达了自己的欣喜之情,小埃米莉受到了鼓励,就怯生生地说:
“现在你还觉得自己不害怕大海吗?”
大海平静了下来,足以令我放心了。但是,毫无疑问,如果看到大的浪头涌入,想到她那些淹死的亲戚的可怕情形时,我一定会撒腿就跑。然而,我还是说了声:“不害怕,”接着又补充说,“你虽然口头上害怕,但实际上你也不害怕。”因为我们刚才走在一条陈旧的防波堤或木质堤道上,她都走得靠近边沿上了,我都担心她会掉下去。
“这样走我不害怕,”小埃米莉说,“但是,夜间海风刮起的时候,我就会醒过来。想到丹舅舅和哈姆,就会浑身颤抖,觉得自己听到了他们喊救命的声音,所以,我才想要做个有身份的夫人。但这样走我并不害怕。一点儿也不,你看!”
我们站立的地方一块凹凸不平的木板突出去,高悬在水面上,毫无防护措施。埃米莉突然离开我身边,顺木板跑着。我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所以,我敢说,自己若是个画家,一定能够把那天的情形清楚地画出来。小埃米莉的神态我永志难忘,她就像朝着死亡奔去(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冲向大海。
埃米莉娇小的身躯轻盈活泼、无拘无束,转身便安然无恙地飘然而至,回到了我身边。我很快就因为自己刚才又是担心又是惊叫的状态而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大呼小叫毫无用处,附近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可是,在从那以后的成人岁月中,我有多少次曾想过,小姑娘突然有了鲁莽行为,热切张狂的目光望着远处,除了可能存在的别的种种隐秘事物之外,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有某种令她神往的东西,吸引着她走向危险,并经她父亲的允诺,诱使她向着他靠近,所以她可能在那一天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从那以后有一段时期,我纳闷着,如果她未来的生活能够展现在我的面前,按照一个孩子对生活的理解而充分加以展示,如果保护她免遭危险是我的举手之功,我会不会伸出手去拯救她?从那之后有一段时期——我并不说那是很长的一段时期,但确实有那么一段,我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那天早晨,如果小埃米莉当着我的面被水淹没了头,是不是会更好些?我的回答是,是的,是更好些。
这可能言之过早了,我也许还不到叙述这事的时候。不过,就顺其自然吧。
我们漫步了很远的距离,见了一大堆我们认为很稀奇的东西,还小心翼翼地把一些搁浅的海星放回到水中——直到现在,我还不甚了解那种鱼,不知道它们是应该感谢我们,还是相反,然后,返回佩戈蒂先生的住所。走到外面放龙虾的棚屋下时,我们两小无猜地相互亲吻了一下,然后满心欢喜地进屋用早餐了。
“就像一对小花美。”佩戈蒂先生说,他说的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就像一对小画眉鸟。我还以为是夸奖的话呢。
我当然爱上了小埃米莉。我肯定自己爱上了那个小妞,尽管后来的爱情也崇高圣洁,但这次的爱与之相比,同样充满了真情实意,同样表现得温柔缠绵,而且更加纯洁无瑕,更加无私无畏。我相信自己的想象中出现了某种东西,弥漫在那个蓝眼睛小妞的周围,使她飘然欲仙,成了个天使。要是在某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她展开一对小小的翅膀从我的眼前飞走,我想,我有理由做好这种思想准备,不会感到很突然的。
我们一向亲亲热热,一小时接一小时地漫步在雅茅斯苍茫古老的滩地上。日子在我们的嬉戏游玩中过去,好像时光还没有长大,也还是个孩子,成天就是玩耍。我告诉埃米莉,我非常喜爱她,还说除非她也表白喜爱我,否则我只能举刃自刎。她说她喜爱我,我毫不怀疑她的确如此。
至于意识到地位悬殊,或者青春年少,或者我们面临的其他阻碍,我和埃米莉都没有去费这个心思,因为我们的心中根本没有想到过未来。如同我们不会为自己越来越年轻做着准备一样,我们没有为自己长大做着准备。我们备受格米治太太和佩戈蒂的羡慕,因为我们夜间也往往会并排坐在我们的小矮柜上,窃窃私语、爱意绵绵。“上帝啊!多美的状态!”佩戈蒂先生嘴里叼着烟斗,朝我们微笑着说。哈姆什么也没干,整个夜晚就是咧着嘴笑。我觉得,他们从我们的身上感受到了快乐,就和从一个精致的玩具或一个古罗马圆形剧场的袖珍模型上面感到的快乐一样。
我很快就发现,格米治太太虽然寄住在佩戈蒂先生家,但是她并不总像大家期待的那样表现得友好随和。她心情烦躁,在这样一个小家庭当中,有时候会怨天尤人,搞得别人不舒服。我很替她感到难过。但是,我认为,如果格米治太太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间可以待一待,一直待到心情好转了,那倒是会有令人觉得亲切随和的时候。
佩戈蒂先生时不时地会上一家名叫“心悦楼”的酒馆。我到了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他就出去了。八点多的时候,格米治太太抬头看了看那具荷兰钟,并说他到那儿去了,还有就是,她上午就知道他会去那儿,这时候我才知道了这事。
那天,格米治太太整天都神情沮丧。早上炉火光冒烟的时候,她便哭了起来。“我真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啊,”格米治太太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就会这么说,“一切的一切都和我对着来。”
“哦,烟很快就会散掉的,”佩戈蒂说——我指的还是我们那个佩戈蒂,“再说,也不就是唯独你一个人不好受,我们大家都一样啊。”
“我就是觉得我更不好过。”格米治太太说。
那天天气寒冷,寒风刺骨。在我看来,火炉旁边那个专属于格米治太太的角落是整个家中最温暖舒适的地方,而她坐的那把椅子毫无疑问也是最舒适的,可她那天还是不自在。她不停地抱怨,说天气冷,冷风钻进了她的脊背,她称为“像讨厌的东西爬进去了”。最后,她说到这事就又哭了起来,嘴里又念叨着:“我真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啊,一切的一切都和我对着来。”
“天气确实很冷,”佩戈蒂说,“大家的感觉都是这样。”
“我比别人更觉得冷。”格米治太太说。
到了吃饭的时候,她还是如此。因为我是贵客,便享受到了优待,而我之后就是格米治太太享受了。那天吃的鱼很小,刺又多,土豆也有点儿烧焦了。我们大家都承认,这顿饭吃得不怎么痛快,但格米治太太说,她比我们大家的感觉更甚,又流起了眼泪,还是满腹委屈,重复了先前说过的话。
因此,等到九点左右佩戈蒂先生回到家时,苦命的格米治太太坐在属于她的那个角落里干着编织活儿,神情凄惨,痛苦不堪。佩戈蒂则兴致勃勃地做着事。哈姆在补一双下水穿的大靴子。我呢,就和小埃米莉坐在一起,念书给她听。格米治太太除了叹气,就不会发出点别的声音,喝过茶之后,眼睛就再也没有抬起来过。
“对啦!伙计们,”佩戈蒂先生说着,坐了下来,“你们大家可好啊?”
我们打着招呼,看看什么东西(表示一种眼色),表示欢迎他回家,只有格米治太太除外,她只是一边编织东西,一边摇头。
“哪儿又不对劲啦,”佩戈蒂先生拍了拍手说,“高兴高兴吧,老妞儿!”(佩戈蒂先生的意思是说“老姑娘”)
格米治太太似乎没办法高兴起来,她掏出一条旧黑丝绸手帕,擦了擦眼睛,但是,没有把手帕放进口袋里,而是拿在手上,又擦了起来,然后还是拿着,准备随时使用。
“哪儿不对劲啦,老妞儿!”佩戈蒂先生说。
“没什么,”格米治太太回答,“你又去‘心悦楼’了吧,丹尔?”
“是啊,没错,我今晚在‘心悦楼’待了一会儿。”佩戈蒂先生说。
“我很抱歉,竟然把你逼到那儿去了。”格米治太太说。
“逼去!我可不要人家逼啊,”佩戈蒂先生说着,爽朗地笑了起来,“我是心甘情愿去的啊。”
“心甘情愿,”格米治太太说着,摇了摇头,擦了擦眼睛,“是啊,是啊,心甘情愿。我很难过,正是因为我,你才心甘情愿地去呢。”
“因为你?才不是因为你呢!”佩戈蒂先生说,“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是啊,是啊,是因为我,”格米治太太哭着说,“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我知道自己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不单单是一切的一切和我对着来,我也和所有人对着来呢。是啊,是啊。我比别人的感受更深,表现得也更明显。都是因为我命苦。”
我坐在那儿耳闻目睹这一切,心里不禁想到,除了格米治太太之外,不幸的命运也降临到了这个家庭中其他人的头上。但佩戈蒂先生并没有这样反驳她,只是用另一种请求作为回答,请求格米治太太高兴起来。
“我也不希望自己这样,”格米治太太说,“我做不到啊,我知道自己的情况。我烦心的事不断。我觉得心里烦,老是不顺心。我希望自己忘记烦恼,可就是没办法。我希望自己能够狠心应对,可就是做不到。我把这个家庭弄得很别扭,这我不奇怪。我把你妹妹和大卫少爷搞得成天不舒服。”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突然一下就软了,然后大声地说:“不,没有的事,格米治太太。”我心里难过极了。
“我做得太差劲了,”格米治太太说,“我不应该这样来报答你。我最好是去济贫院等死算了。我真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啊,最好不要在这儿碍手碍脚的。要是事情同我对着来,我自己就会闹别扭,那就让我回济贫院去闹别扭算了,丹尔,我最好到济贫院去,死在那儿,免得在这儿连累别人!”
格米治太太说完这番话之后,便起身睡觉去了。等她离开后,佩戈蒂先生除了表露出深深的同情之外,别无其他表情。他环顾我们大家,摇了摇头,脸上挂满了同情,低声说:
“她还在一直想着她老头儿呢!”
我当时还不太明白,格米治太太心里一直惦记着的老头儿是谁,直到后来佩戈蒂安顿我上床睡觉时,向我解释说,那指的是已故的格米治先生。她的哥哥每每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总用这个理由来解释,而且总会令他感慨不已。那天夜里他上了吊床之后,我亲耳听见他对哈姆反复说:“可怜的人啊!她还一直想着她老头儿呢!”在我们待在那里的剩下时间里,每当格米治太太从这样一种状态中恢复过来之后(其间又发生了几次),他都会说着同样的话,以此来冲淡气氛,而且总是洋溢着深深的同情。
两个星期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其间没有任何变化,只有潮起潮落,因为这样改变了佩戈蒂先生外出和回家的时间,也改变了哈姆干活儿的时间。当后者闲着没事时,有时候会陪着我们走走,带我们去见识一下大小船只,还带我们去划过一两次船。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往往会同某个地方,比同别的地方有更加特殊的联系,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感觉,尤其是涉及童年时代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每当我听人说起或者在书报上看到雅茅斯这个名字的时候,总会想起海滩上的某个礼拜日,召唤人们去做礼拜的钟声,小埃米莉倚靠在我肩膀上,哈姆懒洋洋地向水里扔石子,远处海面上,初升的太阳喷薄而出,冲破重重迷雾,显露出影子似的船只。
最后,回家的日子到了。我忍受住了同佩戈蒂先生和格米治太太的离别,但是,离开小埃米莉给我的心中带来的痛苦是透心彻骨。我们手挽着手一同走到车夫歇脚的酒馆前,我在路上就向她承诺要写信给她(我后来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过那字写得比手写的房屋招租广告还要大)。我们分别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悲伤,如果在我这一生中心里有过空落落的感觉的话,那一天的情形就是。
唉,我客居在外的整个时间里,又一次对不起自己的家,因为我极少甚至根本就没有想过家。但我刚一转身朝家里去,幼小的内心就充满了自责感,它似乎用一根坚定的手指指向那个方向。我的情绪越发低落,心里觉得,家是我的窝,母亲是我得安慰的人,是我的朋友。
我们越往家的方向走,我的这种感觉越强烈。离家越近,沿途的景物越熟悉,我也就越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家,扑向母亲的怀抱。可是佩戈蒂没有表露出激动的情绪,而是极力克制着(虽然态度上很和蔼),看上去局促不安、心情不佳。
尽管佩戈蒂表现出这样的一种状态,但只要车夫的马匹乐意,总归要回到布兰德斯通的乌鸦巢——而且实现了。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多么清楚啊,那天下午,阴沉寒冷,天色昏暗,像是要下雨了。
门开了,我兴高采烈,心情激动,半是笑半是哭地等着见我的母亲,可等到的不是她,而是个陌生的仆人。
“怎么回事,佩戈蒂!”我神情沮丧地说,“她没回家吗?”
“不,不,大卫少爷,”佩戈蒂说,“她回来了。您等一会儿,大卫少爷,我要——我要告诉您一点儿事。”
佩戈蒂下车时,情绪激动,加上天生笨拙,所以显得像个最最非同寻常的大彩球,不过我当时心里一片茫然,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没有对她说这个。她下车后,拉着我的手,把我带进厨房,然后关上了门,弄得我如堕五里中里。
“佩戈蒂!”我惶恐地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事,愿上帝保佑您,宝贝大卫少爷!”她回答,故意表现出轻松自如的样子。
“我敢肯定出了什么事,妈妈在哪儿?”
“妈妈在哪儿,大卫少爷?”佩戈蒂重复了一声。
“对呀。她为何不到大门口来接我,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哦,佩戈蒂!”我两眼噙满了泪水,感觉自己好像要晕倒了。
“哎呀,心肝宝贝儿啊!”佩戈蒂大声说着,一把抱住了我,“怎么回事?说话,心肝宝贝儿!”
“别是她也死了吧!哦,她没死吧,佩戈蒂?”
佩戈蒂大声喊了句“没有”,声音大得惊人。然后坐了下来,开始直喘粗气,说我把她吓了一跳。
我抱住了她,让她压压惊,或者说让她恢复正常,然后,站立在她面前,用急切和探询的目光看着她。
“你看,宝贝儿,我应该之前就告诉您的,”佩戈蒂说,“可我没找到机会。我或许应该创造一个机会的,但我且实没能,”佩戈蒂紧急情况下调用的词语中,总是用“且实”代替“确实”,“打定主意。”
“接着说吧,佩戈蒂!”我说,比刚才更加惶恐了。
“大卫少爷,”佩戈蒂说着,用一只手颤抖地解开帽子,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您心里是怎么想的?您有爸爸了!”
我浑身颤抖,脸色苍白。有种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或怎么会——与墓地中的坟墓有关,与死者复活有关,像是一股难闻的风向我袭来。
“一个新的。”佩戈蒂说。
“一个新的?”我重复了一遍。
佩戈蒂喘了一口粗气,像是要咽下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伸出手说:
“来吧,去见见他。”
“我不想见他。”
“还有您妈妈呢。”佩戈蒂说。
我不再退缩了,我们便径直到了那间更为豪华的客厅。到那儿后,她就走了。母亲坐在炉火的一边,默德斯通先生坐在另一边。母亲放下手上的活儿,急急忙忙站起身来,但我觉得她战战兢兢。
“行啦,克拉拉,亲爱的,”默德斯通先生说,“冷静点儿!要克制住自己,永远要克制住自己!大卫,孩子,你好吗?”
我把手伸向了他。愣了一会儿之后,这才走向母亲,吻她。她吻了我,还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坐下来接着干手上的活儿。我不能看着她,也不能看着他,心里很清楚,他在看着我们两个人,于是,我走到窗户边,干脆站在那儿看着外面,看着一些在寒冷中垂着枝条的灌木。
我一能够悄悄地离去,便溜到楼上去了,先前心爱的卧室有了变化,我得睡到远离这儿的地方。我又溜回到楼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保持原状。一切都似乎大变样了,我又漫步到院子里,但一下子退缩了回去,因为空荡荡的狗舍里有了一条大狗——像他一样,声音低沉,皮毛黝黑,狗一看见我,便大发雷霆,蹿了出来扑向我。
第四章
我陷于屈辱境地
我的床被搬进了这么一个房间,如果这个房间有知觉,能够提供证据,那我今天兴许会请求它——现在谁睡在那儿,我真想知道啊!请求它替我作证,我那天到那儿的时候,怀着的是怎样一种沉重心情。我朝楼上的那间屋子走去,上楼梯时,只听见身后院子里狗的狂吠声,我打量着屋子,一片茫然,莫名其妙,屋子同样也打量着我。我两只小手相交叉坐了下来,陷入了沉思。
我想到了最最奇怪的事情。想着那屋子的形状,想着那天花板上的裂纹,想着那墙上糊着的纸,想着那窗玻璃上的裂纹,景致形成了一道道波纹和一个个涟漪,想着那脸盆架,支在三条腿上摇摇欲坠,一副满腹牢骚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思念老头儿的格米治太太。我一直痛哭着,但是,除了意识到浑身寒冷和内心沮丧之外,我肯定,压根儿就没想过自己为何要哭。最后,我在孤单寂寞之中开始想到,自己深深地爱上了小埃米莉,而强忍着痛苦离开了她,来到了这儿,没有人像她那样需要我和在乎我。想到这儿,我痛苦万分,就用被子的一角裹住自己,哭着哭着便睡着了。
有人说“他在这儿呢”,并把被子从我热乎乎的头上掀开,我给弄醒了。母亲和佩戈蒂来找我了,是她们中的一位把我弄醒的。
“大卫,”母亲说,“你怎么啦?”
我觉得莫名其妙,她居然问起我来了,于是回答:“没事。”我记得,自己把脸转了过去,不让她看见我颤抖的嘴唇,因为这才是对她更为真实的回答。
“大卫,”母亲说,“大卫,我的孩子啊。”
我可以肯定,她当时说的话没有哪一句像把我称作她的孩子这一句更使我感动不已。我用被子蒙住,不让她看到眼泪,当她要抱我起来时,我的手使劲地推开她。
“这是你干的好事,佩戈蒂,你个残忍的东西!”母亲说,“我对这事毫不怀疑。我不知道,你居然煽动我的孩子与我对着干,或者与任何同我相亲相爱的人对着干,你的良心如何得到安宁?你这是何用心,佩戈蒂?”
可怜的佩戈蒂举起双手,抬起了眼睛,只能用我在饭后祈祷时说的话来回答:“愿上帝宽恕您啊,科波菲尔太太,但愿您永远不会为自己现在说的话后悔!”
“真把我气糊涂了,”母亲大声说,“我还在度着蜜月呢。这个时候,就算是对我怀有宿怨的仇敌,也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不至于嫉妒我过上一段内心平静、幸福快乐的日子。大卫啊,你个淘气孩子!佩戈蒂,你个狠毒的东西!哦,天哪!”母亲大声说着,脸从我们一个转向另一个,气急败坏,态度固执,“这是个多么艰难的世界啊,本来还以为可以生活得尽可能开心愉快些的!”
我感到有一只手触到了我,知道那既不是母亲的也不是佩戈蒂的,于是从床上滑了下来,站在床边。那是默德斯通先生的手,他一边抓住我的胳膊一边说:
“怎么回事?克拉拉,亲爱的,你难道忘了吗?要坚定沉着,亲爱的。”
“很对不起,爱德华,”母亲说,“我是想好好表现来着,可我忐忑不安。”
“可不是嘛!”他回答,“这么快就听到这么糟糕的事,克拉拉。”
“我现在被弄成这个样子,真是太难堪了,”母亲噘着嘴说,“真是——太难堪——对不对?”
他把母亲拉到自己身边,对着她的耳朵轻声说着,还吻了她。我看到母亲的头倚在他的肩膀上,胳膊贴近他的脖子,这时候,我清楚地知道——清楚地知道,他能够把她温柔娴雅的性格塑造成他心目中想要看到的样子。正如我现在明白的,他这样做了。
“你下楼去吧,亲爱的,”默德斯通先生说,“我待会儿同大卫一起下楼。我的朋友啊,”他朝母亲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看着她离开,之后便黑着脸朝着佩戈蒂,“你知道你们太太的姓氏了吗?”
“我服侍太太很长时间了,先生,”佩戈蒂回答,“应该知道的。”
“是这么回事,”他回答,“但是,我想,我上楼时听到你对她说话,用的不是她的姓。你知道她已经随我姓了。你要记住,听见了吗?”
佩戈蒂神情不安地瞥了我几眼,一声不吭地行了个屈膝礼便出去了。我觉得,她看出人家希望她离开,况且也没有待着不走的理由。房间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关上门,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拉我站在他跟前,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的眼睛。我觉得自己丝毫不亚于他,目光被他吸引着,也盯住他。我现在回忆起我们当时对视的情形,仿佛又一次听到了自己的心急速剧烈地跳动着。
“大卫,”他抿着嘴说,嘴唇抿得薄薄的,“如果我要对付一匹犟马或一只凶狗,你认为我会怎么做?”
“不知道。”
“我揍它。”
我先前低声回答问题时气喘吁吁,但我觉得,这时缄口不言呼吸更加急促。
“我要让它害怕退缩、感到难受。我心里会想着:‘我要征服这家伙,’即便那样要了它的命,我也得这么办。你脸上是什么?”
“是污垢。”我回答。
他和我一样清楚,那是泪痕。但是,如果问上二十遍,每问一次都要扇上二十个耳刮子,我相信,自己幼小的心被撕裂了也不会这样告诉他。
“你人虽小心眼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