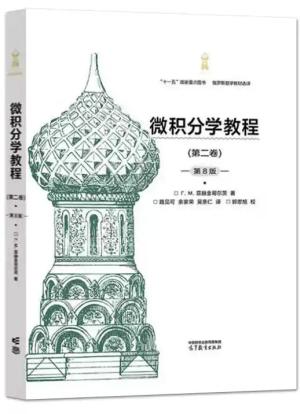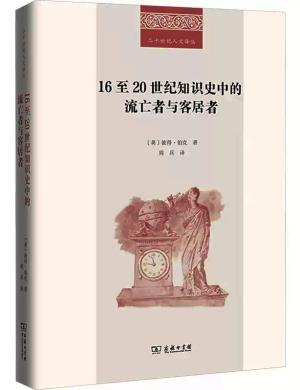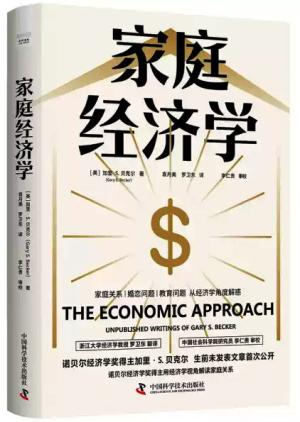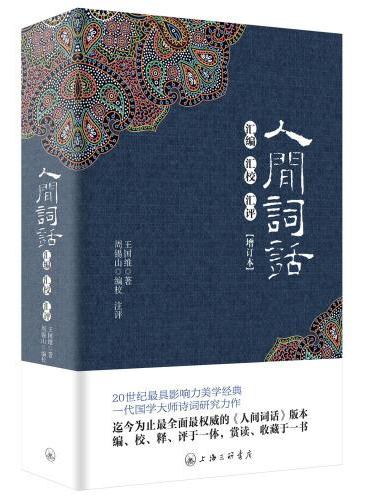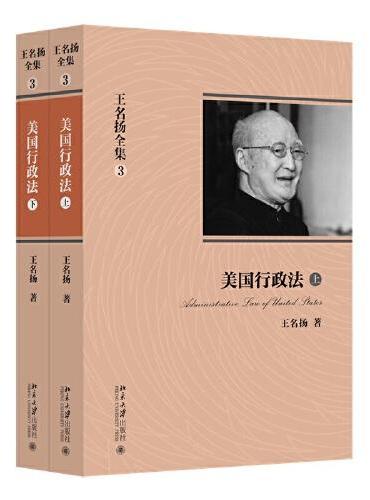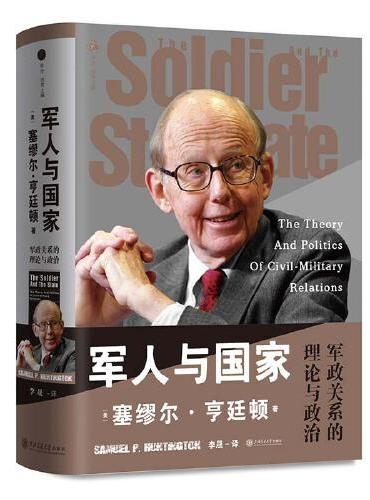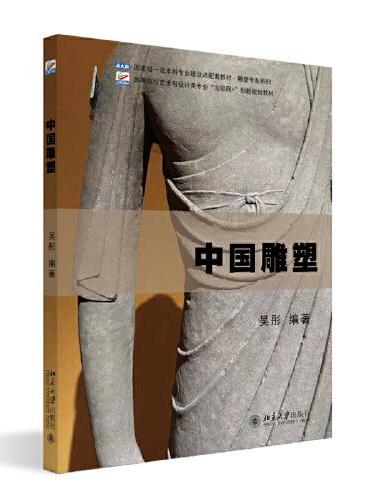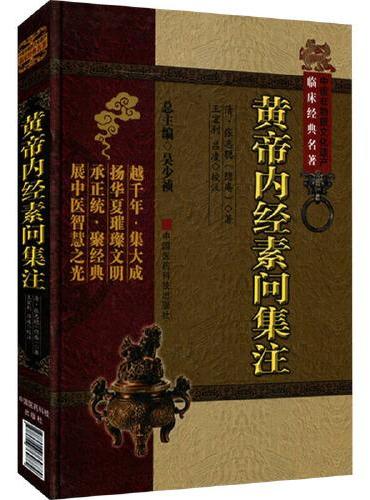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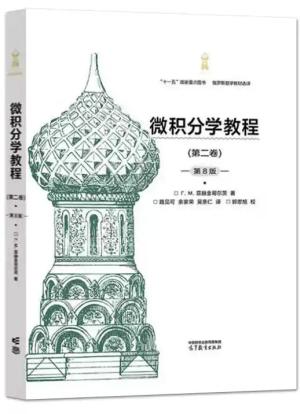
《
微积分学教程(第二卷)(第8版)
》
售價:NT$
5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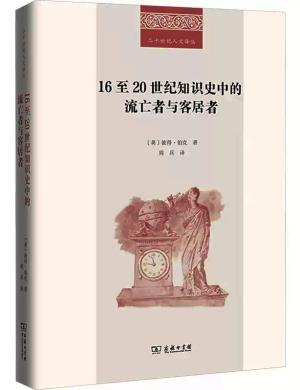
《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
》
售價:NT$
4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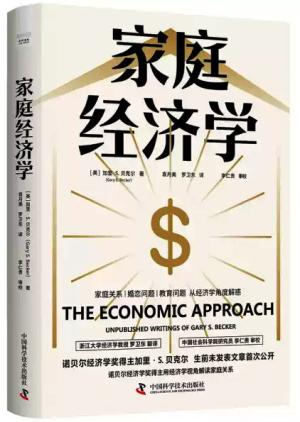
《
家庭经济学:用经济学视角解读家庭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S. 贝克尔全新力作)
》
售價:NT$
3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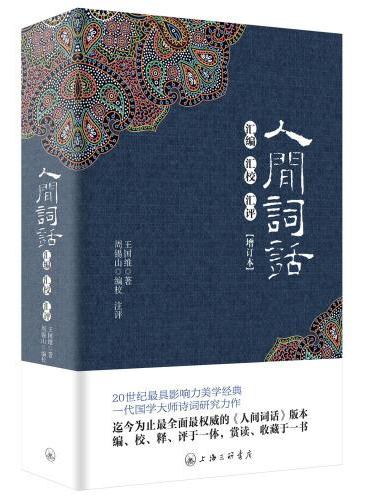
《
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新)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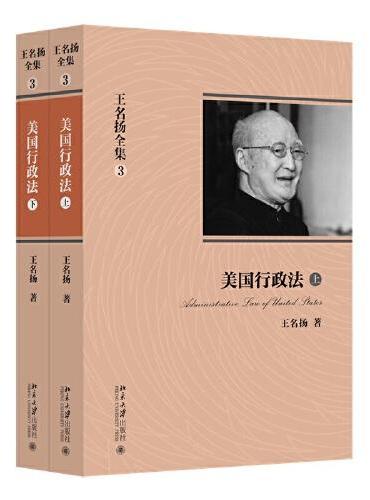
《
王名扬全集:美国行政法(上下) 王名扬老先生行政法三部曲之一
》
售價:NT$
8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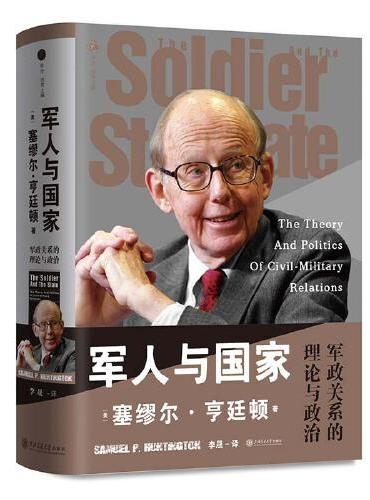
《
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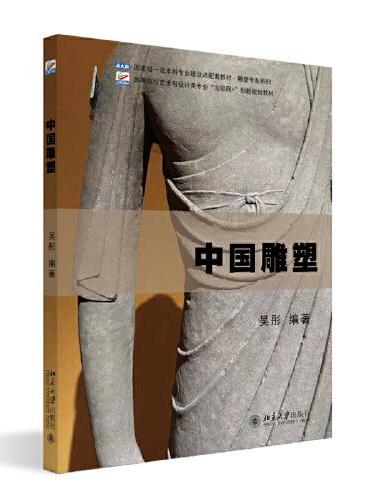
《
中国雕塑 高等院校艺术与设计类专业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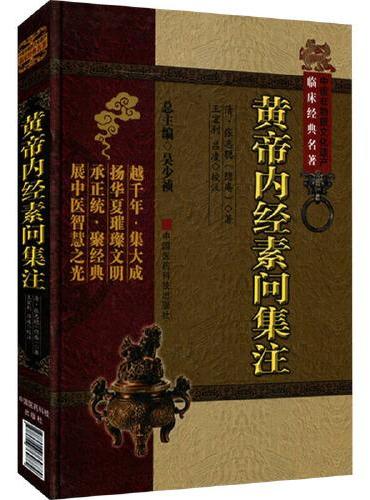
《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
》
售價:NT$
321.0
|
| 編輯推薦: |
17世纪,动荡、变幻莫测的欧洲政治生活和混战促进了思想的碰撞,对宪政主义的攻击被现代政治所取代。16世纪中叶围绕欧洲主要国家的宪政结构发生了一系列争论,17世纪的政治理论灵感来自16世纪晚期的国家理性思想,后向自然法理论转向。本书非常详细地追溯了16世纪中晚期到17世纪中期的政治哲学思想史,含丰富的史料信息,重点叙述了亚里士多德、格劳秀斯、利普修斯、马基雅维利、塞尔登、塔西佗、霍布斯的思想。
2. 拉夫的批评很具道德责任,反映了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对艺术的审美与政治关怀。
3. 本书系统而详细地介绍了拉夫的生平、生活,拉夫创办的重要文学、文化刊物《党派评论》,以及拉夫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政治及文学思想;是一部国内少有的介绍纽约知识分子重要的人物拉夫的基础而全面的专著。
|
| 內容簡介: |
|
本书考察了16世纪中晚期至17世纪中期的欧洲政治哲学思想,通过分析当时代表性理论家作品中对政治必然性和国家理性等概念的论证,展现了独特的现代政治词汇的形成过程。塔克重点关注了蒙田、格劳秀斯、霍布斯和英国革命理论家们的思想,重新审视了他们人文主义思想中概念词汇的起源,特别是怀疑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以及这些词汇在荷兰和法国革命期间的发展和使用。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考察了英国政治思想和欧洲大陆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将政治理论置于道德哲学历史的语境之下,为我们理解政治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
|
| 關於作者: |
|
理查德·塔克(1949—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政治思想史领域著名学者。作品包括《自然权利理论》、《霍布斯》、《战争与和平的权利》等,涉及论题涵盖政治权威、人权、自然法、对霍布斯、格劳秀斯、塞尔登、笛卡尔等思想家的研究等。现研究方向包括国际法、国际政治思想史、20世纪经济思想起源等。
|
| 目錄:
|
前言
第一章 文艺复兴的背景
第二章 怀疑主义、斯多亚主义与“国家理性”
第三章 新人文主义的传播
第四章 其他的类型
第五章 雨果?格劳秀斯
第六章 英国革命
第七章 霍布斯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前言
图利(James Tully)和我曾相约要合作完成一部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17世纪欧洲政治思想史。具体的分工是这样:以霍布斯成熟时期的著述为界(《利维坦》刚好出版于1651年),我负责17世纪的前半部分,图利负责之后的部分,大体上一直延续到乌德勒支条约签订、欧洲国家体系形成为止。不过,为了与习见的那种共同署名的著述有所区别,我们决定保持各自完成的两卷的独立性。于是,这两卷著述也就有了其各自的生命,它们各自的价值要留给读者去判断。
不过,无论我和图利的书有着怎样的区别,我们的研究路径基本上是相似的。自从我和图利在剑桥读书开始,我们之间就一直保持着充分的交流,尽管在观点及视野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关于政治思想史的写作,我们至少有如下两点共识。其一,要理解一种政治理论,首先必须成为历史学家,要尽可能深入地描述政治理论家的实际生活,以及他们所关注的实际政治问题。其二,但他们对这些实际政治问题的回应,却并非纯粹的历史研究所能含摄。它应当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时代所面对的基本相似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十七世纪政治中的基本冲突事实上以某种形态在二十世纪得以重现;我们认为,对这些冲突的历史理解越深刻,它们与当代处境的相关性就越能得到揭示。
当我开始这一卷的写作时,我意识到,对1600年到1651年的主要理论观念的叙述,不太可能是一种发人深思或者说讨人喜欢的研究。其原因在于,本卷的主题涉及的是这个历史时期对宪政主义的攻击、以及取而代之的一种工具性的、不择手段的现代政治。16世纪中叶,围绕欧洲主要国家的宪政结构曾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法国宗教战争和荷兰骚乱中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发生的冲突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昆丁·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二卷的基本主题。17世纪以降,一方面,各派别的宪政立场或多或少还有所延续,对此,斯金纳的文本已经提供了足够深入全面的研究;而基尔克的《自然法与社会理论1500-1800》也讨论了部分后起的宪政主义者的观点。不过,另一方面,毋宁说大部分17世纪政治理论对宪政主义的态度或是毫无兴趣或是充满敌意。我们将看到,它们的理论灵感更多来自16世纪晚期国家理性主义的论证——后者主要出现于1580年至1620年间,它很明显是一种反宪政(甚至反道德)的理论形态。
因此,我决定对我负责的这一部分内容有所取舍:本书认同斯金纳所归纳的16世纪宪政主义的特征,但对其在17世纪的承继者的关注将少于对其反对者即反宪政主义的关注。而其中重中之重是,以某种方式恰当地理解国家理性主义。同时,对国家理性主义的探索也引发了我对早期文艺复兴的重新思考,我注意到(在后来的历史学家看来),16世纪中期的宪政冲突之前、文艺复兴盛期所留存的大量文献,和16世纪晚期的文献有着惊人的相似——例如,马基雅维利就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理性主义的先驱。当然,二者之间也还存在着一些差别;最直接也是最为深刻的差异在于,晚期文艺复兴的学者往往把塔西陀视为古代的典范,而早期的学者则对塔西陀甚为反感,他们往往视西塞罗为典范。另一个更为细微的差别在于,后期文艺复兴的研究更为注重财富在国家中的作用,更多采取经济学的立场,而早期文艺复兴的学者则几乎无人采取重商主义的论证——事实上,重商主义恰是国家理性主义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我开始着手研究的就是这两类人文主义文献的区别,这也是本书第一章的主题。我发现,这两类文献最为重要的差别其实是16世纪晚期出现的怀疑主义:在国家理性的背后,是怀疑主义。这并没有多少好大惊小怪的——因为,置社会的道德法律规范于不顾,恰好是以对道德原则有效性的怀疑主义为必要前提。因此,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主题就是处理16世纪晚期遍及西欧各地的一种主流文化,即国家理性主义、斯多亚主义以及怀疑主义三者合流。怀疑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之间的关系又是重中之重(尤其是这类文化氛围中产生的最为重要的人物——蒙田),历史学者往往对此重视不够(他们往往按时序把蒙田的思想划分为似是而非的两个阶段:怀疑主义阶段和斯多亚阶段)。
为什么在怀疑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之间会产生联系?这是因为,正如它的古典先驱者一样,文艺复兴怀疑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态度,也是一种心理学态度:和别的哲学家一样,怀疑主义者同样是智慧的追求者,但是怀疑主义者往往持有这样一种意见,怀疑主义立场的前提在于,排除一切招致自我损害的意见——也就是说排除一切可能与他人或外部世界发生冲突的意见。斯多亚学派虽然也有类似的宏愿,但一个斯多亚主义者会倾向于认为,自我保存的智慧更多在于排除激情或欲望的干扰,而不在于排除意见的干扰。这两种态度之间的亲和度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完全有理由假定,大多数情感中都有某种认知性成分,只要能控制意见信念的干扰最终也就能控制或排除情感的干扰。正是基于对此类自我控制主题(在图利看来,这也是下一个世纪的标志之一)的考察,本书的书名才定为《哲学与治术》(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因为,我们的主题并不只是国家的治理(Government),也是自我的治理。此类自我规训的政治类比转化为“国家理性”理论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明显,国家基于安全和利益的考虑,也会对所治的人民采用规训和调控的手段。
正如上个世纪的西塞罗主义式的人文主义一样,这类新起的文化并不是没有遭遇挑战,本书第四章处理的就是这一主题。本章我将着重处理这个世纪初仍然保持生命力的宪政主义。有意思的是,这一章中德国思想的地位几乎是独树一帜的,因为,德国知识界对塔西陀主义及其后继者格劳修斯的现代自然法学派都持保留态度。普凡道夫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德国知识界人士属于新人文主义文化的行列,即便是普凡道夫自己,其对新人文主义的批判也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多得多。无疑,这涉及到新人文主义的基本特质——它和所谓“国家建设”问题的联系。无论是怀疑主义者还是如格劳修斯、霍布斯这样的后怀疑主义者,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怎样有效地建设一个1650年之前已经遍及欧洲并开始席卷世界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但德国却处于这一进程之外:神圣罗马帝国领土上的战争(部分地)阻止了这一进程的展开,而德国政治理论则体现出德国对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抵触。
关于国家理性主义引起的反弹就到此为止,本书余下的章节将处理17世纪中叶发生在国家理性主义那里的向现代自然法理论的伟大转型。17世纪思想的转型是我所提出的首要的历史观,我很清楚,仅从思想史素材来看,我的观点是与通常的观点极为不同。从表面上看,格劳修斯、霍布斯和洛克并没有使用国家理性和怀疑主义式的语言,他们使用的是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语言,因而,仅就其表面而言,这套语言与13世纪经院哲学的语言是极为相似的——虽然后者在16世纪恰恰是塔西陀主义的对手——过去一个世纪以来,17世纪学者使用的这套词汇表导致很多学者认为,中世纪和现代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断裂;13年前我的《自然权利理论》其主题之一即研究17世纪自然权利语言的中世纪起源。但即使在那本书里我也曾提到,那个时代最为聪颖也最为敏感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学说与中世纪学者的显著不同。从普凡道夫到康德,道德史的编纂者一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17世纪以后才出现了一种考察道德和政治现象的真正现代和“科学”的方法,其研究路径的新异之处在于,它是对怀疑论式的相对主义的回应。而关于17世纪学者的传记或许只会提醒我们,诸如格劳修斯和霍布斯这样的学者与经院哲学家之间存在的鸿沟仅仅是他们广泛的人文主义兴趣、或者说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这和莫里纳(Molina)、苏亚雷斯等经院哲学家——更不用说此前的维多利亚(Vitoria)或阿尔曼(Almain)等人——有着显著的分别。
道德史学家一般认为,这场新思想运动中的大人物是雨果·格劳修斯、约翰·赛尔登、托马斯·霍布斯以及萨缪尔·普凡道夫——而最为著名的道德史学者巴贝拉克(Jean Barbeyrac)更是指出,格劳修斯是“打破坚冰”的第一人。洛克或者也可以忝列其中。不过,在许多当代学者看来,道德史学家之所以认为格劳修斯是重要的,其理由多少令人吃惊。这是因为,道德史学家的历史叙述后来被康德所摧毁。康德对格劳修斯及其后继者提供的对相对主义的回答极为不满,他试图以自己的学说体系为典范重写整个伦理学史。康德之后的流俗哲学史往往追随康德贬低17世纪自然法学者的突破性成就;然而,一旦我们更为深入地接触17世纪学者的著述,更为深入地体会他们对相对主义问题的回应方式,我们或许就能体会到道德史学家的历史叙述要更为准确得多。当代学者中只有巴蒂斯塔(Anna Maria Battista)1966年出版的在英语国家鲜为人知的著作持有类似的观点。
事实上,我赞同的毋宁是前康德的立场,即认为格劳修斯是这个传统中最有创造性的人物。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指出的那样,格劳修斯觉察到,怀疑主义的心理学前提是它的道德假设。前文曾提到,怀疑主义者关注智慧之路,而智者的生命恰恰在于排除激情和意见的干扰。不过,他们的理论就此而言赋予了自我保存的原则以某种中心的普适的地位(斯多亚学派的立场也大体相同),而自我保存的普适性恰恰对怀疑主义者的相对主义立场提出了挑战。格劳修斯及其后继者将自我保存视为最为根本的自然权利,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后世名之为“自然法学”(natural jurisprudence)的基本结构。循着自然权利的线索,他们提出了某种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后者在大多数场合仅仅意味着,如无必要、勿伤他人(亦即除非出于自我保存的需要)。
在第六章我试图将英国革命的观念纳入讨论的语境。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所习见的是英国革命的宪政主义一面及其向回看诉诸传统的一面,此类政治文献可谓层出不穷;然而,本章的论述可能又一次令他们感到意外;同样感到吃惊的可能还有道德史学家,他们会看到,霍布斯或格劳修斯的思想和平等派(Levellers)的观念得到同等对待。毕竟,1642年到1650年的英国革命是17欧洲最为重大的政治危机,它深刻影响了荷兰和英国的政治理论家。我们将看到,国家理性和塔西陀主义式的新人文主义在一个欧洲主要国家成为基本政治的选项之一;事实上,英国革命与法国宗教战争的区别就在于,英国革命中的当事人其行动领域要比法国宽广得多,他们对旧制度的攻击也要比法国成功——1649年1月人格化为。将17世纪晚期的启蒙政治推向道德史上的神坛,既有当事人的行动,也有伟大的理论。
第七章我将转向霍布斯。事实上,本书的全部内容都可以看作对霍布斯理念的补充说明,因为此前半个世纪政治理论的主题都在霍布斯那里得到体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代表了国家理性转化为自然法学的最令人信服:他的认识论是怀疑主义的,他的伦理学是相对主义的,而他试图在自我保存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人性的科学。蒙田曾指出,为了自我保存,我们应当摒弃自我的意见,顺应祖国的法律和习俗;霍布斯同样主张,为了享有安全,我们应当放弃自我的判断,顺从于我们的主权者制订的法律。霍布斯当然还是这个时代最有魅力也是最为敏锐的学者,但我以为他的原创性或许并不像通常的哲学史所认为的那样。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格劳修斯才是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霍布斯对相对主义的认识比同时代的哲学家要深刻得多。凭此他仍然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最为重要的奠基人:现代国家的结构从霍布斯的时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他对这一国家结构的政治论证依然是我们的范本。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大卫·伍顿(David Wootton)是这个计划的发起者之一,他最初也参与了这个计划;昆丁·斯金纳和约翰·邓恩自始至终阅读了本书的稿件,提出了不少有洞察力的意见,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杰瑞米·迈诺特给予我很多鼓励。安东尼·帕格顿(Anthony Pagden)和帕斯夸尔·帕斯魁诺(Pasquale Pasquino)也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另外,书中一些基本观念的形成还得益于我和约翰·波考克、伊什特万·洪特(Istvan Hont)、彼得·伯克、霍赫斯特拉塞尔(Tim Hochstrasser)、霍华德·莫斯、彼得·米勒、迪安·克南(Dean Kernan)、沃尔特·约翰逊、彼得·博尔施伯格(Peter Borschberg)以及数不胜数的剑桥大学本科生之间的讨论。洪特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所投入的关心和帮助足堪表率。在本书完成之前,维罗里允许我阅读了他正在写作的关于国家理性问题的杰出论著的手稿,因此我得以修正关于国家理性起源问题的一些观点,但我并没有完全采纳他的看法。此外,我不知道在这里表达对于本书原本的共同作者图利的感谢是否恰当,不过,一直以来对他我总是所欠良多,是他让我一次次地感到本书的意义所在。
本书中的翻译除了标明的译本之外,都来自于我个人的译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一般采用作者的本国语言的姓名,而不是其拉丁语名,但也有少数例外,比如我仍然沿用格劳秀斯的拉丁语名(Grotius),而不采取其荷兰语名德·格鲁特(De Groo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