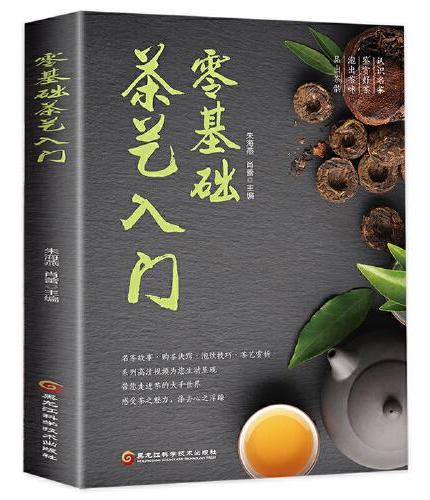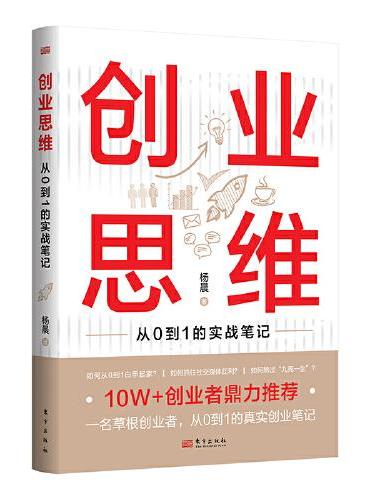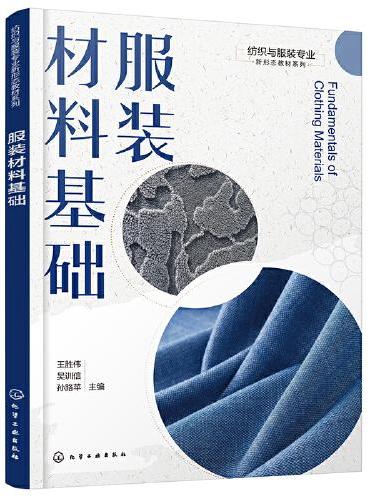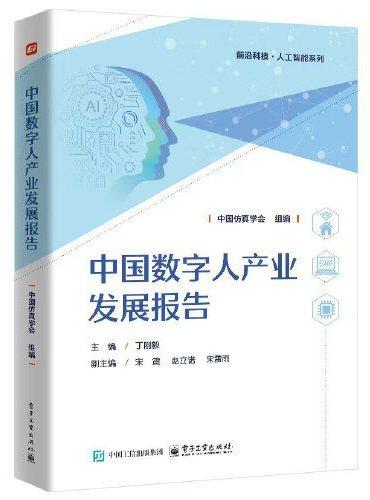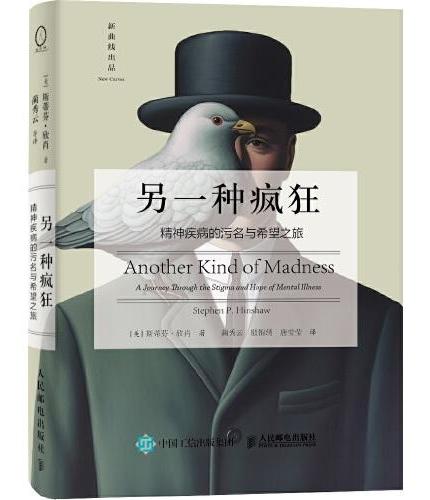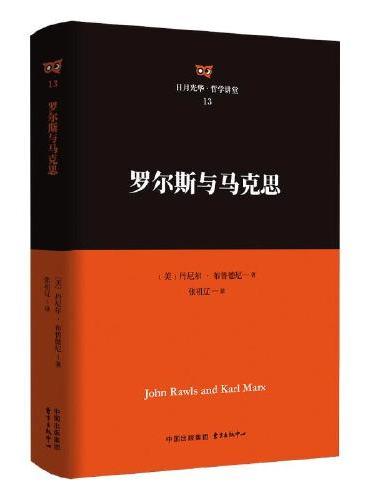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新版-零基础茶艺入门
》 售價:NT$
179.0
《
创业思维:从0到1的实战笔记
》 售價:NT$
356.0
《
家庭财富管理指南
》 售價:NT$
398.0
《
服装材料基础
》 售價:NT$
296.0
《
国家名片C919(跟踪十余年,采访百余人,全景式呈现中国大飞机C919,让读者领略到中国航空科技的最新成就)
》 售價:NT$
653.0
《
中国数字人产业发展报告
》 售價:NT$
500.0
《
另一种疯狂:精神疾病的污名与希望之旅(APS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斯蒂芬·欣肖教授倾其一生撰写;2018年美国图书节最佳图书奖)
》 售價:NT$
296.0
《
罗尔斯与马克思
》 售價:NT$
398.0
編輯推薦:
最受欧洲人喜爱的美国畅销书作家
內容簡介:
在十三岁生日那天晚上,简·霍华德宣告:“我永远不会结婚,也永远不要小孩。”
關於作者:
道格拉斯·肯尼迪
內容試閱
十三岁生日那天晚上,我宣告:“我永远不会结婚,永远不要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