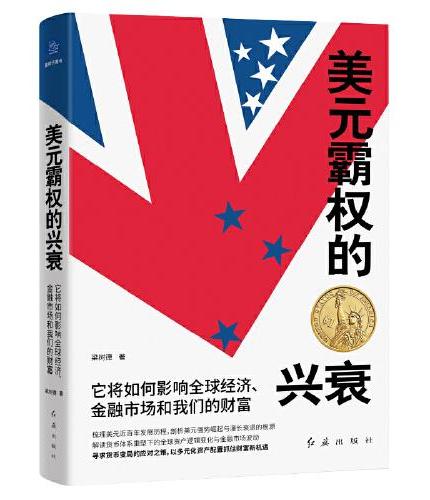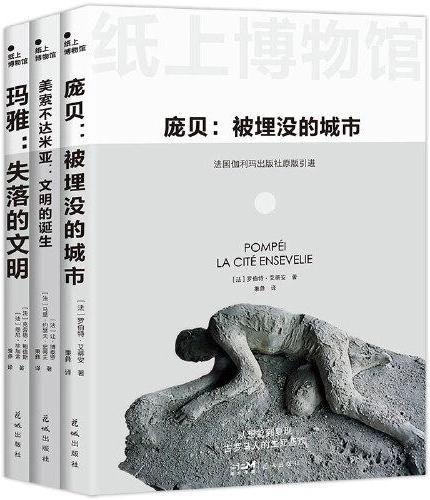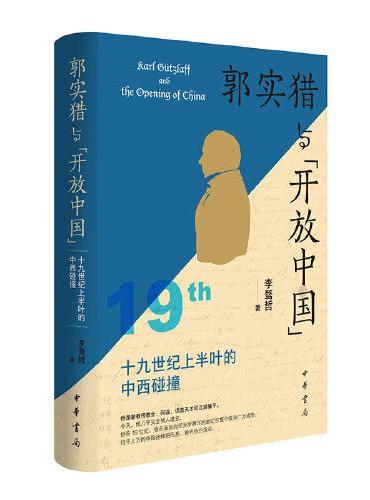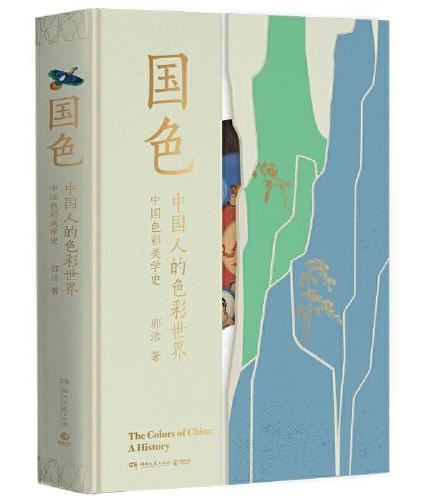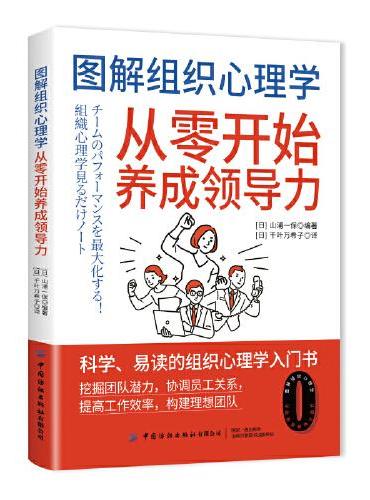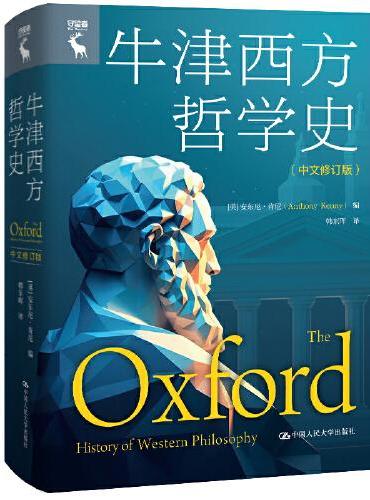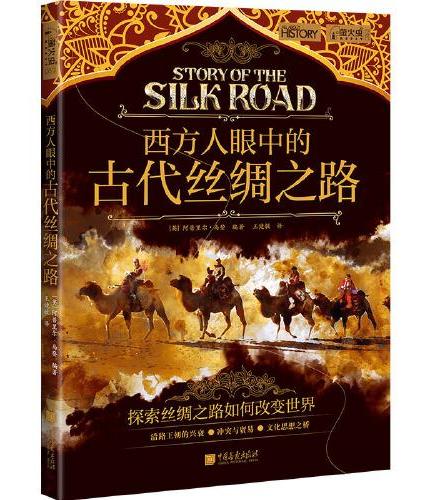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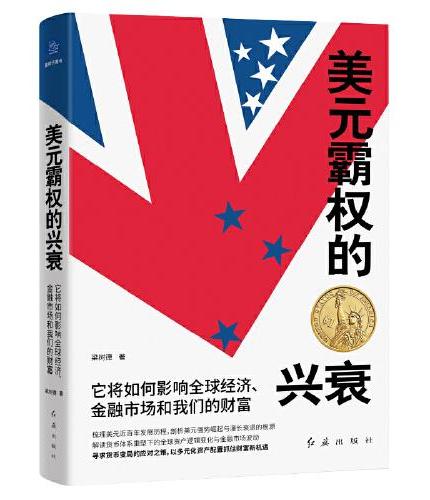
《
美元霸权的兴衰:它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和我们的财富(梳理美元发展历程,剖析崛起与衰退的根源)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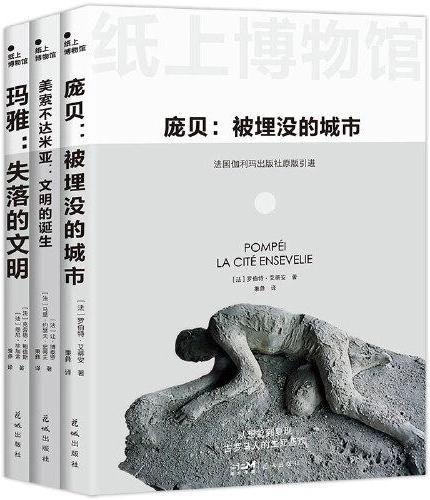
《
纸上博物馆·文明的崩溃:庞贝+玛雅+美索不达米亚(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450+资料图片,16开全彩印刷)
》
售價:NT$
12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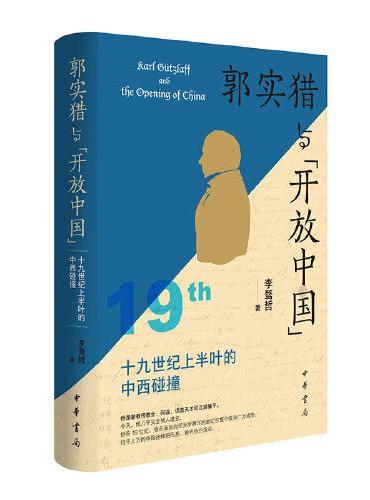
《
郭实猎与“开放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中西碰撞(精)
》
售價:NT$
347.0

《
海外中国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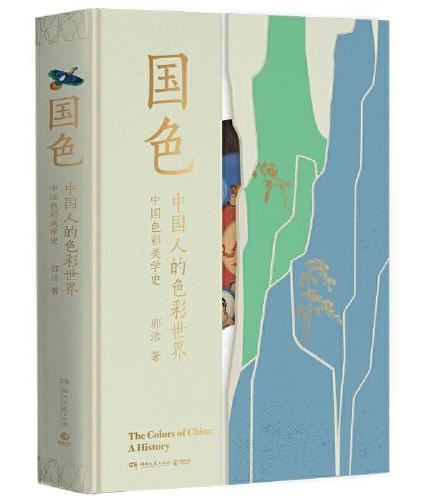
《
国色(《寻色中国》首席色彩顾问郭浩重磅力作,中国传统色丰碑之作《国色》,探寻中国人的色彩世界!)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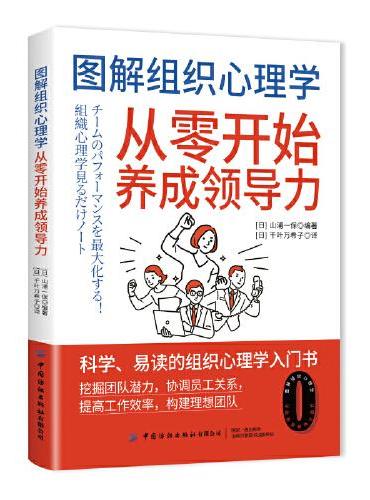
《
图解组织心理学:从零开始养成领导力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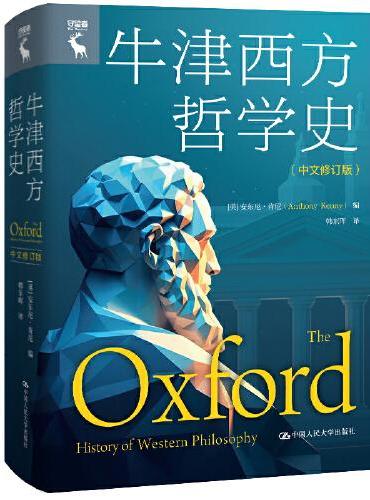
《
牛津西方哲学史(中文修订版)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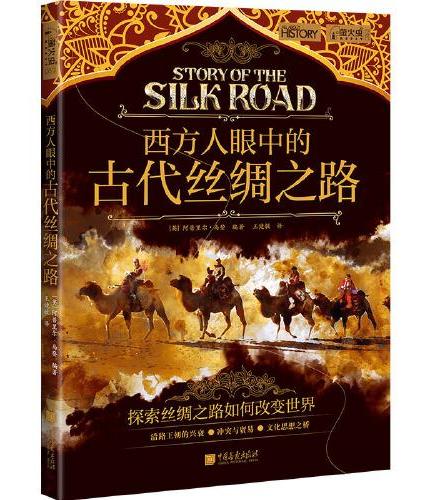
《
萤火虫全球史:西方人眼中的古代丝绸之路
》
售價:NT$
388.0
|
| 編輯推薦: |
以赛亚·伯林是享有国际声望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
伯林交游广泛,与众多同时代的杰出人物都有私交。本书收录19位名人,绝大部分,伯林都亲自见过,熟悉他们的生活、轶事。
《个人印象》极好地体现了伯林风格:生动诙谐的谈话、敏锐的观察、犀利的见解、深情传神的叙述,曾被董桥喻为“伯林最好看的一本书”。
《个人印象》收录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哈伊姆·魏茨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吉尼亚·伍尔夫、埃德蒙·威尔逊等19位名人,在知识界和政界都有巨大影响和个人魅力。
|
| 內容簡介: |
|
《个人印象》记录了19位20世纪知识界和政治界的著名人物,比如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哈伊姆·魏茨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吉尼亚·伍尔夫、埃德蒙·威尔逊等。这些人,除罗斯福外,伯林都亲自见过,对他们非常熟悉。伯林以自然天成的幽默感、睿智轻松的语言、不带恶意的勃勃兴致讲述了他自己对这些人物的个人印象。《个人印象》书中还详细描写了1945年和1956年在前苏联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会面,感人至深。《个人印象》书末的跋,伯林概述了他个人人格的三条主线:俄国人、英国人和犹太人。
|
| 關於作者: |
|
以赛亚·伯林(1909—1997),出生于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六岁时举家迁至俄国,目睹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入读伦敦圣保罗学校和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先后担任全灵学院和新学院研究员、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沃尔夫森学院首任院长,曾任不列颠学会(英国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院)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俄国思想家》、《概念与范畴》、《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观念的力量》、《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自由及其背叛》、《自由论》、《苏联的心灵》等。作为杰出的观念史研究者,先后被授予伊拉斯谟奖、利平科特奖和阿涅利奖。
|
| 目錄:
|
第一版自序
编者序
序言
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
哈伊姆·魏茨曼
爱因斯坦和以色列
伊扎克·萨德赫
刘易斯·伯恩斯坦·纳米尔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在牛津
理查德·佩尔斯
休伯特·亨德森在全灵学院
约翰·兰肖·奥斯汀和牛津哲学的早期起源
约翰·佩特罗夫·普拉门纳兹
莫里斯·鲍拉
戴维·塞西尔
回忆弗吉尼亚·伍尔夫
埃德蒙·威尔逊在牛津
奥伯伦·赫伯特
奥尔德斯·赫胥黎
1945年和1956年与俄罗斯作家的会面
跋:我生命中的三条主线
索引
|
| 內容試閱:
|
1945年和1956年与俄罗斯作家的会面
每一个追求连贯记忆的尝试,到头来都是作假。人们的记忆无法按照顺序逐一重温旧事。书信和日记经常于事无补。
——阿赫玛托娃
一
1945年夏天,我还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当临时官员的时候,被告知下一步要被派到驻莫斯科大使馆几个月,说是那里缺人手,而我会俄语,并且在(此前不久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多少了解一些美国对苏联的官方和非官方态度,可以补缺到年底。战争结束了。波茨坦会议并没有使胜利的盟友之间出现公开裂痕。虽然西方一些地区有不祥的预感,但在华盛顿和伦敦官方圈子里总的情绪还是审慎乐观;在公众中间和媒体上是满怀希望甚至是热忱:苏联人民在抗击希特勒的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和作出的令人吃惊的牺牲,为他们的国家赢得了广泛同情,在1945年下半年,这让很多批评苏维埃体制及其做法的人三缄其口,人们广泛而热切地期待着互相理解和全方位合作。我在这样一个苏英双方充满美好感情的季节里,动身前往莫斯科。
从我家1920年离开(当时我十一岁),我就没有回过俄国,也从未访问过莫斯科。我初秋时节来到这里,在衡平法院(Chancery)分到了一张办公桌。虽然我每天早上要在大使馆报告工作,但我唯一的任务就是阅读莫斯科的报刊,做新闻摘要和评论。这项工作并不费劲:与西方报刊比起来,这里的刊物内容单调、重复而可以预知,实际上是千篇一律。这样我就有了大量空闲时间,就去参观博物馆、古迹和建筑、剧院、书店,在大街上闲逛。与大多数从西方来的非共产主义访问者完全不一样的是,我很幸运地会见了几位俄国作家,他们中至少有两位是杰出的天才。在叙述我与他们的会面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在苏联的十五周时间里所看到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文艺界的情况。
俄国诗歌的繁荣始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艺术上许多大胆而具有创造性、影响广泛的实验。新运动中的主要潮流,包括绘画和雕塑上的符号主义、后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抽象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至上主义和构成主义,戏剧和芭蕾中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特别是诗歌中的阿克梅派、自我未来派和立体未来派、意象派、“超感觉”等等,并没有被战争和革命所拘束,而是继续从新的视角汲取活力和灵感。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艺术趣味是保守的,但那些给予布尔乔亚趣味“当面一耳光”的东西受到了支持和鼓励:这为激动人心的宣言,为所有艺术和评论上大胆而存在争议、富有天分的实验开辟了道路,这些不久之后就对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些作品在革命后幸存的文艺家中,最具有原创性的诗人有:勃洛克、伊万诺夫、别雷、勃留索夫和稍后一代的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赫列布尼克夫、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最具有原创性的画家有:波诺瓦、罗列赫、索莫夫、巴克斯特、拉里欧诺夫、冈察洛娃、康定斯基、夏卡尔、苏丁、克林、马勒维奇、塔特林、利西茨基;最具有原创性的雕塑家有:阿尔奇片科、伽勃、佩夫斯纳、利普契兹、查德金;最具有原创性的制片人有:梅耶荷德、瓦赫坦戈夫、泰罗夫、爱森斯坦、普多夫金;最具有原创性的小说家有: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巴别尔、皮利尼亚克。这些人的名字在西方广为人知。他们并不是一座座孤立的山峰,而是被大片的丘陵烘托着。俄国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这与其他国家艺术界的情况是不同的。小说家、诗人、艺术家、评论家、历史学家、科学家之间互相借鉴,这造就了一种具有罕见活力的文化,形成了欧洲文明中非同寻常的上升时期。
坦白地说,所有这些好得过了头,难以持续下去。战争和内战的破坏、饥馑、独裁统治对各种生活和机构的系统性破坏,其政治后果就是结束了诗人和艺术家自由创作的条件。经过实行新经济政策那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变得强大起来,足以挑战并在20年代后期粉碎所有这些非组织的革命性活动。社会需要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无产阶级艺术。评论家阿维尔巴赫带领一帮马克思主义狂热分子,反对所谓放纵的个人主义的文学异端,或所谓形式主义、颓废的唯美主义、对西方卑躬屈膝、反对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迫害和清洗开始了。但因为胜负难料,这在一段时期里给文学生活带来了某种不祥的动荡。终于,在30年代初期,斯大林决定结束所有这些政治—文学争论,他显然认为这些争论只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左翼狂热分子被清算了;再也听不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或集体主义的创作和评论,也听不到各种形式的反对声音。1934年,党(通过新成立的作家联盟)直接管理文学活动。国家控制的正统观念带来了一片死寂:不再争论;人们的思想不再躁动;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技术和教育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世界这个敌人的物质成就。当务之急,是把没有受过教育的广大农民和工人组织成为一个军事和技术上不可战胜的现代社会。新的革命秩序被千方百计要毁掉它的敌对世界所包围。政治上的紧张气氛,容不得高水平的文化和争论,也容不得关注公民自由和基本人权。旋律必须由体制权威来确定;那些影响犹存的作家和艺术家,必须按照这个旋律起舞。
一些人表示顺从,一些人多多少少不顺从。一些人对国家监督感到很压抑,其他人则接受甚至表示欢迎,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会赋予他们一种被市侩而平庸的西方人所否定的地位。1932
年出现了一些宽松迹象,但并未成为现实。随后是恐怖:大清洗,这从1934年基洛夫被暗杀之后的镇压和臭名昭著的政治公开审判开始,在1937年至1938年的叶若夫恐怖——疯狂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个人和集团,后来是对所有人的滥杀——达到高潮。当时在党和国家具有巨大声望的高尔基还活着,起到了一种缓冲作用。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作为“革命的声音”的名望和声誉堪比高尔基,他在1930年自杀了——高尔基六年之后去世。稍后,梅耶荷德、曼德尔施塔姆、巴别尔、皮利尼亚克、克留耶夫、评论家D.S.米尔斯基、格鲁吉亚诗人亚什维利和塔比泽——这里提到的只是最知名的人物——遭到逮捕并被处死。几年后的1941年,刚从巴黎回来不久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自杀身亡。告密者和非法监视者的活动无孔不入。自我否定、屈意招供、屈服于当局或主动合作,也常常不能使这些知名人物逃脱毁灭的命运。至于其他方面,它给一些从恐怖时期幸存下来的人们,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忘却的痛苦而又屈辱的回忆。
有关这个危险时期——这在俄国的历史上既不是第一次,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记录,我们可以从N.曼德尔施塔姆、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等人的回忆录,以及在另一层意义上从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安魂曲》中看到。遭到流放和杀害的作家和艺术家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1939年的俄国文学、艺术和思想界,就像遭受了可怕的狂轰乱炸,只有几座像样的建筑还相对完好,孤零零地矗立在满目疮痍、荒无人烟的街道上。斯大林终于停止了各种迫害活动:有了呼吸空间;19世纪的经典作品再次受到尊重,旧街名代替了革命的街名。但在这个恢复期,创造性和批判性的艺术实际上是一片空白。
接下来是德国的入侵,情况再次发生变化。这样一些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并且努力保持形象的优秀作家,对爱国主义情感的洪流反应热烈。某种程度的真实性回到了文学中:所有战争诗歌,不仅仅是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所写的诗歌,都源于深厚的情感。在所有俄罗斯人都卷入民族团结高潮的那些日子里,关于清洗的噩梦被关于爱国的抵抗和英雄般殉难的悲壮而令人解放的感觉所取代。俄国的作家,无论老少,都表达了这一点,特别是他们中那些真正有风格的诗人,都被当作偶像来崇拜,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令人惊讶的现象发生了:那些诗人的作品曾经被当局看不顺眼,因而很少出版并且版本非常有限,现在他们开始收到许多前线战士的来信,信中所引用的通常是他们那些表达个人情感的、与政治几乎无关的诗句。据说,勃洛克、勃留索夫、索洛古勃、叶赛宁、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被战士、军官甚至是政治委员们广泛阅读和背诵。曾经长期生活在某种国内流放状态中的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收到的前线来信数量惊人,这些来信引用他们的诗歌,既有公开出版的,也有从未发表过的,多半以手抄本形式私下流传;有索取亲笔签名的,有求证手稿真实性的,有寻求作者对各种问题表态的。最终这一现象深深触动了一些党的领导人:这些作家作为爱国声音——祖国有一天会感到骄傲——的价值,被文学界的官僚们逐渐认识到了。结果是诗人们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人身安全也获得了保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