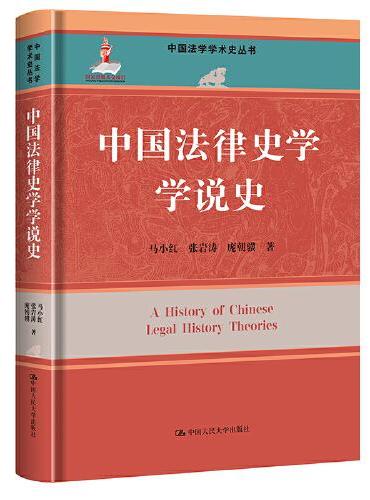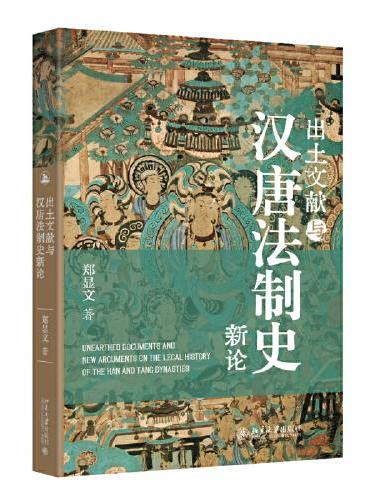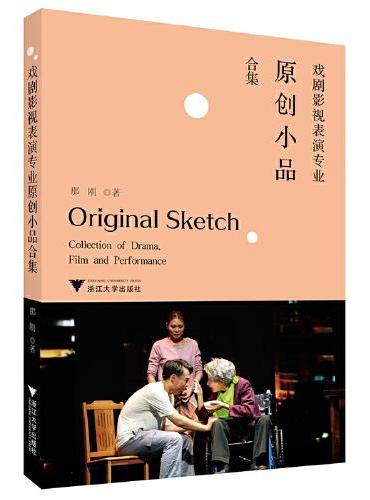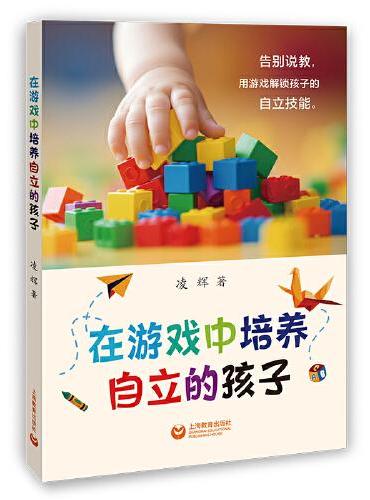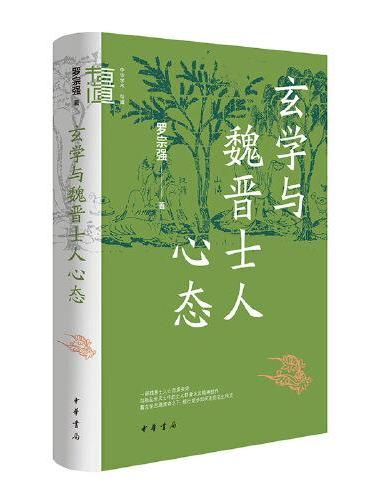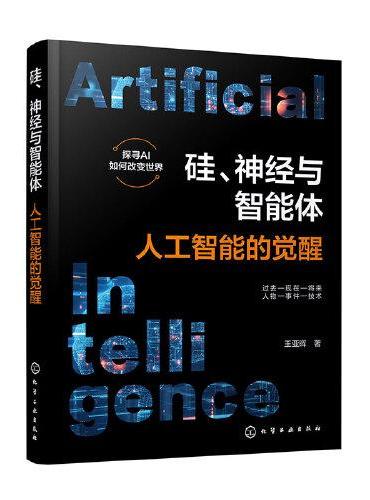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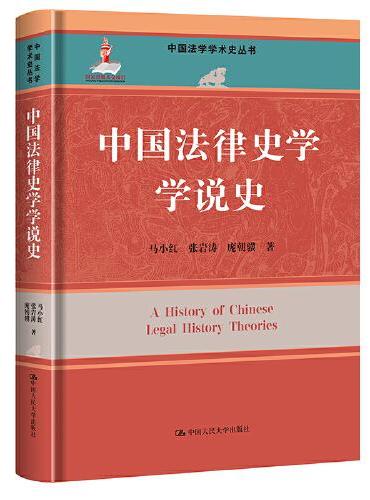
《
中国法律史学学说史(中国法学学术史丛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售價:NT$
857.0

《
方尖碑(全2册)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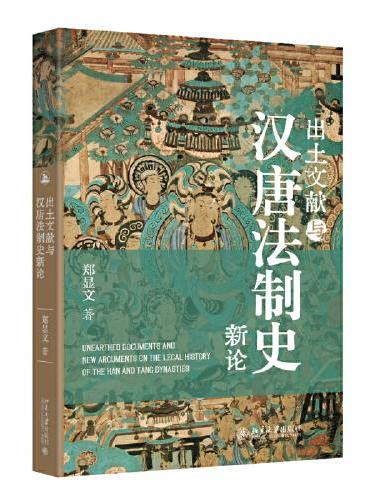
《
出土文献与汉唐法制史新论
》
售價:NT$
398.0

《
最美最美的博物书(全5册)
》
售價:NT$
7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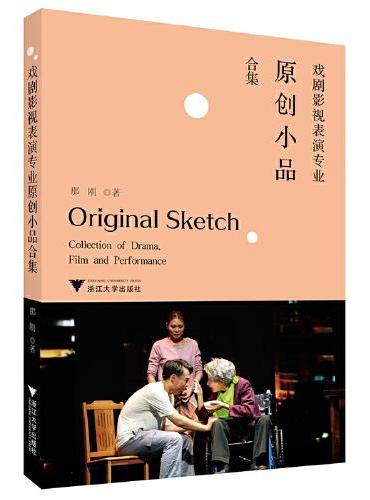
《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原创小品合集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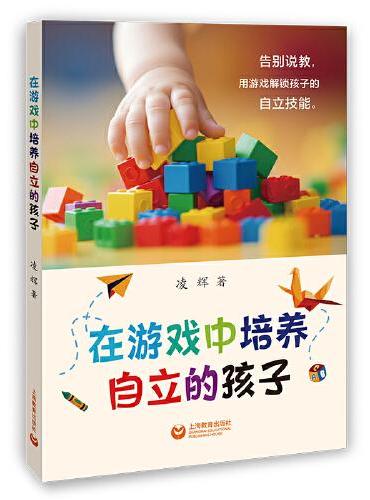
《
在游戏中培养自立的孩子
》
售價:NT$
2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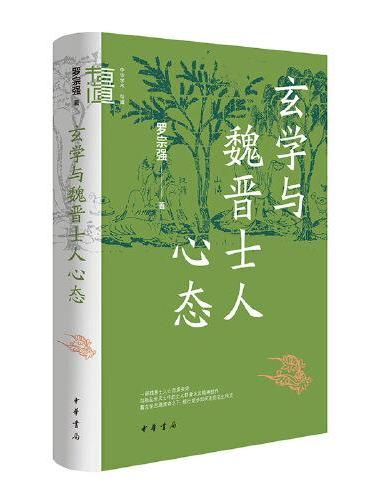
《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精)--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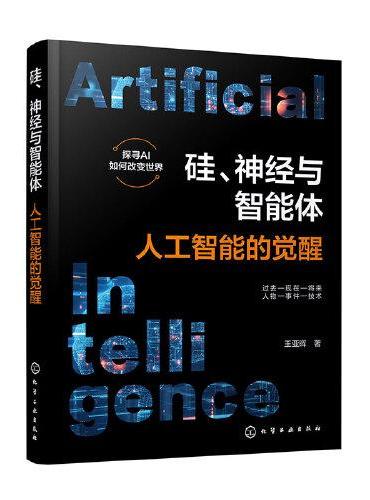
《
硅、神经与智能体:人工智能的觉醒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当代最具盛名的“治愈力”专家
《时代周刊》盛赞的心理学大师
一段感动欧洲的心路历程
一个原本该破碎生命的倾情讲述
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
有悲伤的勇气,生命才能向前
法国亚马逊心理类总榜排名第一
西班牙、德国、意大利、丹麦多国文化界人士感动推荐
西瑞尼克治愈了众多人,众多国家
《时代周刊》
|
| 內容簡介: |
《走出悲伤》,一位世界级心理学大师的生命剖析。这本书中,心理学家西瑞尼克不惧自我解剖,他努力搜寻那些已被埋藏的记忆,质问那些记忆的陷阱,并试图说出在重获安全和自由之后想说而无法说出的感受,探求走出悲伤的心路历程。他以自身经历告诉那些心中有伤的人,走出悲伤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是和他人保持重要的良性联系,二是相信生命与生俱来的内在能量。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的悲伤和命运的曲折,是生活在这尘世中无法避免的修行,我们不能阻止和压抑自己的情绪,但可以选择与悲伤相处,克服悲伤的力量。
人不但能在不幸的阴影中继续活着,而且能够更强大地活着。
要有悲伤的勇气,生命才能向前。
|
| 關於作者: |
【法】鲍里斯?西瑞尼克
(Boris Cyrulnik)
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人类和动物行为学家,土伦大学教授,在欧洲领导着多个学术前沿的研究室。以在心理创伤方面的研究享誉世界。
身为一个犹太人,他童年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朋友,生活自此动荡,七岁的他作为孤儿还被特意安排越过敌军的封锁给法国军队送情报。直到二战结束,他的世界才得以静下来。
此后他接触到心理学,开始进行系统地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了自我,治愈平息了过去的回忆,并最终成为了治愈无数人的心理学家。
|
| 目錄:
|
编者序 在悲伤中更强大的活着
第一章 有一种谎言叫
“别担心,我很好”
嘘,我是犹太人
也许,是我害死了妈妈
我是谁?谁是我呢?
洪水猛兽比我受欢迎
如此死去岂不可惜
战争结束时,恶魔来了
讨好自己,不在旧伤中画地为牢
人生很长,与往事温柔相处
美化过去,我已习惯自欺
我的身后尾随着一个幽灵
说出来,给黑暗记忆一个出口
回忆中没有100%的真实
第二章 心痛:没有伤口,却很疼
世界瞬间如大漠一般荒芜
我在鱼缸里动弹不得
原谅我无法云淡风轻地说起曾经
他们说,战争很美
美丽而悲伤的幽灵
不幸不再时沦为噩梦的人质
感谢你给我一根稻草
有一种坚强叫脆弱
记忆和现实的冲突:难道我记错了
所谓合理,取决于我们能否理解
第三章 我的心里有间隐秘的地下室
我讲述另一个我
拼不完整的记忆拼图
我活了下来,我比死亡更强大
我只讲述别人感兴趣的经历
对悲痛的记忆,绝口不提
记下点滴,虚构比事实更慈悲
小说,隐秘的控诉
同情,或多或少都是假的
第四章 一个人的围城,无法分享的惆怅
不能被分享的个人创伤
借着当下的光,故事真相大白
说不清为什么回忆是美的
迷失乌托邦
共同话题,让人和人亲近
小大人的讲述:假装没有受伤
感恩悲痛的经历给我反常的勇气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第五章 与往事干杯,走出悲伤的练习
回忆里的二度伤害
我的复原力保护人
生命重返,春暖花开
我们可以毫无幻想地活着吗
创伤禁止我讲述疼痛
冰封的记忆开始融化
环境允许我吐露真相
否认过去,逃避现实的代价
没有怨恨,亦无原谅
附录
奥迪勒?雅各布出版社的作者
|
| 內容試閱:
|
嘘,我是犹太人!
那年我六岁,“死”这个词于我而言显得过于生涩,直到我被逮捕后的一两年里,我才对死有所了解生命不可重来。
法尔热太太穿着长睡衣,一边往我的小箱子里塞衣服,一边说道:“如果你们放他一条生路,人们就不会以为他是犹太人了。”我很震惊,这些男人显然想取走我的性命。
听完法尔热太太这番话,我明白了他们用枪指着我的缘由我是犹太人!
犹太人意味着什么,我一无所知。但就在那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活下去,就不能说自己是犹太人。
他们把我弄醒,一只手拿着枪,另一只手拿着电筒,头顶着毡帽,鼻梁上架着黑色眼镜,上衣的领子向上翻起,多么可怕的一幕!难道枪毙一个小男孩,人们就要这打扮吗?
一个看起来像长官的男人回应道:“立刻让这个孩子消失,否则他很快就会成为希特勒的敌人。”我被判了死刑,可我不知道错在哪里。
这个夜晚发生的事情,在我身体里催生出一个扎根于我灵魂的人影 :想取走我性命的手枪,夜色中的黑色眼镜,走廊里肩挎长枪的德国士兵,那句揭露我未来罪犯身份的话语……
我即刻明白了:这群成年人草菅人命,完全不顾惜生命的宝贵。
然而,你们一定难以置信,在经历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夜晚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当时的我不过是个年仅六岁半的孩童。1944年1月10日,波尔多的犹太人突然被逮捕,而当时的我还无法对时局做出判断,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就发生了。
对于第二次出生的经历,少了记忆之外的点醒,我很难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
去年,我被邀请到波尔多,去法语地区基督教广播电台录制一期文学节目。那日天气晴朗,节目录制也很愉快,我感到神清气爽。我正朝出口走,这时,陪在我身旁的记者对我说:“第一条路左转,在路尽头你会看见有轨电车车站,乘上电车你就能到梅花广场,那里是波尔多的中心地带。”
他这么说着,某些情景闯入了我的脑海:那个夜晚,那条街道,沿着人行道用篷布盖住的卡车,把我卷走的黑色汽车,武装的德国士兵围追堵截……我暗自惊讶,是什么触动了回忆的按钮,为什么往昔遥远的回忆来得那么猝不及防?
也是在录制节目这天,我约了人在莫拉书店碰面。
我来到车站,看到一栋高大建筑的白石上刻着:“儿童医院”。
记忆中,法尔热太太的女儿,玛格特的告诫猛然响起:“千万别去儿童医院那条街,那里人来人往,你可能会被揭发。”
我像是被什么套住了双脚,惘然若失,停下脚步时,我早已穿过了安德烈-比斯拉街,走过了法尔热太太家门口,却全然没有察觉。
1944年后,我和法尔热太太再未谋面,不过总有一些迹象,比如石子路间的草坪,再比如阶梯的风格,触发记忆,让我想起那幕被逮捕的场景。即便心情平和时,这样那样的迹象依旧会唤醒过去的种种。悲惨的经历往往经不住生活点滴琐事的引逗,哪怕一些蛛丝马迹,也会牵扯出回忆的千头万绪。我发现,那些儿时的经历从未被遗忘,只是自觉忘记,自动屏蔽,仅此而已。
1944年1月,从未料到我的生活会卷入这个故事。诚然,我并非唯一在死亡边缘徘徊过的人:“我感受过迫在眉睫的死亡,死亡已成为我的一种人生经历 ……”那时,我年仅六岁,所有发生的一切都留下了痕迹。死亡体验铭刻在记忆中,我成长的同时它也在慢慢发育。
也许,是我害死了妈妈
回忆让一些场景显得意义深长。
第一个场景:德国军队鱼贯穿过宽阔的林荫大道。士兵们步伐稳健,脚步同起同落,非常有气势,我看得出神。音乐响起,士兵们开始迈步,厚大的鼓系在每匹马的侧边,节奏铿锵顿挫,既叫人叹好,又让人心生惧怕。一匹马在行进中打滑跌倒,士兵们把战马扶起来,再次发号施令。这难道不是精彩的一幕吗?但我身旁的人都泪流满面,我感到费解。
第二个场景:我随母亲来到邮局,看见德国士兵结成小队在城里溜达。他们没有带枪,也没戴军帽,甚至连腰带都没系,这样的衣着让我觉得他们没那么强横凶猛。其中一个士兵在自己的口袋里搜了搜,递给我几粒糖果。母亲眼疾手快,一下夺走我手中的糖果,还给士兵,口中还念念咒骂:“无论如何,都不准和德国人搭话。”
母亲的举止让我很惊讶。没吃到糖果,多可惜。
第三个场景:父亲获准休假,我们一家人去加龙河河畔散步。那天,父亲和母亲坐在一条长登上,而我在另一条长凳上玩子弹球,长凳一边坐着两个士兵。一个士兵捡起我的子弹球递给我,一开始我不理他,可是看他笑眯眯的,我还是接过了子弹球。没过多久,父亲再次回到部队。自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后来,我的父母失踪了。
回想起我曾不顾母亲的禁令和德国士兵交谈,我不禁想:“如果父母的死与我有关,那么毫无疑问,正式因为我在谈话中无意间透露了家庭住址,父母才会被抓走了。”
一个孩子怎么可能解释清楚父母失踪的缘由,况且他对反犹太法闻所未闻,唯一的可能就是:我违反母亲的禁令,和德国人搭话了。一系列相关的记忆碎片,片片组装有如拼图,让过去的事情变得清晰。
我整理凌乱的记忆,得出这样的结论:父母因我而死。
于我而言,父母离世并没有让我痛彻心扉。他们曾在我生命中出现,然后消失。对于他们的死,我毫无头绪,我仅是得知他们消失了
。我们曾一起生活,他们突然离去,没有他们的日子,我无依无靠。
我成了孤儿,无家可归,可这不值得痛苦。沙漠中的人绝望总是大于痛苦,我的处境正是如此。
我清楚地记得战前的家庭生活,那时我才两岁,牙牙学语,但仍旧记得往昔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厨房的正中堆着一堆煤炭,父亲总是在厨房餐桌上读报纸,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等着我自个脱下鞋子;我总跑去同一层楼的邻居家,眼巴巴地盯着他们吃小烤肉;我的小叔叔,十四岁的雅克,用橡胶箭射中我的额头,我朝他高声嚷嚷,说他一定会受到惩罚;男人们从大船上走下来,背着一串串的香蕉……
直至如今,无数静默的场景我都还记得,这些正是我度过的战前生活。
有一天,父亲回到家,身穿军服。我得知父亲加入了“外籍志愿者边境军团”,一支由犹太人和西班牙共和党人组成的军队。大军在苏瓦松作战,遭到重创
。在那个时代,我自然不懂这些意味着什么,而今,我为有个军人父亲引以为豪,只是我不太喜欢那顶军帽,两个尖点看起来很滑稽。不过,有时候,我也反问自己:“两岁的我真有这种感觉吗?难道不是战后看到照片引发的感觉?”
在幻想的世界中,一切都是真实的,一个怪物可以有公牛的肚子,苍鹰的翅膀,狮子的脑袋,尽管这样的动物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烙在记忆中的每件往事都是我幻想的一部分。回忆中的画面本来真实,经过重组后形成回忆中的故事,那么它就不再是原原本本的事实了。
一件事沦为往事,日后的一次再简单不过的碰面都会勾起回忆。但是,不愿去回忆,不愿去回望。
西德尼?斯图尔德,1945年在美国军队服役,被流放到日本集中营,他身边太多的人不堪地死去,而他为自己能够幸存下来感到惊讶。后来,他成为巴黎的一名精神分析学家,他不认为幸存者有罪,坚持自己是被赦免的。在一次对病人的心理治疗中,精神分析学家和患者之间的会面交流,引发患者回忆的爆发:他的一个女病人对他敞开心扉,她向他讲述了集中营的经历:她曾是囚犯队伍中的一员,那时她还是个孩子,被带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她突然松开了握着母亲的手,走开了,而她的妹妹很快顶替了她的位置。妹妹和母亲走进了毒气室,门合上,姐姐因此逃过一死。“这是至今为止她都不愿揭开的回忆 ”。
我只保留了那些在我身边发生的回忆。母亲离世,有关他们的回忆也随之淡去。
美化过去,我已习惯自欺
被逮捕时,我真正回到了生活中,在此之前,孤独是保护的外衣。那辆载走我的汽车里,一个男子痛哭流涕:对于他来说,生命即将走向灭亡。
如果不因逮捕而痛定思痛,我又怎会开始留心听大人所说的话?怎会追随那些企图逃跑的年轻人?怎会在天花板上缩成一团,挖空心思找到这个难以置信的逃亡办法?若我担惊受怕,我会走向那个把孩子们集合到毯子上并给他们炼乳的女士寻求安全,但孩子们反而因此离死亡越发近了。
社会环境赋予当前发生的事情某种特定的意义。罗兹犹太人区的幸存者之一,小莫里斯讲述道:“我坐上了火车,载我走向死亡的列车,但在我的人生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幸福。”
没有经历过世事,内心空荡。美好的回忆,清晰的自我表征可以引导将来。无法预料的苦难让我们痛苦不堪,常规方法已无法治愈内心,此时不得不另寻妙法。当过于猛烈的苦难让我们万念俱灰,抑或以前留下的伤口让人心如槁木,我们会在极度的苦闷中,担惊受怕,麻木而迷茫。
创伤临床学称之为非寻常回忆:这种侵入性回忆,强行占据心灵的痛苦场景。我们被困在过去的牢笼中,那些不堪忍受的情景不断浮现,午夜梦回,噩梦连连。生活中任何平常的片段都能勾起伤疤的疼:
“下雪了,我想起在山中度过的圣诞节,而脑海中浮现出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结冰的尸体。……”
“湛蓝的天空,炎热的天气,就让人想起日本集中营,1945年,我差点儿就在那丧命。 ”创伤性回忆让受过伤害的孩子变得戒备很深:受到虐待,孩子变得警惕冷静,身处战火纷飞的国度,一丝细微的声响都会把他吓得心惊肉跳。回忆中定格的可怕场景,让受害人惶惶不安,疏离周遭的世界。心灵被过去的苦难纠缠,受害人变得冷漠,麻木,他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他看起来遥不可及,格格不入
,然而内心世界却翻江倒海,不得平静。
创伤性回忆对思想产生影响,改变受害者为人处世的方式。受害者为了缓解痛苦,回避经历过创伤的地点,可能引发创伤性回忆的情况和物件。尤为重要的是,他绝口不提有可能勾起往事的话语。受害者沉默不语,因此很难靠近他,他亲手把自己推入奇怪的境地。他包裹痛苦,用掩饰保护自己,以至于内心的情感无法得到抒发。困在过于强化的创伤记忆中,可怕的回忆让受害者惊惶不安,让他很难与别人靠近。他不再寻找理解,也不想被人理解。孤僻不合群,他感到孤独,感到被排挤
:“我和正常人不一样……或许我是个怪胎。”
我寻思为什么我深陷这类可怕的回忆而痛苦不安,我很快明白只要沉默就能让自己自在。我明白只要绝口不提“犹太人”,就可安然无事。这对我来说并非难事,因为我压根不知道“犹太人”这个词的含义。我也从未看见身边有犹太人。我有对“母亲”的回忆:她站着等我系鞋带;我在玩具店偷来一个小洋娃娃,她强令我把小洋娃娃还回商店;我们去跳蚤市场逛街,我们躺在床上笑闹着……全都是诸如此类的场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去木工厂上班
;为了我不知缘由的事情,父亲绕着桌子追我要惩罚我;父亲一边看报纸,一边嘟囔着“的确,是的,是这样” 。
在我被逮捕的那天夜晚,第一次听到“犹太人”这个词,警察向法尔热太太解释,要把我投入监狱,因为我有罪在身。
卡斯蒂隆解放后,一件微小的事情让我大为震惊。一个我不认识的村民在法国国内武装部队与一个战士攀谈,战士说道:“我们有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我接口说这不算太多。陌生人解释说,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才会这么说的,他示意士兵不要责怪我。随后,他又问我是不是会做噩梦,还会突然地怒不可遏。他知道我曾被逮捕,然后成功逃脱,拉法耶先生把我藏匿在学校里。我的沉默毫无作用,这个陌生人知道我要隐藏的事情,只有隐藏我才有可能活下去!他窥探我的内心,想知道这些一连串的变故是否让我噩梦连连。
我想我是这样认为的:人隐藏再多都不为过。我需得远走他乡,那里,人们对我的故事一无所知。只有这样,我才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越懂得沉默,就越能自在地表达。如今想来,当时我就是那么认为的。我多半没有用孩童的语言,但我的的确确能感受这些词流露出的感觉。
人们觉得我很健谈,滔滔不绝。我会讲述自己的经历,与大街上素不相识的路人搭话。可是谁又会想到,我侃侃而谈正是为了守住心中秘密。我交谈的话语正是为了掩饰那些不愿被提及的事情。我的交往策略显而易见:与他人谈天说地,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对我的谈话感兴趣,用谈话掩饰自己
。通过这种自我保护式的交谈,我在心中默默讲述着另一个故事,不使用社交语言,构成了我精神世界的基调。现实中不能说出口的话,我常常在心中讲述。因为经常重复讲述,故事变得简单。某些回忆是明快的,某些回忆是灰色的。逃离犹太教堂的经历像是电影故事,穿黑色制服的士兵平易近人,他把儿子的照片给我看;在那个气息奄奄女士的床下,军人示意我逃走
,让我十分意外 :我习惯了自我欺骗 ,我对记忆修枝剪叶,只为能坦然接受回忆!我的过去没有那么糟糕。
久而久之,残酷的经历变得温馨:和蔼的穿黑色制服的士兵,和蔼仁慈的军医,美丽动人的女护士,叫我“小个头”保护我的高个男孩,笑我喝太多酒的农业工人,和我一起偷葡萄、扔石头的淘气伙伴,这些经过精心安排的回忆让我从过去的悲痛中解脱。总之,这样处理回忆,我感觉不错。揭发我的童子军,看到我出现火冒三丈的厨师,拒我于门外的修女,口口声声称我是个危险分子,这些经历我都置之不理。
当时,为了帮助我从学校逃走,老师让我戴上风帽,吹哨结束了课间休息。孩子们脸贴着窗户张望,他们一想到参与营救就不由得心潮澎湃,为了避开孩子们的目光,老师们把我团团围住。对此,我感到有些恼怒,老师围着我不正表明我是那个潜逃者吗?我明白他们在竭力保护我,但毫无疑问他们自己因此担上风险。我不喜欢这种方式。
重组后的记忆让荒谬变得合理,难以忍受的悲惨经历甚至染上了童话色彩。我躲过了杀戮者的追捕,无论是德国士兵,还是秘密警察
,都不及我的机灵聪明。我感到了某种力量:我要做的就是守住心中秘密,行动但不辩解 。
我形成了这样的交往方式,给我以后的人生打上了独特的烙印。内心隐秘的讲述重排了记忆,美化了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不再在命运中浮沉,我成为我自己故事的掌舵者
,或许在自己心中,我也是英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