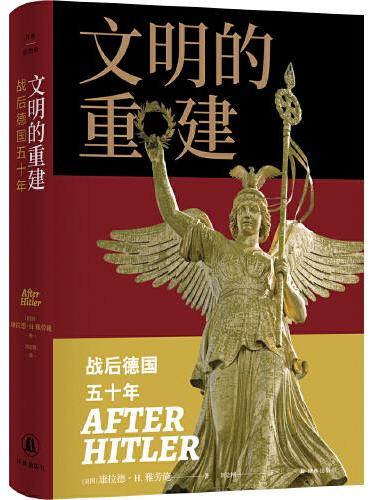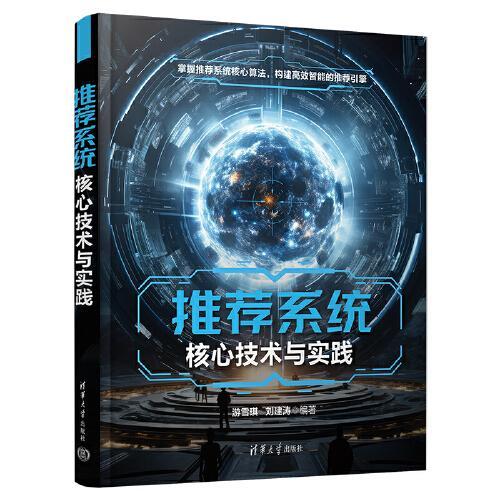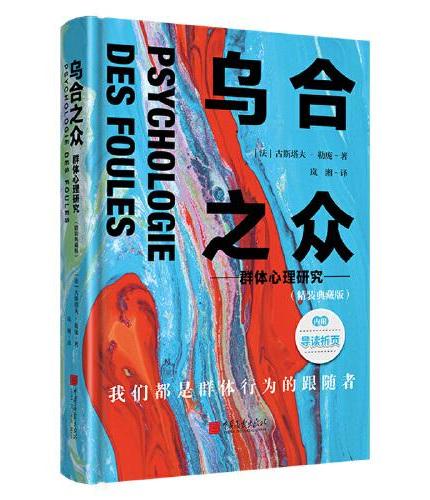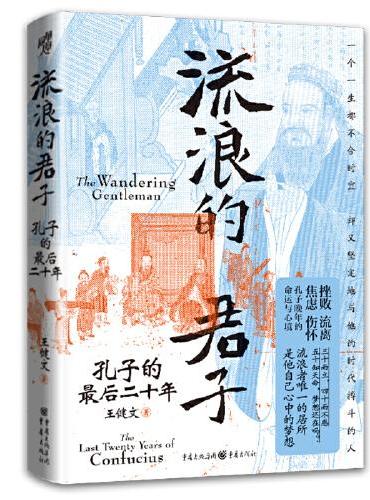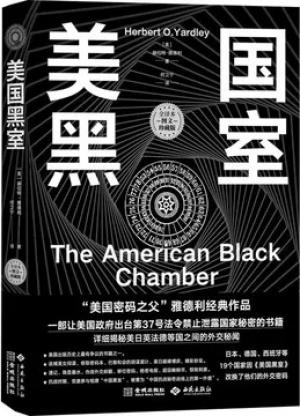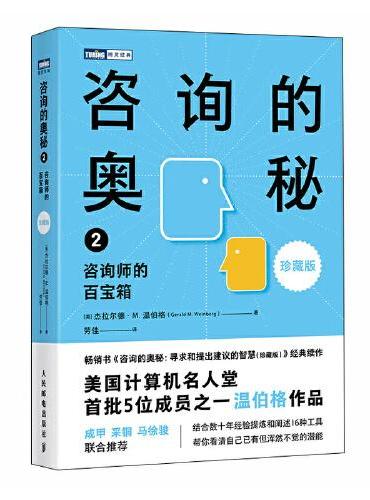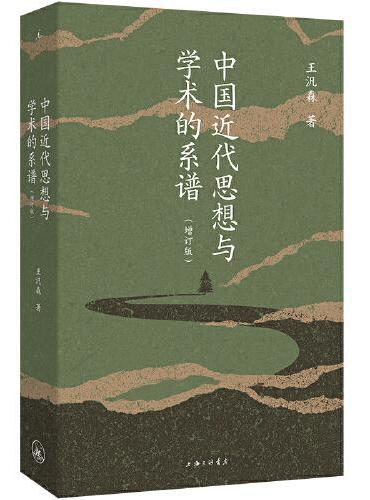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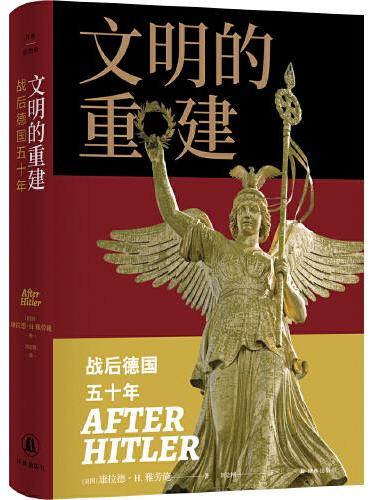
《
文明的重建:战后德国五十年(译林思想史)从大屠杀刽子手到爱好和平的民主主义者,揭秘战后德国五十年奇迹般的复兴之路!
》
售價:NT$
505.0

《
社会情绪的传递与互动研究:以情感符号为视角 (光明社科文库·法律与社会)
》
售價:NT$
4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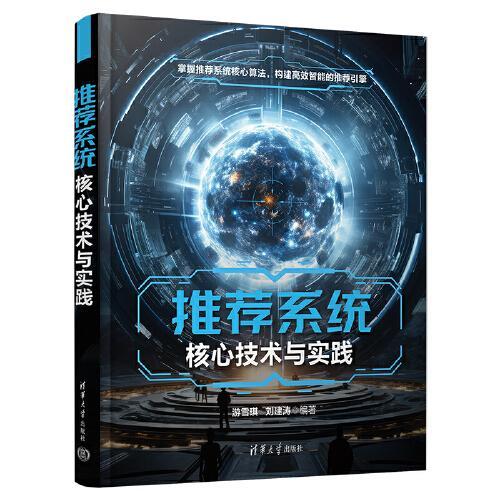
《
推荐系统核心技术与实践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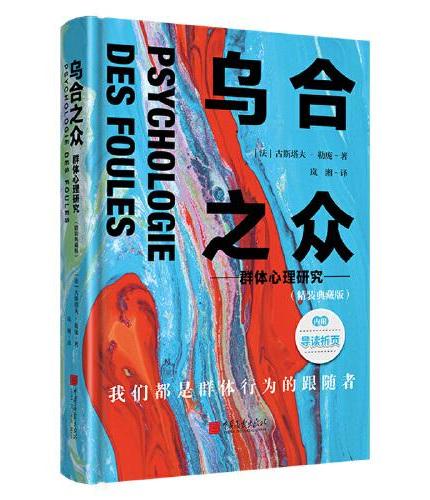
《
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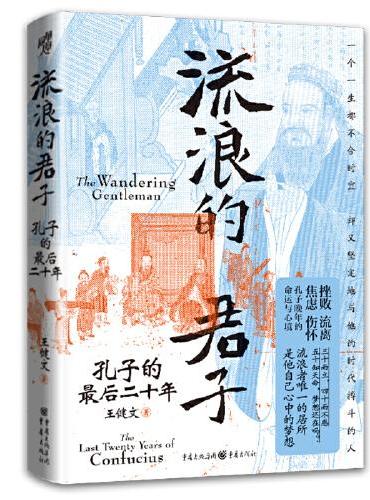
《
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 王健文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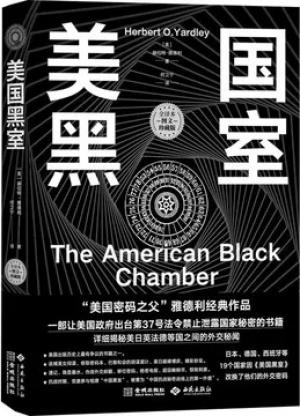
《
美国黑室(全译本 图文珍藏版)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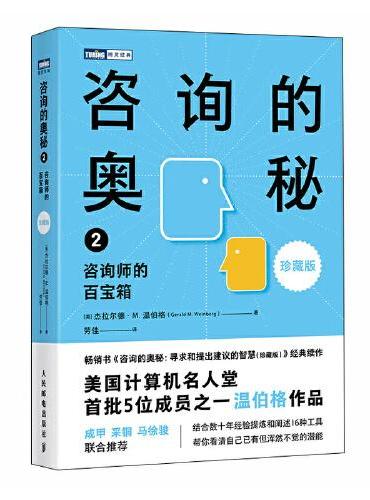
《
咨询的奥秘2:咨询师的百宝箱(珍藏版)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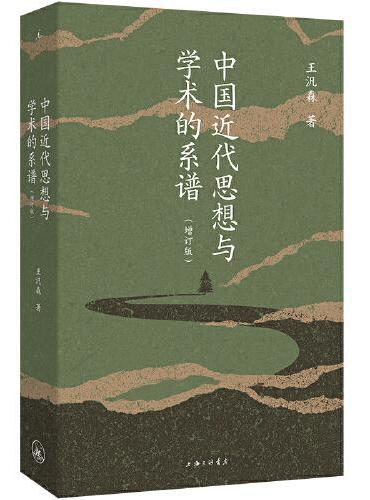
《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
》
售價:NT$
500.0
|
| 編輯推薦: |
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说走就走的旅行,和奋不顾身的爱情。
如果要给它们选一个发生的地点,那么巴黎再完美不过了。
一场归期未定的七年之旅,也许早已不止于旅行。
巴黎的2555个切面,映出了一个中国女孩的倔强青春。
|
| 內容簡介: |
一个女孩只身来到巴黎,将青春中最美好的7年浸泡在这个城市中。巴黎给了她成长和爱情,但这不是全部,就像巴黎不止有埃菲尔铁塔和香榭丽舍大街,也有贫民窟。
你以前可能了解过“巴黎”,但未必了解“生活在巴黎”。
7年的生活体验,周遭每个过客的人生故事,相机捕捉到的每个欲言又止的瞬间——交错成文,为你呈现一个有温度的巴黎。
|
| 關於作者: |
郑乔尹
浙江人,现居法国。已发表若干中文及法语文章,旨在寻求用文字表达美好的情感。浩瀚学海,不断探求中。已出版长篇小说《翡冷翠》《蓝缕》《一念春》。
|
| 目錄:
|
PART 1 肚脐眼里倒香槟
巴黎是座恋爱的城市,情愫无处不在。轻浮的,浓厚的,不经意的邂逅,以及翩然轻擦过的心动……
初来乍到
巴黎圣母院
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
贫民窟的追梦者与富人区的玫瑰
不撞巴黎铁塔不回头
火灾
你好,神父
肚脐眼里倒香槟
卢浮魅影卢浮宫
图书馆前的流浪汉
500欧元一晚的青春
亿万富翁
地下坟墓
圣诞老人
葡萄美酒夜光杯
送创可贴的救护车
法兰西贵族
街头暴力
卖海鲜的帅哥
PART 2 男朋友,女朋友
凌晨,人群终于散尽,埃菲尔铁塔渐渐失了光,变成一堆晨曦中的铁。在距离铁塔几公里的广场,他抱着我,要把我勒死似的,直到天空泛白。
程抱一(Fran,ois CHENG)
不缺钱的小偷
安祖的咖啡馆
拉雪兹神父墓园
爸爸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呀?
安祖的决定,巴黎怀旧之旅
2008年5月12日
男朋友,女朋友
对不起,Tina
最接近上帝的地方
打折季节,全城疯抢
穿绿制服的老先生
钱、钱、钱
巴黎有条北京路
旗袍
PART 3 再走一次香榭丽舍大道吧
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我却以为写的是另一个人。听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有新鲜的心跳声。“以前有个男孩经常在校门口等她,不过他很久没来了,这大概也是她忧伤的原因。”
六年不见双亲面
Facebook,非死不可
病
患有抑郁症的天使
想要拯救地球的怪叔叔
露华忽变霜阵
德国同学的信
又是圣诞节
穿紧身豹纹衣的奶奶
今晚,可不可以陪我去红磨坊
卡米拉的世界
地铁里的打劫者
德国同学的礼物
隐藏在旧货市场的爱情传说
鱼先生和他的幽灵房屋
总统大选
一封信,一张支票
再见,安祖
一念爱,一念恨
毕业前夕的游戏
毕业典礼上闪闪发亮的非洲同学
另一场人生旅程的开始
再走一次香榭丽舍大道吧
|
| 內容試閱:
|
我的青春在法国
——巴黎2555 天
这朵玫瑰7岁。
刚来巴黎那年,他送我的。
它一直倒挂在墙角,渐渐风干,定型,然后落满灰,凝缩成一枝不会动的记忆。
回忆仍活色生香,浸泡在阳光里,飘在风中,淋着雨,覆过雪;枝头绿芽萌发,枝叶浓郁,落叶金黄,枯叶腐烂在泥中;塞纳河的水位年年有落差,水底月亮浮上来又沉下去;朝霞洒在水面,晚霞铺于水底;富人区的玫瑰,贫民窟的垃圾;夏天的音乐节,冬天的圣诞日;头发长了又短、短了又长,年年新衣换旧裳;时有与名人擦肩,时有流浪汉紧紧跟随;总统的誓言,孩子们的笑;城内,花砖路铺向教堂;城外,铁轨蜿蜒至远方……这座城,浮光流影,装着无数人的梦。
你来了,他还在,我们还在。
2555个日夜,我的巴黎!
那个风一样的男子
那年我22岁,他28岁,相识于偶然。
他约我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见面。
他的脸很好看,28岁,那种介于男孩和男人之间的气质很迷人。天冷,他穿了一件黑呢大衣,手提公文包,匆匆赶来。他的名字和前法国总统一样,叫Nicolas。
巴黎是座恋爱的城市,情愫无处不在。轻浮的、浓厚的、不经意的邂逅,以及翩然轻擦过的心动……
他问:“在巴黎生活有困难吗?”
我抬眸一笑,没有回答。
中国留学生大多家境不佳,他很了解中国国情。
他的手很好看,微突的指节,白净修长,透着成年男子特有的质感。白衬衣也很整洁,纯净如见阳光下的纤缕肌肤。
可惜了……我暗叹一声。
他跟我说过,他曾经有过一个中国女朋友,在深圳认识的。那女孩舍不得离家出国,也就没跟他来法国。
他有念念不忘之意。
嗯,还算诚恳。如尔能负心于彼,于我必无情。
可惜不是这个问题,我再叹。
他的脸甚至可以算是英俊,身材亦有西方人的挺拔修长,围巾与大衣的搭配也很有品。他也是巴黎白领。
可惜了……
他继续说:“我想请你教我中文,这样你可以多份收入,巴黎的消费很高……”
我微笑。他想得挺周到,如果光是应聘家庭教师,我想我会答应的。可他是在找一个女朋友,如果我没这意思,那么这工作我也不能要。我微笑。
他很诚恳,还有点儿腼腆。这份腼腆是出于对女孩子的尊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这么认为,一直到现在。
真可惜。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之间……”他比划着。
窗外梧桐成荫,满地镂日光斑,暖浮晴色。
我突然下定决心,觉得应该说明白。我望了他一眼,说道:“谢谢你。我一点儿都不想。”
之后彼此告辞。他的身影转过咖啡馆外的小巷,腿长长的,一方衣角翩飞。
真是迷人的背影。
才28岁,怎么就秃了半个脑袋?
唉。
贫民窟的追梦者与富人区的玫瑰
接下来的日子,我奔波在地铁4号线与11号线之间。早晨去上学,一出地铁站,满目欧洲旧式大学区的安宁与优雅;一回住处,迎面非洲与中亚的气息,黑哥儿冲我叫:“表妹,来几根烤玉米,马伊丝,马伊丝!”
据说,巴黎的风向是从西南吹向东北,位于东北角的19区是传统工业区,历来住着劳工与平民,近年来又成了移民的天下。我回去,房间小小的窗,窗外是临冬的萧瑟风景,几片枯叶被风携起,卷来卷去落地无依。
阿美在喝“保灵孕宝”。恍惚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姨怀我表妹时,桌上也有几盒这样的营养液。阿美他们在遥远的法国,租中国人的房子,去中国超市,看中国医生,替中国人打工。华人圈的时光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
我问她说,我的床垫有个碗口大的洞,能不能替我换一个。
阿美淡然:“你去路边捡一个。”
捡?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路边经常有旧家具,法国人不要就扔了,你可以去看看,有些还是能用的。”她说,“这些桌椅和衣柜,都是我们捡来的。”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以前的留学生也是这么过来的。”她好意,“等阿勇回来,我让他帮你去捡一个。”
我觉得还是自己解决比较好。我跑了趟家具店,一米多宽的海绵床垫卖60欧元,我认为太贵,后来干脆把破床垫调个头,有洞的那头移到脚边,算是了事。
学林教头随遇而安。
阿美有时会跟我聊天,说他们的过往:“我跟我老公10年前出来的。当时去的是瑞士,年龄也就你这么大,年轻没想那么多啊,就觉得这个国家好,办的是留学签证,不过第一天我们俩就去打工了,学没上,只想赚钱。
“后来没法子混下去,不上学没居留只能打黑工。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法国,还是觉得法国的政策好,虽然仍然没有合法居留,不过打工容易些,可以生活,就是有时候要防警察来查。我们‘黑’了很多年了。”
墙上挂着他们去年的结婚照。阿美有些憔悴,我想阿美年轻时应该很漂亮。
他们有过宏伟的梦想,也曾付诸行动,走了那么远,可远方除了遥远还有什么?
一晃10年。
阿美决定生孩子,她说,孩子比较容易成为法国人,以后他们可以以法国公民监护人的理由,试着申请合法身份。
他们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纸合法身份,然后赚钱。
其余的,都不算什么,包括爱情。
阿美上夜班。她的工作是翻衣料,在阴暗的地窖里重复着,一个月赚600欧元。她还没跟人说怀孕的事,怕老板不要她。
她上班前还特地嘱咐我少用点儿电,作业尽量在学校里完成。
他们是从牙齿缝里省钱的漂泊者。
我乐得去学校图书馆写作业。皮制的桌面、光亮的台灯,比窝在不足6平米的小房间里强太多。只是每每到点,街灯绽亮时,回去的路黑漆漆的,心里会有股莫名的不安。
一天放学,阿曼达请我去她家,同去的还有另外几位同学。
阿曼达的住处离学校只有两分钟的路,60平米的公寓,底楼,外带一个私家花园,她一个人住。我曾问她租金多少,她说3000欧元,那时候的欧元与人民币汇率差不多是10:1,3万人民币每个月,我在脑子里过了下,觉得林教头有道理。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某堂课上,丝丽薇问大家,祖父母的工作是什么。我这个中国人,包括日本同学、韩国同学和荷兰同学,回答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美国同学阿曼达的祖父是银行家,祖母是钢琴家。
当时我想,没有被近代炮火洗礼过的国家多幸福啊。
窗台有束新鲜的玫瑰,精心剪过枝,开得刚刚好。空气中有香,室温恰好,人情温暖。我们聊卢浮宫里的藏品,聊巴尔扎克,聊学校咖啡馆里难吃的三明治,也聊香榭丽舍大道著名的“皇后”舞场。
夜幕不紧不慢地拉拢,天色愈变愈浓,最后完全黑去。阿曼达建议大家去外面喝一杯,而我赶着回去,我害怕19区完全天黑后的模样。
路口晃荡的不良少年,街角的劫匪或偷儿,暴力,刀影……这位热情的美国同学不知道我住在巴黎的哪个角落,她也不可能知道阿美的故事。
我到底没有久留。
待我到家时,听见丝丝缕缕的啜泣声,压抑、绝望地隔着门飘来。哭声若隐若现,我一度以为是错觉。
阿美大概10年没见家人了吧。
她快生了。
我记得,那晚的风声特别凄凉。
你好,神父
整个上午都昏昏沉沉的,脑子里不时晃过盈盈缠满纱布的脸、香街漂亮的房子、医院晦暗的走廊和安祖的话,以及自我想象的四处乱窜的火苗。
金基男同学在我面前坐下。
他说:“我去过中国,在西安学过一年中文。”
小小口音,中文说得还算漂亮,他有点儿语言天赋。
我用法语客气道:“才一年就说得这么好。”
他很高兴,开始骄傲:“其实一年不到。”
“很了不起呀。”我还是用法语回答。
他问:“跟我说中文吧,我全听得懂。”
我笑:“现在大家学法语,多练多说。”我才不会给人当免费的中文陪练员。
金基男想了想,说:“我在西安的时候,那里的男人几天不洗头,头发很油,像个饼一样压在头上。我的几个朋友都这样子,天天去网吧。”
“都这样子?”
“嗯,都这样子。”他肯定之余,还点点头。
我说:“韩国女孩都很漂亮。”
他有点儿不自在:“哪里都有漂亮的人啊。”
“不,”我很严肃地摇摇头,“都很漂亮,每个都漂亮,都这个样子。为什么呀?”
朴同学也很漂亮。
金基男气馁,挪回自己的座位。
阮神父冲我神秘一笑。
上课,丝丽薇说今天大家选班长。我当时累,竟趴在桌上睡着了。阿曼达、关、小夜子她们一个个指着我,开我的玩笑:“老师,乔尹当班长挺好的。”
朴同学把手举得高高的,想自荐没成,我帮她:“朴同学挺适合的。”
丝丽薇说:“大家都选你,那就你吧。”
班长的任务就是帮老师收作业,和组织活动。
这时,朴同学举手:“老师,她不合适。”
所有人都看着她。阿曼达撇撇嘴:“这女人真麻烦。”
丝丽薇岔开话题,没理她。
不料当天下课,不知道金基男跟朴同学说了些什么,朴同学恶狠狠地看着我,她的法语口音本来就很重,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但眼见要起冲突。
她朝我扔了本书。
这时,阮神父出来当好人。他的法语也不太好,说得很慢,很有耐心地解释,非常温柔地一个词一个词地劝说。
金基男早逃了。
朴同学第二天就换了班。
“神父,”我问,“我没做错什么吧?”
阮神父摇摇头,说这点小事不要放心上,要学会宽恕他人。还说要是我心情不好,他可以陪我在学校里逛逛。阮神父跟我一般年龄,虽是神父,稚气未脱,走着走着,拿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起来。他会写“阮”这个汉字。
他来自越南南部的一个富裕家庭。
阮神父说:“我爷爷会写很多汉字,我就不行了。”
而我的好奇心始终在于他为什么会选择神父这个职业,我直接问:“你谈过恋爱吗?”
他点点头。
他说那女孩的家境很不好,他妈妈不同意这门婚事。后来那女孩嫁了别人,他当了神父。寥寥几句,云淡风轻。我想象着,他们那时一定很相爱。
我多想问:“为什么不争取呢?”
也许是争取不了的事。
他跟我说他的家乡,稻田,河流,他母亲的生意铺,越南女孩漂亮的长衫,温暖的冬天……
他画了很多个“阮”字,然后扔掉树枝,问:“你现在心情好些了没?饿不饿?我请你吃饭。”
我兀地想起盈盈还在安祖家里。
跟阮神父告辞,他挥挥手:“明天见。”
他也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在巴黎。
肚脐眼儿里倒香槟
落地窗,结着几挂大窗帘,移灯剪雨飘过一行愔愔帘影。
时值午夜。
盈盈的纱布拆了,全身上下只有额头烧伤,不知道医生为什么把她全身缠了个遍。安祖帮她申请了学生宿舍,运气好,只有一个名额,而且下周就可以搬进去。我还不知道有学生宿舍这个福利。
盈盈悄悄对我说:“他真不错。”
安祖要去照顾他的咖啡馆,经常很晚回来,有时候让他妹妹去,他就在家陪盈盈。我见过安祖的母亲,四五十岁的女人,个子不高,烫着很卷的黄发。在她眼里,我们是鲁莽的闯入者,在我眼里,她是一个冰冷的女人。
她极少与安祖说话,只有她与现任华人丈夫生的女儿、安祖的妹妹丽姿在一起时,才表现得像个母亲。
我们是闯入者,安祖也是。而这房子是安祖的亲生父亲留给儿子的财产。
已经很晚了,地铁关闭。我窝在沙发上陪盈盈聊着,盈盈很快睡去,我无聊地换着电视频道。
电视里出现一个裸女,然后出现一个裸男,蜡烛、鲜花、朦胧纱帐,他们在做着人类繁衍必行的工作。这时,纱帐旁出现另一个女人,衣装齐整,相当优雅,她解说各种姿势的优劣,每种姿势不同的愉悦点。裸男和裸女随着她的解说,当场示范各种高难度动作,叠加、纠缠、倒立……两人只露肌肤,没有声音。背景音乐轻柔舒缓,飘着烛影。
当裸男再次把裸女举起来时,安祖推门而入。
他敲过门,不过我没注意,门虚掩着。
他叫我出来,问我要吃什么夜宵。我干脆直接问他:“这节目天天有吗?”
他笑,说周末才有。
因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这类教育节目,觉得新鲜。安祖说他看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集,是男人把香槟倒进女人肚脐里,然后一点点喝掉。
我想,如果有故事情节就好了。
这是我第一次跟异性聊这事,当成学术般探讨,也许夜半思绪奇特,丝毫不见尴尬。他们的性教育很早很全,此类事见怪不怪。而我的初中生理课,有关女生“月经”的章节,生理老师都不好意思讲解,直接跳过去。
指针滑向后半夜,香榭丽舍大道静悄悄的,路灯煲着光,抛洒下霜色无限。
我们慢慢踱着,踱过LV商厦,围着凯旋门绕了个圈儿,一丛丛树影贴在地面,花砖路经典迷人。
路旁一辆车微微地震着,有情事。有意思的是,两名警察往车边走来。
我们闪到一棵树后看热闹。
一名警察凑近车窗看了看,然后对他的同事说:“常事。”
他们开了几句玩笑,走开,没有打扰车里的男女主角。
车继续震着。
这还是冬天,夏天的香街岂不更灿烂?
这般香艳的巴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