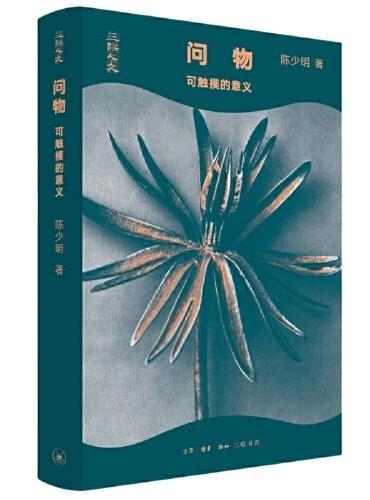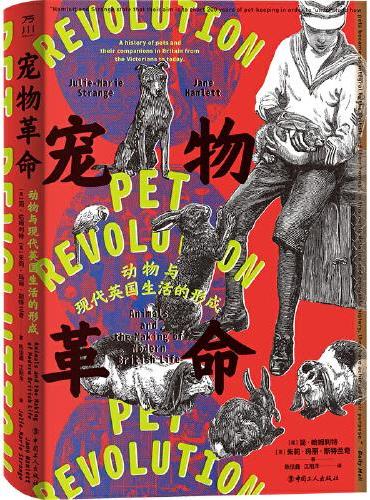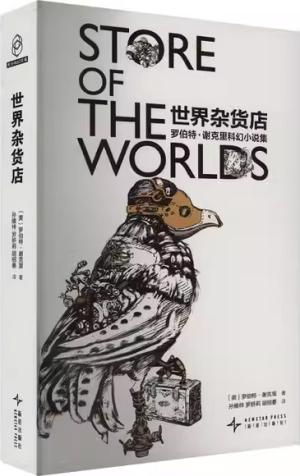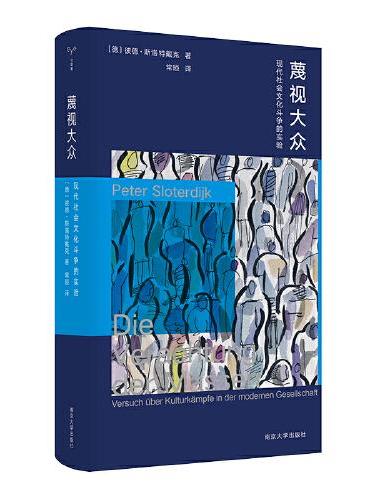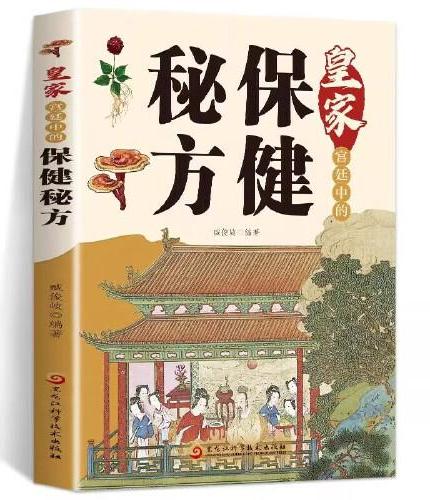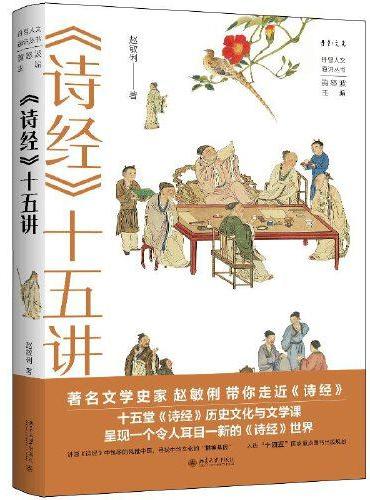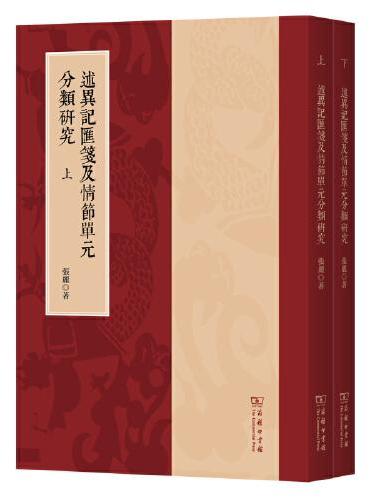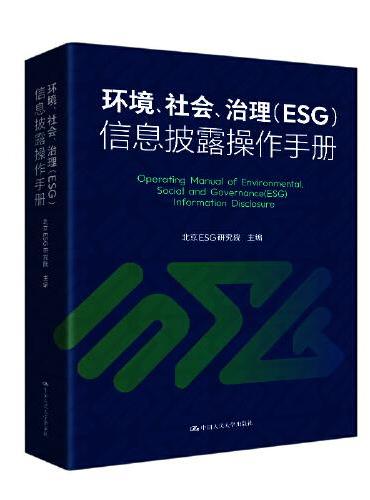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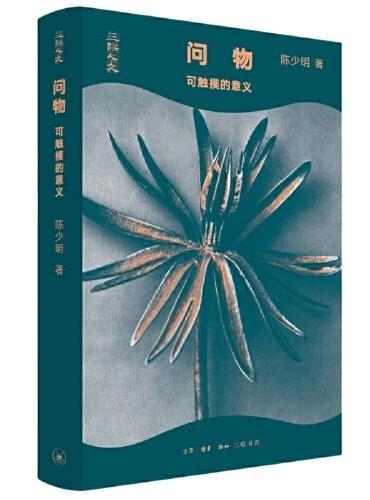
《
问物:可触摸的意义
》
售價:NT$
3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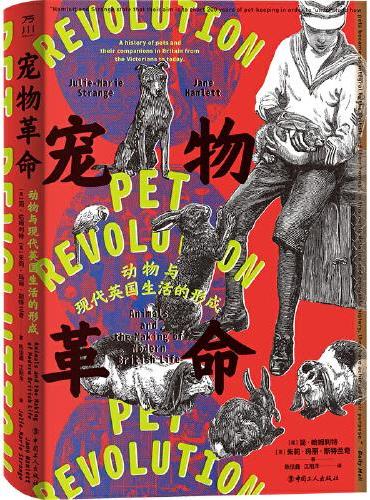
《
宠物革命:动物与现代英国生活的形成
》
售價:NT$
3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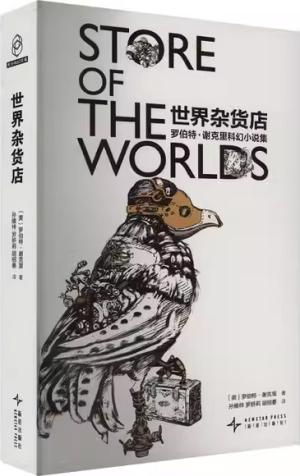
《
世界杂货店:罗伯特·谢克里科幻小说集(新版)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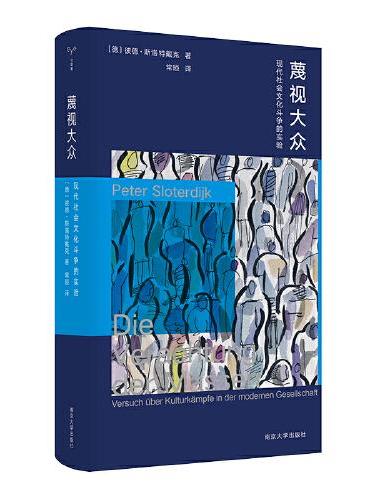
《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蔑视大众:现代社会文化斗争的实验
》
售價:NT$
2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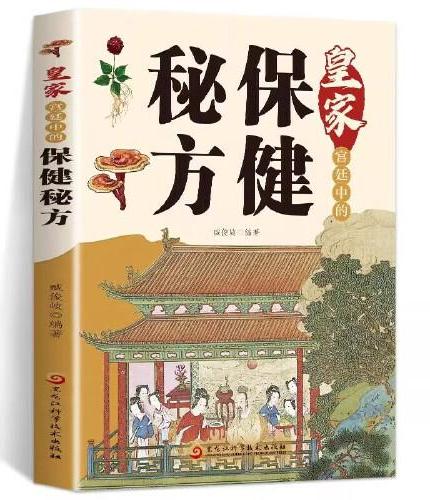
《
皇家宫廷中的保健秘方 中小学课外阅读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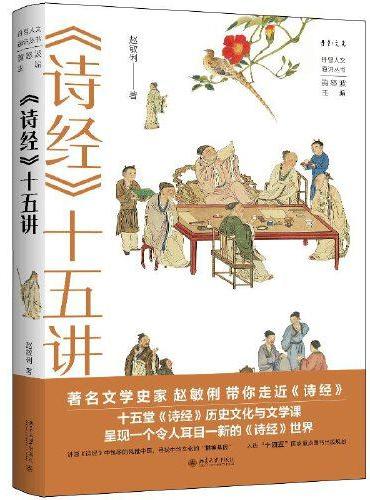
《
《诗经》十五讲 十五堂《诗经》历史文化与文学课 丹曾人文通识丛书
》
售價:NT$
3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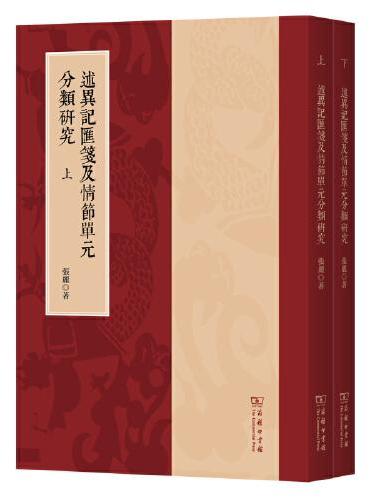
《
述异记汇笺及情节单元分类研究(上下册)
》
售價:NT$
4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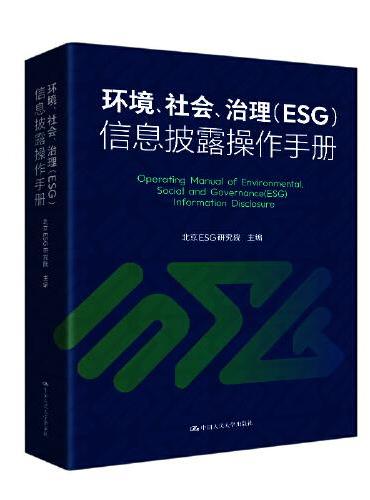
《
环境、社会、治理(ESG)信息披露操作手册
》
售價:NT$
1190.0
|
| 編輯推薦: |
|
●IMPAC都伯林国际文学奖得主、《德尼罗的游戏》作者新作
|
| 內容簡介: |
加拿大籍作家拉维 哈吉出生于贝鲁特,幼年经历过黎巴嫩内战,后移居他乡,2008年他以个人的生存经验为题材,写下这本带有魔幻色彩的小说。
异常寒冷的冬天,加拿大蒙特利尔荒凉的移民社区,一个自称“小偷”的人在公园自杀未遂,被送往当地诊所,被迫接受心理治疗。在女医生的不断追问下,他追忆起在贝鲁特饱受战争折磨的童年、亲人,而这些回忆又与他目前在移民社区的生活现状夹杂在一起。这里,聚集着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尤以中东人为主,如伊朗、黎巴嫩、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在这里,每个移民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到强权的压迫。在这里,小偷每天忍受寒冷和饥饿,在夹缝中生存,想象自己变成蟑螂,侵入他身边那些固执盲目的特权人的生活……
阅读这本书,很容易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不过本书的变形只存在于想象,但同样令人震撼。作者用幽默的语言,暗喻人类如同蟑螂般的生存状态,想象某种即将到来的俗世生活,刻画了一座充满寓意的地下国度“蒙特利尔”,诉说着流亡者和异乡人的经验、记忆、幻觉和幻想。
|
| 關於作者: |
拉维 哈吉(Rawi Hage),1964年生于贝鲁特,在九年的黎巴嫩内战中长大。1984年移居纽约,并于1991年定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先后在道森学院和康考迪亚大学学习摄影和美术,还当过出租车司机。
2006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德 尼罗的游戏》,先后入围加拿大最重要的两大文学图书奖吉勒奖和总督奖,并荣获2008年度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异乡变形记》是他的第二部小说,于2008年出版,同样入围吉勒奖和总督奖,并获得魁北克作家联合会休 麦克莱南小说奖。2012年,出版第三部小说《狂欢节》,入围加拿大作家信任奖(Writers’ Trust Award),并获得休 麦克莱南小说奖。2013年,被温哥华公共图书馆选为第九位常驻作家。
拉维 哈吉目前从事写作和摄影工作。
|
| 內容試閱:
|
我爱上了索瑞。但是我不再相信自己的情绪。我从来没有和女人一起生活过,也没有正儿八经向谁求过爱。而且我一度感到奇怪,为什么自己随便碰上哪个雌性都克制不住想去勾引和占有。
只要一看见女人,我就感到自己的牙齿变薄、变长、变尖。我的后背弓起,额头上冒出两根长长的触须迎风摇摆,以吸引对方的注意。我渴望爬到邂逅女人的脚下,从下往上欣赏她们挺拔的身姿和精致的脚踝。我还感到恶心——是恶心而不是尴尬——一种黏糊糊的狡猾和迫切感。这种奇异的感情与本能的混合物占据了我的身体,迫使我接近这些女人,就像钟楼怪人出现在一群女学生面前。
也许又该去找我的心理医生聊聊了,因为近来这种感觉压得我喘不过气。尽管连心理医生都开始引起了我的饥渴感。最近,当我看见她和一个同事谈笑风生时,我突然意识到她也是个女人。而当她坐在我的对面,让我把这种感觉展现给她看时,我把手放在了她的膝盖上。她扯开话题,镇静而一脸同情地掸开我的手,把椅子往后拖了拖,说:“好吧,那么我们来谈谈你自杀的事。”
上个星期我向她承认过去的我更勇敢、更无忧无虑,也可以说更残暴。但是在这片北国的大地上,没有人给你打砸抢的借口,你甚至找不到理由朝着阳台对面大喊大叫,问候邻居的老娘,威胁他们的孩子。
我把这些话告诉心理医生,她说我压抑着很多怒气。于是我在她离开房间的片刻打开她的手提包偷了她的口红。等她回来后我继续向她讲述我在他乡的成长经历。她时不时用一些问题打断我,比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感受?再告诉我一些。大多时候她只是听我说,一边记笔记,而且周遭环境也不是什么充斥着樱桃木和皮沙发(或者古代航海地球仪)的豪华诊室。不,我们面对面坐在狭小的公共卫生所办公室里,中间只有一张小圆桌。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向她描述我和女人们的关系。我多次试图告诉她我自杀只是为了摆脱无休无止的太阳。我坦率地用有限的心理学知识和口才试着向她解释我自杀是因为好奇,或许是为了挑战自然,挑战宇宙本身,挑战那永恒的光线。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压抑。存在的问题把我耗尽了。
心理医生简明扼要的做派让我恼火。她引出了我自离开家乡后就未曾体会过的施暴欲望。她不明白。在她看来,什么事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我和异性的关系。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对抗这个我无力参与也无力控制的世界中的压迫力量。最可恨的一点是,她时不时会探过身来,面无表情地说:你希望我们的谈话得出什么结果?她总是在嫌我说得不够多的时候来这一套。
我忍无可忍:是法院逼我来这儿的!我不想来。但是我吊在树杈上的时候被一个穿紧身衣的跑步者发现了,他叫来了园警。两个骑警骑着高头大马把我救了下来。那时候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那两匹马上。我那时觉得马倒是个解决技术问题的好办法。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能骑在其中一头畜生上面,我就能够到更高、更粗壮的树枝,把绳子牢牢系在上面,然后把马放走。可惜现实是我被铐上手铐,然后被送去——按他们的说法,就是做评估了。
跟我说说看你的童年,心理医生对我说。
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只虫子。
哪种虫子?她问。
蟑螂,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姐姐把我变成了蟑螂。
你姐姐做了什么事?
过来,我姐姐对我说。我们来玩吧。于是她撩起裙摆,把我的后脑勺放在她两腿之间,把脚后跟抬起来,慢慢地在我上方晃动着双腿。看,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她说,然后她开始摸我。这是你的脸,这是你的牙齿,我的腿是你长长的胡须。我们笑着钻进被窝里,轻轻啜对方的脸。我们来把光挡住,她说。我们用被子把床封住,密封住,这样就不会有光了。我们去地底下玩。
有意思,心理医生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多聊点类似的故事。下个星期见?
下星期见,我说着站起身,经过诊所的墙壁,走下楼梯,走向冰冷明亮的城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