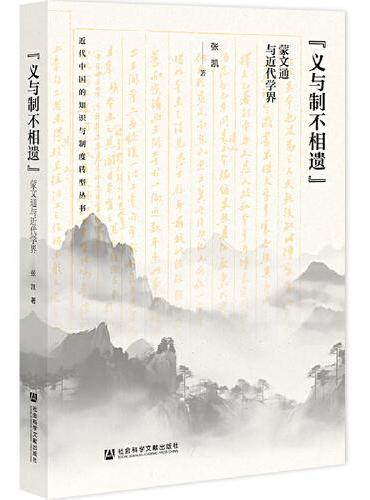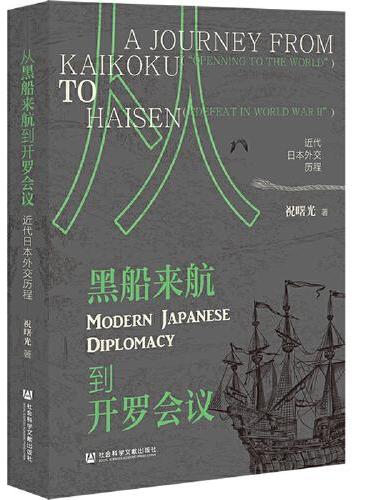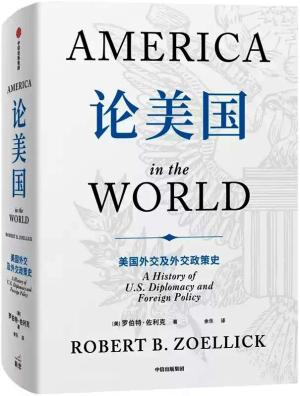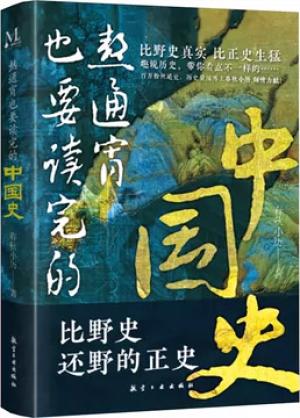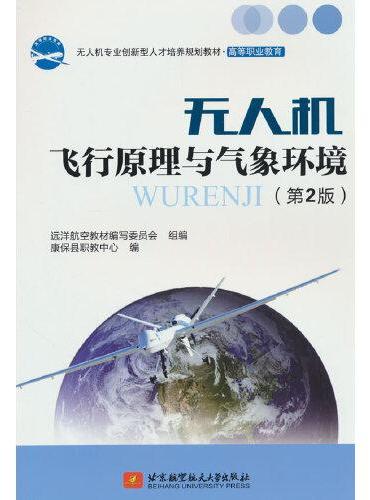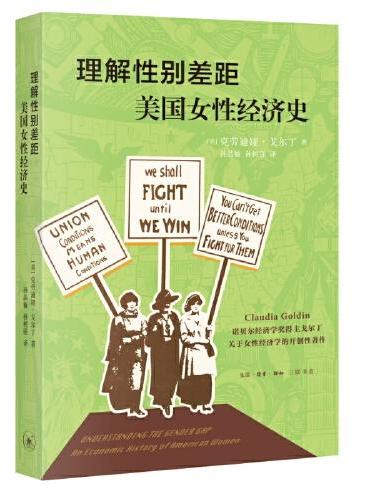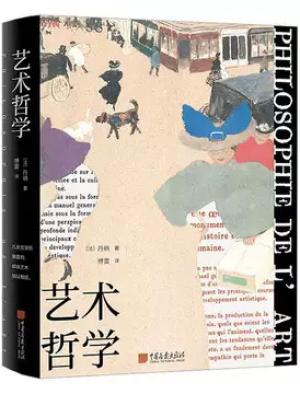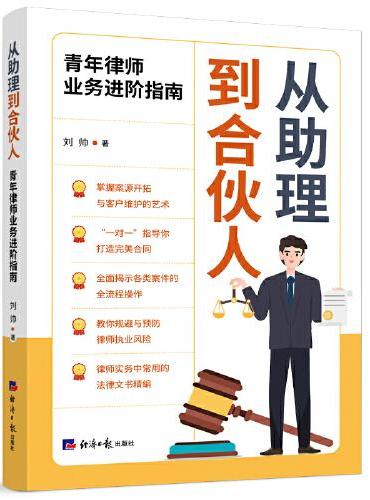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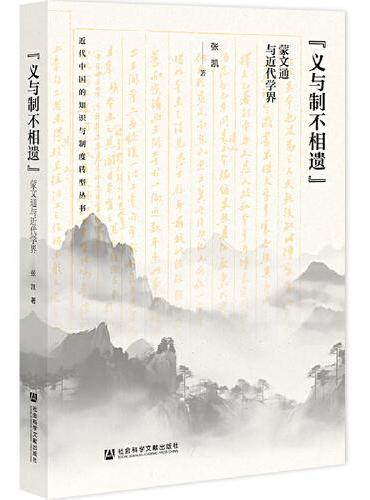
《
“义与制不相遗”:蒙文通与近代学界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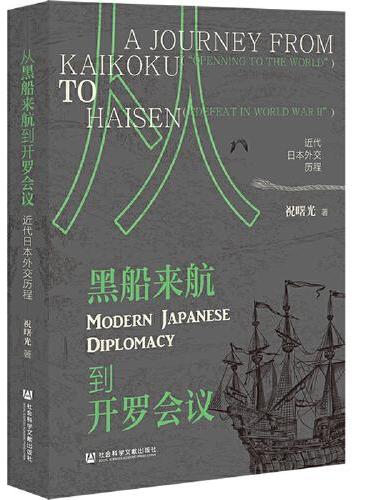
《
从黑船来航到开罗会议:近代日本外交历程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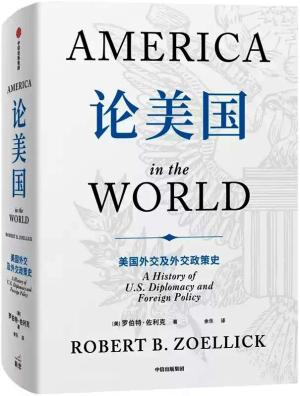
《
论美国(附赠解读手册)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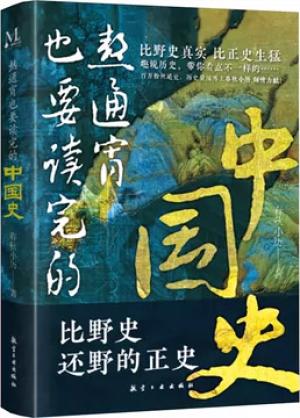
《
熬通宵也要读完的中国史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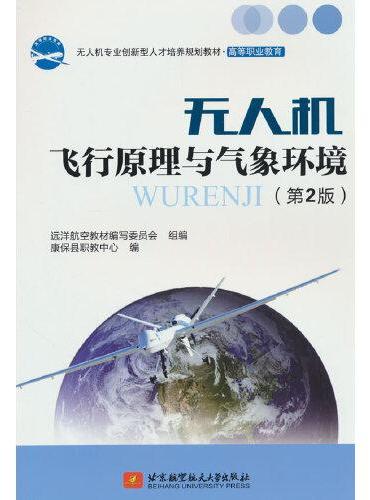
《
无人机飞行原理与气象环境(第2版)
》
售價:NT$
1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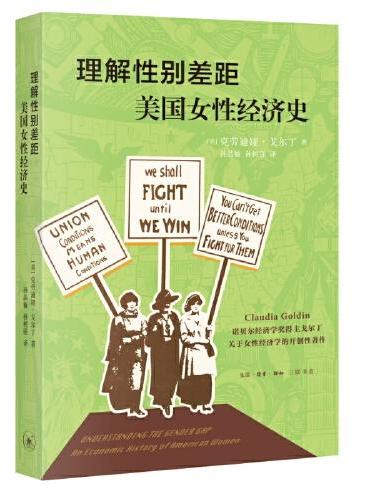
《
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
》
售價:NT$
4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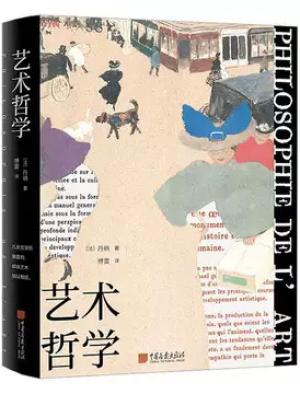
《
艺术哲学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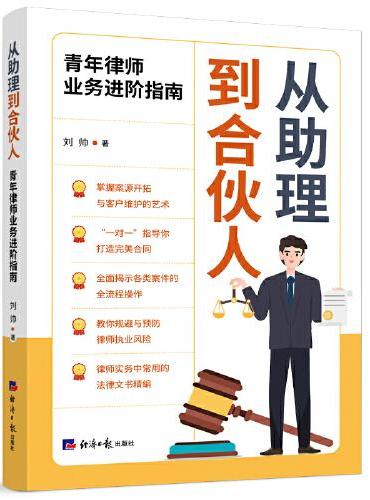
《
从助理到合伙人-青年律师业务进阶指南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
犹太难民在中国重庆的唯一回忆录 以西方人的视角看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新中国成立,别有价值
|
| 內容簡介: |
本书讲述了德裔犹太人卡佛岗一家为逃避德国纳粹迫害,在接连被英、法、荷兰等国拒绝入境后,过境苏联到达中国新疆乌鲁木齐, 1940年到达重庆,并在重庆度过11年峥嵘岁月的故事。
1940—1951,中国历经抗日战争、国共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跌宕起伏的大历史之外,普通民众的生活是怎样的?本书作者沃尔夫岗卡佛岗作为一个外国人,如何在千疮百孔的中国活下来?他看到的中国手艺人、乞丐、美国兵又是如何生活的?他关注的细节往往是被大历史忽略的,这种记录在令我们意外的同时,尤其具有填补空白的历史价值
|
| 關於作者: |
|
沃尔夫岗 卡佛岗,1924年生于德国柏林犹太家庭。1940年,为躲避纳粹迫害,年仅16岁的沃尔夫岗随父亲来到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至此,开始了在中国重庆的另一种生活,直至1951年离开。在重庆的11年,沃尔夫岗生活在普通中国人中间,当过机械学徒,在美军的空军基地当过翻译,在云贵川开卡车从事长途货运,1950年,与中国姑娘刘素兰结婚,1951年和妻子移居以色列,现居住在以色列。
|
| 目錄:
|
自序
1 老师说:坐下,犹大!
2 好日子结束了
3 这个世界还有谁肯接纳我们?
4 从莫斯科到成都
5 重庆:挂球了,挂球了!
6 重庆:生活从不中断
7 军舰和江边酒吧
8 德国医生的好口碑
9 这个洋人真行!
10 父亲的思想停留在德国
11 一个正常的男人不能没有女人
12 我们行医生活的“不合时宜”
13 手艺人、茶馆和乞丐
14 只剩下一个空瓶子
15 空军基地和美国人
16 我想独立生活
17 不能怠慢鬼神
18 帮会里的“洋鬼子”
19 艰险生活中一朵雪绒花
20 遭遇土匪的穷日子
21 父亲的最后夜晚
22 她的芳名是素雅的兰花
23 心心相印,不需要语言表达
24 小公园来了两个警察
25 新政权下的婚礼
26 你们是谁?
27 目的地——以色列
28 我们感觉是在度蜜月
29 以色列,我骄傲地穿着军装到处走
30 素兰突然说,不要走开
|
| 內容試閱:
|
4 从莫斯科到成都
1940年8月1日,我们终于到达莫斯科。苏联的官方旅行社,一家叫国际旅行社的,给我们安排了火车、旅馆以及在旅馆和餐厅吃饭的饭票。我们的整个行程是在莫斯科停留五天,再坐五天火车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然后乘坐俄国飞机到中国境内的第一个机场乌鲁木齐。这条路线是从欧洲到中国最短最快的路线,通常是那些外交官和商人使用的。我们是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使用这条路线的犹太人。
我们到达莫斯科,被安排住进的是一家豪华旅馆,一切都棒极了!我们到克里姆林宫旁散步,不少人开始和我们交谈。他们说的是意第绪语1,却自认为是德语。他们能够看出我们是德国来的,因为我傻乎乎地穿着当时德国少年的标识服——长灯笼运动裤。莫斯科是没人那样穿的。我不时听到周围的人小声说:“德国人!德国人!”但当我父亲向他们打听犹太人的情况,他们就吞吞吐吐,一个个溜走了,好象害怕他们的影子似的。看来,苏联人和外国人打交道显然会惹麻烦的。
我们回到旅馆,倒霉的事便来了。几个便衣警察在等着我们,要我们马上离开莫斯科,因为外国人在莫斯科不能作不必要的逗留。我后来才知道,在我们父子俩到达莫斯科时,苏德间的战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双方都在赶时间2。莫斯科到处是暗藏的德国间谍特务和戒备森严的克格勃3便衣保安。战争前夕的苏联尤其不能让德国来的人作不必要的逗留。
父亲告诉他们,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安排是在莫斯科停留五天。他们说不行,要我们赶快带上行李,他们马上送我们到火车站。他们警告,赶不上当天的火车后果严重。我想:“有多严重呢?是要把我们送到西伯利亚流放吗?”父亲又问:“那到乌鲁木齐的飞机票怎么办?”一个警察说:“赶快上车吧,我们会给你钱,你们到阿拉木图自己买票去。”他说的是英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是父亲给我翻译的。
他们很快把我们拉到国际旅行社,那里给了我们许多现金卢布,因为来不及出票了。然后,又鸣着警笛全速行驶到火车站,拉着我们跟着已经启动的火车赛跑。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跳上了火车。
父亲高声问:“我们的行李怎么办?”
“我们会给你们送去的!”
我父亲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真担心他会发心脏病。苏联在柏林的国际旅行分社应当知道这些规矩。这样的事在德国是不会发生的。
在火车上我们住的是头等厢,豪华舒适。餐车里供应的饭食更是棒极了!一日三餐,每餐都有咖啡、牛奶、黄油等,这在当时的德国是一般人得不到的好东西。我们用国际旅行社发的饭票付账。
我们车厢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士会说一点德语。她刚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遥远偏僻的地方当医生。她抱怨自己身上的衣服太寒碜、苏联的生活水准太低、买不起新的等。她德语说得很不错,很高兴有机会和我父亲交谈,练练口语。另一对夫妇德语也说得挺不错。但是不管他们说得多完美,都可以听出里面夹杂着意地绪语。自然地,父亲的话题就转到犹太问题上来。但他们却吞吞吐吐,想掩盖自己是犹太人这样一个事实,随后他们就告辞,不见了。
长长的火车只有一节车厢是头等厢,里面的装饰很豪华。每个房间内有四张床。有时我们也到其他车厢内走走,遇见很多普通硬邦邦的玉米饼,这就是工人阶级“天堂”的饮食。风景很单调,沿途看到的大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有时也经过一些“波将金村庄”4,那是典型的共产主义粉饰现实的宣传。在面向铁路的一面有高高的美丽建筑物,后面掩盖不住的是泥土房子的平民窟。每次车要起动,动力不足的蒸汽机车都很费劲,那是轮子打滑。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机车必须后退把车厢压紧,然后把机车加足马力,列车才缓缓向前移动。在德国,从来没见过这样起动列车的。沿途还遇到沙尘暴,当炽热的黄沙掠过火车,所有的窗户必须关得严严实实的,我感到我就要被热浪闷死了。在阿拉木图前的一站,有另外一节蒸汽机车加在列车后面,这样,两台机车把整辆火车一拉一推地弄上了山。
最后,我们总算到了阿拉木图。在那里我们要在国际旅行社住五天,然后乘苏联飞机到中国的乌鲁木齐。车站没有国际旅行社的标识,我父亲问人家,他们都回答“亚捏日那唷(我不知道)!”
一个出租车司机把我们拉到一家旅馆,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清楚我们是要去国际旅行社,因为他只是连说:“大大(是的是的)!”
到了旅馆我们先到餐厅吃饭。父亲拿出饭票要付账,女招待只要现金,我们说没有,她就发火了,叫来了经理。父亲想尽办法想向他们说明,我们在德国就已经交了钱,换成了旅行社的饭票,但他们不相信。我父亲天真地拿出那一大迭卢布,那是莫斯科退机票时给我们的,意思是我们不是没有钱付账。那女招待一见就更火了,高声叫起来:“这个人有钱得很,就是不愿付账!”第二天,餐厅经理和我们一起到了当地政府。那里有一个说意地绪语的翻译,帮我们说明了情况。最后,当地领导许诺餐馆经理,他们会去了解国际旅行社和饭票的问题,餐厅会收到钱的。第三天,经理又拒绝我们吃饭,我们又到地方政府去了一次。
我看到离旅馆不远,有一座美丽的雪山。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美丽的风景,它就像磁铁一样把我吸引住了。我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出发向白雪覆盖的山峰走去,我要登上山顶。一整天,我都在原野里飞快地走,不吃不喝。我指着一本小词典问一个农夫,这山有多远。他不会读。到了下午,太阳都快落山了,山离我还是很远,我只有放弃了。回到旅馆已经很晚了,人们都笑话我,因为那山看起来近,实际有60公里远。父亲见我回来很高兴,他已经担心我好久了。
五天之后,我们总算飞到戈壁滩上的乌鲁木齐市,这是救助机构所能付费的最后一程。因为在中国必须用美元付费,而救助机构只能付马克。
我们站在两架飞机旁,一架是把我们送来的苏联飞机,一架是中德航空公司的德国容克Ju52运输机。这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停机坪,除了风向标什么也没有。
Ju52的飞行长官过来问我们到哪儿。父亲说到重庆,但没有票,也没有钱。中国机长用德语说:“没关系,德国大使馆会给你们付的。”
我父亲正要说我们是犹太人,我连忙打断他:“不要说,都一样的!”
飞行员用德语说:“你们可以登机了,飞机马上起飞!”
这正是我想听到的。
我看到他们在给飞机加油。自然是用人工,把漏斗插在飞机翅膀上的油箱口子上,用手提着五加仑的油桶往漏斗里倒油。
起飞后,飞行员给我们吃哈密瓜,我从来没有享受过那么好吃的水果。
经过一段颠簸的飞行,飞机在戈壁上的哈密停下来。这是一个小村庄,沙漠中的绿洲,风景如画,但是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我们被带到一个小“旅馆”,那只是一个泥土房子,和当地其他建筑一样。我父亲想上厕所,但没有人懂他说什么。他只得打手势,这下让人弄懂了,解决了他的问题。
第二天,我们飞到兰州又停了一次,在那里吃了点东西。就在当天,我们飞到了四川省会成都,而不是目的地重庆,因为那天重庆有日本人空袭的警报,这在那段时间是司空见惯的事。
成都中德航空公司经理问我们,要到哪家旅馆下榻,哪家饭店吃饭。父亲很费劲地向他解释,我们是难民,每人只能带五个马克,我们两人随身总共就十马克。经理很吃惊,摇着头用标准的德语叫起来:“从来没听说过!”他马上打发一个伙计给我们拿来了些吃的。飞行员想邀请我们一起去旅馆,但父亲客气地谢绝了。我们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那些办事员和苦力都咧着嘴笑话可怜的外国佬穷成这样。
注释
1 意第绪语属于日耳曼语族。全球大约有三百万人在使用,大部分的使用者是犹太人。而且其中主要是欧洲犹太人在操用此语。意第绪(语)这个称呼本身可以来代表“犹太人”,或者说是用作表示“德国犹太人”的称呼。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意第绪语被认为是“犹太无产阶级”的语言被鼓励使用;同时,希伯来语则被当作“资产阶级”语言。在以色列,意第绪语被现代希伯来语所取代。许多从苏联来以色列的老移民(通常超过50岁)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意第绪语。
2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就撕毁苏德间的协议,对苏联发动猛烈进攻。
3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54至1991年间的苏联情报机构。
4 18世纪俄罗斯元帅格利高里阿力克桑德罗维奇波将金为了制造一种繁荣昌盛的假象取悦女皇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沿着第聂伯河岸用木板建造了许多外表看起来非常精致美观的房子,但这些看起来光鲜无比的村庄背后却是满目疮痍。后来,西方人就把所有的面子工程都叫做波将金村。
5 重庆:挂球了,挂球了!
最后的航程终于把我们带到了重庆。
到达时还是上午,乘坐机场的交通车,我们到了重庆城里。
我们急着找伯伯一家,想通过警察局外事组的人帮忙查外国人的花名册。就在那时,日本飞机的炸弹掉下来“欢迎”我们了。航空公司的员工赶快把我们带到最近的防空洞,等空袭警报解除后才出来。他们邀请我们在办公楼用餐。
重庆与西方整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让我吃惊。大多数员工就在飞机场吃住。当父亲给他们讲我们的遭遇时,我上街逛去了,看着周围的中国人,我好像在梦中。
重庆街上的人都盯着我这个黄头发山羊眼的外国人。怀着复杂的心情,我观察着中国的市民生活。一切和我过去在柏林的生活是那样的不同,来来往往的人流、人力车、店门大开的铺子、数不清的小商小贩,所有这一切,给我巨大的冲击。周围只有中国人,没有一个外国人。我当然高兴再也没有纳粹了,但我又遗憾自己口袋空空,不能给向我伸手的乞丐一分钱。这里真是乞丐遍地。我不敢走远了,怕迷路走不回航空公司的办公室。我既不会说中文又不会说英语,开始害怕起来,就赶快回去了。我父亲正在应经理的要求把我们的问题写下来,经理看不懂父亲的手书,要求父亲用打字机打印。我回来时看见父亲正在敲打字机,这很花时间的。突然,空袭警报又响了,街上的人都不要命的跑,一路高声地喊叫:“挂球了,挂球了!”
我莫名其妙,公司的人说:“没有关系,我们吃了饭才进对面的防空洞,等日本飞机来还有时间。”他们就请我们坐下来就餐。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中国人吃饭。人们围着一个大圆桌,桌子上有很多我从未见过的食物。我不会用筷子,但是他们一教我就会了。我父亲是用调匙填饱了肚子。
饭后,他们带我们进防空洞。他们把防空掩体叫做“防空洞”。在那里,我们和几百个受惊吓的老百姓挤在一起。在这个臭烘烘的洞子里我感觉就要给闷死了。还好,中国人就是流汗也没有我们西方人那样重的体臭。但有些事我不明白,比如在防空洞里面,他们既不许用手电筒也不许点油灯,更不许讲话,说是怕日本飞机发现了,然而炸弹爆炸的声音却大得惊人。我们头一天来重庆就尝到战争的滋味。空袭解除后,父亲继续在打字机上写我们的“故事”。
与此同时,经理在帮我们找伯父。但是,里昂伯父并没有在外事警察那里注册,因此不在花名册上。后来我们才知道,伯父和儿子一家已经加入中国籍了。经理又打发人到外国人圈子里去找,却不再提我们欠的机票钱。
至于是谁付清了我们从乌鲁木齐到重庆的机票钱,我们至今不清楚。大概经理把父亲写的“故事”作为理由,在航空公司把我们的欠账抵销了吧!
一个德国奔驰车代理商碰巧认识我伯父,他就坐人力车上门来,热情得很,让我们也乘人力车,一起到他漂亮的别墅去过夜。在那里,我们好好洗了个澡,这是我们离开柏林后第一次清洁自己。第二天,他给我们找了一辆顺路车去离重庆70公里以外的小镇北碚,我伯父一家就居住在这里。我们真要好好感谢这个德国人,他不像在德国的那些雅利安人歧视犹太人。相反,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们就找不到伯伯。我们在中国内地又不认识任何人,又没有钱,那样就真正悲惨了。
我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车里,站着颠簸了大半天,最后总算见到伯父一家人了。伯父还是老样子,和我们分别了整整七年,刚见我父亲就用脏话开了个玩笑,一下就把气氛活跃起来,大家都笑开了。
就在我们到达的前几天,日本人的炸弹落到伯父的房子前,致使他们一家只能在公园中一个破旧的古庙里暂住。庙里没有玻璃,只是把毛边纸糊在窗框上,既挡蚊子又挡风和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没有厕所,每家只有一个陶土做的“尿罐”,每天有伙计来倒尿罐。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让你想到现代或者文明。没关系,我们头上有屋顶,吃饭睡觉有去处。哪怕生活在非常贫穷的条件之中,家人团聚也给了我一种安全感。我们不介意,我们感觉愉快,因为不再有人问我们是不是犹太人,也没有人像在德国那样,天天骚扰让我们惶恐不安。透过那古庙的窗户,我们可以遥望川江上的美景,苦力划桨拉纤,木船上溯下游,千年河水日夜流淌,平民百姓日子照过,这些真是对我们历经磨难的最大补偿。傍晚,一家人围着圆桌,昏暗的油灯映照着面孔,大家计划着以后的生活。现在的这个村子在风景美丽的清凉亭一带,但当时村子太小,维克托已是村里的医生了,但看病费仍然不够维持生活,我的父亲必须另外找一个地方开业了。
伯父一家住的这个北碚小镇,是重庆有名的风景区,因附近的硫磺温泉而出名。富人常到这里来泡澡健身。伯父是牙医,他儿子维克托是内科、外科、妇科全科医生,父子俩在全村唯一的“诊所”工作。这个“诊所”就是几间屋子,里面除了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外什么也没有,没有水、电、厕所和任何医疗设备。
伯父有时能拔几颗牙。每次伯父拔出一个牙齿都高兴地说:“现在可以吃肉了(猪肉比牛肉贵一倍)!”假若有机会做假牙齿,就像在德国做的那种陶瓷假牙和生橡胶牙托,收费比较高一些,还可以留下一点钱,买一两块美金保存作应急用。伯伯必须自己烧制打模子用的石膏。他和维克托的医疗器械从柏林带到上海,又一路随他们逃难,带到重庆。没有这些器械,他们无法开业求生。他自制了一个脚踩的牙钻,带一个又老又钝的钻头。我是不想让他用这个钻头给我钻牙的。伯父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机构来监管什么开业执照一类的事。
每当有警报的时候,我们全家就躲到山底下的公共防空洞里。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在菜油灯的微弱光照下,维克托的太太戴安娜教我们打麻将。
堂兄维克托在我们来的第二天就教了我几句中国话。那个给我们挑水的苦力的年纪和我差不多,想和我到嘉陵江去游泳。我可以用中文对他说:“好,我们走!”伯父的太太佛莱德尔惊叹道:“他只来了三天,就已经开始说中国话了!”
维克托他们不愿努力融入新生活。来中国有七年了,会说的中国话不超过十个字。他们学英语,但带有很浓的德国口音。维克托至少还努力学,但没有他的中国太太当翻译,他也很难和病人沟通。这是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对医生来说是很大的障碍。他们就靠着德语将就过,感觉德文对他们更重要,不愿意费劲学哪怕一点儿当地语言,或许他们以为,他们不会在中国生活很长的时间,而且他们不太愿意和中国人聊一聊。
一个星期以后,维克托要到温泉附近一个朋友家里,去取放在他那里的显微镜。显微镜是维克托从德国带来的,很珍贵,怕日本飞机轰炸损坏了,就保存在朋友家的防空洞里。维克托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我当然愿意啦。早饭后,我们就沿着泥土路走了很久,从公园到温泉大约十公里左右。事情办完后回家,他问我愿意走路还是愿意乘小船,如果走路,省下来的钱就可以买藕粉吃。藕粉是莲藕淀粉做成的布丁,很好吃。我肚子饿了,选择了藕粉。吃到一半,发现藕粉里有一只苍蝇。维克托把伙计叫来,指给他看,伙计就又给我盛了一碗。维克托羡慕得差点也抓一只苍蝇放在碗里面,但他手不快,肯定抓不着,只有看着我狼吞虎咽。我们回家的路上,突然变天了,又是雷又是雨的。我们没有一点准备,在泥泞的路上淋得像落汤鸡。我的鞋是德国战时生产的,后跟中间夹的是纸板,只有最外面一层是皮,鞋底泡湿后钉子冒起来顶我的脚。天很快漆黑一片,只有借着闪电,才能看得见。我试着用石头把钉子锤回去,还是不能走路,最后我只有把鞋跟撕下来。维克托的鞋很快就不行了,他不能赤脚走路,我就把自己的鞋脱给他穿。(我可以打赤脚。以前当孩子时一到暑假,我就光着脚到处跑,而维克托规规矩矩,从来不赤脚。)直到午夜,我们才回到家。我们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我发着抖,累得精疲力竭。都是维克托这个吝啬鬼,提出这个倒霉的藕粉建议。(他一直都这样。如果要买什么,带的钱刚好够用,从不多带一分钱,以免受诱惑多花钱出去。我们说他吝啬,他反驳:“你不能让钱从两只手上溜走!”)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靠他!
到中国后的开头几个月,我父亲完全没有收入。他和伯父弟兄俩准备从北碚到重庆去,看能不能找到工作,凑凑和和过日子。我们的小村庄在嘉陵江畔,嘉陵江往南流入扬子江,而重庆城就在两条江的汇合点。于是我们三个挤上一艘老式的机动船,和船上的一百多人当天抵达重庆。
6 重庆:生活从不中断
我们先去看了伯父的德国朋友赫尔斯坦蒙。他在扬子江的南岸一个叫龙门浩的地方,临江开了个带酒吧的饭馆,河对岸就是重庆城闹市区。他的顾客主要是江面上停靠的美国舰艇水兵。有时候,英国舰艇也在此抛锚。我听说很久以前德国的舰艇也在这里靠过岸。舰艇的军事目的我不清楚,但它们让这个酒吧生意很好。很有可能是在战乱不安的环境下,这些军舰代表了它的国家对本国的生意人提供避难和保护。更重要的是军舰上的电台,让这些侨民与本国保持联系。重庆因为是战时首都,日本飞机轰炸很厉害,但这不能阻止我父亲和他的哥哥找工作。酒吧老板赫尔斯坦蒙给了我们一个房间暂住。我们的第二步是去找伯父的一个中国朋友,懂德语的皮肤病性病专家宁医生。他可以说写流利的德语,这是很不简单的,我知道,其他很多在德国学习的中国人语言都没有过关。这位宁医生同意让我父亲在他的诊所专治肺病,其他病人还是归他自己来治。父亲的主要问题是要搞到治肺病的特效药结核菌素。
这个宁医生是个很有趣的人,50岁左右,有点灰白的头发,中等身材,总是带着让人愉快的微笑。当我第一次听到他和我父亲伯父说话,德语说得那样完美无缺,不带一点地方口音,没有一点语法错误(德语的语法很复杂的),我真是惊讶极了。但是,他有时喜欢说点笑话,带上几句反闪米特人的语言。我想他没有什么恶意,并不想冒犯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他的语言能力很强,对流行语也精通。他可能并不知道,我们对非犹太人说反闪米特语言是很敏感的。
酒吧老板赫尔斯坦蒙的大半辈子都住在中国,娶的是中国妻子,但她很久以前就去世了。老人体态笨重,满脸络腮胡子,秃头蓝眼睛,离开德国这么多年,乡音未改。看起来,他很高兴和我们说自己国家的语言。我没问他年纪,但我估计他有七十多岁了。他是老板,还有一个合股的广东人。老人之所以同意我们住他那里,不仅是出于友谊和社交,也因为他知道父亲是医生。他老了,担心身边没有人照顾,健康状况会变得越来越糟。
在所有事情都安顿好了以后,我们乘一个小小的汽轮回到北碚。上水行船慢,我们花了两天才到。在船上我病得厉害,腹泻不止。上岸后,我连爬上在山顶的庙子中的家的力气都没有了。伯父叫了两个苦力抬轿子,当地叫“抬滑竿”,把我抬回了家。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维克托狠狠地把我教训了一顿,这是给初来乍到者绝好的一课:“不准喝生水,不准用生水漱口,不准吃生蔬菜水果,不准没戴帽子就在太阳下面走。你让蚊子咬了,会得疟疾;你被死老鼠身上的虱子咬了,那就更可怕,会得黑死病。”教训得好!我再也不能痛痛快快地喝一杯自来水龙头下接的凉水了!
不久,我们父子俩,伯父夫妻俩,一行四人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