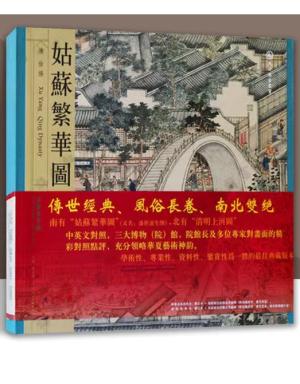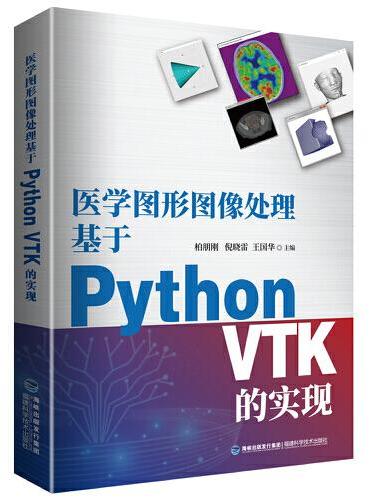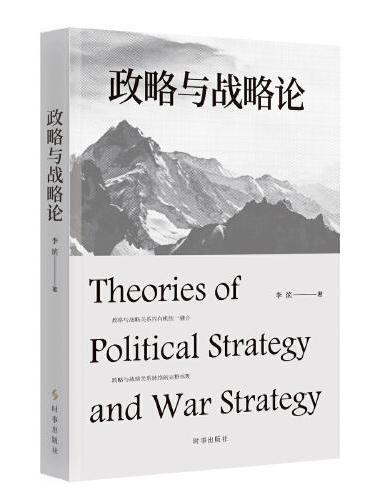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黄庭经详解(全2册)
》
售價:NT$
660.0

《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大系·绘画卷(全十册)
》
售價:NT$
47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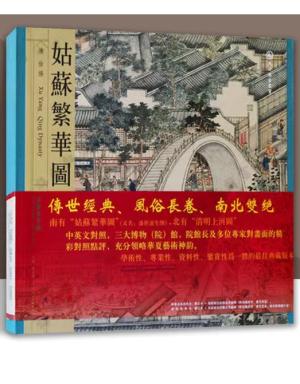
《
姑苏繁华图
》
售價:NT$
3190.0

《
人的消逝:从原子弹、互联网到人工智能
》
售價:NT$
484.0

《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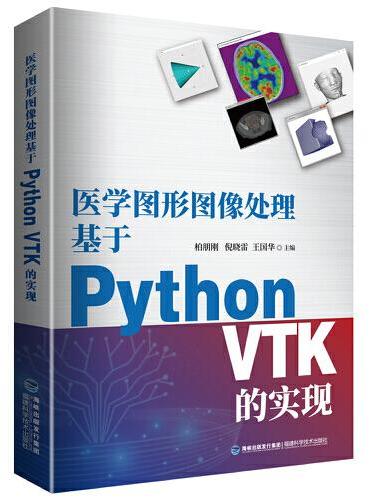
《
医学图形图像处理基于Python VTK的实现
》
售價:NT$
760.0

《
山家清供:小楷插图珍藏本 谦德国学文库系列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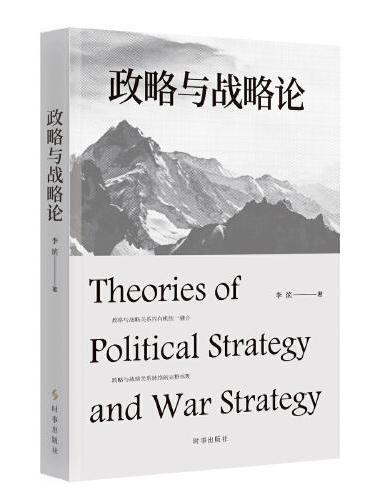
《
政略与战略论
》
售價:NT$
638.0
|
| 內容簡介: |
黄昏将至。
这是武周夺唐的前夜,在历经吏选改制的狂风暴雨和重重阴谋之后,更大的考验在等待着裴行俭和琉璃。
最险恶的陷阱,来自女皇深不可测的算计;
最残酷的背叛,来自好友翻脸无情的出卖;
最绝望的别离,来自爱人阴差阳错的误解。
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她发誓,就算永坠地狱,万劫不复,她也要亲眼看到那些害了他的人得到报应;
当过往都尘埃落定,他叹息,人生大错已铸,岁月无几,他又有什么资格去奢望幸福。
在阡陌纵横的人生里,在血雨腥风的变局中,有没有一条路,可以让他们携手走到终点?
|
| 關於作者: |
蓝云舒
女,生于湖南,居于北京。学过几个专业,码过各种文章,最后才发现,自己最爱干的事情是宅着,最爱码的文字是小说。原因无他,人生平淡,性格疏懒,而心底那些或波澜壮阔或飞扬跳脱或梦断魂伤的狂想,也只能寄于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并与大家分享。
起点女生网热门作家,作品《千蛊江山》、《大唐明月》等均超百万点击量,读者收藏破万,读者推荐超越十万;作品先后登上青云榜、八大分类大封推、强推榜、热门推荐、首页大封推、粉红月票榜前十等重量级榜单。
|
| 目錄:
|
第一章人命大案惊天逆转1
第二章一洗前辱终得报应15
第三章美人恩仇帝王心术33
第四章龙颜震怒黄雀在后55
第五章生死一线祸福难辨73
第六章斯人已逝祸事未已95
第七章如梦初醒醍醐灌顶109
第八章平地惊雷此心无悔127
第九章天子之怒君子之仇143
第十章故地重游疑云再起161
第十一章旧案难解新宠莫测177
第十二章怒发冲冠心腹大患197
第十三章万里奔袭一举成擒213
第十四章空穴来风平地生波229
第十五章千金散尽用心良苦245
第十六章百口莫辩大智若愚255
第十七章无由狂怒莫名深仇275
第十八章不计祸福谁共死生291
第十九章闻捷忧宠献俘惊变303
第二十章天道无私人欲难填313
第二十一章苍天有眼报应有时325
第二十二章疑影再现真相大白341
第二十三章至亲至疏英雄末路363
第二十四章一念之差万劫不复375
第二十五章此情可悯此心可诛389
第二十六章初心不转恩仇了断405
第二十七章别情依依此恨绵绵417
第二十八章繁华落尽明月千里435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人命大案惊天逆转
对于长安城的市井男女来说,人生里最不能错过的热闹有三桩,一是春日去大慈恩寺旁听高僧俗讲,二是元宵在西市街头掺和胡人踏歌,三是随时到县衙门口围观人间奇案。尤其是这第三桩,因为可遇而不可求,更是分外要紧。若能赶上什么毒杀亲夫、残虐前子的人伦惨剧,那便足以充当一生一世的谈资,便是发白牙松之时,也能拍着大腿跟后生们感叹:“你是没赶上永徽年间的那次毒妇游街哟!”
这个“哟”字,自然要说得回肠荡气,就如记忆里那一去不复返的大好时光。
因此,咸亨元年的春末夏初,当长安县的一次泼皮争产渐渐演变成带有香艳色彩的人命大案,又陆续拉扯进了几位刚刚入选的官家人时,整个长安城都轰动了。
这一日,晨鼓刚刚响起,长安县县衙门前的空地上就有人开始探头探脑,待得红日初升,附近里坊的闲人已三五成群地聚拢了过来,没过多久,住得远些的好汉们也陆续赶到,连小贩们都闻风而至,在渐成气候的人群里高声兜售着刚刚收来的胡饼和浆水。
等到太阳爬上了衙门前那棵老槐树的枝头,这里已是人头攒动,除了满脸兴奋的各路闲人,居然还有不少看上去极为体面的人物——那打扮低调、言谈文雅的,多半是昨日才拿到告身的新晋官员;那装束利索、神色倨傲的,自然是给贵人办差的管事。他们的到来,不但让县衙前围观群众的档次陡然上升,连带着附近几个酒楼靠窗雅室的费用也水涨船高,视线最好的几间已涨到了五千钱一间,而且还在持续攀升。
离县衙最近的薛记酒铺里,掌柜抬头看了看座无虚席的大堂,低头又看了看柜台下钱盒里那些闪闪发亮的金饼金块,眼睛已眯成了两条缝。
他的头顶上一阵脚步声响,几个闲汉笑嘻嘻地走下楼梯,围拢在柜台前,领头的抬手便丢了块金灿灿的东西进来。
掌柜低头一看,半边眉头顿时挑得老高。闲汉低声笑道:“这是最后一间了,某掂量着得有二两,成色也好,足足抵得一万钱,掌柜是夹一半下来,还是待会儿让我家兄弟过来装钱?”
掌柜毫不犹豫拿起夹子,瞧准地方一用力,金饼齐齐整整断成两半:“四郎挑一块去!”
领头的闲汉哈哈一笑,眼珠在两块金子间滴溜溜转了七八个来回,才貌似随意地抓了一块:“掌柜果然痛快,下回再有这样的活计,一定记得叫上咱们兄弟!”
掌柜苦笑着点头:“这还用四郎吩咐?就只是不晓得再有是哪年哪月了!”
闲汉也是一拍脑门儿,也是,长安城有刑部,有大理寺,有雍州府,官家人平日可是不会到县衙来受审的,自然也没有这么多贵人旁观。这种大清早帮店家先占了雅室,回头卖给贵客,再把收入与店家二一添作五的巧宗儿,当真不晓得什么时候再能赶上了!
两人脸对脸叹了口气,意犹未尽地正想感慨几句,店门口的伙计却突然拉长了声音:“这位郎君,里面请!”
这声调分明是又有贵客上门,几人忙回头去看,却见从门口进来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穿着件不起眼的玉色素面长袍,只是眉目俊逸出众,神情闲适清冷,那容光与贵气仿佛把整间堂屋都映亮了几分。
伙计们都忙得脱不开身,掌柜赶紧从柜台后迎了出来:“这位郎君……”
来人并未答话,他身后的小厮抢上一步道:“我家阿郎要一间靠窗雅座。”
掌柜的脸顿时皱成了苦瓜:“不敢欺瞒贵客,当真是一间都没有了。”
小厮笑道:“烦劳掌柜行个方便,价钱好说。”说着掌心一翻,手上已多了一块金饼,比刚才那块明显还要大上一圈。
旁边几个闲汉眼都要绿了,心中的悔恨简直难以言表。掌柜的脸看起来就像霜打过的苦瓜,声音里满是货真价实的悲痛:“当真是……没有了!”
小厮皱眉道:“掌柜莫要诳我,你们这楼上还有两间雅座窗子都没开,里头定然是空的!莫不是嫌这钱少?”
掌柜吓了一大跳:“小老儿哪敢欺瞒贵客,那两间一间是墙板坏了,坐不得人,还有一间是贵人早早就预订好了的!”
小厮眨了眨眼睛,转头去看他家阿郎。那男子略一思量,嘴角突然露出了一丝笑意:“却不知那贵人是姓萧还是姓乔?”他这一开口,声音竟是十分醇厚动听。掌柜却立时变了脸色——那两位贵人的确姓萧,可这事儿是东家亲自安排的,还反复叮嘱过不得外传,他怎么知道?他不由迟疑道:“郎君认得那位公子……”
来客淡淡地道:“我姓麹,今日与他们是一道的,劳烦前头带路。”
掌柜多少还有些发蒙,但对方轻描淡写的吩咐里自有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气度,他不由自主点了点头,恭敬地领着这位麹公子往楼上而去。
几位闲汉见没什么热闹可瞧了,也摇头晃脑地往外走去。麹公子经过他们身边时,却转头看了他们一眼。小厮立时拦住了这群闲汉,笑嘻嘻地一抱手:“各位请了,却不知诸位可有谁知道今日这桩案子的来龙去脉?”
几位闲汉相视一眼,还没答话,那小厮托了托手上的金饼,笑容更是诚恳:“我家阿郎今日无事,就想看场热闹,诸位若能到雅室给我家阿郎说一说前头的事,待会儿再帮忙去堂前看一看今日的情形,这就算是我家阿郎的酬劳了。”
闲汉们几双眼睛顿时大亮,领头的黄四毫不犹豫地点头:“好说好说,黄某这便上去!你们几个,都去衙门口前守着,把眼睛放亮点,耳朵伸长点,待开审之后,一炷香工夫换上一人到这边来传信!”
闲汉们应诺一声,一窝蜂涌了出去。小厮与那黄四上了楼,自有伙计引着他们到了当头第二间的雅座。只见这雅室甚是宽阔齐整,酒水食盘俱全,显然早就布置好了。那位麹公子正坐在窗边,手里端着一个白瓷杯悠然看着楼下,修长的手指看去比杯子似乎还要白皙几分。
黄四心里不由嘀咕: 这莫不是哪家的王孙?他不敢多加打量,上前抱手行礼。
麹公子并没有转过头来,声音也依旧是淡淡的:“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四忙清了清嗓子:“启禀公子,这桩案子原是前几天另一桩案子引发的,却不知公子可听说过西市这边有位何娘子?”
麹公子的眉头微微一皱:“似乎……听人提过。”
黄四笑道:“这位何娘子可是个大善人!她在东西两市附近盖了好些院子,租给大伙儿住。上个月因要出远门,这些院子竟是白送给大伙儿住两年。这原是天大的功德一桩,谁知西市那边有个姓金的泼皮,兄弟俩都租着何娘子的房住,弟弟因欠赌债跑了,兄长两个多月前又一病死了,这空出来的房子自然归了院里其他人家。那弟弟前几日回了长安,见兄长和房子都没了,哪里肯依?一状就告到了长安县衙,说是兄长死得不明不白,邻居们还强占了他们的房子。
县令接了状纸,把相关人等都叫到了衙门问话。邻居们都说冤枉,那金大郎是去年十二月摔了一跤,跌坏了手,在家里歇了十来日,年前却突然发起病来,正月初四夜里死的。那时何娘子还没说出门,谁会无故去害他?何况邻居们当时瞧他病得蹊跷,怕是伤寒,原是想把他挪到病坊去的。还是何娘子心善,把后罩房腾出来给他住,请了坊里医师来看不好,还请了外头的,最后还赏了他一副棺木!虽说当时因无亲友出面,金大郎的棺木是直接拉去了城外的乱葬岗,如今已没处寻摸,但前后两个医师来看过,病死的还能有错?
事情到了这一步原也好说了。没想到衙役们把坊里的医师带到堂上一问,却又问出了另外一桩事情。金大郎哪里是得了什么病?他是被人打坏了!因外头伤得不算重,他也没当回事,只说摔了跤,打算在家悄悄养好了再说,却不知早已伤到了根本。这种伤势一旦发作就是难救,因此后来虽也吃了几副药,拖了几天,到底还是一命呜呼了!
那弟弟听医师这么说,自然愈发不依,磕头流血,求明堂拿下打死他兄长的凶手。明堂便把与金大郎交好的泼皮都拿到堂上问了一遍,才知道这金大郎当日是在平康坊那边与人争一个妓女,才叫人打伤的。待得昨日把那边的妓女、武侯都叫来问话,却牵出了更大的事情。那打人的并不是寻常人,乃是今科来京城候选的官家人,听说有几个都已授了官职,立马就要赴任去了!
人命关天,明堂不敢耽误,当时就让少府带着人去了皇宫那边,恰恰将那几个堵了个正着!今日这边就要公开审理,让他们当堂对质。若真如那泼皮所说,此事就大了,事涉官家人,又是人命案,只怕立马就要转到大理寺去!”
想到这场大热闹就此到头,也不知哪一天才再有机会狠狠宰这些吃多了撑的公子哥儿,黄四不由怅然若失,好不忧伤地叹了口气。
他眼前那位吃多了撑的公子哥儿听得倒也入神,半晌才转头瞧了瞧不远处的县衙大堂,嘲讽地翘起了嘴角:“这位长安县令果然是雷厉风行!”
黄四一怔,这话听着怎么有些古怪?他干笑了一声道:“明堂这回的确利落。大约也是情势所迫,这原是最寻常不过的泼皮争产,谁知每天都有一番变故,一会儿是查找棺木,一会儿是验看药方,一会儿是捉拿泼皮,昨日连平康坊的美人都拿来了两个,今日更是牵出了这么些官家人,大伙儿谁不想过来看个稀奇?公子有所不知,这四五天里,外头听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当真是说什么的都有,明堂大约总要把事情弄个明白,才好收场。”
麹公子感兴趣地抬起了眸子:“说什么的都有?那到底有什么说法?”
黄四笑道:“有人说这姓金的是鬼迷心窍,一个泼皮,跑到平康坊去与人争美,结果被几个书生三拳两脚就打死了,这不是命数已尽,自己上赶着找死么?也有人说那些官家人太过凶残,为争个妓女就能下死手,要是真的当了官,平头百姓还能有活路?也不知朝廷这次是怎么选官的,竟选了这么些心狠手黑的玩意儿!”
麹公子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几分,不知为什么看着却让人有些发冷:“好!这话说得好,有理有据,意味深长!这事儿也做得好,水到渠成,天衣无缝!”
黄四摸了摸头,实在拿不准眼前这位贵人的喜怒,正不知如何回话,就听雅室门外有人笑了一声:“果然是玉郎!”
门帘一起,从外面走进两位男子,前头一个三十多岁年纪,微微有些富态,后面则是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两人穿戴都十分寻常,只是落在黄四这种人物的眼里,那身富贵气却比和尚脸上的胭脂还要来得抢眼。他赶紧低头欠身,悄然退到了门外。
雅室里,麹崇裕已不紧不慢地起了身,像是头一回见到萧氏兄弟般从头到脚将两人打量了一遍,抱手一笑:“果然是贤昆仲的手笔,麹某佩服!”
萧守规与萧守道相视一眼,心头越发惊疑不定。适才楼下的掌柜说有位姓麹的公子在雅室里等他们时,他们就吓了一跳,麹崇裕不是过完年就去洛阳了吗?是什么时辰回来的,而且直接找到了这里?这一进门,他居然劈面又是这句话……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萧守规便笑道:“玉郎此话怎讲?我们兄弟不过闲极无聊,过来瞧瞧热闹,什么手笔?”
麹崇裕微微一笑,优雅地欠了欠身:“原来如此,是麹某误会了,抱歉。”
萧氏兄弟只觉得一拳打到了空气里,想再解释几句又无从说起。待得三人分宾主落座,两人更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麹崇裕却是随意往凭几上一靠,伸手端起了面前盛着冷浆的杯子,一面瞧着窗下的情形,一面慢慢啜饮,那神态,仿佛不是身处闹市酒楼,而是对着高山林泉、白云空谷,哪里有半点要开口询问的意思?
萧氏兄弟顿时有些傻眼,还是萧守规咳了一声,开口笑道:“今日的确是巧了,却不知玉郎是如何知晓小弟在这酒楼定了雅室的?”
麹崇裕依然是一脸的漫不经心:“麹某能知道什么?麹某前日才回长安,突然听说出了这么桩事,自然要来瞧瞧热闹,不曾想大早上的这酒楼的雅室竟已客满,我瞧着有两间似乎还没人,一问掌柜才知,是早就被订了出去。麹某一时想岔了,提了提萧贤弟,没想到却是歪打正着。”
这话说了跟没说有什么两样?萧守道到底年轻气盛,忍不住问道:“这也奇了,玉郎为何听说有人订了雅室,就会想到我们兄弟头上?”
麹崇裕慢悠悠地低头喝了一口:“自然是因为麹某想岔了。”
萧守道眉头一皱,还要再问,萧守规忙向他使了个眼色,自己动手给麹崇裕满上了浆水:“玉郎有所不知,这家酒楼的青梅酒和青梅浆都极为有名,这些都是小弟昨日就订下的,玉郎尝着可还新鲜?”
麹崇裕欠身道谢。萧守规这才笑道:“玉郎也知道我们兄弟的,最是闲人两个。小弟我也是昨日才听人说起长安县衙这边闹得有些稀奇,立马便打发人过来订了个雅室,没想到竟会遇见玉郎。玉郎莫不是屈指一算,便算出长安城里就数我们兄弟最闲?”
他这边姿态放得十足,萧守道脸色就有些不大好,伸手倒了杯酒,闷头就喝。
麹崇裕的目光在两人身上转了转,脸上露出了自嘲的笑意:“大郎说笑了!麹某若是会算,又如何会落到今天这田地?不瞒两位说,有些事,麹某在西州时做得着实不算少,因此昨日一听此案,便觉得天下哪能有这般巧事?今日掌柜又说早有贵人订了雅室,更是落实了我这念头。因前几个月修建裴府时,就数大郎二郎助我最多,麹某未免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唐突之处,还望两位海涵。”
萧氏兄弟顿时松了口气。当日麹崇裕和裴行俭在西州究竟是哪番情形,他们虽然不大明了,但结果却是板上钉钉的: 裴行俭抢了麹崇裕的西州都护!两人回了长安后,面上还算有来有往,走得却不算近,这次裴行俭强人所难,非要麹崇裕两个月就修好宅子,更是无礼。看来麹崇裕在裴行俭手下当真是吃过亏的,而他之所以疑心到自己兄弟头上,也只是因为当日他们太过关切裴宅的修建,并不是真的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萧守规便笑道:“玉郎如此坦诚,倒叫小弟羞愧无地了。不瞒玉郎说,当日小弟的确是有些私心。守道今年也要参加吏选,那什么试判,他怎么做得来?自然是巴望着出点什么事,把试判早些弄黄了才好,没想到却是白忙了一场,倒是叫玉郎见笑了。”
麹崇裕同情地点头:“那试判的确害人不浅!我恍惚听谁说过一句,二郎和乔府三郎都是因笔迹不合被驳落的?”
萧守道脸上微微一红,萧守规已举杯笑道:“不提这些扫兴的事了,今日既有好戏可看,玉郎,咱们不如换上酒水助兴?”
麹崇裕扬眉一笑:“好!”
三人换了酒杯,推杯换盏喝了几口,就听下面一阵乱响,却是长安县衙已排开仪仗,开门审案了。就见那大堂上,差役分班而列,从后堂被请出的五位一字排开站在了堂前,前头是四位新晋的官员,末尾一个则是作寻常士子打扮。五人都生得仪表堂堂,穿着也比寻常人体面,此时笔直地站在那里,倒也颇有点一排玉树的意思,顿时激起了一片议论。
酒楼上,莫说萧氏兄弟瞪大了眼睛,连麹崇裕都放下杯子,凝神看了过去。
大堂之上,霍标几人依次报上了姓名来历,他们并不是平头百姓,莫说霍标已是大理寺八品评事,就是落选的舒侠舞也是正经的明经出身,自然不用下跪陈情。经过一夜煎熬,几个人的脸色都不大好,言谈举止却还未失方寸。
长安县令也颇为客气,只是笑道:“今日将诸位请来,原是本县有位金大郎于两个月前蹊跷毙命。据医者所云,他乃伤重不治,这位金大郎的伴当则说,他之所以身受重伤,是在平康坊与人殴斗。本县召来平康坊的武侯等人询问,人人都说,诸位就是当日动手的一方。相关证词,都已录供。本官虽不大相信,却也不得不将诸位请过来问上一声,不知诸位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午后,在平康坊北里中曲张氏宅中,可曾与人殴斗?”
堂上堂下,顿时变得静悄悄的。
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苏味道忍不住转头看了霍标一眼,却见那张俊朗的面孔此刻颜色灰白,分明写满了挣扎,他不由暗暗一声叹息,默然低下了头去。
他们几个昨日到了县衙之后就被分头“请”进了不同的房间。他在屋里坐立不安,一直等到天黑,才有位姓刘的主簿过来将事情分说了一遍,当时他便觉得五雷轰顶——唐律对杀人案判得极重,就算群殴打死人,首犯也是要抵命的,皇亲国戚都不能免罪。自己卷进了这种案子,就算侥幸得活,也是前程尽丧,名声扫地!
好在那主簿话头一转,说当日旁观者甚多,大伙儿都看得明白,伤重致死的那位金大郎是霍标动手教训的,与旁人并无干系,只是人命关天,相关人等总得问到,因此今日才不得不把他们都请过来。苏味道听得这句,腿脚都差点软了——幸亏出事的只是霍标动手的那个,幸亏自己没碰那位一根手指头,不然要论成群殴,自己这些人哪个能脱得了干系?只是霍标他,如此一来……
主簿最后也叹道:“霍评事可惜了,只怕……唉!少府几个纵然并无人命干系,少不得也要在公堂上如实禀告,方能离开。如此一来,莫说霍评事心里会有芥蒂,旁人瞧着也难免叹息。人言可畏,三人成虎,传到后来还不晓得会是怎样的情形!
苏少府,你们当日若是再喝多些,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不记得,反倒是好了!”
这感慨的声音此时仿佛还在苏味道耳边回响,他心里越发百感交集: 自己难道真要在大庭广众下亲口指认好友伤人致死?虽说句句是实,但此事做来……
他这里犹自纠结不休,那边县令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本县请诸位过来,原是一片好心!若是案子转到大理寺,少不得要拖上十天半个月,岂不是耽误了诸位的行程?到时说不定官位难保,又是何苦来哉!我再问诸位一句,你们可还记得当时的事由?若是实在记不起来,也只能委屈你们去大理寺分说了!”
他的目光在几人身上缓缓掠过,盯住了张茂:“张参军,你说呢?”
张茂身子微微一颤,沉默片刻,涩声回道:“启禀明府,下官记起来了。当日乃是试判之期,下官承蒙霍评事之邀,去张宅宴饮,酒宴过半,有一泼皮突然闯入院中,满嘴污言秽语,不忍卒听。霍评事受辱不过,方出去与他理论,争执之中动了手脚。下官与苏少府几个,则拦住了这泼皮带来的伴当,将他们赶了出去。事情原委,便是如此。”
苏味道心里暗暗松了口气,却听身边的霍标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心头一跳,转头看去,却见霍标脸色已变得十分平静,嘴角甚至还带上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笑意。苏味道的耳根顿时有些发烧,低头不敢再看。
这边县令又问过许弘毅,得了差不多的说法后,却又问道:“也就是说,当日殴伤金大郎的,乃是霍评事,与你等无关?”
许弘毅咬了咬牙,低头回道:“的确如此。”
苏味道虽不敢转头,眼角却清清楚楚地瞟见,霍标嘴角的笑意似乎又加深了几分,他心头的憋闷简直难以言表,耳边听到那县令已问到自己头上:“苏少府,当日你可曾看清,到底是谁人动手?”
仿佛有块巨石蓦然压在了苏味道的身上,他几乎无法抬起头来。“启禀明府,当日、当日……”惶然无措中,一句话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飞快地冲口而出,“下官喝得有些多,记不清了!”
县令皱了皱眉:“此话怎讲,少府难不成连自己动没动手都记不清了么?”
苏味道心里一横,咬牙抬起了头:“的确记不清了!”
霍标、张茂和许弘毅都惊讶地转头看了过来,霍标的眼里满是不可思议,张茂和许弘毅的目光里却渐渐带上了不满。苏味道不由一惊: 自己这么说虽然对得起霍标,却是陷他俩于不义了!只是话已出口,再没有反悔的余地……
县令看着苏味道点了好几下头,转眸又看向了舒侠舞:“却不知舒明经是否还记得当日之事?”
舒侠舞满不在乎地抱了抱手:“学生不敢欺瞒明府,学生只记得当日喝到一半,有人过来乱骂,学生似乎是与人打了一架。不过,学生当日喝得不少,只记得自己乱打了一通,却不记得还有谁动了手,也不记得自己打了谁。”
这话一出,连苏味道都被吓了一跳,这舒侠舞自打试判得了蓝缕,便颇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没想到在这场合下,居然能胡来得如此光棍!
县令倒是笑了起来:“有两个记得清,两个记不清的,霍评事,你又怎么说?”
霍标神色复杂,目光在几个好友脸上缓缓掠过,一字字道:“霍某当日做东,喝得也是最多,霍某,也记不清了!”
苏味道心里顿时一沉,旁人也就罢了,霍标怎么也含糊其辞?他是害怕刑罚,还是记恨张茂和许弘毅说了实话?可事实本来就是如此,大家也是没有办法。何况那日的情形,看见的人又多,供词都已经录好了,他这样做,除了能把几个人都拖在这案子里,耽误大伙儿的行程,又有何益?
那边张茂便皱眉道:“霍兄!你这是……”
霍标神色漠然地瞧着他:“人命关天,难道张兄就不许霍某实话实说么?”
县令瞧着他们针锋相对的模样,脸上慢慢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这样说来,你们倒是记不清楚的居多。也好,这和本县昨日问得的口供倒也对得上,看来那金大郎的确是被群殴而死!”
什么?堂上五个人里,倒有四个遽然变色。苏味道只觉得耳边轰然一响,惊得几乎回不过神来。张茂也是满脸愕然,锐声道:“明府此言何意!刘主簿昨日明明是说,县衙已将事情查清,下官适才也并无一句虚言,怎么又成了群殴?”
县令诧异道:“刘主簿?张参军昨夜是没睡好么?本县何曾有过什么刘主簿?”
苏味道心里一急,脱口道:“昨夜的确是有一位刘主簿过来说过,明堂已将事情查得明明白白,让学生,让学生……”
县令冷笑一声:“怎么,是他让你上堂来别说实话,只说喝多了记不清了?苏少府,你当本县是傻子么?天下会有这样的道理?”
苏味道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觉得手脚冰凉,呼吸困难,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声音: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县令伸手一指门外,声音更洪亮了几分:“昨日堂审,诸位父老百姓都听得清清楚楚,被带来的女伎、奴婢还有平康坊的两位武侯都说了,当时是一场混战,诸位人人有份!诸位是想说,本县昨夜派了个什么刘主簿来诱你们的供词么?真真是笑话!你们自己要互相推诿,原是人之常情,却莫要扯到本县的头上!诸位难道以为,有官袍在身,我大唐的诬告之罪就治不得尔等了?”
这话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外面,自有离得近的高声复述,顿时赢来了一片哄然叫好。这声音仿佛一记清脆的耳光甩在了苏味道的脸上,他蓦然清醒过来: 这不是误会,不是疏漏,这是人家早已布置好的陷阱,而自己,已是无从脱身!
县令冷哼一声,踱回了高案之后:“尔等身为士子,轻狂无度在先,互相推诿在后,当真令士林蒙羞!不过今日本县是不会将你们如何的,这武侯、女伎的供词都已在此,日后到了大理寺的堂上,诸位自然想如何当堂对质就可以如何当堂对质。还请诸位稍候片刻,本县这里还有本案最后一位证人,待本县问过这位医师之后,自然会请诸位去大理寺一行!
诸位,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瞧着眼前这张正义凛然的面孔,苏味道简直有些想笑出来: 他们这些人,的确够轻狂,自负学识过人,自以为锦绣前程已然在手,转眼之间却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跳到别人早就挖好的坑里!而直到现在,他们却连对方是谁,对方为何要下这样的狠手,都一无所知。愚昧至此,无能至此,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转头看了看张茂几个,那一张张灰败的面孔上,写着的是一模一样的绝望。唯有霍标一直低着头,看不清表情如何。
堂上的声音变得颇不耐烦:“诸位若是没什么可说的……”
“且慢!”霍标猛然抬起头来,一双眸子竟是亮得惊人。
他上前一步抱手行礼,沉声道:“下官愿意自首赎罪。望明堂明鉴,下官当日之所以轻狂无度,乃是因为在试判之前,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已答应下官,会让下官试判入等,注官留京!”
这几句话随着堂外一声声的传递,仿佛在油锅里泼进了一瓢冷水,顿时让人群彻底沸腾起来。
一片喧闹之中,没人注意到,薛记酒铺最当头的那处雅室,不知何时打开的一条窗户缝已悄然合拢,坐在窗边的女子缓缓取下了头上帷帽,露出的面孔竟是霜雪不足以喻其晶莹,花月不足以方其妩媚。她端起面前早已盛满的酒杯,一点一点将整杯酒都喝了下去。
仿佛是喝下了世上最甜美的琼浆玉液,那张美丽面孔上慢慢绽开了一个欢悦之极的微笑。
随即,她毫不犹豫地起身戴上帷帽,低声道:“走吧。”
一旁的侍女疑惑地往外看了看,也谨慎地压低了声音:“娘子?咱们冒险留下这么久,您不是说……”
女子轻轻摇头,那带着笑意的艳丽容光仿佛隔着面纱也能晃乱人的心神:“不用再看了,老天有眼,竟然还有这样的意外之喜,他们也算是报应到头,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再贪心,咱们就走不了了!”
雅室墙上的小门无声无息地打开又合拢,空荡荡的屋子里看去依旧整洁而清冷,仿佛从来就没人在这里出现过,唯有案几上那壶残酒和屋里犹自飘荡的那缕幽香可以证明,在酒楼的幽暗斗室中,在长安的十丈红尘里,曾有美人悄然而来,飘然而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