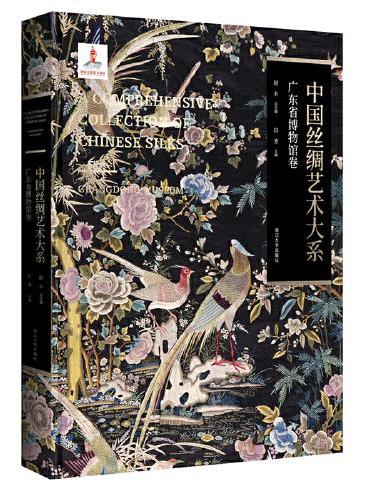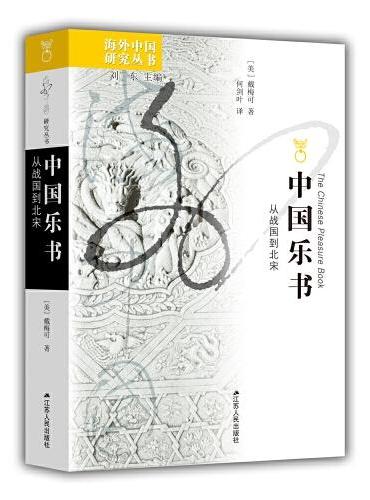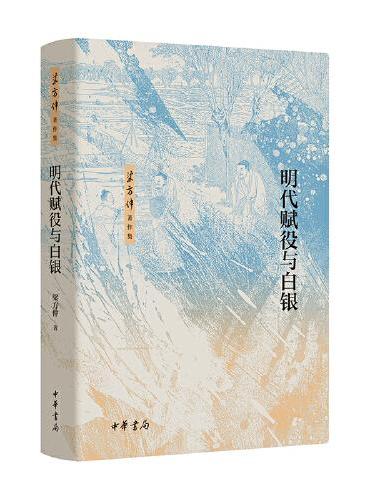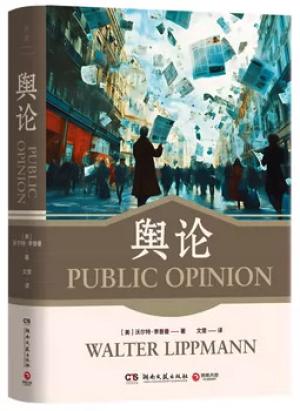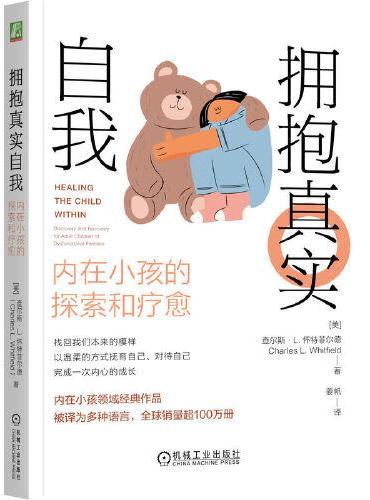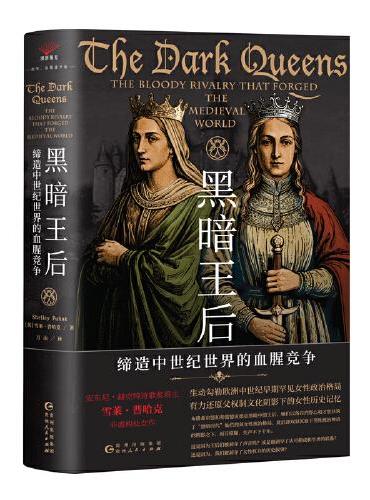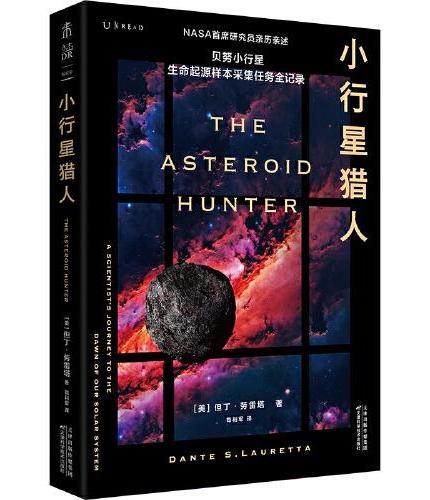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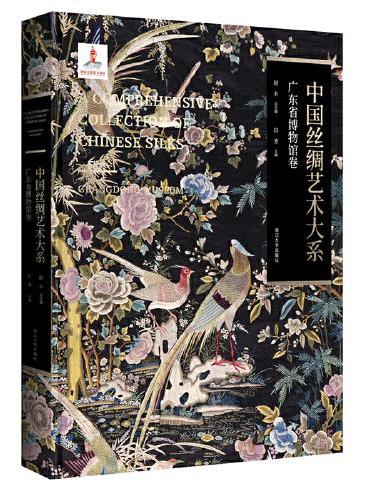
《
中国丝绸艺术大系·广东省博物馆卷
》
售價:NT$
49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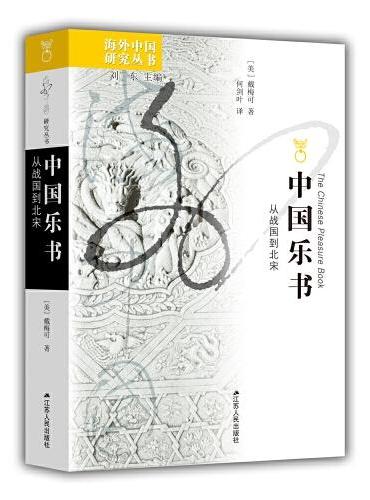
《
海外中国研究·中国乐书:从战国到北宋
》
售價:NT$
7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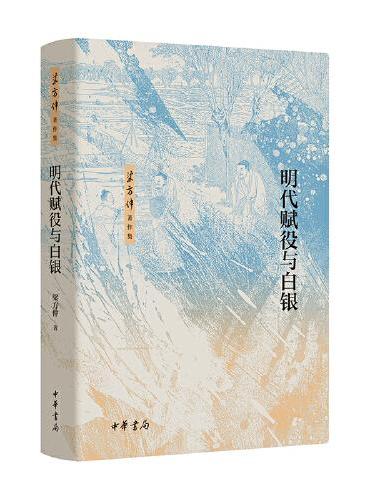
《
明代赋役与白银——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367.0

《
量子纠缠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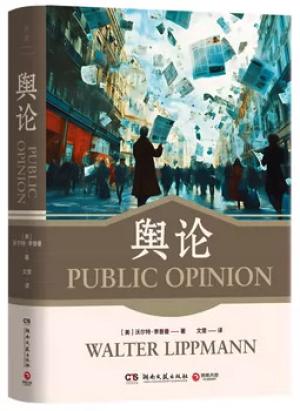
《
舆论(普利策奖得主、“现代新闻学之父”沃尔特·李普曼传播学经典)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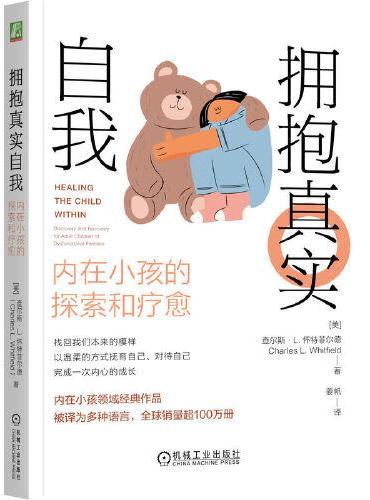
《
拥抱真实自我:内在小孩的探索和疗愈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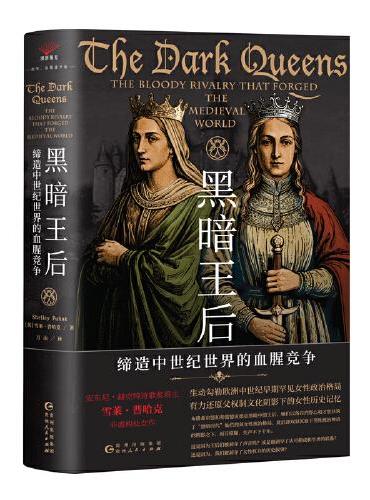
《
黑暗王后:缔造中世纪世界的血腥竞争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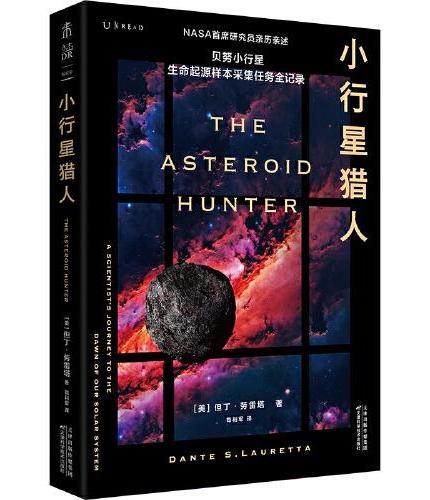
《
小行星猎人:贝努小行星生命起源样本采集任务全记录
》
售價:NT$
296.0
|
| 編輯推薦: |
无数精彩历史细节的饕餮大餐 20世纪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经典传奇 美国-延安-天安门
见证中国重大历史变革的个人记忆 澎湃的革命激情背后,又是怎样的现实生活逻辑 美国革命者李敦白,青年时代来到中国,为实现改造世界的美好愿望,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开始了他在中国跌宕起伏的三十五年人生历程。相隔七十年以后,2013年,李敦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徐秀丽研究员一起,共同完成了这部堪称理想主义者经典传奇的口述历史著作。
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爷爷是州议员,父亲是大律师。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李敦白,从少年时代起,就发现了社会的种种不公,他为了改造旧世界,建立一个理想的美丽新世界,19岁时加入美国共产党,参加工人运动。作为口述历史的开篇,“早年岁月”部分鲜活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社会的状况,美国的工人运动,美国革命者的思想和观念,以及美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理解,其中很多细节都非常有意思,比如,李敦白父亲对他说的两个观点:“第一,你信奉社会主义我赞成,资本主义制度太坏,不过我家庭的利益已经跟资本主义紧扣在一起了,我本人没有办法。第二,我觉得谁也还没有创造出比
|
| 內容簡介: |
|
一个深度参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美国人 以独特的视角、罕有的诚实与宽广的胸怀 讲述他一生执着追求理想、跌宕起伏乃至惊心动魄的命运历程,并直白表达他深入的思考和见解。 在无数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与碎片中 折射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真实历史境况和纹理 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以一颗赤子之心,抱着改造旧世界,建立公平合理新世界的美好理想,秘密加入美国共产党。二战结束时来到中国,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动荡起伏的三十五年历程。他与我党许多高级领导人,包括宋庆龄、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光美、任弼时、邓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镕基等,都有私人交往;他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并亲眼目睹很多高层发生的事情,叙述中他披露了领袖人物在生活与工作中的大量细节,弥为珍贵。他以“一个中国的美国人”的视角、罕有的诚实坦率,讲述了他在中国的非凡经历。个人生活的跌宕起伏,折射着历史的华章与疯狂,发人深省。而李敦白对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救赎与疗治,于中国读者则深具启发价值。李敦白称他的妻子王玉琳是上天下来的天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与妻子重回美国创业,生活美满幸福,而直到今天,他对中国发展的关切仍然一往情深。本书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编写严谨、规范的口述史著作。
|
| 關於作者: |
李敦白(口述者)
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美籍中共党员。1921年出生,二战结束时来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长期在新华社从事英语广播工作,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最高领袖以及陈毅、聂荣臻、李先念、王震、江青、王光美等中共重要人物都有交往。在中国度过跌宕起伏的三十五年,1980年回到美国后,生存的逻辑使他由革命者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
徐秀丽(撰写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编审,《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研究方向及成就主要为中国近代经济史,涉猎近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
|
| 目錄:
|
致中国读者 李敦白
第一部分 早年岁月
你有多少钱,就可以买多少公道
有一些人,他们最像基督徒,他们是共产党员
参加美共
权利是你以为你有的东西
从反战到入伍
你到花园里挖个洞,对面就是中国
斯坦福受训
第二部分 中国经历
一、 木仙之死
二、 上海印象
三、 宣化店“告密”
四、 到延安去
五、 “特殊任务”
六、 从牢房的糊窗纸上,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七、 外国专家
八、 “黄金十年”
九、 又一次“特殊任务”
第三部分 智慧疗法
一、理解和爱让我宽容
二、辩证法帮了大忙
三、尽可能保持身体健康
四、监视孔成为沟通世界的重要管道
五、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六、对“不朽”的理解
第四部分 我的天使
就这样认识她
我做了炒饭,你来吃吧
初到美国的王玉琳
附 王玉琳:我与李敦白
十七岁才第一次吃水果
我妈说,你为什么非要嫁一个外国老头
革命年代的生活
“美国特务”老婆
为了得到李敦白的消息,我要求离婚
第五部分 风雨故人
一、 宋庆龄
二、 周恩来
三、 陈毅
四、 王震
五、 李先念
六、 刘少奇
七、 王光美
八、 邓小平
九、 任弼时
十、 廖承志
十一、 陆定
十二、 聂荣臻
十三、 贺龙
十四、 彭真
十五、 张体学
十六、 陈少敏
十七、 师哲
十八、 温济泽
十九、 丁一岚
二十、 于光远
二十一、 丁铃
二十二、 周扬
二十三、 新华社的“怪专家”
二十四、 陶铸
二十五、 冀朝鼎
二十六、 陈翰笙
二十七、 孟用潜
二十八、 钱钟书
二十九、 郭沫若
三十、 杨宪益
三十一、 江青
三十二、 张春桥
三十三、 陈伯达
三十四、 王洪文
三十五、 王力
三十六、 蒯大富
三十七、 聂元梓
三十八、 斯特朗
三十九、 马海德
四十、 爱泼斯坦
四十一、 寒春、阳早
四十二、 马尼娅
四十三、 舒子章
四十四、 朱镕基
第六部分 归去来兮
一、 是回去的时候了
二、 从此岸到彼岸
三、 协助华莱士访华
四、 葛培理牧师
五、 “通往中国之路”
六、 你们最需要的是:我!
七、 “李敦白有限公司”
第七部分 如是我思
一、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二、 我看毛泽东
三、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四、 中美关系
五、 宣传形象,关键得有“形象”
六、 我相信中国的未来
七、 我的选择,是我一生的幸运
李敦白先生印象记
后记
|
| 內容試閱:
|
节选五、“特殊任务”我一生中领受过两次通向监狱的“特殊任务”,第一次是1949年初在东柏坡。
我在东柏坡是突然被抓的,那应该是1949年2月中下旬。当时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我们正期待着早日前往北平。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廖承志处报到。我兴冲冲地到达后,他给我看了一份由刘少奇签署的命令,让我和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到北平执行特殊任务。我以为,即将承担的任务一定与处理中共跟美国的关系有关,很可能是为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沟通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我很激动,我终将承担历史赋予我的重要使命,终将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留下自己身影。我匆匆忙忙地回宿舍收拾了几件衣服和盥洗用具。没时间跟妻子魏琳告别了,我留了一张纸条给她,说我先走一步,我们很快就会在人民的新北平见面。
与我同行的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师哲。我上了师哲上的吉普车。他穿着军装,好像还穿了一双小短靴,是个出远门的样子。我很高兴与他同行,我们原来就认识,我的印象中,他是位很和气的老革命。事后回想,有两件事比较特别。第一件,出发前,我正跟廖承志聊天时,新华社记者丁明拿着一个塔斯社的电报跑进来,说“臭名远扬的美国特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另一件是告别时廖承志拥抱我,说小洋鬼子,不要太担心,事情总会搞清楚的,你可不要像“刘备进荆州”那样。按说这两件事都是非同寻常的,斯特朗我那么熟悉,怎么可能是美国特务?而我虽然看了《三国演义》,刘备进荆州是怎么回事却毫无印象。照常理,这两件事我都应该问一下,但我正沉浸在高度兴奋中,脑子自动屏蔽了这些疑问。
车上还有一个年轻的干部,后来知道他姓徐,别人叫他徐科长。师哲坐后排,年轻干部开车,我坐副驾位。我们的吉普车越过滹沱河,往北开了一段,车上还聊起刚刚听到的斯特朗被驱逐出境的事,师哲显得很吃惊的样子问我“真的吗”?走了一会,年轻干部突然说:糟糕,我忘了拿暖壶,路上没有茶喝。师哲说:路途很远,还是回去拿吧。吉普车调了个头,再次越过滹沱河,到了一个听起来叫“怀社”的村子的一个地主大院门口,他们俩走了进去,让我坐在车里等。过了一会,年轻人出来对我说:师哲同志有点事,要耽搁几分钟,你不如进来喝茶吧。
我下车,走进这个大院。院里有东西两个耳房,他把我带到左边的耳房,让我坐在桌边,说他去拿茶。这时,外面石板地上传来“笃、笃、笃、笃”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什么。正猜疑间,门忽然被推开,进来一个柱拐杖的人,他戴着很厚的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我以前从未见过此人,后来听说好像是刘少文——我就见过他这么一次。他两眼瞪着我,说:李敦白,我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逮捕你,你受美帝国主义的指派前来破坏中国革命!
好像头上被狠狠打了一棍,顿时天旋地转,只觉得整个屋子飞速转动,眼前星星乱飞,还感觉脑子里被什么东西使劲拽了一下。不,我没觉得他在开玩笑,我不认识他,而且他的态度非常严厉。马上上来几个士兵,把我衣服都扒了,有一个还扒开我的嘴检查,发现有个补过的牙,我很怕他们会把那颗牙挖出来,幸好没有,士兵只报告了这个情况。他们让我穿上黑色的衣裤,把我推到右边的耳房。这间屋子的窗户被木板钉得严严实实,里边一团漆黑。
在哨兵把我推过院子时,我哭了起来。哨兵对我说:没有关系嘛,有什么问题,组织上不会解决吗?他的话给了我另外的信息,震惊之中又添加了迷惑。
几分钟后,又把我带回左边的屋子,开始审讯。一起乘车的那个年轻军官主审,师哲在场。师哲说,我们对你的情况一清二楚,现在就看你自己的态度,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以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政策当时就有。我心里想,好像天下的审讯者都一样,伯明翰的警察抓我时,说,我们对你清楚得很,比你妈还清楚。然后问,你的全名怎么拼写?我对师哲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这样的人。他大发脾气,说你把我们看成乡下佬,笨蛋,把自己看得很高明,你以为我们没事干呢!他还说,你是敌人对准我们的一把刀,我们现在要把刀口转过来指向敌人,如果你痛痛快快地交代,把你的特务关系都说清楚,我们上车继续去北平,这个小屋子里发生的事情,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是第一条道路,你还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选,就是拒绝交代,不过,我们有办法让你讲,你最后一定会讲。说到这儿,他拍拍自己的身子,接着说:但是,你会受不了!我立即抓住了这句话,说:你们威胁我,要给我上酷刑。他马上退缩了,说: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即使我们想这么做,毛主席也不会允许。
后来我说,我愿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毫无保留。师哲说,我们不需要你长篇大论胡说八道,你只要交代你的特务关系就行了。他还说,我们知道你到解放区以后没有干过坏事,有些特务来了,受到感化,或者出于胆怯,没有干原来想干的事,我们只要你交代你的关系。我巴不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但没办法,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关系”。后来我在美国讲演,还跟听众开玩笑,说最好大家事先准备好可以交待的材料,万一哪天被捕就有得说了。就这么翻来覆去地审问了一天。中间师哲还用很轻蔑的口吻对我说,你们美国人最看重的是自己的生命,另外就是女人,美酒。我不同意他的话,我说我们美国人同样可以为正义事业献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争夺太平洋岛屿的战争,美国人多么勇敢,多么不怕牺牲。师哲听后没有反驳。他只参加了第一天的审讯,后来都是那个年轻人审。他不让我交代问题,只反复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两句话,叫我端正态度,说只要态度端正了,接下去的事很容易办。
端正态度花了几个星期,没什么效果。徐科长就说,你说你要交代,那好吧,你说,我给你记下来,但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开始讲,从头讲起,特别是自己认为可疑的事情,我都提了,怕日后查出来更说不清。比如我有个表兄,其实我们没见过几次面,他是个律师,也是个FBI。我还讲了跟斯特朗的关系,他装作没兴趣。
先后大概讲了两三个星期。也不是每天讲。我当时思想上有很大的迷惑,一直摇来摆去,摇来摆去,一会儿觉得他们搞错了,一会儿又觉得他们是在考验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整风。我在新华社的朋友和熟人,几乎都在整风运动中挨过整,有的神经衰弱,有的不再能够写作,只能改行摄影之类的工作,有的战战兢兢什么都怕。我对自己说,他们搞错了,但我不能埋怨党,那样的话我这个人就变了,就不是原来的我了。我也不能被整垮,那样的话离开这里之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也想到,把我搞错的事传出去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影响不好。
反复摇摆中,我决定来一个假自首。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承认我是特务,他们会判我十年二十年刑,把我送到某一个荒僻的地方劳动改造,我会表现得很好,他们最终会发现我不是特务。这样,我的嫌疑最终能够洗涮,而党也不受损失。
我确实没干坏事,但编造假自首,也能找到一些“根据”。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时候,CIA的前身OSS的前身SSU(StrategicServicesUnit,战略服务部)曾到我们班上挑选志愿者,准备把他们空投到中国的敌后,跟八路军取得联络。我很高兴地报了名,但没被挑上,我的两个同学挑上了。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被空投,大概没有吧,听说他们后来到了桂林,搞解密工作。另外,我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的时候,我们视察部的主任,这个人原来是陆军情报部的上校,还有我们的副署长,发现我喜欢解放区,都说过希望我留意有关的情况。我把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串连起来,编了一个故事,说我答应了上校的要求,就到解放区来了。这样编,不涉及解放区的任何人,不会连累别人。
我跟哨兵说,我准备自首。第二天上午,师哲来了,他让我坐下,说你准备坦白?我说是。他两眼瞪着我,问:你是特务?我看着他的眼睛,突然呜呜呜呜哭了,边哭边说我不是我不是。师哲很生气地来回走动,说,咳,你不相信我们,你也没有理解我们,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你,隐瞒是犯罪,夸大也是犯罪,谁让你说假话?看来这个事情我们还得重来。最后他说了一句:你应该经得起这个考验。听了这句话,我如获至宝,看来确实是考验,是整风。事实证明,这种摇摆对我的精神产生的破坏作用很大,如果能够始终面对现实,后来的情况可能不会那么糟。他让我回去好好考虑交代,说你是有问题,不是没有问题。
回去坐了两天,徐科长又提审了我。这一次,他满面笑容,说,师哲同志批评了我,说我对你帮助教育不够,以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就提出来,我来帮你。
又过了两三天,还是这个徐科长提审我,这次又变脸了,特别厉害。他说,李敦白,你以为你很聪明,以为骗得了我们,我告诉你,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
然后把我放了几天没理。我坐在黑屋子里,觉得非常苦闷,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明白徐科长为什么翻云覆雨,脑子高度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哨兵拿了两片白色的小药片给我吃,说我们发现你最近感冒了,这是给你的药,我说我没感冒,他说反正你得吃药,不吃就灌。此后,每天三次、每次两片让我吃药。记不清吃了多长时间,因为脑子乱了之后就不知道是否继续吃了。这个哨兵姓白,后来到北京对我的看管松下来后,已经成为看守的老白拿了另一种药给我,说这种药是为了解除以前那种药的药效。关于这种小药片,我后来问过曾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大夫,据他讲,当时给俘虏营的部分战俘吃过一种药,其作用是刺激神经,让人紧张,睡不好觉,倒没有别的坏作用。我吃的可能就是这种药。
我确实觉得精神极度紧张。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同志,没穿军装,我以前没有见过他。他开始态度很和蔼,问我,李敦白,你觉得最近身体怎么样,情况怎么样。我说我觉得没有问题。突然,他也变脸了,说,我们发现你很相信美帝国主义,你也很怕美帝国主义,比怕我们还要怕,你应该怕我们,再不交代,有你好看!他们这样变脸,也大大增加了我精神紧张的程度。
关我的黑屋子很小,四分之三被土炕占据,炕前面一块小空间可供移动,但熄灯之后,必须躺着,连坐在坑上都不行。墙上凿一个洞,里面放一个小灯盏,点的是豆油,发出小小的黄色的火焰。有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看着那个小火苗,看着看着,那个火苗就变成了一个跳舞的小人,我觉得自己仿佛跟着那个小人,越走越远,直到睡过去。一会儿,又突然惊醒过来,觉得非常紧张。我意识到自己不对头,很害怕,我请哨兵允许我下炕走一走,他说“不行”。我又请求他把徐科长叫来,他说过我有问题可以叫他帮助,我现在实在需要帮助。他还是不允许,让我睡觉,别捣乱。我开始大叫:“徐科长,徐科长!”我并不知道他是否住在院里,看来是,他一会儿就过来了,打开门,抖着手里的手铐,说:李敦白,如果你不遵守纪律,我们就会用纪律来制裁你。我说你不是答应帮助我吗?我不是装的,我真的很紧张。他说,我没说你是装的,我说的是你要遵守纪律。然后“砰”地关上门,走了。那天我整晚未睡,很怕自己精神要垮台。
第二天上午又提审,徐科长笑嘻嘻的,说,李敦白,昨天晚上你给我们唱洋戏,你还会唱什么戏,唱给我们听。哨兵走过来,递给我一个小馒头,说,最近你吃得少,吃一个馒头吧。我拿过来,刚咬了一口,就一头晕倒在地。我醒过来时,几个哨兵正在把我抬回牢房。他们把我放在炕上,我大概精神失常,乱踢乱闹,他们用我的军大衣捂住我的脸,我窒息过去。再次醒来,脑子就完全乱了。
这一乱,就乱了几个月。出现种种幻觉。幻觉中,我的好朋友彭迪来了,说周副主席很关心你,要你好,钱行(她的丈夫)也要你好。毛主席手里拿着把刀子,旁边是缩成一团的马海德,马海德哀求我赶快交代,不然他要受苦。我吃虫子,吃泥土,什么都吃,我还乱闹,闹得厉害时他们就给我上手铐,越挣扎手铐越收紧,我便昏死过去,等醒来,手铐已去掉,手腕上鲜血淋漓。可是,在头脑混乱中,我仍然有一种非常悲痛的感觉,每天晚上都觉得第二天不会再醒来。那段时间,可以说和死神同寝。幸好,即使在最混乱的时候,心灵深处还保留着最后的一丝清明,那就是觉得自己病了,不正常,得想办法让自己好起来。
夏天,我被装上一辆盖着毡布的日本卡车,运到北京,关进北京市第二监狱。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到了北京。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