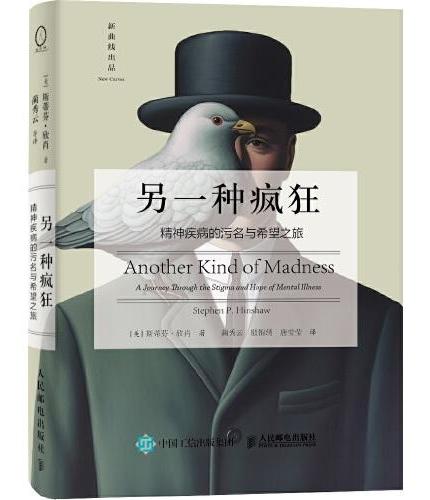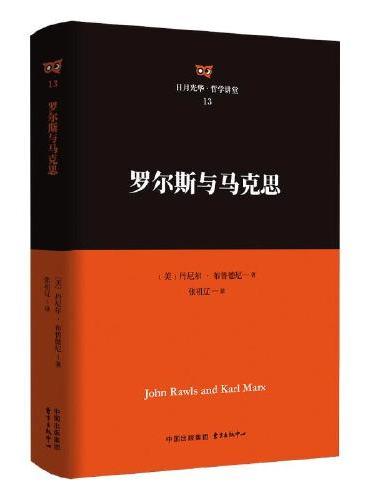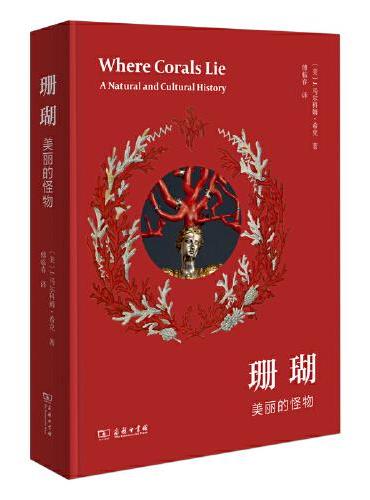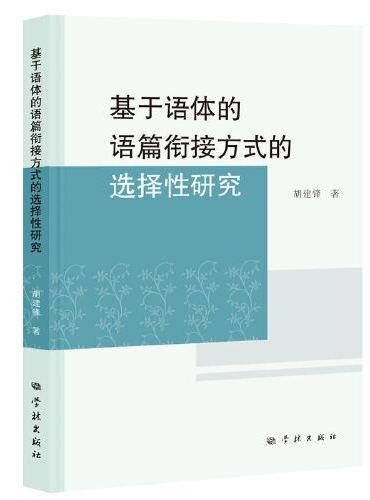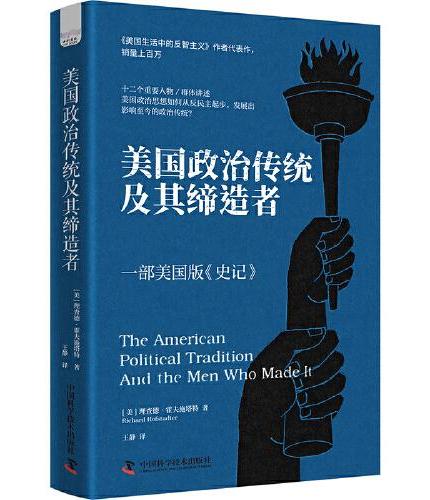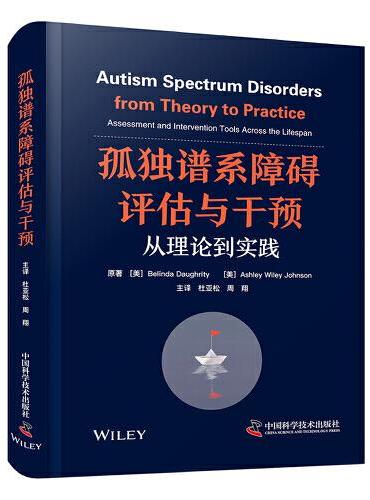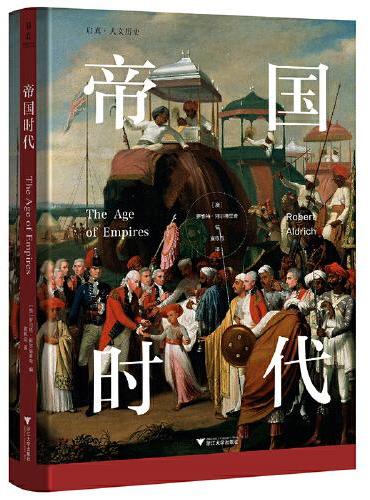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另一种疯狂:精神疾病的污名与希望之旅(APS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斯蒂芬·欣肖教授倾其一生撰写;2018年美国图书节最佳图书奖)
》 售價:NT$
296.0
《
罗尔斯与马克思
》 售價:NT$
398.0
《
珊瑚:美丽的怪物
》 售價:NT$
587.0
《
基于语体的语篇衔接方式的选择性研究
》 售價:NT$
347.0
《
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部美国版《史记》
》 售價:NT$
449.0
《
孤独谱系障碍评估与干预:从理论到实践 国际经典医学心理学译著
》 售價:NT$
1061.0
《
大数据导论(第2版)
》 售價:NT$
352.0
《
帝国时代
》 售價:NT$
959.0
編輯推薦: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D. H. 劳伦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1928年在佛罗伦萨秘密出版。
內容簡介:
康妮嫁给贵族查泰莱为妻,但不久他便在战争中负伤,腰部以下终生瘫痪。在老家,二人的生活虽无忧无虑,却死气沉沉,直到庄园的猎场看守重新燃起康妮的爱情之火及其对生活的渴望。《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英国小说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品之一,长期遭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宣布开禁后,小说一度洛阳纸贵,长期高踞畅销书排行榜并长销至今。
關於作者:
D. H. 劳伦斯(1885—1930),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出生于矿工家庭,当过厂商雇员和小学教师。曾在国内外漂泊十多年,对现实抱批判否定态度,谴责西方工业文明对人的“兽化”。代表作有《虹》、《恋爱中的女人》、《儿子与情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
目錄
废墟上生命的抒情诗(译序)
內容試閱
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