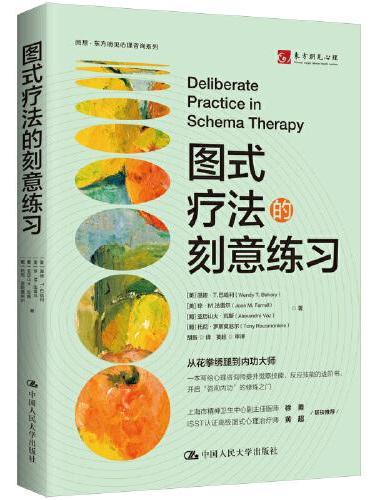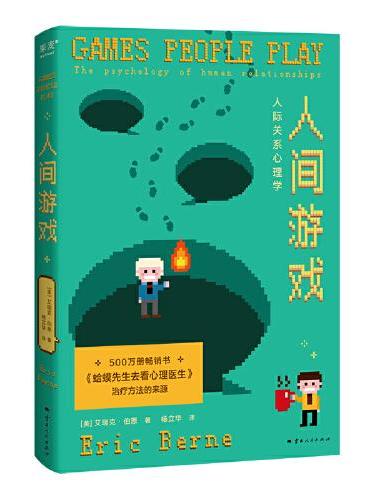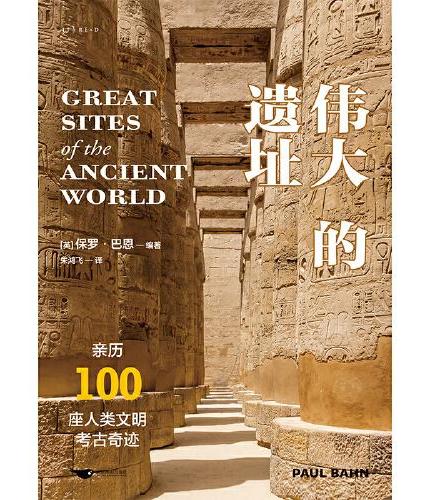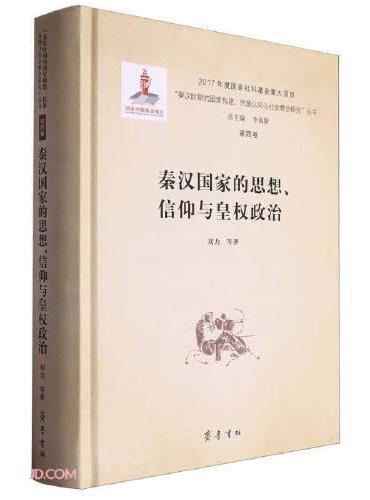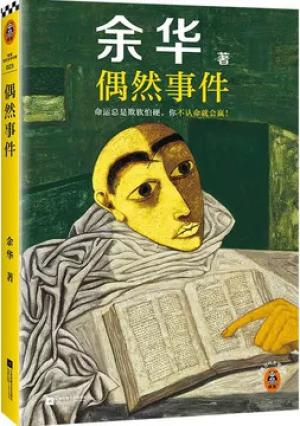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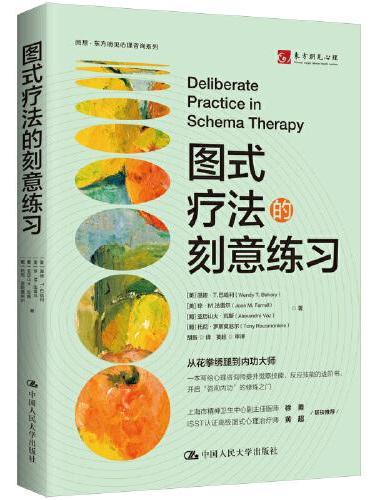
《
图式疗法的刻意练习
》
售價:NT$
4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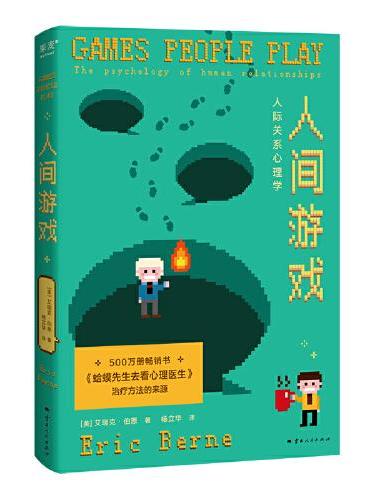
《
人间游戏:人际关系心理学(500万册畅销书《蛤蟆先生》理论原典,帮你读懂人际关系中那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
售價:NT$
2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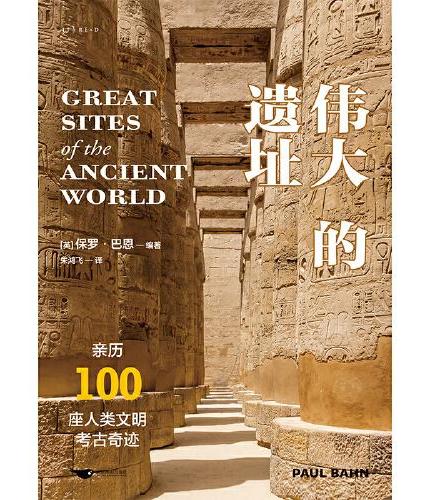
《
伟大的遗址(亲历100座人类文明考古奇迹)
》
售價:NT$
95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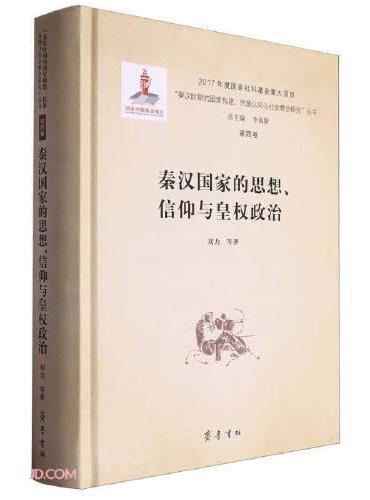
《
秦汉国家的思想、信仰与皇权政治
》
售價:NT$
1000.0

《
反卷社会:打破优绩主义神话(一本直面焦虑与困境的生活哲学书!)
》
售價:NT$
3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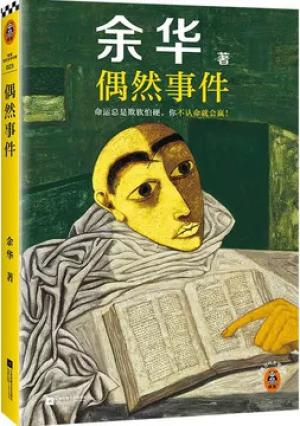
《
偶然事件(命运总是欺软怕硬,你不认命就会赢!)
》
售價:NT$
255.0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NT$
959.0
|
| 編輯推薦: |
1、在一个线性时间的来龙去脉中,范小青以中庸的力度打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哲学,一个是现实。
2、“我的叙述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疑惑,同时也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温情”,范小青如是说,如是一个奇光四射的后现代文本熠熠诞生。
3、全书没有甲骨金石的形容;不比喻,不咏物,不状事,不涉教益,无关见地,只有竹木帛纸的大白话叙述,惟有叙述。
在一个线性时间的来龙去脉中,范小青以中庸的力度打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哲学,一个是现实。
一个极简的故事主题:我丢失了弟弟,我又去寻找弟弟。故事叙述中,患有智障的弟弟恰如龙卷风,把所有人物都裹挟了进去。丰富庞杂的情节,循环往复的纠结,谵妄无休的盘诘,把故事的迷径写得海咸河淡,温度适中。
独到的以萤火之光起笔,以一片废墟收山,显示出作家卓越丰稔的艺术功力。于细腻微妙的人物关系循序渐进地深入到肌理细纹,深入到骨髓,再转化为小说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的重要结构,便极大地强化了小说人物的悖反张力。
全书没有甲骨金石的形容;不比喻,不咏物,不状事,不涉教益,无关见地,只有竹木帛纸的大白话叙述,惟
|
| 內容簡介: |
|
《我的名字叫王村》有一个夺人眼球的开头:“我的弟弟是一只老鼠。”随即叙事者向你娓娓道来:弟弟是一个把自己想像成一只老鼠的精神分裂病患。由于他的举止、生活习性都和老鼠相同,给他人带来了很多麻烦,尤其是阻碍了家中其他兄弟姐妹的婚事,使家人蒙羞,所以在带弟弟去看精神科医生无果后,一家人商量派叙事者“我”去“把弟弟丢掉”。但这一理性对疯癫的排斥却并不如福柯描述的那样理想化,也并没有因为弟弟被确定为精神分裂而导致所谓理性与非理性的“对话的破裂”。相反,从“我”带弟弟看病开始,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纠缠不清、界限模糊,甚至理性常常有被疯癫战胜、同化的危险。
|
| 關於作者: |
|
范小青女,江苏南通籍,出生于上海松江,从小在苏州长大。78年初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82年毕业留校任文艺理论教师,85年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委员。80年起发表文学作品,以小说创作为主,著有长篇小说十九部,代表作有《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等,中短篇小说三百余篇,另有散文随笔、电视剧本等。共创作字数一千多万字。有多种小说被译成英、法、日、韩等文字。短篇小说《城乡简史》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城市表情》获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第三届中国小说学会短篇小说大奖,另有《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奖项。
|
| 內容試閱:
|
一
我弟弟是一只老鼠。当然,这是他妄想出来的,对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来说,想象自己是一只老鼠,应该不算太过分吧。
其实弟弟很小的时候就得了病,可是谁会相信一个小孩子说的话呢,就算他说自己是老虎,也不会有人理会他的。何况我们家,子女多,钱少,人傻,爹娘要靠劳动养活我们一群兄弟姐妹,哪有多余的精力去在意一个满嘴胡说八道的小东西。
作为一只老鼠的弟弟渐渐长大了,长大了的老鼠比小老鼠聪明多了,这主要表现在他把自己的妄想和现实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比如弟弟听到一声猫叫,立刻吓得抱头鼠窜;比如弟弟看到油瓶,就会脱下裤子,调转屁股,对着油瓶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想通了,那是老鼠偷油。我们谁都没有看见过老鼠是怎么偷油的,只是小时候曾经听老人说过,老鼠很聪明,如果油瓶没有盖住,老鼠会用尾巴伸到油瓶里偷油,弟弟学会了运用这一招式。弟弟还会把鸡蛋抱在怀里,仰面躺下,双手双脚蜷起,如果我们不能假装是另一只老鼠把他拖走,他就会一直躺在那里。
当然,话要说回来,弟弟也不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以为自己是一只老鼠,也有的时候,他是糊涂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人,也会说几句人话。但是你千万别以为这时候他就一切正常了,这时候如果有人好心跟他说,弟弟,这才是你自己啊,你不是老鼠,你是人啊。弟弟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他会生气。弟弟生气的方式和一般人不一样。这一点你们完全不必惊讶,他本来也不能算个一般人。弟弟一生气,立刻就会想起自己是一只老鼠,他立刻将自己的双手蜷起来,做成尖利的爪子的形状,搁到下巴那儿,然后再从下巴那儿快速地伸出去攻击他人,又抓又挠,嘴里还发出“吱吱”的叫声。
大家哄笑着四散躲开。有人说:“不像,不像。”
另一个说:“像只猴子。”
其实大家并不怕他,毕竟弟弟只是一只扮演得不太像的老鼠。
我这样说,看起来是在为弟弟开脱,其实才不呢。我心里恨透了我弟弟,即使一天只有一个小时甚至更少的时间认为自己是一只老鼠,也减少不了我们对于弟弟的深恶痛绝。
因为弟弟其实比一只真正的老鼠更烦人,一只老鼠除了做老鼠能做的恶事之外,它做不了别的事情,而弟弟比真正的老鼠要高明许多,因为他除了有老鼠的一面,还有别的很多面。比如,他有人的一面,特别是有人的坏的一面,至于人的好的一面,在我弟弟身上,我还没见识过呢。
你别看他平时懒懒散散,对任何人都很冷淡,连斜眼看一下我们都不愿意,基本上不跟我们说话,似乎一点儿也瞧不上我们,可是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一点儿也不冷淡了。他会吃很多的饭。如果我们干活晚一点儿到家,他甚至会吃光锅里所有的饭,让我们活活饿一顿。老鼠晚上不睡觉,弟弟晚上也不睡觉,害得我们常常要在半夜里出去找他。那时候他在村子里到处窜走,在地上到处看,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但是谁知道他在找什么呢?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在到处寻找的时候,他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只老鼠。
到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弟弟病了,我爹让我带弟弟到城里的医院去看病。我们到了医院,挂号的时候我傻了眼,我虽然认得字,但是我不理解这些字的意思呀,精神科,神经科,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普通精神科,老年病专科,儿童心理专科,妇女心理专科等等等等——我正对着它们发愣,就听小窗口里那挂号的问:“喂,你看什么病?”我赶紧说:“不是我看病,是我弟弟。”我把弟弟拉到窗口让她看了一眼。那挂号的却说:“我不管你们谁看病,我是问你挂什么科?”她看我呆呆地回答不出来,又启发我说:“你看病总要挂号的吧。”我为难地说:“我还、我还不知道我弟弟是什么病呢。”那挂号的笑了笑,说:“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还能看什么病呢?”不过她还算热心,见我为难,主动说,“我看你们是头一次来吧,你弟弟是怎么个情况?”我说:“我弟弟是一只老鼠。”那挂号的并不觉得好笑,也没觉得我是在作弄她,她大概见得多了,所以只是“哦”了一声,就告诉我应该挂精神科。
我递了钱进去,并且报上名字和年龄,她动作十分利索地扔出一个病历给我,还嘱咐了一句:“在二楼。”我带着弟弟到二楼,坐到走廊的长椅上等候。坐下来时没有什么感觉,过了一会儿,觉得浑身有些不自在,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周边有一些神情异常的人都在盯着我们看,我看了看弟弟的表情,他倒是若无其事。那是当然,他找到同类了呗。但是我怕弟弟被他们影响得更严重,想拉着弟弟离远一点儿,就听到护士叫到弟弟的名字了。
我赶紧说:“弟弟,轮到你了,我们进去看病吧。”弟弟一动不动,护士又喊了一声,弟弟还是不动。我着急了,但还是尽量和蔼地对弟弟说:“弟弟,你答应过我要听话的,我们就是来看病的,现在号也挂了,队也排了好半天,总算轮到你了,你不能——”弟弟打断了我,他忽然说话了,他口齿不清地说:“老鼠跳到钢琴上。”
护士没听懂,不明白弟弟是什么意思,只顾朝我看。她是精神病院的护士,见识肯定不少,但对于一只老鼠,恐怕也是无可奈何的。好在有我,她朝我看是对的,因为只有我知道我弟弟的语言,我一直以来就是弟弟的翻译,弟弟所说的“老鼠跳到钢琴上”是一个谜面歇后语,谜底就是乱弹(谈)。一翻译过来,我立刻就恍悟了,直拍脑袋骂自己笨,也顾不上让护士释疑,赶紧对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挂号的时候,把名字写错了。”护士说:“没事的,我先帮你改一下,你进去让医生在电脑上也改一下。”她把改过的病历交给我,弟弟果然不再反对,我顺利地带着弟弟进了门诊室。
这里的门诊室和其他医院不一样,病人只能一个一个地进,家属也只能进一个,不像其他医院,医生给一个病人看病的时候,许多病人和家属都盯在边上,赶也赶不走,门诊室里常常围得水泄不通,医生就在大家紧张的盯注下,在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中,在焦虑烦躁压抑的气氛里给人看病。
好在精神病院的情况不一样,这里是讲规矩的,又干净又安静。给我弟弟看病的这个医生年纪不大,但神色淡定,胸有成竹的样子。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好像弟弟的病一旦交到这个医生手里,弟弟就会从老鼠变回人来了。
听说有本事的医生是不用病人自己说话的,但是我从前没有见过有本事的医生,更何况我弟弟这个病人和一般的病人也不一样,不可能指望他会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医生。
所以,到了这儿,无论这位医生有没有本事,都得由我向医生倾诉弟弟的病情,我把不言不语的弟弟拱到前面,我站在弟弟身后说:“医生医生,你快帮他看看,他是一只老鼠。”医生的目光掠过弟弟的脸面,投到我的脸上,看了看我,问道:“你看病还是他看病?”我没有听出医生是在讽刺我,赶紧回答说:“医生,他看病,他是我弟弟。”医生抢白我说:“你刚才说他是一只老鼠,现在又说他是你弟弟,他到底是谁?”说实在话,那时候我见的世面太少,听不懂人话,仍然不知趣,继续向医生提供我弟弟的情况,我说:“医生,医生,你不了解我弟弟,这会儿你看他人模人样的,一会儿他就会变成老鼠的样子,很骇人的,手,会这么样,嘴,会这么样——”因为我做不像老鼠的样子,我怕医生看不懂,赶紧催我弟弟说,“弟弟,你做个老鼠的样子给医生看看,你快做呀。”
可弟弟是个病人,病人哪有那么听话的,你希望他是个人,他就偏做个老鼠给你看,让你烦死,等到你要让他做老鼠了,他又偏不做,人模人样地杵在你面前,又让你急死。
弟弟不肯扮演老鼠,我可真急了,我怕医生会以为我弟弟不是老鼠,我怕医生会误诊,急中生智又想了一个绝招,“喵喵”地叫了几声。
弟弟还没有来得及逃窜,医生一伸手就捏住了我的胳膊,朝门外喊:“护士,护士——”我以前见过的护士都是眉清目秀的姑娘,这会儿正心存歹念,不料进来两个腰圆膀粗的男人,他们一进来,就冲着我来了,我赶紧喊道:“不是我,不是我,是我弟弟,他才是老鼠——”可是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离奇的疑惑,我敏感地一回头,顿时魂飞魄散,哪里有我弟弟,刚才还在我身边的弟弟,忽然间就不见了。
男护士并不知道之前这屋子里还有个弟弟,他们朝我看了看,一个先说:“医生,我早就在门口准备着了。”另一个更是配合说:“一看他眼神就知道有问题。”医生被他们说得也有点儿疑惑了,问我:“你有病,你弟弟也有病,你们家族有精神疾病遗传吗?”那两个男护士未等医生的话音落下来,就上前准备掐我了。我吓坏了,紧紧闭上嘴巴,咬紧牙关,防止他们硬往我嘴里塞药,但是我还有话要说,我有许多话要说,我不得不说,我只能在喉咙里发出声音:“我不吃药,我弟弟是老鼠。”
没有人听到我喉咙里的声音,看这阵势,就算他们听见我的话,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只有一眨眼的工夫,那两个男护士已经掐住了我的脖子,反转了我的胳膊。我被冤枉了,我冤死了,我比窦娥还冤,我比什么什么还冤。
我继续抿紧嘴巴,在喉咙里狂喊:“我不是老鼠。”但是我有预感,我马上就会被他们打成老鼠了,果然,那个医生受了护士的蛊惑,准备开检查的单子了,他说:“先做个CT,看看脑部有没有病变情况。”
不过医生在开单子的时候,又疑惑起来,问我:“刚才你是和你弟弟一起进来的?这个病历上,到底是你的名字还是你弟弟的名字?”
他已经错得不能再错,我再也不能只在喉咙里说话了,我必须得张开嘴巴了,我张开了嘴巴放声说:“我弟弟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就是我弟弟的名字。”医生朝那两个架住我的男护士丢了个眼色,虽然他没有说话,但是我看得出他的意思,他已经再一次地认定我是病人,我急得辩解说:“不是的,不是的,医生,你听我解释,我弟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喊他的名字他是不会理睬的,喊他的名字等于没有喊,他只认我的名字,所以只能用我的名字代表我弟弟的名字。”
医生又看了我一眼,不再和我计较,开好了检查单子,对那两个男护士说:“陪他来的那个家属不见了,你们带他去CT室,小心一点儿,这个病人虽然看起来没有暴力倾向,但他的伪装性很强。”
天哪,我好好儿的,竟然要我去做CT。CT是什么,我还没见过,只是听人说过,是一种很昂贵的检查,一般都是得了重病才用的,我才不需要做CT,我也不能再被他们纠缠下去了,我不得不像疯子一样地拼命挣扎并且大喊大叫,我喊道:“你们什么医院,你们什么医生,你们什么护士,我明明没有病,你们要叫我做C——”一个“T”字被他们用手捂住了,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再喊的话,用胶布封嘴。”
天哪,要是再用胶布封住我的嘴,我还有活路吗?
万幸万幸,我还有活路,那是老天有眼,叫我命不该绝,关键时候有人救我了。
你们猜得没错,正是我弟弟。
我弟弟真是我的救命星,关键时刻他在桌子底下“吱吱”地叫了起来。
那两个男护士更觉离奇了,一个屋子里怎么会有两个病人,这医院没有这样的规矩,向来只允许病人一个一个地进来。两个男护士疑惑地互看了一眼,接着又看我,又看我弟弟,还看医生,我感觉出来,他们的怀疑不仅在我和我弟弟身上,甚至到了医生身上。
但医生毕竟是医生,他火眼金睛,他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看出来谁是病人了。医生弓身到桌子下面,把手伸向蜷缩在地上的弟弟,弟弟竟然乖乖地被医生牵了出来。
我看见了弟弟,一阵激动,又要上前说话,但是医生已经吸取了前面的教训,朝我摆了摆手说:“你别说话了,你再说话,一切又要搞乱了。”停一下,又补充一句,“对不起,刚才差点儿误会了,主要是你话太多,我这儿有许多病人的特点就是话多,所以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对不起。”我听了医生这话,没有马上回答,认真地想了想,我心里承认,我的话是多了一点儿,不过以前并没有人这么说我,家里也好,村里也好,学校也好,从来没有人嫌我话多,因为他们都不怎么说话,我多说点儿话,好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活着,至少知道自己的耳朵还没有聋。
现在医生提醒了我,我细细回想一下,才对自己和自己周边的环境渐渐有了一点儿新的认识和知觉。
其实我也知道,医生虽然用了两遍“对不起”,听起来很客气,但其实他很不耐烦我,想让我闭嘴。可是为了说清弟弟的情况,我还是不能根据医生的意图及时改正我的犯嫌,我依然强调说:“可是我如果不说,我弟弟是说不出来的,他平时就不肯说话,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或者应该说,他是一只沉默寡言的老鼠。”医生皱了皱眉头,但依然保持着风度,说:“好啊,沉默是金啊。”我没听懂医生这话是什么意思,想了想,我得继续说,我说:“所以医生,就算我弟弟不沉默,就算他肯说话,他也说不清楚,他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他不是什么。”医生终于被我惹恼了,再次改变了平和的神态,用尖利的目光剜了我一下,说:“你要是再说话,就请你出去。”
这一招把我吓着了。我不能出去,我不能把弟弟一个人扔在这里,虽然这里有医生有护士,但弟弟毕竟可能是一只老鼠,老鼠是无法和人沟通的,即使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医生,但医生也无法和老鼠对话呀。所以我不能有片刻让弟弟离开我的视线,我赶紧向医生保证:“医生,我不说话了,保证一言不发。”医生说:“本来这就不是你说话的地方,我来提问题,让他自己回答。”
那两个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的男护士这才退了出去,医生让弟弟坐下,亲切地拍了拍弟弟的手背,开始向弟弟提问,医生说:“你觉得自己是一只老鼠吗?”弟弟不理睬,我只能代他回答:“是,是老鼠——我弟弟是老鼠。”医生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继续问弟弟:“你的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弟弟仍然不回答,仍然由我回答:“从他是一只小老鼠的时候开始的。”
医生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又被他的目光吓了一下,以为他嫌我话多,要赶我走,不料医生只是叹了一口气,不仅没赶我走,还对我说:“病被你们耽误了。”我赶紧辩解说:“医生,不能怪我们,不是我们有意耽误的,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都以为他在跟我们闹着玩呢。医生,你仔细看看我弟弟的样子,他完全就是人的样子呀,谁会想到他会是一只老鼠呢,一直到后来,后来一直到——”这医生和我天生犯冲,不知冲的是生辰八字还是星座什么的,反正我看出来他特别不爱听我说话,刚才且容忍了我一下,这会儿他又犯毛躁了,严厉地说:“话多也是一种病,你知道吗?”我怕他又说我有病,赶紧闭嘴。
医生见我闭了嘴,还不甘心,又吓唬我说:“下面我还要提一些问题,让你弟弟回答,你要是插嘴,就是破坏我诊断,后果你自负。”
我不想自负,赶紧闭上嘴听医生向我弟弟提问题。
医生问:“现在是哪一年?”
这算什么问题,医生也太小瞧弟弟、太不把弟弟当回事了,弟弟虽然以为自己是老鼠,但他毕竟不是真的老鼠,我差点儿提出疑义,但是看到医生一脸的严肃,我也只能严肃地等待弟弟的回答。
可惜我这个弟弟实在是不争气,连今年是哪一年他都懒得回答,这样下去,医生岂不是要误认为弟弟的病非常严重吗,岂不是要误诊吗?我心里一急,对答如流地说:“今年是某某某某年。”我不仅回答正确,还加以说明,“今年为什么是某某某某年呢,因为去年是某某某某年,因为明年是某某某某年,所以,今年就是某某某某年。”
我说过了后,有点儿兴奋,折胳膊握拳,对着弟弟做了个鼓励加油的手势。可是弟弟麻木不仁,眼中根本就没有我,他把我当个屁。不对,屁还有点儿臭味呢,他没闻到臭味,他把我当空气。唉,弟弟啊,你真是麻木不仁,你哪怕认为我是错的,你哪怕朝我翻个白眼,哪怕朝我吐一口唾沫也好呀。
这医生也真是个知错不改的医生,他居然又问弟弟:“现在是几月份?”
我忍不住抗议说:“医生,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能查病吗?”
医生说:“我让你插嘴了吗?”他虽然批评了我,却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下一个问题,他没有再问今天是哪一天,而是改变了一个方向,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抢答说:“小王村。”
医生对我的回答充耳不闻,又随手把钢笔套子旋下来,放到弟弟面前:“这是什么?”
弟弟真是个睁眼瞎子,连面前的钢笔也看不见,还是我替他回答,但是我已经厌倦了医生的无聊,我回答说:“这是钥匙圈。”
我原以为医生会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来为难弟弟,这样才能查出弟弟和我们不一样,哪知这医生如此没有水平,我得刺激他一下,让他提一些有难度的问题,所以我有意将钢笔套说成钥匙圈。
可医生不吃我这一套,他和我弟弟一样,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只当我不存在。不过我并没有计较他,因为他对我弟弟的态度很好,和对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我会原谅他的。
医生把我和我的回答撇在一边,十分和蔼地对我弟弟说:“既然你不肯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就换个方式,你不愿意说话,你就不说话,你闭着嘴都行,我提问题,我自己给答案,如果你认为是对的,你就点头,如果你认为是错的,你就摇头,好不好?”
不等弟弟表态,医生就自说自话地开始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的硬币,举到弟弟眼前,问道:“这是一个硬币,是几块钱?”然后他自答说,“是两块钱。”
我忍不住“嘻”一下笑出声来,看到医生眼睛朝我瞪着,我赶紧收回笑声,去提醒弟弟:“弟弟,这明明是一块钱,他说两块钱,你摇头呀,你快摇头呀。”见弟弟不理睬我,我又赶紧告诉医生,“医生,他是有意的,他有意不告诉你,让你无法了解他的真相,其实他认得钱,就算他什么也不认得,他也认得钱,有一次,我让他到小店里去买——”
医生真生气了,我看得出来,他的脸涨成了紫红色,龇着牙说:“脑残啊?听不懂人话啊?”
我再次被吓到了,我以为医生误诊了,我赶紧解释说:“医生,医生,我弟弟可能是脑残,但是脑残不等于他很笨,你千万不能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你不知道我弟弟有多聪明呢,我弟弟还会、还会——”
医生冷冷地打断了我,他替我说道:“还会掘壁洞呢吧?”
我和医生这里,已经闹翻了天,我弟弟呢,真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在这么专业的医院里,弟弟竟然如此这般的木呆,太丢人了,他简直、简直连一只老鼠都不如了。一只老鼠,你要是踢它一脚,它一定会逃跑;可我这个弟弟,这会儿,在医生面前,简直丢死人了,别说踢他一脚,就是拿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他恐怕也是岿然不动的。
我也生气了,我气得推了弟弟一下,说:“弟弟,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你明明会说人话的,今天到了这里,你连一个字也不肯说,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呢,还是存心跟医生过不去?你是觉得车票钱、挂号看病的钱都不是钱呢,还是觉得应该让我白白地陪你跑一趟?你是觉得这个医院配不上你这样的病人呢,还是觉得——”我说着说着,话又多了,又扯开去了。医生是不会让我再继续下去的,他朝我摆摆手,让我住嘴,可是我不能住嘴,我说:“医生,你听我说,他平时确实不是这样的,他平时不扮老鼠的时候,和人是一样的。”医生说:“你以为我现在在干什么呢,我是在玩吗?”我说:“你不是在玩,你是在给我弟弟查病呢。”医生抢白我说:“原来你知道啊,你知道还不闭嘴。”我说:“医生,我得给我弟弟当代理人,否则——”医生说:“你怎么老是要代表病人?要不,干脆,你来当病人算了。”我又赶紧解释:“医生医生,我是怕、怕你不了解我弟弟。”医生又冷笑说:“我不了解,你了解?那我这医生让给你当算了。”
我再一次败下阵来,但说实在的,我仍然不死心。求医生不成,我转而求弟弟了,我说:“弟弟,弟弟,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开口说说话吧,哪怕说一句话,哪怕说一个字,哪怕骂我一声,要不然,要不然,医生会以为你是哑巴,而不会把你当成老鼠。弟弟,你自己拿个镜子照照看,你这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一只老鼠呀,你要是想让大家知道你是一只老鼠,你好歹得扮点儿老鼠的样子出来呀。”
我已口干舌燥,像一条上错岸的鱼,弟弟却依然稳坐钓鱼船,我看着弟弟淡定的姿态,又想想我自己上蹿下跳的样子,一时间,我竟疑惑起来,到底是我带弟弟来看病,还是弟弟带我来看病?我这么想着,简直就昏了头,我觉得我的思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乱闯,就要失控了。
思想失控,那是什么,那可不得了,那就是疯子啊,难不成我带出来一个精神病,要带回去两个精神病吗?
我可不能疯啊,我家里有一个弟弟是个疯子,就已经够全家人受的,我要是再疯了,让我们家的人怎么活呀。可是我怎么才能保持冷静,不让自己疯呢,我心里很清楚,只要医生能够给弟弟诊断,然后治疗,我就不会疯;那么,怎么才能让医生给弟弟诊断和治疗呢,现在医生面对一个哑巴精神病,束手无策了。那么,首先,至少,我得让弟弟开口说话。
我换一招,以情动人,我对弟弟说:“弟弟,我知道你最喜欢我喊你弟弟,你也知道咱们家就咱哥俩最亲,这样好不好,我喊你一声弟弟,你就说一句话,好不好,弟弟,弟弟,弟弟——”可我弟弟喊得再亲,仍然不奏效,我急火攻心,忽然心里就被这火照亮了,我脱口说:“弟弟,我不叫你弟弟了,我叫你、叫你一声王全!”
我这完全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哪知一匹死马还真被医活了,这“王全”两字一出来,弟弟竟然开口了,弟弟欢快地说:“老鼠老鼠,爬进香炉——”
听到弟弟说话了,那垂头丧气的医生顿时来了精神,赶紧凑到弟弟跟前说:“你现在肯说话了,我们重新开始,我问问题,你回答——”
弟弟说:“老鼠老鼠,爬进香炉——”
医生对精神病人有研究,但是对老鼠没有研究,他不知道老鼠爬进香炉会是什么,我只得替弟弟做翻译说:“这是一个谜面歇后语,老鼠爬香炉,谜底就是碰一鼻子灰。”我一边解释,一边观察医生的脸色,看了医生的脸色,我的心顿时一冷,才知道,最后是我碰了一鼻子灰,完蛋了。
医生果然不再发一言,拿过一张空白的方子,低头就填写起来,我急得问道:“医生,你这是干什么?”医生说:“开药呀,你到药房配了药,回去按说明给他吃药。”
说罢医生就把病历和药方交到我手里,朝我挥了挥手,说:“好了。”又朝门外喊:“下一个,35号。”我捏着弟弟的病历,觉得这结果来得太快了,前面我和医生两个人,忙了大半天,铺垫了那么多,不就是为了让弟弟配合诊断嘛,可是弟弟还没开始配合呢,结果就已经出来了。这算什么呢,这算雷声大雨点小,还是算虎头蛇尾,或者,这就是精神病院的医生和别的医生的不同之处?我十分不理解,向医生提出疑问:“医生,这就好了?”医生说:“好了呀,走吧。”我没有理由不走,但是我努力地想了想,终于想出理由来了,我说:“医生,为什么我明明没有病,你刚才却让我去做CT,我弟弟明明有病,你却不让他去做CT?”医生说:“这就是你和他的不一样嘛。”我没听出医生是在嘲笑我,我放心不下弟弟的病情,又说:“医生,不做CT你就能看到我弟弟的脑子吗?”医生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说:“我这是人眼,不是X光。”他这样一说,我更加不安了,我试探着说:“医生,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不给我弟弟做CT,你也能治我弟弟的病?”医生没精打采地看了我一眼,心灰意懒地对我说:“我说过我能治他的病吗?”
医生这话我又听不懂了,这时候,35号病人和家属已经在门口探望了,医生见我仍然傻站着,他忍耐住自己的不耐烦,又跟我说:“我的眼睛虽然不及X光和CT,但是,我有我的经验和我的检查方法。”我犹豫地说:“那,那就是说,你刚才问我弟弟的那些问题,就算是检查了?”医生说:“你没见过吧。”我心想,我不仅没见过,我还真不敢相信,这样就算是诊断过了?江湖郎中看病还比这要复杂一点儿呢,至少还要看个舌苔把个脉吧。但我不敢直接这么说出来,我仍然以疑问的方式和探讨的口气说道:“医生,你刚才的检查方式,不像医生,倒像是老师。”医生没听懂,说:“你什么意思?”我说:“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提问,而且,问题比你提得还多。”医生说:“怎么,你还嫌我问少了,你有钱吗?”他突然从提问说到了钱,让我猝不及防,我愣了一下,没有能够马上回答。
关于钱的事情,我得交代一下,我不能绝对地说我有钱,也不能绝对地说我没钱。其实,钱我家是积攒了一点儿的,但这个钱是不能动的,那是要派大用场的。所谓的大用场,你们一定能够想到,那是我准备娶老婆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能说我有钱,因为如果我娶老婆,我的钱就全部用掉了,我就没有钱了。
更何况,这多年积攒下来的钱,并不在我手里,始终由我爹紧紧捏着,我做梦都别想把那钱从我爹手里夺过来给弟弟看病。
再坦白一点儿说,我也不想把对弟弟的恶劣态度推到我爹一个人头上,即使这钱捏在我手里,我又会拿出来给弟弟治病吗?
所以,我和我爹是一样的货色,我弟弟不能指望我们。
当然,我应该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我先把娶老婆的钱拿出来给弟弟治病,等弟弟病好了,我再重新攒钱娶老婆。但这个办法是无法实施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对象能不能等得及我再一次地攒钱;我也不能去征求她的意见,因为一征求意见,我就得把事情和盘托出,她就会知道我弟弟的真实情况;她一旦知道我弟弟的真实情况,她就会——她就会怎么样,我现在似乎是无法预测的,但我在娶老婆的问题上,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我必定是朝不好的方面去想事情的。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险,所以,我其实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我的思想走得远了一点儿,一时没有收回来,医生看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又给我补充说明:“你要是有钱,去交住院费,让你弟弟住院治疗,我就会向他提更多的问题,我会天天向他提问题,我会比老师还老师,到时候,你就不会嫌我问得少了。”我结婚用的钱是不能给弟弟治病用的,所以我赶紧说:“我没有钱,我家也没有钱。”
这一下,医生乘机把话说到底了,医生说:“没有钱,你就把他带回去吧,他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好在他只是一只老鼠。”
医生的话并不完全正确,“好在他只是一只老鼠”,这叫什么话,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他还说“好在”?他难道不知道,一只老鼠也会祸害人、会给人带来晦气的。
果然的,我们还没出医院的大门,晦气就来了,我们迎面看到一个人,算是熟人,但又不太熟,他和我们村上的王图是亲戚,他常到王图家来做客,在小王村我们碰见过;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是王图的亲戚,他还和我对象赖月是同一个村的,我到赖月家去的时候,也见过他几次,这样等于是两个小半熟,加起来可以算大半个熟人了,这会儿我理应热情地上前打招呼,可是,可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地方啊,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我能让他看见我吗?
我假装不认得他,一脸漠然,两眼发直地拉着弟弟从他身边走过。他好像也没有注意到我们,他的目光只是在我脸上打了半个圈,就滑过去了。我心中暗喜,不料还没喜出来,就听到身后“哎哟”一声尖叫,我一回头,他冲我笑着说:“都说我眼尖,我的眼就是尖哎,你没有认出我,我倒一下子就把你认出来了。”他一边说,一边高兴地上前和我握手。我可以抵赖,我有的是办法,比如我可以说:“你认错人了。”或者我可以说,“以后再聊吧,我们赶时间坐车呢。”很明显后面这一招比前面这一招更智慧,既不承认认得,又不说不认得,让他没个准。可是,还没等我把办法使出来,他已经抢在我前面和我攀亲了:“哎,你是,你是那个谁,是王图那儿的吧。”他也太抬举王图了,王图虽然是小王村人,但不等于小王村就是王图的,他这么说,显得王图很牛,好像小王村就是王图的,比村长还牛,比我爹还牛。我加强语气纠正他说:“我是小王村的。”他听不出我的意思,高兴地说:“我说的吧,我记性好吧,你就是王图那儿的。”然后他又想到了更重要的事情,兴奋地说,“对了,你同我们村的赖月是谈对象的吧,你们谁来看病啊?”
我顿时魂飞魄散,关于我弟弟的病,我从来没敢告诉我对象。我不敢告诉我对象,并不证明我对象有多么的不好,也不能证明我对象知道我有个精神病的弟弟就会和我分手。但是,反过来说,我也同样不能保证她不会那么做。我可不敢下这个赌,冒这个险,这个赌注太大了,这个风险太强了,一想起来我的心肝尖儿都发颤。
现在麻烦大了,险已经逼到我面前了,险把我抵到了墙角,我无处可退了,但我即使无处可退,我也不能告诉他我带我弟弟来看病呀。
可是,此时此刻,我们身边,除了我弟弟就剩我了,我无路可走,只能挺身而出,把事情扛起来,我说:“是我,是我来看病。”
话一出口,我才知道我犯了更大的错误。你们替我想想,我弟弟有病我都不敢说,我对象要是知道我有病,我对象不是立马就成了我前对象了吗?我顿时惊吓得浑身直冒冷汗,正着急着怎么跟他解释,怎么把谎言重新圆过来,不料那人却哈哈大笑起来,说:“你果真爱开玩笑,我倒是听赖月说过,你是个幽默的人,以前不怎么了解,今天才知道哈。”我犯了蒙,傻傻地问道:“你知道什么呀?”他说:“你自己瞧瞧自己,你像有病的样子吗?”
我惊心动魄地逃过一关,赶紧把话题从我和我弟弟身上扯开,扯到他那儿去,我反问说:“你呢,谁看病呢?”他又奇怪地反问我:“咦,你不知道吗?你自己村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吗?”我真不知道,我们小王村除了我弟弟是老鼠,难道还有别人是老鼠吗?他见我真的犯糊涂,也不再难为我、不再让我猜谜了,说:“就是我表哥王图呀,王图得了病你真不知道啊?”又说,“他在这里住院,我是特意来看他的。”
这事情真是太出人意料了。
王图竟然会和我弟弟一样,打死我我也不敢相信。这王图可是我们小王村数风流的人物,除了前村长能够和他PK一下,别的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虽然许多年来,我并不关心村上的事情,但是我爹关心呀,王图的事情,我就是从我爹那里听来的。
几年前,王图承包了村里一排废弃的厂房,他拿来养鸡,鸡生蛋,蛋又生鸡,没完没了,正数钱数到手抽筋呢,村长又想重新办厂了,要收回。王图哪是这么好说话的,乘机敲竹杠,狮子大开口,怎么谈也谈不拢,双方的底线离得太远太远,像隔着太平洋那么远呢。村长急了,翻找出当年的协议,仔细一看,发现有机可乘,那协议漏洞百出,根本就是胡乱一写,完全不合法,不受法律保护。可村长懂法呀,他太懂法了,赶紧告上法庭,结果判了王图败诉,厂房被无偿收回。
王图如此人物,照样被迫害成精神病人,他比我弟弟冤多了,我弟弟反正天生就这样,可王图本来好好的一个人,不仅是好好的一个人,还是一个人物,一个人才,一个人精。
真是太冤了。
我们还没聊完王图的事情,忽然就看到王图从住院部那边出来了,神清气爽,哪里像有病的样子。他那亲戚愣了一愣,先是奇怪,后又紧张起来,说:“表哥,你怎么逃出来了?”王图觍着脸上前就冲我过来,一下将我搂抱住,嘴上说:“抱抱,抱抱——”我吓得直往后躲,一边尖叫起来:“逃出来了,逃出来了!”王图说:“王全,我不是逃出来的,我出院了。”那表弟更是奇道:“你不是昨天才住院的吗?”王图说:“那只是一个程序而已,经过这些程序,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就可以出院了。”
他说话时,我在一边注意观察他,我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病,但我又想,有病的人也不一定个个都会表现出来,即使是我弟弟,病得这么重,不犯病的时候,也是一个英俊青年呢。
王图又和我套近乎说:“你们看过病了啊?”他没有明确说出是我带我弟弟来看,还是我弟弟带我来看病,他只是说“你们”,比较含糊。我心里蛮感激他的,至少他的那个亲戚,听了“你们”,不能一下子就判断我和我弟弟的情况,他总不可能以为我和我弟弟都有病吧。
我得回报他,拍他马屁说:“王图,你肯定是误诊吧,你不可能得精神病的。”王图笑道:“还真不是误诊,我真得病了,是被气出来的,精神抑郁症,村里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我仔细辨别了他的神态,又重新想了想,既然这个王图和村里有仇,他会不会为了对付村里,假装生病了,以病来要挟村长。
但再转而一想,似乎也不大符合,如果是这样,他看到我,必定会装出有病的样子,而不会这么笑逐颜开。我疑惑着说:“王图,你是装的吧?”话一出口,我还担心王图会不会生我的气,不料他仍然笑呵呵地说:“你看出来了啊,我就是装的呀,我本来是想装其他病的,但是其他病都有仪器可以检查,查得出真假,只有精神上的病,才查不出真假。”我还没反对,那表弟倒不服了,说:“表哥,你说得不对,精神病也一样,能够查出来的,到精神病院看病,就是查病治病的嘛。”王图笑道:“你以为啊。”那表弟十分疑惑说:“表哥,莫不是你真的病了?没听说有人愿意自己给自己戴一顶精神病的帽子呀。”王图说:“我就愿意。”他见我们都不能理解他的胸怀,又强调说,“他给我苦头吃,我也要回敬他一下,让他吃苦头。”
他谈笑风生地说自己有病,又谈笑风生说装病是为报复别人,他的话该不该相信呢?我肯定丢不开对他的怀疑,我说:“王图,既然你没有疯,你‘抱抱’干什么?像个花痴似的。”王图笑道:“拿你练练兵呗,等到了村长面前,我得抱抱他呀,男人抱抱男人,多恶心呀,我得先试着适应哈。”
我不想和王图谈论恶心的问题,我想得更深更远,我试探他说:“王图,你把你的险恶用心直接向我坦白了,你不怕我去告诉村长?”王图才不怕,他从口袋里摸出了病历和医生证明,朝我扬了扬,说:“我有医生的证明,证明我是病人,有医院的公章,这就是铁证,这就是法,到哪里他都不能否认的。不像王长官个狗日的,当初和我签的承包协议,居然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我算了算日子,王图承包土地那时,王长官已经不当村长了,并不是发生在他任上的事情,我说:“那时候王长官似乎已经是前村长,怎么可能代表村里跟你签承包合同呢?”王图说:“前村长?个狗日的从来就没有‘前’过,也不会有‘后’,他当村长也是他,他不当村长也是他,小王村什么事情不是他一锤定音,只不过有时候在当面,有时候在背后而已。”
我觉得王图这话颇有道理,我们的前村长就是这样一个灵魂人物,无论他当什么或不当什么,他都是我们的村长。
王图和前村长王长官,两个人都是人物。现在这两个人物就要发生事情了,跟我无关,我看戏而已。
我甚至连戏都不想看,我只想让我弟弟能从一只老鼠变回一个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