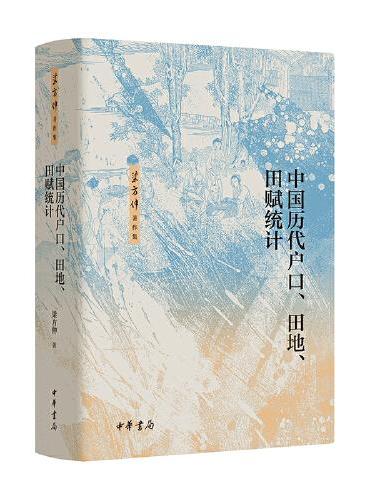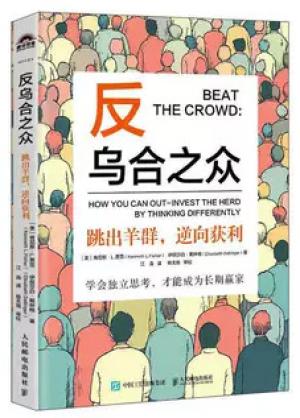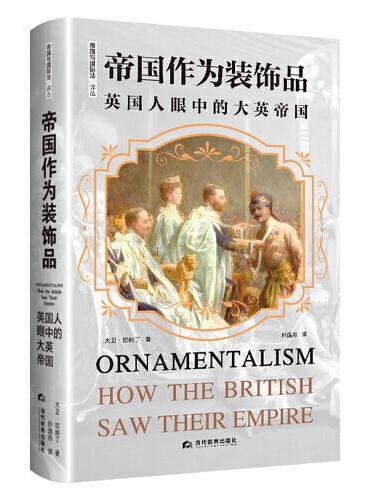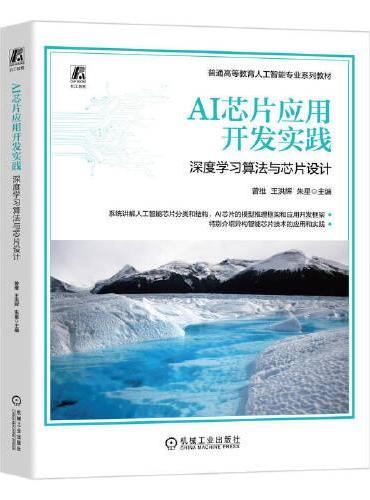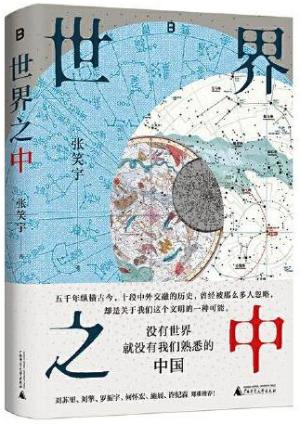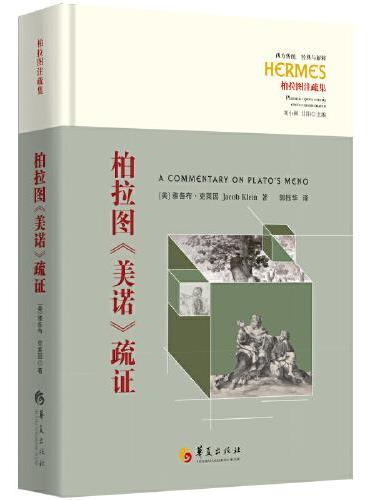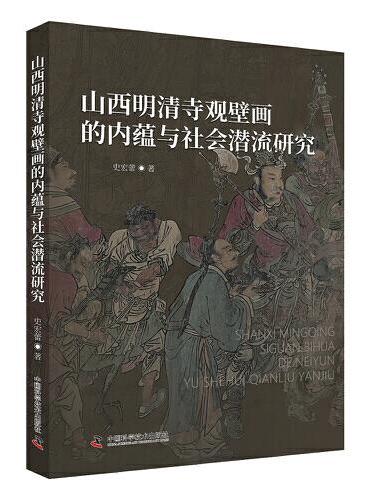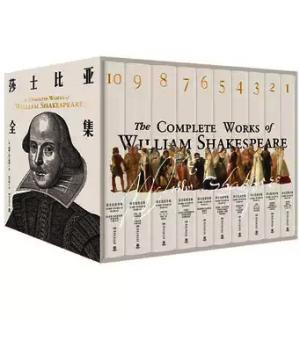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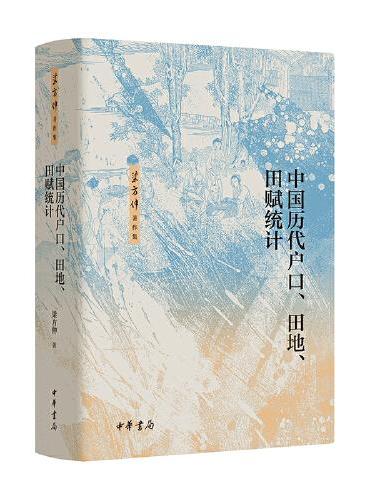
《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6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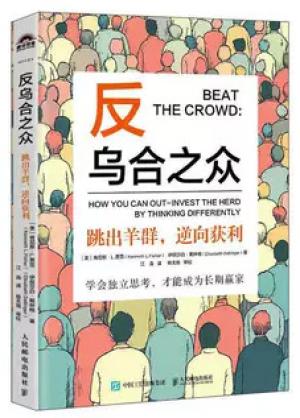
《
反乌合之众——跳出羊群,逆向获利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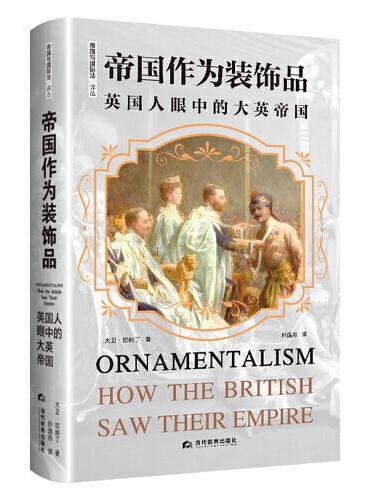
《
帝国作为装饰品:英国人眼中的大英帝国(帝国与国际法译丛)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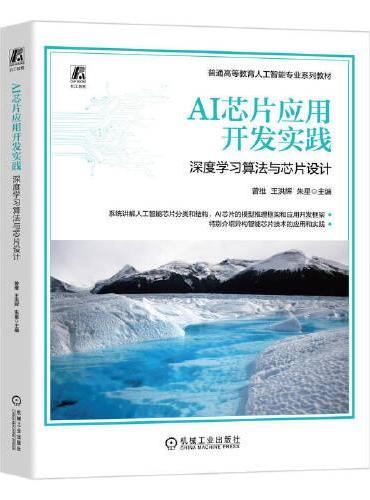
《
AI芯片应用开发实践:深度学习算法与芯片设计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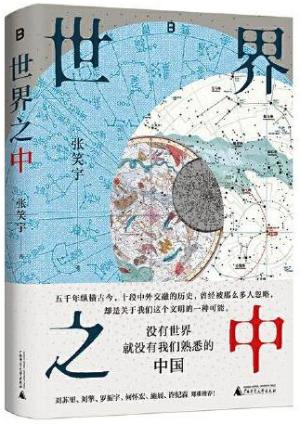
《
世界之中(文明三部曲之后,亚洲图书奖得主张笑宇充满想象力的重磅新作)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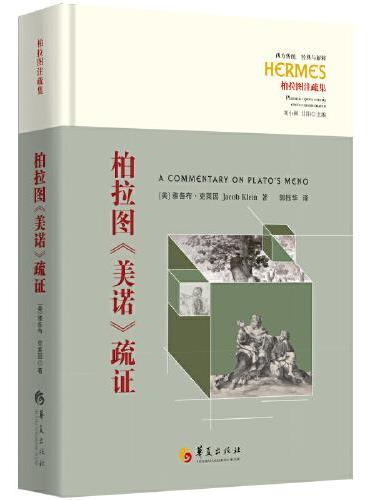
《
柏拉图《美诺》疏证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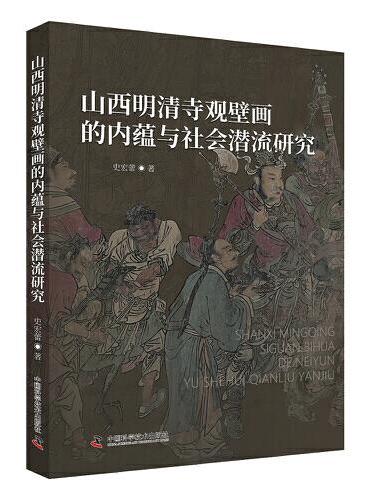
《
山西明清寺观壁画的内蕴与社会潜流研究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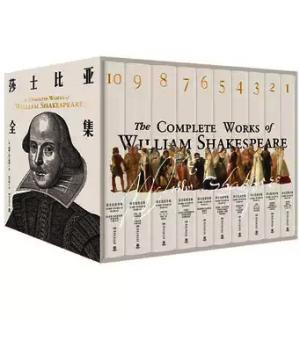
《
莎士比亚全集十卷
》
售價:NT$
2744.0
|
| 編輯推薦: |
★把握基层脉动,寻求善治善为。从“管治”到“法治”,实现基层善治。
★“政经分离”如何破题?集体经济如何转型改制?草根经济活力如何释放?村居自治重重矛盾如何化解?聚焦中国基层治理热点,深度解读村治改革密码。
★ 郑永年、刘守英、邓伟根推荐。
|
| 內容簡介: |
本书以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考察背景,以南海为样本,研究珠三角的基层善治路径,对南海“政经分离”、集体经济转型改制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作者以新闻从业者的敏锐触觉和反思精神,通过一系列娓娓动听的小故事,引导读者在感受故事的同时,跳出故事本身去思考珠三角的改革全景。希望南海在村居治理方面的思考与探索,为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基层管理与创新提供参考与启迪。
本书不同于市场其他关于基层治理的政经图书,它以讲故事的独特方式介绍广东南海的村治变化,比如,出嫁女想“回家”、城里人“哭着喊着”要到农村去、邓Sir跑了224个村等等,让政经图书不再乏味枯燥。
|
| 關於作者: |
舒泰峰
出生于东南,问学于西北。历任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笔、时政部主任,《财经》资深记者,《东方周报》副总编辑。兼任《新京报》特约评论员,东方网专栏作者。著有政经畅销书《十问中国梦》《中国大趋势3:中国拒绝捧杀》。
尹冀鲲
《南方都市报》记者,曾长期观察南海顺德两地基层改革。
黎诚
南方日报社珠三角新闻部编辑,基层政经观察者。
|
| 目錄:
|
邓伟根序:以基层善治促国家治理现代化
刘守英序:乡村治理是一道绕不过的坎
自序:村居自治,拓宽了社会改革的纬度
第一章 南海瓶颈:基层治理遭遇“死结”
夏西村往事
争抢“红苹果”
出嫁女想“回家”
城里人“哭着喊着”要到农村去
流动人口的“他乡之壑”
新乡土社会:城非城,乡非乡
“希腊村”隐忧
异化的村居自治
第二章 捍卫基层:“政经分离”解扣
邓Sir跑了224个村
村改居“二次革命”
政经分离拉开大幕
社区合并为哪般
消失的村民小组
胡春华:政经分离探索精神可贵
汪洋:还是应该政经分离
第三章 协同共治,多元治理:重构社会纽带
基层自治的新加坡经验
村居自治:社会治理有了脚
政府放权社会:新的社会秩序形成
都分离了,党干什么
第四章 再饮头啖汤:释放集体经济活力
集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南海实验
集体之困
市场化改造
股权固化故事
让股份流转起来
北京郑各庄启示
第五章 网络倒逼行政
“影响稳定的一是基层,一是网络”
“樵山潮人”和南海微博群
透明村务,纷争减少
把权力关到网络的笼子里
第六章 南海思辨
重构基层秩序:以多元对多元
三重确权:厘定权力边界
基层治理“新四化”
治以自治,断以法尊
别论:善治保障
后记
|
| 內容試閱:
|
出嫁女想“回家”
陈妹(化名)是大沥镇六联村怡兴第一股份经济合作社(下称怡兴经济社)土生土长的村民。
1985年,六联村完成股份制改造,农民洗脚上田。1987年,经人介绍,她嫁给了盐步居民黄生,但户口留在村中,成为一名出嫁女。
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在陈妹婚后的头两年,村里还给她分红,大约一年几百元。此后,村小组有关负责人通知她:“你是出嫁女,以后就没分红了。”
陈妹仅有小学文化,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在田里干活。村里完成股份制改造后,无田可耕,只好外出四处打工,曾在玩具厂煮饭,也在水泥厂做过杂工。说起现在的职业,陈妹很不好意思:“现在当走鬼,卖些小东西,饰品啊、衣服啊,什么都卖过。”
2009年的时候,陈妹月收入约600~700元,她觉得生活动荡不安,毫无保障,“小儿子还这么小,我们都到了快打不动工的年纪了”。
怡兴经济社所在地毗邻黄岐黄海路,交通四通八达,物业甚多,出租收入也较可观。村里分红多的人家,一年甚至可拿到5万元。村里过“三八”妇女节,女的发400元,男的发300元,出嫁女却一分钱都没有。
出嫁女希望分红,但是经济社成员反对给他们分红,原因很简单,分的人多了,红利必然摊薄。他们更担心一旦出嫁女进来,那么其子女生生不息,如果都来要求分红,那么红利势必将更为薄弱。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种传统的思想观念则进一步阻碍了外嫁女获得分红。
为争取村内分红权益,陈妹从1988年就开始上访,最远去过北京。“村、镇、市、省,每一级政府都去过了。”走鬼和上访,成为她生活的常态。
怡兴经济社内,像陈妹这样的外嫁女和子女共有11人。怡兴经济社是六联社区(原六联村)的11个经济社之一,六联社区最早有400多个外嫁女。
六联社区党委书记叶聘娥是个40多岁的干练女性,对外嫁女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她说,在计划经济年代,一个生产队如果是100人,意味着这块地产出来的粮食,交了公粮和余粮之后,要分给100人。当时粮食紧张,每个人一年只能分到几十斤。不论人口增减,土地的面积是固定的。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自然越来越紧张。
六联毗邻广州,村里的女性迫于生计,开始去广州做工,或者嫁出去。嫁出去后,村里便不用再给她分粮食。但是按照当时的户口政策,外嫁女的户口不能迁出,仍留在原村。
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双方相安无事。但后来改革开放春风一吹,饥饿很快成为过去时。村里开始搞征地,搞产业,外嫁女看到了福利分红等实际好处,便开始要求同等待遇。村民不同意,外嫁女便说,“我的户口在这里”。
叶聘娥回忆,吵得很厉害的时候是1995年,当时南海区、黄岐镇还有村成立了三级联合工作组,由区副书记领衔,专门解决六联外嫁女问题。工作组召集每个经济社开会,要求配股给外嫁女,村民以各种理由反对。争执不下,只好投票,结果仍是不配。
这样的结果显然不能解决问题,在区里支持下,六联对外嫁女采取了一次性经济补偿。村里卖了一部分土地,政府出了150万元,加起来1000多万元,400多个外嫁女每人分得22270元。当时的两万多不是一个小数字,同期南海城中心地带的一栋商品房才四五万元。
叶聘娥的前任李棠佳正是当年补偿方案的参与制定者和执行者,60多岁的李棠佳是南海“老牌”的村支书,区委书记也有时向他问计。1995年,他刚担任村支书不久,新官上任就遇到了外嫁女难题。他的理念是“一炮打准,重手一点”,大不了村委会穷几年。他的想法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于是有了1000万元的补偿方案。这种做法也是全国第一例。
李棠佳说,彭妹的情况与别人不同,她当年没有要补偿,村里给了她分红。她并不是为自己争,而是为女儿挣分红。这样的例子目前六联只有四五例。
六联花钱买平安的方式并不是南海区的常态,普遍性问题还得区里统一化解。2008年,南海区出台《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的文件。要求实行“五同”,即“同籍、同权、同龄、同股、同利”,也就是说,户籍性质相同的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相同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年龄相同的股东享有同等数量股数和股份分红。
根据这份文件,2009年3月2日,大沥镇政府对怡兴经济的纠纷做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上述“出嫁女”及子女具有该经济社成员身份,并无偿享有相应股权权益;此外,还要求怡兴经济社在收到决定书10日内发给上述人员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
收到行政处理决定书后,怡兴经济社没有选择服从,而是提出行政复议,但南海区政府维持了大沥镇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书。
怡兴经济社认为大沥镇政府这一处理满足了少数人利益而损害了绝大多数村民的合法权益,引发了更大的不稳定因素。一怒之下,一纸诉状将大沥镇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法院撤销大沥镇政府做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成为国内首宗农村经济合作社关于“外嫁女”权益纠纷起诉镇政府的案件。
当年11月6日,南海区法院对此案做出了判决。维持大沥镇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
陈妹她们虽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但是在刚性的利益面前,执行成为另一场“战争”。
2009年1月,南海区首次启动法律程序,由区人民法院对大沥镇横江村江心南村民小组进行强制执行分红,落实了8名“出嫁女”的合法权益,此举是南海首次动用司法手段打“出嫁女攻坚战”的开始。同年6月,大沥镇沥西村风雅经济社2名负责人分别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及妨害执行,被区人民法院实施司法拘留15天。
“行政引导为主,司法强制为辅”的办法解决了大部分出嫁女的问题。截至2010年12月,全区共1766个经济社中的1756个,19534名“出嫁女”及其子女中的19395名的股权得到落实,落实率达到99.3%。而在1756个已落实股权的经济社中,有1572个兑现了“出嫁女”及其子女的分红,兑现率89.5%。
但是,出嫁女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一些经济体在落实股权后又出现反弹,拒绝签发出嫁女及其子女的股权证。
事实上,即使成为股东,其权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同样是问题。大沥镇沥西村风雅经济社一位年轻的“出嫁女”母亲反复讲述她孩子的遭遇:她的孩子通过出资购股成为集体经济成员,但是在公示的文件中,别人的名字都是铅印,而她的孩子和其他几个“出嫁女”的孩子,却是用笔添上去的。
更为关键的是,她的孩子在村办幼儿园享受的是“二等股东”的身份,其他村民的孩子可以在幼儿园吃午饭,她的孩子却不可以。孩子问她:“妈妈,为什么我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呢?”这让这位母亲愤愤不平,“我们也是村里人,我们一直生活在这里,也作了贡献,为什么我的小孩就要被别人看不起呢?”“在幼儿园里就有被孤立的感觉了,这以后怎么办呢?”
矛盾仍在延续。2011年,西樵、百西、大同、朝山等村的出嫁女仍不断上访要求政府落实政策。更为复杂的是,反对出嫁女及其子女享受股份分红的村民也开始上访。
出嫁女问题的难解在于它触及了发达地区农村最深层次的困境——农村集体成员权及其权利边界的确定。
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自身处于多重模糊状态。首先是主体定位不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最大尴尬是法律地位不明确,国家并没有针对集体经济进行立法,这使得集体经济的资产很难明晰地加以确认。在南海区,股权证只是用来对身份进行说明,但没有严格的法律加以保护,这直接影响到出嫁女等有资格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员的权利。
其次,集体经济组织产权不分明。一般而言,农村集体资产由农民集体所有,但是“农民”这一概念所指的内涵并不明确,它会变动,产权也随之发生变动。产权不清晰,就无法建立合理有效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拥有哪些条件可以成为集体经济成员,退出需要哪些程序,如何补偿,都没有明确的规则。
此外,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职权同样不清晰。在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制改造之后,其管理仍沿用“村务+经济”的传统模式,也就是由小组长或村支两委兼任经济组织的管理者,村支两委大权在握,村务、经济两手抓。这种模式的好处是高效快捷,但风险也显而易见——村务和经济只要一方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村庄的瘫痪。出嫁女问题,本应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化解,却往往演化为整个村庄的矛盾,这也导致问题的扩大化。
事实上,在集体经济的圈外,除了出嫁女这个老大难问题,一共有13类人要求进入,其余的有知青、军人、大学生等。
这13类人加起来一共有3万人,他们天天上访,分裂了农村,使农村变成了“熟人的陌生社会”,造成基层不稳。如何破解?这是中国农村先发地区遭遇的前沿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