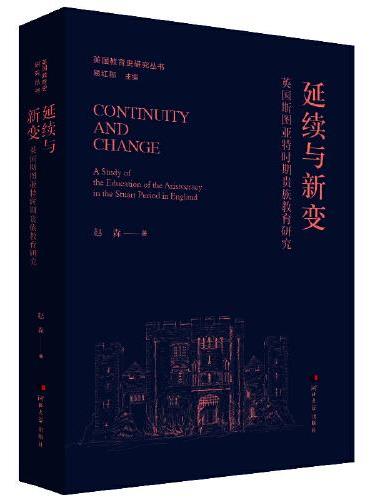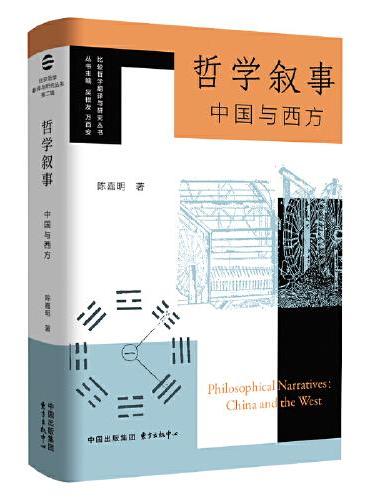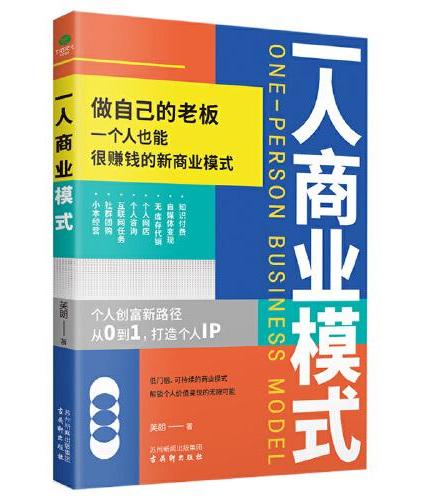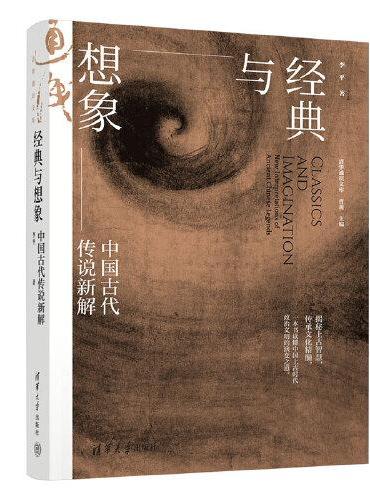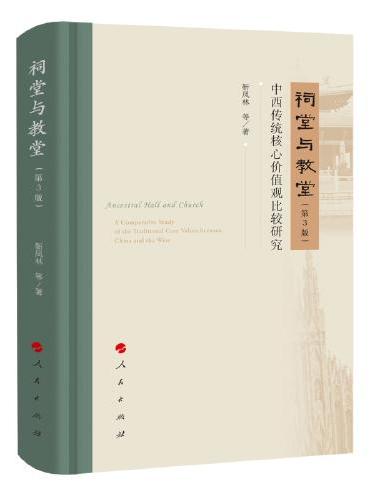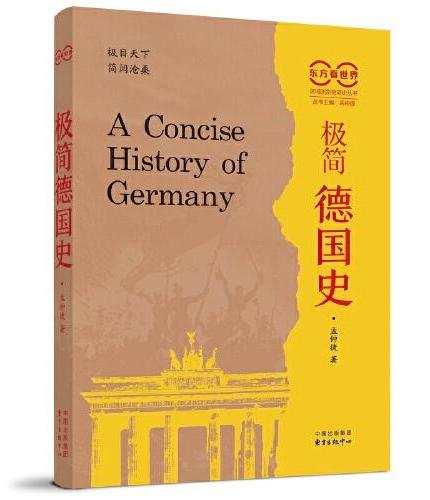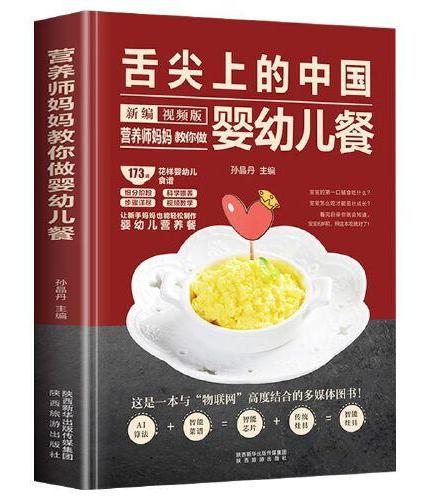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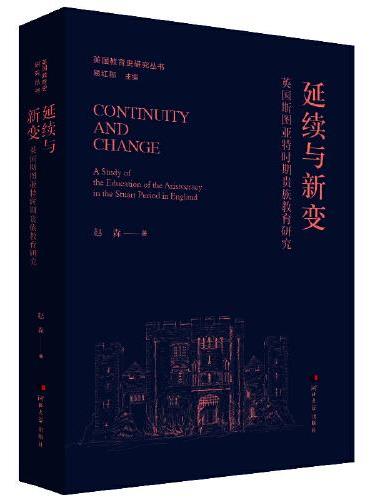
《
英国教育史研究丛书——延续与新变:英国斯图亚特时期贵族教育研究
》
售價:NT$
505.0

《
更易上手!钢琴弹唱经典老歌(五线谱版)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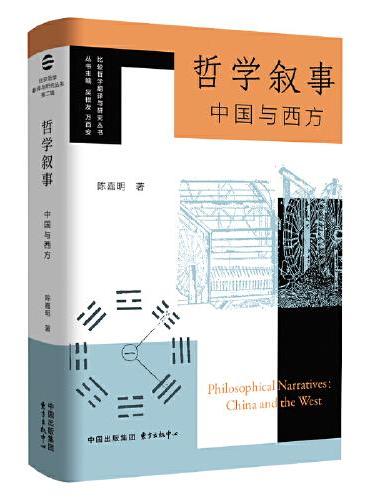
《
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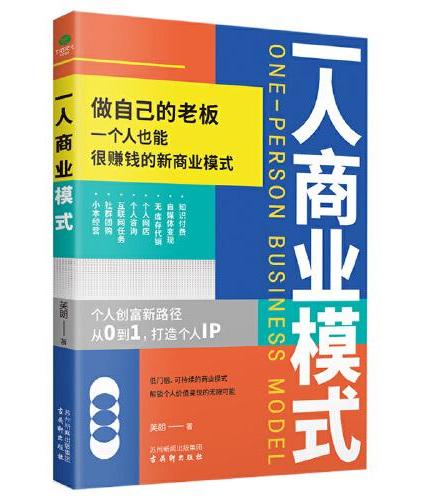
《
一人商业模式 创富新路径个人经济自由创业变现方法书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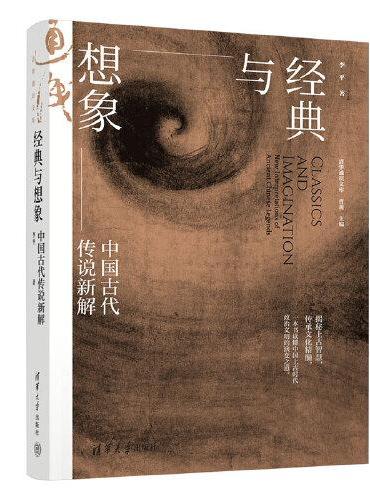
《
经典与想象:中国古代传说新解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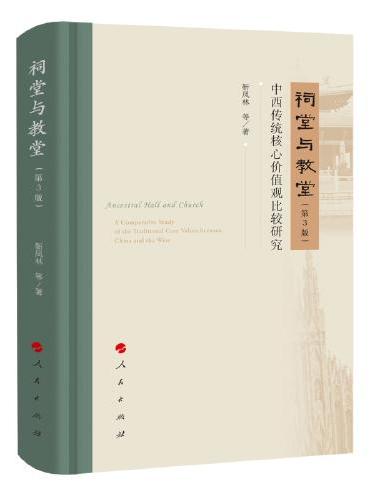
《
祠堂与教堂:中西传统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第3版)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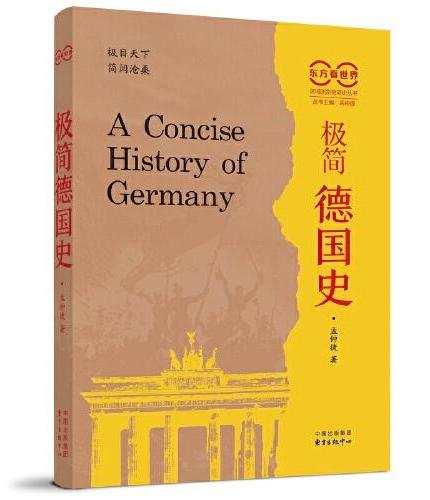
《
极简德国东方看世界·极简德国史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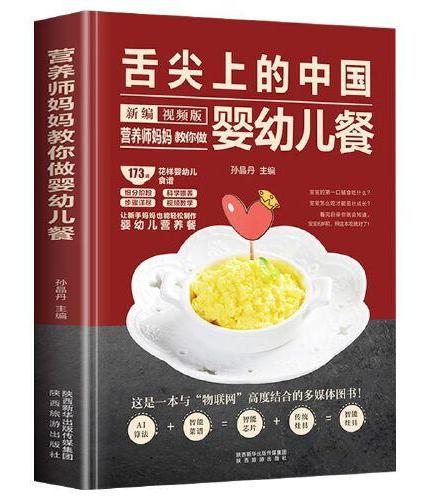
《
舌尖上的中国新编视频版营养师妈妈教你做婴幼儿餐
》
售價:NT$
296.0
|
| 編輯推薦: |
|
知识分子论丛第12期,王汎森、许纪霖、许章润、金观涛、刘擎、崇明……共同寻求“现代中国”。
|
| 內容簡介: |
《何谓现代,谁之中国?》为许纪霖、刘擎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12辑。本辑关注的话题是重构现代中国想象,内容包括王汎森谈中国思想史研究经验、许章润谈革命、金观涛谈契约论的起源、崇明谈承认政治等。
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是现代中国”,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而是有待建构的一套想象。 何谓现代,谁之中国?对现代中国的再阐释并不是一个事实性的揭秘,而是一个知识性的解读,它包含各种各样竞争性的话语,也包含各种不同的知识类型。主观和客观相互交错在一起,在当今新的历史语境里,
我们该如何来生产关于现代中国的知识?
我们无法依托一个清晰、可靠、稳定的中国元素来奠定对中国的认同。在这样一个时代,你必须要有一种大无畏的成熟:与流动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共存。康德曾说,启蒙是一种成熟,就是勇敢地公开运用你的理性。而我觉得,现代人要有另外一种成熟,就是与这个时代的很多不能化解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暧昧性共存。——刘 擎
当下中国亟需政治决断以展现政治成熟。值此情形下,如何提炼中国民族的政治气质和政治智慧,使中国走向政治成熟,蔚为一个政治的国族,是一切追究政治立宪和国家理性的理论体系之衷心寄托所在,也是中华民族得为亿万国民分享文化、政治家园的历史和政治前提。——许章润
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转,其前提是存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如果共同体走向分裂和对抗,自由民主也必然失败。自由民主能够有效运转,不仅仅是因为其保护了个体或群体的权利,更是因为其锻造了公民,创造了促进共通善的政治生活。——崇 明
知识分子论丛简介:
CSSCI来源辑刊。
一线学者,一流视角,一个对话空间。以中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关心国事,有表达能力和号召力。论丛以中外思想史、知识分子研究、政治哲学、社会理论及都市研究为核心,每辑聚焦知识界共同关怀的某个公共问题,为中国和全球知识分子的跨学科交往提供一个合宜的公共空间。
|
| 關於作者: |
许纪霖
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刘擎
1963年出生。1978年就读上海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85年获工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1赴美国攻读政治学,先后获得硕士(马凯大学)与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学位。2000-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7月回到上海工作,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2005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2007-2008年美国Fulbright访问学者。2013年7月起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
| 目錄:
|
◎现代中国的再阐释
许纪霖:何谓现代,谁之中国?
叶文心:重读西洋汉典:从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谈起
对 话:从民族到国家
刘 擎:批判语境主义视野下的现代中国
瞿 骏:在“古今交缠”中理解现代中国
对 话:从传统到现代
◎思想史研究的传统与方法
王汎森:思想史研究方法经验谈
王汎森 叶文心 齐慕实 许纪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传统
◎现场 :革命、文人与国家理性
许章润:革命、文人与国家理性论纲:重读托克维尔
对 话:革命、立宪与国家理性
◎中国思想史研究
金观涛:论社会契约论的起源和演变
崇 明:宽容与自由主义
邓 军:“献身的热望”:以陈独秀的“宗教感”为主题的一项考察
高 波:民初代议制危机与贤人政治论的展开
◎西方思想选译
史蒂芬·P.马尔克斯:从“匪夷所思的一纸宣言”到“六十亿人的‘十诫’”?
托马斯·班德:智识生活的文化:城市与专业
|
| 內容試閱:
|
许纪霖
什么是现代中国?这个问题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空洞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史学界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我称之为“碎片化”的现象。也就是说,过去各种各样的宏大叙事趋于消解,大家的研究都在自己个别的微观领域来进行。今天中国的史学界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恰恰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趋势。在微观领域有很多突破,但是宏观背景却一片模糊。好比说,各自提供了一棵棵很好的树,甚至是一片很好的树叶,但对于那片森林,认识却是非常模糊的。每位学者都在自己的局部下棋,缺乏大局感和全局感。在这个意义上,什么是现代中国,这一被认为是过于宏观和空疏的大问题,需要再次提出来引起我们的思考。任何一个微观的研究,都要借助某种宏观的知识背景,即使不研究宏观问题,也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于某一个或几个理论预设或者框架背景;而任何一个微观领域的研究,其真实的意义也只能放在宏观的知识背景里面才能获得理解。
中国研究的四种模式
关于“什么是现代中国”,过去存在着四种不同模式的理解。第一个模式首先是费正清提出来的冲击—反应论,把现代中国理解为由西方的冲击而产生的回应。第二个是列文森的传统与现代模式,这个模式到今天还有巨大的影响,甚至某种意义上在大陆史学界还是主流,把现代中国看成是怎么克服传统、走向普遍的现代性的历史过程。第三种模式,柯文把它概括为帝国主义论,在中国史学界过去更多地体现为革命高潮论,把现代中国的历史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革命,最后取得胜利的历史。第四个可以称之为中国中心观,这是柯文最早提出来的,试图跳出欧洲中心论的框架,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出发来理解现代中国;在日本和韩国,不少学者也试图超越西方的视野,提出东亚现代性,认为东亚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同欧洲完全不一样,有自身的脉络和历史渊源。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不是1840年以后的事,而是从宋代以后就有一个缓慢的、自身演变的过程。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史学界也出现了中国(历史)特殊论的观点,而且开始逐渐变得主流。
虽然现在许多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拒绝谈宏观问题,但谈也好,不谈也好,它总是在那里,只是你不自觉而已。所以,我认为对“何谓现代中国”需要反思,从而获得一个“背景性的自觉”,以便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微观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对已有的四种模式进行反思。对现代中国的阐述,不是重新开天辟地另搞一套,而是从原有的四种模式再出发,再阐释。
谁之中国?
我们先来看什么叫中国。过去关于研究中国的各种模式里面,中国似乎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但是在今天这个碎片化的时代里,一个整体的中国似乎已经消解了,似乎难以言说。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有各自不同的中国想象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史学界,这二十年来出现一个潮流,就是政治、外交、思想史的衰落和社会文化史的兴起。政治、外交和思想史是在国家的整体层面作研究,所以它有一个整体中国的想象;这些年由于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整个研究的眼光下移,开始从那些长时段的社会文化来思考和研究中国。所以,区域史的崛起、城市史的崛起,开始把某个城市、若干的区域,乃至某个乡村作为研究中国的对象。这种趋势出现以后,伴随出现的问题是整体中国的消解。中国今天已经被撕裂成为一个个区域性的中国、局部性的中国。我们对于中国的理解当然离不开对局部的、碎片化中国的理解,但是,部分相加的总和并非意味着整体,整体的中国并不是部分的相加,哪怕把岭南、江南、巴蜀、齐鲁、陕北、东北……这些区域的研究全部加起来,也并不意味着获得了对整体中国的理解。今天中国史学界的问题,在于局部中国的图案越来越清晰,但在局部清晰的背景里,整体的中国却显得模糊起来。经过了理解区域中国的积累以后,整体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如何在区域中国、城市中国的基础上,获得对于整体中国的深层次理解?这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即使各种理解是竞争性的、多元的,也仍是必需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再反过来深化对区域中国的研究。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何为“中华民族”。现代中国继承了清代的遗产,它的内涵不仅是汉民族的历史,也不仅是汉民族所生活的区域,它还包括满、藏、回、蒙等其他各族。我们今天对中国的理解大都是汉人历史视野中的中国,缺乏少数民族的视野。这些年,由于新清史提出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理解中国的主体视野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我们要重新理解一个多民族视野下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现代中国建立的是nation-state,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但是从它的存在形态来说,就像白鲁恂所说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国家伪装下的文明国家。中国这么大一个版图事实上的确是以帝国的方式存在的,而不是一个典型的nation-state,即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事实上,不同的民族视野下所看出来的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原与边疆的视野就有很大的差别。民族视野里面看出来的中国和我们过去以中原视野看出来的中国有什么区别?显然这也包含在我们要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国的问题之中,进而言之,什么是“中华民族”,这个nation是什么?这同样是这些年提出的一个挑战,值得我们思考。所以说“中国是什么”,这本身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它是有待建构的一套想象。
何谓现代?
何谓现代性?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模式,或西方现代化的模式里,所谓“现代”就是以西方为代表的价值和制度设置,甚至是可以量化的一套现代化物化指标。但这几十年,这样的理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出现了多元现代性的趋势。多元的现代性出现之后,是否消解了现代性的普遍性呢?或者说,现代性不再以某种普遍的方式存在,而只是相互之间不可通约、不可比较的各种特殊的现代性?
如果说各种现代性都只是特殊存在的话,那么现代性本身就已经去普遍化了,它本身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提出这个问题,乃是要思考,所谓现代中国中的“现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而言,“现代”究竟是普世的,还是特殊的?或者是特殊之中蕴含着普世的性质?
我们之所以走不出普遍与特殊对立的怪圈,乃是由于过去我们是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来思考和理解“现代”的普遍性。我这几年的工作乃是试图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的方法来重新理解“现代”的普遍性。就像亨廷顿所说的,所谓的普世文明,并非以西方为代表,而是各种不同的现代文明当中共享的那部分,也就是说,“现代”的普遍性存在于各种特殊的现代性当中,而共享的那部分是普世的,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类似”的方式存在。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现代中国所呈现的现代性不是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一方面它具有某些“家族类似”的特征,具有现代性的大部分特征,但另一方面,中国依然有自己的特殊性。所谓特殊性,就是在现代性的各种价值和元素之中,将富强这一价值作为优先的选择,而将另外一些价值,比如说自由、民主和法治作为次要的选择。
现代性与中国性这两者之间,我们应如何理解?过去我们总是把现代性视为普遍的,中国是特殊的。现在讲中国特色的什么什么,实际上也是把某个东西看成是普遍的,而中国只是普遍当中的某个特殊而已。当我们以家族类似的方式重新理解现代性之后,普遍与特殊、现代与中国就不是被放在对立的、二元的位置,而是可说所谓的“现代中国”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现代中国一百七十多年的现代化历史,既是中国特殊的道路,同时又提供了某些现代性的普遍经验,又因为一度以所谓的特殊性对抗普遍性,走过弯路。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必须既符合普世文明的那些“家族类似”价值,又具有中国自身的特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