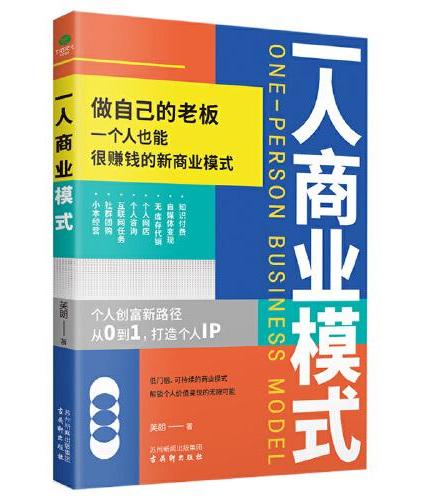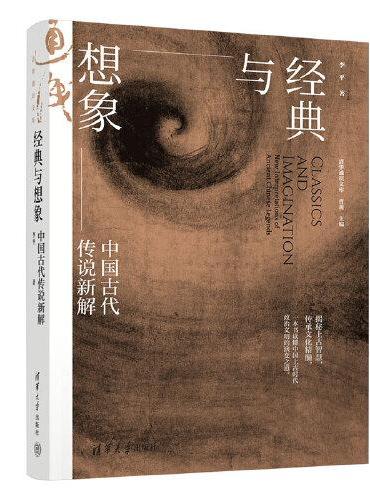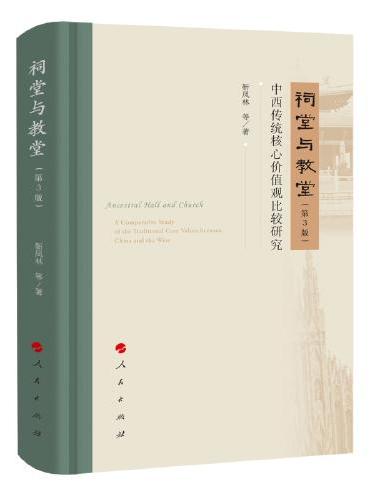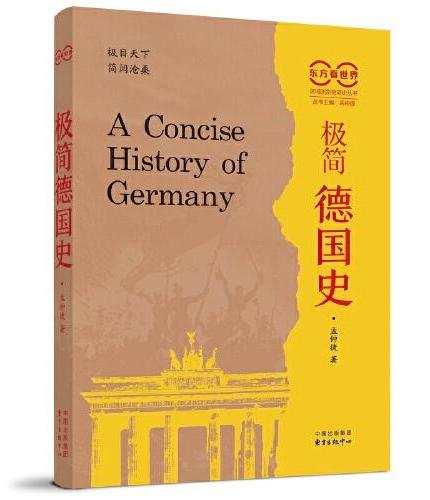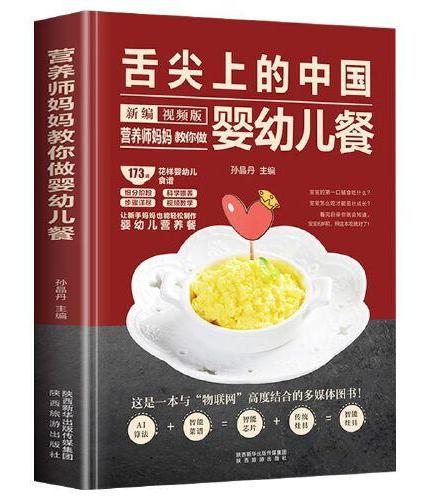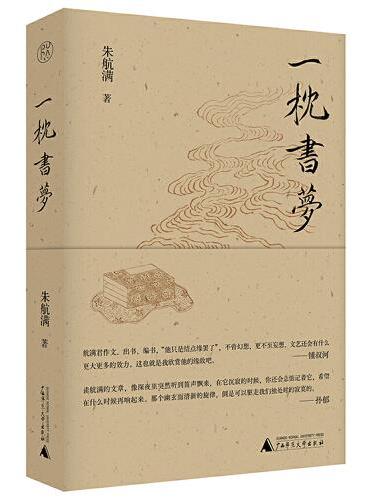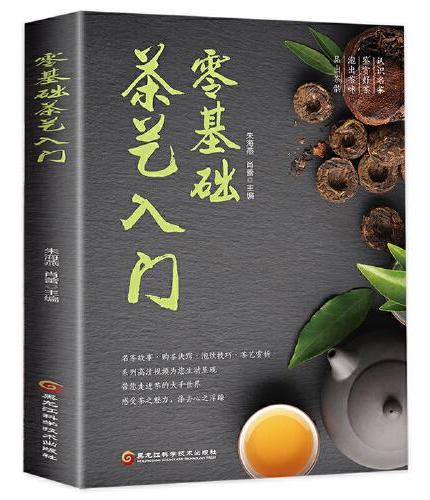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一人商业模式 创富新路径个人经济自由创业变现方法书
》 售價:NT$
254.0
《
经典与想象:中国古代传说新解
》 售價:NT$
398.0
《
祠堂与教堂:中西传统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第3版)
》 售價:NT$
551.0
《
极简德国东方看世界·极简德国史
》 售價:NT$
347.0
《
舌尖上的中国新编视频版营养师妈妈教你做婴幼儿餐
》 售價:NT$
296.0
《
Scratch创意编程进阶:多学科融合编程100例
》 售價:NT$
500.0
《
纯粹·一枕书梦
》 售價:NT$
367.0
《
新版-零基础茶艺入门
》 售價:NT$
179.0
編輯推薦:
畅销书《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Proust Was a Neuroscientist)作者乔纳?莱勒最新力作。作者是牛津大学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关注20世纪的文学艺术,对艺术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乔纳?莱勒曾于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神经学,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的实验室里做过有关记忆的生物学研究实验。
內容簡介:
畅销书《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作者乔纳·莱勒将艺术与科学相结合,以科学的视角揭示了大脑是如何产生创造力的:左脑还是右脑更擅长创造?爱做白日梦更有利于发挥创造力吗?鲍勃·迪伦怎么创作歌词?马友友是如何做到即兴演奏的?莎士比亚为何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者?皮克斯是如何创作动画电影的?城市有利于激发人的创造力?以上问题都是本书围绕“我们如何想象”这一主题来探讨的。
關於作者:
乔纳·莱勒
目錄
《想象》测试题
內容試閱
鲍勃·迪伦的大脑 大脑是创造力产生的生物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