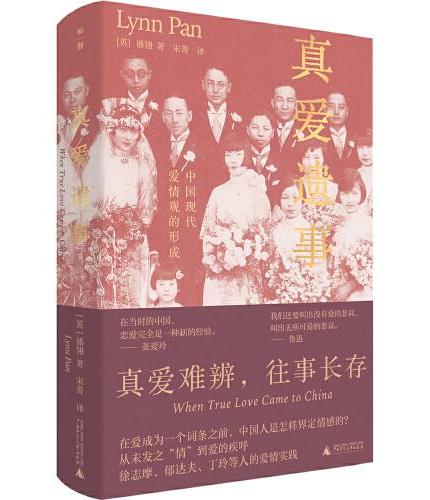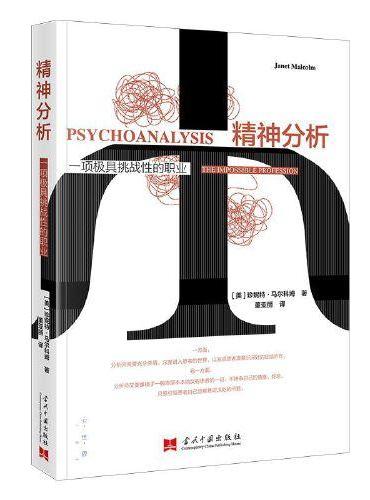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布克哈特书信选
》
售價:NT$
439.0

《
DK园艺的科学(100+个与园艺有关的真相,让你读懂你的植物,打造理想花园。)
》
售價:NT$
500.0

《
牛津呼吸护理指南(原书第2版) 国际经典护理学译著
》
售價:NT$
959.0

《
窥夜:全二册
》
售價:NT$
407.0

《
有底气(冯唐半生成事精华,写给所有人的底气心法,一个人内核越强,越有底气!)
》
售價:NT$
347.0

《
广州贸易:近代中国沿海贸易与对外交流(1700-1845)(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国际知名史学家深度解读鸦片战争的起源!)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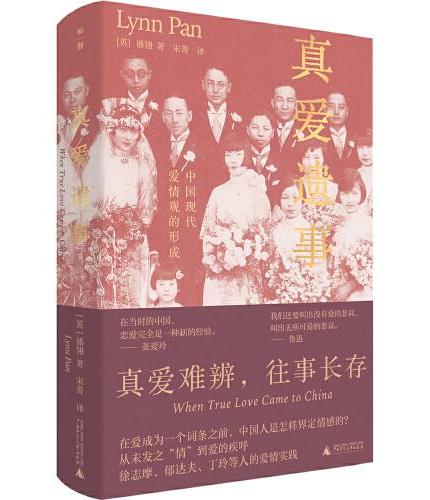
《
真爱遗事:中国现代爱情观的形成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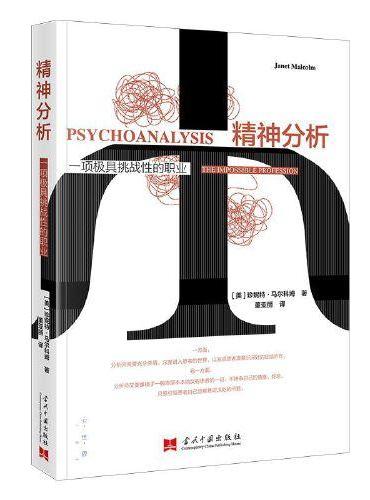
《
精神分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职业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权威 国内研究沈从文第一人凌宇主编
纯美 国家一级美术师李晨插图
全面 收录作者目前面世的所有小说
原貌 最大程度保持作品发表时的风貌
|
| 關於作者: |
|
沈从文(1902-1988),苗族,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
| 目錄:
|
卷一:鸭子·蜜柑·入伍后
卷二:阿丽思中国游记
卷三:篁君日记·雨后·长夏
卷四:公寓中·梓里集·采蕨
卷五:神巫之爱·一个天才的通信
卷六:旧梦·石子船·龙朱
卷七:虎雏·阿黑小史
卷八:月下小景·如蕤
卷九:边城
卷十:八骏图
卷十一:新与旧·长河
卷十二:楼居·芸庐纪事·雪晴
|
| 內容試閱:
|
往事
这事说来又是十多年了。
算来我是六岁。因为第二次我见到长子四叔时,他那条有趣的辫子就不见了。
那夏天秋天之间。我仿佛还没有上过学。妈因怕我到外面同瑞龙他们玩时又打架,或是乱吃东西,每天都要靠到她身边坐着,除了吃晚饭后洗完澡同大哥各人拿五个小钱到道门口去买士元的凉粉外,剩下便都不准出去了!至于为甚又能吃凉粉?那大概是妈知道士元凉粉是玫瑰糖,不至吃后生病吧。本来那时的时疫也真凶,听瑞龙妈说,杨老六一家四口人,从十五得病,不到三天便都死了!
我们是在堂屋背后那小天井内席子上坐着的。妈为我从一个小黑洋铁箱子内取出一束一束方块儿字来念,她便膝头上搁着一个麻篮绩麻。衖子里跑来的风又凉又软,很易引人瞌睡,当我倒在席子上时,妈总每每停了她的工作,为我拿蒲扇来赶那些专爱停留在人脸上的饭蚊子。间或有个时候妈也会睡觉,必到大哥从学校挟着书包回来嚷肚子饿时才醒,那么,夜饭必定便又要晚一点了!
爹好像到乡下江家坪老屋去了好久了,有天忽然要四叔来接我们。接的意思四叔也不大清楚,大概也就是闻到城里时疫的事情吧。妈也不说什么,她知道大姐二姐都在乡里,我自然由她们料理。只嘱咐了四叔不准大哥到乡下溪里去洗澡,因大哥前几天回来略晚,妈摩他小辫子还湿漉漉的,知他必是同几个同学到大河里洗过澡了,还刚重重的打了他一顿呢。四叔是一个长子,人又不大肥,但很精壮。妈常说这是会走路的人。铜仁到我凤凰是一百二十里蛮路,他能扛六十斤担子一早动身,不抹黑就到了,这怎么不算狠!他到了家时,便忙自去厨房烧水洗脚。那夜我们吃的夜饭菜是南瓜炒牛肉。
妈为捡菜劝他时,他又选出无辣子的牛肉放到我碗里。真是好四叔呵!
往 事那时人真小,我同大哥还是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为四叔担去的!大哥虽是大我五六岁,但在四叔肩上似乎并不怎么不匀称。乡下隔城有四十多里,妈怕太阳把我们晒出病来,所以我们天刚一发白时就动身,到行有一半的唐峒山时,太阳还才红红的。到了山顶,四叔把我们抱出来各人放了一泡尿,我们便都坐在一株大刺栎树下歇憩。那树的杈桠上搁了无数小石头,树左边又有一个石头堆成的小屋子。四叔为我们解说小屋子是山神土地:为赶山打野猪的人设的;树上石头是寄倦的:凡是走长路的人,只要放一个石头到树上,便不倦了。但大哥问他为甚不也放一个石子时,他却不做声。
他那条辫子细而长正同他身子一样。本来是挽放头上后而再加上草帽的,不知是那辫子长了呢还是他太随意,总是动不动又掉下来,当我是在他背后那头时,辫子尖端便时时在我头上晃。
“芸儿,莫闹!扯着我不好走!”
我伸出手扯着他辫子只是捹①,他总是和和气气这样说。
“四满注一,到了?”大哥很搔急的这么问。
“快了,快了,快了!芸弟都不急,你怎么这样慌?你看我跑!”他略略把脚步放快一点,大哥便又嚷又摇的头痛了。
他一路笑大哥不济。
到时,爹正同姨婆五叔四婶他们在院中土坪上各坐在一条小凳上说话。姨婆有两年不见我了,抱了我亲了又亲。爹又问我们饿了不曾,其实我们到路上吃甜酒米豆腐已吃胀了。上灯时,方见大姐二姐大姑满姑注二各人手上提了一捆地萝卜进来。
我夜里便同大姐等到姨婆房里睡。
乡里有趣多了!既不什么很热,而夜里蚊子也很少。大姐到久一点,似乎各样事情都熟习。第二天一早便引我去羊栏边看睡着比猫还小的白羊,牛栏里正歪起颈项在吃奶的牛儿。我们又到竹园中去看竹子。那时觉得竹子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本来城里竹子,通常大到屠桌边卖肉做钱筒的已算出奇了!但后园里那些南竹,大姐教我去试抱一下时,两手竟不能相掺。满姑又为偷偷的到园坎上摘了十多个桃子。接着我们便跑到大门外溪沟边上拾得一衣兜花蚌壳。
事事都感到新奇:譬如五叔喂的那十多只白鸭子,它会一翅从塘坎上飞过溪沟。夜里四叔他们到溪里去照鱼时,却不用什么网,单拿个火把,拿把镰刀。姨婆喂有七八只野鸡,能飞上屋,也能上树,却不飞去;并且,只要你拿一捧包谷米在手,口中略略一逗,它们便争先恐后的到你身边来了。什么事情都有味:我们白天便跑到附近村子里去玩,晚上总是同坐在院中听姨婆讲打野猪打獾子的故事。姨婆真好,我们上床时,她还每每为从大油坛里取出炒米,栗子,同脆酥酥的豆子给我们吃!
后园坎上那桃子已透熟了,满姑一天总为我们去偷几次。爹又不大出来,四叔五叔又从不说话,间或碰到姨婆见了时,也不过笑笑的说:
“小娥,你又忘记嚷肚子痛了!真不听讲——芸儿,莫听你满姑的话,吃多了要坏肚子!拿把我,不然晚上又吃不得鸡膊腿了!”
乡里去有场集的地方似乎并不很近,而小小村中除每五天逢一六赶场外通常都无肉卖。因此,我们几乎天天吃鸡,惟我一人年小,鸡的大腿便时时归我。
我们最爱看又怕看的是溪南头那坝上小碾房的磨石同自动的水车:碾房是五叔在料理。那圆圆的磨石,固定在一株木桩上只是转只是转,五叔像个卖灰的人,满身是糠皮,只是在旋转不息的磨石间拿扫把扫那跑出碾槽外的谷米,他似乎并不着一点忙,磨石走到他跟前时一跳又让过磨石了。我们为他着急又佩服他胆子大。水车也有味,是一些七长八短的竹篙子扎成的。它的用处就是在灌水到比溪身为高的田面。大的有些比屋子还大,小的也还有一床晒簟大小。它们接接连连竖立在大路近旁,为溪沟里急水冲着快快地转动,有些还咿哩咿哩发出怪难听的喊声,由车旁竹筒中运水倒到悬空的枧注三上去。它的怕人就是筒子里水间或溢出枧外时,那水便砰的倒到路上了,你稍不措意,衣服便打得透湿。我们远远的立着看行路人抱着头冲过去时那样子好笑。满姑虽只大我四岁,但看惯了,她却敢在下面走来走去。大姐同大姑,则知道那个车子溢出后便是那一个接脚,不消说是不怕水淋了!只我同大哥二姐却无论如何不敢去尝试。
往事
这事说来又是十多年了。
算来我是六岁。因为第二次我见到长子四叔时,他那条有趣的辫子就不见了。
那是夏天秋天之间。我仿佛还没有上过学。妈因怕我到外面同瑞龙他们玩时又打架,或是乱吃东西,每天都要靠到她身边坐着,除了吃晚饭后洗完澡同大哥各人拿五个小钱到道门口去买士元的凉粉外,剩下便都不准出去了!至于为甚又能吃凉粉?那大概是妈知道士元凉粉是玫瑰糖,不至吃后生病吧。本来那时的时疫也真凶,听瑞龙妈说,杨老六一家四口人,从十五得病,不到三天便都死了!
我们是在堂屋背后那小天井内席子上坐着的。妈为我从一个小黑洋铁箱子内取出一束一束方块儿字来念,她便膝头上搁着一个麻篮绩麻。衖子里跑来的风又凉又软,很易引人瞌睡,当我倒在席子上时,妈总每每停了她的工作,为我拿蒲扇来赶那些专爱停留在人脸上的饭蚊子。间或有个时候妈也会睡觉,必到大哥从学校挟着书包回来嚷肚子饿时才醒,那么,夜饭必定便又要晚一点了!
爹好像到乡下江家坪老屋去了好久了,有天忽然要四叔来接我们。接的意思四叔也不大清楚,大概也就是闻到城里时疫的事情吧。妈也不说什么,她知道大姐二姐都在乡里,我自然由她们料理。只嘱咐了四叔不准大哥到乡下溪里去洗澡,因大哥前几天回来略晚,妈摩他小辫子还湿漉漉的,知他必是同几个同学到大河里洗过澡了,还刚重重的打了他一顿呢。四叔是一个长子,人又不大肥,但很精壮。妈常说这是会走路的人。铜仁到我凤凰是一百二十里蛮路,他能扛六十斤担子一早动身,不抹黑就到了,这怎么不算狠!他到了家时,便忙自去厨房烧水洗脚。那夜我们吃的夜饭菜是南瓜炒牛肉。
妈为捡菜劝他时,他又选出无辣子的牛肉放到我碗里。真是好四叔呵!
往 事那时人真小,我同大哥还是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为四叔担去的!大哥虽是大我五六岁,但在四叔肩上似乎并不怎么不匀称。乡下隔城有四十多里,妈怕太阳把我们晒出病来,所以我们天刚一发白时就动身,到行有一半的唐峒山时,太阳还才红红的。到了山顶,四叔把我们抱出来各人放了一泡尿,我们便都坐在一株大刺栎树下歇憩。那树的杈桠上搁了无数小石头,树左边又有一个石头堆成的小屋子。四叔为我们解说小屋子是山神土地:为赶山打野猪的人设的;树上石头是寄倦的:凡是走长路的人,只要放一个石头到树上,便不倦了。但大哥问他为甚不也放一个石子时,他却不做声。
他那条辫子细而长正同他身子一样。本来是挽放头上后而再加上草帽的,不知是那辫子长了呢还是他太随意,总是动不动又掉下来,当我是在他背后那头时,辫子尖端便时时在我头上晃。
“芸儿,莫闹!扯着我不好走!”
我伸出手扯着他辫子只是捹①,他总是和和气气这样说。
“四满注一,到了?”大哥很搔急的这么问。
“快了,快了,快了!芸弟都不急,你怎么这样慌?你看我跑!”他略略把脚步放快一点,大哥便又嚷又摇的头痛了。
他一路笑大哥不济。
到时,爹正同姨婆五叔四婶他们在院中土坪上各坐在一条小凳上说话。姨婆有两年不见我了,抱了我亲了又亲。爹又问我们饿了不曾,其实我们到路上吃甜酒米豆腐已吃胀了。上灯时,方见大姐二姐大姑满姑注二各人手上提了一捆地萝卜进来。
我夜里便同大姐等到姨婆房里睡。
乡里有趣多了!既不什么很热,而夜里蚊子也很少。大姐到久一点,似乎各样事情都熟习。第二天一早便引我去羊栏边看睡着比猫还小的白羊,牛栏里正歪起颈项在吃奶的牛儿。我们又到竹园中去看竹子。那时觉得竹子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本来城里竹子,通常大到屠桌边卖肉做钱筒的已算出奇了!但后园里那些南竹,大姐教我去试抱一下时,两手竟不能相掺。满姑又为偷偷的到园坎上摘了十多个桃子。接着我们便跑到大门外溪沟边上拾得一衣兜花蚌壳。
事事都感到新奇:譬如五叔喂的那十多只白鸭子,它会一翅从塘坎上飞过溪沟。夜里四叔他们到溪里去照鱼时,却不用什么网,单拿个火把,拿把镰刀。姨婆喂有七八只野鸡,能飞上屋,也能上树,却不飞去;并且,只要你拿一捧包谷米在手,口中略略一逗,它们便争先恐后的到你身边来了。什么事情都有味:我们白天便跑到附近村子里去玩,晚上总是同坐在院中听姨婆讲打野猪打獾子的故事。姨婆真好,我们上床时,她还每每为从大油坛里取出炒米,栗子,同脆酥酥的豆子给我们吃!
后园坎上那桃子已透熟了,满姑一天总为我们去偷几次。爹又不大出来,四叔五叔又从不说话,间或碰到姨婆见了时,也不过笑笑的说:
“小娥,你又忘记嚷肚子痛了!真不听讲——芸儿,莫听你满姑的话,吃多了要坏肚子!拿把我,不然晚上又吃不得鸡膊腿了!”
乡里去有场集的地方似乎并不很近,而小小村中除每五天逢一六赶场外通常都无肉卖。因此,我们几乎天天吃鸡,惟我一人年小,鸡的大腿便时时归我。
我们最爱看又怕看的是溪南头那坝上小碾房的磨石同自动的水车:碾房是五叔在料理。那圆圆的磨石,固定在一株木桩上只是转只是转,五叔像个卖灰的人,满身是糠皮,只是在旋转不息的磨石间拿扫把扫那跑出碾槽外的谷米,他似乎并不着一点忙,磨石走到他跟前时一跳又让过磨石了。我们为他着急又佩服他胆子大。水车也有味,是一些七长八短的竹篙子扎成的。它的用处就是在灌水到比溪身为高的田面。大的有些比屋子还大,小的也还有一床晒簟大小。它们接接连连竖立在大路近旁,为溪沟里急水冲着快快地转动,有些还咿哩咿哩发出怪难听的喊声,由车旁竹筒中运水倒到悬空的枧注三上去。它的怕人就是筒子里水间或溢出枧外时,那水便砰的倒到路上了,你稍不措意,衣服便打得透湿。我们远远的立着看行路人抱着头冲过去时那样子好笑。满姑虽只大我四岁,但看惯了,她却敢在下面走来走去。大姐同大姑,则知道那个车子溢出后便是那一个接脚,不消说是不怕水淋了!只我同大哥二姐却无论如何不敢去尝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