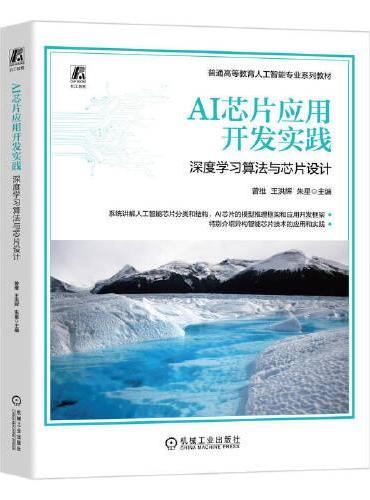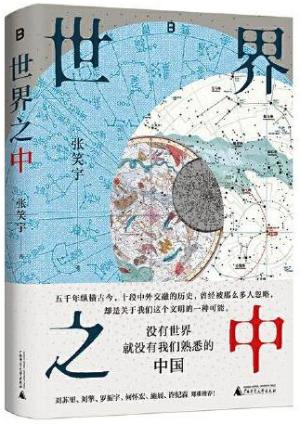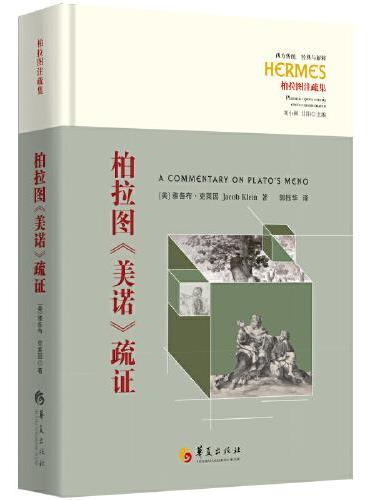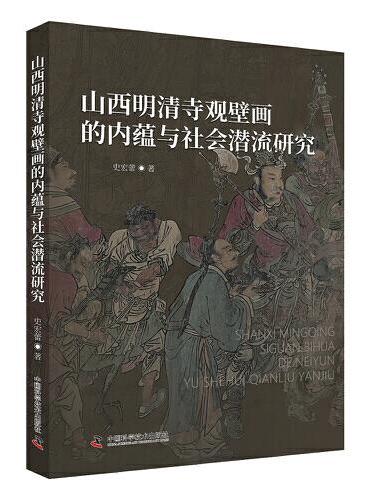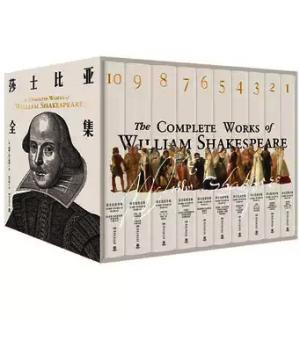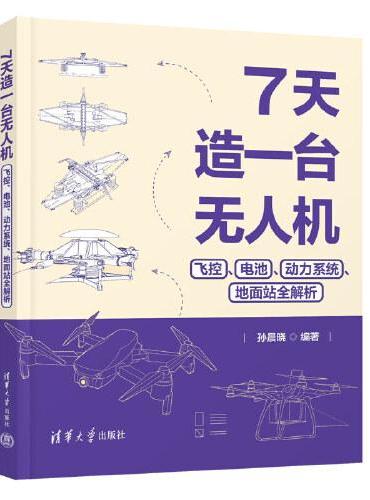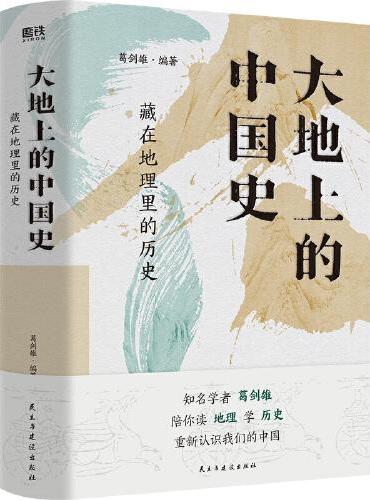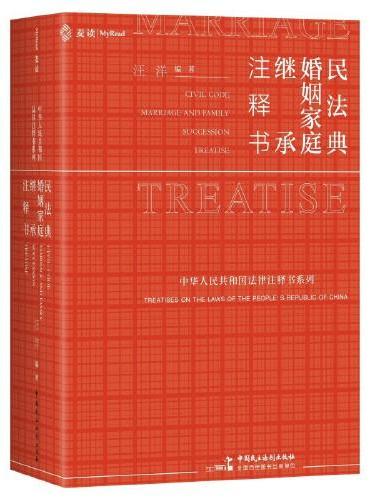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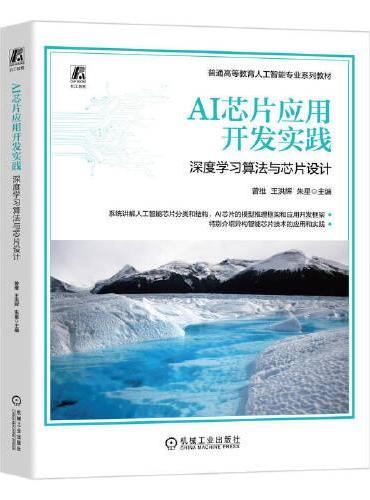
《
AI芯片应用开发实践:深度学习算法与芯片设计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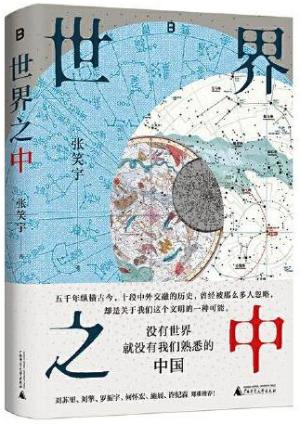
《
世界之中(文明三部曲之后,亚洲图书奖得主张笑宇充满想象力的重磅新作)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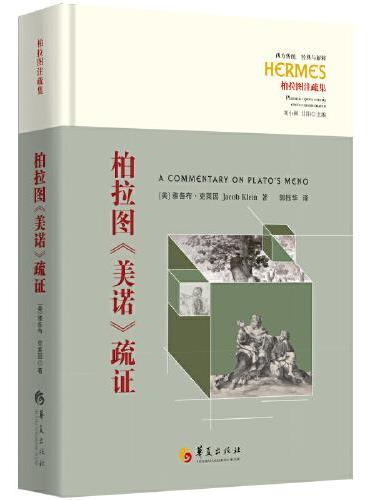
《
柏拉图《美诺》疏证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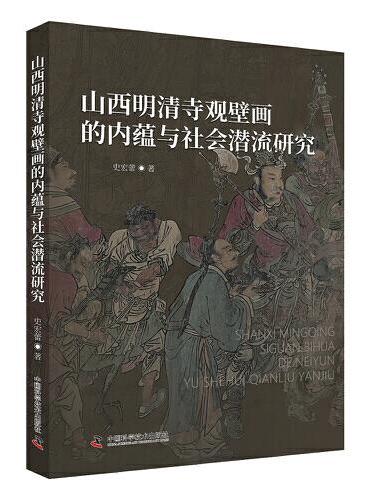
《
山西明清寺观壁画的内蕴与社会潜流研究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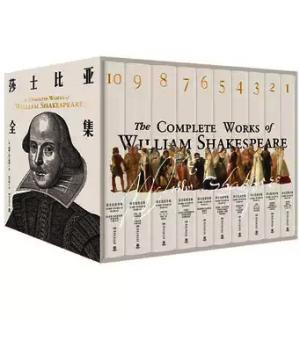
《
莎士比亚全集十卷
》
售價:NT$
27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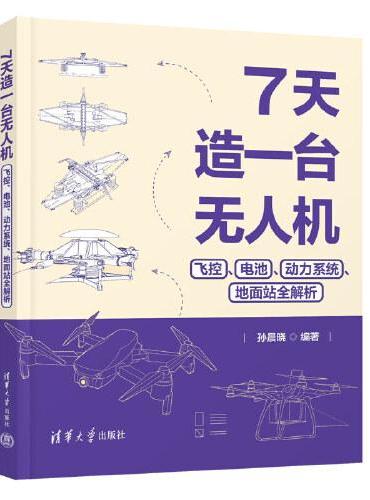
《
7天造一台无人机:飞控、电池、动力系统、地面站全解析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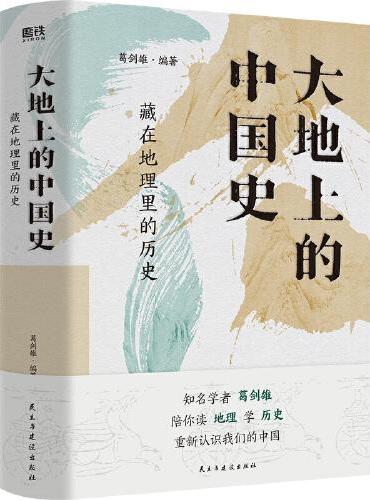
《
大地上的中国史:藏在地理里的历史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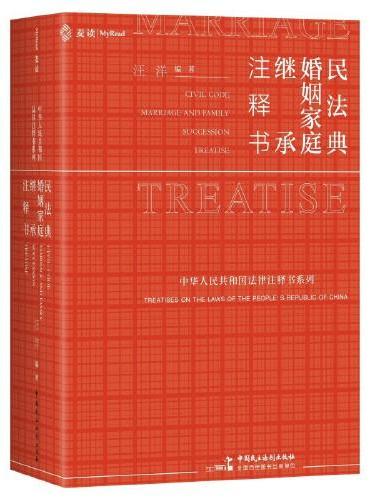
《
《民法典·婚姻家庭继承注释书》(家事法专用小红书,一书尽揽现行有效办案依据:条文释义+相关立法+行政法规+地方立法+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地方法院规范+权威案例,麦读法律54)
》
售價:NT$
607.0
|
| 編輯推薦: |
1.《京城艺事》一书,采用高档米黄色带底纹特种纸封面,内文80克纯质纸,外观高大上,艺术气息浓厚。
2.首部讲述北京曲艺圈圈内圈外六十年的发展之路的作品。
3.该书讲述了北京知名的曲艺人如侯宝林、田占义、梁爱民、李金斗、郭德纲、李菁、嘻哈包袱铺
4.《京城艺事》一书,聚焦了“坚持”这一词,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如夜场、洗澡堂等地过往的艰辛岁月。已经成名的回味过去的成名之路;还没有成名的正在努力地坚持着;更有一些人只在乎“爱”的过程。让人在隐隐心痛的同时带着一股“上进”的勇气。
|
| 內容簡介: |
当今浮躁社会最缺乏什么?坚守。本书通过对二十多位曲艺圈内的人物的采访,讲述了北京曲艺六十年的发展史。其中既有六十年前抗美援朝下曲艺人的牺牲与付出,更有今日市场经济下曲艺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四处出击的无奈。在六十年中,他们唯一没有丢掉的是对曲艺和传统文化的热爱。
曲艺的圈里圈外,既有人世间的一切丑
更有人世间的一切美
向所有曾经、现在、未来坚守的人
致敬
人生如有来世
我仍旧爱你——曲艺
|
| 關於作者: |
|
祝兆良,1970年生人,正宗评书——北京评书第九代掌门连阔如徒孙、连丽如之徒,因师兄弟排行第三,曲艺圈内称为“三爷”。主打书目《东汉》《康熙私访》《雍正剑侠图》,自创评书《赛金花》等长篇书目。
|
| 目錄:
|
我非世家——田战义
肉铺票房——记与李菁、张金山的评书往事
能示弱才是真正的强者——李增瑞
相声艺术不能省事——刘洪沂
相声隐忍中铸就辉煌——赵福玉
侯门大弟子——贾振良
“惟一”的“连盟”——连旭
一代宗师——梁厚民
活在曾经时代的人——马星野
快书凤凰——章学楷
笑眼小孩——演员程磊的故事(主谈侯宝林等老艺人)
蓄势待发——秦永超
弹挑之间度春秋——孙洪宴
曲苑一家人
曲终人散——记忆中的单弦票房
谭派传人——张蕴华
岔曲要造反的保守者——记我的老师张卫东
随缘乐——司瑞轩
艺坛贵族——王金凤
《开心茶馆》主持人——康大鹏(主谈郭德纲的成长经历)
话剧曲剧相声——记演员李林
另类帅哥,记曲艺杂家崔琦
票界名宿——高家兰
寻访“南城二哥”
附录
小院里的评书梦
风尘挽歌——创作《赛金花》随笔
浅论评书演员之形体修炼
新评书体系
曲苑姻缘票房牵
|
| 內容試閱:
|
代序:风中的承诺——演出十二年琐记
夜色阑珊,霓虹灯闪耀。亚运村的一家饭店大厅内,人头攒动,桌上杯盘狼藉,无数人在吞云吐雾,一片香烟缭绕。大厅北侧搭了一座小台,前面放着两个不时嗤嗤作响的麦克风,一位老先生正带着我说相声。虽是吃饭的地方,但一老一少身着长衫在那儿一站,大都觉得很新奇,所以“给耳朵”。
那天我激情澎湃,一段《八扇屏》气口上虽然不准,但当时身体状态不错,倒也酣畅。见“底”了,我心中暗喜,这场活总算圆满。恰在此时,正对着台的头一桌站起了一个人,他瘦得像麻秆,戴着眼镜,嘴角挂着令人恶心的坏笑:“你们这俩孙子先别说了。”他指了指坐在中间的一个人,那人长得臃肿肥硕,留着平头,嘴唇外翻,嘿嘿地笑着,一望便知,是黑道中人。“麻秆”说:“我们老板今天过生日,让你们捡个便宜,说一百句祝寿的话,给你们五百块钱。”周围的七八个人一起鼓掌,冲我们吼道:“妈的,快点!快点!”
老先生侧过头来看着我,表情好像在问“怎么办?”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的确幼稚,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竟是打架。但对方大约十个人,我知道,这些人几乎每个随身都佩匕首。当然他们也有所顾忌,动手的时候,大拇哥掐在刀尖往下一寸多的位置,扎在人身上横着一豁,能把肉揦开,却不伤里面的内脏。不过,这是在道上混了多年的老流氓才懂的,初入江湖的“生瓜”,根本没有这种“寸量”。
敢陪我打架的伙伴那天都不在,若动手,我一个人是净等着吃亏。当时自己内心的感觉,竟不是恨这些挑事的人,而是恨自己的犹豫、迟疑。我当时真傻,在台上骂了一句“说你姥姥”后,转身就往台下跑,不用回头,听声音就知道那些人扑过来了,同场的老先生冲我大喊:“小祝,快关门!”我冲进后台,把门“咔吧”锁上了,紧跟着门外就是凿门、踢门、谩骂的声音,我真是个孩子,当时心很慌,从饭馆的后门一溜烟儿跑到了大街上。
过了大概一个钟头,才转回来,刚进后台的门,迎面就碰见那位老先生,他狠狠地在我的后脑勺上撸了一把,“小兔崽子,你跑了,把我扔里头了!”我问:“大爷,吃亏了?”老先生抖了抖身上的袍子,“看看,扣儿都扯掉了。”我连忙说:“回头我给您做件新的吧!”他用手拍拍我的脸:“哈哈,当真啦,大爷跟你开玩笑呢!”听他说这话,我心里有一阵儿发酸。很多人觉得曲艺圈的人坏,其实大错特错,真正干这一行的人,都是极仗义的。
人品坏的,都是假充内行,是圈外人,但滥竽充数的太多了,真的就变成假的,假的倒叫人以为是真的了。几个后台的阿姨也围过来,嘱咐我:“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多留神!”饭店的老板走进来,大家都不敢说话了。他手里拎着一条挺大的钢板尺,先在桌子上“啪啪”抽了两下,嘴上动了动,听不清说什么,好像是在骂我,然后大吼道:“滚吧,我这儿不用你了!”1998年,那年我十八岁。
有人误以为,我的家境一定不好,因为生活所迫,才跳进这个火坑。其实,我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家里也不在意我往回拿了几个钱,我从小衣食无忧,从未体会过囊中羞涩的感觉。之所以做这一行,纯粹是因为喜欢。至今,对于影响我选择这门艺术的那一段背景我仍然记忆犹新。
十八岁那年夏天,一日天出奇的蓝,我独自一人骑车到了紫竹院,公园外的铁栏杆下有一条小河,两岸是绿草坪的堤坡,一座朱红色的小桥横跨河面。这一片风景,我仿佛在梦里见过。我把车支好,顺着堤坡走到河畔,见碧波荡漾,河面泛起层层的小浪花,我陶醉了,觉得人世间极致的幸福莫过于看着这一番景致。河中有鱼,黑黑的,如梭般穿过。我脑子里想着,怎么才能将它们捉上几条。我侧头向不远处望去,约二十米处,有个老妪望着我。她冲我笑了笑,走向我,说话的声音像眼前的河水,“你的相貌特别,愿意的话,帮你看看?”我说:“抱歉,没带零钱。”“不要钱。”“……好。”我把脸扭过来,朝向她。她含笑不语,过了片刻,说:“看看你的手。”我递出左手她略一摇头:“右手。”
我换过来,她没用手接,却说:“很软。”我问:“好还是不好?”老妪说:“外表文弱,却爱冒险,这样的脾气,早晚会成就一番事业。”“什么时候能成?”“别急,越晚越好,懒惰些,不过……”我说:“你说吧,我能扛得住。”“你脸色不太好,天生肾气单薄,肝火倒旺。记住,洁身自好,不然,你这一生,成也在女人,败也在女人。”
“多谢您指点。”老妪极自然地问:“现在几点?”我看了看表,“四点半。”她脸上有些着急,“我女儿还在家等我呢,附近怎么没有公交车啊?”这些人情世故我还是懂的,掏出二十块钱给了她,她冲我一竖拇指:“小伙子,你一定能成事,因为你不在乎钱,记住,要能忍!再见。”她转身往前走,倒背着手,把钱掐在指间,渐渐远去了。这时,我突然觉得有些害怕。
一个月后,我在街边看到一家洗浴中心招聘演员,壮了壮胆走了进去,有人马上向我鞠躬行礼,一个气质沉静的女人接待我。她的办公室里,光线暗淡。她身穿黑色的套装,不算很漂亮,但一双眼睛摄人心魄,不知是谁的禁脔。呼吸间,有幽兰的香气,她坐在我对面,身体下的沙发吱吱作响。“祝先生,”当时很少有人这样称呼我,她说,“我也很喜欢听评书,每天中午都听。”“噢,你喜欢听谁?”“那个……梅兰芳。”“哦……”我懒得去修正她,此时再看她,已经是个毫无魅力的女人了。
她带着我先在楼里转了一圈儿,有按摩女郎从身边走过,她们把双手搭扣在一起,向我点头行礼,只是双眼无神。我记得有人说,做这种职业先要把灵魂与肉体分离开来,她们不需要所谓的解救,因为喜欢这种麻木的感觉。
一层是浴池,二层是休憩的茶室,三层是桥牌室。当时我觉得这儿很不错,环境优雅,所有工作人员都彬彬有礼。大家都管那个女人叫“刘总”。刘总向我歪歪头,指着茶室内一个小舞台说:“以后你们就在这儿演。”这时我才注意到舞台前面有十几张躺椅,我皱了一下眉,刘总察觉了,“怎么?”她问。“没事,先试试吧。”“记得,明天晚上八点之前来上班啊。”她把公文夹挡到脸上,吃吃地笑了两声。
我问:“笑什么?”“没有,没有,还没听你说呢,光看你,就觉得逗。”多年后,有个朋友向我提起这个女人,“她很讨厌你,说你骨子里有股‘狂劲儿’,背地里常骂你。”我说:“我算老几?她犯得上在我面前装吗?”“呵呵,她也常说‘天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另外,毕竟你是北京人。”
若现在有人问我该如何创业,我一定会劝他少读书。读书太多的人,一定没手段。这个场所聚集了各种演员,表演流行歌曲、京剧、曲艺、魔术、杂技。演员们见面个个嘻嘻哈哈,背地里却互相骂娘。
若谁在台上演“泥”(术语,演出失败或反响不好)了,马上就有人上报给刘总。有一次她对我说:“在台上放开点儿演。”我知道有人在她那儿“点”了我,我做了些调整,总算挽回了一些局面,才没被开了。并不是为了钱(那时一场挣八十),而是怕自信心受挫。演员赔了钱可以再赚,自信心若伤了,恢复起来可就难了。当时在台上最火的是个唱二人转的演员,大伙儿叫她“胡姐”,四十多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她的头发枯黄,眼下浮肿,脸上、脖子上抹着厚厚的油粉,体形肥胖臃肿,走起路来有些蹒跚。
胡姐说话时声音嘶哑,但不管讲的事情如何令她气愤,却从未听她带过一句脏话,听人说,她原来是上过大学的。每次我走进后台,总会看到她坐在圆凳上,身上汗津津的,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手里拿着一把绣花的小折扇,呼哒呼哒地扇着。看到我,她眯起眼,点头笑笑,说:“来啦?”我对她既无好感,也无恶意,只是觉得她在台上太不拿自己当人了。她唱的二人转不算地道,最拿手的是《十八摸》,但还是有走音的地方,却善于和观众“互动”。
每唱这段,都要叫上几个人联合演出。那些人对她动手动脚,她则故作羞态。台下有人起哄,下流的言辞不堪入耳。为保住“最佳地位”,她想尽一切办法。记得有一次,她叫几个保安搬上来一个长条沙发,对台下的人说:“大家看过台湾的七十二式吗,哪位愿意上来和我一起表演一下?”有不少男人纷纷举手,然后在左侧排成一队,轮番与她“合作”。她是台柱子,刘总却一直对她不屑。她经常苦巴巴地要和领导说点儿事,可刘总总先伸出胳膊把她挡住,然后捂住鼻子,说:“你就站这里,别离我太近,说吧!”
有一次,她的举动令我惊讶不已。那一天我去得稍早些,门虚掩着,我穿着运动鞋,声音大概很轻,我进门,她没有察觉。只见她双手按住化妆台,身子向前倾着,睁大眼睛看着对面的镜子,然后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揪扯着头发,跟着开始抽自己耳光。她大概是从镜子里看到我站在她背后,马上停止了动作。也许是为逃避尴尬,她把长头发拢到了脸前,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我懵住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该出去!此时她突然嘿嘿地笑了出来,“被你看到了,小祝,姐不是不要脸,我儿子比你小不了两岁,他要上大学了,家里没钱啊……”她随后便呜呜地哭起来。我说:“哦,我去背背词儿。”
演员里,我那时是最不受观众欢迎的一个。通常情况下,我会被安排在整场演出的中间的位置,让观众有方便的时间。
我也并不在意,只当是对自己心智的磨炼,而且的确有效,在台上比从前“稳当”多了。在这一行里,一些膏粱子弟、名门之后,他们去电视台录像,台下配合的是虚拟的掌声,或者到哪个高等学府演一场,不管说得如何,现场一定火爆。但若在无人“保护”的环境下,场下稍有骚动,他们就会六神无主,稍错一句“纲”(话)(术语),就不知道后边如何接了。
他们所缺的是对心灵的蹂躏,有人把你的尊严踩在脚下,你就有机会在羞辱中得到涅槃。古人有句话说得很辨证——人贱才可无畏。那一晚,八点多了,还很冷清,观众席里空无一人,有演员撺掇着干脆去打牌。这时有一位刚刚“出浴”的大人物,据说是什么局的副局长,有人告诉他,二楼还有演出,要不要看。他说当然要看,于是搂着一位女郎窝在躺椅上。刘总说,不能得罪他,要演。有几个演员轻声嘀咕了几句,然后,一位练杂技的眨了眨三角眼,用手指指我,对刘总说:“让评书先上吧!”刘总看看我,说:“你们演员之间的事,自己决定吧。”于是,我被推上台。这位大 人物大概以为演员里会有女色,我一上来,他便有些倒胃,好在怀里搂着一个。以他的权势,这女人应当是他挑的。
要知道,男人的品位有所不同。他搂着的“小心肝儿”,激不起我任何的欲望。那女郎穿着黑色的比基尼,只一侧有吊带,脖子短粗,猩红的嘴唇一直在嚅动着,不知在和副局长说着什么。唯一的亮点是一部肥臀,副局长揉捏着,她则用手拍着客人的肩膀,好像在说:“你真坏,你真坏。”我在台上都替他们不好意思。说了十五分钟,二位可能一句也没听。侧面的楼窗开着,一阵凉风吹过,也许是觉得有点冷,他侧身把头压在女人的胸脯下,口中说“真热乎”。
我心里多少有点来气,说书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变大了,这下搅了客人的雅兴,他扭过头来,冲我大吼道:“小点儿声,妈的!”我已不是一年前的我了,这时觉得很轻松,走下台,来到棋牌室,告诉那几个正在用十块钱“豪赌”的演员:“我被哄下来了,你们上吧。”几个人把牌往桌上一扔,低声地骂着我,各自转动心思,要推出下一个倒霉蛋。这时,胡姐一拉我,“走,姐请你吃羊肉串儿。”
我点点头,说了一声“等我一下”,把湿透的大褂儿脱了,只穿背心,随着她走出后门。门外路边,支着个羊肉串儿摊子,胡姐买了二十串儿,分给我十三串。我说:“姐,买得太多了。”“你还小呢,还是长身体的时候,应该多吃。”胡姐转身,用手扶着膝盖,慢慢坐在台阶上,“小祝,做这一行要厚脸皮,别人说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等以后发达了,他们自然就会来巴结你。我知道,你和他们不一样。”我说:“姐,哪里不一样?”“你肯钻啊,而且你也不笨,有自己的想法。”“姐,给我提提意见吧。”她扬起头,一边咀嚼,一边在想。
“眼神,眼神不太好,不聚光,要练,每天多盯着一个地方看。”我忽然明白了自己从小到大老不合群儿的原因,为什么自己总看到人的缺点呢?夜色中,胡姐的眼睛仍旧浑浊,却能“说话”。“还有,声音也不太好,显得不饱满,你身体弱,可以多做做仰卧起坐,跑跑步。”她嘿嘿地笑:“你不要以为我很那个的,其实有些道理我也懂的。”她拍了拍胸口,“我老家在江西,我是老三,我家就我一个闯出来了。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场面也见过一些的,小祝,实话实说,这里算不错哦,我想在这里多干一段。”
她说的是实情,我见到过,在寒风中,立交桥下,十几个北漂艺人在等着,隔一两个小时,会来辆面包车,“穴头”打开车门,高嚷着“要杂技,魔术,再来仨唱歌的,三十,快点儿”。艺人们往车里挤,能上车的不是技艺最高的,而是力气最大的。经常为上车,艺人们大打出手,有人争得头破血流,只为了三十块钱,为了能吃几顿饱饭。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电视上所说的,改革开放之后,所谓文艺演出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胡姐说:“做了这么多年了,姐看过的人不少,小祝,你是有天分的。”这时,她把肉吃完了,把晶亮晶亮的签子举过了头,挥了挥,突然提高了几个调门:“小伙子,努力啊!有希望!”数年后,从别人口中得知,胡姐死于胰腺癌,终年五十一岁。那个被她供养上了大学的儿子,一提起母亲,便会暴怒大吼道:“我哪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妈!”
这才是天下最了不起的母亲。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曾听到过侮辱谩骂,曾见到过冷眼怒目,当我面对邪恶心存恐惧的时候,当我不得不和心爱的女人分开的时候,总会回想起那一幕——凉风习习的夏夜,胡姐坐在台阶上,把晶亮的签子举过头,挥动着,冲我大喊:“小伙子,努力啊!有希望!”
一个月后,刘总找我谈话,她说:“我不是说你的评书讲得不好,但确实是不符合我们的环境。”我说:“好的,我懂了。”她把公文夹抱在胸前,仿佛一直在用它保护自己,嘴角挂着微笑。记得那时她常教导我,“你在台上怎么不会笑呢?要培养自己的亲和力。”她当时的笑容,散发出的腥气,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多给你一次演出费,记住我就是你姐,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说话间,她把钱放进我的上衣的口袋。
“谢谢。”我学她的样子,歪歪头,笑了笑,退出屋门,把钱放在地上,说:“刘姐,我走了。” 气得她直跺脚。夜市上,人潮汹涌,讨价还价的声音 令人烦躁。我觉得,在这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还是有所得的。人可以通过看清别人,来了解自己。
此后,我在京城内辗转,不算夸口,所有的专门的曲艺演出场所,我都登过台,那时没拜师,因此,饱受欺凌。后台鱼龙混杂,这里有个怪现象,你越是对人谦和有礼,别人就越敢和你拍桌子瞪眼。终于,我明白,尊重下三滥,就是在贬低自己的人格。我学会了张嘴骂人。有时,用暴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是有效的。和人打架不可动气,气急败坏的情况下,宁可别打。要有心计,与人动手是有目的的。行有行规,下贱之人与世间道德相反,比方说在后台有人拿你的父母开玩笑,你若翻脸,别人还会说你是“空子”。最好的处理方法是走到他面前,盯着他笑笑,叮嘱他“注意安全”,然后转身离开。这样,他摸不着你的底,心里就会一直忐忑。我还是认为,人前挑衅,背后总去搬弄是非的人,大多是自认为是内行的外行,他们在台上绝没什么真本事,只好去钻营这些。真正的曲苑中人,深沉儒雅,可与大学教授比肩。我曾出入于夜总会、娱乐城,演完了,给多少是多少,不给,我拔腿就走,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真打起来,吃亏的一定是你。但有些场所根本不拿演员当人,我那时狂热地健身,为的就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保护自己。
我曾在各种曲艺小剧场待过,对这些剧场也算是颇有心得。若论曲艺的专门剧场,自德云社之前,北京也曾开设过很多,有些能坚持一两年,大部分数月就草草收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院团保守主义。一个团体承包一个剧场,本身就缺乏“叫得硬”的节目,但不希望请外援,因为角儿怕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2. 演员流动性过大。曲艺演出需要捧角儿,次次走马换将,观众怎么去捧?
3. 活路太窄。有的人说相声只会三段,他在专业团体,其实是“空子”,更要命的是,不会又不鼓励创新作品。
4. 演员之间互相倾轧,管事的难以协调。
5. 剧场方变本加厉地盘剥。
6.“杵头”(演出费)分配不合理。不管水平如何,所拿的酬金都一样,或论资排辈,青年演员受压制,才华得不到施展。
那时,每到周末下午,我必然要到剧场观摩。我说过,真正的行内人是讲义气的,常常靠他们把我带进去,若没有熟人,则会很狼狈。我也知道,每个园子少人看管的侧门在哪里,有时候,我可以从废弃的下水道钻到后院,再挂着一身脏泥出现在观众席。我和一些门口售票的大姐也认识,在没有领导监督的时候,她们悄悄冲我瞟一个眼神儿,我便像条游鱼似的,贴墙溜进包厢。那里价格昂贵,通常是没有人的,演出间隙,她们还会往里给我扔俩橘子。
每看一场高水平的演出,我都像充电一样。优秀的演员会有一种魅力磁场,他站在台上,观众就会感到滋润身心,作为要当演员的我,则受到他们气质的熏染。在湖广会馆,我曾见识过单弦大家张伯扬的儒雅风度;在北京音乐厅,我为姚雪芬老师情真意切的乐亭大鼓感动得落泪;在前门广德楼,袁阔成先生的神完气足,令我心潮澎湃。
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一代的演员,都曾受过一个人的影响,那便是后来威名远震的郭德纲。初见他,是在西琉璃厂的京味茶馆,在我的记忆里,那原本是个相声爱好者自娱自乐的场所,直到来了郭德纲,才有了大批真正的观众。当时为他捧哏的是王玥波,还有个叫王昊的演员,很有书卷气,后来看不到了。
郭德纲那时二十多岁,梳着三七分,演出的风格和现在大不一样。他是第一个让我乐得肚子疼的演员,但如今,他早已远远地超过了这个阶段,日臻化境。一段相声乐得次数过多是不对的,真正的大师,懂得“笑的生理规律”,当中要让观众有缓冲,并且会考虑整块活的完整性,但他那时的水准,已可让很多主流演员膜拜。真正抖响的包袱,像是在观众席里扔了个炸弹,“嘎”的一声,再四散而开,没抖响的包袱,观众会发出“嗤嗤”的声音,郭德纲没有不响的包袱,但常是两个“嘎,嘎”落在一起。
他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知道在台上还可以如此活络,如此机智,最重要的,他对艺术的热忱感染了所有人。有人说,郭德纲是为钱才说相声的,但若没有对这门艺术融入血骨的爱,他会在那样困苦的日子里坚持十年?你坚持一个让我看看?由于复杂的原因,他后来离开京味茶馆,几年后再见他,是在广德楼。我在后台侧幕看了他一场演出——观众瞧不见他的后背,全是湿的。
在他两脚周围,木质的台板上撒了一圈儿的汗,但他的激昂,让你相信,那一刻他是幸福的,虽然,观众席里只有十几个人。等到他下场了,我发现,他的气质有了明显的变化。脱下长衫,身上像洗了澡似的。他个子矮小,精神气儿却显得凛然挺拔,令人看着心头一振。男人什么时候最有魅力呢?就是为自己的事业拼搏得大汗淋漓的时候,全世界,都会为他倾倒。
有人觉得,郭德纲身上有“江湖气”,其实,他们哪里见过真正的江湖?那里深藏着一门高深的处世哲学。有位老艺人,在自己食不果腹时,穿得比谁都讲究——几千元笔挺的西装,老人头棕色的皮鞋擦得一尘不染,梳着背头,令人望而生畏。在火穴大赚时,我穿着皱皱巴巴,袖口上还有洞,故意几天不洗脸。业内人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意经。但郭德纲无论是穷困之时,还是在成功之日,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管别人是不是瞧得起我,我自己尊重我自己”。其实,他身上毛病也挺多,尤其是那一张利口,但我赞同孔庆东老师的话——郭德纲,是个英雄。
很长时间,郭德纲面前如有一座高山,就一个人向上攀爬,周围有无数只脚想把他从半山腰踹下去,他隐忍着,咬着牙,被踹下山底,再重新往上爬。我曾看到过他所受到的排挤、打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