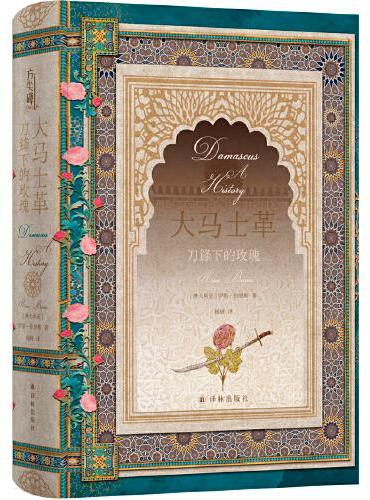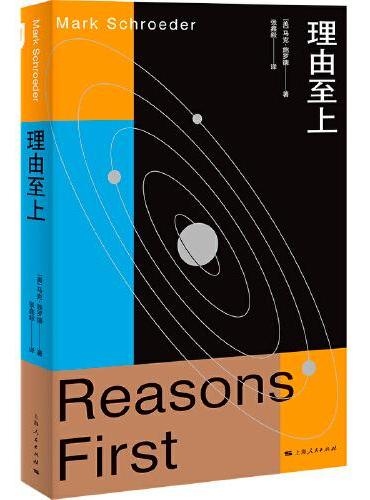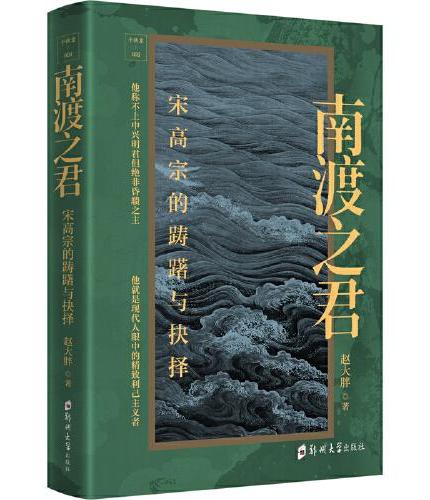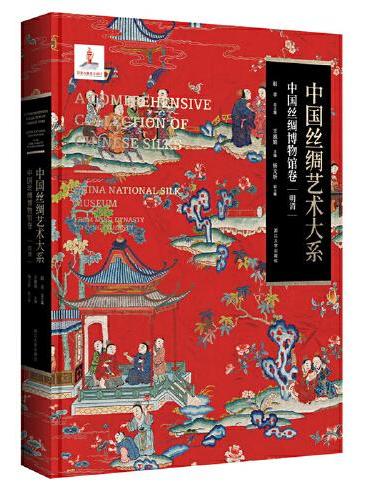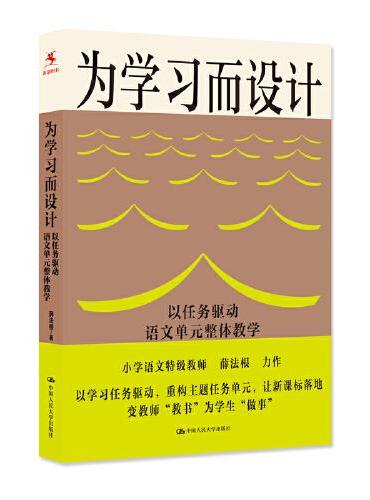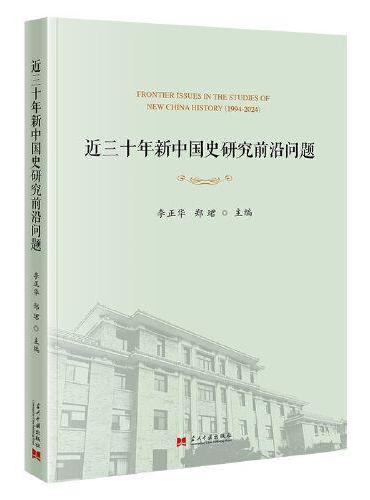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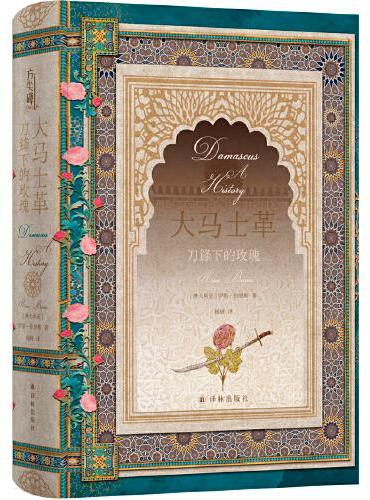
《
大马士革:刀锋下的玫瑰(方尖碑)
》
售價:NT$
607.0

《
造脸:整形外科的兴起(医学人文丛书)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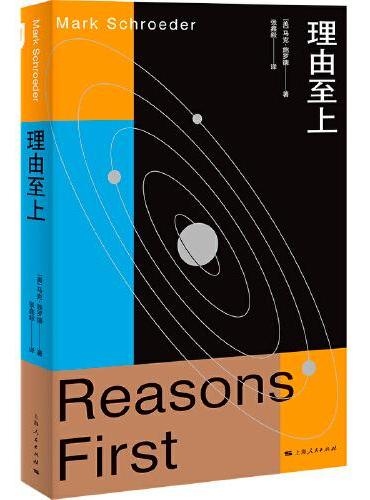
《
理由至上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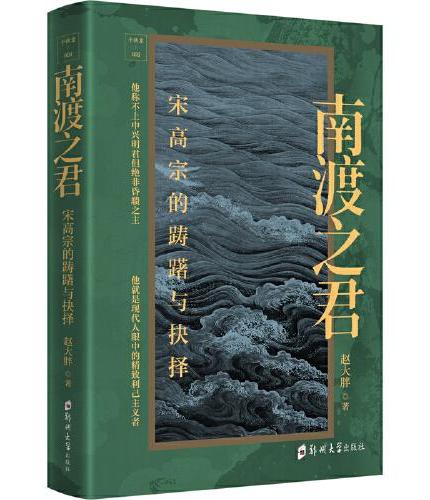
《
千秋堂丛书003:南渡之君——宋高宗的踌躇与抉择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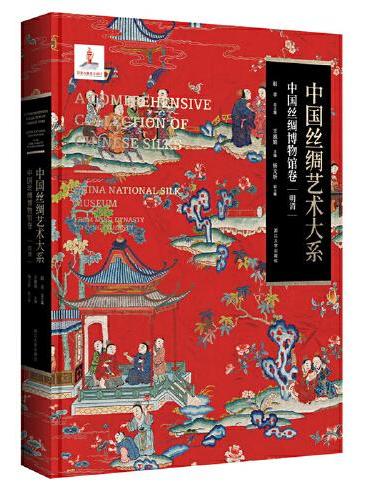
《
中国丝绸艺术大系·中国丝绸博物馆卷(明清)
》
售價:NT$
49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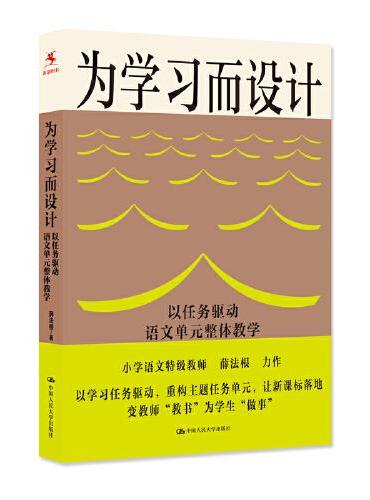
《
为学习而设计:以任务驱动语文单元整体教学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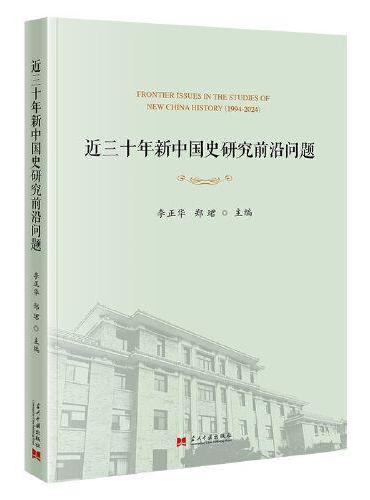
《
近三十年新中国史研究前沿问题
》
售價:NT$
500.0

《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
售價:NT$
449.0
|
| 內容簡介: |
|
“惜三十年来……所著书达五十余册,竟无一本能过于此者,悲夫。”这是陈传席先生在本版《六朝画论研究》的序中自叹,可见这本书在陈先生的心目中之地位。本书由八篇研究六朝画论的论文和八篇对六朝著名画论的标点、注译组成。八篇论文为:《重评顾恺之及其画论》《宗炳画山水序研究》《王微叙画研究》《论中国画之韵》《谢赫与古画品录的几个问题》《《姚最和续画品的几个问题》《山水松石格研究》《玄学与山水画》;八篇点校注译为:《论画》点校注译、《魏晋胜流画赞》点校注译、《画云台山记》点校注译、《画山水序》点校注译、《叙画》点校注译、《古画品录》点校注译、《续画品》点校注译、《山水松石格》点校注译。
|
| 關於作者: |
|
陈传席,著名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出版著作50余部,《中国山水画史》《六朝画论研究》《画坛点将录——评现代名家与大家》在读者中有很大影响。本社曾出版其散文集《北窗臆语》《悔晚斋臆语》(精装)。
|
| 目錄:
|
自序
原序
台湾版自序
一、重评顾恺之及其画论
一从谢赫《古画品录》谈起
二张彦远对顾恺之的评价
三关于顾恺之绘画创作的几个故事
四顾恺之和六朝几位画家的比较
五顾恺之的贡献主要在画论
六关于顾恺之三篇画论问题
七中国绘画在艺术上的彻底觉醒
八顾恺之传神论的产生
九顾恺之画论的影响和评价
二、《论画》点校注译
一《论画》点校注释
二《论画》译文
三、《魏晋胜流画赞》点校注译
一《魏晋胜流画赞》点校注释
二《魏晋胜流画赞》译文
四、《画云台山记》点校注译
一《画云台山记》点校注释
二《画云台山记》译文
附录:顾恺之介绍
五、宗炳《画山水序》研究
一最早的山水画论
二“道”、“理”、“神”、“灵”、“圣”
三山水画功能论
四写山水之神
五以形写形,以色貌色
六远小近大原理之发现
七道家思想的浸入——对后世画论和画的影响
六、《画山水序》点校注译
一《画山水序》点校注释
二《画山水序》译文
附录:宗炳介绍
七、王微《叙画》研究
一王微思想简说
二考王微《叙画》写于宗炳《画山水序》之后
三山水画功能论
四山水画是独立的艺术画科论
五写山水之神
六明神降之上
七明神降之下
八对后世文人画的影响
八、《叙画》点校注译
一《叙画》点校注释
二《叙画》译文
附录:王微介绍
九、论中国画之韵
一原“韵”
二韵和神的关系
三韵用于画之意义
四韵的含义之发展
五以气取韵为上
六“南宗”画尚韵说及韵与人格之修养
七结语 196
附录:原“气” 199
十、谢赫与《古画品录》的几个问题 203
一《古画品录》的原书名问题 203
二《古画品录》的著作权问题 205
三谢赫及其著书年代问题 206
四谢赫的理论和实践之对抗性问题 208
五“六法”句读标点问题 211
六骨法—传神—气韵 212
十一、《古画品录》点校注译 213
一《古画品录》点校注释 214
二《古画品录》译文 253
十二、姚最和《续画品》的几个问题 259
一姚最的生平和思想 259
二《续画品》的著作年代 262
三《续画品》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63
十三、《续画品》点校注译 268
一《续画品》点校注释 268
二《续画品》译文 304
十四、《山水松石格》研究 310
一《山水松石格》的作者和年代 310
二《山水松石格》的贡献及其影响 313
三色彩的研究和破墨的提出 320
十五、《山水松石格》点校注译 322
一《山水松石格》点校注释 322
二《山水松石格》译文 331
十六、玄学与山水画 332
附录一:云冈石窟雕刻 338
附录二:戴逵、戴颙在雕塑史上的地位 343
后记 347
|
| 內容試閱:
|
一、重评顾恺之及其画论
顾恺之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位极有影响的人物。然而古今论者对其评价却是误解甚多。一位对顾恺之素有研究的专家就说过:“(顾恺之)在中国的画学演进史上是开山祖,在中国的山水画史上也是一位独辟弘途的功臣,他不但代表了第四世纪初叶前后的画坛,今日看起来,也许足以称为第七世纪以前的惟一大家。”①论者多指顾恺之的画而言。如是,则如群星灿烂的六朝其他画家皆成附属,热烈的古代画坛顿显寂寞。其实,顾恺之的主要贡献在画论。因无可靠的画迹存世,对他的画难作结论。但把他的画称为六朝最杰出的,却是没有根据的。
本文前四节主要是对今人错误理解古代文献的廓清,其次借评顾恺之以理清六朝绘画发展的一些经过,包括对唐及唐以后的影响。
第五至第九节围绕顾恺之的画论问题,作再评价。我总觉得以前一些文章对顾恺之画论的意义认识不足,有很多问题尚须进一步研究。而研究六朝绘画,其重点亦应在画论,因为它不仅影响了以后千余年的绘画,同时也对以后的文学、哲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启导作用。
本文试而论之,凡是别人谈过,而我没有补充或不同意见的,便略而不谈。或因孤陋寡闻而致误者,恳请专家批评。
(一)从谢赫《古画品录》谈起
1.要重视谢赫的结论
六朝绘画评论家不止一人,还有一些非专门家,但却是显赫一时的人物,对顾恺之也作了不同程度的评价。然而评论者之中水平最高、态度最认真的当首推名垂画史的权威评论家谢赫,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以前论者对谢赫的理解却误会的多,甚至对他的品评有完全颠倒的理解。倘能真正地理解谢赫,那么,理解顾恺之就有了头绪。
谢赫提出的“六法论”,至今还在绘画创作和评论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谢赫之后的评论家无不根据“六法”来论述绘画,所以在顾恺之之后、张彦远之前这四百年间,谢赫作为一个评论家还真正是“分庭抗礼,未见其人”。对于这样一个高明的评论家,他的话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
谢赫把孙吴至南梁中大通四年(532年)之间的二十七(原二十八)位画家的作品列为六品。把陆探微的画列为第一品,又第一名。说陆的画:“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但价重之极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这段话大意是说陆的画把人物的气韵彻底地表达出来了,生动之至,绝不在非本质的问题上下功夫……他的画价重达到了顶点。上品之外,又没有等第可言,所以列在第一等。陆的画被列为第一等第一名,谢赫认为还太委屈了。而顾恺之的画只被列为第三品,还在姚昙度之下,和陆的画差距如此之大,甚至连被列为第三品第一名的姚昙度,得到的评价也比顾恺之高得多。谢赫是亲眼看到他们的画之后才评论的。谢赫对顾恺之评价低到如此程度,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2.顾恺之的名望
谢赫的品评之所以未成定鉴,是因为顾恺之的名望太高。顾本是当时社会的名流,他被誉为:“才绝、痴绝、画绝”。《世说新语》和《诗品》中提到顾恺之“才绝”的地方,多是赞美他的文才。从他的现存诗赋看,他的文才确是很高的,《诗品》称:“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文虽不多,气调警拔。”乃至于把顾诗评在曹操、班固之上。
所谓“痴绝”实则是他的保身哲学。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晋宋文人装“痴”而逃避政治以自保,是不乏其例的。从记载看,顾的“痴”真可谓“绝”矣。
在绘画方面,最早推祟他的人是谢安。谢安是晋代王、谢世族中最为显赫的人物,也是掌握国家命运的关键人物,淝水之战,他指挥将帅,大破苻坚,保住了偏安江南的晋室。他一生除了处理军国大事外,便喜下棋吟咏,携妓游赏,是当时人们议论的中心人物。谢安未掌握国家大权之前,曾为桓温的部将,而顾恺之当时也是桓温的部将,且二人在同一幕府中供事。但顾和桓温的关系更为亲昵。当时尚依靠桓温的谢安说顾的画“苍生以来,未之有也”。
到底是什么场合下讲的?是出于什么目的?是客气话,是漫与之语,还是认真之语,我们可以作各种分析。但不论怎么说,谢安不是专门评论家。他的话绝没有谢赫的话有分量。但在当时,谢安的影响却是超过任何一个评论家的,他的话“分量”之重是不言而喻的。连他的鼻子有疾病,讲话音浊都有人(包括名流)用手掩鼻跟着仿效(见《谢安传》)。他“推崇”顾恺之的话,一经传出,其影响之大,乃可想见。人贵耳贱目,乃是通病。在当时,陆探微、张僧繇这些画家还未出现,曹不兴的画仅有一幅龙头,还深藏在秘府里。戴逵又隐居,且拒绝和统治者合作,甚至斥责他们,当然不会得到他们宣扬。顾一生喜爱和权贵人物打交道,附和喧闹之声也就愈高。但遇到谢赫这样一位眼光高超的评论家,就很难被这一片鼓噪之声所迷惑,这就显示出谢赫的不同流俗的见解。
但谢赫把一个本来声望极高的画家评到如此之低,惊动是很大的,第一个奋起反对的便是姚最①。
3. 姚最的品评
姚最在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尤其是评论作风,和谢赫相比,相差太大。而且姚最不是画家,也不是专业评论家,他“校书于麟趾殿”,又“习医术”,又参与政治斗争,最后死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见《周书》卷四十七)。
姚最著《续画品》时年仅十五岁或至多二十岁左右(参见本书十二《姚最和〈续画品〉几个问题》)。而谢赫著书时已是富有经验的老评论家了。当然,我们既不欺无名,也不因人废言,而应看看他讲得是否有道理。他说:“顾公之美,独擅往策,荀、卫、曹、张,方之蔑然,如负日月,似得神明,慨抱玉之徒勤,悲曲高而绝唱,分庭抗礼,未见其人,谢云‘声过其实’,可为于邑。”②说来说去,还是从顾的名望来论述和分辨,什么道理也未讲出来,而顾的画到底什么样子,到底有哪些优点,其他人的画有哪些缺点,不得而知,这就很难使人信服。
姚最一是根据名望来评价艺术;其次是根据地位评人和艺术,翻开他的《续画品》,第一个画家便是湘东殿下,即后来的梁元帝萧绎,姚最把他吹得天花乱坠,说他“天挺命世,幼禀生知”,“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斯乃听讼部领之隙,文谈众艺之余,时复遇物援毫,造次惊绝,足使荀、卫阁笔,袁、陆韬翰”。这就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因而,他对梁元帝的评价也未得到其他人的赞许。而荀勖、卫协、袁倩和陆探微的绘画地位也一直是超过萧绎的。
姚最论画的水平本来就大逊于谢赫,态度又那么不严肃,他对谢赫的反驳更未讲出任何道理,当然也就不能轻信。比较起来,也还应该说谢赫的话更有分量。〔补注:此文写于1980年,尔后,我对姚最的评价略有改变,然亦仅限于他的画论成就方面。〕
4.谢赫的品评
姚最之后,还有几位评论家如唐代的张怀瓘、李嗣真等也是反对谢赫之说的,但大多囿于顾的名气,皆未讲出什么道理。
谢赫把声名昭日月的顾恺之列为第三品,把皇帝的画列为第五品,是不是专和名人作对呢?不然。我们看第一品陆探微之下就是曹不兴,谢赫评:“观其风骨,名岂虚成?”可见曹不兴虽然大名鼎鼎,谢赫还是赞许的,承认他名副其实。第一品中的荀勖更是显赫于魏晋二代的有权有势的贵族画家(荀勖是司马氏集团中重要成员,在平蜀决策中,他起到重要作用。《晋书》有传)。谢赫评画决不因地位高低、名望大小而论其品第。下面让我们再认真看看谢赫对顾的评价有没有道理。谢云:“深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逮意,声过其实。”“深体精微”,是说顾对于绘画中所应要表现的内容体验得深刻,很精确,很微妙。这主要是指他的画论而言的。“笔无妄下”是说他不随便下笔,下笔便非常认真慎重。他画人数日不点睛,他画云台山,预先把构思写成文字,反复推敲,可见其认真而笔无妄下的程度。“迹不逮意”是说他的画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图,不能达到他所要追求的意境。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我们仍能看到,不正可以证实谢赫之论的确然吗?这卷画第一幅中的汉元帝,就不具和熊搏斗的神态,二昭仪也不具惊恐之神态。“同衾以疑”一幅,男女坐床上,直不知所云。所以张怀瓘说:“不可以画图间求。”一接触到顾的画,也就会有谢赫的“声过其实”之感了。名声超过他的实际,谢赫本来也是听闻到顾的声名的,但一看到他的画,大失所望,才作出这样的评价。
谢赫的四句话,决非空泛的议论,也不是不合实际的捧场以及无聊的攻击。
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评鉴的二十七人,除顾一人之外,其他历来都被公认为是公允的,然而正是对顾恺之这位当时“如负日月,似得神明”的画家的画,他能不随众议,正确地道出它的长处和短处,把它放在第三品姚昙度之下,才显示出他在评论上的卓越造诣、正派学风和超人胆量。谢赫不愧为伟大的评论家。对这样一位伟大的评论家的品评,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庸才批评天才从来都是常见的事,“后之浅俗”对谢赫的批评乃是一例,但决不可以此否认天才而附和庸才。
(二)张彦远对顾恺之的评价
1.历来对张彦远评顾的歪曲要廓清
中国古代绘画评论家,谢赫之后,最伟大的人物当推唐代的张彦远,这是众所周知的。张彦远生于三世宰相之家,藏画巨富,可与秘府相当。他鉴赏精到,理论高妙,其《历代名画记》被后人誉为“画史之祖”。至于张氏成就之高,不须多说,需要论及的是,后世评论家和画家多借张彦远为“锺馗”以“镇鬼”。有人说:“谢赫对顾恺之的评价引起后世的强烈不满,特别遭到张彦远的不满”。有人说:“张彦远……几乎把顾恺之推祟到最高的境地了。”有人说:“张彦远其实通篇文字推崇得最高的唯顾一人而已。”有人说:“张彦远谓顾恺之是‘天然绝伦,评者不敢一二’的最杰出的画家。”有人说:“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亦赞扬顾之作品为‘天然绝伦’……”
在国外,如金原省吾的《支那绘画史》等书也都是这样理解张彦远的。这都是误解,必须廓清。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顾恺之的地方很多。专门发表对顾恺之评价的有两处。其一是卷二《论师资传授南北时代》,此篇开头专谈顾恺之,所占篇幅最多。其二是卷五《晋·顾恺之》条。只要认真读一读这两篇文字,读懂了,就会知道张彦远非但没有把顾恺之推崇到最高地步,而且对过高推崇顾的话,几乎是一一加以驳斥,甚至讽刺并表示气愤。
一、卷二《论师资传授南北时代》是张彦远在书中第一次评顾“自古论画者,以顾生之迹,天然绝伦,评者不敢一二”。明明是“自古论画者”的观点,而不是张彦远本人的观点,论者多断章取义认为是张彦远推崇顾恺之“天然绝伦”,何颠倒也。接着下半句:“余见顾生评论魏晋画人深自推挹卫协,即知卫不下于顾矣。”好了,“卫不下于顾”,便是张彦远第一个结论,很清楚,张彦远认为卫协不在顾恺之之下。
再接着:“只如狸骨之方,右军叹重,龙头之画,谢赫推高,名贤许可,岂肯容易?后之浅俗,安能察之?详观谢赫评量,最为允惬;姚李品藻,有所未安(原注:姚最、李嗣真也)。”这段话大意是:像书法中的《狸骨帖》一样,被王羲之赞叹,又像绘画中的龙头之图被谢赫推崇,名贤许可,难道是容易的吗?后之浅俗(指反对谢赫评量的姚最、李嗣真等人)怎么能看出来呢?详细分析谢赫的评价和品第,最为公允恰当,姚最和李嗣真的品藻使我感到不安。这里张彦远维持谢赫的“原判”态度明白如火,可见“谢赫对顾恺之的评论遭到张彦远强烈反对”的说法与事实绝对不符。
再接着:“李驳谢云‘卫不合在顾之上’,全是不知根本,良可于悒。”张彦远的态度一层比一层强烈,他对李嗣真驳斥谢赫说“卫不合在顾之上”的话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全是不知根本”。
张彦远气愤之余,并对当时评论书画优劣,不察真情实际,依声望而妄相附和的作风,大加痛骂:“今言书画,一向吠声。”“吠声”一词出自《潜夫论·贤难第五》(中华书局版彭铎校正本四十九页):“谚云:‘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伤世之不察真伪之情也……”一只狗见其形影乱叫,其他的狗连形影皆未见,便跟着声音乱叫起来。这就是张彦远对待吹捧者的态度,讲得虽重些,但也表达了他鲜明的立场。
二、卷五《顾恺之》条下,此节因收有顾的三篇画论,所占篇幅最多。然出自张对顾赞美之词只有十五个字:“多才艺,尤工丹青,传写形势,莫不妙绝。”这样的词只是对一般画家的赞美词。如:“吴王赵夫人……善书画,巧妙无双”;“康昕……画又为妙绝”;“王濛……丹青甚妙,颇希高达”。这些画家都是画史上毫无影响的少闻者,张亦称其“妙绝”,所以这句话决非张对顾的倾倒之词。
其他的赞美之词皆非张彦远之语,其中姚最和李嗣真对顾的推崇最高,也最坚决。姚最的话,张在卷二作了强烈的反对,此处毋须赘言。李嗣真“以顾之才流”来强调顾的画“独立亡偶”,不应列于下品,张彦远又一次针锋相对,给以批判说:“彦远以本评绘画,岂问才流?李大夫之言失矣。”驳了李嗣真:张对顾之态度亦尽藏于不言之中。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两处专谈顾恺之的地方,都表达了他的基本立场是鲜明的。至此,我们可以说,所谓张彦远反对谢赫评顾之说和推崇顾恺之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
三、尚有一段话被人误解得最深。张彦远曾对顾恺之创作的《维摩诘图》表示欣赏和赞叹,这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犹如一位二流的诗人偶尔以自己熟悉的题材写出的诗超过一流诗人的某些诗句,是常见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不是最得妙理吗?但许浑仍然不是一流诗人。“维摩诘”是六朝名士的形象,顾最熟悉。更重要的是,张彦远讲这段话是为了阐述“榻写”上的一个问题。题目是《论画体、工用、榻写》,他说的内容是在“榻写”部分,和“榻写”有关,很多论者误解了张的本意。张说的“顾生首创《维摩诘像》……陆与张皆效之,终不及矣”,本意是说画家作画贵在创新,仿效终不及“首创”,顾“首创”了一种新形式的“维摩诘像”,就值得推崇。陆与张在《维摩诘像》上没有新的突破,乃是仿效顾的形式,就终不及顾的创新精神可佳了。张彦远一贯反对因袭,提倡创新,在《论画六法》中他强调“至于传模移写,乃画家末事”,本节“论榻写”中,又一次强调自己对模写与首创的态度。
我们必须注意作家论说的场合,“榻写”一段必和榻写、临摹有关,不可以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强加给作家。张彦远这段话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连他自己也预料到的,所以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他在后面又加上一段解释:“张墨、陆探微、张僧繇并画《维摩诘居士》终不及顾之所创者也。”他们或仿外国的形式,或仿前人的形式,而缺乏创造性。注意顾是“首创”、“所创”,其余人是“皆效”“并画”,原文中“顾生首创……陆与张皆效之,终不及矣”,意已表达尽致,为什么又加上这个解释呢?原是怕引起人们的误会,反复解释,张氏用心可谓良苦。然而越是害怕和担心的事,越是容易出现。
补充说明一个问题。记载中亲眼见过顾恺之的画的人,还有张彦远的祖上高平公,他于元和十三年呈献一大批书画真迹给皇帝,其中有顾、陆、张、郑等“名手画合三十卷”,他说:“前件书画,历代共宝,最称珍绝,其陆探微《萧史图》妙冠一时,名居上品。”按常理,应提顾画为代表,因为顾早于陆,且名气大,实际上他只提到陆的一张画为代表,而不提顾,优劣高下,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见卷一)。
认真考察一下张彦远对顾恺之的评价。其一是认为谢赫把顾的画列为第三品,最为允惬,并驳斥那些过奖顾画的人,这种态度是很鲜明的。其二是认为顾和陆、张等人平等皆为六朝第一流大画家,这是张彦远评论他人时顺便给顾的最高评价。张对顾的这种最高评价并非出于诚心,即使如此,他也不肯自己直接出面,而借他人之口。由于顾的影响,书中也多次提到,但在关键时刻,他决不肯给顾过高评价,还时时设法抵消顾的影响,卷五《王廙》条下称王过江后,为晋代书画第一。这就否认了顾为第一了(连东晋第一都不许)。
在卫协条下:“彦远以卫协品第在顾生之上,初恐未安”,但结果还是“不妨顾在卫之下,荀又居顾之上”。这里他又把顾放在荀、卫之下,何鲜明也。
综而观之,他否认顾为第一流画家的地方多,态度也鲜明。但张决没有把顾作为六朝惟一大家来评论过,这是真的。
2.《历代名画记》中“品第”问题之研究
张彦远既然不承认顾恺之是第一流大画家,也就是说他认为顾的画不是第一流的作品,那么在卷五顾恺之条下,为什么注上“上品上”的等第呢?这个“上品上”,倘若是张彦远的观点,当然不会是随意挥写的漫与之语。为此,我研究了《历代名画记》一书中的“品第”问题。原来,所有的“品第”皆不是张彦远本人的观点,而是当时或稍前评论家的评品。张彦远采取当时多数人的看法注上,即使错了,也不加改动,但另加说明,即如今之“校正”。有的观点和张彦远的观点相反,有的相差较多,有的相差少许,当然也有部分不谋而合。不同的观点,有一部分张彦远在专门论述中加以说明,有一部分虽然照录在前,但在后面加上“彦远按”、“彦远云”、“彦远曰”等字样。凡有“彦远按”之类字样的内容,才是彦远本来的观点。兹考如下:
一、画家中,凡是前人未有“品第”的,张彦远一律不自加“品第”。如卷六南朝宋代画家谢庄(字希逸),书中记载的,在他前前后后的画家皆有“品第”,惟他无“品第”;还有记载中的南陈惟一画家顾野王,亦无“品第”,这是什么道理呢?张彦远在卷一中说得清楚:“如宋朝谢希逸,陈朝顾野王之流,当时能画,评品不载。”这两位画家在前代画史中无专门记载,当然也就不会有“评品”,张彦远“探于史传”(卷一),从《宋书》和《陈书》中,了解到这两位画家,列于画史。如果品第皆是张彦远的“品第”,这两个画家理应加注“品第”,可见“品第”皆前人“品第”,而非张氏“品第”。
还有后魏、北齐部分画家亦无品第,即是张所说的“顾野王之流,当时能画,评品不载”。从张注的“见后魏书”、“见三国典略”等字可知,这些画家都是张从正史书中探求而知,史书上当然不会有“品第”,张亦不再加注“品第”。
二、书中记载的画家前部分轩辕、周、齐、秦、汉的画家皆无“品第”,卷九唐代画家陈义以后的画家亦皆无品第。像吴道子这样的大画家,张彦远推崇极高,如果他要加注“品第”的话,会毫不犹豫地加上“上品上”,但前人未加,他也就未记。还有卷十所有画家皆无品第,因为这些画家皆彦远“旁求”而得知(陈义、吴道子之后的画家大都晚于李嗣真、张怀瓘,时人尚无品评)。
三、在后汉赵岐之后、唐代杨德绍之前共一百六十八人左右,不加注“品第”的是六十人左右;全书三百七十余人,加注“品第”的画家是一百零五人左右。
第一个加注“品第”的画家是后汉的蔡邕,品第亦非彦远所为,乃是来自唐中书舍人裴孝源的品评,张彦远自注云:“裴孝源所定品第云:伯喈在‘下品’。”第一个画家的品第,彦远注明出处。以后的“品第”皆不注出处。
四、在卷六南朝宋代画家史敬文以后十九名画家中有十八名加注“品第”,独范惟贤没有“品第”,其原因张彦远在下面注说中讲得清楚:“诸家并不载品第。”彦远就不能记,亦未自加。这里又见“品第”是前人的“品第”,而非张氏本人的“品第”。
五、有些“品第”,张彦远是不赞成的,但他并不擅自改动,而在下面说明,即用“彦远按”“彦远曰”等类字样。比如卷四中的曹不兴,谢赫评为第一品,但李嗣真云:“不兴以一蝇辄擅重价,列于上品,恐为未当。”彦远立即加以驳斥云:“李大夫之论,不亦迂阔。”彦远认为:“不兴画名冠绝当时。”按彦远之论,理应列为上品,至少应列于上品中吧?但因为李嗣真不赞成列为上品(李嗣真的品评在当时可能有很大影响),彦远仍然采取当时之论加注“中品上”,而不加“上品”的“品第”。
六、在宗炳、王微条下加注“下品”和“中品”,品第是不高的。而实际上彦远对宗、王评品是很高的,他说:“宗公高士也,飘然物外情,不可以俗画传其意旨。”“宗炳、王微皆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而俱适,纵烟霞而独往。各有画序,意远迹高,不知画者难可与论。”通览全书,可知宗、王在张氏心目中有更高的地位,在《论画六法》一节中张氏坚认:“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动一时,传芳千祀。”彦远论宗、王,正是他理想中的“善画者”——“逸士高人”。然而他仍加注为“下品”、“中品”,这就决非张氏本意了。
七、卷八“郑法士”条,彦远认为“郑合在杨(子华)上”。而“郑法士”条下加注“中品上”的“品第”,并没有在杨子华之上,原来又是按李嗣真的品第“在上品杨子华下”。彦远虽“以李大夫所评郑在杨下,此非允当”,却仍加注于低于“上品”的“品第”。但杨子华的画也未有按照李嗣真的说法注为“上品”,却和郑法士一样的“中品上”,估计李嗣真品评杨为“上品”,品郑为“中品上”,但张怀瓘(略晚于李嗣真)又品杨、郑皆为“中品上”,张彦远的“品第”可能是采取较近的一种说法。当然也有李评张未评或张评李未评的,张加注的品第到底是采取哪些人的说法,如何取法,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不过有些问题不论怎样研究,也不如他自己说得清楚。张彦远编写这本《历代名画记》包括其中加注的“品第”,他自己有一个总的原则,卷一中他明白地告诉读者:“彦远……聊因暇日,编为此记,且撮诸评品,用明乎所业,亦探于史传,以广其所知。”“撮诸评品”的“撮”是“采取”的意思。所以,凡加注的“品第”皆是采取“诸评品”,而不是彦远的“自评品”。
不仅“品第”如此,连一些不该列于画史的画家,他也按照前人的记载照编不误,如卷七南齐丁光,仅能画蝉雀,且笔迹轻羸,又乏其生气。彦远按云:“若以蝉雀微艺,况又轻羸,则猥厕画流,固有惭色。”这样的人,如按彦远自己的意思,就不应列于画史了,但旧录有名,彦远为了“以广其所知”,仍旧“编次无差”。
问题搞清楚了,我们便可以知道,加在顾恺之条下的“上品上”,也是“诸评品”之一,而不是张彦远的“评品”。
继《历代名画记》之后,宋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其序中说:“昔唐张彦远尝著《历代名画记》,其间自黄帝时史皇而下,总括画人姓名,绝笔于永昌元年。”这段话中惟“永昌元年”为误记,其他意思表达得皆很准确。
但继《图画见闻志》之后,宋邓椿作《画继》,其序中,在“唐张彦远总括画人姓名”之后,无故加上“品而第之”四字,完全曲解了张彦远,真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了。
(三)关于顾恺之绘画创作的几个故事
关于顾恺之绘画创作的几个故事,见于《晋书·本传》,亦见于《历代名画记》,它一直为论者所津津乐道、称赞不衰。若稍作分析,亦颇有趣。
其一,顾“画裴楷真,颊上加三毛,云:楷俊朗有识具,此正是其识具,观者详之,定觉神明殊胜”。裴楷颊上有没有三毛,不得而知,但为了表现裴楷的“俊朗”,只是靠加三毛的办法,也值得称赞不绝?南宋陈郁在《话腴》中说:“写照非画物比,盖写形不难,写心唯难也。”肖像画理应在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上下功夫,顾恺之自己也十分强调“传神”,“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而不在三毛。六朝文士皆知道这一点,《世说新语·排调》有一段话谓:“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生坐,瞻瞩甚高。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须发何关乎神明?”对于肖像画的传神来说,三毛只是不关乎神明的非本质内容,除非传神的技巧不高,才只好以此区别对象,这是不言而喻的。岂有称道或提倡之理?
其二是“又画谢幼舆于一岩里,人问所以,顾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岩壑中。”“一丘一壑”何谓?众说纷纭,多数论者认为是“喜爱游山”和“自比丘壑”的意思,两说皆含糊。据《晋书》所载,谢鲲(幼舆)是一个以“远畅而恬于荣辱”闻名的人,他“通简有意识”,王敦“以其名高雅相宾礼”,“尝使至都,明帝在东宫见之,甚相亲重,问曰:‘论者以君方(比)庾亮,自谓何如?’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鲲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一丘一壑”和“庙堂”相对,表达了谢不专务庙堂,“远畅而恬于荣辱”的“清高放达”品格。
为了刻画这样一个人物性格,将其形象放置在岩壑中,就行了吗?而在岩壑中的人是否都是“远畅而恬于荣辱”呢?梁楷画《李白像》,毫无背景,寥寥数笔,把李白那种“一生好入名山游”、“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旷达神态表现得很精到。诚然,肖像画不是绝对不能画复杂的背景,但关键是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的刻画。以背景衬托,毕竟不是肖像画的根本。
其三,“画人尝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亡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认识到点睛是传神的关键,无疑是对的,点睛要格外慎重,也是必要的,但数年不点,未免孟浪。我们看吴道子作画“数仞之画,或自臂起,或从足先,巨壮诡怪,肤脉连结”,“与乎庖丁发硎,郢匠运斤”(《历代名画记》)。张彦远认为“真画一划,见其生气。夫运思挥毫,自以为画,则愈失于画矣”(同上)。苏东坡谓吴道子:“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张怀瓘云:“吴生之画,下笔有神。”再关键的地方,只要技巧纯熟,“点画信手烦推求”,岂需数年时间?当然技巧不高,那就要反复琢磨、试画,甚至要涂改,所需时间亦长,但欲得其生气,恐亦难矣,张彦远谓之“死画”。
顾恺之作为一个大理论家,作画的得失,他是十分清楚的,然而技巧上的拘限,给他的创作造成了逆境。以上三个故事,便是活证。所以,谢赫说他“迹不逮意”是言之有据的。
(四)顾恺之和六朝几位画家的比较
1.顾恺之和戴逵的比较
戴逵和顾是同时人,据《晋书》卷九十四《戴逵列传》推算,戴年长顾至少十岁①。且戴少年时代书画等艺即有惊人的才华。与顾比:
其一,据《历代名画记》卷五所载:“晋明帝、卫协皆善画像,未尽其妙,洎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释氏,范金赋采,动有楷模。”戴画成为楷模,而同时的顾画却未成为楷模。这里说的楷模主要是佛教画。《宋书·戴颙传》:“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晋以后中国画几乎被佛画所独占,戴逵创造的佛像楷模为绘画和雕塑家所师法,“其后北齐曹仲达,梁朝张僧繇,唐吴道子、周昉,各有损益……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斯万古不易矣”。由是观之,著名的“四家样”乃是在戴逵的“楷模”上发展起来的。戴逵首先把佛像的创造推向一个理想境界,风靡全国,直至曹、张出,其间一百五十余年,皆是戴逵的“楷模”。顾的佛画和他擅长的肖像画之影响,就没有这么大。
其二,谢赫评戴:“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善图贤圣,百工所范。荀、卫以后,实为领袖。”但谢也把戴画评为第三品,不知是何道理。他说戴画为“百工所范”、“实为领袖”(可与张彦远评其为“楷模”相印证),决不会假。顾虽画冠冕胜戴(孙畅之语),因戴从来不画冠冕。但任何书中皆不见顾在绘画方面有领袖地位。
其三,顾恺之《论画》一文评戴逵:《七贤》“以比前诸竹林之画,莫能及者”。顾也画过“七贤图”,可能受了戴的影响,顾又称戴画的《临深履薄图》:“兢战之形,异佳有裁”。戴画不仅为“百工所范”,连上层一些知识分子也是佩服的。谢安原只知道顾恺之,不了解戴逵,本很轻视他,但听到戴“说琴画愈妙”,也不得不佩服①。
其四,中国古代绘画遗存最多的是佛教画,实际上,从魏晋始至唐绘画也主要是佛教画。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变化过程,就是人物造型及内心世界的刻画,渐渐世俗化,这是艺术的一条正确道路,戴逵是走在这条正确道路上的前导。《历代名画记》“戴逵”条下:“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庾道秀看之,语戴云:‘神犹太俗,盖卿世情未尽耳。’戴云:‘惟务光当免卿此语耳。’”(《世说新语·巧艺》亦有同样记载,但庾道秀作庾道季。按以“季”为是)从庾道季评戴画话中可知,戴画已经世俗化了。在此之前的画恐怕大多都有点公式化(主要是外来样式)。庾说戴画的“人”太世俗气,是因戴本身世情未尽故,也就是说戴的精神气质反映到绘画中去了。戴不接受庾的批评,反驳说:“惟务光当免卿此语耳②。”二人的意见是不相容的,但反映的实质是一致的,戴逵的画已经世俗化了,戴逵的精神气质已经反映到作品中去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戴为艺术走向正确的道路建立了功勋。从记载来看,在绘画上对后世的重大影响,顾在几个方面都逊于戴逵。
2.顾恺之和陆探微、张僧繇的比较
陆、张对中国画线条发展的贡献
中国画中线条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画发展到唐及唐以后,山水画占主流地位,其一派是金碧山水,如李思训之流用细匀无变化的线条勾勒出轮廓,填以青绿颜色,这派山水是魏晋以来的山水画形式发展到最高阶段的标志。另一派是水墨山水,始于吴道子。吴纯用墨线,磊落逸势,“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气韵雄壮,几不容于缣素”。这就打破了山水画中的精雕细刻的青绿形式。其后经王维、张璪等人的努力,水墨山水遂占山水画的主流。吴之后山水画技法渐渐丰富,勾、皴、点、染,表现力比吴之前的勾线填色强得多。虽然这一种山水到五代、宋才成熟,但变化改革的关键人物是吴道子。吴改革山水画,首先打破了战国秦汉以来占画坛主流的所谓“春蚕吐丝”一类的线条。“春蚕吐丝”如发丝一样细匀,无粗细变化,到了李思训画中,其作用已尽,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改革这种线条,山水画恐怕就要停止在李思训的阶段,再要前进就缓慢了。
吴道子的人物画在西安碑林中尚有摹刻石碑“观音像”,用的是兰叶描兼蚯蚓描,粗细随意,变化多端。如张彦远记载:“离、披、点、画,时见缺落。”只有这样的线条(包括点画),应用到山水画上才能启示画家继续变化发展,继而产生多样的勾皴擦点,使山石的量块、质感充分地表达出来。
吴的线条是继承张僧繇而有所发展。张怀瓘说吴是“张僧繇后身”,张彦远谓此“可谓知言”。据文献记载,张僧繇最早解放了“春蚕吐丝”式线条,开创了“点、曳、斫、拂”的形式。而张的“点、曳、斫、拂”和“春蚕吐丝”之间乃是南朝宋的陆探微的“精利润媚”。陆的“精利润媚”之所以“新奇妙绝”(张彦远语),因为它已不是“春蚕吐丝”式的单调,其精而利,润且媚,乃是张僧繇改革传统线条的先声。
“春蚕吐丝”式线条亦不始于顾,战国时已有之,马王堆西汉帛画证明,这种线条到西汉已经成熟。历东汉,逾三国,经西晋,至东晋还是这种线条,顾恺之就没有改革它(这种线条格调高古,有其优点,但勾勒山石、树木及所有人物、动物都用这一种线条就有缺憾)。
顾恺之也研究书法,常和大书法家论书,但他就没有把新的书法的用笔用到绘画中去。“春蚕吐丝”线条近于篆但与晋及晋前的隶行草等书法都无关。
《历代名画记》明确记载的第一个吸收书法用笔于绘画的乃是陆探微,其次是张僧繇,“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吴道子“援笔法于张旭”,亦借鉴于书法,和陆、张一脉相承。我们看初唐以后到五代、两宋、元、明、清的绘画,其中各种线描以及勾、皴、点、染、破墨、泼墨,等等,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越来越丰富,而唐以前,除极少数画(其中包括民间一些成熟的画法)外,大都是千篇一律的表现手法。前者丰富,后者单调,而丰富的开始乃是吴道子,他于山水、人物都有杰出的贡献,而启导吴道子画笔成功者乃是张僧繇,陆探微又首先吸收书法用笔于绘画,为张的大变革作了桥梁作用。中国画的表现,主要是借用线条,六朝时代陆与张对线条的改革皆有杰出的贡献,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顾的“春蚕吐丝”线条只是传统的继承,而不是变革和解放。
陆、张对塑造人物的贡献
《人物志》有云:“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陆探微画人“穷理尽性”,乃最传神。《历代名画记》记载正式师法顾恺之的仅陆一人,陆是宋明帝时人,距顾之死已六十年左右。大约顾提出的“传神论”,陆实践得最好。故谢评其为第一品第一人。《宣和画谱》称陆:“真万代之蓍龟衡鉴也。”汤垕见了顾恺之画“初见甚平易,且形似时或有失”,尽管他也赞扬了顾的画,但最后的结论仍是:“谢赫云,恺之画‘迹不迨意,声过其实’,近见唐人摹本,果得其说。”但他认为陆探微“此卷行笔紧细,无纤毫遗恨,望之神采动人,真希世之宝也。”
张僧繇创造了“张家样”,贡献也不小,比张晚大约五十年的曹仲达又创“曹家样”,张、曹二家样一度并行,成为中国佛教画的典型,到了唐,吴道子在继承张僧繇的基础上形成了“吴家样”。“四家样”中张的影响最大,时间最长,形成也最早。“张得其肉”,又“张笔天女宫女,面短而艳”(米芾《画史》),可见“张家样”是比较丰满的,到了唐代只是更加丰满圆润而已。从各地美术遗迹可以证实,梁以后二百多年的佛画佛雕的造型,除了部分地区在北周前后有“曹家样”外,其他皆如“张家样”。唐开元以后的造型样式仍是“张家样”的延续和发展,而顾恺之在塑造人物上就未有如此重大之影响。
张僧繇的影响
梁以后,张僧繇的绘画形成一股巨大流派,成为二百多年间的主流。据《历代名画记》记载,追随张的著名画家梁至唐有张善果、焦宝愿、郑法士、孙尚子、李雅、阎立德、阎立本、范长寿、何长寿、吴道子,其中有的是隋唐时代的代表画家,有的被称为百代画圣。唐武则天时代,李嗣真云:“……独有僧繇,今之学者,望其尘躅如周、孔焉。”又说:“天降圣人为后生则。”僧繇成了画家心目中的圣人和楷模,影响可谓大到极点。李嗣真的评论或有出入,他说的“张公骨气奇伟、师模宏远”、“六法精备”等等我们可以再考虑,他把张与顾、陆同论,“请与顾、陆同居上品”也未讲出具体内容,但他亲身经历的时代,张对画坛的影响程度之记录是不会有误的。
张彦远亲眼见过张的《定光如来像》、《维摩诘》并《二菩萨》,自云:“妙极者也。”顾恺之名气固大,但其绘画作品的影响,何尝一日有张僧繇之大呢?且张创没骨法、凸凹法,也是顾所无的。
3.山水画萌芽不始于顾恺之
有些论者确定顾是山水画始祖,其证据有二:一是顾写了《画云台山记》;二是顾《洛神赋图》中有山水成分。其实《画云台山记》一文,固然谈到了山水布局之类,但不能说明他最早画山水,也不能说明他的山水画得最好,至于《洛神赋图》被说为顾作,在元代之前的任何著录中都不载,在顾诞生一千多年中,没有任何根据说顾作过此图,所谓据说,实则根本无据。目前我们所见的《洛》图,最早见于清代《石渠宝笈初编》,距顾已一千四百余年,《石渠》作者是根据图上所谓赵孟頫、李衎、虞集等人的题跋和印章而定。但这一切经鉴定:“均伪”(连乾隆皇帝都看出非顾之作)。“身份证”是伪造的,身份必伪。
据《历代名画记》载:卫协、司马绍、戴逵、戴勃等人都画过山水。孙畅之《述画》云:“《上林苑图》,协之迹最妙。”(戴勃)“山水胜顾”。可见画山水不但有比顾早的画家,还有比顾画得好的画家。
4.余论
顾恺之和谢赫一样,在绘画上尽管是他所处时代的一时之秀,但说他是六朝时代最杰出的画家,第七世纪以前的惟一大家,就未必公允。弄不好就会影响对画史的正确把握。从文献上看,顾的画风只代表六朝的普通画风和一般水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六朝绘画,唐宋摹本和出土文物中绘画以及龙门等地一些类似绘画的美术遗迹(如礼佛图等)①,都不能代表六朝时代的先进水平。不但像陆探微那样的“如锥刀焉”,“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以及张僧繇“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的画法,我们未见到,就连卫协那样颇得壮气的画法,也未见到,所见皆是顾恺之式的“春蚕吐丝”类一种勾线画法②。这种画法在汉代已经成熟。今人至少不应该有这种短见,一看到线条变化多端,点曳斫拂和一气呵成的画法,就认为不是六朝画,或者一提到六朝画,脑子里只有那种细匀无变化的线条。这都是片面的看法。
很难确定顾恺之还有画迹存世,论者多以记载为据,而画史上见过顾画的人有记载在,一些可靠的大评论家有评语在,都不能证明顾是六朝最杰出的大画家,更不是“惟一大家”。
但顾恺之在画史上却另有伟大的贡献,强烈地震动着中国画坛一千多年,以下专文论述。
(五)顾恺之的贡献主要在画论
顾和谢赫一样,在绘画方面,虽为一时之秀,但在整个六朝时期,他们都还不能算是第一流大画家。但是他们都是六朝时代伟大的绘画理论家。
六朝绘画创作和绘画理论各有五大家,前者是曹(不兴)、戴(逵)、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后者是顾(恺之)、宗(炳)、王(微)、谢(赫)、姚(最),后者在绘画上也都有一定的成就。顾是第一位绘画批评家,谢是第一位绘画批评理论家,宗、王是山水画论之祖。
顾恺之,他是中国绘画理论的奠基人。在顾之前还未有一篇完整的、正式的画论。顾不但第一个开创了这个学科,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主张,其“传神论”成为中国绘画不可动摇的传统。他发现了绘画的艺术价值在“传神”,而不在“写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绘画的彻底觉醒。顾的画论之建立,乃是中国绘画艺术大发展的起点,从此,中国绘画日新月异,以超乎往昔的惊人速度登上高峰。
(六)关于顾恺之三篇画论问题
顾恺之画论,因《历代名画记》的收录,存有三篇,其题目曾一度被人误解。我这里先作一清理工作。
1.《论画》不误
顾恺之的《论画》和《魏晋胜流画赞》两篇文章,俞剑华先生以为题目误倒,在他的很多著作中反复提及,而且很多论者盲目相信,直至现在。其实,完全不误。
《论画》是顾恺之评论绘画作品优劣的文章,而且开始还有一段简短的论述:“凡画,人最难,次山水……”颇见精义。所评《小列女》“面如恨,刻削为容仪,不尽生气”等等内容,我们看来,是道道地地的论画文章,顾的传神论主要在此文中阐明的,题目叫《论画》是很切实的,无可怀疑。
《论画》的内容不仅全文被收录,而且张彦远还引用过其中内容去介绍其他画家,并明确注明是《论画》中的语言。卷五·卫协条下,介绍过卫协之后,张彦远说:“顾恺之《论画》云:‘《七佛》与《大列女》皆协之迹,伟而有情势。《毛诗北风图》亦协手,巧密于情思。’”这正是顾《论画》中的文字。
又说:“及览顾生集,有《论画》一篇,叹服卫画《北风》、《列女》图,自以为不及。”这里所提到的内容,在《论画》中都能找到印证,顾恺之在《论画》中,对卫协画《北风》、《列女》评价很高,确为“叹服”,前后内容是一致的。
总之《论画》的“题”与“文”是不误的。前前后后未有纰漏,这是很清楚的。
张彦远还不至于那么粗心,多次接触而不见其误。
2.《画赞》的内容
《论画》是不误的,很清楚。问题出在《画赞》上面。张彦远所收的《画赞》内容实际是模写内容,所以必须弄清《画赞》的内容。否则,《论画》虽然站住了,有可能被人从外部推翻。很多论者把“画赞”理解为对前人绘画作品的赞扬或评论,是错误的。其实画赞不是对画的赞扬,也不是评论画,而是有画有文同时赞人。“赞”本是一种文体,以赞美为主,六朝时颇为盛行。《文心雕龙》有《颂赞篇》,梁萧统《文选序》有:“美终则诔发,图象则赞兴。”“赞”是赞人,而未有赞文和赞画的。《文选》中还专列《赞》篇(见卷四十七),选了《东方朔画赞》和《三国名臣序赞》二文,皆赞的是人。《东方朔画赞》是三国人夏侯孝若所作,内容是记他见到东方朔先生的遗像时所发的一通赞语(“……想先生之高风……见先生之遗像……慨然有怀,乃作颂焉。”)。其中内容无一句赞画的好坏,而是赞画中人的高风。
“魏晋胜流画赞”就是画魏晋胜流的像,再作“赞语”以赞这些胜流。和“东方朔画赞”的内容形式相仿佛,皆非赞画。
还有一种“画赞”是根据文字记载的内容而作画以赞人,也是画和文同以赞人。《历代名画记》卷三:“汉明帝……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而且还有“五十卷,第一起庖牺五十杂画赞。”不论哪一种“画赞”,都不是赞画的优劣。
张彦远说顾恺之:“著魏晋名臣画赞,评量甚多。”顾恺之确实著过此文(画赞)。距顾不远的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及刘孝标的注引中很多内容皆可证实。其《巧艺》篇:“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条下注:“恺之历画古贤,皆为之赞也。”即是张彦远说的“著魏晋名臣画赞”这件事。顾恺之《画赞》的内容,我们还可以见到一部分。
《世说新语》卷三《赏誉第八》“羊公还洛”条下注:“顾恺之画赞曰:涛无所标明,淳深渊默,人莫见其际而其器亦入道,故见者莫能称谓而服其伟量。”
(同上)“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如何”条下注:“顾恺之画赞曰:涛有而不恃,皆此类”也。
(同上)卷四《赏誉第八》(下):“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注“顾恺之夷甫画赞曰:‘夷甫天形瓌特,识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按王夷甫就是王衍,《晋书》有传(见卷四十三),其曰:“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王敦过江常称之曰,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顾恺之作《画赞》亦称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顾恺之作《画赞》”,看来不会假,《晋书》的作者还引用顾的《画赞》之文来赞晋之名臣,未尝把它作为赞画的优劣的文字。《晋书》是唐人所著,顾的《画赞》在唐代还有流传,张彦远也是唐代人,他既说“顾著……画赞”,可想是看过的。
由上可知,顾恺之的《画赞》,当时及其后确有流传,而且内容是赏誉魏晋名臣(胜流)的,而不是称赞魏晋名臣的画,那些名臣也很少有人会画,绘画的作者有的根本不是名臣。
《画赞》的内容清楚了,与论画无涉。便进一步保住了《论画》的“文”与“题”不误。
又《画赞》的全文,我们见不到了,《世说新语》《晋书》等书引用其中部分内容,大体还可以了解其内容性质,因赞词和绘画无关,所以张彦远未录及。因为“恺之历画古贤,皆为之赞”,其中有文有画,张彦远在《画赞》的内容中明明写着:“凡将模者……”是说明模写方法也属于《画赞》的一部分内容,但模写方法也明明不是“画赞”,这正如《唐诗三百首》,里面却有“蘅塘退士”的内容,“蘅塘退士”既不是唐诗、也不是唐人,但他和此书有关。一本书中附有不是本题的直接内容,但和本题内容有关的文字,从古至今常见。模写之法虽不是“画赞”,但和模写这些名臣的画像有关。顾说:“凡吾所造诸画,素幅皆广二尺三寸。”这是供临摹他的画的人作参考的。“其素丝邪者不可用”,因为“久而还正,则仪容失”,这也是提醒临摹者注意的。后面的文字谈作画时应该如何如何,读原文便知。
3.“模写要法”及其他
《论画》和《画赞》的“题”与“文”不误,是明白了,但张彦远又说过顾:“著魏晋名臣画赞,评量甚多,又有论画一篇,皆模写要法。”“评量甚多”,从上引部分《画赞》内容,可证其实。《论画》实际上是顾恺之临摹学习前人作品时的心得记录,反映了他对绘画的认识水平,但当时他还是给临摹者以提醒注意的。《画赞》中所收的内容是模写要注意的方法;《论画》中内容才是要法,才是要注意的本质东西。
很多研究家实际上都明白地把模写要法只当作介绍工具的使用和操作的方法来理解,似乎顾恺之的时代,谈临摹,谈学习传统,只知道谈一些绢素的尺寸和对放,“笔在前运,而眼向前视”,以及用笔用墨的“上下、大小、浓薄”之类的内容(诚然这也是摹写方法或妙法)。似乎“不尽生气”、“伟而有情势”这些内容,不是临摹时所要注意的要点,这真是误解。
硬说《画赞》就是《论画》,“论×”的文章在顾前后都有,常见的曹丕《典论》二十篇之一的《论文》,和现在的论文形式无异,其中有论点有论据,立论说理甚清楚。而此文全是谈临摹,怎么能取名《论画》呢?何况《论画》问题,我上面已作分析,题与文都是未有纰漏的,已经清清楚楚。
再谈谢赫的《古画品录》(谢不称“画赞”),其序云:“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这当然是评画的序言。细读顾《论画》序言:“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这明明是告诫学画人的语言,和单纯的评画之关系又隔了一层,乃是给学画人的指教。
“顾恺之画论的中心是传神”。这是无可辩驳的,所以顾谈临摹的中心要点也在“传神”。诚然,《画赞》中也谈了“以形写神”等问题,但《论画》中,给予学习者、临摹者的指教更为具体,更为深刻。现在我们也可以明白了,张叙顾时只提到这两篇,而未提到《画云台山记》,恐怕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两篇一篇是模写要法,一篇是模写方法,而《画云台山记》则是他一幅创作构思的文字记录(云台山,可能真有其山,《抱朴子》书中也说:“余昔游乎云台之山,而造逸民。”)但在后面,他倒把《画云台山记》全文收录了。
张彦远在卷二《论画体、工用、榻写》中也提到:“顾恺之有摹榻妙法。”此文实际可分为三个部分。从开头到“岂可议乎画”,是第一部分,乃谈“画体”;从“夫工欲善其事”到“宋人善画,吴人善治(冶),不亦然乎”是第二部分,乃谈“工用”;《画赞》的前部分有些内容实际上和“工用”有关。从“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至最后是第三部分,乃谈“榻写”。“榻写”部分之“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等内容精神和《论画》的内容精神是差不多的。也未尝把“榻写”的内容只当作是工具的使用和操作的方法。
(七)中国绘画在艺术上的彻底觉醒
顾恺之的画论,强调以“传神”为中心,提出了“天趣”、“骨趣”等著名论点,以及“骨法、用笔、用色,临见妙裁,置陈布势”和临摹等具体的绘画方法。在传神的刻画上,他又特别强调眼睛的刻画,以及体态动势、人物关系、环境的衬托等等,乃至于用笔用墨的轻重、构图的效果等等。他还提出“迁想妙得”。“迁”字是变动不居、上升之意,古时称官职提升为“迁”;又《系辞》有云:“变动以利言,凶吉以情迁。”“妙”字就是《老子》书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妙”,顾恺之所谓绘画的奥妙就是“传神”。“四体妍媸,本亡关于妙处”,即无关于“传神”处,因“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得”字老、韩书中常见。顾评《伏羲神农》:“居然有‘得一’之想。”“得一”就是《老子》三十九章中“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的“得一”,顾是赞美这幅作品的作者画出了“伏、神”这两位古代“侯王”有“天下贞”的气魄、神态。“之想”乃画作者之想,也即“迁想”的“想”。“迁想妙得”,指出画家在努力观察对象的基础上,根据“传神”的原则,反复思索包括对对象的分析理解,必得其传神之趣乃休。所以谢赫说他“深体精微”,“笔无妄下”。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顾恺之已经认识到画人、山水、狗马都可以“传神”,只有“台榭”难以“传神”(这一错误之论,也为后人所纠正)。
以上这些都说明顾恺之对绘画已有了相当的研究,这在顾之前是未有的。顾的理论标志着中国画的艺术理论上的彻底觉醒。这一意义非同小可。《东方朔画赞》中有“嘘吸冲和,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俗登仙”几句话,倘用以说明顾的画论影响,是很合适的。
我们可以作一比较,魏晋以前的绘画,我们不打算介绍得过远,张彦远说:“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始得而记。”其实秦汉绘画,不论是各种各样的画像石(砖),还是出土的墓室壁画,或者作为“升天图”的彩绘帛画,大都是简单的、外在的、形式化的。秦汉之前的战国绘画,已比以前大为进步,但所画的人物仍是一个简单的轮廓,符号化的现象依然存在,甚至用五根短线代表五对手指,作人面多侧面。西汉时代个别人才认识到“君形”在绘画中的作用,但不是在专门论画的著作中论述的,且是偶尔一提,在绘画界几乎未有什么反应,今日从石刻上看到的东汉绘画,大都是靠动势来表现的。
且魏晋以前的绘画,主要是由画的故事来表现其意义价值,其表现的是神灵、明君、贤相、忠臣义士、孝子贤孙,以达到“成教化,助人伦”,“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目的,出游图、牛耕图等也是为死者服务的,这是求意义价值在于绘画自身之外。汉画像石乃是靠表现忠臣孝子之类的故事而存在,它是牌坊的一部分,它的主要价值不在本身的艺术性。这和以后的绘画,虽然有的作品也属于依附性质不一样,因为一旦发现了绘画的艺术本质,明确了绘画自身的艺术任务,绘画的发展便有自律性,虽是依附品,艺术表现上却有一定的独立性,仍会按照艺术的规律去创作,它是以自身的艺术去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和靠故事内容去决定其意义价值不同。魏晋前后的绘画就有这种蝉蜕龙变的差异(当然不是全部)。
艺术的规律是否被揭露出来,对艺术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愈是早期的艺术愈是有其一致性,愈是后期的艺术愈是有其多样性。
魏晋之前还很少见到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绘画,绘画多属依附品,到了吴曹不兴画屏风、晋司马绍画《洛神赋图》,才真正有了独立审美意义的绘画作品。王充说:“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论衡·别通》)艺术品的使用价值首先在于欣赏(艺术的社会功能必须在审美中得以完成),王充认为绘画无用,是不懂得绘画存在的基本价值是画的艺术。但当时的绘画也确实未有太高的艺术,所以,“形容具存,人不激劝”。
顾恺之总结前人绘画的经验,加上他自己深入的研究,指出人物画艺术的关键在“传神”,而外形、动势、服饰、用笔等等皆是为了达到或有助于“传神”而进行。这就突破了原来的绘画只是描写外形(尽管形中有时也包含一定的神),甚或是描写象征符号形式的外形,而发现了艺术描写的本质。
顾恺之这一发现代表了绘画艺术的彻底觉醒。
日人金原省吾所著《支那绘画史》一书中,在宋画部分提出画面上形体本有两个(见日文版第四节“宋画的特质”)。我曾因粗心,误译为第一形体和第二形体,倒成了我的“创造”,不妨郢书燕解下去,对人物画来说,第一形体乃是人的外形,第二形体方是存在于人体中的神。对于一个人来说,神是更重要的,躯体的本质是相同的,精神的本质却决不相同。艺术上的神是可以通过第一形体流露出来的,不仅有第一形体不同而第二形体不同,也有第一形体相同而第二形体不同,文学上的张飞、李逵、牛皋第一形体相差无几,而第二形体决不相同。沈宗骞也讲过一段有意思的话:“今有一人焉,前肥而后瘦,前白而后苍,前无须髯,乍见之或不能相识,即而视之,必恍然曰:此即某某也,盖形虽变,而神不变也。”(《芥舟学画编》)
宋陈郁说得也好:“写屈原之形而肖矣,傥不能笔其行吟泽畔,怀忠不平之意,亦非灵均,写少陵之貌而是矣……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否则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贵贱忠恶奚自而别,形虽似何益?”
诚然人的神是复杂的,略早于顾恺之时就有人说:“夫貌望丰伟者不必贤,而形器尪瘁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抱朴子·清鉴卷二十一》)但反映在艺术上却有一定的典型。我们常说某人的作品概念化,人物刻画缺乏个性,内心世界未表达出来,就是说他只刻画了第一形体,这是不能称为艺术的;反之有个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被再现出来了,就是说他注意到第二形体,注意到艺术的本质。艺术家如果不能从人或物中发现第二形体并把它表现出来,他的作品必是失败的。
但顾恺之之前的画人尚不能在理论上明白这些。顾的传神论出,使艺术家明白:艺术只能成立于第二形体之中。“以形写神”其实就是以第一形体写第二形体,而第二形体才是实质,才是目的,第一形体只是实现第二形体的手段,得“鱼”是可以忘“筌”的。陈去非《墨梅》诗云:“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九方皋把马的牝牡骊黄都看错了,却发现了马的本质。犹如X光透视镜,略去人的皮毛骨肉,一眼看出内脏的质地是衰病的,还是健康的。
顾的“传神论”代表魏晋时代绘画的大飞跃,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顾指明绘画艺术的本质是传神,而不是写形,这样就为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画家有了正确的努力方向。魏晋时,中国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人物画不再是由画的故事来表现其意义价值,画的意义价值不只在画的自身,而是通过形以表现被画的人物之神来决定其意义价值,画的基本价值在本身的艺术性,这一基本价值得以保证之后,才能考虑其他的价值,否则便不是艺术品。
中国绘画在艺术上的彻底觉醒,才真正地有了美的自觉而成为美的对象。顾恺之之功不可谓不大。从此,中国画自觉地摆脱了附庸地位,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日益起着重要作用。千百年来,顾恺之绘画理论在中国画的创作和欣赏上,起着指导作用,“传神”遂成为中国人物画不可动摇的传统。
(八)顾恺之传神论的产生
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哲学的贫困》)顾恺之的“传神论”亦然。东汉末年,由于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东汉政权由名存实亡到名实俱亡,公元220年曹丕以魏代汉,265年司马氏以晋代魏。长期战乱,人口逃亡流散,土地荒芜,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地主豪强纷纷带着自己家兵转徙四方。社会的动乱引起了政治上的重要变化,即官僚选拔制度由汉代的乡举里选代之以“九品中正制”。《晋书·卫瓘传》有记:“魏氏承颠复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当然“九品中正制”的确立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当时还不知用科举考试办法选拔人才)。“九品中正制”是由每州“大中正主簿”和每郡的“中正功曹”来主持人物的评选,他们把当地人物评为“上上,上中,……下下”九等,供政府选用。于是对人的品评议论便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
议论在当时本有了传统,汉代通过地方察举和公府征辟取士,所以社会上品鉴人物已经风气大盛。汉末国家设立的太学到郡国设立的精舍配合党争引起了朋党交游活动,产生“清议”,“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