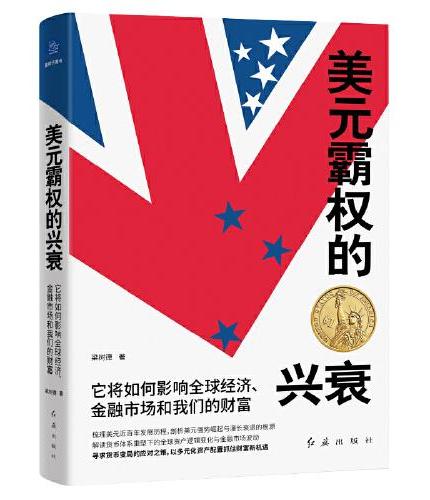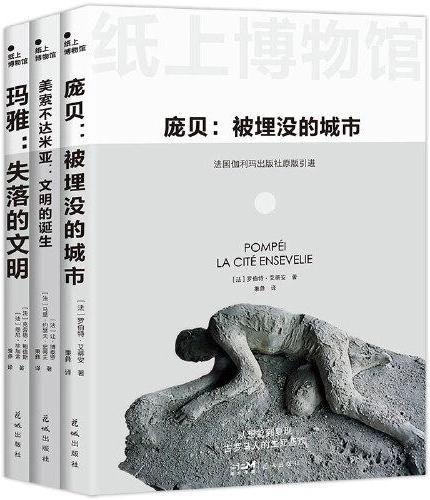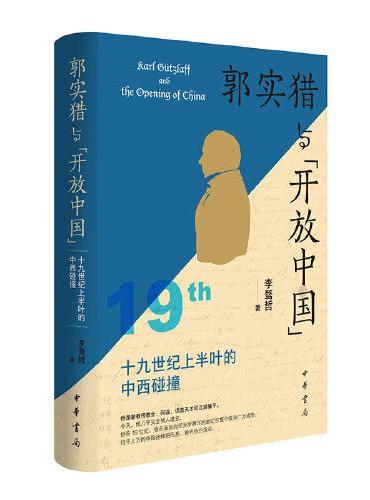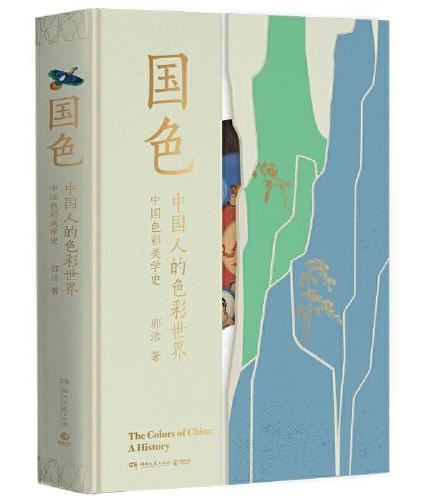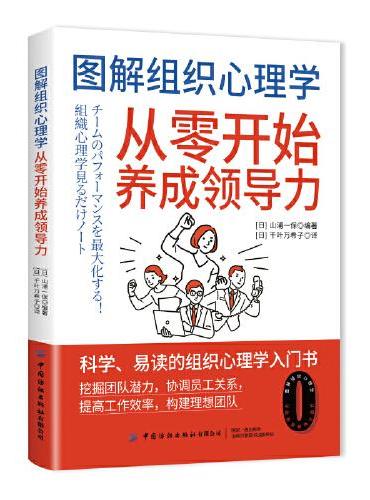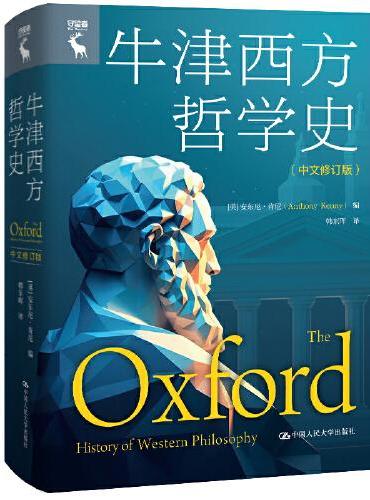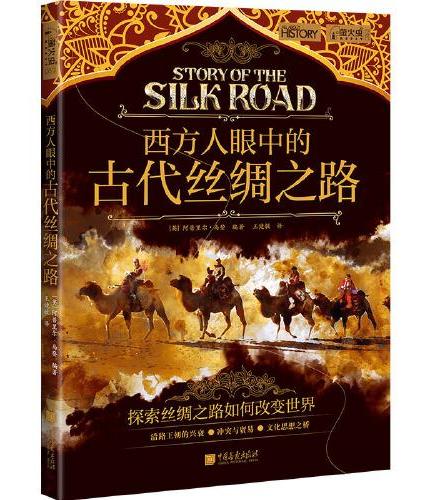心火
儿时的往事逝去得实在太久了。
无论是生存规律的制约还是社会条件的改造,都足以使像我这样的生长在大都会的青年渐渐淡忘了[渐渐淡忘了]自己在血统上的那一点独异。人到中年,潜心民族历史且又迷恋文学,常会有对那些难以追溯的故事的叹憾,总觉得自己太不懂得珍惜,觉得自己不觉之间已然失去了什么。
能记得的,是我家在下雨时烙饼的锯末火。那是昏黑的胡同巷子深处,白发苍苍的外祖母用一柄令箭样的条铲,拨着平时向木匠讨来的锯末。面饼的香味儿扑满了小院。邻居们都在小声议论,孩子们则围着不散——看着我们这家山东人的新奇吃法。那火微微的,火苗又小又柔,锯末漫上后,甚至熄了似地烟也不冒;但不久,那柔柔的火苗又悄然爬了出来。
像那锯末火一样,在我心底里和那些淡薄的记忆一起,也还有一点朦胧的光亮,像一苗慢慢燃着的,淡蓝微黄的火。
比如,似乎在上小学时,有一次听姐姐说过:你的名字叫赛义德。虽然她仅仅说过这么一次,而且直至今日我都未曾问问母亲这桩事——但这句话却时隐时现地沉入了我的心底。
现在已经无需向母亲询问了:我知道这是一个波斯语词。元初经略云南的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的名字中就有这个成分。据《史集》记载,这个名字是圣裔才用的,赛曲赤是一个真正的华族。
再比如,还记得小时常见的外祖母独自跪在墙前,微低着头,神情艰忍[坚忍],口中默诵着什么。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她嘴角颤抖着,“主啊——”她唤道。
她的这种举动给我留下了烙刻般的印象。或者说,她传达给我了一种痛苦的刺激[刺激]。水泥地板上,我想,她的膝盖多疼呐。我长久地无法赞同她。我不承认这种无形的苦。
——而现在,甚至在吐鲁番的阿撒吾克甫,当看到膝上绑块胶皮,一爬一屈地从和田赶来朝拜圣徒墓的无腿的乞丐,我也不觉惊奇了……我甚至想,他们才算真正传递着清真的传统,而外祖母和我们这一支山东的回族却改变得太多了。
像我家那顽强地舐着熏得黑黑的锅底的锯末火一样,这一苗微火也不熄地在我心里留存下来了。我长久地不能理解它和记住它,但我已经意识到了。
我想,这种心火并非专属于回族儿童。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藉以[借以]相互区别的心理基础。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儿童来说,他们原先并不懂得什么民族的情感,他们不过是从这萌芽般的小小火苗里意识到:这里有自己。
但是,使人们尊重这种“自己”是一件极难的事。
我相信每个北京城里的回族儿童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胡同里,在球场上,在因为蜻蜓、弹弓或者一张香烟盒折成的三角而发生的厮扭中,对手祭起了法宝:“小回回,奸又奸,拿根猪尾巴往家颠。”这种开心的歌谣也像北京城的豆汁、鸟笼子、糖葫芦一样,世代相传,源远流长。它增添着老北京人饭后茶余的闲趣,也伤害着一批批本来可以更开朗、更光明的纯净童心。
现在,我早对这种无可厚非的玩艺儿[玩意儿]充分原谅了。我甚至觉得,若是连这点东西也没有了,世界也未免太不真实。历史上,在民族集团之间,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也常常开这种玩笑的,开到血流成河的地步。芸芸众生中万相纷纭,这点事情又算什么呢。
只是那心火的种子击在侮辱的石上,它燃起来了。像许多回族少年一样,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形变。既凶蛮,又羞涩;既怯弱,又自尊。不过,那时的一切心理和作为,今天看来都显得既愚蠢,又好笑。
时间长了。我们虽然还被人们同体的世界。也许这片世界还是贫瘠的或是不发达的,但这里却生存着许多优秀的精神。在我们努力地企图走向富裕、走向现代化和新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应当用一切努力来发扬这些精神。
我想,民族范畴内的一切:无论是民族的研究还是民族题材的文学,都应当有促进我们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的任务。
我在小说《雪路》里写到了人们之间缺乏了解的这种现实,也写到了我们——无论哪个民族——必须互相依存、互相帮助着走完历史安排的这条漫长道路的这更大的现实。我想,这种现实是深刻的和雄伟的,也充满了感情和热量。我们的民族文学应当描写这条雄伟历程上的奋斗,也应当揭示其中的矛盾和问题。在这征途的前方,我们会和我们的亲人一起,用各种语言歌唱我们看到的一切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