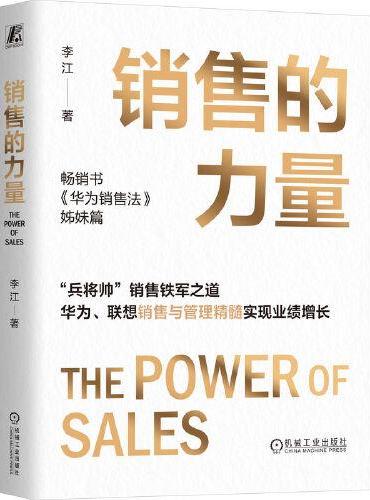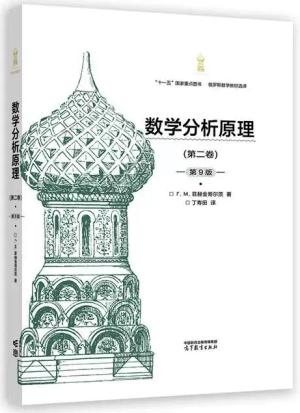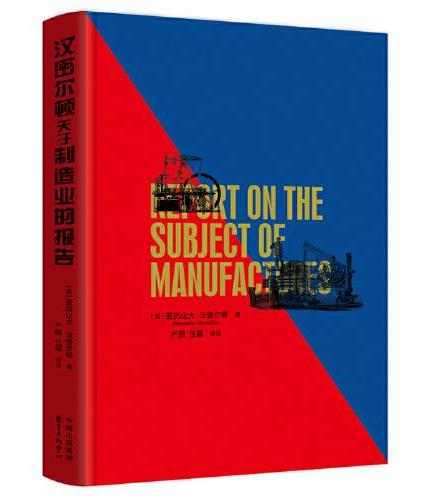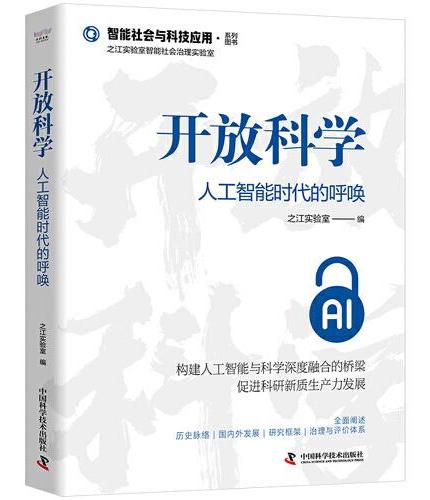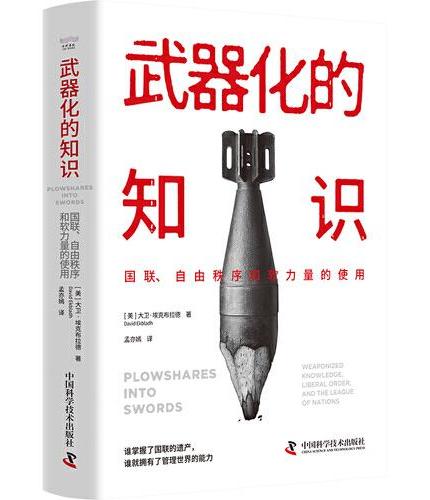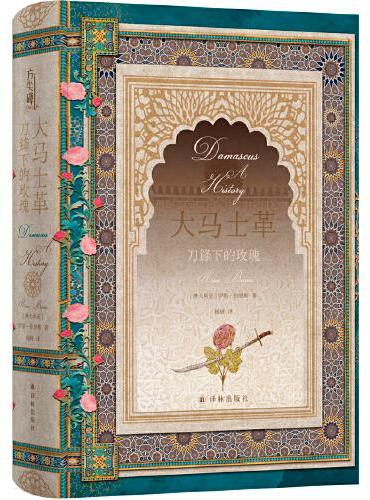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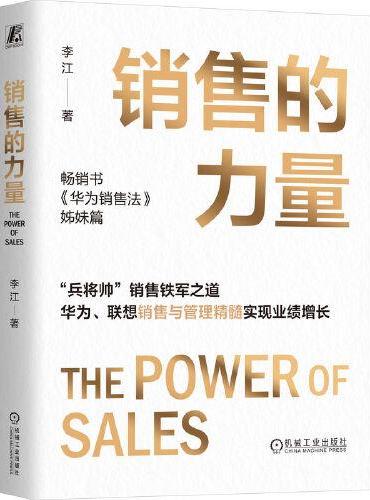
《
销售的力量
》
售價:NT$
454.0

《
我活下来了(直木奖作者西加奈子,纪实性长篇散文佳作 上市不到一年,日本畅销二十九万册)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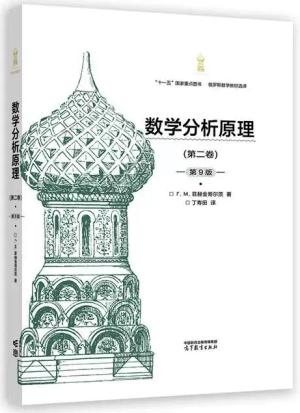
《
数学分析原理(第二卷)(第9版)
》
售價:NT$
403.0

《
陈寅恪四书
》
售價:NT$
14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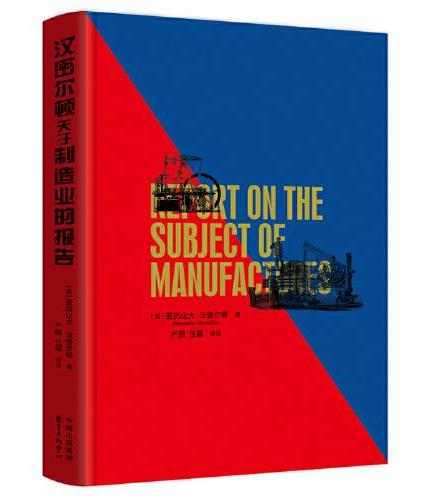
《
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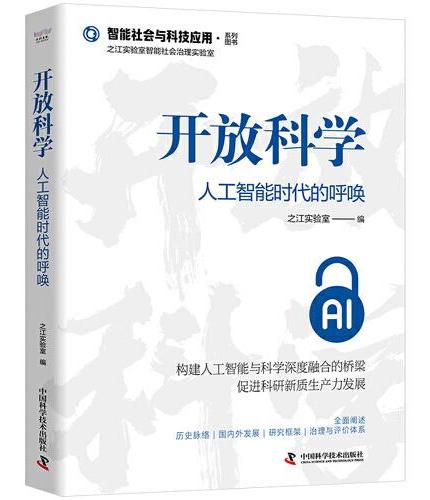
《
开放科学:人工智能时代的呼唤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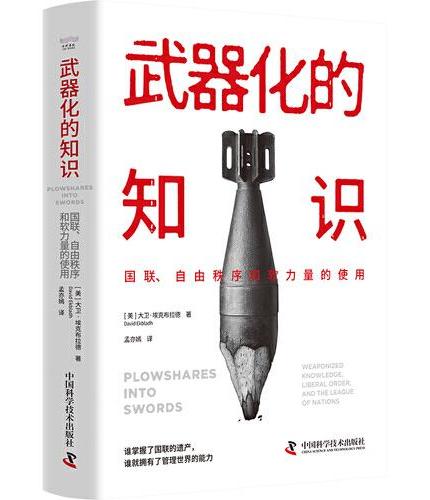
《
武器化的知识:国联、自由秩序和软力量的使用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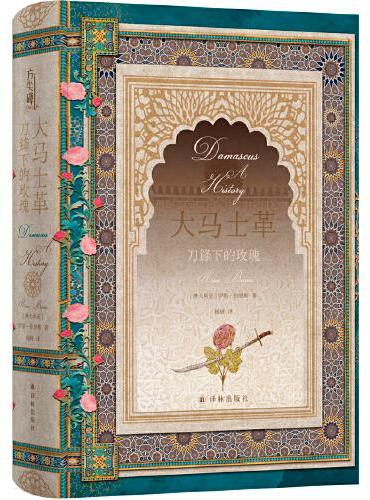
《
大马士革:刀锋下的玫瑰(方尖碑)
》
售價:NT$
607.0
|
| 編輯推薦: |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年度选编,从全国数百种文学报刊当年发表的千万字的代表作品中精选出部分精华篇目,向大众读者呈现中国年度文学创作的成绩,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年度作品。
本套丛书由多位权威主编进行文章的选编工作,所选取大众最为熟悉,在当下文学阅读环境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样式,散文、随笔、文史精品、纪实文学、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闪小说、校园文学和儿童文学。评选出全年文学作品中的精华之作,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它们反映出2014年度文学领域的风貌和突破,让读者感受到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
|
| 內容簡介: |
|
《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4》由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主编,精选2014年全国各媒体、报刊所发表的最优秀短篇小说,描绘当下社会的的众生之相,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内容简练,余韵深远,对社会有教化意义。要求独特性,无论是在语言、结构还是意蕴的传达上,都有着强烈的独特性和高超的艺术性,短篇小说处在文学观念与文学创造的前沿,是文学中最绚丽多姿的浪花。
|
| 關於作者: |
|
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主要著作有:《众神狂欢》、《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与程光炜合著)、《想象的盛宴》、《坚韧的叙事》、《文化批评与知识左翼》、《游牧的文学时代》、《中国当代文学通论》等二十部。主编文学书籍8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发表论文、评论400余篇。日本、法国、中国台湾及大陆多有评论和介绍。文章多被《新华文摘》、人大书报社中国现当代文学专辑、文艺理论专辑、文化研究专辑转载,被多种论文选本、年度论文等选编收录。部分文章、著作被译为英文、韩国文等。获文学奖项十余种。
|
| 目錄:
|
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
虚拟
野象小姐
在酒楼上
东北平原写生集
头头是道
可悲的第一人称
哑巴
徐记鸭往事
虹
我们的塔希提
章某某
金山寺
房间
礼拜二午睡时刻
大师
无人之境
南来北往谁是客
一颗扣子
无法澄清的谣传
百花二路
寻找梅林
|
| 內容試閱:
|
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
邓一光
黄昏的时候,我搭乘一辆顺路车从福永去南澳。姆妈跟着我。她一路上都没有和我说话,要么打盹,要么看着窗外的景色发呆。我们在路上遇到一辆抛锚的车牌为“滇B”的车、三个出了点麻烦的年轻穿越族、两对在海岸上拍婚纱照的新人和一大群在夕照中返回东部山区森林的白头翁。说实话,我希望能叫出他们和它们的名字,这样也许我们能够说说话,在漫长的路上大家都会好过一点儿。我们还遇到一场来去无踪的阵雨,这在岭南的夏季是常有的事,但这些都没什么。
车在山海相连的东部群山中穿行,这里气流乱涌,常常有诡异的风从森林中蹿出,聒噪地破窗而过,风中能闻到灵猫、鸢、赤腹鹰、褐翅鸦鹃、穿山甲和蟒蛇的气味,让人觉得指环王时代又回来了。据说东部大山里有野牛和野猪出没,我猜大多数深圳居民和我一样,并不认识它们。在市区里待惯了,有点像刑期过长的犯人,人们习惯了城市牢狱有保障的生活,出城跟出狱似的,免不了有些紧张,如果和野牛、野猪遭遇上,需要翻译才能沟通。
夜里两点钟,我离开湿漉漉的大鹏所城,去了哥哥所在的夜总会。这个时候大部分游客都回市里去了,或者没回,在附近的客栈安顿下来,哥哥有机会出来见我。之前我在古城里毫无目的地逛了两小时,在“将军第”对街的小摊上吃了三个茶叶蛋,啃了两个加了玉米香精的煮玉米棒,坐在城门楼垛子下刷了两小时微博,又打了两小时盹。这期间我和姆妈没有说话,她也没和我说。有时候她走到我身边来,好像想要说点什么,但到底没说,站一会儿又走开了。更多的时候,她在什么地方无声无息地走动着,或者走进某栋老宅子里,在那里消失掉。我知道她会那样。她不会和任何人说话,但我不会勉强她。
哥哥手里握着一支金属材料拐杖从猩红的夜总会大门里一瘸一拐出来,就像一块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异物,有些伤感,有些不耐烦。他是个瘸子,有那么一点,不太严重,喜欢随身带一支金属手杖,但并不怎么使用。我站在街对面的山墙下看他。他其实并不老,才三十出头,至少不应该像看上去那么老。好在我能认出他。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九年吧。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见面。我是说,虽然我俩同在深圳,我在福永,他在南澳,相隔不过几十公里,可是九年了,我们从来没在这座城市里见过面,一次也没有。我是说,自打离开老家以后,我俩就再没有见过面——他根本不愿意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见到我,我也一样,我认为我们只不过是兄弟,各活各的,谁也不欠谁,见不见的没什么。但这一次我俩必须见,而且需要好好谈一谈。我们不能在夜总会里见,他只是夜总会保安队的小头目,夜总会不是他的,就跟伶仃岛不是他的一样,要是我请他在夜总会里洗个澡或者干点别的什么,他会认为我在污蔑他,说不定会杀了我。
“我们吃点什么吧。”等哥哥走近,我开口对他说。
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把一些不必要的程序省下,他不用把我带到他家里去,让我认识他的家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我们可以随便去某个地方坐一坐,假装消夜什么的,在那里把该谈的事情谈了。在路上我就决定了,我不会花他一分钱,不管吃什么,账单都由我支付。
听了我的话,哥哥看我一眼,扭头就走。在那之前他没有正经看过我,对此我什么也没说,跟上了他。
我们去的地方不是正规夜市,是海边的一个鱼鲜码头。码头上空荡荡的,码头的入口处停放着两辆贩鱼鲜的小型货车,夜晚的海风带来一阵阵沉闷的海腥味,四个男人坐在海堤上,借助码头上昏暗的灯光甩扑克。码头靠着出口,一溜摆着几个卖海味的烧烤摊档,节能灯吊在锅灶上,锅灶前油烟蒸腾,影影绰绰。离着码头不远是一条曲里拐弯的巷子,巷子口有两家门脸不大的私家旅社、一间乱哄哄的发廊、一间卖成人用品的小店和一个个进出之人都形迹可疑的水果小摊,没有什么像样的人来往。
哥哥在一张油腻腻的低矮小桌前坐下,有点不耐烦地大声召唤摊档主。脑门发亮的中年摊主过来,看上去有点紧张。在此之前他不那样,和两个熟悉的食客笑骂着。姆妈没有跟上我们。我猜她不想参加我俩的谈话。她不会感到饿,她只想知道我和哥哥谈得怎么样,这样就足够了。
我问哥哥想吃什么,或者喝点什么。哥哥骂骂咧咧——不是骂我,我刚到,还不至于——是骂顺着节能灯纷纷往下掉的木蠹蛾。摊主拘谨地站在哥哥面前,用力揩着手上的油污,他肯定想躲得远远的,不愿意见到我哥哥,但是没有办法,他的排档炉火正旺,还有别的客人,不能不负责任的一走了之。
我要了一份炭烤海鲫,一份白水煮濑尿虾,一份姜汁煲鱿鱼须,几瓶啤酒,六瓶吧。酒菜很快上来,我们吃喝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坐下来了,哥哥用不着一瘸一拐到处走动,这让他心情好了一点儿,气氛有所融洽,他谈起让他烦恼的事情。我用纸巾抹掉酒瓶上的水珠,启开瓶盖,把啤酒递给他,听他说。我还给他剥虾壳,那是一门手艺,你不能忽略掉虾线和虾头上的黄油,也不能让虾肉留下遭受过摧残的痕迹,得用锦衣卫执行廷杖的那种巧劲,就是说,人没了,皮肉完好如初。
没过多久我就弄清楚了,我到之前,哥哥刚把焦萍萍揍了一顿,他是为这件事烦躁。焦萍萍是我嫂子,他俩结婚六年了。也许时间更长,这个我不知道。之前他俩各有配偶,再之前焦萍萍是商职校的学生,哥哥在离婚之前还有别的配偶,但没结婚。我不清楚哥哥有过多少配偶。我说过我不知道,我们之间从不来往,没谈过这些事情。哥哥和焦萍萍有一个孩子。哥哥还有一个孩子,但不是焦萍萍生的,孩子的姆妈是代孕女,一手交孩子一手数钱,人钱两讫,然后就失踪了。
“看她的肚子就知道,至少还能生五个,也许八个,可惜了。”哥哥遗憾地总结说,他说的是那个替他生下儿子的“天使女”。
这一次,哥哥把焦萍萍的脸打肿了,就是这件事让他烦恼。听他的意思焦萍萍人长得漂亮,他很看重这个,一般不打她的脸;他有别的办法让她听他的话,而且,他不许她因为挨了打就离开他,更不许提离婚的事。
“我一直在为她打拼,为孩子们打拼,”哥哥委屈地说,“我还在打拼,就要成功了,她想怎么样?”
哥哥看重他的两个孩子,尤其是小的一个,就是代孕女生下的那个,是个男孩。据说那孩子长得有点灵异,老把拇指含在嘴里盯着人看,像缺了点什么,不如头一个女孩讨人喜欢。这些都是我听老乡说的。我没见过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妈。我还听说,哥哥在南澳一带很有名,是龙岗区的优秀务工人员,他没有高学历和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没有国家级技能竞赛奖励、发明专利和高额纳税数,但他靠着顽强的个人纳税、参保、固定居住、与人合办公司、做义工、参加青年志愿者行动和不间断地去献血站献血,差不多已经为自己积满了入户的分数,很快就能成为深圳市的户籍人口了。像他这样仅仅花了九年就能积满分的外省人不多见。但不管他的两个孩子长成什么样,他俩都是我侄子,两个都是。
“每次揍焦萍萍我都想哭,你说这算什么?她为什么不理解我?我为了谁,还不是他们母子三个?”哥哥灌了一气啤酒,不耐烦地看我了一眼,“你来干什么,嫌我还不够乱?”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我原以为他不会这么问,这让我一时无语。我为什么来南澳找他,这件事我俩之前在电话里简单说过。我从一个老乡那里找到他的电话。我没有他的电话,姆妈也没有。我回过头去寻找姆妈。我看见了她。她出现在鱼鲜码头,离我们有点远,站在礁石嶙峋的海堤上,呆呆地看黑漆漆的大海。哥哥没有跟着我朝海堤那边看,他要么是没看见姆妈,要么是故意,但似乎也没有太大关系。
姆妈要死了,这就是我来找他的目的。是我俩的姆妈。我们的父母从来没有跟别人睡过,他们就生了我俩。我来找哥哥,他是父母的大儿子,小时候他们通常不叫他名字,管他叫老大。我找老大认真谈一谈,我俩得对姆妈要死了这件事情做点什么,不能什么都不做,那就说不过去了。
“你为什么不回去?”哥哥说,从桌上操起酒瓶,撸一下瓶嘴,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回不去,不能回去。”我说。这件事我也在电话里给他说过,我说过为什么我回不去。公司派人去土耳其安装光纤通信设备,名单上有我,为这个指标我等了三年,为争取等待这个指标的资格我苦熬了另一个三年。也许从土耳其回来我就能晋升二级职员,我所在的那家公司一万多号基础层蓝衣员工,像我这样的大学生有三千多,其中五分之一揣着硕士本,每个人都憋着劲往金字塔顶上爬,粥少僧多,要是错过机会,下次就轮不上我了。我觉得我已经等够了,不能再等了。我觉得这件事我已经说清楚了。
“老头的后事是你处理的,你有经验,他俩一样。”哥哥用力拍了一巴掌脸,从那里拿走一只血肉模糊的木蠹蛾,“我们最终都得死,对不对?”
“他们不会再给我机会,我只有一次机会。”
我很恼火哥哥的不近情理。我不能确定他说“他俩一样”指什么,可我在一家拥有白金版现代管理体系的大企业工作,和他不一样,我不想做水客,没有“新义安”的人可以帮我,也做不到一次次往街头义务献血点冲,为自己积攒一大摞献血证,再去换积分,我只想他能帮我一次,就这一次。
“我进公司六年了,已经干腻了,不能永远都待在基础层,这样什么前途都没有。”也许就算去过土耳其也改变不了什么,我还是进不了骨干层,但至少我努力过,不会后悔,这就是我的想法。
还有,我们的确会死,但不是现在,现在要死的是姆妈,这个也不一样。
“你就不该去血汗工厂,”哥哥愤愤地扬手赶走头顶上的木蠹蛾群,“我早说过,那里听上去不错,但你活在别人的错误里,活在所有人的错误里,这回你爽歪歪了,我没说错吧?”他把一块虾肉拣进嘴里,吮吸一下吐到脚边,用脚碾,好像那是一块突然活过来的基因突变物,是他自己,他必须那么做才能拯救地球,“她到底想干什么,就不能忍一忍?”他满是怨气地瞪着我,这回没有一掠而过,看得很仔细,“她总是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要不是这样,情况会好很多。”
他说“她”,他指的是姆妈,自打我俩离开家以后,他就一直这么称呼姆妈。我想他这样是错的,要是姆妈不生下我们哥俩,这些事情都用不着了,也轮不上我俩在这儿谈什么情况好不好了。但他那么说并非一点儿道理也没有——姆妈不是病入膏肓,她的确有一些病,甚至可以说病得不轻,但还能撑一段时间,几年,或者时间更长一点。但她不想撑了,觉得没脸撑下去,撑不动了。
“我走不开。”哥哥说,口气不容置疑,“我这条腿要了我的命,它现在越来越不听使唤,而且我不会再回到那堆狗屎里去,永远也不会。”
“那我俩谁回去?”我问。
“别问我。”他说。
“总得有人回去。”我坚持。
“你问她,问她自己,看她怎么说。”他不耐烦到了顶点,操起酒瓶,把剩下的半瓶酒一气灌掉。
我没有回头去看海堤那边。我知道姆妈还在那儿,要是她听见了哥哥怎么说,她会难过。我还知道哥哥有情绪,我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父母把能够攒到的钱全都给了我,一分也没有给他。我读大学需要花钱,他出来打工应该赚钱补贴我,这就是父母当时的想法,为这个,他一直不肯原谅他们。但他把我们家所在那座方圆上百里的大山叫作狗屎,这是不对的,而且他也不该提他的那条腿,他那样是在冒犯黄泉下的父亲。
我在想我和哥哥离开家乡那一天,姆妈送我俩一直送到县城。七十多里山路,是真正大山里的路,要是走公路就得乘班车,姆妈不想把钱花在车票上,坚持走去走回。我和哥哥没带行李。家里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行李。我俩各背一只帆布包,包里装着换洗衣服。我的包破了,姆妈头天晚上替我缝好,家里为我攒的学费严严实实缝在夹层里。那天我和哥哥的表现不同。哥哥急匆匆走在前面,不断地朝路边的刺稞丛里啐唾沫,谁也不看,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绝。我有点兴奋,又有些不安,不知道到了学校以后别人会不会笑话我。那个时候我还不会说普通话,为这个我一直忐忑不安。父亲当时已经病了,他老是犯肝疼,怕花钱,硬撑着没去检查,自己到山里采了一些草药煎水喝,喝得人黑成一段漆木。姆妈本来不想送我俩,说她受不了,父亲非让她送,她就只能送了。
“他就想让我受罪,他就会这个。”背着父亲姆妈抱怨说,“他知道我会哭死,他自己也会哭死,但他让我受这个罪。”
发车的时候姆妈并没有哭。也许我看错了,但她的确没有抬手抹眼泪。脏兮兮的长途汽车从她身边驶过,她离得很近,如果不是车窗挡着,我都能摸到她被风吹乱的头发。她好像不相信车就这么开走了,不相信我们,她的两个儿子就那么离开了她,茫然地站在飞扬起来的尘土中,有点不知所措,有一只刚出生的小狗在她脚边歪歪倒倒地嗅着什么,但是一眨眼她和小狗都不见了。
“你什么时候回去?”我问哥哥。我们已经喝掉了三瓶啤酒,主要是哥哥喝,我象征性地陪他。我不能在南澳逗留太久,天亮以后就得赶回福永,不然就赶不上下午出境了。
“回去干什么?”哥哥困乏地抬头看我,好像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你以为是怎么回事,随便说一句你什么时候回去,我就得乖乖听着?门都没有。”
我看哥哥。他说门都没有,他说了那个话像是松了一口气,把酒瓶子往脏兮兮的桌上一墩,在沙锅里抓起一块鱿鱼丢给一只蹲在屋落里的猫。那只猫一直蹲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我猜它是在看哥哥,他们认识。我猜哥哥在等待这个时机,我是说,某种东西,它一直捆绑着他,令他困惑和痛苦,现在那个东西终于要断开了,“铮”的一声,他在等待这个时刻,然后他就彻底解脱了。
离我们不远的一个排挡开着一台短波收音机,食客比我们这个排挡多不少,都是附近客栈的旅游客,摊主不断地往桌上送去一些煮好或烤好的马鲛鱼、明虾、带子螺、花蟹和小柽子。收音机里正播着一个夜间节目,听众一个接一个往里打电话,主持人是个女的,她让打进电话的人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上,说自己遇到的麻烦,她再劝打进电话的人想开一点,念一些孔夫子的话,仁爱、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什么的,说一半掐断电话,进入药品广告阶段,糖尿病、肥胖症、抑郁症之类的特效药,然后主持人再继续念孔夫子的话。
哥哥回头朝收音机喊了一声。我没听清楚他喊的是什么。也许他不是冲收音机发火,但收音机立刻关上了,孔夫子也没了声音。坐在我们身边的一对年轻男女背包客结账走了。我注意到那个女的,离开时她回头看了哥哥一眼,目光中有一丝不屑。隔壁排挡也走了好几个客人,他们没吃完盘子里的炒河粉。一溜几家排挡,无论摊主还是食客都低着头吃东西。看上去情况有点不对劲,大家都有点怕哥哥。我是说,哥哥在这里很有威信,这和老乡告诉我的情况一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