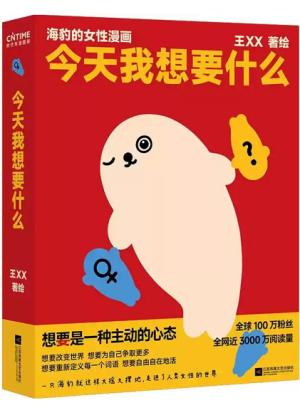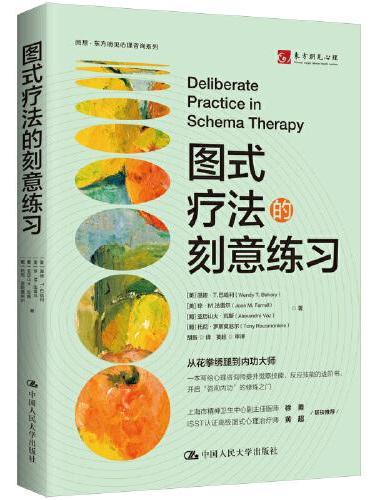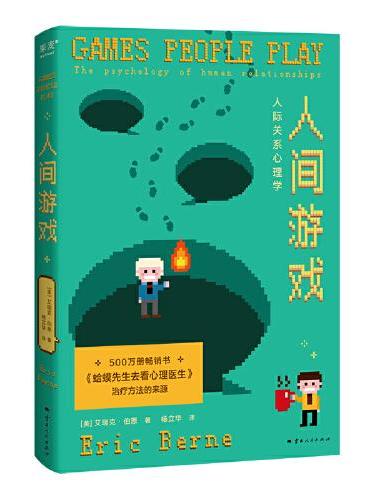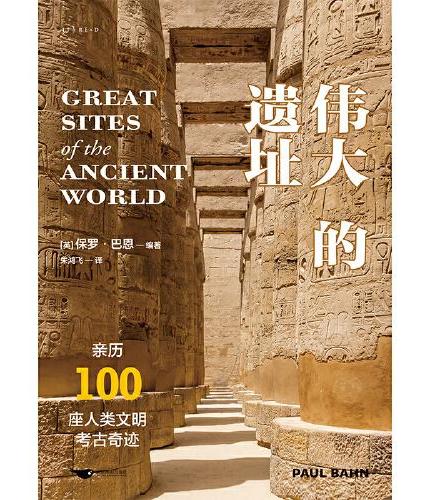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海外中国研究·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经典收藏版)--重构宋代文人的精神内核
》
售價:NT$
500.0

《
埃勒里·奎因悲剧四部曲
》
售價:NT$
14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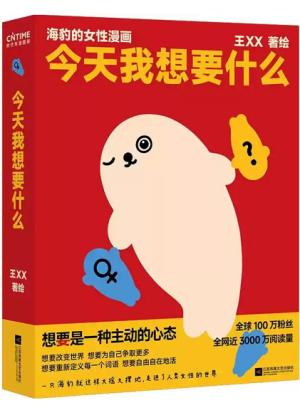
《
今天我想要什么:海豹的女性漫画
》
售價:NT$
347.0

《
日常的金字塔:写诗入门十一阶
》
售價:NT$
347.0

《
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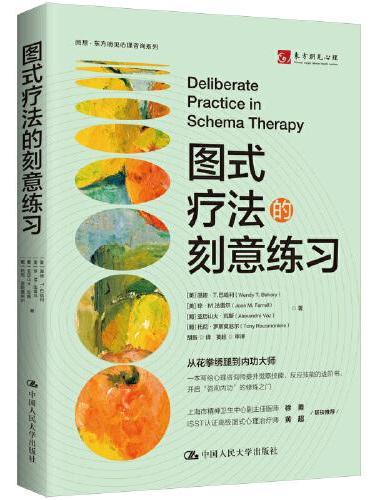
《
图式疗法的刻意练习
》
售價:NT$
4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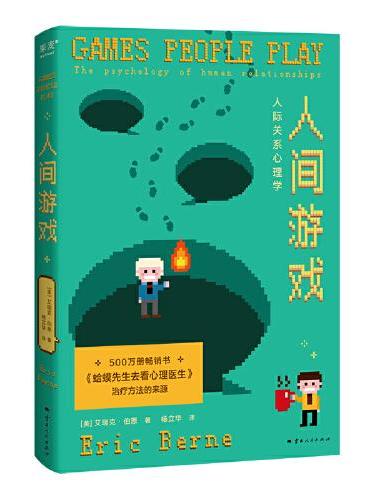
《
人间游戏:人际关系心理学(500万册畅销书《蛤蟆先生》理论原典,帮你读懂人际关系中那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
售價:NT$
2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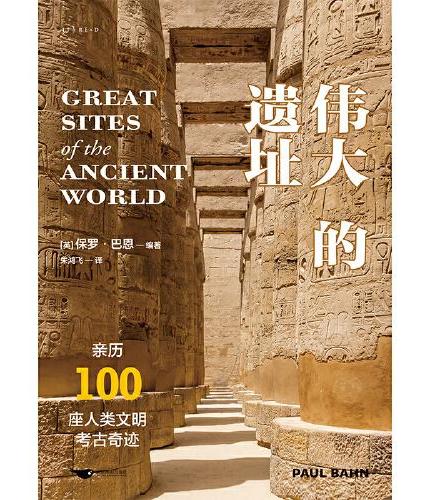
《
伟大的遗址(亲历100座人类文明考古奇迹)
》
售價:NT$
959.0
|
| 編輯推薦: |
当代知名女作家任晓雯长篇处女作。
莫言作品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女士隆重推荐译出。
当代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朱大可、张柠鼎力推荐。
在《禁闭岛》上,一群精神病人演绎《饥饿游戏》,结果变成了一场《大逃杀》。
|
| 內容簡介: |
“疯子”方秦珉被隔离到孤岛上,在那里遇到了一帮形形色色的“精神病人”。正当她逐渐适应岛上的生活时,一场大逃杀已经拉开了序幕。在不断逃亡的过程中,她无意中发现了岛上可怕的秘密,与此同时,她的记忆也渐渐恢复,拼贴出令人震惊的真相。
一部引人入胜不忍释手的小说,从头至尾紧张惊险,扣人心弦。
——陈安娜
|
| 關於作者: |
任晓雯
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毕业。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岛上》、《她们》、短篇集《飞毯》、《阳台上》,其中《她们》获2009年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提名奖。小说见于《人民文学》、《花城》、《钟山》、《大家》、《天涯》、《上海文学》等。随笔、评论等见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世纪周刊》、《新京报》、《书城》、《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纽约时报中文网等。学术文章见于《二十一世纪》(香港)、《东方》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瑞典语等。
|
| 內容試閱:
|
楔
明太太眼睛特别深。黄昏的暗色下,镜片不再反光,瞳仁就映出锈迹斑斑的天。我盯着那对眼睛,心想:这是明太太吗?这是她的声音,正读一本书。在字和字的间隙,她停顿了太长空白,每个句子都似没念完整。明先生听得一脸耐心,鼻翼的开阖节奏适中,像要配合字句抑扬。一只可乐瓶盖那么大的沙蟹,从脚背上蹿过去,他微抖了一下趾头。身边的人正仨仨俩俩离去。一个精瘦的老头,腆着不相称的大肚子,挽一名紫发少女。一对穿黑T恤的中年夫妇,高矮胖瘦差不多,五官也彼此相像。另有一些人,拎着躺椅、水瓶、毛巾垫被、折叠遮阳伞,陆续走远了。“谁在那儿?”明先生忽问。
我吓一跳。明太太顿了顿,继续念书。“没听见吗?我问谁在那儿?”明先生探一只手,拢在眉骨上远眺。
明太太变了脸色,书一扔。我大叫起来。
“嚷嚷什么!”明先生目光严厉,停到我脸上时,即刻变得柔和。“哼,眉来眼去的!”明太太瞪着我,“方蓁岷,你是不是偷我老公?”
我互搭着的指甲顿时煞白。“勾搭很久了吧,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慌里慌张看明先生。他别过头,给我一个冷冰冰的后脑勺。“哈哈,逗你玩呢。”明太太放肆地笑。她今天嘴唇特别红,睫毛分外长,笑容也媚。眼神被风吹散,一飘一飘,粘到男人心坎上。这不是明太太,平日她的目光在厚玻璃镜片里躲闪,像两坨放久了的劣质胶水。明先生递给我一厚本书。书皮像失血的面孔,正中几个大黑字,认得偏旁,组合起来又陌生。翻起第一页,空白,再翻,还是空白。我手掌渗冷汗。明先生不再有耐心地笑,指关节在膝盖上轻磕。眼神一碰我的脸,迅速跳开。黑颜色从地平线浩荡荡升起,把妃红的天和黛绿的海,一块一块吞噬进去。“给我书干什么?”“你说呢?”明先生大半个脑袋孵在阴影里。“为什么要我念?我不想念。”“哈哈,不念就不念,干吗生气,”明太太又笑,“说啊,方蓁岷,你是不是恨我。”“是的,我恨死你啦!”“哈哈呵呵哼哼——”明太太笑个不停,声音逐渐冷却,“那你杀了我吧。”嘭一下,枪响了。明太太倒地,双手仍捧住刚才朗读的书。我捡起那副飞到脚边的眼镜,架在鼻梁上。透过镜片,明太太又恢复令人生厌的模样。“蓁蓁,你把她杀了!”
“没有,不是,”我举起双臂,随手勾掉眼镜,“我哪有枪?”明先生指了指。我摘眼镜的右手,居然握一把枪。“不是我干的。”枪粘牢着,甩不掉。“就是你。”明先生逼过来,呼吸在镜片上喷出薄雾。我起身奔跑。散去的人群又包围过来。
“抓住她——”明先生扯起嗓子。
黑T恤夫妇紧跟在我身后,步子划一,嘴里嗬嗬作声;老头和女孩从斜对面包抄,她像一件大衣似地挂在他臂弯里。明太太的血如沙蟹般爬行神速,一下漫过脚踝。跌倒的瞬间,我瞥见身边有大沙洞,赶忙跳进去。黑天匍匐在暗地,像上眼皮搭住下眼皮。有人在头顶哭,有烟雾钻进眼鼻。我顺着黑暗奔跑。“小燕子,穿花衣……”一个尖嗓子从远方刺来。我循声而去。甬道慢慢透出亮光。“她醒了。”这句话从旋律的尾梢挤进耳朵,音调像在唱歌。“医生,帮忙倒点水。”脚步变轻,又响。有人托起我的头。清水渗入唇缝。“医生,你去工作吧,有我陪呢。”脚步顿了顿。门链发出金属纠葛声。木屑落在地上,微小的窸窸窣窣。我睁开眼,这个过程费力又漫长。看到一点,再看到一点。光线将视野渐次撩开。
第一章
1
美佳是我在孤岛认识的第一个人。据她介绍,东北面本来有姊妹岛,后与陆地逐渐黏连。站在孤岛北侧屋后,或者爬上东面小土丘,都能影绰绰看见陆地。但没人敢爬小土丘,因为它的另一边,是“禁林”。“千万别去禁林,最好想都不想。那里有电网,会电死你。”美佳有张幅员辽阔的脸。说话爱笑,嘴唇一翻,颧骨就凸起。在我昏迷的两个月里,美佳照顾我。她说她是我的同屋,也是岛上后勤总管。美佳讲这些时,我刚跑出杀人噩梦。看到光,听见美佳的声音。最后意识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
“包,包……”我的第一句话,声音虚飘。
“包?”美佳没头没脑地找,“啊,在这里!”
她把包从床脚拎起,拍掉灰尘,放到我枕边。我摸了摸,放心了。
阳光很好。风从木窗子钉着的几块花布间蹭进来。我躺在一间不大的屋里,正中并排两张床,床边凳上摆着瓶瓶罐罐,和一根表面磨花的体温计。床单是起球的麻布,白得污浊了。枕头形状古怪,枕套掉了线脚,裸出肮脏的棉絮,将面颊磨得痒痒。
美佳坐在床边,捏我的手,嗲声道:“记得波波吗,和你同车来的小男孩?他今天能下床啦,你也会很快好的。波波好可怜噢,他妈妈翻车时扑到他身上。儿子保护下来,妈妈却死了。告诉我,怎么半路翻车的?撞到树上吗,还是滑进沟了……”
我渐渐走神,注意起她的衣服:那是一只麻布口袋,开了几个洞,分别让脖子和胳膊伸出来活动。
“……只逃出来三个人,噢,不,四个,还有阿乌,他背你回来的。他也受伤了,不过他好壮耶,硬是救了三个人。阿乌是哑巴,他也说不出车是怎么翻的。血,都是血啊……”美佳有张疙疙瘩瘩的方脸,眉毛丛生,鼻孔粗大。眼睛倒还端正,但憋出矫揉造作的温情。见我在观察她,笑得更殷勤,一粒带咸湿气的唾沫星子溅向我。“……好可怜噢,波波全身上下皮肤烂透了。太惨了,太惨了。现在好了,结疤了,整天在那里喊痒……哎呀不说他了,你怎么样?让我看看还有没有烧?”她忽将额头压到我脸上:“好像不烧了耶,不过还是要给你量量的。别动,小心手上管子,你在吊盐水呢,小傻瓜。”她略带黏潮的手,摸得我冷。“我想休息。”“什么?”“我想休息。”
她花了几秒钟,弄明白我的意思。热情微微受挫,但很快恢复:“好吧好吧,你要我走开吗?”
2
我从带血的藏腰刀上确认了这件事。
刀长十几厘米,牛角刀柄缠着银丝,顶端箍有铁皮,刀鞘一朵古铜色雪莲花。精钢锻成的刀刃乌黑了——鲜血凝固的颜色。
他死了吗?一定是的。车子爆炸时,他身无遮挡。即便没炸死,挨一刀也够呛;哪怕刀伤不致命,也只好在荒山野岭等死——那个叫什么阿乌的,不可能有力气背他回来。
我将藏刀放好。包里还有一本书,都是我的宝贝。刀是段仔的礼物,书是明先生的纪念品。这只贴身小包是青山医院护士长发的,我管它叫“小青”。在医院时,整天挂于胸前。段仔笑我是袋鼠。后来我被医院绑出来,塞进闷仄的车厢,又逃生到孤岛,“小青”始终不离。它脏旧了,血斑、泥印、刮痕。包肚上的楷体字依稀可辨——青山。它们是从医院门匾拓下的。书写者腕力不足,“山”的竖划颤颤发抖。但护士长说写得好。“青山精神医疗保健中心”,烫金大字悬在门口,亮堂堂扎眼。有次她无意提起,说是市领导亲笔题字。妈妈说,小医院合适,有人情味,管理也好。还说市里重视小医院,经费足,设备药品比大医院好。“小青”是刚进院发的,还有毛巾牙刷,和一只搪瓷碗。护士给我理发,换病服,领进房间。“小青”拉链在离院时豁了,背带或是翻车时断的。都被缝补好,留下粗糙的线脚。我抖抖包肚,除了两样宝贝,还掉出一面镜子,几撮面包屑。镜面碎裂过,又被一片一片粘合。我想像美佳的粗手指,覆在窄小镜面上。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
3
书皮残破了。拆开,露出白色封面。随手一翻,有字被加了着重线。我想象明先生在书桌前,捏着墨绿木头铅笔,从书页上淡扫而过。他脸相端庄,戴金丝边眼镜,头发微乱,遮住镜脚。书桌是橡木雕花的,左手侧一个圆形茶杯烫印。他看书写作戴袖套,后来用了电脑,打字还戴袖套。不打字时,他抽烟,一根接一根。香烟的味道,我也喜欢,绒线衣袖上烟味浓厚。拉起他的袖子闻,他就用指节轻叩我的后脑勺。明先生,你亲我。明先生亲我。嘴湿湿的,印在脸上像沾过水的棉花。明先生,把眼镜摘掉,我看不清你。他反而把眼镜扶正,傻瓜,不戴眼镜怎么看书。书?我讨厌书。明先生送书给我,说是法国人写的,翻成了英文。他搞到了法文原版,就把英译本送我。英文法文爪哇文,我读不懂也不爱读。但这是明先生送的,必须喜欢。
明先生教导我,要多读书。我要多读书,不然明先生不爱我了。他和明太太都是博士,同一个系任教。他们讨论问题时,冗长拗口的词汇抛来掷去,仿佛撇下我,进入另一个富饶高深的世界。明太太肯定意识到我被拒之于外的苦恼,她会突然停下,征询我的意见。我就在她幸灾乐祸的镜片反光中,看到自己被夸大了的窘迫。在医院半年,我每天的必修课之一,是强迫自己盯住书里一页页字母。我没上过学,只在养病间隙,向家教老师学了皮毛。我瞎猜加联想。有时以为弄通了一句话,用指甲掐一道痕。过了半天,回头去看,又不能确定。于是我大叫大嚷,把被子撕破,搪瓷碗摔到地上。
我真是笨死了。因为我的笨,明先生才离我那么远。
4
“姐,你不笨,你聪明着呢。”段仔说,我只是有些走火入魔。
段仔是我在青山的唯一朋友。我自称是姐,他就喊我“方姐姐”。段仔父母下岗,颠沛愁苦,没精力管他。他和一帮哥儿们混,学着港剧,互称“仔”啊“哥”呀的。这样,他成了“段仔”。
段仔用偷自行车的钱染黄头发。因为不肯出卖“大哥”,被送工读学校。出来后继续鬼混,在工读学校几进几出。未满十八,不能进监狱,父母就把他送来精神病院。“我知道他们恨我,巴不得我死。自己都养不活,为什么要生我?不是不负责任吗?看着吧,我会活得好好的。”段仔说起父母咬牙切齿,我们有了共同语言。段仔说:“你妈有钱有气质,你为什么恨她?”妈妈只来看过我一次,段仔正好在门口碰到。问我那个“又漂亮又高贵”的女人是谁。我给了他几爆栗。段仔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当警察,因为“新警服很好看”。我说:“你当了警察,要为方姐姐的爸爸报仇啊。”关于爸爸的死,我印象模糊。妈妈说,我记忆不清是因为病了,吃药会好起来。我不信,妈妈才是我最大的病。这个坏女人,爸爸一定是她害的,现在又想来害我,这不,天天喂我毒药。阿婆说,我从外公死后开始吃药。那时年龄小,她把药片化在小匙里,加几粒砂糖骗我吃。世上只有阿婆疼我,但阿婆也得听妈妈的。段仔不信我妈歹毒,又怕我大呼小叫。安慰道:“方姐姐,你妈是个大坏蛋,我当上警察,就把她抓起来。”不久,段仔被远房阿姨接走,之后来探望我,说真要去当警察了。“姐,我准备考警校呢。”他低着头,觑着眼。“有出息。”“好玩儿,混混呗。”“段仔,我们这辈子见不着了吧。”“姐,说什么呀。我会来看你,或者你出来看我。”“恐怕我们不是同一世界的人了。”“怎么会?”段仔笑了,“除非你这个富家小姐不想见我。”我喜欢他笑。有十个大太阳从他的笑靥里升起。段仔找了张纸,把阿姨的地址抄给我。“以后我们一定会见的。”他送我一把藏刀,说是以前“大哥”赠的,会带给我好运。那以后,藏刀再没离开我。
5
段仔走后,“青山”愈发衰落。隔壁新来的疯女人,整日吵嚷,拿锐物往自己身上捅。他们套住她的手脚,钢链串起脚镣和手拷,固定在走廊尽头杆子上。她不知哪里弄来一片玻璃,割开手腕。一名卫校实习生,发现了满地血泊,吓得直僵僵尖叫,也有点疯傻。这件事后,不少病人被家属转走。运营维艰的“青山”,变成地区医院门诊分部。金字门匾被摘,留下我们拉拉杂杂几号人,锁在各自房内。每天听门外有人走动、哭泣、咳嗽、呻吟,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
禁闭的那段时间,早晚都得打针,脑袋涨痛,没完没了睡觉。我看见一些人在天花板上,认识的、不认识的。床边、屋角,挤满各种透明线条,水母触角似的动呀动。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但不意味着我在做梦。我能感觉我的手,我的胳膊,我正仰面躺在床上呢。护士小姐刚打过针,早餐吃稀饭榨菜,加两撮过期肉松,有股酸苦味。
我高高兴兴看天花板上的人们,他们像赶集,又似在露天剧院表演,有时停下来搭话,有时顾自走开。我的眼睛努力寻找明先生。他还是老样子,忽而亲切,忽而淡漠。明先生,明先生在哪里?他为什么不来看我?我在这里,全是因为他。但我不怨他,他是神,神是不会犯错误的,我这样的凡人才不完美。我的神游被入侵者们打断。那天护士打完针,进来两个壮男人,把以前对付疯女人的钢链铁索套在我身上。我叫喊,指甲抓他们,脚踢他们。但他们多有力啊。我虚脱了,被锁在床头。灯开了,满世界亮光。门锁咔嗒,很多张新鲜面孔,叽叽喳喳涌入。一个女人念书似的说:“小朋友,静一静。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最后一个精神病人。大家轻声,不许靠近,不要惊动她。”小朋友们噘起嘴,食指放在唇边,纷纷“嘘”着。几个孩子互相推搡,阿姨将他们分开。忽然,有小男孩问:“老师,我们的话她听得懂吗?”另一女孩更大声问:“老师,她生下来就有病吗?”提问声顿时此起彼伏。“老师,她从来不洗澡吗?”“老师,她爸爸妈妈怎么不管她?”“老师……”“老师……”我偏偏脑袋,让长发盖住面孔。身上衣服多脏啊,虱子、跳蚤、污垢。我突然羞愧了,扭动身子。铁镣“叮呤当啷”响。不知哪个调皮蛋,扔来一块橡皮头,砸在我脑门上。我尖叫。我能这么一直叫下去,直至整座房屋轰塌。小学生们呆住了。但只一瞬,制造出一堆更尖锐的声音,踩着挤着往外逃。也有几个胆大的,反而围近看究竟。老师喊:“同学们快走,疯子发疯了!”“疯子发疯了——”一个女孩叫。“疯子发疯了——”有人跟着嚷。“疯子发疯了——”……很多稚气的声音,在屋内、屋外、远处、近处。整个世界燃烧起来。
“疯子发疯了,疯子发疯了——”
火光里,天花板像蜡那样溶化,上面走着的人纷纷掉下:明先生、疯女人、段仔、阿婆……只有妈妈悬浮半空,大嘴巴能吞几十个人:“哈哈,你终于疯了,终于疯了……”“我没疯!”
我大叫,却听不见自己声音。所有东西被淹没,只留我独自在这儿。人们跑出去了,屋子暗下来。我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呼吸。毒链缠身,一切遥不可及。一只粗手撩起我满是针眼的胳膊,把注射器顶过来。更多双手横七竖八抓住我。我没疯,我要出去,我没疯,我要出去……一副大眼镜凑近:“把她搬到床上去,当心,手铐别解开。”“为什么让那些人来看我?”“根本没有人!”大眼镜哼一声,“除了我们,谁都不会来。”“小孩子,小孩子呢。”“什么小孩子,又是幻觉。”大眼镜转身,对护士长说着什么。护士长哗哗翻记录本。“状态不稳定。”大眼镜说。“尤其这两个月,越来越严重。”护士长把记录本啪地合上。“家属呢?”“联系过了,同意让我们处置。”“那可以把她送走喽?”我眼皮耷拉下来,手臂沉重,大腿发麻。重新醒来时,我的上身被缠个严实,腰里圈一根麻绳,一头绑在床边。护士长正解开它。
大眼镜冲我龇牙一笑:“你解脱了,他们带你去个更适合疯子待的地方。”随后,他们把我扔进车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