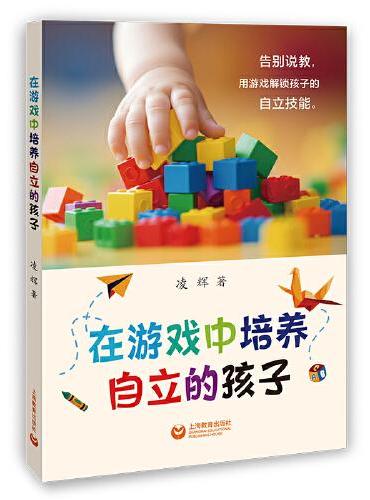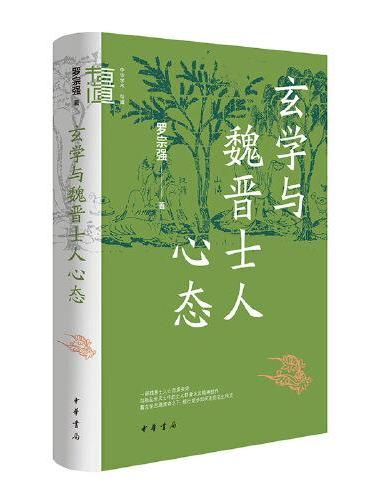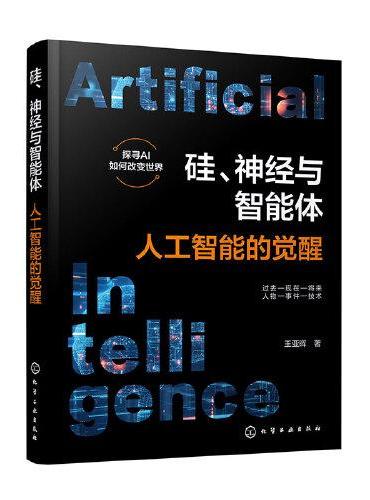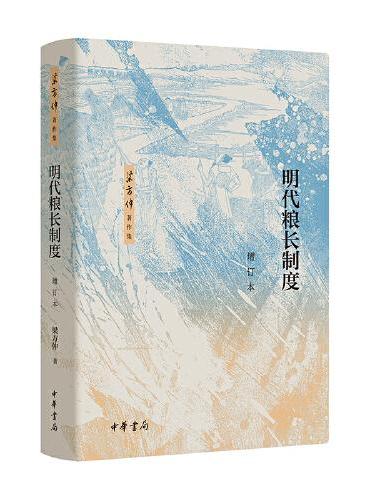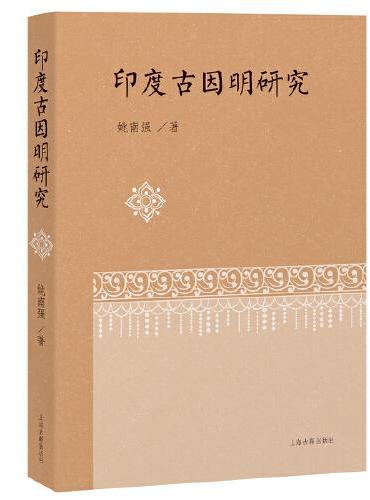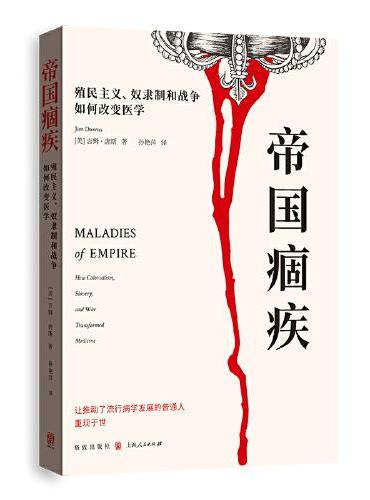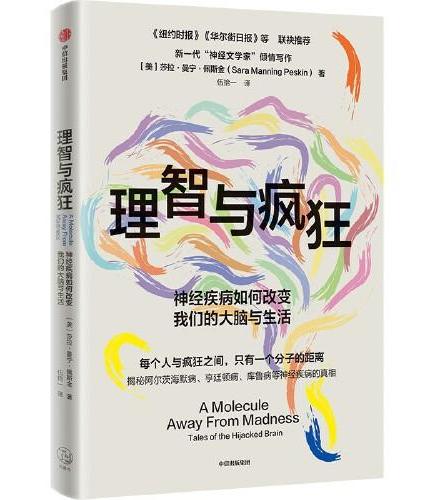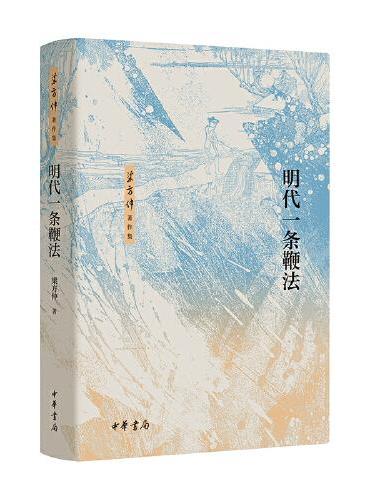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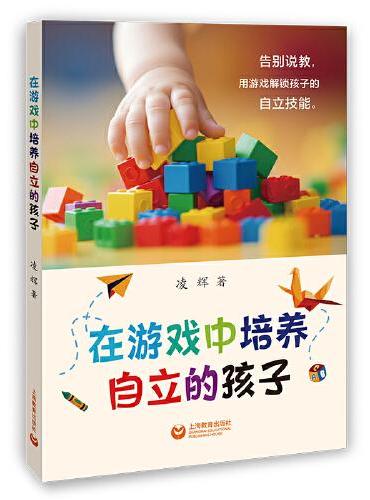
《
在游戏中培养自立的孩子
》
售價:NT$
2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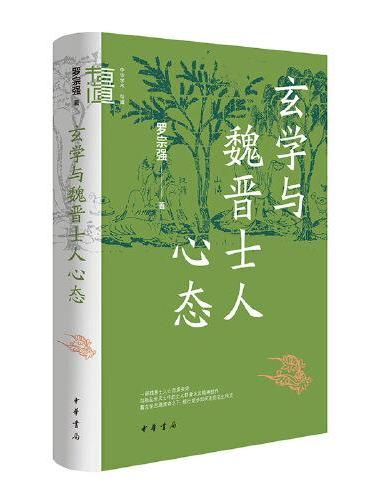
《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精)--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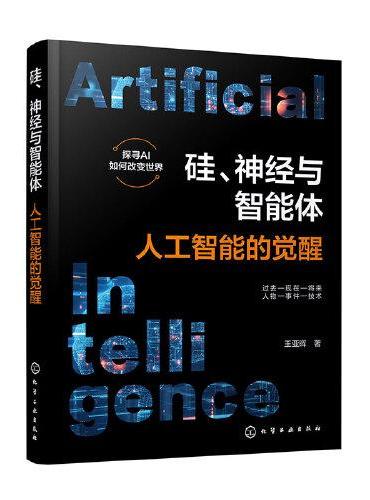
《
硅、神经与智能体:人工智能的觉醒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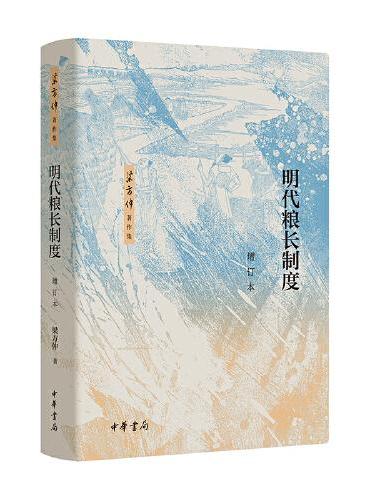
《
明代粮长制度(增订本)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3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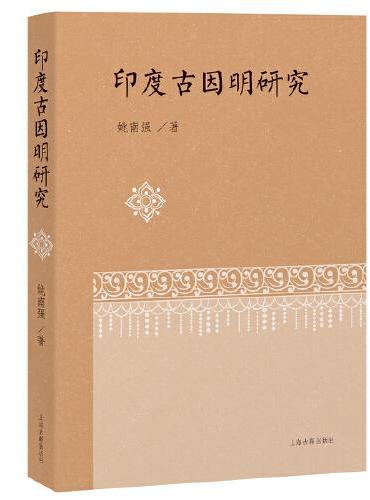
《
印度古因明研究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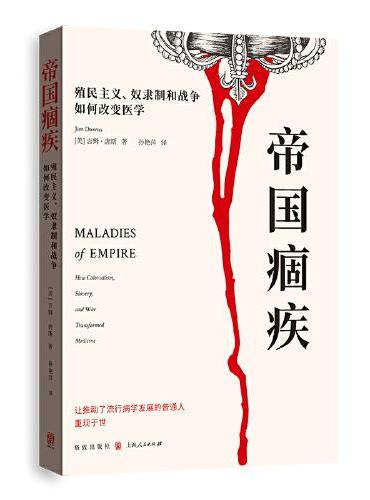
《
帝国痼疾: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如何改变医学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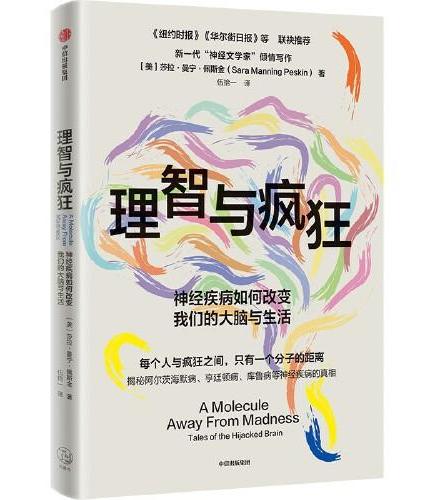
《
理智与疯狂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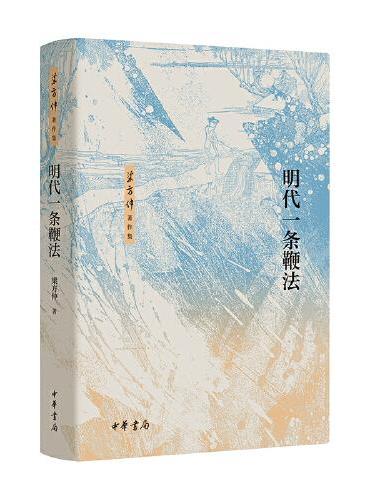
《
明代一条鞭法(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山田洋次,成长于中国东北,从卖鱼小贩到国民大导,创作超过一百部卖座影片;
山田洋次,艺术与商业共赢的常青树,中国最为家喻户晓的日本导演;
山田洋次,分享从影六十载的编剧、导演秘密,心路历程及艺术观念全公开;
细数片场趣事与生活感悟,带你感受“含泪的笑容”与“幸福的泪水”。
|
| 內容簡介: |
|
日本国宝级电影大师山田洋次在本书中将其几十年从影经历娓娓道来。其中既有编剧、导演的方法技巧,又有充满人性温度的生活细节。如同他的电影风格,山田洋次以平和而温暖的行文,介绍了自己从影的动机和愿望;论述了素材与剧本的关系;并以《寅次郎的故事》《幸福的黄手帕》等影片为例,分享现场执导的体会,探讨导演应具备的修养和能力。读者不仅能从中管窥山田洋次是怎样拍电影的,也会收获一份心灵的感动。
|
| 關於作者: |
著者简介
山田洋次,道尽日本人心事的电影大师,有“喜剧山田”、“庶民剧大导”之称,更被封为“日本人心灵的代言人”。他擅长反映平民生活的影片,主要作品有《寅次郎的故事》《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黄昏的清兵卫》《东京家族》《母亲》等。
译者简介
蒋晓松,1951年出生于上海市。电影导演蒋君超和演员白杨之子。文化人、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博鳌亚洲论坛主要策划人和推动者。其制作的电视纪录片《小木屋》荣获第28 届纽约国际电影节电视导演奖。
著者山田洋次 获奖状况
一生中在各大电影节曾获奖项18次,提名45次
奥斯卡金像奖
第76届2004 - 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黄昏清兵卫 The Twilight Samurai 2002
柏林国际电影节
第60届2010 - 柏林摄影金奖
香港电影金像奖
第23届2004 - 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黄昏清兵卫 The Twilight Samurai 2002
日本电影学院奖
第36届2013 - 协会荣誉奖
·第26届2003 - 最佳影片黄昏清兵卫 The Twilight Samurai 2002
·第26届2003 - 最佳导演黄昏清兵卫 The Twilight Samurai 2002
·第26届2003 - 最佳编剧黄昏清兵卫 The Twilight Samurai 2002
·第17届1994 - 最佳影片学校 A Class to Remember 1993
·第17届1994 - 最佳导演学校 A Class to Remember 1993
·第17届1994 - 最佳编剧学校 A Class to Remember 1993
·第15届1992 - 最佳影片儿子 My Sons 1991
·第6届1983 - 特别奖
·第4届1981 - 最佳编剧远山的呼唤 A Distant Cry from Spring 1980
·第1届1978 - 最佳影片幸福的黄手帕 Shiawase no kiiroi hankachi 1977
·第1届1978 - 最佳导演幸福的黄手帕 Shiawase no kiiroi hankachi 1977
·第1届1978 - 最佳编剧幸福的黄手帕 Shiawase no kiiroi hankachi 1977
亚洲电影大奖
第2届2008 - 亚洲电影终身成就奖
东京国际电影节
第17届2004 - 黑泽明奖
|
| 目錄:
|
上篇 我和电影
一 登上影坛
进松竹公司
从《二楼的房客》到《过分的糊涂虫》
《寅次郎的故事》的诞生
二 初看电影
《路旁之石》给我的深刻印象
新的发现
三 电影是什么
艺术是使人愉悦的
中学时代的经历
谈谈娱乐电影
当今文化的现状
四 电影与现实主义
落语和浪花节
现实主义的潮流
五 谈谈“滑稽性”
在“50日元食堂”的体会
生活感受与笑
六 观众与创作者的共鸣
信赖观众的丰富想象力
切肤之感
对“寅次郎”的共鸣
要尊重人
对现实的认识与电影
七 “寅次郎”与美国人
美国人的共鸣
面向本国的电影
谈谈卓别林
中篇 素材与剧本
八 冲动的力量
强烈的创作欲望
《家族》的诞生
《寅次郎的故事》的诞生
《幸福的黄手帕》的诞生
我想拍的电影
《同胞》的诞生
九 谈谈剧本
《砂之器》的剧本
技巧的模仿问题
《无法松的一生》
感性的重要性
下篇 拍摄现场
十 我的导演工作
舞台与电影一样
棘手的分镜头
十一 导演与摄制组成员
心心相印的摄制组成员
摄制组成员的努力
十二 《寅次郎的故事》摄制组
我的朋友们
本色的演技
十三 导演与演员
演员的经历与成长
导演的责任
span style="
|
| 內容試閱:
|
进松竹公司
我是1954年(昭和29年)进入松竹公司的,当时投身影坛的我并没有明确目的。要说有什么动机,只是因我在大学时代曾参加过电影研究会,接触过一些电影界人士,觉得他们性格爽朗、情绪乐观。我想,如果将来能在这些人的圈子里工作那该多好啊,这种模糊的憧憬成了我报考电影工作的动机。这次考试也真走运,居然及格了,如果落榜,我也许会走上与此截然不同的道路。1954年和1955年,正是日本电影的繁盛时期。也是东宝罢工刚刚结束,以被清洗的赤色电影人士为中心的独立制片社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这时影片产量也很高。松竹摄制的《请问芳名》(1953)、《二十四只眼睛》(1954)等影片票房成绩极佳,它并拥有小津安二郎、木下惠介、涩谷实、川岛雄三等出类拔萃的导演。
当时由于就业困难,人们被电影企业的繁盛所吸引。报考松竹副导演的人员蜂拥而至,竟然有二千人之多,我是其中之一。其实,我成绩并不怎么理想,当初本不会被录用,不过,凑巧当时日活公司恢复拍片,松竹的副导演西河克己、今村昌平等许多人被拉了去,因而有了空缺,所以才把我补充进来。
我是从中国撤退回国的,所以大学时代一直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而今侥幸进了松竹公司,我记得十分清楚,首先领到了饭票,到了食堂看到盛得满满的大碗米饭,顿时感到一种由衷的幸福,心想,这下总算可以不愁吃了。当时我的工资和其他职业相比也不算低。
就这样,我当上了副导演,因为我的工作只是手拿着场记板,溜溜达达、东游西逛,就可以拿到工资,感到十分幸福,所以也就没有想当导演的远大抱负。原因是我以为自己没有当导演的能力。和我同时进公司的大岛渚在这一点上就与我不同,他好像一开始就确信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导演。果然,他不满三十岁就当上了导演。
我在很多方面和他截然相反,如果说只有像他那样才华横溢的人才能当导演,那么我想自己就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可是,孩子长大了,单靠副导演的微薄收入,在经济上也很困难,所以得想法当上编剧。我觉得当一名编剧也许有希望,于是就孜孜不倦地写剧本,边写边学。写剧本的才能多少也得到了公司的承认,主要是和野村芳太郎一起写他导演的剧本。
后来,随着新浪潮的兴起,我周围的同龄人都非常神气地当上了导演,纷纷执导他们的处女作,这时我才注意到只有我一个人还是老样子,光写公司指定的剧本。而且写公司指定的剧本,也很少是由自己独立完成的新作,大多是老编剧草就的作品,由于导演与公司觉得还不够满意而让我加工。
其中有第一部宽银幕作品,是一位老导演执导的《被拥抱的新娘》(1957) ,这部影片被誉为典型的松竹喜剧杰作。因为担任该片主演的高桥贞二在拍片中途死于车祸,留下了一半以上的场面未拍,所以必须想办法改写剧本。这样,公司就把这令人头痛的任务交给了我。因为我在野村先生手下干的工作主要也是拍喜剧片,所以我写的几乎全是喜剧剧本。
可是当时我想,假如我当了导演,恐怕绝对拍不了喜剧片,就自己的能力而言,无论从哪方面讲,只能拍些调子低沉的爱情片。后来我才重新认识到,是不是我仅看到了自己外表上的认真严肃的样子,而没有发现自己内在的松懈、爱开玩笑和随便的性格呢?
当时的副导演为了学习,都写剧本,而且为了提高,经常公开各自的作品。大岛渚他们写剧本的方法是先定主题,然后再树立人物形象、规定情景等等,显得很有气魄。可是我只能写随处可见的,例如面条铺的姑娘和菜店的小伙子谈情说爱的剧本。所以,总让大家瞧不起。他们问:“为什么你写的净是些平凡的故事?”别说人家笑话我,就连我自己也有同感,所以对自己的作品不可能有自信。不过,我也只能写些这类的作品。所以,当时我有些绝望,总觉得自己只会写些发生在自己周围和自己最熟悉的事。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有幸结识了作家早乙女胜元先生,向他倾吐了自己的苦恼,他安慰我说:“我也和你一样,只会写些平凡的故事。可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从《二楼的房客》到《过分的糊涂虫》
在这期间,我好歹也写了不少剧本,加上野村导演的推荐,公司领导决定让我担任导演试试看。那个时代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拍了一种叫作SP的短片,这种短片兼有考查导演和演员水平的目的。大岛渚的《爱与希望之街》(1959)也是这种性质的作品。公司对于这种实验短片根本就没指望卖座,如果从中能产生几位有培养前途的导演,就足够值得高兴的了。而我们纯粹是受惠于这种良好的环境。这种实验短片比一般片子短些,只有一小时左右。
按此要求拍摄的就是《二楼的陌生人》(1961)。原作是部推理小说,所以我竭尽全力把它改编成富有推理色彩的剧本,不知怎么搞的,结果拍成了带有喜剧色彩的作品。尽管公司对影片的好坏未置可否,我也没得到什么赞扬,但我因此体会到了导演工作的乐趣,也感到非常充实。至于影片的成就如何,我虽没有自信,但也没有感到太后悔。当然,在改编剧本和执导过程中,我饱尝了艰辛,然而心灵深处也得了一些欣慰。虽然我因这部处女作被搞得精疲力尽,但从某种意义来说的确因此而有了得救之感。
我导演的第二部影片是《市区的太阳》(1963)。当时,倍赏千惠子演唱的《市区的太阳》这首歌深受欢迎,所以公司计划以这首歌为主题歌,拍摄一部歌曲音乐片。公司把倍赏千惠子和胜吕誉称作“太阳的情侣”,以此招徕观众,并要求以其为内容拍一部主题歌贯串始终的、具有柔情蜜意的青春歌曲音乐片。然而我导演的《市区的太阳》,主题歌只出现了一次,不但没有柔情蜜意,而且恰恰相反,拍成了一部十分拘谨、总显得那么低沉的影片。
其实,在该片开拍之前不久,当时的公司经理城户先生还把这个剧本说得一无是处,因此,我一边拍片一边骂娘。不知是否受了我的情绪的影响,《市区区的太阳》这部影片充满了我以后导演的影片中所没有的抑郁情绪。所以,我对这部作品颇有亲近之情。但是,从影片整体来看,拍摄手法和素材很不一致,力不从心之处非常之多,事实上观众看了也不会舒服。如果说有值得赞赏之处的话,我想那就是年轻的演员倍赏千惠子那富有魅力的演技,她犹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蓓蕾,充满了活力。
把影片拍成这个样子,公司方面好像很为难。但是,当时的制作部部长白井昌夫先生并没有当面对我发火。白井先生深深地吸了口气说:“如果这种影片受欢迎那就没问题了。”白井先生当时说话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是非常婉转的训斥。该片自然在发行方面也不怎么好。
翌年,我导演了由花肇主演的《过分的糊涂虫》,这部影片的评价还比较高。此后。我和花肇合作,连续拍了八部影片。
《过分的糊涂虫》的原作是藤原审尔的中篇小说《院子里的一株白木兰》,小说以濑户内海的某村镇为舞台,描写一个少年同一个叫安五郎的流浪汉结交成朋友的故事,采用的手法是通过这位少年的视野展现安五郎对往事的回忆。原作由许多回忆片段组成,从故事情节上看,很难改编成电影剧本。但是,我很喜欢这篇小说,而且我同小说中的那位少年一样,很喜欢安五郎这个人物,所以我很珍惜这种感情,就把自己读这部作品时的感情如实地搬上了银幕。也就是说,我按小说原来的结构,把它改编成了由一个个回忆片段组成的、乍一看结构似乎是很简单的电影剧本。如果按起承转合这种结构方法处理,这种依样画葫芦的剧本改编法真是一种冒险。但实际上,继这个作品之后,我的剧本几乎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当然也包括《寅次郎的故事:男人之苦》(1969)。
当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拍片预算很少,本来应该去濑户内海摄制外景的,由于经费不足,只得把千叶县的鸭川当作冈山县的市街来拍了。同时,日程安排也相当紧,我只好废寝忘食地拚命拍摄。拍完之后,把胶片接起来一看,影片根本没有连贯性,这里说的“连贯性”是制片厂的行话,意思是情节展开要自然,感情描写要平稳,然而,这部影片看上去支离破碎,好象是胡乱地把胶片接在一起的。而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能使人哈哈大笑的场面,只能让人感到呆板,毫不连贯。我绝望了,我几乎被这种绝望压垮,甚至想到,“如此彻底失败,就此罢手吧”。很久以后摄影师高羽告诉我说,那次看了样片后,我在工作室的椅子上低头默然坐了整整一个小时。
不久,首次公映的日子来到了。我没有勇气去影院,躲在世田谷住宅区的自己家里正发愣的时候,制片人打来了电话。我忐忑不安地握着话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制片人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你马上到影院来,上座很好.观众都在哈哈大笑呢。”我怀着不敢相信的心情赶到了新宿的首轮影院,一看果真像制片人说的一样。我记得很清楚,观众们一边大笑一边看着我的影片,而且是我完全料想不到会引起观众发笑的场面竟然博得了哈哈大笑,我不禁愕然了,在电影院里思忖着:“如果观众认为这部影片滑稽可笑,那么,我也许能搞喜剧。”
继这部影片之后,我拍了两部“糊涂虫”连续剧,三部“一发必胜”的连续剧,之后又拍了《如果运气好》(1966)、《吹口气就会飞走的男人》(1968)等片,此后就着手拍《寅次郎的故事:男人之苦》了。
《路旁之石》给我的深刻印象
我在小学一二年级时看的影片几乎都是喜剧片。
那时,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他在南满铁路公司工作),当时我住在中国东北。父亲爱看电影,时常带我去散步,顺便去影院看一场电影。我还记得,傍晚时分父亲对我说:“跟我去吗?”我总是异常地兴奋,心想,今天又能去影院看电影了,于是便装做老实听话的乖孩子,跟着父亲去散步。每当走到电影院门口,父亲停下脚步注视广告或剧照时,我总是紧张地察看着父亲的表情,心里催促道:“快进去吧,快进去吧。”每当掀开电影院的门帘,走进一片漆黑的大厅时,我会产生—种整个身体像被吸进了另一个世界,紧张得直打颤的惬意之感,使我念念不忘。
看电影时,我经常放声大笑。因此父亲总是唠唠叨叨:“带你去看电影够麻烦的,瞧你那傻笑,成何体统!”那时,看的榎本健一啦、花菱啦等演的喜剧片中的一些场面,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虽说尽是些无聊,荒谬、胡诌的片子,倒也别有风趣。不知为什么,这种有趣的片子,今天已经绝迹了。
少年时代看的影片,留在我记忆中的都是喜剧片。喜剧以外的影片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学二年级或三年级时看的,由田坂具隆导演的《路旁之石》(1926)。那时,有一个叫阿文的姑娘在我家当佣人。当时到中国东北去当女佣的,大都是些在日本生活不下去的贫困的农家姑娘或渔家姑娘。阿文就是九州五岛的渔家姑娘,她所讲的故乡五岛的美丽景色,我这个对日本一无所知的日本人听起来,简直成了我所没有看到过的异国风光,勾起了我的想象和向往。
这位阿文姑娘曾和我一起看过电影。当时正是李香兰(即现在的山口淑子)红得发紫之时。李香兰和长谷川一夫二人合演的《白兰之歌》(1939)上映之后博得了高度评价。当时的详情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阿文姑娘是这二位演员中一位的崇拜者,她可能跟我父母说想去看这部影片。我母亲担心一个年轻姑娘独自外出会发生意外,虽说我只是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但两人结伴总比—人好,于是母亲对我说:“你也一起去吧。”我喜出望外,因为能看场《白兰之歌》嘛,我连声答应便去了。当时,电影院一场放两部片子,那天同映的片子是《路旁之石》。我从来没听说过《路旁之石》这部影片,我的目的是看《白兰之歌》。那么,这部《白兰之歌》是什么情节,我现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相反,同映的《路旁之石》一片,在相隔四十年之久的今天,我却记忆犹新。当时,我好像看外国影片似的,想不到“内地”有这种生活。它之所以是一部优秀影片,因为它能打动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特别是最后一场戏,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些镜头——擦着灯罩的少年吾一被蛮不讲理的小姐臭骂了一顿,吾一忍无可忍,气愤地将灯罩摔在院里的铺路石上,又把擦好的三四个灯罩全摔了个稀巴烂,然后一手提着用包袱皮包着的行李,当着那位被惊得呆若木鸡的小姐的面,飞也似地跑出她家。少年吾一趿着木屐,走在昏暗的小胡同里,发出咯嗒咯嗒的响声,不久便来到了大路.漫无目的地向着远方走去。一辆有轨电车慢吞吞地驰向前方……
去年电视里又播放了田坂具隆导演的《路旁之石》,使我有幸能在四十年后再度欣赏这部影片,最后的—场戏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除了跟拍少年吾—走在胡同的镜头格外长是这次新的发现外,结尾仍然是一辆有轨电车慢吞吞地朝着前方驰去。电影是多么美妙的艺术啊!我为此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
新的发现
《路旁之石》对我具有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作品本身出色。
比起作品来,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坐在我旁边的阿文看此片时扑簌扑簌直流泪的情景。我是带着—种看国外奇闻的心情看这部影片的,而对阿文来说,影片里所描写的事情完全是她的生活。就连我这颗幼稚的童心也能体会到:啊,少年吾—的生活和阿文姑娘太相似了,我好像茅塞顿开,理解了阿文的生活经历。
我很喜欢阿文,但是,那时我还年幼,还不是对她的生活、人生认真思考的那个年纪。当时,能使唤佣人的,最起码也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我处在这种地位,免不了要把阿文当作女佣人而轻视。当看到阿文为少年吾—的命运而潸然泪下的情景时,我这颗幼小的童心大为震惊,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啊,这部影片可以说不是为我拍的,而是为阿文拍的。
居然有这样看电影的人——他们把电影里所描写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亲身生活经历而沉浸在电影中失声痛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发现。当然,看了《路旁之石》也有我的感受,然而阿文的感受与我却大不相同,她把影片的内容当作自身的生活写照,好像其中的主人公就是她自己。这种影片欣赏法也许是我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在看榎本健一的喜剧时,哈哈大笑,忘乎所以的我在对电影的态度上与阿文相比有很大的距离,说起来我不过是观赏电影而已。
我拍电影时经常回想起这段少年时代的经历,而且至今还使我联想起许多问题。例如,我认为欧洲人(只限于欧洲人,因为我认为美国情况稍有不同)对电影的欣赏方法和日本人对电影的欣赏方法差异甚大。把影片中出现的人物看成是自己的亲兄弟—样,边看边产生共鸣的欣赏方法,不是欧洲人的欣赏方法。说具体一点,像阿文这样流着眼泪把影片中的人物和自己融合成一体,或者身临其境的积极欣赏法,我怀疑欧洲人是很难做到的。
欧洲人在拍摄以欧洲人为题材的电影时,有某种独特的、反映自己生活的感受。因此,有时影片拍得很好,我们往往看得出神,仿佛我们也成了欧洲人似的。而我们日本人在拍摄以日本人为题材的电影时,不能用欧洲人观察欧洲人的方法来观察日本人自己。我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慎重考虑的话,就容易陷入莫名其妙的错觉之中。
归根结底,电影这种艺术并不是日本的电影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欧洲的电影只有欧洲人才能理解,我认为:关于日本人是怎样看待日本人这个问题,同外国人在看日本电影时,也会感动和兴奋一样,比如说,酱汤对日本人来说是何等的鲜美,外国人是绝对难以理解的。但他们一定能想象出他们与之相当的东西,并为此而高兴。就是说,如果日本人认为,酱汤的独特味道外国人未必理解,那么,外国人也是会理解这一点的。这是我在国外旅行时所想到的一些问题。最近,有些影片虽然是日本影片,但它却以外国人观察日本人的眼光来描写日本人,或者相反,以日本人观察外国人的眼光来描写日本人.这类影片我好像经常看到。
谈谈娱乐电影
柳田国男在他的著作中一再主张,艺术必须要有娱乐性。今天,我们还应该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到,要创作出一部具有娱乐性的作品是何等的艰巨。
我对那些在《男人之苦》—片中常常出现的江湖艺人——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过他们的演出,也不了解他们的现况如何——抱有一种奇妙的景慕和亲近感。虽说演技并不高超,但他们为了博得观众的喜悦而竭尽全力进行表演,把生存中一切的喜悦都寄希望于观众的犒赏。凡是这样的人,和我们是一家人,都是兄弟的关系。
已经是至少十五年前的事了,我曾和工会的一些人就电影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反复探讨。当时,某大公司的一位工会领导发表高论说:进步电影必须是如此这般。我问那位领导:“您最近看了些什么电影?”他说,因为工作忙几乎没怎么看。当时正是植木等的《无责任时代》(1962)一片风靡一时之际,他便补充道:“前些时候看过一部名叫《无责任时代》。”顿时,大家哄堂大笑。大概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便搔搔头说:“不过,疲劳的时候还是想看些喜剧影片。”算是为自己解了围。但是,当时我觉得这人说话真怪,不看电影就对电影问题大发议论。
更奇怪的是,他自己根本不愿看进步影片,却大谈特谈进步电影必须如此这般,还说疲劳之时也想看些喜剧片。这真令人不可思议,难道这人不知道自己说话自相矛盾吗?疲劳之时想看些有趣的影片是人之常情,是人们极其自然的愿望,可他为什么不从这种人之常情的欲望出发来看问题呢?当时我就想拍些民众疲劳之时想看的娱乐电影,而决不去拍那些工会干部和搞电影研究的大学生们在这种会上大发议论的那种电影。
细细想来,当时不仅是电影工作者自己蔑视娱乐影片,甚至连那些要我们拍影片的资本家或者公司也根本瞧不起这类影片。恐怕日本电影的衰落就是从此开始的吧。我觉得,在电影工作者中,有许多人认为:拍娱乐片是二流导演的事,总想自己有朝一日当上一流导演,把川端康成的原作改编成电影,拍成文艺巨片。
最近我又碰到了这样一件事。某电视台的制片人找我谈他的计划:“我不想把这个剧本拍成单纯的青春电影,所以想请您来搞。”我说:“请听我说,要我搞的话,我就把它拍成单纯的青春电影。”他又说:“你嘴上说得轻巧,你以为你所说的单纯的青春电影就那么容易拍成吗?”
与此同样,常常听到有些人评论影片时常以赞赏的态度说“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娱乐影片。”可是,我认为,就是这些评论家们根本没有很好地思考过什么叫娱乐电影。满不在乎地说不是单纯的娱乐电影之类话的人,实际上不过是以为艺术这门学问,任何人只要想搞就能轻而易举搞好的人而已。
我的结论是,艺术产生于作家那使人愉快、欢乐,而其本人恬淡无欲的精神,这种精神越旺盛,越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诚然,如此创作出来的作品里也会有毫无价值的东西。但是,在一百部、二百部的作品里,肯定会有那么一二部优秀作品,堪称艺术而流传于后世。不重视娱乐的人就不能称为艺术家。那些声称自己不想拍单纯的娱乐电影的说法以及在概念上把艺术和娱乐对立起来的想法是绝对创作不出杰出的艺术作品的。
现实主义的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及战后,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等人为首创作出了一批新现实主义作品,引起了世界各国电影界人士的强烈反响。新现实主义也称为半纪录主义。摄影师走出摄影棚,用纪录片的形式拍摄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例如把米兰、罗马的街道,那儿居民的真实情况如实地摄制下来,再把这些现实生活和虚构中的主人公融合为一体,使观众感到自然和谐。这要按以前的电影常识来看,是一件难以想象、大大出格的事。
在新现实主义诞生以前,好莱坞的电影都是在摄影棚中拍成的。譬如为了拍摄纽约大街就必须搭一个庞大的外景,让临时演员走来走去,让车辆在景内行驶,以此取得真纽约一样的效果。而意大利的现实主义者却用摄影机如实摄取罗马街道和人群的场面。这种拍片法是电影史上的—大变革。
美国杰出的导演达辛(Jules Dassin)等继承了这种新现实主义的方法,创作了《不夜城》(The Naked City,1948)这一优秀作品。从此以后。以摄影棚为中心的好莱坞电影的声誉一落千丈。当今美国生产的优秀影片,几乎都是以真实的外景为主,而不是在摄影棚里拍成的。以前一直认为,在摄影棚里拍片,导演支配画面上的一切,而外景拍片,由于各种不需要的因素过多地混进画面,以致画面显得不完整,效果很差。所以,被誉为完整主义的巨匠们,例如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他们的导演工作都是以摄影棚为中心的。而新现实主义创造的方法可以说把电影作家从以摄影棚为中心的想法中解放出来。如何通过摄影机把现实生活反映在画面上,这个问题和作家的感性或者认识有关,而且从拍摄的画面之中会发现什么,这一点,作家和观众都可以体验,同时也必然涉及作家的想法、心情、主张或思想。
电影的本质是蒙太奇,这一原理至今未变。但现在已经奄奄一息、日暮途穷的好莱坞影片以及日本影片中,大部分影片是把蒙太奇原有含义的一部分内容,大大扩展并完全倚靠它而拍成的。换句话说,蒙太奇成了徒有虚名的形骸了。至于电影的蒙太奇问题必须进一步研究,但这不是说单纯地研究镜头的蒙太奇,而是有必要扩大研究范围,研究一场戏的蒙太奇、一个片段的蒙太奇。在这个基础上再汇总一下,有必要对全面情况进行考虑。
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对于现实地表现真实的手法上,常常犯极大的错误。为了真实地反映残暴性,必须以写实的手法描写流血,于是就研究与真血相似的血浆。名副其实地打开一条“血路”。当然,我认为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如果一部影片只靠这些吸引观众,那么只能说这部影片是荒诞不经的变种。
我经常这样想:所谓现实主义就是更加丰富地表现现实的方法,它不是生搬硬套现实,必须更有想象力,更有创造力。
在“50日元食堂”的体会
虽说我拍了不少喜剧片,但是还常常认真地想:“什么叫滑稽?”“什么叫笑话?”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滑稽。不过,如果说把这个问题搞透彻了就能拍出喜剧,我看也并非如此。
span style="font-famil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