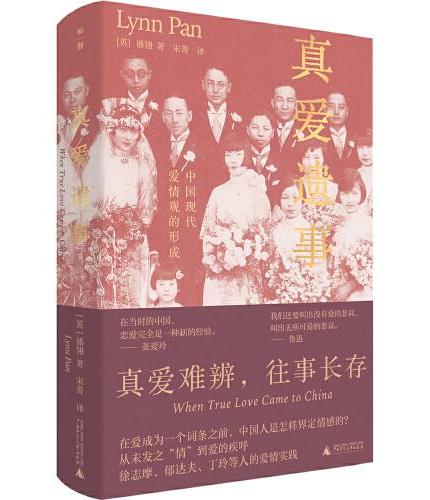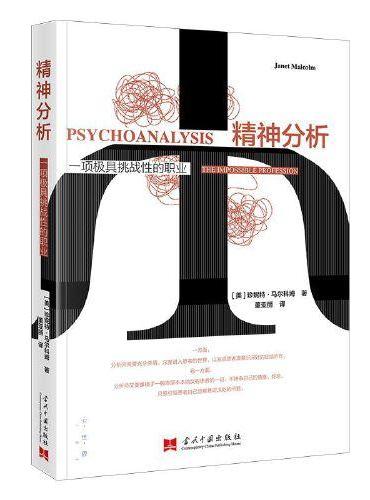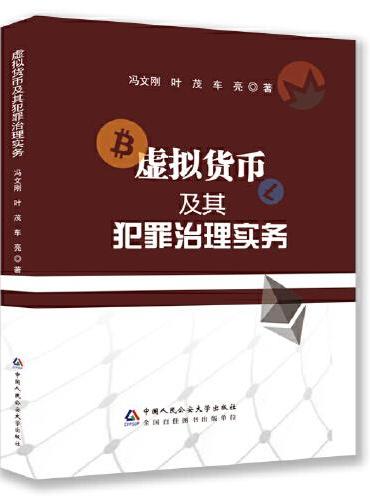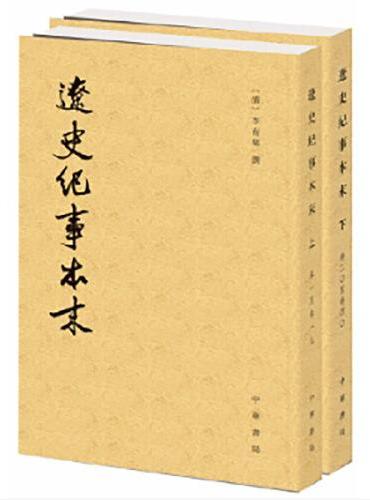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牛津呼吸护理指南(原书第2版) 国际经典护理学译著
》
售價:NT$
959.0

《
窥夜:全二册
》
售價:NT$
407.0

《
有底气(冯唐半生成事精华,写给所有人的底气心法,一个人内核越强,越有底气!)
》
售價:NT$
347.0

《
广州贸易:近代中国沿海贸易与对外交流(1700-1845)(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国际知名史学家深度解读鸦片战争的起源!)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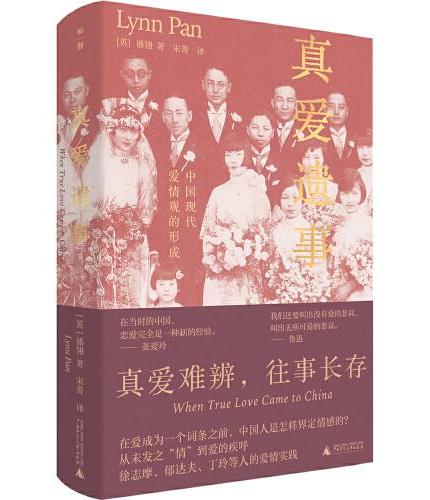
《
真爱遗事:中国现代爱情观的形成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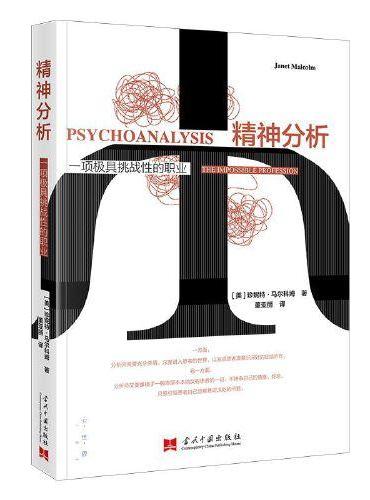
《
精神分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职业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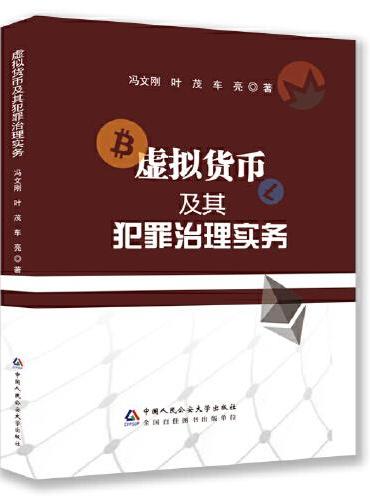
《
虚拟货币及其犯罪治理实务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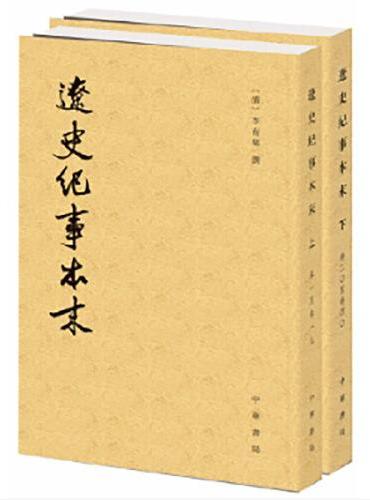
《
辽史纪事本末(历代纪事本末 全2册)新版
》
售價:NT$
500.0
|
| 內容簡介: |
抗战时期的天津形势几多险恶,年轻的地下党员刘海涛工作、斡旋在一个汉奸杂志社里。
看他如何以顽强意志、聪明智慧和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把这家杂志社变为了地下交通站,在敌人眼皮底下演出了一幕幕让人叫绝的抗日活剧。
|
| 關於作者: |
|
岩波——原名李重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河北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宏创乐途文化公司作家顾问,天津文化艺术传播公司主任编剧。曾出版作品多部,近400万字。
|
| 目錄:
|
第一章 凶残日寇3
第二章 两条战线上的骁将16
第三章 英雄豪气28
第四章 意外的任务41
第五章 老蒋部下评说老蒋53
第六章 救命药品66
第七章 夺军马78
第八章 日本顾问酿的血债91
第九章 宿 敌103
第十章 茅厕之计116
第十一章 浴火女人129
第十二章 血腥慰安142
第十三章 清 剿156
第十四章 刺杀目标170
第十五章 壮士西去182
第十六章 跤场的下九流194
第十七章 雄关漫道207
第十八章 矢志不渝220
第十九章 年轻人之间的意外较量234
第二十章 日军投降后的疑案247
尾 声260
后 记266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凶残日寇
满地打滚的枯叶还没有被秋风刮净,初冬的第一场小雪已经天女散花一般漫天飘舞了。与寒冷肃杀的天气相对应的,是1942年日军进行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半年后的一天,对日军顶礼膜拜的天津《东亚晨报》在二版头条位置登载了这样一条让人触目惊心的消息:
“共产党交通员王三身上携带重要情报,在蓟县卡口遇大日本皇军搜检,王三拒不交出,而是吞咽腹中,于是遭大日本皇军的刺刀穿膛,切开胸腹,后被石磨碾成肉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还望国人吸取教训,积极配合大日本皇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做顺民做良民,远离一切危险。”
这家报纸一向配合日军,为其占领和统治天津、掠夺经济资源进行舆论宣传,被老百姓私下叫作汉奸报纸。这样的报纸登载的消息靠得住吗?
在《大天津》杂志社做编辑的年轻人刘海涛就从来不看《东亚晨报》。屋里的同人举着报纸低声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让他突然一个激灵,大脑“轰”的一声,犹如五雷轰顶!王三是弟弟梁海山的化名,弟弟就是交通员。报纸上的王三是不是指的弟弟呢?难道弟弟就这样牺牲了吗?
弟弟什么时候去的蓟县,父亲怎么没对自己透露一点点口风?难道又是《东亚晨报》正话反说在造谣?父亲一直认为刘海涛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优柔寡断,在女朋友问题上撇不清;还认为他有恐日情绪,便对他不是十分信任,并没有因为是亲父子而有所改变。
其实,刘海涛有所不知,他身边一直与他关系腻腻呼呼的齐有为便让父亲不放心。父亲大半生阅人无数,看人眼睛很刁,齐有为的一切在刘海涛眼里似乎很正常,而在父亲眼里,单从齐有为“鬼头蛤蟆眼”的做派,就让人心里打问号。
快下班的时候,邮差给刘海涛送来一封“《大天津》编辑刘海涛收”的信件,信皮上注有“稿件”字样,但刘海涛凭经验就猜到,这是“上线”专门寄给他个人的。他急切地打开信笺,见是一篇1000字左右的短稿,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阴霾排空,东邻失脚。马上告诉周掌柜,礼尚往来,欠债还钱,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了解内情的人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刘海涛却看明白了,弟弟确实出事了,应该立即将消息通知父亲。他心脏怦怦乱跳,恨不得马上便跑到父亲那里去。他不时看看墙上的挂钟,压抑着焦灼不安的心绪。
掌灯时分,刘海涛审完最后一篇稿子,便到后院请示总编室主任,是不是可以下班。总编室主任马向前和日本顾问小野,还有两个市里商会的人在打麻将。四杆烟枪吞云吐雾,屋里乌烟瘴气。小野是个中国通,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牌桌上稀里哗啦的声音冲击着刘海涛的耳鼓,他非常烦闷地等候马向前发话,偏偏马向前不发话。而小野却冷不丁说道:“十块钱一锅的,不过瘾,涨到二十块钱的一锅,金杠的、天儿和的、清一色的统统十块钱。”这里说的多少块钱是指大洋,不是当时很毛的日本钱票。刘海涛低眉顺眼地站着,听着小野公鸭嗓般的声音,恨不得一个箭步扑过去掐死他。
“傻站着干吗,还不淘几个手巾把儿递过来!”马向前把烟蒂摁死在烟缸里,乜斜着眼睛说道。刘海涛知道,这是对他说的。他便在小野身后盆架上的脸盆里兑好稍热一点的水,淘洗了手巾,攥出一个热手巾把儿,先递给小野,等他擦完脸,刘海涛再淘洗手巾,递给商会的人,最后递给马向前。刘海涛虽然心里着急,该做的事却一点也不含糊。瘦成一把骨头的马向前接过毛巾把儿说:“我可告儿你刘海涛,咱们给皇军干活,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你可知道,皇军的刺刀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说挑出你的肚肠子只是一句话的事儿!”刘海涛急忙点头哈腰道:“主任,我时时刻刻在想着刺刀呢。”
马向前擦着脸说:“想着就好,否则我也得跟着沾包儿。”
“我可以下班了吗?”
“急什么!把我们四个人的鞋脱下来,拿到外面去掴打掴打。”
刘 海涛心里生气,脸上却不得不赔着笑。他紧抿着嘴唇蹲下身子,先把小野的黑卡其面的布鞋脱下来,忍着那股子酸汗味儿拎到屋外,“啪啪啪”地掴打了一阵子,然后拎回来给他穿上。给小野穿鞋的时候,他感到小野可憎的小腿短得与大腿不成比例,据说日本人为此也对身材匀称的中国人嫉恨。“有朝一日,我会亲手砍断他的短腿!”刘海涛心里愤愤地想着。他耐着性子把两个商会人的鞋和马向前的鞋也掴打了,最后站起身在一旁侍立,静等马向前发话。
马向前知道刘海涛等着他说“你可以走了”这句话,可他偏偏不说。而是将手边的手巾把儿还给刘海涛,说:“再淘淘。”刘海涛无奈,点头哈腰地接过手巾把儿,打上肥皂又淘了一遍,然后把脸盆里的水换上新的,再把手巾把儿淘一遍,最后搭在盆架上,就又侍立一旁,继续等待马向前发话。终于,马向前伸出一只手摆了摆,意思是你可以走了,却连嘴都懒得张,眼睛只是盯着桌子上别人出的牌。
马向前曾经私下跟刘海涛说过:“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给他。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刘海涛当然明白。他明白的不是这句话,这句话有什么可费解的?他明白的是马向前其人。
“欧儿——”街上的警车狼嚎一般拉长了声音呼啸着飞驰而过,接着传来几声带着回音的枪响:“噼啪!噼啪!噼啪!”
刘海涛的编辑室是东厢房,隔着院落正对着西厢房。他在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西厢房正有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他,而他却毫无知觉。
刘海涛的良民证和工作证上写的都是刘海涛,其实,没来天津以前他的本名叫梁海涛。自从进了天津,接连不断地跟父亲身边的人打头碰面,他便改名为刘海涛,今年满打满算26岁。他原来是天津北洋工学院的大三学生,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北平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平研究院内迁西安,合并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而他没有跟着走,考虑到父亲工作的需要,他留在天津,在这家叫作《大天津》的杂志社谋了职,转眼已经干了五六年。
事情让刘海涛不敢想,想一想就会咬牙切齿痛不欲生。平津沦陷以后,日军占据北洋校园作为兵营,将教学用的珍贵标本和仪器全都掠往日本,将相关教学设施悉数损毁,名噪一时的北洋工学院化为乌有。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教育的摧残,是毫不客气的。他们明白“一国之本,教育为先”的道理,他们将天津的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的校园夷为平地,在北平占领清华园后,将校园转用于军事,将机械系的工厂设备用于修理枪炮。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就在于重视教育,侵入中国以后马上毁灭和摧残中国教育,也真是找到要害了。
早在1937年春,刘海涛就从校刊上得知,北洋工学院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院长李书田先生满怀希望地瞄准世界水平,拟就了《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书》,计划若能实现,二十年内,北洋将分八期建成文理、工、法、医5个学院,22个系及4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这个计划绝不是虚张声势地放空炮,那时候,北洋工学院相当兴旺。当时中国土建,水利,铁路,矿业,机械……各领域都布满北洋学生,有时整条铁路、整个矿山的各种技术人员中几乎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而刘海涛因为是文科生,就走到了今天的这个地步。
刘海涛与孔德贞,是在谋职以后因为工作而产生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与齐有为的关系则始自北洋工学院的时候。那时候大学里有个诗社,诗社办有油印诗刊,刘海涛每每有了得意的诗作便送到诗社在诗刊上发表。被天津各大报纸发现以后,约稿者纷至沓来,刘海涛这个诗名不像新星那样冉冉升起,而是犹如一道闪电,蓦然间出其不意地照亮了天津卫诗坛。北洋工学院所有的教授学生没有不知道刘海涛其名的。
班里一个家境殷实的男生齐有为对此非常羡慕,却苦于才疏学浅,一首也写不出来,但他心思很深。日军进攻天津的时候,刘海涛家房子被炸毁,老娘被炸死,家里一时非常缺钱,这时候作为富家子弟的齐有为主动站了出来,为刘海涛慷慨解囊,料理了老娘后事,还把房子盖了起来。刘海涛欠下齐有为一笔深深的人情债。欠债的滋味不好受,他急于还上这笔钱,便饥不择食地谋了职。而齐有为本来可以稳稳当当找到比刘海涛好得多的事由,但他偏偏脚跟脚进了刘海涛进的杂志社。后来刘海涛凑齐了钱要还给齐有为的时候,齐有为却坚决推辞,说:“这点钱在我们家是九牛一毛,你就别寒碜我了。”
借钱不还,不是刘海涛做人的风格,他也口气坚决地说:“你们家再有钱,终归是你们家的,我借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这么做不是让我一生不踏实吗?”
齐有为正色道:“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如果看不起我,我就更不能接这个钱了。因为我从来没借给你钱。你能借到钱,是老天爷给的,我不过是过路财神帮着转了一下手。”他说什么也不要,还当着刘海涛的面把借条烧了,让刘海涛既纳罕又十分无奈。
谁都不知道齐有为的心思,他有个深埋心底,对谁都不能说的雄心壮志:要跟定刘海涛三十年,要搅得刘海涛50岁前一事无成。“我不行,你也别想行。”这是齐有为每天夜里睡觉时都会自言自语的话。
这样的用心不能不说十分险恶,然而刘海涛对此一无所知。一个那么热心帮助他的人竟打定主意毁他一生,刘海涛做梦也想不到,他根本就不可能往这方面想!
刘海涛供职的这家叫作《大天津》的杂志社几年前被日本人占领和接管,成为人们明损暗骂的“汉奸刊物”,因为,这本刊物一夜之间就演变为专门为日本人侵略行径歌功颂德,为日本人掠夺中国物资涂脂抹粉,为日本人残害中国人寻找借口和理由的无耻无度无良的刊物。杂志社占据着一个二进的四合院,原是一家国民党军官的宅邸,国民党撤退以后,日本人用枪托子砸开了院门铜锁,见小院很整齐很安静,还有树木、石凳,便将改头换面的《大天津》杂志社搬了进来。
刘海涛从小院里推出十分破旧、稀里哗啦乱响的自行车,刚要骑上去,西厢房的齐有为突然跑出屋子,从后面走过来一把按住了他的车把,说:“等等我,我去推车,我跟你去。”
“你知道我干什么去,就跟着我?”
“这个时间,你不是去见父亲就是会女朋友,那还用问?”
“我就不能有一点私密空间吗?”
“我不会影响你,我打一个照面就离开。谁让我崇拜你呢!”
这人怎么这么黏人啊?但刘海涛素来优柔寡断,虽然心里别扭,却没有阻止齐有为。两个人一起骑上自行车,迎着渐渐降下的夜幕,向父亲住处驰去。在两个路口,经过了两次盘查。最后来到海河边一拉溜商铺的其中一家的门前,将自行车支好落锁。这家商铺与两旁无异,按照市公署的要求,门窗的玻璃都贴了“米”字纸条,屋里头顶上吊着的电灯灯罩上蒙着黑布。推门进屋,便见迎门立着一块不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踊跃献铜献铁,为了大东亚共荣圈”。显然,这一切都表明,父亲跟着市公署走,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走板。
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正蹲着往一块玻璃柜台上糊报纸。刘海涛蹲在父亲身边,问:“好好的柜台,糊报纸干什么?”
“刚才来了个日本人,我送他一条‘恒大’牌香烟,他心情愉快,便抬起钉着铁掌的皮鞋踢了一脚,把玻璃柜台踢了个大窟窿。”
“真他妈不是东西!”齐有为道。
“唉!”刘海涛无奈地一声长叹。
“有为,你不要这么明目张胆地乱骂,会给你和我们惹麻烦的。”父亲说。
“好的,以后我会注意的。我走了,我不打扰你们了。”齐有为在刘海涛屁股上轻拍一掌便离去。
刘海涛和父亲都没有跟出去送客。此时他们都对齐有为十分厌烦,却又不愿意生硬地得罪。父亲站起来的时候,刘海涛看到了贴在柜台上的报纸,是后来被称为汉奸报纸的《东亚晨报》,出于职业习惯,几个粗黑的标题跃入他的眼帘:《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要纲》、《讨论推进治运》、《确立华北治安迈进东亚解放》等,在右下角的广告栏里,他无意中看到了京剧名家汪晓秋的戏目《醉我南风》、《夜深沉》和《夜明珠》。职业习惯使他读出汪晓秋的话外之音,他打算抽空找一趟汪晓秋。
这时,父亲脸色阴沉地说:“以后你能不能别带着齐有为到这儿来?”
“我没想带他,他非要跟着。我又不能得罪。”
“你的嘴就那么笨,只会说憨直话不会说婉转话?”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您得给我时间不是?”
“你呀你!我刚刚在大经路(后来叫‘中山路’)看好一个门脸,近日打算搬过去。”
“大经路天天有日本人过往,实属危险之地。”
父亲沉默了。他从口袋里摸出“哈德门”香烟,叼上一支,擦着了火柴,却迟迟没有点上火,直到烧了手。
刘海涛抓过火柴,重新给父亲点上,说:“爸,是不是弟弟海山出事了?”
父亲不说话,眉头紧皱,手上颤抖,半天才略略点了点头,两行老泪汩汩而下。
刘海涛又低声说:“刘掌柜来话儿了,说‘礼尚往来,欠债还钱’。让我立马把这话儿捎给您。您说,我应该干点什么?”
“唉!”父亲突然抹了一把眼泪,“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脑瓜一热任着性子擅自行动,要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
“国恨家仇,我咽不下这口气!”
“咽不下也得咽,记住,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刘海涛咬牙切齿,手里的火柴盒被捏成了一个球。忍着,忍着,几时是个头啊!
父亲催促刘海涛赶紧离开,回自己的寓所去,短时间都不要再来这里。刘海涛不想走,父亲便拿起两盒“哈德门”揣进刘海涛的口袋,硬是把他推了出去。
刘海涛无奈,出得门推了自行车刚要骑上去,两个巡街警察截住了他,浑身搜他,便将他口袋里的两盒烟顺走了。刘海涛强忍着一言不发,回身朝他们的背影吐了口唾沫骑上自行车就走了。此时,年轻的女画家孔德贞也许正在寓所里坐等他的到来。
刘海涛为掩饰身份,在南门外大街的日租界与一个经常给《大天津》投稿的言情小说作家万家铭的一家三口合租了一个小院。这个小院总共四间屋,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库房,卧室都是里外间,厨房和库房是两家合用。
他们这个小院的邻居,就是一家日本人。男人好像是商界的,女人在家里带着两个男孩。刘海涛经常见她穿着浅色和服和木屐,站在街上娇声娇气地招呼:“阿嘎江,阿路内,一马拿斯斯嘎!”好像是招呼孩子回家吃饭的意思。日本投降后,刘海涛亲眼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背着破筐拾毛褴 (捡破烂)的男人用带着钉子的竹棍,在这个日本女人脸上狠狠乱钉,直钉得鲜血直流。此为后话。
齐有为也在附近租了房子。论理,齐有为家里趁着三个连体三进的四合院,打着滚儿住也住不完,他却偏要追随着刘海涛,要获得与刘海涛相同的生活体验。当然,他的更深一层的念想是没法说出口的。他经常到刘海涛家里来,不光和作家万家铭十分熟识,还与邻居日本女人打得火热,曾对刘海涛夸口:“海涛,你几时遇到麻烦,我可以请日本人帮你。”那年月,与日本人成为朋友,是让一些人感
到荣耀的事情。有一次,齐有为还把那个日本女人领到刘海涛家里,介绍他们相认。说这个日本女人正在学习中文,以后说不定会经常来请教刘海涛。
“谁让你国文底子厚实呢!”
刘海涛心里那个堵啊,可是,人家一直在捧着你,你能说什么?你能不讲方式地直截了当地得罪那个日本女人吗?你能说清那个日本女人身后站的是日本商人还是日本特务?要报国恨家仇也该从长计议,听从组织上安排不是?
夜晚,女画家孔德贞在来刘海涛寓所的路上遭遇了两个便衣特务的拦截。
“良民证!”一个便衣伸手就摸孔德贞的胸口。
“干什么?”孔德贞奋力推开便衣的手,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良民证。
“天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另一个便衣快速伸手摸了她的脸颊一下。
“摸什么?没见过女人吗?”孔德贞愤恨地收起良民证夺路欲走,两个便衣嘻嘻笑着,挡住她的去路。
“急什么?陪我们俩说说话再走。天这么冷,我们俩在外面溜达,容易吗?”
“我可告诉你们,我是治安军副司令孔令诚的亲侄女,小心你们的鸟食罐儿!”
“嘿嘿,吹牛X谁不会!我们不吹,我们告诉你实话,我们是日本特务总队长官雨宫巽的部下。既然你是孔令诚的亲侄女,对雨宫巽总该有所了解吧?”
“我没时间跟你们闲扯,放我走!”
“走?没这么容易。不聊上半小时你甭想走!”一个便衣又伸手摸了一把孔德贞的脸颊,孔德贞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但眼下却又一时想不出对付他们的主意。孔德贞比刘海涛小两岁,亭亭玉立,风度翩翩,正当青春花季,椭圆脸,细长的眼睛,梳着时下知识女性非常时兴的荷叶头,脖子上总是围着一条浅驼色的毛围脖。说话的时候总是“仨大钱俩手攥着,一是一二是二”,简明果断,落地砸坑。
她毕业于坐落在天津市中心三岔河口的北洋女师范学堂。她追随刘海涛的诗名至少小十年了。上中学的时候读刘海涛的诗,上大学以后又读刘海涛发在《大天津》上的文章。她非常信奉时下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话:“出名要趁早。”她崇拜刘海涛的诗名,也幻想自己能在天津画界站住脚。她曾经来到杂志社对刘海涛说,他写诗便激情四溢,写文便严谨温润。及至谋面,又一派名人气质大家气象。直说得刘海涛满脸通红,心脏怦怦乱跳。他还真没让人这么直白地夸过。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很感性却又温吞水的人,写诗往往是兴之所至,写文章又往往是急就章。几首小诗谈什么“名人”,几篇小文谈什么“大家”?从来没觉得自己像孔德贞所夸的那样。
刘海涛把孔德贞的情况说给父亲的时候,父亲立时冷下脸来:“你不要和这样的女子撕撕扯扯,一来咱家和她们不匹配,两家人不可能走到一起;二来对咱们的工作有影响——接触时间长了你总会流露出一些情绪,或工作上的蛛丝马迹,你知道她几时会把你举报给日本人啊?”刘海涛听了这话频频点头,知道父亲的担心不无道理。怎奈事情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孔德贞从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马向前那里要了刘海涛的住处,便不时来寓所坐坐,拿些插画的业务。其实,她并不缺钱。她父亲是盐商,叔叔是天津卫声名远播的伪治安军副司令孔令诚。如果她父亲给杂志社一笔广告费的话,她的画会随便登;若是来损的,让孔令诚出面压杂志社一下,马向前还会把所有的插画业务全给她,还不敢不给高价,根本用不着她自己抛头露面。但孔德贞坚持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对父亲和孔令诚从来都只字不提,只是就画论画,以自己画品的质量谈价格,以自己的实际能力揽业务。对孔德贞,刘海涛是没法拂逆的。孔德贞正在被两个便衣纠缠不休的时候,刘海涛骑着自行车经过这里,在昏黄的路灯下,他一眼就认出了孔德贞,而且,知道她遇到了麻烦,便急忙滚鞍下车,虚张声势道:“嘿,孔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孔司令说好今晚见面的,你怎么能在这里耽搁着呢?”
孔德贞看见刘海涛来了便像见到救星,急忙说:“是啊,这两个浑球儿死缠着我,不知道锅是铁打的,看这意思非要把我叔叔请出来他们才放我走。”
刘海涛道:“德贞,你甭生气,他们是跟你闹着玩儿呢。走,上我的车。”
刘海涛蹬起了自行车,孔德贞抓住刘海涛的衣服,一纵身就坐在了自行车后架上,自行车便快速驰了起来,把两个便衣甩在了身后。
……
父亲经常悄悄地向刘海涛讲述天津近年来的林林总总,曾经告诉刘海涛,你现在看到的破败的街道,凋零的商铺,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街坊邻里,并不是老天津的真实样子。只是因为几年前,天津这座繁华的华北地区的经济文化重镇,在“卢沟桥事变”以后陷入敌手,惨遭蹂躏。当然了,国民党驻天津的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在李文田的带领下,与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激战,一度攻占了天津东站、北宁铁路局、烧毁了东局子停机坪上日军十余架飞机,并且包围了海光寺兵营,攻进了日租界,应该说战绩不错。但终因寡不敌众,武器也不够凑手,告败撤出天津。
那时候,天津城里一片火海,浓烟四起,房屋倒塌,老百姓哭号连天。当天死于战火的市民就有2000多人,难民10万以上。南开大学被日军泼油纵火,烧成一片瓦砾。事后当局统计,天津沦陷的当天,市区被毁的房屋达到2500间,日军破坏和强占的校舍有377间,摧毁企业、工厂53家,财产损失达2000万元(大洋)之多。若干年后,这个数字十分平常,而在当时,差不多是令人捶胸顿足的天文数字。
父亲也告诉刘海涛,在时局非常艰危的情况下,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彭真做出了重要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共产党员和抗日人员,都要撤出并设法到乡村拿起武器打游击。按照这一指示,天津市委决定:除留下少数人员坚持市内地下抗日工作外,要组织其他党员、“民先”成员、救亡团体成员聚集到英租界,分批乘英船离津,一路经大后方转至太原、延安;一路去河北保定转至八路军游击区;一路南下走津浦线到东光一带开辟新区。市内只留下小站、王兰庄、西北乡三个党支部和市内极少数党员、“民先”队员坚持工作。
于是,在距离南市不远的海河边,有一家不太起眼的杂货店,父亲租了下来,起名叫“周家栋商铺”。后来刘海涛知道了,这是党组织留下来的一个地下交通站。父亲便是站长。父亲原名叫梁雨松,是时五十四五。他是不是党员刘海涛始终不知道。在那个时期,刘海涛曾经对父亲说,我想加入共产党,父亲冷漠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在党外工作会更方便。”从父亲的口气,刘海涛猜想,父亲应该是党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