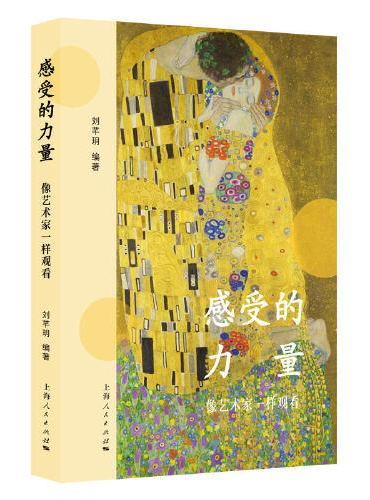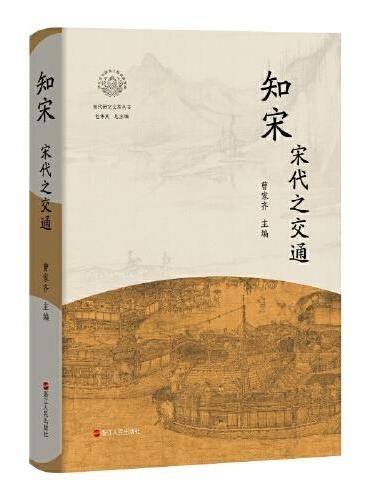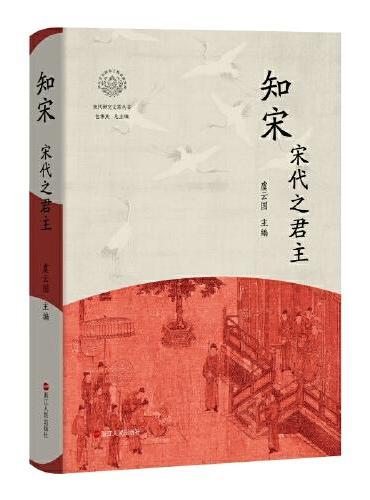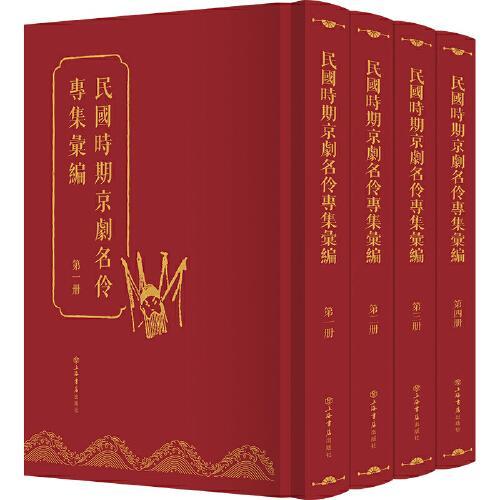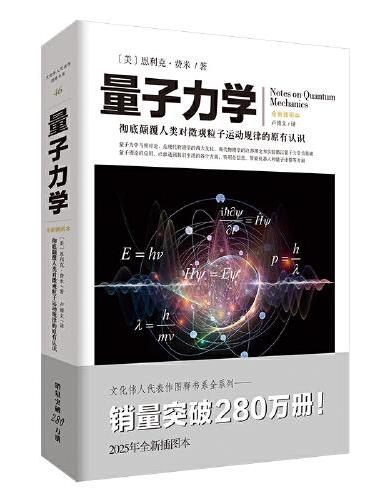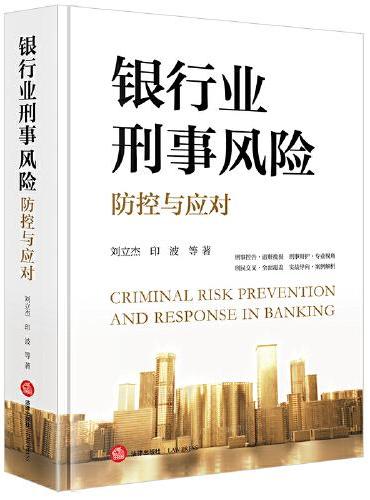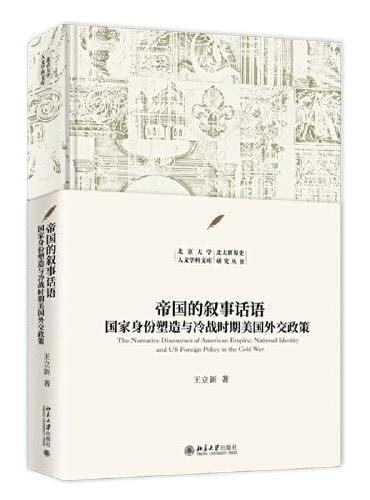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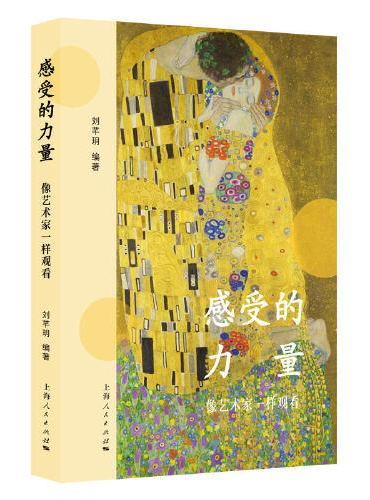
《
感受的力量--像艺术家一样观看
》
售價:NT$
2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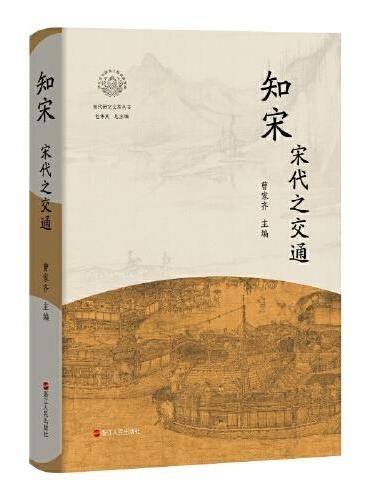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交通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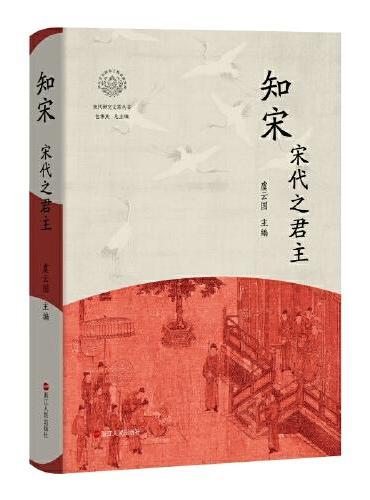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君主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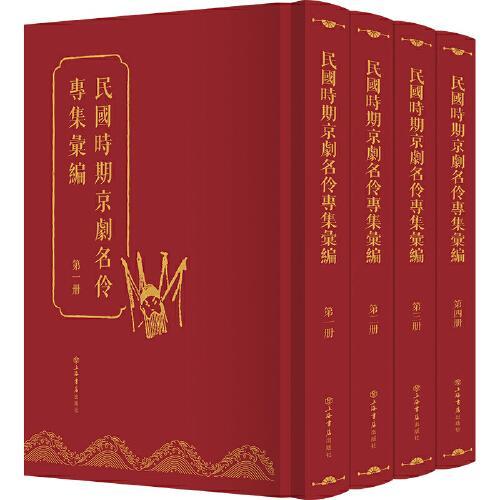
《
民国时期京剧名伶专集汇编(全4册)
》
售價:NT$
202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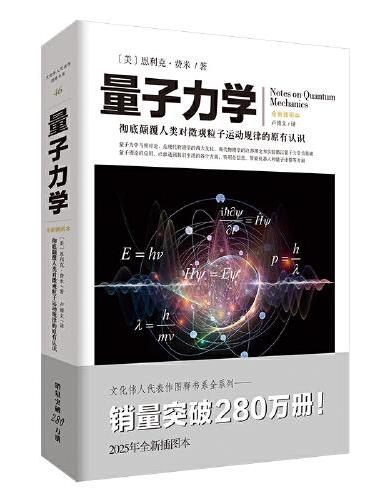
《
量子力学 恩利克·费米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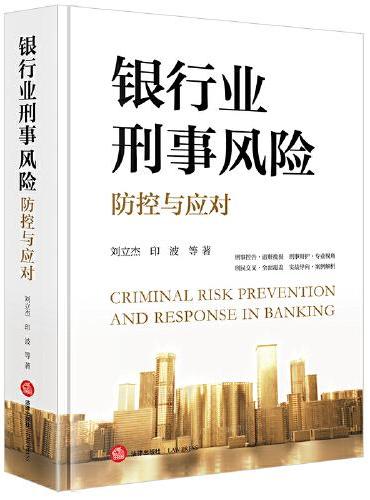
《
银行业刑事风险防控与应对
》
售價:NT$
449.0

《
语言、使用与认知
》
售價:NT$
3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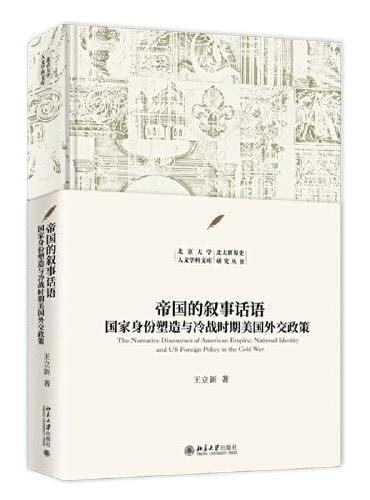
《
帝国的叙事话语:国家身份塑造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
》
售價:NT$
704.0
|
| 編輯推薦: |
|
《亚里士多德的》是法国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典范,从亚里士多德言明的特征出发,对各卷的研究对象进行定义,提供了一个可以迅速进入《形而上学》文义的全景式结构。
|
| 內容簡介: |
这本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为主题的小书源于作者当年的博士论文,彼时为探寻《形而上学》文本本身的内在逻辑而作,如今已成为法国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典范,其主要目标是“从亚里士多德言明的特征出发,对各卷的研究对象进行定义”。
《亚里士多德的》的成功之处在于:一、在研究层面,它结束耶格尔的“发生法”长久以来对亚里士多德研究范式的决定性影响,开辟出对统一理论的解释;二、在哲学教学层面,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迅速进入《形而上学》文义的全景式结构。
|
| 關於作者: |
安若澜(Annick Jaulin),生于1945年,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荣休教授,杰出科研津贴获得者。她对古希腊古典时期,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传统有深入的研究,并研究这一传统对中世纪思想的深刻影响。
译者曾怡,2007-2012年在法国的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安若澜教授,201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精通古希腊文、法文、英文,研究领域主要为亚里士多德哲学。
|
| 目錄:
|
给中文世界的读者们(代序)
引言
继承与问题
智慧与诸原因(卷一)
亚里士多德的智慧
诸疑难(卷三
结论
实体
问题的地位
实体与实质
柏拉图的型,亚里士多德的形式
结论
原理和原因
原理和原因的本性
原理和原因之间的关联
潜能与现实
结论
被探究的科学
诸理论哲学
第一哲学和定义
结论
结语
附录:中法专名对照表
参考书目
|
| 內容試閱:
|
给中文世界的读者们(代序)
在此强调一下这本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为主题的小书的特殊性,也许对读者有所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从亚里士多德言明的特征出发,对各卷的研究对象进行定义”,而刻意跳过那个并不为亚里士多德本人所知的“形而上学”这一题名。所以在对此书进行理解之时,我们就将这一题名及其连带意义加括弧悬搁(epokhè)起来,这样处理是想要对那些在阐释时,被不经意卷入后发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可能性保持一种反思性的警惕。准确来说,“形而上学”这一题名出自一种分类学逻辑,它来自对亚里士多德撰述进行编辑的安德罗列柯(约公元前60年):他将一系列独立的研究与物理学文稿相分离,再重新合并为一组,笼而统之题名为meta ta physika;希腊文的复数形式意指这些研究是后于(meta)那些“物理学研究”(ta physica)的。这一编辑方面的史实为研究者所熟知,比如奥本柯[P.Aubeque],因为这个掌故,他把自己对形而上学的研究的导言命名为“无名的科学”,而自罗斑[L.Robin] 始,我们就频繁地引用这样的说法
当我们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最让人惊讶,就是这些学说缺乏整体性。他把《形而上学》看作重新汇编的散篇,其中包括了“哲学词典”,而且它其实包含了两个部分性的形式。
这两个广为人知的证据充分证明了我们都错误地认为被后世命名为形而上学一书的作者是有意识地建立了西方哲学这一学科门类。
与形而上学捆绑在一起的知识的形式,亚里士多德对之有很多命名,诸如卷一所谓“智慧”,“研究是其所是的科学” epistèmè hè théorei to on hèi on ,或者卷四和卷五所谓“第一哲学” protè philosophia,其后它们都由于各卷的内容而分别有所规定,因此,其含义不是自明的,更何况它们又由安德罗列柯重新编辑过。总之,重新对亚里士多德给出的研究所针对的对象进行探讨,既不夹携对形而上学本质的种种前见,又不对所展示的某类形而上学的偏见,不仅仅是一个文献学可排除的结果,而且是一种对理解这种缩略风格所成的研究课题的最佳哲学取径,如此也才能谈得上对之进行批评性评价。除此,一切别种研究方案都不免部分地或偏隘地追随另一个哲学家的阐释,可能这位哲人也相当伟大,却也没能把它统一起来。这么做不止会让我们忽略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本身,还会让我们忽略这位哲学家把他想要“呈现”和“欣赏”的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结成新作的那个思想过程,换言之,这等于让人无法把握阐释者将他自己对古代作者的阐释置于何种视野之下。我们就如此遭遇了双重的理解障碍,一是对古代作者的,因为我们没有区分他的论题与作注者阐释时候对其的理解;同时,其实我们也无法很好地理解注家本人的,因为这要求我们透过他本人的思想才能进一步去把捉他作注的风格。
对《形而上学》(或形而上学诸研究,就希腊文而言这里处理为复数更本于原意)文本提供给注释的空间如此之多,以至于怎么去思考都总显得不充分。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一文本使用的泛滥,比如有下述这样的做法:无论他们的思想是如何与亚里士多德的文本背道而驰,他们也可以将其看作与他们自己试图建立的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的相似物,却又在他们自己的研究计划中破坏了亚里士多德的文中之义。出现这种与文义对立的这些对文献的用法,是因为亚里士多德采用了辩证法来展现自己的思想:以亚里士多德的思路为导引的对前人关于原理与原因的理论考察,打开了与自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主义,尤其是柏拉图学说的辩论,这样就使得文本本身包含着亚里士多德本人所反对的那些重要论据。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第一哲学始终保持在这种与各种关乎原理和原因的对立学说的抗辩活动中。
这里我们就不一一介绍那些就这些相互关联的论据所展开的多样阐释,但却可以将这些后续的研究兴趣作一个类型学的勾勒。这一类型学不当遮掩这样一个事实(但这一类型学也不可能进一步深入这一事实),即,阐释不只涉及个体阐释者与亚里士多德的直接关系,还根植于阐释者与其处身的时代之间的论辩语境。例如,托马斯.阿奎那,在他对亚里士多德的阐释中,未被言明的那个对话者是阿维罗伊;同样,海德格尔,在读亚里士多德时,他的潜在对话者是黑格尔和此前传统的大部分观点。这里就涉及到我们所谓“阐释策略”。在所有情况中,它都是或隐或显地被提及的,对阐释者而言,这涉及怎么“使用”亚里士多德,或怎么将之处理为一个“工具”,借此来面对他们支持或反对的当代论题。
在西方传统中,亚里士多德也就如此成了一卷隐迹写本,任何阐释者都不是完全中立的,也许在这里我们更该指出(以一种概括的方式)对《形而上学》文本进行阐释的那些趋向。事实上,在流传过程中,某些分析线索会伤及另一些对于理解原文的论证性语境更重要的线索。当流传史决定了理解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阐释者复兴了亚里士多德针对更早的哲学家的那个态度:当亚里士多德重提在他之前的自然哲学家的理论之时(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德谟克利特),他表达他们所使用的词汇并不是前人自己的,而是转译为构成他自己论题的术语。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是黑格尔的先师,黑格尔不也是这样处理他的前人的思想的么。然而他们两者之间还有文足征与不足征的差异:因为大部分自然哲学家的文本都是通过亚里士多德本人或其学派的转述而为我们所知,我们就无法对质亚里士多德与其所阐释者,但有充分的文献储备,让我们可以对质亚里士多德本人与后世阐释者的思想。
对于《形而上学》一书而言,似乎没有注家早于阿芙罗蒂西亚的亚历山大专门对之作注,他是雅典(公元2-3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主讲人。这一注本并不接近所注文献的时代,它出现在罗马帝国时代,正当其时的主流是拉丁的斯多亚主义;但这仍不妨碍它成为后世注释——希腊、拜占庭、阿拉伯和拉丁各传统——之滥觞。他开启了一个注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世代,自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是通过读他的注释来读亚里士多德的)而至于现代。这一长时段以其注家将形而上学概念处理为科学而被称道,这正是亚历山大注释的核心议题之一。亚历山大注本的历史重要性在于,它还为后起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特米斯特乌斯、叙尼阿乌斯、阿斯科勒皮乌斯)所用,内化于他们自己的注释工作:对于新柏拉图主义者而言,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被认为是极难读的一部著作,他们对它的理解都来自亚历山大。此外,亚历山大作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成员,因此他的阐释也很自然会被其他学派视作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正统。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兴趣则主要集中在逻辑学的问题上,关注形式的地位和属的本质;他们在物理学方面,则关心时间性和运动的问题,而一与存在的关联则是存在论方面被关注较多的问题。他们所有的人都信奉世界的永恒性。
不仅如此,亚历山大的注释对于阿维罗伊(12世纪)理解亚里士多德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尽管流传的情况又与新柏拉图主义盛行的时期有所不同,一神论成为了新一轮论辩活动的关切核心,尤其关于世界的永恒性、信仰与理性的 关系、一般存在论与神学的分野,然而那些关于个体与属的本质的论战仍旧持续着,直到在中世纪形成所谓的“共相之争”。此外,文献传世的情况也影响我们评估亚历山大和阿维罗伊之间的关系:我们只有亚历山大的五卷释文(其余卷注被归到以弗所的米歇尔名下,他是十二世纪的拜占庭学者),而阿维罗伊则看过亚历山大注的全本(卷一到卷十四),这个全本是转译叙利亚文译本而来的阿拉伯本。阿维罗伊对于注解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拉丁传统(尤其对于托马斯.阿奎那)极为重要。事实上,阿维罗伊的阐释激发了它的拉丁读者的思想活力,首先它获得了一批拥护者,而后又有人因信奉它而获罪,在1270和1277年两次被巴黎主教定罪为信奉“拉丁阿维罗伊主义”。
这一由亚历山大开创的注释传统所揭示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在康德的《导论》中被批评为教条的形而上学之后,我们也许会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今天不再有历史上那样重要的意义了。但这显然是一种误判,因为在康德批评形而上学的同时,他对一种可能的形而上学重构还是借用了希腊第一哲学的语汇:如phénomènes(现象)和noumènes(本体)(§32)之分,以及判断上分析的和综合的之分,以及范畴系统出现的必然(§39),即使亚里士多德建立的范畴系统形式被认为是混乱而当加以抛弃的。其实,“对我们观念的研究”的这一做法的批判,总是伴随着这一背景事实,即“科学仍旧是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所认为的科学”。诚然,在这种情况下,对亚里士多德的征引是出于否定性的考虑,因为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科学是应当被超越的,但同时,我们也就建立了与它之间的直接关联,返回亚里士多德文本就成为理解康德如何规划“一种能成为科学的未来形而上学”的方案的不可或缺的步骤,这一科学的对象即为是其所是的是,同时这也是获知它们是否在后世传统中成为康德所批判对象的亚里士多德本人或变形的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的必要步骤。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