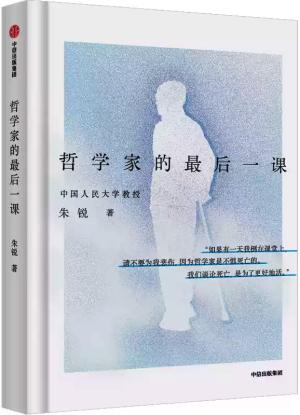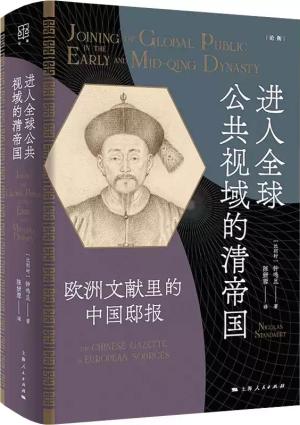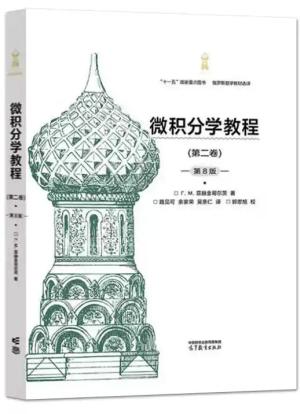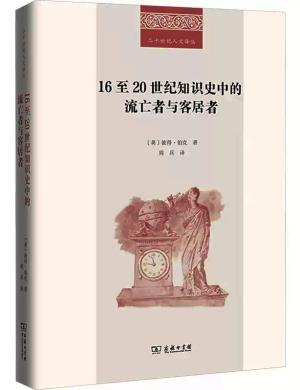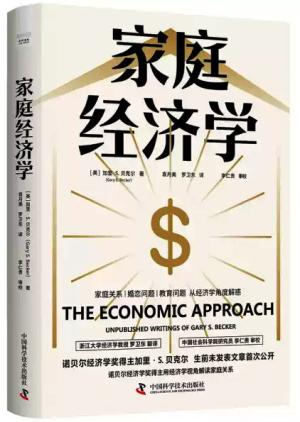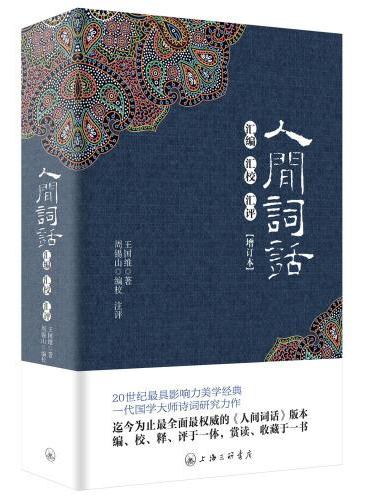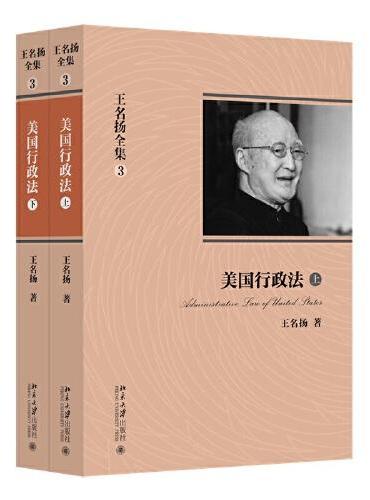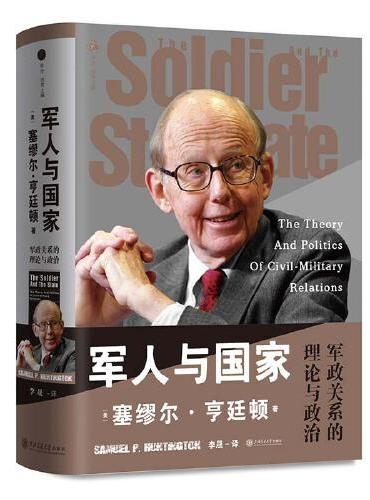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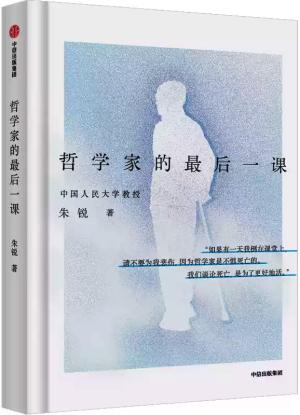
《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
售價:NT$
2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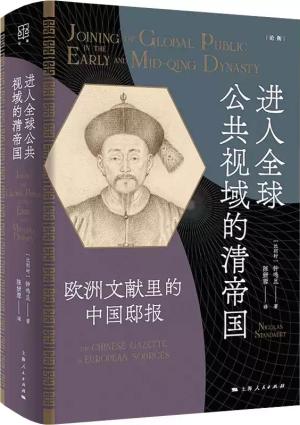
《
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
》
售價:NT$
6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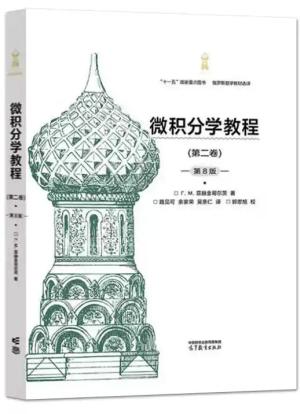
《
微积分学教程(第二卷)(第8版)
》
售價:NT$
5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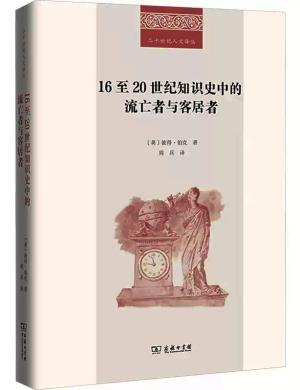
《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
》
售價:NT$
4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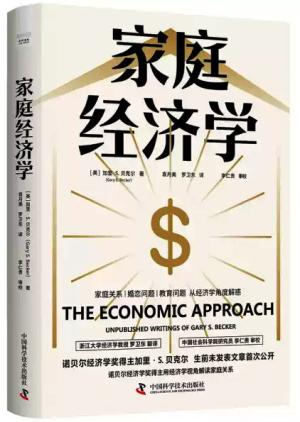
《
家庭经济学:用经济学视角解读家庭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S. 贝克尔全新力作)
》
售價:NT$
3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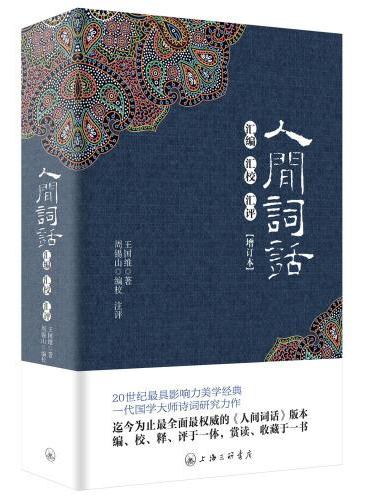
《
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新)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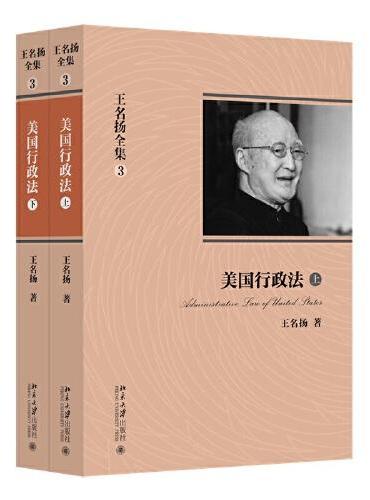
《
王名扬全集:美国行政法(上下) 王名扬老先生行政法三部曲之一
》
售價:NT$
8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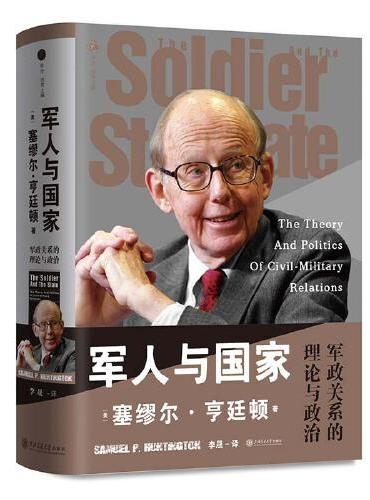
《
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
》
售價:NT$
653.0
|
| 編輯推薦: |
1.编辑推荐
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林少华先生的散文集《高墙与鸡蛋》。
|
| 內容簡介: |
3.内容简介
内容分为陌上花开、校园风月、浮世云烟、书海夜航、他山之石五个部分,涵盖了林少华先生的近百篇优美散文,表达了作者对现实、文化、文学、生命的思考和感悟。“最理想的社会是没有高墙的社会,没有高墙也无所谓破碎的鸡蛋。整个社会好比一个巨大的孵化器,保障每只鸡蛋都有新的生命破壳而出——孵化自由,孵化个性,孵化尊严,孵化和谐”。引用的村上春树的一句话道出了这部作品《高墙与鸡蛋》名字的由来,林少华先生通过散文这一手段来歌颂、捍卫着自由、个性、尊严、和谐等。
|
| 關於作者: |
2.作者简介
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曾任教于暨南大学、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和在东京大学从事学术研究。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著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为了灵魂的自由》、《高墙与鸡蛋》、《雨夜灯》。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等四十一部村上春树作品系列以及《心》、《罗生门》、《金阁寺》、《伊豆舞女》、《雪国》、《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七十余部,广为流布,影响深远。
|
| 目錄:
|
4.目录
原版序言 1修订版序 5
陌上花开
杏花与乡愁 2
卖杏的幸福 6
四合院里石榴红 10
清晨的蛙鸣 14
寂寥之美 18
小镇“别墅”译《雪国》 22
假如院里有两棵柿树 26
除草机和野菊花 30“伊甸园”的苹果 34
美景与美感 38
混凝土不是土 42
关东的雪 46
邂逅冻梨 50
三十五年的梦 54
《挪威的森林》:获奖在广州 58
翻译的诀窍就是不翻译 62
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空缺:谁该羞惭? 66
何必拔自己的根 71
书箱和牵牛花—— 我的精神家园 77
父亲的遗物 87
电脑与人脑 91
校园风月
致人大校长公开信 96
大学:警惕“自我官场化” 100
高考季节的大学问答 104
钱学森为何而叹 108
“常凯申”:清华怎么了 112
大学老师的修养 116
谁是知识分子:韩寒,还是教授? 120
那一刻让我内疚—— 献给教师节 124
假如有一间教授室 128
南开情思 132
军校的男生 136
假如我的研究生当保姆…… 140
“代沟”与毕业典礼致词 144
之于我的高中和高中校服 147
村上母校:“教育嘛,就那么回事!” 151
餐桌对面的易中天 154
浮世云烟
村上春树:为了破碎的鸡蛋 160
油菜花和商品楼 164
消费与浪费之间 168
院士:纸巾的12~14 171
鸡蛋、牛奶与道德感 175
世博:看与不看之间 179
足球与高俅 183
NBA、GDP与农民的知情权 187
1.7 个亿:最贵的荷花 191
乳汁与甘蔗汁 1953000 万新娘何处觅 199
以瘦为美的忧虑 203
为何就我们得不到诺贝尔奖 206
自然:任其自然最好 210
自驾车游:傻还是不傻 214
东北人的热情 218
这就是河南人 222
飞机上的细节 226
“副省长谁知道!” 230
人生意义于三姑 234
曾经的怕,永远的爱 238
书海夜航
之于我的书,之于书的命运 246
诺贝尔文学奖和《山楂树之恋》 253
莫言获诺奖:翻译和翻译以外 259
《挪威的森林》“生日”纪事 269
片山恭一:村上春树没意思 277
村上春树:虚无中的独舞 281
《品三国》是不是成果 286
诗意与激情中盘升的灵魂 290
风流何以绝代 294
远去的身影,民族的灵魂 298
大师之大 大在哪里 302
“南京”:我们永远的痛 307
《孔子》:南子很有水平 310
“新《三国》”:价值观的错位 314
包扎伤口还是包扎刀子 318
《性别战争》:动物们的“性生活” 323
鲍鱼和“鲍鱼师傅” 327
“炸香的太阳” 331
文体中的黛玉 335
绵软中的尊严 338
“哭着写”的女囚故事 341
丽江能否疗伤 344
写得有趣的日本 348
日本小学生:圆周率是3 ! 353
他山之石
“日本美”:美在哪里 35
8夏目漱石和他的作品 373
芥川龙之介和他的作品 379
永井荷风:唯美观照下的欧美风情 387
小林多喜二:并未消失的“蟹工船” 392
川端康成:“日本性”与“非日本性”之间 402
三岛由纪夫:生存之美与毁灭之美 415
三岛由纪夫为什么自杀 424
竹久梦二:丰子恺的“老师” 429
东山魁夷:一片冰心在玉壶 438
片山恭一:爱,人的α 和ω 443纯爱的可能性 449爱情拒绝物化 456
迷失的和不迷失的 462
象的失踪与海豚的失踪 467
市川拓司:捡拾细小的快乐 476
河合隼雄:玩也是学习 483
新渡户稻造:什么是真正的修养 487
|
| 內容試閱:
|
有一种东西,无论我们置身何处,无论我们怀有怎样的信仰和世界观,都会从深处从远处一点点温暖我们的心,那就是乡愁,nostalgia。而所有的乡愁,都可归结为四个字:杏花春雨。春雨很小,很细,如烟,如丝,温馨,迷蒙,若有若无,正是乡愁的物化。杏花,无疑代表故乡的村落和老屋。或谓“沾衣欲湿杏花雨,拂面不寒杨柳风”,或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或谓“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故园之思,游子之情,羁旅之苦,于此尽矣。万井笙歌,一樽风月,不足以化解;千里莼羹,西风鲈脍,莫能比之也。
多少年没看见杏花了呢?十八年客居岭南,岭南没有杏花;数载游学东瀛,东瀛只有樱花。
终于看见了杏花。几天前一位同事邀我去郊外踏青,一开始我拒绝了,刚从外地回来,累;而当对方说那里有杏花的时候,我满口答应下来。
那个地方叫少山村。没等进村就看见杏花了。始而一两株、三四株立在路旁野地里,落下车窗看去,果然是杏花。在欲雨未雨阴沉沉的天空和欲青未青乱蓬蓬的荒草地的衬托下,微微泛红的白色杏花让我眼前陡然一亮,顿生惊喜之情。杏花渐渐增多。很快,两山之间开阔的谷地忽一下子铺满了杏花。车在杏花间穿行,如一个不懂风情的莽汉愣生生闯入一群婆娑起舞的白纱少女之中,但觉缀满杏花的树枝仿佛轻舒漫卷的衣袖拂过脸颊,一股久违的杏花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
一行人赶紧下车步行。村外茫茫花海,村中一片杏林。家家皆有杏树,户户红杏出墙——“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诗在这里不是诗,不是隐喻,不是调侃,而是实景、实况。这是真正的杏花村。人在杏花下穿梭,狗在杏花下歇息,鸡在杏花下觅食。喏,那条大黄狗偎着杏树根闭目合眼,那只大公鸡和好几只老母鸡在横逸斜出的杏树枝下或左顾右盼或低头啄地,多幸福的狗多幸福的鸡啊!没准鸡蛋都一股杏花味儿。
拐过“书院旧址”,走过“处女池”,沿一条小路朝后山爬去。两侧山坡陡峭,前方石峰如削,簇拥着山脚一方花坞。这里安安静静,几无人影。我得以独自在杏树间尽情徜徉,仔细打量一片片、一树树、一枝枝、一朵朵杏花。间或有樱桃花。同是五枚花瓣,樱桃花开得重重叠叠,密密麻麻,一副难解难分的样子。而杏花疏朗得多,个体绝不淹没在整体之中。无论开多少朵都一朵是一朵,一朵朵历历在目,矜持、自我,而又和谐、端庄,如黛蓝色的天幕上均匀分布的银星。酷似梅花,但毕竟不像梅花那样孤芳自赏;近似樱花,却有别于樱花的扎堆起哄和华而不实。樱花全是“谎花”,开完什么也剩不下。而这里的杏花开完不出数月,就是满枝满树的“少山红杏”,一张张关公般的红脸膛掩映在茂密的绿叶之中,成就另一番动人景象。
我是在有杏花的小山村长大的。小山村很穷,用韩国已逝前总统卢武铉的话说,“连乌鸦都会因找不到食物哭着飞走”。小山村又不穷,因了房前屋后的杏花。杏树是爷爷栽的。前院一棵歪着脖子,几乎把杏花从窗户伸进屋里。后院四五棵踞坡高过房脊,七八月间,熟透的黄杏从房脊噼里啪啦滚到屋檐下。杏固然好吃,可我还是更喜欢杏花。五月开花时节,放学离家很远就能瞧见草房脊探出的杏花,粉粉的,白白的,嫩嫩的,那么显眼,那么温暖,如亮丽的晚霞。近了,但见一只喜鹊在歪脖子杏树枝“喳”一声啼叫,或两只春燕箭一般掠过杏花飞进堂屋。及至春雨潇潇,杏花随之幻化为一窗朦胧的倩影……
这就是记忆中的故乡,故乡的老屋,老屋的杏花。几十年来,我总想在春雨时节回去看看杏花,但我回去的时候不是寒假就是暑假,杏花当然等不到我,一如我等不到杏花。杏花终究成了一缕绵绵的乡愁。
如今,山村已经荒废,老屋已经易手,杏花还在开吗?还在等我吗?
(2010.4.18)
说出来你怕也难以置信,在青岛这座所谓副省级旅游城市,出租车跑50 元钱就能跑到从树上摘杏吃的地方。
拐过一座始建于魏晋时期的古老寺院,车沿一条不宽的路往山里一座名叫少山村的村庄开去。少山村四月中旬来过一次,那次是为了看杏花。我是山民出身,深知杏花的厚道——开花必然结果。于是看花以来的两个月时间里,我天天计算杏熟的日子,反复在脑袋里播放一片花海变成满目果林的喜人场景。由想象少女顾盼生辉的亮丽眸子,转而想象村姑那忽然羞红了的脸蛋。看到城里果摊杏陡然增多,我断定时候到了,钻进路边一辆出租车,带着一种莫可言喻的期待感穿出市区。
果然,花变成了果,眸子变成了脸蛋。或者莫如说一群白纱少女倏然中止了轻歌曼舞,而换上一身身绿裙托出无数果盘。说来也真是神奇,无非两个月六十天,杏花居然发生如此根本性以至颠覆性的变化。而我怎么看也什么变化也没有,既未长高半厘米,又没多生出一只眼睛,怎么回事呢?看来,我——我们人类——还是谦卑一点儿好,别太张狂。不服气?不服气你给我开朵花结个杏试试!人家就是厉害嘛,喏,瞧那杏结的:红扑扑、肥嫩嫩、圆滚滚、水灵灵,有的都快探进车窗来了,几乎擦脸而过。还有的因为路基变高而就在脚下,让人不由得踮起脚,生怕踩着这些可爱的宝宝们!
下车进村,杏就更多了。家家香气扑鼻,户户红杏出墙。“一枝红杏出墙来”,较之杏花,在这里我以为指杏果更合适——这里的杏就叫少山红杏,上了国家名特产目录,俗称“关脸红”。不用说,关脸指关公关云长。也罢,我说的村姑脸蛋难免叫人怜香惜玉,不忍下手。关脸也好村姑也好,反正都强调红,红杏!但见红杏在村道旁一摊摊排开,我们一家人早已等不及了,赶紧买下一堆“关脸红”,拎到杏树下,围着石桌一口口咬将下去,任凭金黄金黄的果汁从头到脚“哗”一下子涌满每一个细胞。比什么美国提子富士苹果泰国山竹以及苏东坡赞不绝口的岭南荔枝甚至孙猴子猪悟能他们偷吃的人参果好吃多了——百分之百是天下第一水果,这点我敢和任何人打赌。
吃罢抹一把嘴巴,像猪悟能那样摸着圆滚滚的肚皮沿小道爬山。山谷红杏笑靥迎人,山腰合欢花开似锦,山顶云雾半锁轻笼。时而伸手摘杏把玩,时而抬头忘情山水,所谓人间仙境,谅也不过如此了。
游玩半日,提杏下山。仲夏时节,艳阳高照,走罢一程,脑门冒出汗来。忽见村口路旁有一位老婆婆卖杏。篱笆院,杏树荫,老妪,竹篮,杏——久违的故乡场景!我们没等老婆婆准许,就像自家人一样坐在她眼前光滑的石头上歇息。杏树把阳光屏蔽得严严实实,加之一阵山风飒然吹来,要多舒坦有多舒坦。老婆婆到底慈祥,笑眯眯叫我们吃杏:“什么钱不钱的,吃杏吃杏,尝尝也好!”我说刚才饱饱吃过,又买了满满两袋,吃不动也拎不动了。老婆婆非叫我们吃不可。见我们吃了,笑得更慈祥了。她头发几乎全白了,穿一件针织半袖衫,慈眉善目,仿佛每一条皱纹都会笑。“可有七十?”“八十六。”八十六!“家里几口人?”“我一个,一个人生活!”啧啧,八十六,一个人生活!我不由得向院里望去,三间老瓦房,木窗棂,窗台趴一只花猫,窗前三五朵月季开得正红。院里五六棵高大的杏树。树间七八株南瓜秧,几垄茄子、西红柿、青葱,数架豆角,整洁、利落、质朴。回过头时,老人已在半袖衫外面像模像样地加了一件短褂——到底是从注重男女有别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蓦地,我觉得卖杏的老婆婆其实很幸福。至少,她不用介意别人说自己翻译的日本村上如何如何,不用担心论文能否在核心刊物如期刊出,不用挂念申报的科研项目能否通过,不用……心动不如行动。我开始替老婆婆卖杏:“甜杏甜杏,5块两斤!甜得要死,甜得要命,不甜不要钱,甜也不多要。甜杏甜杏……”正是下山时间,男男女女成伙走过,可惜都只是报以善意的微笑,压根儿没有买的意思。一位男士还对旁边的女伴笑道:“一看就知他不是卖杏的。”
可我还是想卖杏。如果我八十六岁的时候能够坐在这杏树荫下卖杏,那该多么幸福啊!
(2010.6.30)
喜欢旅游。总觉得旅游途中有什么等我,等我与之相遇,而且仅等我一人,仿佛曾有一个私密的前生之约。对方有时候是古玩铺角落里一个灰头土脑的青花罐,有时候是书画店里一幅不起眼的手绘农民画,有时候是郊外夕阳下半截残缺的旧砖墙……
最近则是一株石榴树,四合院里开红花的石榴树。
山东,淄博,周村区,周村。
远在江南的周庄早就知道了,因了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因了陈逸飞《故乡的回忆》,因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而近在身边的周村则刚刚知道。相邻大学一个文学青年家在周村,送了我一大盒“周村烧饼”——不是武大郎在郓城叫卖的那种厚墩墩暄腾腾的,而是薄薄脆脆的——我说好吃,他当即向我铺排周村除了好吃的各种好来:古色古香的清一色明清古建筑,光绪三十年开埠的“天下之货聚焉”的商业重镇,“济南、潍县日进斗金,不如周村一个时辰”的清代华尔街,据传乾隆帝御赐“天下第一村”的美誉,以及电视剧《大染坊》、《旱码头》的主题和舞台……
于是,初夏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动车组用恰好一百分钟把我忽一下子送到淄博,出租车又忽一下子运抵周村古商城“大街”。街并不大,两侧古屋俨然,青砖灰瓦,错落有致,飞檐斗栱,各呈风姿。大清国邮局、钱庄票号、茶庄酒楼、书局文具,以及酱菜、烟草、丝绸、杂货等各种店铺。门前或商幡招展,或匾额高挂,或宫灯迎风,或石狮对卧。古朴、浑厚、素雅、沧桑。在一家名叫异芝堂的药房前,我对着门联凝视良久:“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古人就是有文化、有品位、有道德感,比学校后门那家药店好多了。那家药店没等你进门就有八个美女一齐伸长脖子问“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不知是何居心。
记不得是在大染坊还是在杨家大院抑或状元府了,只记得大院里的一座小四合院,院正中有一株石榴树,石榴花开了大半。石榴花的红是真正的红,如翠绿的枝叶间一枚枚亮丽的火炭。房是平房,青砖墙,青砖有的已经风化。上下对开的细格木窗,窗棂油漆斑驳,大部分露出开裂的木纹。小院只我自己,除了树梢偶尔一声鸟鸣,什么声音也没有。太阳已经偏西,石榴树把长长的影子打印下来,印在青苔隐约半砖半土的湿润地面。倏然,我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这座四合院、这株石榴树正在等我,似乎我们之间在遥远的往昔悄声许下一个的承诺,承诺今生今世今日今时在此相会。恍惚间,房门吱呀一声开了,慈祥的外婆仍穿着那身青布长衫,颤颤巍巍从屋里走出,招呼我,让我赶快进屋……我的眼角有些湿润,就那样在院里石榴树下站了很久很久。
黄昏时分,我走出古商业街的古老街门,沿昔日的护城河往北走去。护城河已经不成其为河了,只河床中间歪歪扭扭流淌着巴掌宽的水,黑黑的稠稠的,流得很慢很慢。不过河边垂柳还生机蓬勃,朝河床和路旁垂下无数柔软的枝条。路的另一侧是民居,火红的月季间或从院内探出墙来,也有时一丛丛粉色白色的蔷薇在墙外蒸蒸腾腾,攀援而上,和天边迤逦的晚霞相映生辉。我想,既有护城河,那么就该有城墙,至少断墙残垣总该有的。正好前面大柳树下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婆婆,遂问哪里有城墙。老婆婆看样子是退休多年的小学语文老师,健谈。她告诉我:“哪里还有城墙呀,解放前扒一段,‘大跃进’扒一段,‘文革’又扒一段,扒来扒去,把个四四方方的古城墙和四座城门扒个精光!护城河倒是没扒,剩下来了,可是你看,这哪里还
是河哟!五十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水清得能数里面的小鱼小虾,渴了就从河里直接舀水喝!下雨水满满的,都能划船!可现在呢,你看你看!这还不算,你没闻到吗?还一股臭味……”老婆婆用手捂了捂鼻子。果然,一阵风从河床卷起一股臭味。作为游客,谁能想象这就是几十年前能喝、能划船的护城河呢?
所幸,刚才的四合院和石榴树还在,石榴花还红,还在那里等我——人生途中总有什么等我、等待我们。或许,唯其如此,我们才不时置身于旅游途中。
(2010.6.18)
不知是因为上了年纪还是心理有了变异,近年来总是有感于寂寥之美。例如,较之旭日东升霞光万道,我更乐意在半截古旧的青砖墙下寻找昨晚遗落的夕晖;较之百花齐放姹紫嫣红,我的目光宁愿在落有一只白粉蝶的狗尾草上流连;较之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更倾向于打量岸边荒滩弃置的一条小船;较之万马奔腾龙吟虎啸,我更留意野外那只低头吃草的羔羊……是的,对于我,较之辉煌、壮观、美轮美奂,还是寂寥、索漠乃至荒凉的景物更能契合心间弥散的人生况味。
最近一次深切而具体的寂寥体验,发生在暑期回乡期间,发生在故乡那座小镇。老屋不在小镇,回乡寄居的大弟新屋也不在小镇,小镇在八华里以外。去小镇的路正在重修,坑坑洼洼,中巴颠簸得厉害,但还是没用十分钟就开到了。小镇四面环山,确实小。仅两条路。一条直的,从镇中间穿过;一条弯的,往坡上稍微绕了一下,在东头和直路碰头。沿两条路兜了一圈后,我发觉有什么触动了自己。
为了确认那个什么是什么,我又兜了一圈,兜得比刚才还慢。寂寥!是这里的寂寥触动了自己。往远里说,“文革”时焚烧古书旧书和打篮球的小广场,如今只有一只芦花鸡和两只杂毛鸭低着头缓缓踱步,仿佛一起思索“我是谁”的哲学命题;下乡时我作为民兵连长参加三级干部大会时进入的“俱乐部”,虽然建筑物还在,但门上的铁锁早已锈成铁疙瘩了,钥匙想必永远忘在了脱离桌子的抽屉里。往近里说,几年前还不少人出出进进的火车站检票口的木门此刻已经钉死了。原来摆满花花绿绿的糖果和布料的供销社,现在外墙上写着租售联系电话,字显然写好久了,缺胳膊少腿,活像日文字母。更让我诧异的是,前年回来时还在路边抽烟打扑克或无事闲逛的年轻人此时全然没了踪影。休说年轻人,即使不年轻的人也没有几个——街上几乎无人。
无人,人住的房子就格外突出。大部分房子门窗紧闭,开着的也只开小半扇,但应该有人住或有人照料。因为门前打扫得很干净,有的种一排花,有的栽一垅葱或几株西红柿什么的。花开着,葱绿着,西红柿则刚开始泛红。我在上坡一段弯路那里停住脚步。路两侧的房子都有小院子和菜园。小院一地细沙,菜园满园瓜豆。篱笆上零星开着牵牛花。路旁长着凤仙花、百合花,花开得不多,但很洁净,一尘不染。鸡冠花正悄然聚敛成形。还有一排高高低低的蜀葵,叶片像小向日葵似的,花也没开几朵,仿佛绿色湖面上的几叶小舟。比花更少的是人。人都哪里去了呢?没有人,也就没了声息,没了喧哗,没了热闹。只听得两只鸟在老榆树上“啾啾”叫了两声,随即飞过房脊,朝山外飞去,俨然村上春树笔下的“世界尽头”。
可我打心眼里喜欢上了“世界尽头”,喜欢上了“世界尽头”的寂寥。并且,寂廖也似乎喜欢上了我。走进一家小店买冰棍时,我随口说了一句“这附近可有卖房子的?”一位老者当即要我跟他去看房子:三间砖瓦房,独门独院。房间大块地砖,宽敞明亮。房前半亩菜园,绿油油长着茄子、辣椒、玉米和豆角。西侧一株海棠三棵李子树,果可以吃了。再往西不到一百米是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河水很浅很清。过了河是望不到尽头的幽深的松树林,静得几乎可以听见针叶飘落的声音。一条羊肠小路朝山那边蜿蜒而去,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看罢环境,看回房子。多少钱?“5 万。”5 万?不是
10.5 万或15
万?“5 万!”5 万在城里能买到房子的什么呢?半个卫生间?一个北阳台?而在这里却能买一座房子,能买一片寂寥!我开始想象告老还乡后住进来的自己——或堂上高卧或树下乘凉,或林间漫步或河畔徜徉。白天青山满目,傍晚蛙鸣满耳,入夜繁星满天。兴之所至,临窗涂鸦,或译或写,或比或兴,优哉游哉,不知老之已至。
寂寥——不知是否可以说,寂寥接近与世无争的冲淡与释然。那当然是一种美。
(2009.9.4)
教授有别墅如今并非多么难以置信的事,但我的“别墅”绝对难以置信。价钱最低:5 万!不是5 万英镑5 万美元,而是5 万人民币。不仅价格低,环境也好,三间砖瓦房,半亩果菜园,所在小镇森林覆盖率85%,天然生态氧吧。相比之下,城里动辄三五百万冠以洋名的别墅不过是小孩过家家的玩意儿罢了。“墅”者,“野”、“土”之谓也。无野无土,墅自何来?说句粗话,纯属扯淡。
“别墅”是去年暑期买的。一年来给我庸常的生活带来了兴奋和期待,也带来了浅薄和猖狂:东京巴黎算什么,华盛顿夏威夷又怎样?哼!
暑假终于到了。下午四点青岛起飞,一个半小时抵长春,再一个小时到“别墅”。正是夕阳落山时分,金色的夕晖把小院镀上了梦幻般的光彩。凤仙花如一个个玲珑剔透的小精灵,鲜活生动,多彩多姿。番薯花如小向日葵扬起一张张娇嫩的脸庞,红色、粉色、黄色,雍容华贵,相映生辉。大波斯菊娉娉婷婷,仪态万方,毅然挑起世界上所有的彩蝶。最显眼的到底是一排万年红,红得透明,红得鲜亮,红得轻盈而倔强——便是这些美丽的花将我从大门口夹道送往房门口,于是我神气得如走向领奖台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或前去颁奖的瑞典国王。花径的一侧是蔬菜:西红柿胀鼓鼓的,有的胀裂了,裂出月牙形的嘴,如动漫笑脸;一架架四季豆则如一堆堆绿色的火焰,上面缀满了惊叹号。此外还有茄子、大葱、辣椒、香菜、芹菜、韭菜……菜是大弟帮我种的。没施化肥,没喷农药,用他的说法,“百分之百纯绿色”。
是啊,绿色!绿色是所有彩色的根据,是所有美的前提。这样的美当然不在城里而在乡间,在乡间的大自然。无须说,自然美是最完全最合理最自足的美。
我在美的拥抱中开始重译川端康成的《雪国》。众所周知,《雪国》是使得川端走上并非虚拟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的名作,尤以表现“日本美”为人称道。译的当中我明白了,在川端那对以凝视空虚或虚空而广为人知的眼睛看来,美的前提是洁净,美的极致是悲哀,美的表现是徒劳。“洁净”(清潔)、悲哀(悲しい)和徒劳(徒労)是《雪国》的点睛之语。容我就此借题发挥。
“洁净”。别墅所在小镇无疑是美的。家家瓜果满园,
户户花草拥径。四面环山,无山不绿,八方来风,无风不清。
一条小河从小镇中间淙淙流过,河水一清见底,时见小鱼游
踪。可是十分可惜,不少居民把垃圾倒在河边,极不雅观,
更不洁净。于是我对邻居抱怨,旁边就是镇政府,镇里不能
出面建几个垃圾点吗?年老的邻居说:“他们能干这个?
天底下会有这样的事?一百来号人,天知道在那楼里干什
么?”虽然同川端所谓美丽的极致是悲哀毫不相干,但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