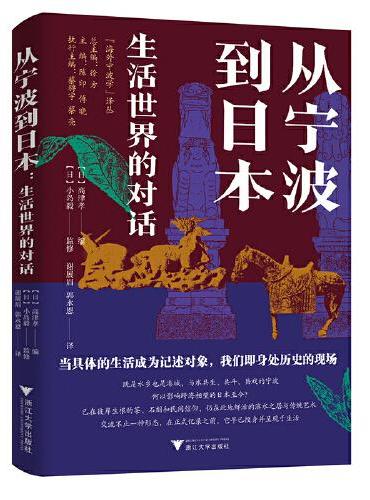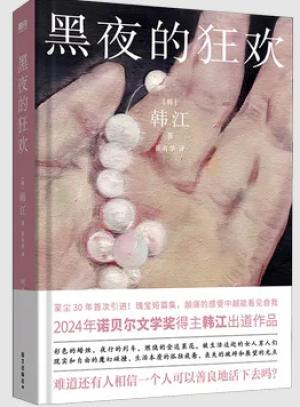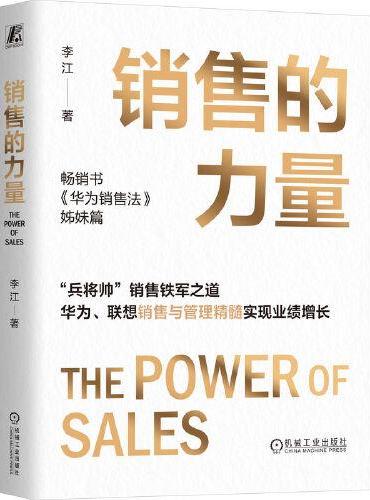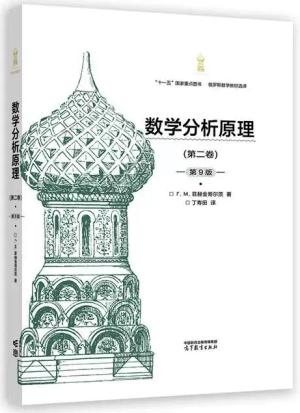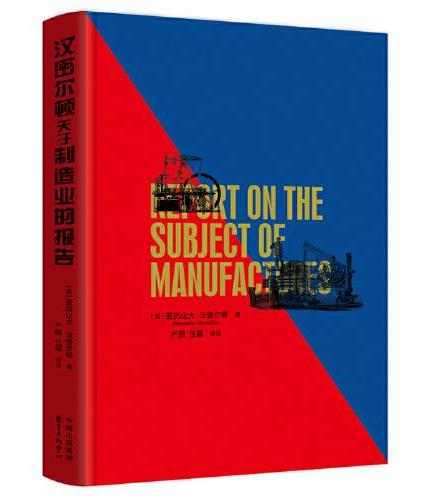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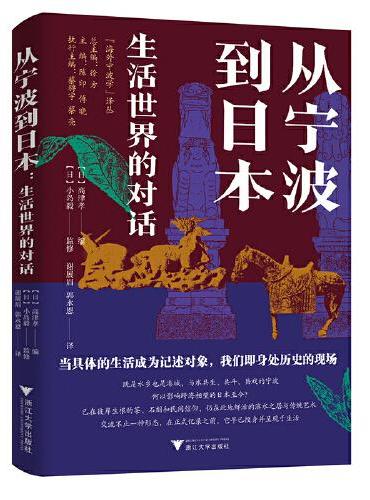
《
从宁波到日本:生活世界的对话
》
售價:NT$
347.0

《
怪谈:一本详知日本怪谈文学发展脉络史!
》
售價:NT$
2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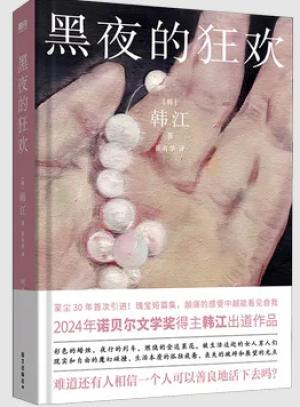
《
韩江黑夜的狂欢: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出道作品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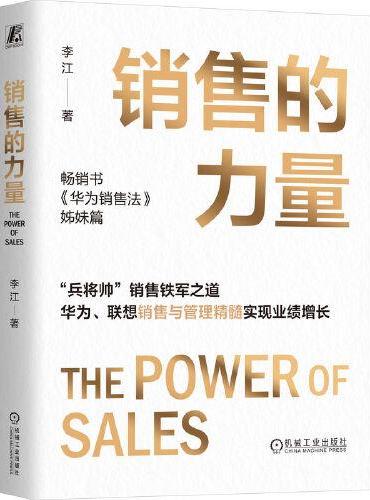
《
销售的力量
》
售價:NT$
454.0

《
我活下来了(直木奖作者西加奈子,纪实性长篇散文佳作 上市不到一年,日本畅销二十九万册)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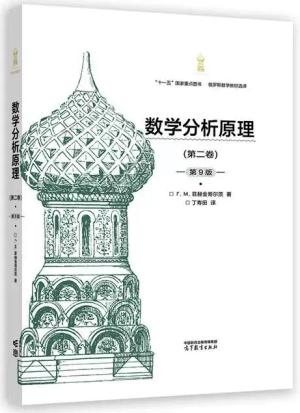
《
数学分析原理(第二卷)(第9版)
》
售價:NT$
403.0

《
陈寅恪四书
》
售價:NT$
14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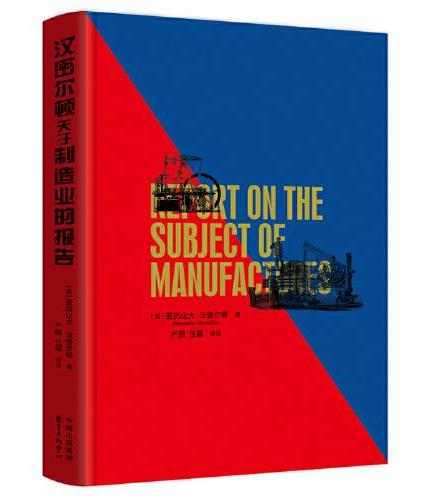
《
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沈从文小说、散文等作品收录最全的文集,全套12卷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师之一
◆沈从文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文字诗意浪漫,语言格调古朴,写尽人性的真善美
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
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有论者视他为实证主义的作家、现实主义的乡土作家写意小说作家。还有论者分析说他是"现代文化人中一个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甚至有人把他归入启蒙主义。更多的论者则认定他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金介甫在《沈从文传》引言中写道:"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
|
| 內容簡介: |
这是目前沈从文小说、散文等作品收录最全的文集,一套共12卷。
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师之一,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沈从文文集(全12卷)》共12册,其中小说8册,散文2册,文论2册,收录了他的《边城》《长河》《湘行散记》等作品百十余部。这些作品描绘了一个从未有人描绘过的、多彩多姿的湘西世界,极大地丰富了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创作,并把现代抒情小说创作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沈从文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
| 關於作者: |
|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著作有小说集《龙朱》、《阿黑小史》、《边城》、《长河》;散文集《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
| 目錄:
|
沈从文文集 第一卷 小说
■ 鸭子
雨
往事
玫瑰与九妹
夜渔
代狗
腊八粥
船上
占领
槐化镇
■ 蜜柑
初八那日
晨
蜜柑
草绳
猎野猪的故事
■ 老实人
老实人
船上岸上
雪
连长
我的邻
在私塾
一件心的罪孽
一个妇人的日记
■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一卷)
■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
沈从文文集 第二卷 小说
沈从文文集 第三卷 小说
沈从文文集 第四卷 小说
沈从文文集 第五卷 小说
沈从文文集 第六卷 小说
沈从文文集 第七卷 小说
沈从文文集 第八卷 小说
沈从文文集 第九卷 散文
沈从文文集 第十卷 散文、诗
沈从文文集 第十一卷 文论
沈从文文集 第十二卷 文论
|
| 內容試閱:
|
鸭子:
《鸭子》1926年11月由北新书局初版,为无须社丛书之一。原作品收录作戏剧、小说、散文、诗。原目收入小说作品:《雨》《往事》《玫瑰与往事》《夜渔》《代狗》《腊八粥》《船上》《占领》《槐花镇》。
雨
朝来不知疲倦的雨,只是落,只是落;把人人都落得有点疲倦而厌烦了。
各人在下课后左右无事耍了,正好到电话处去找朋友谈天。那方面若是一个女人,自然是更有意思!
叫来叫去,铃儿时时刻刻是丁丁当当嚷着的。
电话器死死的钉在墙壁上,接线生耳朵中受惯了各方催促,铃儿又是最喜欢热闹的一件东西;所以都还不生出什么脾味来--就中单苦了大耳朵号房。
他刚把一个洋服年青青儿的胡子后生从四舍十三号找来,眼见那后生嘴巴对着机子叽叽咕咕开合了一阵,末后象生气似的样子,霍地挂上耳机走出去了。休息换不到十口气那末久,墙上那铃儿又丁丁地在同他打知会。
"喂,你是哪--这是农业大学。……咸先生罢?你贵姓?喔,喔,又找他来?是,是,"他把耳机挂到另一个钉子上去。从响声沉重中可以看得出他被人无理麻烦的冤抑来。这冤抑除用力的挂耳机外,竟也无从宣泄。"又是咸先生!"他还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自己能够听到的话。
这本来可以随意扯个谎,说找不到,就完事了。但他是新来这里不久的人,虽然每日里同到专司收发信件那位崔哥一起歇宿吃饭,还学不到这些可以偷闲的事。而且,自己一想到月前住在同乐春每日烧火,脸上趋抹刺黑,肚板油刮得不剩什么时的情景,责任心登时也就增加起来了。少不得又举起那只左手来,(因为如今是穿长衣,所以右手失了空间。)挡拒着屋檐口上掷下来的大颗大颗雨点儿,用小步跑到四舍去找那年青的胡子后生。
桌子当中摆着那一座四四方方的老钟,一摇一摆,象为雨声催眠了似的,走得更慢更轻了。钟旁平平的卧着那一本收信簿,也象在打磕睡。靠着钟身边挨挤极近的一个小茶杯,还有大半杯褐色茶水,一点热气都没有。……
他眼睛看到那后生对着耳机笑笑嚷嚷,耳朵却为门外雨声搅着,抽不出闲空来听那后生谈的那么浓酽倒了的,究竟是些什么话。他便觉得那后生但对着耳机大笑,真是无聊。
后生又出去了。
当那后生从他身边过去的当儿,洋服裤子擦到他正垂着在胯骨边的左手时,随着有阵怪陌生但很好闻的气味儿跑进了他的鼻孔。他昨天到消费社时,曾见到那玻璃橱内腼腆腆的躲在橱角上,手指头儿大小的瓶儿;瓶中贮的什么精。--这时的气味,便是那瓶中黄水水做的,他自信没有猜错!
这气味使他鼻子发痒,有打个把喷嚏的意思。不由得他不站起身来随同那后生走出门外。
雨还是不知疲倦,只是落,只是落。瓦口上溜下来的雨水,把号房门前那小小沟坑变成一条溪河了。新落下来的雨点,打成许多小泡在上面浮动,一刹那又复消失。一些小小嫩黄色槐树叶子,小鱼般在水面上漂走。倘若这些小东西当真是一群身小麻哥鱼崽,正望着它们出神的他,不用说早就脱了鞋袜,挽起袖子,告奋勇跳下去把它们捉到手中了。--这好象它们自己也能知道本身不值价,不怕什么意外危险事到头!不然,眼看到大耳朵在那号房门前站着,痴痴地把视线投到它们一举一动上面来,为甚还是大大方方的在水上漂来漂去?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三日于窄而霉小斋
往事
这事说来又是十多年了。
算来我是六岁。因为第二次我见到长子四叔时,他那条有趣的辫子就不见了。
那是夏天秋天之间。我仿佛还没有上过学。妈因怕我到外面同瑞龙他们玩时又打架,或是乱吃东西,每天都要靠到她身边坐着,除了吃晚饭后洗完澡同大哥各人拿五个小钱到道门口去买士元的凉粉外,剩下便都不准出去了!至于为甚又能吃凉粉?那大概是妈知道士元凉粉是玫瑰糖,不致吃后生病吧。本来那时的时疫也真凶,听瑞龙妈说,杨老六一家四口人,从十五得病,不到三天便都死了!
我们是在堂屋背后那小天井内席子上坐着的。妈为我从一个小黑洋铁箱子内取出一束一束方块儿字来念,她便膝头上搁着一个麻篮绩麻。弄子里跑来的风又凉又软,很易引人瞌睡,当我倒在席子上时,妈总每每停了她的工作,为我拿蒲扇来赶那些专爱停留在人脸上的饭蚊子。间或有个时候妈也会睡觉,必到大哥从学校夹着书包回来嚷肚子饿时才醒,那末,夜饭必定便又要晚一点了!
爹好象到乡下江家坪老屋去了好久了,有天忽然要四叔来接我们。接的意思四叔也不大清楚,大概也就是闻到城里时疫的事情吧。妈也不说什么,她知道大姐二姐都在乡里,我自然有她们料理。只嘱咐了四叔不准大哥到乡下溪里去洗澡。因大哥前几天回来略晚,妈摩他小辫子还湿漉漉的,知他必是同几个同学到大河里洗过澡了,还重重的打了他一顿呢。四叔是一个长子,人又不大肥,但很精壮。妈常说这是会走路的人。铜仁到我凤皇是一百二十里蛮路,他能扛六十斤担子一早动身,不抹黑就到了,这怎么不算狠!他到了家时,便忙自去厨房烧水洗脚。那夜我们吃的夜饭菜是南瓜炒牛肉。
妈捡菜劝他时,他又选出无辣子的牛肉放到我碗里。真是好四叔呵!
那时人真小,我同大哥还是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为四叔担去的!大哥虽大我五六岁,但在四叔肩上似乎并不什么不匀称。乡下隔城有四十多里,妈怕太阳把我们晒出病来,所以我们天刚一发白就动身,到行有一半的唐峒山时,太阳还才红红的。到了山顶,四叔把我们抱出来各人放了一泡尿,我们便都坐在一株大刺栎树下歇憩。那树的杈桠上搁了无数小石头,树左边又有一个石头堆成的小屋子。四叔为我们解说,小屋子是山神土地,为赶山打野猪人设的;树上石头是寄倦的:凡是走长路的人,只要放一个石头到树上,便不倦了。但大哥问他为甚不也放一个石子时,他却不做声。
他那条辫子细而长正同他身子一样。本来是挽放头上后再加上草帽的,不知是那辫子长了呢还是他太随意,总是动不动又掉下来,当我是在他背后那头时,辫子梢梢便时时在我头上晃。
"芸儿,莫闹!扯着我不好走!"
我伸出手扯着他辫子只是拽,他总是和和气气这样说。
"四满乡人呼叔叔为满满。,到了?"大哥很着急的这么问。
"快了,快了,快了!芸弟都不急,你怎么这样慌?你看我跑!"他略略把脚步放快一点,大哥便又嚷摇的头痛了。
他一路笑大哥不济。
到时,爹正同姨婆五叔四婶他们在院中土坪上各坐在一条小凳上说话。姨婆有两年不见我了,抱了我亲了又亲。爹又问我们饿了不曾,其实我们到路上吃甜酒、米豆腐已吃胀了。上灯时,方见大姐二姐大姑满姑满姑乃最小之姑母。各人手上提了一捆地萝卜进来。
我夜里便同大姐等到姨婆房里睡。
乡里有趣多了!既不怎么很热,夜里蚊子也很少。大姐到久一点,似乎各样事情都熟习,第二天一早便引我去羊栏边看睡着比猫还小的白羊,牛栏里正歪起颈项在吃奶的牛儿。我们又到竹园中去看竹子。那时觉得竹子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本来城里的竹子,通常大到屠桌边卖肉做钱筒的已算出奇了!但后园里那些南竹,大姐教我去试抱一下时,两手竟不能相掺。满姑又为偷偷的到园坎上摘了十多个桃子。接着我们便跑到大门外溪沟边上拾得一衣兜花蚌壳。
事事都感到新奇:譬如五叔喂的那十多只白鸭子,它们会一翅从塘坎上飞过溪沟。夜里四叔他们到溪里去照鱼时,却不用什么网,单拿个火把,拿把镰刀。姨婆喂有七八只野鸡,能飞上屋,也能上树,却不飞去;并且,只要你拿一捧包谷米在手,口中略略一逗,它们便争先恐后的到你身边来了。什么事情都有味。我们白天便跑到附近村子里去玩,晚上总是同坐在院中听姨婆学打野猪打獾子的故事。姨婆真好,我们上床时,她还每每为从大油坛里取出炒米、栗子同脆酥酥的豆子给我们吃!
后园坎上那桃子已透熟了,满姑一天总为我们去偷几次。
爹又不大出来,四叔五叔又从不说话,间或碰到姨婆见了时,也不过笑笑的说:
"小娥,你又忘记嚷肚子痛了!真不听讲--芸儿,莫听你满姑的话,吃多了要坏肚子!拿把我,不然晚上又吃不得鸡膊腿了!"
乡里去有场集的地方似乎并不很近,而小小村中除每五天逢一六赶场外通常都无肉卖。因此,我们几乎天天吃鸡,唯我一人年小,鸡的大腿便时时归我。
我们最爱看又怕看的是溪南头那坝上小碾房的磨石同自动的水车;碾房是五叔在料理。那圆圆的磨石,固定在一株木桩上只是转只是转。五叔象个卖灰的人,满身是糠皮,只是在旋转不息的磨石间拿扫把扫那跑出碾槽外的谷米。他似乎并不着一点忙,磨石走到他跟前时一跳又让过磨石了。我们为他着急又佩服他胆子大。水车也有味,是一些七长八短的竹篙子扎成的。它的用处就是在灌水到比溪身还高的田面。大的有些比屋子还大,小的也还有一床晒簟大小。它们接接连连竖立在大路近旁,为溪沟里急水冲着快快地转动,有些还咿哩咿哩发出怪难听的喊声,由车旁竹筒中运水倒到悬空的枧剜木以引水之物。上去。它的怕人就是筒子里水间或溢出枧外时,那水便砰的倒到路上了,你稍不措意,衣服便打得透湿。我们远远的立着看行路人抱着头冲过去时那样子好笑。满姑虽只大我四岁,但看惯了,她却敢在下面走来走去。大姐同大姑,则知道那个车子溢出后便是那一个接脚,不消说是不怕水淋了!只我同大哥二姐,却无论如何不敢去尝试。
玫瑰与九妹
大哥从学堂归来时,手上拿了一大束有刺的青绿树枝。
"妈,我从萧家讨得玫瑰花来了。"
大哥高兴的神气,象捡得"八宝精"似的。
"不知大哥到哪个地方找得这些刺条子来,却还来扯谎妈是玫瑰花,"九妹说,"妈,你莫要信他话!"
"你不信不要紧。到明年子四月间开出各种花时,我可不准你戴,……还有好吃的玫瑰糖。"大哥见九妹不相信,故意这样逗她。说到玫瑰花时,又把手上那一束青绿刺条子举了一举,--象大朵大朵的绯红玫瑰花已满缀在枝上,而立即就可以摘下来做玫瑰糖似的!
"谁希罕你的,我顾自不会跑到三姨家去摘吗!妈,是罢?"
"是!我宝宝不有几多,会希罕他的?"
妈虽说是顺到九妹的话,但这原是她要大哥到萧家讨的,是以又要我去帮大哥的忙:
"芸儿去帮大哥的忙,把那蓝花六角形钵子的鸡冠花拔出不要了,就用那四个钵子分栽。剩下的把插到花坛海棠边去。"
大哥在九妹脸上轻轻的刮了一下,就走到院中去了。娇纵的小九妹气得两脚乱跳,非要走出去报复一下不可。但给妈扯住了。
"乖崽,让他一次就是了!我们夜里煮鸽子蛋吃,莫分他……那你打妈一下好罢。"
"妈讨厌!专卫护大哥!他有理无理打了人家一个耳巴子,难道就算了?"
妈把九妹正在眼睛角边干擦的小手放到自己脸上拍了几下,九妹又笑了。
大哥这一刮,自然是为的报复九妹多嘴的仇。
满院坝散着红墨色土砂,有些细小的红色曲蟮四处乱爬着。几只小鸡在那里用脚乱扒,赶了去又复拢来。大哥卷起两只衣袖筒,拿了外祖母剪麻绳那把方头大剪刀,把玫瑰枝条一律剪成一尺多长短。又把剪处各粘上一片糯泥巴,说是免得走气。
"老二,这一些是三种(大哥用手指点),这是红的,这是水红,这是大红,那种是白的。是栽成各自一钵好呢,还是混合起栽好--你说?"
"打伙儿栽好玩点。开花时也必定更热闹有趣……大哥,怎么又不将那种黄色镶边的弄来呢?"
"那种难活,萧子敬说不容易插,到分株时答应分给我两钵……好,依你办,打伙儿栽好玩点。"
我们把钵子底各放了一片小瓦,才将新泥放下。大哥扶着枝条,待我把泥土堆到与钵口齐平时,大哥才敢松手,又用手筑实一下,洒了点水,然后放到花架子上去。
每钵的枝条均约有十根左右,花坛上,却只插了三根。
就中最关心花发育的自然要数大哥了。他时时去看视,间或又背到妈偷悄儿拔出钵中小的枝条来验看是否生了根须。妈也能记到每早上拿着那把白铁喷壶去洒水。当小小的翠绿叶片从枝条上嫩杈桠间长出时,大家都觉得极高兴。
"妈,妈,玫瑰有许多苞了!有个大点的尖尖上已红。往天我们总不去注意过它,还以为今年不会开花呢。"
六弟发狂似的高兴,跑到妈床边来说。九妹还刚睡醒,正搂着妈手臂说笑,听见了,忙要挣着起来,催妈帮她穿衣。
她连袜子也不及穿,披着那一头黄发,便同六弟站在那蓝花钵子边旁数花苞了。
"妈,第一个钵子有七个,第二个钵子有二十几个,第三个钵子有十七个,第四个钵子有三个;六哥说第四个是不大向阳,但它叶子却又分外多分外绿。花坛上六哥不准我爬上去,他说有十几个。"
当妈为九妹在窗下梳理头上那一脑壳黄头发时,九妹便把刚才同六弟所数的花苞数目告妈。
没有做声的妈,大概又想到去年秋天栽花的大哥身上去了。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于北京窄而霉小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