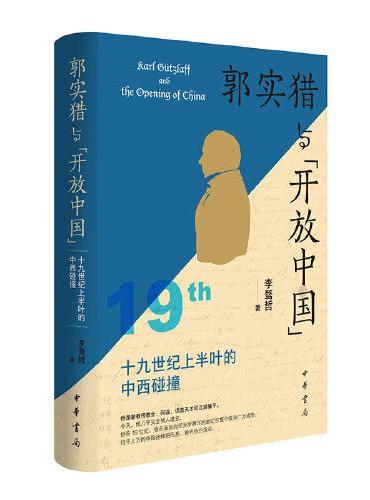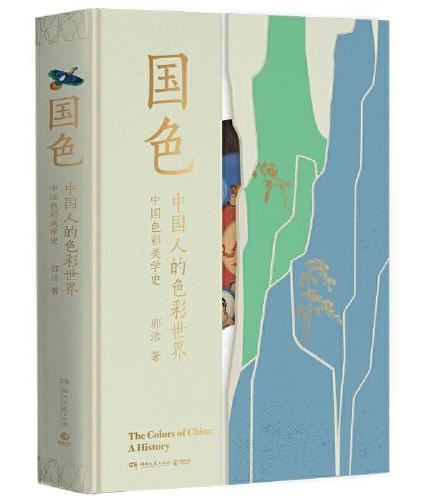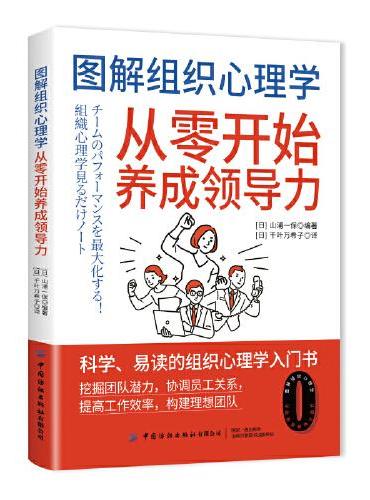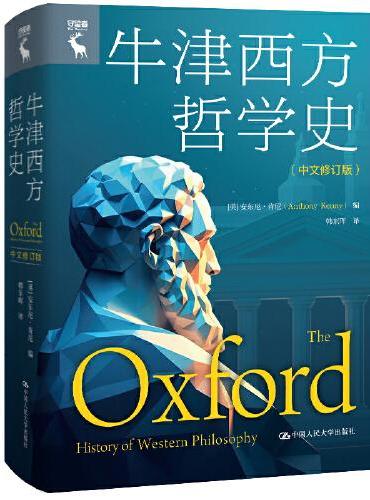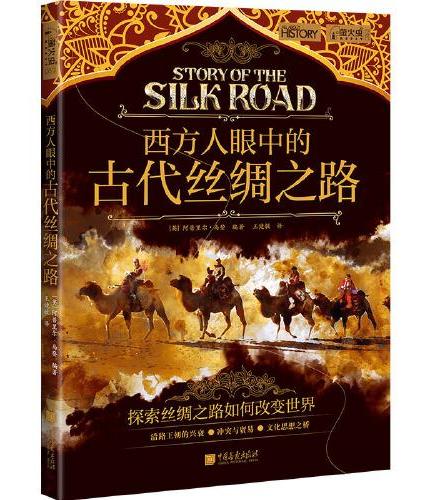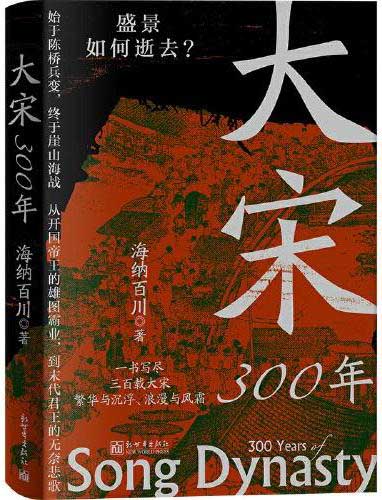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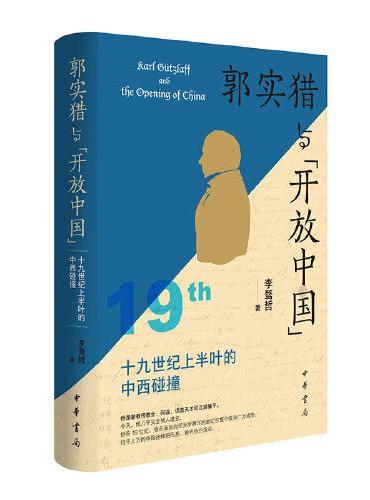
《
郭实猎与“开放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中西碰撞(精)
》
售價:NT$
347.0

《
海外中国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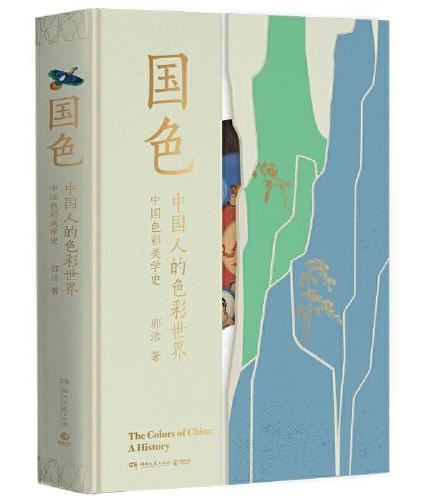
《
国色(《寻色中国》首席色彩顾问郭浩重磅力作,中国传统色丰碑之作《国色》,探寻中国人的色彩世界!)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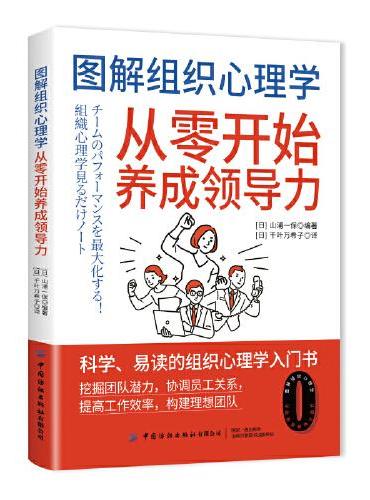
《
图解组织心理学:从零开始养成领导力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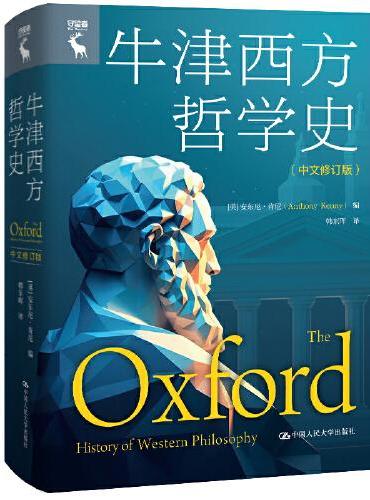
《
牛津西方哲学史(中文修订版)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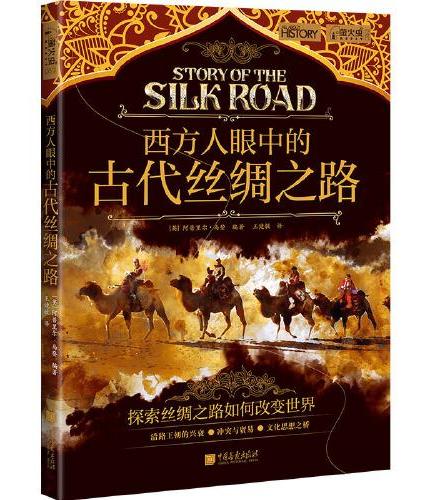
《
萤火虫全球史:西方人眼中的古代丝绸之路
》
售價:NT$
3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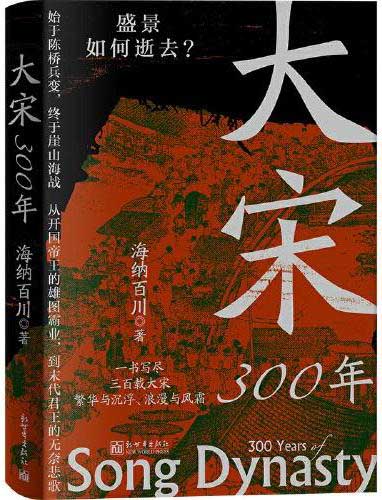
《
大宋300年(写尽三百载大宋繁华与沉浮、浪漫与风霜)
》
售價:NT$
352.0

《
害马之群:失控的群体如何助长个体的不当行为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
龚鹏程,是当代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的顶级学者和著名思想家,精通中国文学、史学、中国、宗教,常以孔子自比、自励。他自幼才华横溢,而且精通武术、书法,深广的学力贯通古今、融会中西,人称当今天下“第一才子”。本书是他四十岁时回顾自身前半生经历的自传文字,一个率真坦荡、不拘常俗、志向高远、勤奋自砺的学者、行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当代孔孟”、“天下第一才子”龚鹏程先生四十岁时撰写的回忆录,记叙自身求学问道、入世历事的经历和感悟,一个率真坦荡、不拘常俗、志向高远、勤奋自砺的学者、行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
| 關於作者: |
|
龚鹏程,1956年生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曾任淡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南华大学创校校长,佛光大学校长,中华道教学院副院长等教职;及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道教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著书四十余种。
|
| 目錄:
|
汤一介序
卷一 诗
逆俗 用情 失乡 游学 问道
卷二 思
窥机 从师 交友 树异 主智
卷三 事
因境 执教 涉世 试剑 感兴
卷四 史
困知
得法
历事
藏史
返本
|
| 內容試閱:
|
梅新先生策划了一系列访谈,第一位是古龙,要我去做记录。我仿古龙文体整理了当日之访谈内容。黄老师与梅新先生很满意,古龙更满意,还派人来取了一份。不久之后,古龙即因酗酒而死,该文成了古龙晚年最重要的谈话。也是在十五年后。早期出版古龙成名作《大旗英雄传》《楚留香》等书的真善美出版社少东宋德令先生,由美返国,重新投入武侠小说出版事业,找到我为这一系列作品重写导论,并制作电脑游戏版楚留香。即是这段因缘的后续发展。
访了古龙之后,接着访李敖胡茵梦、高阳、牛哥、颜元叔,谈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文学批评、漫画、治学、爱、性等等。稿子后来都辑入汉光出版社《历史中的一盏灯》。只有古龙一篇,因汉光老板宋定西不喜欢古龙而未收入。宋先生是张梦机老师的“兄弟”,依辈分,我应喊他师伯。硕健朗锐、亦理平头,但蓄须,有威仪,曾是拳击国手,亦为江湖好汉。有次乘计程车,与司机发生争执,司机邀他下车单挑,他一拳就把对方打晕了。聘张老师为其公司顾问,张师中风后,振济恤赡,尤见古侠士风,我甚景仰之。他对我很赏识,屡邀我去主持其公司编务,我都不能应命。如此豪侠,却对古龙不欣赏,也是趣事。
这些访问,郑明蜊曾推许为是她所见过最精彩的访问稿。其实不全是我的功劳。访问时主要当然是我,但不只有我发问,梅新大多参加,也邀一些艺文及学术界朋友莅场,许多有深度的问题是他们提的。我只是费了一些气力予以整理罢了。唯整理亦非易事,当时我尚无力购买录音机,借别人的机器与带子录好,带回龟山去整理,翻来、复去,拼起、删掉,组织成文。于整理中体会受访者之思路、欣赏其语言运用、回忆谈话时之气氛,而以文字追踪之,是非常难得的经验。所访问的这几位,也都是罕见的人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其中最特殊的是高阳先生。他原本是准备招徒的,曾由汪中老师介绍了王文进,二人不契,他又另行物色。梅新要我访问他,本亦有意撮成此事。但访问过后,他一直喊我鹏程兄,常邀我去吃海鲜、谈清史、论红学。一杯在手,语惊四座。我顺其谈锋,随处贡疑献证,他便越谈越起劲。有时来函论学,亦累累数页。在联合报写《曹雪芹别传》时,更指定要我写篇访谈,以当前言。后他又发现靖应鸥藏脂批本可能是赝品,我也附和写了一篇《靖本脂评石头记辨伪录》,刊在成大学报中。当时他很欣赏邱世亮先生在《红楼梦解》中认为该书系影射雍正夺位之见解,由我找到邱先生,三人谈了一次,准备合作写个东西。后虽亦不果,然我之红学知识,实由先生启之。其他所谈,当然亦不限于红学。
他每次打电话来,都是:“鹏程兄!高阳!哈哈哈”。约见面,纵酒倾谈。高睨雄文,同一世之豪也。然时愈久,饮酒愈多,先生之体力乃愈衰,终于一九九二年六月因心肺功能衰竭而逝。那天我去看他,适巧其女公子刚刚走开返校,医生电击心脏抢救无效,先生唇角鲜血溢出,未及与我交谈便去了。我大哭,通知了联合报、中国时报与中央日报,回去赶了几篇追悼文字,纪此缘会,并志感怆。
这也是访谈的续曲。在访谈以外,我并帮副刊写些稿子。例如钱钟书《管锥编》新出,我读后有些意见,写了书评。卜少夫(无名氏)适来台,见之,大为欣赏。常对人说:大陆上捧钱捧上了天,龚鹏程一篇书评就将他打倒了。其实我没那么大本事,只是大陆学界哄抬“钱学”闹过了头,易惹人厌而已。
又如我为了研究汪荣宝,曾去拜访其哲嗣汪公纪先生,获赠其《思玄堂诗》《金薤琳琅斋文集》及清史著作,回来草成《汪荣宝的历史形象与地位》。待一九九四年,又是十五年后,汪先生忽赐一函,谓“久仪清望,无缘识荆,怅恨,怅恨”。且云当年我那篇文章在报上刊登时,他只剪存了上半篇,希望我能再将下半篇寄奉。我很惶恐,忙将文章寄去,并回函说其实他见过我的,我就是当年去麻烦他的那个年轻学生。汪先生又回信说:“家大人思想,蒙代为仔细剖析,使其伟大处完全明了,裨益后人,使得留名千古,胥拜先生之赐矣。公纪不学,先人所遗诸书不能尽识,况今已届耄耋之年,又患中风。而今能遇先生,使其略能领会先人之伟大,真万幸”。我还没来得及逊辞,他就抱病枉驾亲来致谢。使我非常惭愧。其实童子何知?汪公纪先生曾任驻日
代表团公使副团长,学贯中西,而对后辈如此,正与高阳俯与我等后生交友,或卜少夫先生不吝奖饰末学一样,都是老成仪型,足堪式范。我以文字因缘得此殊遇,颇感荣宠。
后来梅新先生离开台时,副刊由周浩正先生接手,我也写了一阵。待梅新转至正中书局时,他便来邀我办《国文天地》月刊。
办此刊物,是他的理想。构想的来源,是从前开明书店的《国文月刊》。他认为这类刊物既能做学校师生修习国文之参考,又可提供社会语文知识,而适为台湾所无,故积极游说正中书局办。先与师大谈合作,未谈成。一九八五年他又拿了计划给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先生看。因正中是党营事业,宋先生支持这个计划,拨了半年一百二十万经费,所以就开办起来了。
正中总经理是蒋廉儒先生,他很支持这个刊物,但其他人则未必。梅新时任正中编务,兼任社长,我是总编辑,另聘原在救国团的杨俊先生为总经理。总共就这么三个人,没有兵,唯有一兼职美工,是联副的陈泰裕。办公室,则把正中四楼会议室隔了一小间给我们用。人员与经费不属于正中编制,只提供一些桌椅设备。所有编务、印务、业务,都得靠自己,但整体方向及运作,却须受正中之节制。
这是多么奇怪的体制?正中是党营事业,有其特殊之文化,副总经理陶佩瑚先生有次举了首打油诗告诉我这种文化乃是:“一枝铅笔五颗章,等因奉此无事忙,只见桥梁不见水,没有子弹空有枪”。公司员工一百多,出版量大约与后来我任职之学生书局相埒,但学生书局总共不过十二人。这么多人,出了些堆在仓库找也找不着之书,而门市、业务、编辑各自为政,日子倒也过得不错。我从私立学校来,处此真是大开眼界,极端不习惯。幸而月刊社与正中关系暖昧,在半独立状态中,稍事忍隐,尚可相安,但精神上是痛苦的。
编务也不容易对付。我此前在出版社编过东西,也担任过采访工作,但编杂志是另一套,我毫无经验。从策划内容、安排段落大要、约稿、设计封面、催稿、改稿、发排、校对、配图、计算栏位、补白、贴版、清样、晒蓝,到印刷、上光、转送书报社,一步步都要学过。我号称总编辑,其实是校长兼撞钟,全得自己动手。我不怕动手,只是不懂,不知如何动手。陈泰裕这时帮了我最大的忙。我其实是在跟着他学,然后找市面上其他的杂志来研究,到底杂志该怎么编。真不懂,也只能旁敲侧击地问,否则总编辑不知如何编刊物,说出来不唯笑死人,也影响士气。
这真是打落门牙和血吞,强忍硬撑着做。那年端午节我就没回家,睡在编辑桌上。当时正中因属党营,门禁与公家衙门类似。夜里来加班,会发现电梯锁了,或铁门关了。有时要从二楼一西餐厅的厨房钻上去。有时加完班下来,准备回家,会出不去,只好在办公室窝一晚。
刊物第一期于一九八五年六月推出,以小鸡即将啄破蛋壳出来为封面图案,标榜“知识的、实用的、全民的”。因为国文是一切人文知识的基础,运用于一切生活之中,并非研习国文之老师学生才需要补充此类知识,每个人都必须注意语文能力的提升。《国文天地》之宗旨即在于此,偏向社会语文学的路线。故除了介绍传统的历史语文学知识外,更要结合社会,讨论语文环境如何改善、语文现象如何了解、语文能力如何加强等。因此刊物一出来,大家耳目一新,觉得仿佛与一般讲国文教育的老夫子面貌有别。创刊号一版印了一万册,迅即售罄,一周后即再版,共卖了一万六千册。半年以后,又获得了新闻局的优良杂志奖。
《国文天地》在创刊时,有人预估不会卖超过四百本,谁能料到居然还能再版?熟悉台湾杂志,特别是人文刊物市场者都晓得那是多么困难的事。但要维持业绩也很困难。刊物的划拨、业务、广告,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勉强发展,其实也非常吃力,
这些我并不能不管。因编辑部后来陆续有王美琴、黄秋芳、林慧峰、蔡素芬君加入,分担了许多工作,所以我便又策划开办“文化讲座”。邀王邦雄、曾昭旭、康来新、蔡信发、颜昆阳……等人来讲《庄子》《红楼梦》《史记》等,学员须交费,以此挹注刊物收入,且扩大宣传与影响。试办效果甚佳,场地不够用。正中便把二楼西餐厅收回,改装成社址兼教室。当时此亦为创举,后来曾老师他们也在《鹅湖月刊》开办,也很成功,渐渐乃广为各界所采用。
针对校园内部的国文教学,我又找了萧丽华、陈贤俊等一批年轻朋友编了一套《国文教学动动脑》,强调教育的创造性、思考性,并提供较丰富的参考资料。这就又使《国文天地》开始出版丛书了。不但杂志已刊之文章可再结集重编为书籍,亦可另行策划,与杂志相互搭配。例如我就找了几位漫画家,编了四本《画说成语》。
杂志乃因此而亦成为一文化综合体,有杂志、有丛书、办文化讲座、结合国文教育界与各文化团体之力量,共同探讨国文知识,多角经营,好不热闹。当时我已贾祸,抨击过中文学界的各种弊端。执编上述刊物时,许多人认为中文学界应该会抵制我;此刊物之风格又带有现代感,恐不易获得支持。刚开始时或许是,但办出气势来了。中文学界的人力反而被我调动起来,没有了支不支持我的问题与权力。而我也恰好有此机会,把刊物办得热热闹闹,表示我不是光会张口批评的人,也能办点实事,具有实践性。正中之态度,也逐渐好转,蒋先生升任董事长、黄肇珩先生来接任总经理,书局经营形态有所调整,对杂志愈趋于积极。
这时我仍在淡江校长秘书处上班,但张先生因已任北市议长,不能再兼校长,遂改任董事长,申庆璧师乃趁隙退休,又向张建邦先生建议让我回到系里去,较能发挥。因我在淡江一直是以行政职员兼教钟点的方式聘用,并未因我已获博士学位而返系专任。经申老师争取,张先生问了我的意愿之后,同意我回中文系专任,改任教师,不再兼行政工作。董事长秘书一职,则把已离开学校,去了铭传的王樾找回来做。
此时系主任由傅锡壬老师担任,我觉得在系里亦未必能发挥。曾昭旭老师已接掌中央大学中文系,颜昆阳准备离开淡江去中央,我便与他一道参加中央的甄选,获得通过,正要返校办手续。新任校长陈雅鸿先生找我,要我负责接手系务。事出突然,情不可却,只好硬着头皮接受派令,并回《国文天地》去向黄肇珩先生辞职。
黄先生希望我仍能留下来,并说正中总编辑也正好悬缺,属意我担任。正中总编辑,是有历史荣誉性的位置,历来都是有名望的学者才有资格担任的。我有些心动。但仔细衡酌之后,仍然决意返回校园。
我像鸟,在外面飞翔之后,总还想回到巢里。学校是我习惯了的巢穴。学术研究是我的志业或生活方式,教育则是我的理想。原本只是因在体制内部推动不了,故以社会教育的方式来带动体制的革新,达成教育的功能。现在既有机会返回校园、实践一些想法,当然还是回去了。
总计我在《国文天地》编了二十六期。把这个冷门的刊物办到有口碑,也有实利,自认为是颇不容易的;替国文教学打开了一条新路向,更是国文教育史上不可漠视的一页。当时联合报社长刘洁先生常在刊物上写稿,后来怂恿联合报系也办了一个《历史月刊》,亦可算我有间接催生之功。我曾见李瑞腾有一文,把这两个刊物合起来讨论,其中评价《国文天地》说:“两年多来确实做了不少事,其中还包括举办六期文化讲座。在刊物上写稿的,可说是中文人力空前的大结合,让我们看到原来被视为僵硬、枯燥的国文,更有它活泼的生命力”。瑞腾与我,是中文学界唯二提倡杂志编辑学的人,后来他办《台湾文学观察杂志》还写过一篇文章谈:“什么是文学杂志学?”故他的评价应该是公允的。
不过,在我卸任后,刊物几经转折,由傅武光、林庆彰先生等先后接办,因与正中发生龃龉,终至决裂,退出自组董事会。这本是可大展鸿图、更上层楼的机会。但文史学人办刊物,不知杂志编辑学另是一门工夫。把刊物宗旨改为“发扬中国文化,普及文史知识,辅助国文教学”,又广用大陆文稿、办图书公司卖大陆书。我则以为如此恐怕会越走越窄。在我离职时,刊物尚有盈余百万元,现在则或堪虑。唯我既不主事,自应默尔。天下事无经久不变者,绩业未必能够长保,此等遗憾,但能还诸天地。
回学校办学不久,有天蒋廉儒先生忽邀我于福华饭店见面,说其友人刘恒修先生在高雄办有《中国晨报》,要扩编,增加北部版。并邀蒋先生出面,组织主笔群,强化言论阵容。蒋先生自己不便出面,嘱我担任。我在正中期间,先后两任总经理蒋先生及黄肇珩先生都对我十分器重、十分礼遇,蒋先生既要我做,我自然不能推辞。况且我已涉足出版、杂志业,报业倒还没真正参与,有此机会,也很难得,于是竟完全未考虑到我对报业的无知,便贸然接下了总主笔的工作。
中国晨报总社在高雄,台北仅一办事处,传真机又不普遍。要由我在台北集稿之后,专人来取,或寄发,联系颇为费时。主笔群则包括曾祥铎、陈瑞贵、傅栋成、潘锡堂、徐定心等。每天注意时事,追踪新闻,与编杂志又甚不同。中国晨报言论倾向较为关注南部社会需求,多社会面之探讨,而较少针对中央政府政策法规之缄砭,在两岸关系上,则属于赞成统一的。风格非常特殊。
可是,该报刚开始在北部发行,体系尚未建立完成,我买不到报纸,必须等第二天才能收到寄来之旧闻。如此怎能掌握言论导向?又无专属之办公室及设备,集稿或与主笔们讨论均甚为困难。再加上言论部门与业务部门,方向上颇有差异,更觉得苦恼。原因是晨报在高雄起家,业务与广告必然受限于南台湾之社会及商业特性,故色情业、六合彩之消息不少。报纸为了促销,也影射明牌,刺激六合彩赌徒之买气。此与言论部门的端言谠论,殊不协调。几经讨论,无法改善,我只好写了封信给刘先生谨辞总主笔一职。
虽然如此,这仍是个有趣的经验。遽操笔政,讥弹时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但言论代表报社,落笔自多斟酌,需从多方面审衡,相关法例、政策、组织及社会脉络也要熟悉。且由此而对报业经营有了一些了解,收获实多于投入。后来我又担任过《民生报》《中时晚报》《联合报》的主笔,也可说是这项工作的延续。
这时我与出版及杂志业之关系也没有断。周安托离开时报出版公司后替业强出版社编书,出了我《文学与美学》《思想与文化》两书。接着他自办金枫出版社,又嘱我企划一套《经典丛刊》。选择经典,予以标校注释,加上导读,连出了几十种。我自己写了十来篇导论,其余请师友帮忙。书的开本很特殊,初出时配合一套“四九五系列”,每册只卖四九元五角,超低价袖珍本,在各书店制作特殊旋转架陈列,很有特色。
时方怡正在汉声电台主持“爱书人”节目,便邀我上电台谈“经典与现代生活”。我每周去录音,随兴谈讲。节目做完后,她把所有录音带送了我一套。我偶然听说有些人还挺喜欢这个节目,甚至逐次录音。便找了几位学生把它整理出来,由新未来出版社印行,以利有兴趣者参考。
新未来出版社是洪俊贤先生办的,由杨树清、郑松维主持,编杂志与丛书,我是顾问。郑兄是我在联亚的旧识、杨兄则早在他任职《书评书目》时期即开始合作。他有“佞龚”之癖,常替我剪存收集文章,也替我编过几本文集。所以这个出版社我介入颇深。每期杂志都参与编务,也出版了《大侠》《经典与现代生活》等书。待一九八八年大陆开放,我与郑松维即赴大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洽谈了他们所编《外国文学》的版权。当时两岸出版尚未交流,外文所副所长吕同六特地从北京搭火车赶至上海与我商谈,决议合作同步出版,每期北京编好后,将清样以国际快递送至台北,同时出台湾版。这当然是个重大的突破,但洪先生财务忽然出了点状况,遂致延宕,最后并搁置了这项计划,使社科院外文所蒙受了些损失,我这中间人也觉得十分尴尬。
失败的经验不止此一桩。稍早吕学海负责久大图书公司,要我找人弄一套日本汉学译丛。我即请张火庆兄来帮忙,邀了些译稿,但周折甚久,亦迄未完成。出版事业充满了不稳定性,于此亦可见一斑。
学生书局此时正好刘兆祐先生辞去总编辑工作,书局即找我去帮忙。因为书局就在我家巷口,稿件都拿回家来处理,十分方便。这是家很有规模的书局,董事长丁文治先生曾任联合报总编辑,历任总编辑如吴相湘、屈万里等亦皆十林硕彦,已办了三十年,出书数干种。总经理鲍家骅待我至为温厚,副总经理黄新新目录之学天下知名。我与他们合作很愉快,也学了很多,校印过《嘉靖徐州志》《直隶河渠书》等明清史料几十种,改版《书目季刊》,策划了不少书,还编过一册《学生书局三十周年纪念集》,替出版史留点纪录。
由学校伸出脚来,涉足采访、出版、杂志、新闻事业,并非学以致用,或以学应世,而是“入世为学”。在工作与事务中学习,以逐渐明其术、知其理、达其体而能致其用。在商业利润、人情世故中打滚,在文化理想与现实条件中折磨冲撞,这不是关在象牙塔中治学者所能了解的。
反之,我从前由张建邦先生处学习到了些有关资讯社会的理论,也要到真正参与编辑出版工作,才能体会资讯传播复杂化、多样化、快速化的时代特性;也才能与工作经验相结合,去考虑资讯伦理、资讯环境、资讯社会学之类问题。而这些,也不是一般新闻、出版从业技术人员所能理解的。现在我办佛光大学,准备开创传播学院、出版学研究所,正有得于这一段阅历,方能彻底反省国内之传播环境、结构与教育。发现出版与新闻有其不同之功能与理则,不能以新闻之角度来涵括传播问题。出版在资讯时代,已发展至电子、音声与文字交错结合之境地,须予正视。同理,同内资讯业界与学界,只知电脑,以为资讯就是电脑。资讯研究所,不是工程就是企业管理。最近才开始开展资讯社会学的面向,并试图结合传播、图书馆与人文学研究。我办佛光大学的资讯管理研究所也即要在此贡献心力。若无这十五六年来长期泽润于此传播环境中之体验与思省,我是不可能有这些作为的。
人世为学,摸索试炼,自是诸苦备尝。涉足既深,关系绵密复杂,江湖道上恩怨纠缠,也不是很好处理。但业界回报我的,也很富厚。例如我初接手淡江系务时,颇以私立学校经费拮据为苦。周安托立刻送了我五万元,说是捐助。这对我来说,是笔大数目。因为我系办公室每年办公费只有一万元,单是请系里老师开会吃便当就吃光了,还能做什么事?得此义助,军心大振,后来政通人和,与此甚有关系。
待我受星云和尚之嘱,筹办佛光大学时,因我早年曾参与陈达弘先生环宇出版社所办《大学杂志》的编务,陈先生遂出面替我组成佛光大学图书劝募委员会。出版界朋友结集组成此类团体,替大学募书,本是不可能亦无先例的。因为大学正是出版界最主要的顾客,新成立大学之购书款更是出版界的救命金丹。现在出版界不但不向我们赚钱,更热烈捐输,且还要去拉别人来捐,天下岂有此理?但中华民国图书出版协会、台北市出版同业
公会都出面劝募。九歌、文史哲、三民、学生、远流等书店也往往整套整套地送。如此厚谊,求诸当世,岂可多得?
同样地,我在发表批评大陆委员会主管的文章而准备离职时,出版界朋友立刻来电致意,并安排餐叙,表示感谢我在任内替业界的服务。可是,我在任内花了同样气力为之争取权益的演艺界,却等不及我离开,便立刻送来花篮,巴结尚未上任的继事者荣膺新职。人情之冷暖,两相对照,特别能感受到文化人的温暖与文化素养。义气侠情,皆见于此等处。
总之,理事相融,涉世有功,当可作为这一段经历的注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