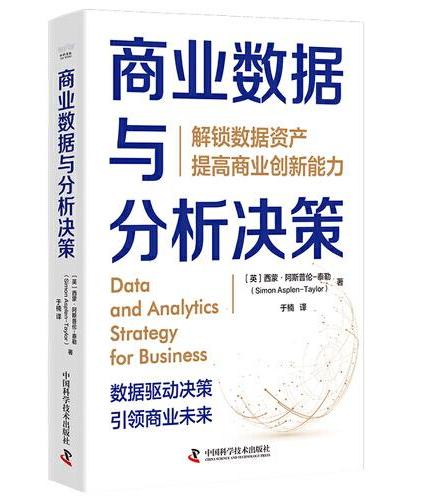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MySQL版)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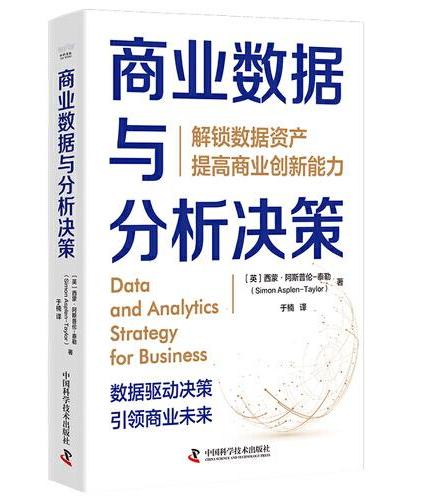
《
商业数据与分析决策:解锁数据资产,提高商业创新能力
》
售價:NT$
367.0

《
倾盖如故:人物研究视角下的近世东亚海域史
》
售價:NT$
357.0

《
史学视角下的跨文化研究(一): 追踪谱系、轨迹与多样性
》
售價:NT$
485.0

《
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论衡系列)
》
售價:NT$
551.0

《
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革命不是新制度推翻旧制度,而是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殊死斗争!屡获大奖,了解光荣革命可以只看这一本)
》
售價:NT$
1010.0

《
东方小熊日本幼儿园思维训练 听力专注力(4册)
》
售價:NT$
408.0

《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
售價:NT$
500.0
|
| 編輯推薦: |
★ 柏林银熊奖、戛纳评审团奖得主王小帅的“三线”记忆
★ 《青红》《我11》《闯入者》创作背后的真实故事
◆模糊的回忆、幸存的老照片、儿时的画、家书、剧照、几经手改的文稿,订成一本私人笔记。
◆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迁徙流变,勾画出一代人的集体遭遇:一群没有故乡的人仅以留存的记忆碎片。
苏童、杜琪峰、刘小东、高圆圆推荐珍藏
唯一一部入围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影片《闯入者》于2015年4月30日在全国上映!
|
| 內容簡介: |
导演王小帅一直说不清自己是哪里人。在上海出生4个月后,他跟随父母来到贵阳“支援三线”,13岁因父亲工作调动迁到武汉,15岁考上央美附中来到北京,23岁北影毕业后分配到福建,两年后无片可拍的他逃离体制,开始他的“北漂”和独立电影创作生涯。
从《青红》到《我11》、《闯入者》,他一遍遍在光影中回望他的童年所在地贵阳,作为一个“三线子弟”,他对讲述和发现这段历史有着无法释怀的责任感。
但这本《薄薄的故乡》却无关宏观历史。这本书中的文字、无意中幸存下来的老照片、儿时的素描、父母的家书等,装订而成的,是一个无故乡的人的精神故乡,是一个四口之家颠沛流离的命运。与其说它是在向读者讲述,不如说它是作者的私人笔记——在撰写整理这本笔记的过程中,他让自己沉浸到往事中,他发现自己不免絮叨,更加发现回忆的不可靠;他意外地找到以为早已丢失的照片和画,惊喜地知晓了一直好奇的谜底。
现在这本笔记已经完成,如一部最终剪辑而成影片,不再私有。
|
| 關於作者: |
中国独立电影先锋导演。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导演之一。
生于1966年。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26岁的王小帅自编自导了他的首部长片《冬春的日子》(1993年),该片成为中国独立电影开篇作之一,并于次年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此后,王小帅凭借其强烈的个人色彩与人文关怀、坚持不懈的独立创作精神,成为中国“第六代”导演中享誉国际的标签式人物。2001年,他凭借《十七岁的单车》斩获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2005年,电影《青红》又令他成为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的获得者,该片也首次把“三线建设”带入观众视野。近年来,他相继导演了电影《左右》、《日照重庆》、《我11》,并于2010年获得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一直到最新作品《闯入者》,王小帅仍坚持不走随波逐流的创作路线,在保持一脉相承的创作风格的同时,一方面力求电影语言的创新,另一方面敏锐捕捉时代脉搏。
2014年,新作《闯入者》作为唯一一部华语影片入围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王小帅也因此成就了第六代导演中的首位“大满贯”。
|
| 目錄:
|
序
镜中无光
湖边青年
城域边缘
电影中的乡愁
父亲
母亲
附录:王小帅父母回忆“三线”
|
| 內容試閱:
|
城域边缘
(一)
回到北京已经是90年代初了。街边多了许多大排档,店主直接用电线把灯泡吊在外面,有的铺面外挂上了灯帘,由小灯串起,当时很时髦,人们叫它满天星。黄昏来临的时候,满天星亮了起来,北京看起来更加热闹了。
我们坐在东四和隆福寺之间的一家饭馆外面,这是一家广东大排档,据说是两个广东的姐妹开的,在当时的北京城,吃粤菜是一种时尚。刘小东和我喝二锅头,喻红喝汽水,吃的什么记不起来了。从1981年考入美院附中,我就和小东认识了,那时我15岁,小东18岁,比我高一届。他很早就和喻红偷偷谈恋爱,大家一起玩耍已经是他们进入三年级的时候了。之后,他们进入美院,我随后一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89年我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在当时这意味着我将永远离开学习生活了八年的北京,离开许多的中学和大学的同学,包括他们俩。
其实我真正到福建报到是分配一年以后的事情,这期间刘小东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并且一次性把画卖了出去,成为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和有钱人。后来我在福建期间,在我们仅有的一次通信中,我说出我的绝望,他说我要赶快干事,这样友谊才能持续并平等。
我是90年9月份到的福建,92年初回来,然后我们就坐在东四的这个时髦的大排档,喝着二锅头,吃着粤菜。我们有两年没见了,我说我回来了,而且不走了,重新当回北京人,就算当不回北京人,我也要赖在这里不走了。
就是在那个粤式大排挡里,我决定流浪北京。并且为了让小东相信我这个朋友不会连累他,会像他信里说的会做点事,不拉大差距,我正式宣布我要拍电影了。显然我还不知道要拍什么,只是恐惧让我必须要先把它说出来。当时我一个人坐在小桌子的一边,小东和喻红并排坐在对面,我看着他们俩,念头就冒了出来,我说就拍你们俩吧。他们说为什么是他们,我说没有别人,因为还没有一分钱,不可能找正式的演员来演。他们说他们能演戏吗?我说不用你们演,待着就行,拍他们也就是拍我们。他们同意了,就是为了帮我成就自己的一个事,这样将来可以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同学,导演王小帅。
其实冒出这个不靠谱的想法以后,我第一个找的不是他们,是邬迪。在学校期间邬迪已经以机械员的身份拍过几部戏了,按当时的说法算是跟过组的人。后来他参加了一个留学生的学生作品的拍摄时候,我们认识了并成为朋友。
邬迪的父亲是儿影厂的职工,所以他在学校边上儿影厂的家属楼有一个小小的一居室,那个一居室就成了我们的窝点。那时候能拥有一个一居室完全像已经拥有了天堂。读书期间和毕业之后等分配的那段时间,我们就在哪儿喝酒、打牌、谈恋爱,留下了许多轻狂记忆。分别两年之后再找到他,他已经有了正式女朋友,小窝点没法长住了,我只能背着唯一的一个挎包,开始流浪北京。记得在学院边上专利局招待所十元一铺的地方睡过一晚,小月河一个剧组的美术的床上睡过一晚,第二天一早等剧组乱哄哄地出发之后,自己再顺着墙边溜走。有一天转移到小月河后面的一家不知名的旅社时,我彻底绝望了,巨大的恐怖伴随着寂静的黑夜笼罩了下来,难道就这样了吗?那个从贵阳到了武汉,又从武汉兴冲冲来到北京,做了将近十年临时北京人的我,就这样再一次被彻底遗弃了吗?在北京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户口,没有了档案,没有了与朋友平等的座位。街边新建的一栋栋楼房,每一个窗户里都亮着温暖的灯光,街边新开的饭馆、大排档,人们坐在那里喝着啤酒,这一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恐惧和孤独压迫着我的每一根神经。回想自己义无反顾地奔向中国地图上最偏远的那个省份,那个之前几乎没在意过的城市,以为电影的大门会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敞开。而现实是,你几乎用生命跟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如今没人能够挽救你了,学校跟你的关系结束了,朋友也都一样年轻迷茫,这天下只剩这么一个幼稚无知的大傻子了。在那个深夜,我咒骂着自己的愚蠢。但这不是最后,生命和世界都还没有结束,明天天还会亮,你还要离开这个旅店,在街上寻找下一个可能免费的床铺,你必须做点什么!我是干什么的?我想干什么?
天亮的时候,我找来了邬迪,还有何建军,我说我要拍电影,马上,不能等了。他们说你有投资了?我说一分都没有。他们说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再去找九个导演,九个摄影,一起当导演,一起当摄影,来拍我们的第一部电影。我认为这样不行,导演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工作,人多了会乱,还是得单独干,自己闯出一条血道。集体创作的事情被放到了一边。
再后来我找来了刘杰,加上邬迪,摄影师我有了。刘杰和我跑回了他的老家取得了保定胶片厂的同意。保定乐凯胶片当时已经不生产能用于电影拍摄的大本胶片了,大本胶片出厂时都被裁成35张一卷的照相用的胶卷,我们说服他们再次振兴国产胶片,他们同意将在我们拍摄期间特意为我们保留一些大卷,这样我有了胶片。我们又在北影厂的器材库里找到了一台早已弃用的摄影机,这台摄影机不能用于同期录音,一开机哗哗地响,像是拖拉机从你耳边开过。我不管那一套,只要能挂上胶片,把人拍动起来就行,声音后期再配,这样我有了一台摄影机。
于是,我坐在东四街口的广东大排档里向小东和喻红宣布我要拍电影了,演员是他们俩,这样,我有了演员。
剧本在美院的学生宿舍里完成了前半部分,取名“冬春的日子”。我向小东和喻红道歉,我说这个电影里的他们还没有办过个展、卖出过画,还没有成功。这个电影里,他们是迷茫的两个人,连爱情都要走向绝路。我拍的是他们的影像,可附着的全是我现在的心境,一个恐惧、迷茫、失败的黑白世界,这个世界还联结着我们89年毕业的所有人的境遇。
十几年前,一个抱着当画家的理想的青年,一个人离开武汉,开始了在北京的独自生活,那个时候的他,完完全全想不到他未来的职业会是一个如此遥不可及的梦。父亲苦心经营的绘画理想结束了。父亲曾反复劝告他,不要走有关戏剧或电影的路,说这条路太辛苦,所有的一切你都决定不了:演员可能一辈子等不来一个机会,导演可能一辈子无法自由表达——一方面戏剧电影本身的集体创作形态使一个作者很容易就被淹没掉个性,另一方面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度,由于我们的意识形态特性,很多时候导演只不过是个傀儡罢了。绘画就不同了,绘画你可以独自一个人完成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可以是山,是水,是花鸟,无关乎别人,无关乎政治。在绘画艺术里,你可以自由自在。
因为父亲一生的经历,我相信他说的话。
……
(二)
真正一次觉得自己彻底乡下了是在电影学院毕业以后,我在地图上第一次认真查找了一个叫福州的地方,它在离北京最远、或者说中国版图上最边缘的东南角,甚至已经超越了西南贵州的位置。贵州下面还有广西,而福建的外面,就是海了,海的对面,是台湾。我被告知正式分配到那里,福建电影制片厂,户口和档案已经离开电影学院,如果我不去,我将无处安身。记得那是1989年8月左右,当时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著名编剧陈剑雨先生亲自到学校要人,陈厂长的女儿是如今著名雕塑家向京,我在附中的同学。陈剑雨找到了我们,承诺我只要同意去福影厂,那里将是我施展才华的天地。我答应了。
我永远记得一年后的那次报道旅行,从北京去往福建。
小时候坐过时间最长的一次火车是从贵阳到北京,两天两夜。但是因为年龄太小,过程已经记不清了。另一次是15岁时只身从常州的大伯家坐火车赴北京,那次是去美院附中报道,从上车就被堵在车厢边的厕所门边再也挪不动半步,就这样两天一夜地站到北京。然后就是九年之后的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漫长的火车之旅,整整三天三夜。头两天,窗外基本还是曾经熟悉的景色,对时间还有概念。进入第三夜的时候,突然感到不对劲:怎么火车还在开啊,我这是要去哪儿啊。望着窗外墨一般的黑暗,看着铺位上睡得很香的同学凌云和一整个车厢沉入梦乡的旅客,恐怖和孤独感如凉水般慢慢地浸透了全身。他们睡得多香啊,他们有的是回家,有的可能只是短暂地出差、游玩。凌云虽然也和我一样被分配到福建厂,但他的爱人已经早早地安定在了福州,他这也是回家啊。而我是算什么呢?奔赴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不是暂时,而是永远要生活在那里了,自己23岁以后的人生就这样永远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朋友、同学,未知的一切要在那里展开了。崩溃出现在次日早晨,当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的时候,车轮枯燥声音粗暴地持续着。还在开吗?窗外的景色已经全然变了,眼前一条宽阔的河流跟随着前进的火车,河面上蒸腾着一片蒙蒙的雾气,使河岸两边的树木、山丘掩映在一片朦胧之中,初升的太阳血红而无力地悬挂在那里,就象一个刚刚睡醒的人打着慵懒的哈欠,它的光芒还没有完全显现,但这光芒已经逐渐代替了值更的黑夜,时间无情。这是哪里啊,这还是中国吗?这是我二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视觉经验。“闽江,”凌云说,“我们已经进入福建了。”“遥远”这一概念第一次那么真切地呈现在我脑海中,它已经不单单指物理上的距离,还含有心理层面对未知的无望和恐惧。
这已经是第三个白天了,虽然这一天我们也将抵达这一次旅途的终点,但不行,这一切都错了。我强烈地意识到如果等到了终点,等这趟列车真正到了终点,一切都来不及了,一切都没法改变了,我就要站在那个陌生的土地上,成为那里的一个居民,不是过客,不是游客,而是一个真正的当地人了,一切就都是真的了。我跟凌云说我要在下一站下车,我不要到那个地方去了,我以为只要我中途停下来,对某个东西说我错了,我就能改变一切、回到过去,让一切从新来过。我急切地重复着,表露这不加掩饰的恐慌。我要下车,我要坐火车回去,不能等到一切都变成事实。
我在那辆载着我奔向那个不可逆转的结局的火车上做着徒劳的挣扎,我跟凌云描述着我想象中的情景,那里没有人会来接我们,我们到了那里,会有一个门房老头问我们是干什么的,然后会有人把我们领到一个招待所的房间,然后我们就被扔在那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对,不是我们,是我。因为你会直接回家,吃你老婆已经给你准备好的饭菜,睡上你和你老婆的床,然后第二天早上你会穿着拖鞋、睡衣,在自己家门前的小院子里散步、喝茶,你的一切都会尘埃落定,你心满意足。凌云看着我,无言以对。
太阳终于显现了光芒,白天冷酷地驱走了黑夜,时间继续着冰冷地脚步,无论你如何挣扎,都已经无法改变在前方等待的事实了。
那一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终于被这个毫无感情的庞然大物驮到了终点站福州车站。
没有人来接我们,甚至凌云的老婆都没有来,完全陌生。我乞求地看着四周,巴望着哪怕有一个可以抓住的同情的眼神,这个眼神会走过来说,我知道你不属于这里,来,我送你回去。
凌云陪着我先到厂里,谢谢他没有直接回家。一切与我预想的一样,空空的厂门口,门里一个不大的小院,院子中间一个小小的水池,池边用铁栏杆围着,水池后面是一座三层的小楼,灰白色。这个楼除了办公还兼着一些职工的宿舍,厂长室在二层左手靠近走廊的第二间。厂门口左右各有一栋宿舍楼。绕过办公楼有一个小广场。比篮球场大一点,再绕到办公楼后面是一个四层楼的招待所,厂里不拍戏的时候这里空无一人。自从我进厂后,它一直空无一人,我曾经是它唯一的住户。在招待所的边上、小广场的身后,有一个摄影棚,不算大,但已经是一个正式的摄影棚。就是这些了。门房的老头问过了我们的来意,叫来了一个中年妇女,是管后面的招待所的,她把我们领到招待所,我们爬到了三楼,随便停在一个房间前,妇女打开了门。屋子里没有窗帘,四张生锈的铁皮床架子,上下铺,可以睡八个人,没了。妇女说食堂在楼下的平房里。可以先找她换饭票,一会儿她会抱一床褥子和被子过来。记得那时已经过了中午,阳光灿烂,除了我们仨和门房,整个过程中未见到一个人影。宁静中可以看到阳光下飞舞的小虫和偶尔被我们唤醒的粉尘。妇女给我抱被褥去了。凌云和我抽了一根烟,“我走了,弄好了哪天到我家吃饭去。”
随着他的脚步最后消失,一切尘埃落定。
在死寂一般的空气中,我,只有我和我在一起了。
我确信这是一个幻象,一切都不是真的。但是我的确信不起作用。我坐实了这里,这间屋子,这些铁床,这里的空气,有一点发霉的灰墙,是我,是真的我在感受这一切,一切都是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