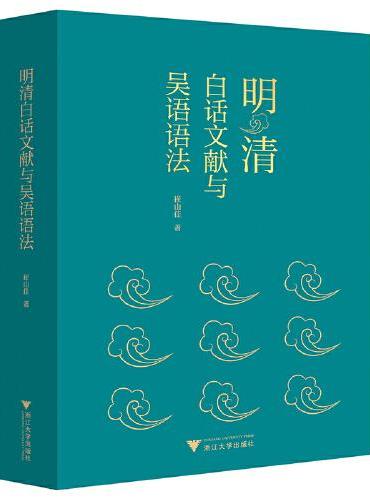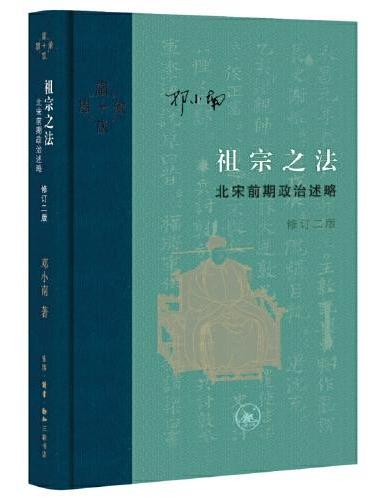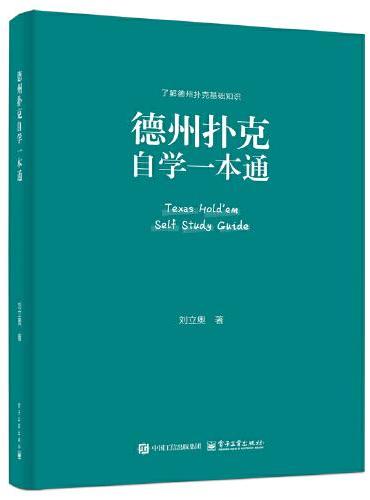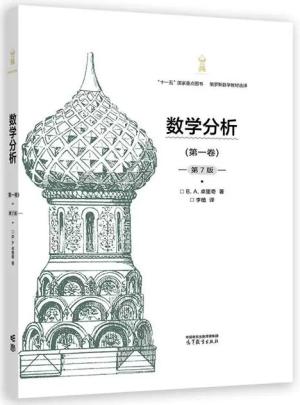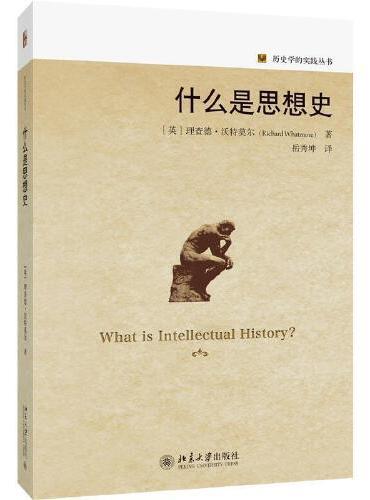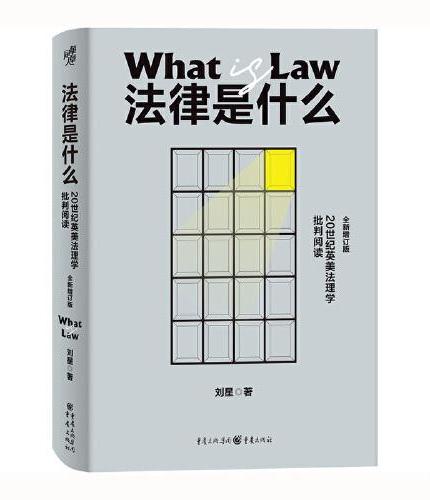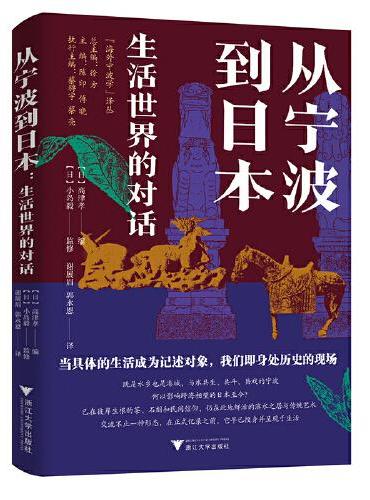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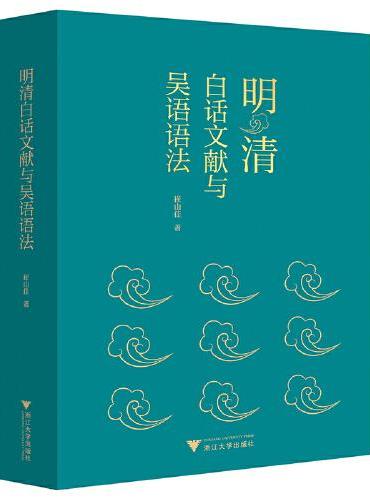
《
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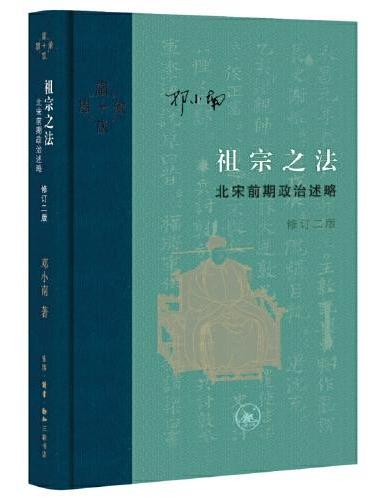
《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二版)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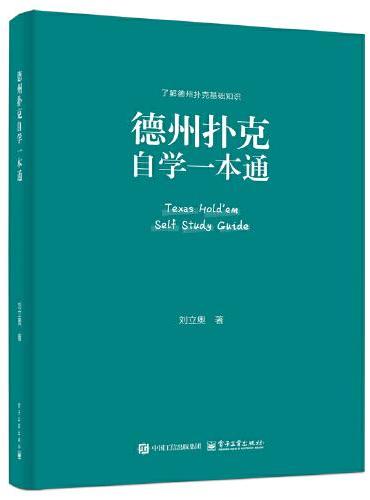
《
德州扑克自学一本通
》
售價:NT$
2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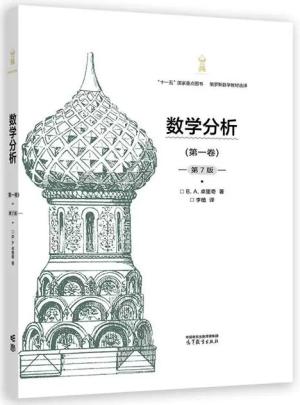
《
数学分析(第一卷)(第7版)(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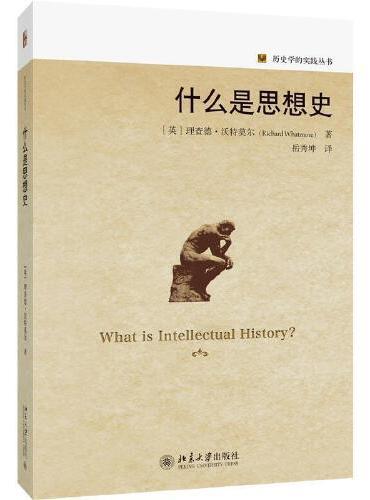
《
什么是思想史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
售價:NT$
2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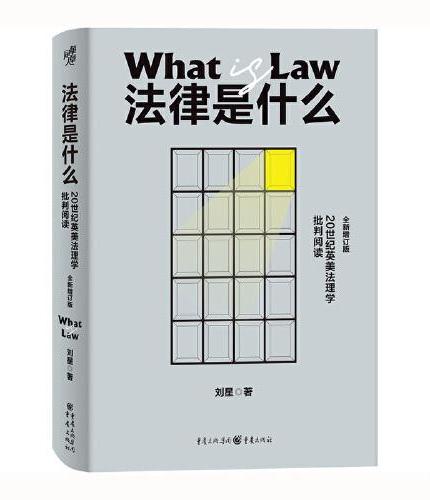
《
法律是什么:20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全新增订版)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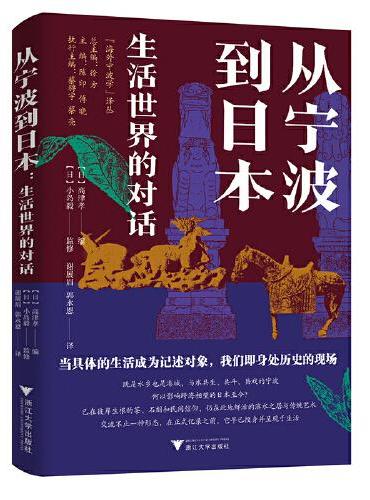
《
从宁波到日本:生活世界的对话
》
售價:NT$
347.0

《
西夏史(历史通识书系)
》
售價:NT$
357.0
|
| 編輯推薦: |
一位不该被遗忘的顶级国学大师,历任北大、北师大、中大、浙大、西南联大教授,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书写者。西南联大中文系讲课最好、最受欢迎的系主任,绰号“罗叫天”。
七十年来《习坎庸言》就像传说中的《葵花宝典》,而今首度公开面世。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由“习坎庸言”和“鸭池十讲”两部分组成。《习坎庸言》是罗庸先生在西南联大习坎斋(取《易》之“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之意)自己寓所作的学术讲座讲稿,主题包孕广博,分为勉学、识仁、六艺、诸史、九流、理学、经世、文章、种族、文化、质文、礼乐、乡党、学校、儒侠、风俗等内外学术16篇,由学生李觐高根据笔记整理。《鸭池十讲》是罗庸先生在昆明期间另一系统的演讲。收其讲演稿十篇。因昆明的滇池在元代名鸭池,“以记地故,因题此名”。十篇文章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谈儒,论诗,谈士,娓娓道来,足见其学识之博,见解之深,更可窥其于国忧家难之即,对民族精神之阐释。
|
| 關於作者: |
罗庸(1900—1950)
字庸中,号习坎,蒙古族,生于北京。著名国学家。原籍江苏江都,清初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同时兼任北大讲师,女师大、北师大教授。1926年参与创办华北大学。1927年应邀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同年秋,应鲁迅之邀,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浙江大学教授,1932年起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讲授《诗经》《楚辞》《论语》《孟子》等课程,后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病逝于重庆北碚。生前出版的著作极少,只有《鸭池十讲》和《唐陈子昂先生伯玉年谱》等。
|
| 目錄:
|
习坎庸言
缘 起
规 约
内篇一 勉学
内篇二 识仁
内篇三 六艺
内篇四 诸史
内篇五 九流
内篇六 理学
内篇七 经世
内篇八 文章
外篇一 种族
外篇二 文化
外篇三 质文
外篇四 礼乐
外篇五 乡党
外篇六 学校
外篇七 儒侠
外篇八 风俗
后 记
鸭池十讲
前 记
一 我与《论语》
二 儒家的根本精神
三 论为己之学
四 感与思
五 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
六 诗人
七 思无邪
八 诗的境界
九 少陵诗论
十 欣遇
|
| 內容試閱:
|
习坎庸言
内篇三 六艺
昔人治经,往往拘于门户,致有今古之争、汉宋之争。五四而后,复有对经学发生怀疑,倡为废经之论。而亦有视经为史料,以纯科学态度研究之者,遂与今古之争、汉宋之争并立,成为经学中之四派焉。今就所知稍加论列如次。
先论六经定名。六经或称六艺(刘歆《七略》有六艺略),孔子时无此称也,《论语》中亦无以六经教弟子之记载,然细按之,则夫子固尝以礼乐教弟子矣。颜回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是孔子以礼教也。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子击罄于卫,是孔子以乐教也。《论语》论诗之处尤多,而书则少,论及尧日一篇,是否孔子所说,疑未能定。孔子作春秋之事,《论语》无明文,称易之处则有: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其下文曰。不占而已矣。未能剧指此曰孔子尝以易教也。《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由、子夏。孔子之教弟子者,如此而已。
《庄子·天道篇》:孔子……翻十二经以说。或曰十二经即六经六纬,实则庄子之所谓十二经者,未易知其果何指也。(十二或为六字之讹)礼记经解,絜静精微易教也,恭敬庄俭礼教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良易乐教也,疏迩知远书教也,展辞比事春秋教也。此易、诗、书、礼、乐、春秋次第即为汉志所本,后之《隋书·经籍志》,逮清《四库全书》,莫不放此。《周礼·地官·保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又大司徒之职,以师三物教万民……一曰六艺,六艺次第同此)。自汉人以易诗书礼乐春秋为孔门艺,因别称礼乐射御书数为古之六艺焉。《周礼》本为晚出之书,然亦保有不少古代原料,此六艺或即古之六艺(《论语》论射御处甚多,书数为小学之事,故未论及),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之名当起于战国,此证以《论语》而可见者。《论语》凡孔子弟子所记多称子曰,多单句;凡称孔子曰者,则多再传弟子所记,文多成格套(如尊五美,屏四恶,君子有三畏等),《礼记》经解篇已有整齐之六艺理论,是知六经之说或已定于春秋战国之际也。
至汉而有今古文之分。今文靠口传,重大义;古文靠简册,重训诂(清人尤重训诂)。至宋而又有汉宋之争,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因之各经显晦亦随时代而不同。
古之六艺与孔门六艺不同者,六经无射御书数,古六艺无易诗书春秋,一古射御或当有经,由礼大射可以推知)。而礼乐居六艺之首,则其所同者也。吾人在古代文化方面着眼,从孔门教学态度着眼,则六经次第礼应居第一,乐第二,诗第三。诗为乐词(乐言其音调,诗指其篇章);书太史所掌,是书已包之于礼之中;春秋亦太史所掌;易,太卜纀所掌,均应包括于礼;诗亦应为国史所掌,《大雅·生民》《小雅·六月》即是史诗。史诗乃诗的正宗,诗人即史家。卫宏诗序:国史明乎得失之故,云云可证。此章实齐所以有六经皆史之说也。由是论之,诗应居书前,春秋应列书后,易为卜筮之书,实如禅宗之教外别传。以此意排六经次第,则当为礼、乐、诗、书、春秋、易。然经解何以置易于六经之首?盖战国之末,秦汉之初,六经逐渐成系统化、哲学化,故置易于首,其余五经遂与易成为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此盖儒家与阴阳家合流之结果也。有一旁证焉,即由荀孟之别亦可得窥六经之次第。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此语不见于孟荀列传,见赵岐《孟子题辞》,观附注),是以法先王,盖长于诗书,未必长于礼乐也。荀子隆礼乐而杀诗书,故法后王。《劝学篇》“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云云,故继之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荀子视礼乐在前,以六经为经世致用之学;孟子以诗书在前,视六经为义理训诂之学。盖荀子深得孔门立教之意,为儒家正宗;孟子实为儒家别派。(汉时荀孟并称,隋唐之后,贬荀尊孟,至宋而极。是以读六经者,只见其训诂名物而不知经世致用也。然由荀子至于韩非李斯,儒家一变而为法家,孔门以六艺设教之意,经数度变迁,原始精神盖不可复观矣。
今依新次分论之:
一、礼。《说文》:礼,复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古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国之大事也。今所见者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仪礼为礼经,今存十七篇,汉人称之为士礼(所谓推士礼以至于天下),实属记录节文之书。如《聘礼》《燕礼》所记,盖一礼节单子而已。就今所见之十七篇而论,知仪礼来源甚古。仪礼形式多仿自周人,至春秋仍通行,然士丧祀,祝有夏祝、商祝、周祝,夏祝商祝即夏商仪礼之残留,可知其源甚古也(惟夏祝商祝于丧礼中执事殊少)。《士昏礼》《士丧礼》篇后皆有义,此即礼记,约为老儒解短经,弟子笔记,本与礼经有别也。
今之社会学家读仪礼,目亲迎礼之为掠夺婚姻;新史学家读仪礼,目之为变性的遗留者。细按仪礼概非无故,《士昏礼》后之《昏义》,若与《礼记·昏义》相比,则知礼记曲解处多,然则墨守经传欺,抑从社会学者与新史学者之说欺,此孔门教学态度所宜先知,否则必生无所适从之苦。欲识孔门教学态度,必先识仁,仁者大用流行之谓(宋人曰天理流行),完全看重自己的生命,亦即全人类生命之谓,把人生看成活的,动的,向前进的,以人为主,以物为偿,不仅不随物转,且不容身外之物停留不进,因如此则有累有遗。此为孔门讲学主旨所在,足以对于历史上的遗产,可用者用之,其不可用者革之,可以存在者因之,其不应存在者去之,一切外物均须顺我的条理,我不能就它的范围(如茶杯本用以饮茶,若以饮酒即可目为酒杯),孔子于此认识极为透彻。故礼已由野蛮入与文明,孔子乃利用之使之更文明,且追而使人忘其野蛮之一面。人的地位高,一切皆我的注脚,一切皆为我所用也。仪礼原由野蛮而来,然至孔子面目已为之一新,盖孔子学有根源,故能贯之以道。不明乎此,扬甲抑乙,要为不通之论耳。(《五礼通考》为读礼必读之书)
戴记,仅有少数篇目真为礼记(如冠义、昏义皆有仪礼为经),其他各篇凡七十子后学所记均收入,实为儒家一大业书,由汉晋至唐,学者多注意昏义丧义,甚少理会乐记、学记、仲尼燕居各篇,犹存古意。宋人反是。此为讲学态度之转变。今欲分析礼记内容,则殊不易,韩非显学所称之八儒恐皆包有之。《王制》《月令投壶》《深衣》所记皆为礼学专篇,既非释经之传,亦不得称为儒学。大戴记多曾子语,若合二戴记以分析儒之派别,则讲《论语》可无笼统浮泛之病,然则此非本篇所论者矣(清人除朱彬《礼记训纂》,孙衣言《礼记集解》外,尚无佳疏,仍待重作)。
《周礼》本周官经(以别于《尚书》之周官)。冬官亡佚,汉人补入《考工记》。古文家尊《周礼》,今文家则斥为刘歆伪造。《周礼》中盖有丛杂不全的古史料甚多,曾经刘歆整理,然亦不可一概斥之为汉人伪造也(如周礼论诗六义之次第,曰风赋比兴雅颂,甚有根据,盖得古之遗意)。《考工记》为晚出之书甚易见(由地理考之似为晋人之书),记中以燕秦胡并举,是则战国时之说也。后人以《周礼》配《仪礼》《礼记》,称曰三礼,所包至广。盖儒者以礼为本,荀子隆礼,其意深远。欲治六经必先自治礼始,此大本大原也。(礼之用《礼乐篇》再详论之)
二、乐:乐无经,诗三百篇即《乐经》(《乐记》二十一篇,戴记合为一篇)。汉文得乐人宝公善说乐,然亦只记其铿锵鼓舞而已。是以《汉书·艺文志》曰:“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云云。大约古乐无谱,仅赖口耳相传而已。《尔雅》:“大版谓之业。”《左传》:“臣属肄业及亡。”后人乃误以案属乐谱,盖不然也。《汉志·诗赋略》著录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称之曰曲曰折,推想汉乐谱盖宇旁尽有曲折也(汉人乐谱已不可见,唐乐谱宇旁有曲折,《大藏经》《点山集》及道藏中有之,约略可以推见汉乐谱之大概,至歌态舞容,征之故记亦尚零星可见。然晋唐而后,学者聚讼,唯在吹律旋宫,乐学日益湮毁矣。(乐之用《礼乐篇》详之)
三、诗:诗即乐章。今人所聚讼者为诗系孔子手订抑系民谣问题。余意论诗有必须注意者二:读诗不能忘记音乐,一切解释均不能离开音乐,根据音乐解释,则可知二南何以编排在前,周颂何以在后。旧说以诗经按照年代编排,由音乐见地论之,此说甚谬。诗之内容代表周代文化面目,不必多牵涉孔子与先王之泽,而比较各地风诗之异同,则甚重要。就篇章字句而言,以音乐为之纲领;就诗的内容而言,以周文化作为纲领,由此读诗距诗意必不太远。《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理,可以群,可以怨,为读诗最重要见解,名物训诂抑其次也。
讲诗不必从毛,亦不必从三家,将古书中讲话之处连缀来讲,则必多所通解,如此则汉儒拘泥可以打破。盖三家与毛不同,宜汇通不宜墨守也。朱子从白文观诗之大义,其方法甚为可取,惟拘于三体三用之说,其极必言美剌,是朱说大病。近之说诗者,悉能打破旧说,惟多忘记诗乃代表周文化的面目,以是多浮浅不切之病。诗教不如是之卑也。(此节未尽之意《文章篇》详之)
四、书:今古之手可置勿论,仅就二十八篇言之,则书之面目已非固有,其中必多改动之处,如盘庚用语与用字是否为商代的即颇有问题也。书之内容颇为丛杂,如牧誓、大诰、酒诰仅为命令,顾命则多陈丧礼,与尚书之体不合。吕刑为中国最古法律条文,禹贡与礼王制性质为近,如此顾命并入仪礼,禹贡并入礼记,始与《尚书》记言之体相合。《洪范》一篇所托,或为阴阳家言,或为礼官之语,盖为后人连缀而成。而于行文之前加武王胜殷,杀纣,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的帽子而已。设将书中各篇归类整理之,则知《尚书》材料极不整齐,盖残缺亡佚者多矣。
《尚书》所记武王伐纣事与儒家说合,而《逸用书》所记则适相反(此书多战国纵横家色彩,然亦有真的史料保存其间,此治古史者不可不知),盖儒家所论文武,往往使之典型化,汉人托古改制之说即本斯意而来,读书者不可泥也。
五、春秋:非鲁史专名(《史通》六家二体所论甚精要,可参看)。因古今文之不同,三传之微言大义亦有不同,古文家不能离传而独解经,今文家则专从书法着眼,是以公谷简略,左氏繁详;公谷多言劝惩,左氏则详于史实。
于此有宜论及者,《左传》与《国语》为一书为二书?《左传》究解经典否?
《左传》本晋语(高本汉说),与《国语》原为一书,钱玄同先生《新学伪经考序》论之甚详。然文字颇有不同:《国语》文字较古,《左传》较近;《国语》讲典章制度亦古,《左传》则近。《周礼》《国语》对古代典章制度之面目,存真为多。《左传》则多改易。《国语》文字繁复,亦疑有后人改动之处。《左传》本不附经,后人乃引传附经耳。《左传》论礼多与《周礼》合,此必后人改动,然是否为刘歆则不可知。《左传》中之“君子曰”三字,约为后人所加批语,后世不察,误入正史,此与《左传》真面目甚有关系,故特及之(《左传》中去君子曰则文义甚连,可知为后人混入正文)。至春秋尊王攘夷三世三统之说,则属西汉之学,故不论云。
六、易:易本难解,今则解易者纷出,而易愈趋难解,然若众家系辞,专看卦词爻词,则知易实为卜筮之书,本阴阳家言,论为官守,则属太卜,此易之本来面目也。京房所论仍为易之真面貌,焦延寿、易林、杨子云、太玄皆循此系统而来,子翼则为儒学,然终汉人之世未为显学。逮王弼注易,易遂变质,成为哲学上的最高宝典,其流遂成南北朝三玄之学。宋儒谈性理,亦从王弼转蜕而来。自周敦颐太极图说至朱熹易传,易与阴阳家若合若离,关系始终未断。易本非儒家之书(近年甲骨出土渐多,多有以甲骨文字解卦辞爻辞),以儒解易,当为七十子之后,与阴阳家打通而成的儒之别派。易之子曰恐亦非儿子语,盖以《易经》义理兴《论语》之仁实为两途,与《中庸》《大学》《礼记》所记反为一类,然在哲学上实极其高明也。
王弼注易,所据为老子义。盖易为占卜之书,多语人以趋吉避凶,与老子为近。道与阴阳本源同而路殊,宋儒讲易,多不能脱离阴阳与道,盖变易简易不易均为老子之学也。治学者从易入手,往往流于纯理哲学,流于玄想而不顾实用,篆象系辞所论,本甚圆融,意通于《论语》之仁,然仍为外在的,仍与老庄为近,而与儒说为远,(尚记民国二十年客杭州,熊十力先生称马一浮先生曰:正法眼藏。盖马治学以六经为主,熊自易入手。熊又曰:儒家毕竟正大,正大一词甚得儒家真面,附记于此,为解儒与道之一助焉)。余意由卜辞以明占卜,由王弼卜论三玄之学,由儒之学庸以论易,三家融会贯通,夫然后易之真面灼然可见。若以易包括六经,则《论语》之仁不易见。汉志列易为第一,此正为阴阳家含射儒家之结果,几微之处不可不辨也。
七、《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论语》大意已见《识仁篇》,《孝经》为初学之书,《尔雅》则为字典,《孟子》至唐后始尊,至宋而有十三经之目,至此经之意与古书无别矣。(段玉裁党主张多加说文经为十四经)
分段论之,则前乎孔子之六经应为一段,自孔门弟子至汉初为一段,汉世今古文之争为一段,自东晋至南朝末为一段。东晋礼学最发达(礼中丧服最发达,此盖渡江而后,极力尊重门阀家族,示不忘本,且别于异族也),诗书春秋之学渐微,至唐转为义疏之学,不过为传笺圆谎而已。经自可贵而笺疏俱不足贵。唐代《孝经》为家弦户诵之书。宋儒讲春秋,严夷夏之辨,治诗改重序,尚书之学发展甚少。在科举制度提倡之下,四书礼家皆成显学,此风至清不变。清儒治训诂,于旧说多有更订,厥功亦伟。民国而后,怀疑经书之风起,复古之士乃倡为尊经之说以相抗,然多无识,固不足以张其军。夫离经则无中国文学,此经学之不可不讲也。然经学固多歧途。以上文所言为纲领,则不致徘徊,待其大义既明,再以儒家论仁之意融贯之,则四辟大通,无甚窒碍矣。
觐高笔记 五月十日下午二时至四时
鸭池十讲
前 记
这一本小册子,共收入讲演稿十篇,大半是近五年来旅居昆明所讲。昆明的滇池,在元代本名鸭池,在我书室内悬挂的一幅昆明玉案山筇竹寺元代白话圣旨碑文,就称昆明为“鸭池城子”,以记地故,因题此名。
近五年在昆明的讲演,大致不出三个范围:一种是关于为学做人方面的话,一种是关于诗的,还有一种是关于文学史的。开始集这小册子的时候,本有《论读专书》《文学史话》《诗的欣赏》《中国诗的前途》四篇,这都是讲演稿;后来,看看内容不大相称,便把这四篇抽出,另编入《论为己之学》《思无邪》《少陵诗论》《欣遇》四篇,仍旧是十篇。《论为己之学》是为三民主义青年团西南联大支团部的刊物《联大青年》写的,《思无邪》是为《国文月刊》写的,《少陵诗论》是抗战前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新苗月刊》写的,后来发表于《经世季刊》,《欣遇》是为昆明《文聚月刊》写的,都不是讲演稿,也不限于昆明,但既已题为《鸭池十讲》,也就不愿再改名目了。
敬谢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国文月刊社的主任编辑余冠英先生,他允许我把这些讲稿刊出,因为有许多篇是在《国文月刊》发表过的。谢谢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助教马芳若先生、中法大学文史学系助教李松筠先土和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同学王宾阳君,因为有几篇稿子他们替我重抄过。
一九四三年五月四日,罗庸记于
昆明大绿水河畔之习坎斋
(一)所谓中国文化者
有些人根本否认中国有其自己的文化,以为:我们穿的是胡服,睡的是胡床,听的是胡乐,历史上文化交流的结果,所谓中国文化者,早已成为极不明确的名词。但我们这里所谓文化者,并不是指的一些具体的文明,乃是指的一民族自己的生活态度,中国人有其与西洋人不同的生活态度,那就是中国文化。
观察一民族的文化,首先应当明了这文化的由来。中国自殷周以来,建立了以农立国的基础,散漫的农村社会,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民族心理,造成了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人与人之间,只有亲族的伦理关系,最远的推到朋友而止。天子号称“家天下”,也不过是把天下看成一个大的家族。君臣以义合,只不过是朋友的变相。力田,尽伦,长养子孙,生活便算圆满了。农业社会,三分靠人力,七分靠自然。农村的生活,最先感到的是自然界的伟大、和平和有秩序,尤有意味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一片生机。孕育在这种环境中的人类,除了力耕自足而外,如何与自然求谐和,成了唯一的人生目的。所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成了人生哲学上最高的境界。反观其他动物界的搏击吞噬,同类相残,便憬然发生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觉悟。由此人的自觉,而有仁、义、礼、乐一套的理论与实施。
这一套农本、人本的人生哲学,奠基于周,而完成于孔子,推阐于七十子以后的儒家,形成了三千年来的民族意识。只要中国的农村本位的社会没有根本的改变,则这一套文化的形式永远不会变更。至于人的自觉这一点,则更是几千年志士仁人出生入死拼命护持的所在,纵使粉身碎骨,也不肯为禽兽之归的。
以农村的自给自足形成了寡欲知足,以力求谐和自然,故极力裁制人欲,这样子是不会有长足进步的物质文明和工业制造的,因而也就免除了财富的兼并与经济斗争。以安土重迁故不勤远略,因而没有拓殖的欲望;故步自封是毛病,但也永远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者。以人的自觉老早成熟,故很早便脱离了宗教的束缚,因而像欧洲历史上宗教的黑暗和战争是没有的。人本的思想使得对人类只有文化的评价而无种族的歧视,“中国进于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因而养成了对于异族的同化力和大度宽容。记得严粲诗辑评《诗经》的周诗一句话说,“周弱而绵”。中国文化表面看来似乎是散漫而无力,但是这绵的力量却是屡遭侵略而终不灭亡的根源。
假使帝国主义的暴横残杀是人类文化的病态,则中国文化无论有什么缺点其最后的核心到底是人类文化的正常状态!
代表中国经济层的是农民,代表中国文化层的便是士大夫,此外,兼并的豪商,独裁的霸主,都是中国人厌弃的对象。
(二)士大夫的历史及其前途
士大夫实在是中国文化的轴心,他的责任是致君泽民,上说下教。他一方面是民众的代表,一方面是政府的监督,而以尽力于人伦教化为其职志。自从东周政衰,世卿的制度崩溃,所谓王官失守,学在私门,有心的士大夫便以在野之身,积极地作文化运动,孔子便是这时代唯一的代表。但战国的局面,正在封建制度崩溃的前夕,诸侯的军备扩张,造成了农村的破产。大都市繁荣的结果,增加了商人赚钱的机会。士大夫也者,没有了代耕之禄,不得不学商人的样,挟策求售,曳裾王门。读书人商业化的结果,造成了游士之风,贤如景春,也不免艳羡,称他们为大丈夫。秦始皇帝和李斯似乎很有办法,他们对付都市膨胀的办法是毁名城,对付土豪的办法是杀豪俊,对付资本家的办法是徙富豪十二万户于咸阳,对付散兵游勇——不能归田的农民——的办法是北筑长城,置戍五岭。剩下那些剩余商品的游士,就只好活埋了。这种大刀阔斧的做法,在我们读春秋战国三百多年的历史头昏脑胀之余,诚然是一件快事;但可惜积极方面忘却了中国的社会基础是散在农村。中国文化的中心是仁义之道。结果,努力造成的一个集权的中央,不旋踵而遭遇了散兵革命。汉袭秦法,只有重农的一件事,却根本地挽回了当时社会的生机。惠帝的奖励孝弟力田,窦太后的好黄老,文景四十年的与民休息,恰是适合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在这里,贾谊晁错的眼光,实在高过李斯。所以,在两汉四百年中朝廷上尽管宗室打外戚,外戚杀宗室,宦官又打外戚,外戚又杀宦官,而农村的基础和文化的根基却日见稳定。读书人以居乡教授作处士为荣,东汉的气节,在士的历史上造成了空前的好榜样。这样,刘家一姓的私事,才不至于动摇整个的社会下层。
董卓的入卫,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军阀专政之局,曹氏、司马氏,以及宋齐梁陈,刻板地在定型下互相抄袭,造成了几百年奸雄的历史。处士一变而为党锢,再变而为文学侍从,三变而为世族的门客。读书人的生活,从居乡教授到运筹决策,再到作劝进表,加九锡文,最后到应诏咏妓,南朝士人的身份降到无可再降。而隋唐之际一些来自田间的笃实之士,却在北朝异族的统治下培养出来,实在是一件很可伤心的事。
隋唐的科举,虽然造成了乞怜奔竞之风,但究竟在“白屋”中,拔出些“公卿”,读书人犹得以气类相尚。北宋的宰相,大半是寒士出身,眼光渐渐由都市转到乡村,使得久居被动的农村,又有独立自存的趋向。两宋理学家于讲学之余,大都注意到农村的组织和建设,如《朱子家礼》《吕氏乡约》,都是意义深长,有其远大的看法的。只可惜明清两代的八股科举,与腐败的胥吏政治相为因缘,造成了所谓土豪劣绅的一阶级,出则黩货弄权,处则鱼肉乡里,士大夫的意义,早已不复有人顾及了。
近三十年来,读书人的现象大家都知道,不必再说;现在只须问一句话:我们现在究竟是应该继东汉、两宋之风而有所振拔呢?还是任着青年走战国、南朝和明清士人的旧路?
迷途未远,近年来事实上的要求逼得朝野都有些觉悟,复兴农村和知识分子下乡,已由理论渐进于实行,这正是我们垂绝的民族文化一线光明的展望。
(三)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士的风节
古曰士大夫,今曰知识分子,名实相类,而知识分子一名,实不足以尽士大夫之全。因为士大夫之所以为士大夫,在其全部的志事与人格,而知识分子仿佛只靠了有些知识可以贩卖。所以我们还是说士大夫,简称曰士,说士君子也好。
士是不事生产的,所谓“无事而食”。所以王子垫要问孟子“士何事”,而孟子回答的却是“尚志”。再问“何谓尚志”,孟子的回答只是“仁义而已矣”,“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原来士之所以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负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为,所以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然必其先有自发之志,然后能有所奔赴,所以尚志是第一件事。能尚志必能好学,哪一段有所奔赴不容自己之情,便会使他“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谋食、怀居的私欲减轻,那一副虚明刚大的胸怀便会喻于义,然后可以“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然后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到了欲罢不能的时候,“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是很自然的结果。但看“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洒落与坚刚!
士便是以这样的一种精神毅力成己成物,立己立人。有了这样的风节,无论从政讲学,都会有一贯的内容和面目。有了这样的风节,自然对自己和社会有他的深到的看法与合理的安排。
中国民族便是在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陶冶中出生入死支持它的生命到如今。为了负荷人的自觉的使命,受尽了异族的蹂躏,而终究不沦于绝灭者,就在人类的向上心毕竟不会完全失掉;到了途穷思返的时候,中国文化正在以人类的正常态度和平而宽厚地等待他们。
这便是中国民族的自信力,而这自信力的培成,却全靠士以他的整个的人格来负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