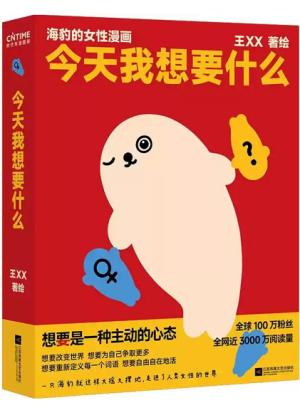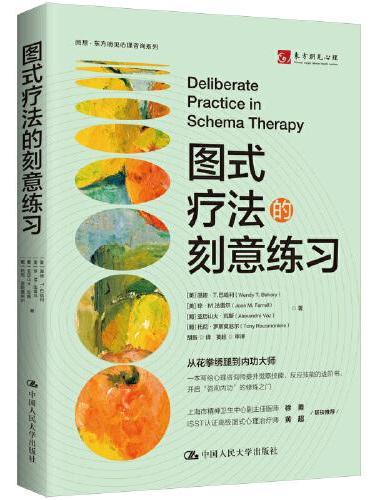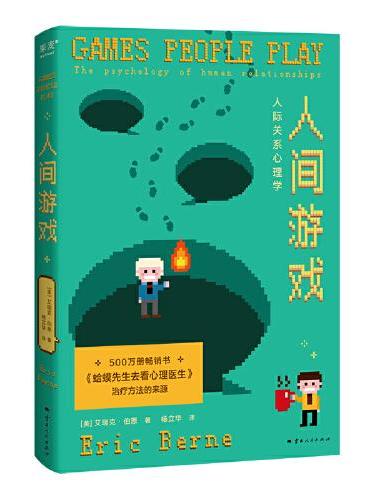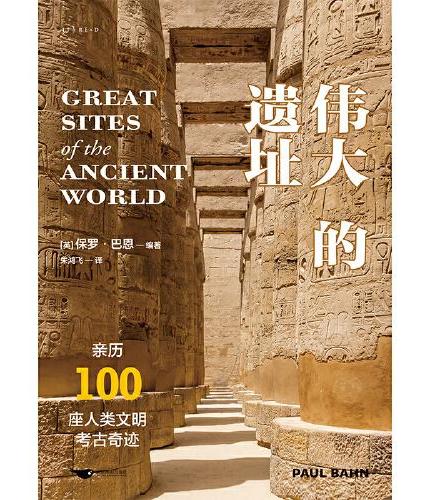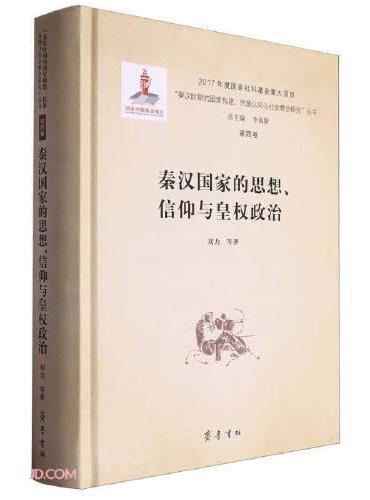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埃勒里·奎因悲剧四部曲
》
售價:NT$
14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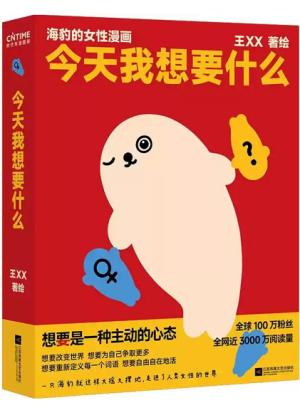
《
今天我想要什么:海豹的女性漫画
》
售價:NT$
347.0

《
日常的金字塔:写诗入门十一阶
》
售價:NT$
347.0

《
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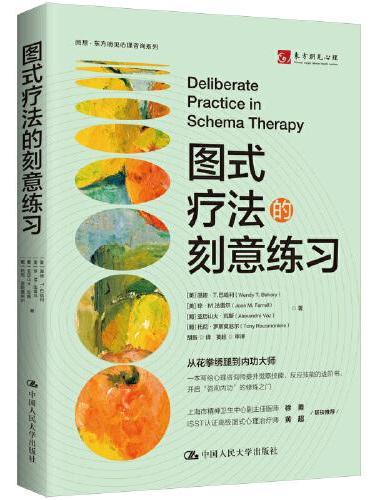
《
图式疗法的刻意练习
》
售價:NT$
4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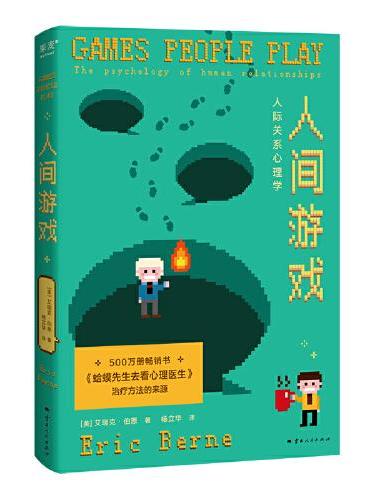
《
人间游戏:人际关系心理学(500万册畅销书《蛤蟆先生》理论原典,帮你读懂人际关系中那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
售價:NT$
2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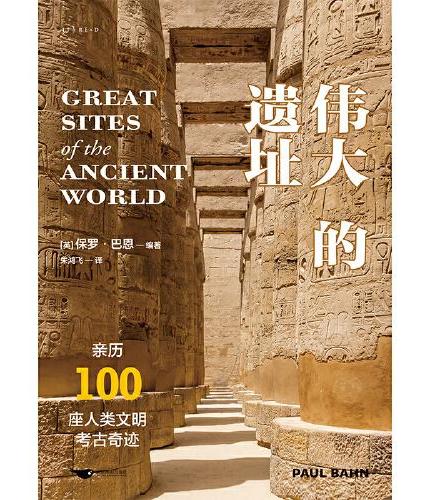
《
伟大的遗址(亲历100座人类文明考古奇迹)
》
售價:NT$
95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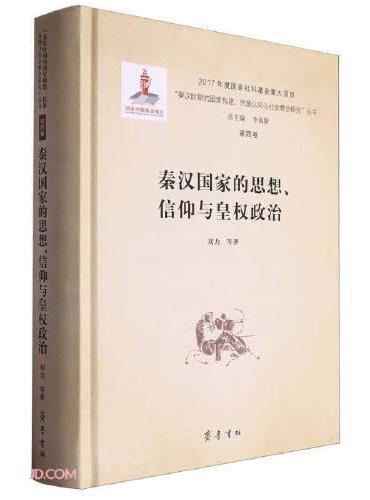
《
秦汉国家的思想、信仰与皇权政治
》
售價:NT$
1000.0
|
| 編輯推薦: |
|
葛剑雄跨越三十余思想随笔精粹,纵论历史,激评现实,“我们还没有值得陶醉的胜利,毫无盲目乐观的理由,只有深刻反思的责任!”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为著名学者葛剑雄先生迄今最为精彩的思想随笔集。作者年近七十,直面问题,以省思和追问警醒国人;全书以编年的形式,精选三十余年间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或学术前沿,或畅谈文化,或分析历史迷局,或探讨社会热点,无论何种文字,都带着强烈的思辨精神与深厚的人文关怀,从酣畅犀利中显出精神风范和学者情怀。
|
| 關於作者: |
|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出生于湖州。1965年当中学教师,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师从谭其骧教授,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1年留复旦大学工作,历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任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环境史等方面研究,著有《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史》(主编,第1卷作者)、《中国移民史》(主编,第1、2卷作者)、《中国历代疆域变迁》、《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历史学是什么》、《葛剑雄文集》(1-7卷)等。
|
| 目錄:
|
自序七十而思
1978年
我的1978年
1980年
清朝全国地图的测绘
1981年
西汉人口考
1982年
略论我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1983年
汉武帝徙民会稽说正误──兼论秦汉会稽丹阳地区的人口分布
1984年
西汉时期西北地区的人口迁移
1985年
我国部分省界形成的历史──政治因素举例
1986年
关于我国古代人口调查的几个问题
1987年
耕耘历史地理园地五十年的结晶──读谭其骧《长水集》
1988年
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
1989年
论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政治机制
“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同义词
1990年
中国移民史发凡
1991年
中国人口发展史·余论
1992年
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
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1993年
宋代人口新证
1994年
中国人口:21世纪的忧思和希望
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
1995年
我们应有的反思
1996年
纳税人的义务和权利:社会公正的基础
开放观念与世界新文明
1997年
永恒的追求:真实的历史
1998年
邂逅霍金
寻访李约瑟
1999年
在历史与社会中认识家谱
2000年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2001年
我亲历的南极
2002年
玄武门之变真相推测
2003年
有财未必富,开源胜节流
为何“太空见长城”的谬说会长期重复
2004年
人与自然:不仅是敬畏
从历史地理看西北城市化之路
2005年
河流伦理与人类文明的延续
得天下与治天下
2006年
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变——“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研制及其意义
惟有人文足千秋
2007年
利用、改造、普及代替不了保护
从历史地理看长时段环境变迁
2008年
中国古代为什么有重视历史的传统
建议以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
2009年
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厕所:杂忆和现实
2010年
移民与都市文化
礼失求诸野
2011年
从中国历史地理认识郑和航海的意义
三峡大坝,责任谁负
2012年
地图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
方言的“传”和“承”
2013年
中国的传统生存智慧与生态观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序
2014年
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
怀念侯仁之先生
|
| 內容試閱:
|
自序 七十而思
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策划了一套“三十年集”系列,邀我参与。“三十年”,是指1977年恢复高考与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至此已30年,因此他想在这两年或稍后考上大学或研究生的人中物色一些人各编一本集子。集子的体例是每年选一二篇文章,学术论文与其他文章均可,再写一段简要的纪事,逐年编排成书。我按体例编成一书,取名《后而立集》。“三十而立”,可惜我到33岁刚考取研究生,学术生涯开始得更晚,能够编入此书的任何文字都产生在“而立”之后。
到了今年,梁由之兄得知12月将是我七十初度,极力怂恿我续编至今年,重新出版。他又主动接洽,获贺圣遂先生慨允使用《后而立集》的内容。于是我仍按原体例,续编了2008年至2014年部分,同样每年选了两篇文章,写了一段纪事。新出版的书自然不宜沿用旧名,由之兄建议以其中一篇《我们应有的反思》的篇名作为书名。开始我觉得题目稍长,在重读旧作后就深佩由之兄的法眼,欣然同意。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每到逢十生日,总免不了用孔子的话对照。但圣人的标准如此之高,每次对照徒增汗颜,因为自知差距越来越大。年近七十,不仅做不到不逾矩,而且离随心而欲的境界远甚。这些旧作基本都是我四十岁后写的,却还谈不上不惑,相反惑还很多。但毕竟有幸躬逢改革开放,特别是当初倡导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否则我不可能在1988年写出《统一分裂和中国历史》这样的论文,并且能入选“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并获奖。这些文章在学术上未必有多少贡献,差堪自慰的是我始终在反思,所以尽管时过境迁,对今天及以后的读者还有些意义。
就以《我们应有的反思》为例,那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在1995年写成的。由于此文的重点是反思,有些观点和说法与主流有差异,发表过程还颇有周折。有幸发表后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包括日本的舆论在内,后来一位日本学者还专门到复旦大学找我讨论,一位旅日学者发表赞同我观点的文章后还引发激烈争论。19年后,面对中日关系的复杂形势,我认为我的反思不是过头了,而是还不够,但基本是正确的。去年和今年我两次向政府建议应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是当年反思的继续。但当年的反思也有两点失误:一是没有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如此迅速,以至不到20年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我对中国的评价与预测都偏低;一是当时尚未了解历史真相,还沿用了蒋介石、国民党不抗日的陈说,涉及历史的一些说法在今天看来多有不妥。还有一点,当时不知道中日建交后日本究竟给了中国多少援助,政府赠款和多少,日元代款有多少,直到200年中日建交三十周年时政府才公布总数达1900多亿人民币,并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谢。我支持我国政府的立场,这笔援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确起了很大作用,该感谢的还是应该感谢,不能与战争赔偿混为一谈。
在其他方面,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我在研究生期间开始研究历史人口地理、人口史,以后发表了《中国人口发展史》,合著了《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参与撰写《中国人口总论》也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参加过多次专题讨论会。由于这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所以在1995年我提出,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应及时作出调整,从独生子女改为“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但今天看来还不够,从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从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的变化看,还应进一步调整到“确保一胎,鼓励二胎,允许三胎”。除了政策调整外,还应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那就赋予孝道新的内容,教育青年将生儿育女当作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和国家的应尽的责任,当作真正的孝道。
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一直鼓励我们要超越前人,包括要超越他。他自己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在他留下的最后一篇未完成的论文中,他还极其坦率地承认他的成名作《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中对移民数量估计的失误。在他的鼓励下,我也质疑他的某些观点。例如,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他形成的观点是“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而我近年来的看法是,如果说1840年前的中国疆域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此后到今天的中国疆域也是“自然形成”的。(详见本书《地图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
我当然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但只有不断反思方有可能。只要不断反思,即使永远达不到这一境界,也能逐渐接近,所以在年近七十时,我想到的是“七十而思”。这并不是说以前没有思过,而是思得不够,要永远思下去。
我的1978年
1977年,当高校重新招生的消息传出后,我的上大学愿望死灰复燃。但看到具体规定后,我发现对考生年龄的规定是30周岁,而当时我已满31足岁。抱着一线希望,我又去招生处询问,得知对“30周岁”的解释是“不满31足岁”,我已失去报名资格,看来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
我是1964年从上海市北中学高中毕业的,但在此以前,我的大学梦已经破灭。那是在1962年的5月,我正读高二,在学校一次体检透视中,我被发现患开放性肺结核。经过拍片复查,确诊无误,医院通知我立即病休,三个月后复查。拿着这张诊断书,我不知是如何从福建北路闸北区结核病防治所回到家中的,也不知是如何回答母亲的询问的,直到晚上睡在床上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事实。进高中不久我就已瞄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也是语文、历史、英语等教师心目中最有希望的学生,一直享受着他们的格外关照——可以到教师阅览室看书,能通过教师借书,上历史课时不必听讲而可看我自己的书。尽管在政治学习或讨论时我也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准备考大学,但也准备考不上大学时服从分配,到新疆或农村去),实际却只有一种准备。要是不能在三个月内治愈,或者影响报考大学,这一切都完了。于是我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疗和休养上,按时服药,严格按时间表作息,每天早上去公园学太极拳。当时主副食品都是计划供应,居民每十天配售二两肉,但凭肺结核病的证明可到菜场办一张“照顾卡”,凭卡增购肉和鸡蛋若干,还可订一瓶牛奶。我尽量增加营养,以便及早康复。但是每三个月一次的复查都是一次新的打击——我一直无法进入钙化期,因此不能复学。直到1963年11月,同班同学早已毕业,绝大多数考入大学,我才在休学一年半后获准复学,转入下一届高三“试读”。可是到第二年5月高考报名体检时,我的肺结核还没有完全钙化,不符合报考条件。
在老师的劝说下,我暂时放弃了继续报考大学的打算,因为医生说像我这样的病情,很难保证下一年就能通过体检,而且作为一名新团员,服从组织分配是起码的要求,我接受了参加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的安排,留在母校市北中学实习,1965年8月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打算,心想即使工作十年,我还符合报考大学的年龄,总能找到机会。所以当年就报名
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二年级,进修英语。但“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一心上大学是不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祟,所以不仅自己公开暴露思想,还一次次进行自我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些都成了大字报中揭发批判的内容。“文革”期间,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最新指示发表,曾经给我带来一线希望,但马上破灭,因为毛主席特别指出“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而且随后开始的招生,都是由各单位推荐“工农兵学员”,在职教师显然没有资格。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对1977年的意外遭遇相当平静。而且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我对“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心有余悸,所以尽管报名处的工作人员曾建议我凭“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和新当选的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争取在年龄上破格,我也不敢一试。
到1978年公开招收研究生时,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而且为了“不拘一格”,对学历没有任何规定。我再也无法抵制大学的诱惑,但一点儿没有把握,所以在单位开证明时还要求领导给我保密,再三说明只是想检验一下自学的结果,以免这种异想天开在学校引起不良影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