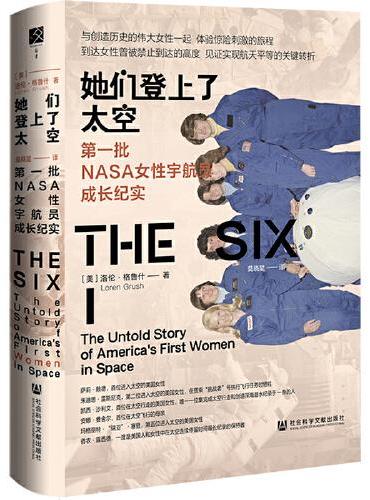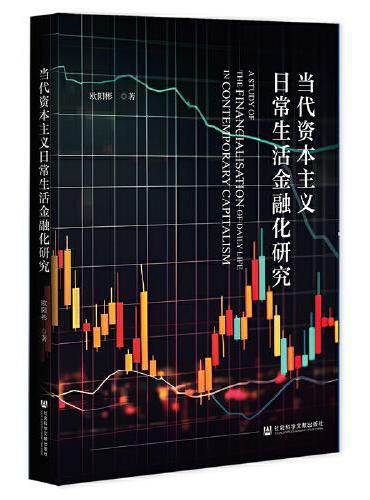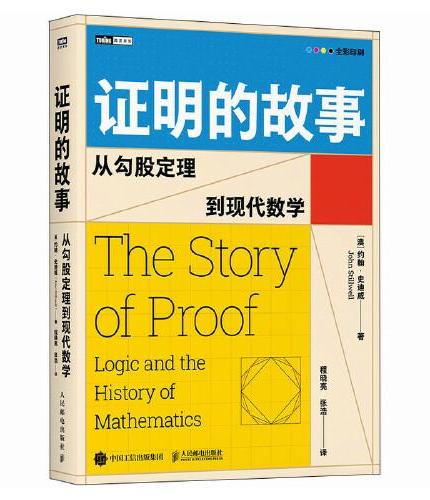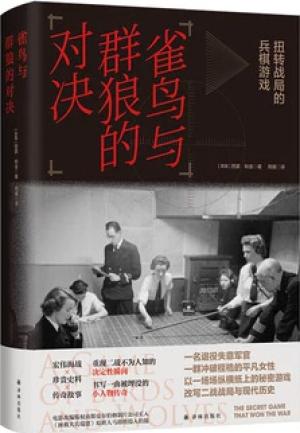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论衡系列)
》
售價:NT$
551.0

《
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革命不是新制度推翻旧制度,而是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殊死斗争!屡获大奖,了解光荣革命可以只看这一本)
》
售價:NT$
1010.0

《
东方小熊日本幼儿园思维训练 听力专注力(4册)
》
售價:NT$
408.0

《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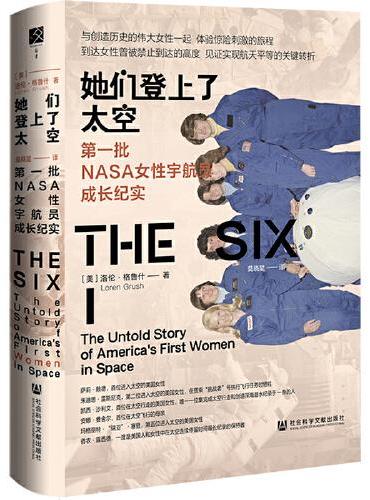
《
她们登上了太空:第一批NASA女性宇航员成长纪实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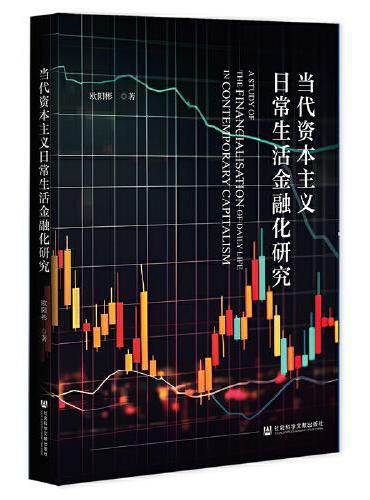
《
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金融化研究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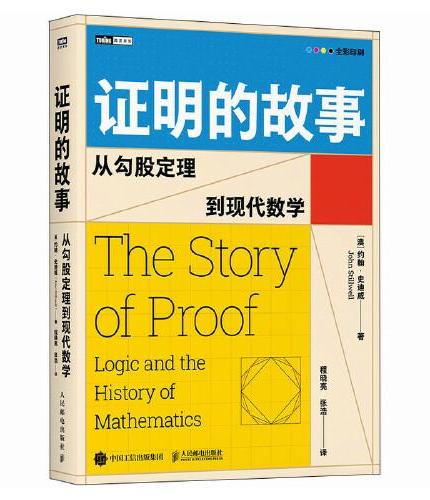
《
证明的故事:从勾股定理到现代数学
》
售價:NT$
6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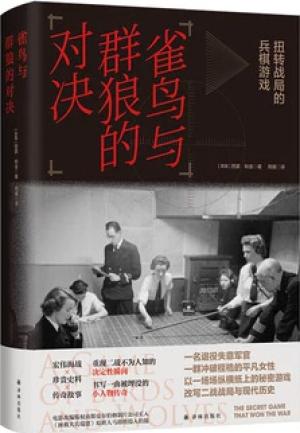
《
雀鸟与群狼的对决:扭转战局的兵棋游戏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作家太宰治代表作品;
村上春树御用译者林少华全新译本,首次使用“人的失格”中文译名,17个版本中最权威的译本;
收录日本战后文学的金字塔之巅作品《斜阳》《人的失格》;
思考青春与迷茫的经典之作;
旅日作家李长声将之列入日本文学十一本必读书目!
|
| 內容簡介: |
《斜阳》
没落的贵族,夕阳般的生活。旧道德的毁灭,是否有新道德的产生?和子和母亲放弃东京西片町的家,搬来伊豆这座略带中国风格的山庄,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年的十二月初。然而生活并不安静,母亲病倒了。这个贵族之家,已经开始没落。
集太宰文学之大成的《斜阳》,描述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成员的心理转折,交织成对人生希望与失望的透视,激荡出孤独的新生,被誉为“日本的《樱桃园》”。曾创下战后文学作品畅销的记录,“斜阳族”一词作为没落贵族的代名词而广为人知。
《人的失格》
人的失格,即丧失为人的资格,刻画主角叶藏从青少年到中年,饱尝世态炎凉,沉缅于酒色,最后毁灭了自己。太宰治临终前写成的《人的失格》,可以说是他整个一生的自画像,从中可以看到他从多愁善感的少年一步步丧失为人资格的过程,被誉为日本文坛“不朽的杰作”,是太宰文学的“总决算”。
|
| 關於作者: |
太宰治(1909-1948)
三十九年生命,二十年创作,五次殉情自杀,最终情死,日本无赖派大师,毁灭美学一代宗师。日本战后新戏作派代表作家,生于清森县北津轻郡金木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本名津岛修治。父亲曾为贵族者员,并在本乡兼营银行。为防农民暴动,家筑高墙,太宰治住在这样的深宅大院里有种内疚和不安感,甚至出现了一种罪恶感,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
太宰治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是1932至1937年,这是左翼运动被镇压的时代。著有短篇小说集《晚年》(1933~1936),共收入40篇,这些短篇都充满了青春时期的热情,多角度地反映了作家自己的主张和内心世界。此后又发表《虚构的傍徨》(1936)、《二十世纪的旗手》(1937)等作品。
中期是1938至1945年。著有《女学生》(1939),获第四届北村透谷文学奖。此外尚有《童话集》(1945),发挥了作家奔放的想象力。后期是1946至1948年,一般认为,太宰治的后期创作最有成就,战争刚结束,他就发表了《潘朵拉的匣子》和《苦恼的年鉴》等小说,提出了追求“丧失了一切,抛弃了一切的人的安宁”的观点,以农本主义的幻想批判战后虚伪的文人骚客。在他战后的作品中,短篇《维荣的妻子》(1947),中篇《斜阳》(1947)、《人的失格》(1948),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代表作品。这些小说发表后,无不引起巨大的反响。《维荣的妻子》写一个出身贵族、生活堕落的诗人及其妻子自甘堕落以示对社会道德的反抗。《斜阳》反映了战后贵族后裔的社会地位日益衰落,荣华显耀的时代已付诸东流的主题。《人的失格》是太宰文学最杰出的作品,取材于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一个性情乖僻的青年知识分子,饱尝世态的炎凉,绝望之余沉缅于酒色,最后自己毁灭了自己。从一定角度揭示了现代日本社会人的异化问题。
1948年6月13日太宰治因对人生感到绝望而投水自杀。他的一生经历了日本革命运动被镇压到日本战败这一大动荡的时代,日本评论家平野谦说:“太宰的死,可说是这种历史的伤痕所造成的。”
|
| 目錄:
|
太宰治:“无赖”中的真诚林少华
斜阳
人的失格
|
| 內容試閱:
|
斜 阳
一
清晨。母亲在饭厅里轻轻啜了一勺汤,发出轻微的叫声:
“啊!”
“头发?”
我以为汤里进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不是的。”
母亲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再次轻快地把一勺汤送入口中。随即一本正经地转过脸,把视线投向厨房窗外盛开的樱花。就那样侧着脸,又一次轻快地让一勺汤滑进娇小的嘴唇之间。轻快这一形容,用在母亲身上绝不夸张,那同妇女杂志上介绍的用餐方式之类截然有别。一次,弟弟直治一边喝酒一边对作为姐姐的我这样说过:
“不能说有爵位就是贵族。就算没有爵位,拥有天爵那样像样的贵族也是有的。还有像我们这样的——爵位倒是有,却和贱民差不了多少,根本算不得贵族。至于岩岛(直治举出一个伯爵同学的姓氏)那种家伙,简直比新宿烟花柳巷的皮条客还要分文不值!近来参加柳井(他举出一位子爵次子的姓名,也是弟弟的同学)的兄长的婚礼,那个混账居然穿了一件什么无尾晚礼服,何苦穿哪家子无尾晚礼服呢!那也罢了,起身致谢辞时还满口之乎者也,真是匪夷所思,令人作呕。阴阳怪气,虚张声势,和优雅风马牛不相及!本乡一带常有‘高等学生公寓’招牌,而实际上大部分华族都和高等乞丐彼此彼此。真正的贵族根本不像岩岛那么装腔作势!我们这一族嘛,正宗的贵族也只母亲一位了,是吧?那才叫正宗,比不得的!”
拿喝汤的方式来说,我们都是稍微伏在盘子上,横拿汤匙舀起,就那么横着送到嘴边。可是母亲把左手指轻轻放在桌子边缘,也不弯上半身,头好端端扬着,看也不好好看盘子就横拿汤匙迅速一舀,随即同口部成直角举起——轻盈潇洒得简直想用飞燕来形容——让汤从汤匙尖端流入唇间。漫不经心左顾右盼之间,就像鸟翼一般轻快无比地处理汤匙。喝得一滴不漏。而且全然没有喝的声音和汤匙的声音。那或许不符合所谓正规礼仪,但在我眼里显得十分可爱,觉得那才正宗。事实上,那种使汤汁流入口中的喝法也好喝得不可思议。不过,我因为是直治所说的高等乞丐,没办法像母亲那样轻松自如地使用汤匙。出于无奈,只好把头伏在盘子上,按照所谓正规礼仪闷头喝个不止。
不止喝汤,母亲所有餐饮方式都同礼仪有相当大的距离。肉一上来,她就刀叉齐举,两下三下就全都切成小块。而后扔开刀,右手拿叉,一小块一小块叉起,慢悠悠乐滋滋放入口中。还有,吃带骨鸡肉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在不让盘子出动静的情况下让肉骨分离。而母亲满不在乎地一下子用指尖抓起见骨头的地方,不以为然地用嘴把骨头和肉撕开。动作那般野蛮,而由母亲做来,可爱且不说,甚至显得罗曼蒂克——真正的贵族就是不同!不光吃带骨鸡肉,即使午饭吃香肠火腿什么的,有时也用指尖轻轻抓起。
“紫菜饭团为什么好吃,可知道?那是因为,是用人的手指攥出来的呀!”母亲还这样说过。
的确,有时我也心想大概手抓好吃,却又担心像我这样的高等乞丐,若是弄巧成拙,那可彻头彻尾成了乞丐了,只好忍着。
就连弟弟直治也说比不上妈妈。我也深切觉得模仿母亲很困难,困难得近乎绝望。一次在西片町我家的后院——那是个月光皎洁的初秋夜晚——我和母亲两人在池边凉亭赏月,笑着说狐狸新娘和老鼠新娘的嫁妆有什么不同。这时间里,母亲忽然站起,走进凉亭旁边胡枝子深处,继而从胡枝子白花丛中探出更加白得鲜明的脸庞,微微笑道:
“和子,妈妈刚才做什么去了,猜猜看!”
“折花去了。”
听我一说,母亲低声笑了起来:
“撒尿!”
我吃了一惊:根本就没蹲下嘛!可那有一种我这样的人横竖模仿不来的由衷可爱之感。
倒是跟今天早上喝汤的事离得远了:最近我看一本书,得知路易王朝时期的贵妇人们在宫中庭院和走廊角落等地方随意小便。那种率性实在好玩得很。我想我的母亲怕是那种真正贵妇人的最后一位了。
言归正传。由于今早啜一口汤低低发出一声“啊”,我就问“头发?”。母亲回答不是。
“怕是咸了。”
今早的汤,是把近来用美国配给的豌豆罐头里的豌豆过滤出来做的浓汤。我原本就对做饭没信心,即使母亲回答“不是”,我也还是提心吊胆。
“做得不错!”
母亲认真地这么说罢,喝完汤,手抓紫菜包的饭团吃了起来。
从小我就不觉得早餐好吃,不到十点肚子不饿。所以当时汤倒是好歹喝完,但懒得吃饭。饭团放在盘子里,把筷子戳上去,戳得乱七八糟。然后挟起一小块,仿照母亲喝汤时的汤匙,让筷子同嘴巴呈直角,活像小鸟啄食一样捅入口中。如此磨磨蹭蹭时间里,母亲已经全部吃完,悄然起身,背靠晨光辉映的墙壁,默默看我吃饭。看了一会儿,说道:
“和子,那不行啊,早餐要吃得有滋有味才成!”
“您呢?有滋有味?”
“那还用说,我又不是病人!”
“和子我也不是病人嘛!”
“不成,不成。”母亲凄然笑着摇头。
五年前,我因为肺病躺倒,那病是一种老爷病。而母亲最近的病,那才是真正让人担忧的可怜的病。可母亲总是为我操心。
“啊。”我应道。
“什么?”这回轮到母亲发问了。
两人对视,觉得有什么完全心照不宣。我呵呵一笑,母亲也好看地一笑。
每当有不堪忍受的耻辱感袭来,我总是幽幽发出这奇妙的叫声。六年前离婚时的事此刻蓦然浮上眼前,历历如昨。这让我心里难受,不由得“啊”了一声。而母亲不至于有我这样耻辱的过去。不,或者也有什么不成?
“母亲刚才也肯定想起什么了吧?想起的是什么?”
“忘了。”
“关于我的?”
“不。”
“直治的事?”
“嗯。”旋即歪起头,“或许。”
弟弟直治读大学期间被征召入伍,去了南洋岛上,从此音讯全无,直到战争结束也下落不明。母亲虽然口说已经死心了再也不想直治了。但我一次也没有死什么心,一门心思认为肯定能见到。
“本以为已经死心了,但喝好喝的汤的时候,总是想起直治,心里受不了。对他再好一些就好了!”
从上高中时开始,直治就格外迷上了文学,开始过差不多像是不良少年的生活,不知给母亲添了多少麻烦。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每喝一口汤就“啊”的一声想起直治。我往嘴里扒着饭,眼角一阵发热。
“不要紧的,直治不要紧。直治那样的坏小子,绝不会死的。死的人全都是乖顺、漂亮、温柔的。直治么,棍子打都打不死的。”
母亲笑着拿我开心:
“那么说,你倒可能是早死那伙的。”
“哎哟,为什么?我这样的大脑门坏蛋,活到八十岁都没问题!”
“是吗?那么,母亲我保准活到九十岁喽!”
“那是。”
说罢,我有些费解。坏蛋长寿,长得漂亮的早死。母亲很漂亮,但我希望母亲长寿。这点让我相当困惑。
“捉弄人啊!”
说罢,下唇不住地颤抖,泪水从眼睛里涌了出来。
是不是该讲一下蛇?四五天前的下午,附近孩子们在院墙竹丛中发现十来个蛇蛋。
“蝮蛇蛋!”孩子们一口咬定。
想到如果竹丛中生出十条蛇来,自己就很难随便下到院子了,就说:
“烧掉吧!”
孩子们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跟在我后面。
在竹丛旁边堆起树叶和木柴点燃,把蛇蛋一个个投入火中。蛋怎么烧也烧不着。孩子又把树叶和小树枝扔在火上,加大火势。但蛇蛋还是烧不着。
坡下一个农家女孩从墙外笑着问:
“干什么呢?”
“烧蛇蛋。孵出蛇来,太吓人啦!”
“大小有多大?”
“鹌鹑蛋那么大,雪白雪白的。”
“那是普通蛇蛋,不是蝮蛇蛋吧。生蛋是怎么都烧不着的。”
女孩似乎十分好笑地笑着离开了。
烧火烧了三十多分钟,但蛇蛋横竖不起火。于是孩子们从火中拾起蛇蛋埋在梅树下,我归拢小石子做了墓标。
“过来,大家拜一拜!”
我蹲下合拢双手。孩子们乖乖蹲在我身后,做出合掌的样子。和孩子们分开后,我一个人慢慢爬上石阶。石阶上面的紫藤架下站着母亲。
“你这人,做了一件狠心事啊!”母亲说。
“以为是蝮蛇,原来是普通蛇。不过,已经好好埋了,不要紧。”
话是这么说,可心里还是觉得被母亲看见不好。
母亲绝不是迷信的人,但自十年前父亲在西片町家中去世以后,就怕蛇怕得不得了。父亲临终时,母亲看见父亲枕边落有一条黑色的细绳,漫不经心地正要拾起,竟是蛇。蛇吐噜噜跑了,跑去走廊,再往下就不知去了哪里。看见的只有母亲和和田舅舅两人,两人对视一下。为了不惊动客厅里给父亲送终的人,都忍着没有作声。所以,尽管我们也在场,但蛇的事一无所知。
不过,父亲去世那天傍晚,院子池边所有树上都爬上了蛇的场景,我也实际目睹了。我已是二十九岁的半老太婆了,十年前父亲去世时我也已十九岁,早已不是孩子了。所以,即使十年过去,当时的记忆现在也一清二楚,不可能错。我去院子池边剪花上供,在池边杜鹃花那里停住脚步,蓦然看去,杜鹃树枝头缠着一条小蛇。我有些吃惊。接下去,正要折棣棠花枝时发现那条枝上也缠着蛇。旁边的桂花树、小枫树、金雀花树、紫藤萝、樱花树,不管哪里的树上、每一棵树上都有蛇缠着。可我没感到多么害怕。只觉得蛇也大概和我同样,为父亲的去世而伤心,爬出洞来参拜父亲之灵。我把院子蛇的事悄悄告诉母亲。母亲也很镇定,略微歪起脖子,似乎在思索什么,但什么也没说。
不过,两起蛇事件自那以来使得母亲极度讨厌蛇则是事实。或者说较之讨厌蛇,好像更对蛇怀有尊崇、惧怕即敬畏之情。
烧蛇蛋的事被母亲发现了,母亲肯定感到一种极不吉利的东西。想到这点,我也陡然觉得烧蛇蛋是非常可怕的事。说不定这将给母亲带来不好的报应。我为此担忧得不行,日复一日耿耿于怀。而今早却又在饭厅里顺口说出长相漂亮的人早死这种不着边际的胡话。说罢怎么也无法圆场,以致哭了出来。收拾早餐碗筷时间里,自己胸口总好像爬进一条缩短母亲寿命的可怕的小蛇,厌恶得不得了。
这么着,那天我在院子里看见了蛇。那天风和日丽,我忙完厨房里的活计,把藤椅搬到院里的草坪,想在那里用毛线织东西。刚搬藤椅下到院子,就看见院石细竹丛那里有蛇。啊,讨厌!但这只是一闪之念,再没多想,搬着藤椅折回上到檐廊。把藤椅放在檐廊里,坐在上面织东西。到了下午,想从位于院子一角的佛堂深处藏书中取出洛朗桑画集。刚下到院子,就看见一条蛇在草坪上慢慢爬行。和早上的蛇一样,细细长长,模样优雅。我猜想是母蛇。它静静爬过草坪,爬到蔷薇背阴处的时候,停住扬起脖子,晃动火焰般的细舌,一副东张西望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垂下脖子,无精打采地盘在一起。那时我也只是把它看作一条美丽的蛇,而少顷去佛堂取出画集回来往刚才有蛇的地方悄然一看,蛇已不见了。
傍晚,我和母亲在中式房间一边喝茶一边目视院子。只见石阶第三阶那里,早上那条蛇又慢慢闪了出来。
母亲见了,说道:
“那条蛇是……”
说罢朝我这边跑来,抓着我的手呆立不动。母亲那么一说,我也心中一惊,一句话脱口而出:
“蛇蛋的母亲?”
“是、是的!”母亲的语声沙哑起来。
我们手拉着手,屏息敛气,默默注视那条蛇。在石头上懒洋洋盘成一团的蛇,东摇西晃似的蠕动起来。随即有气无力地穿过石阶,往燕子花那边爬去。
“一大早就在院子爬来爬去来着。”我小声告诉母亲。
母亲叹了口气,瘫痪似的坐在椅子上。
“是吧?是在找它生的蛋呢,怪可怜的。”母亲以忧郁的声音说。
我无奈地呵呵笑了。
夕晖照在母亲脸上,母亲的眼睛看上去闪着蓝光。那约略含怒的脸庞,美得让人恨不得扑上去。啊,我觉得母亲的面容,和刚才那条美丽的蛇有相似之处。不知、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自己的胸间盘踞的蝮蛇般丑陋的蛇,有可能迟早把甚为伤心的那般美丽的母蛇一口咬死。
我把手搭在母亲柔软纤弱的肩上,浑身无端地挣扎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