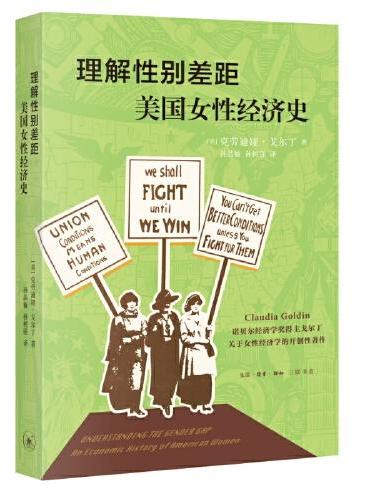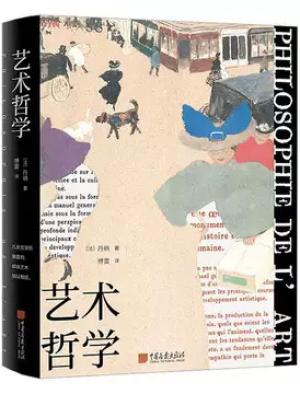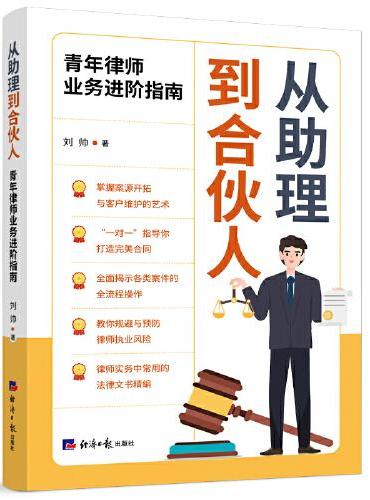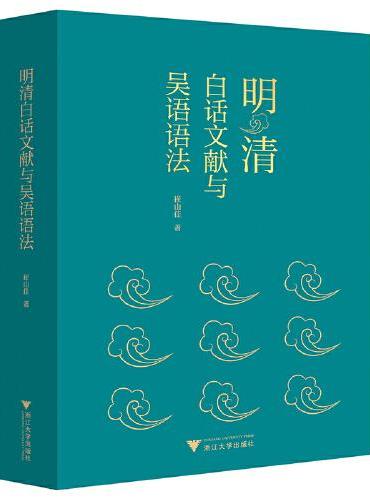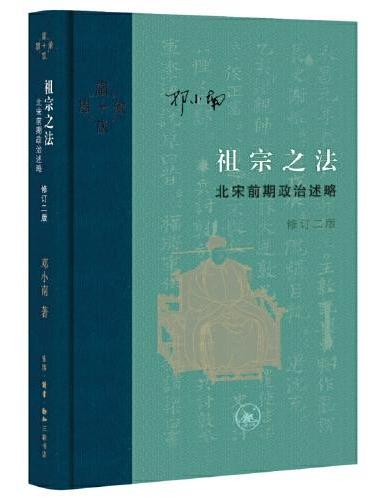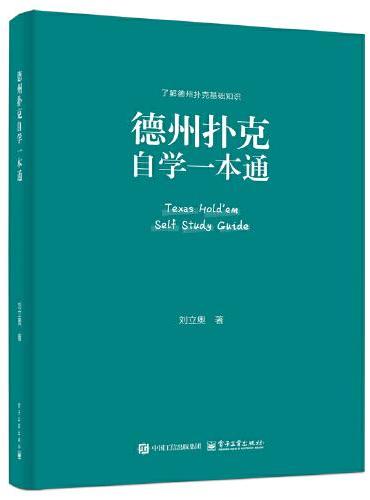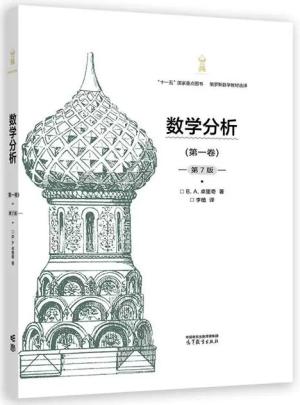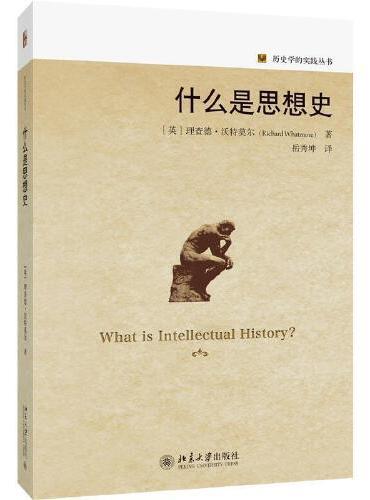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
》 售價:NT$
418.0
《
艺术哲学
》 售價:NT$
449.0
《
从助理到合伙人-青年律师业务进阶指南
》 售價:NT$
347.0
《
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
》 售價:NT$
1010.0
《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二版)
》 售價:NT$
500.0
《
德州扑克自学一本通
》 售價:NT$
255.0
《
数学分析(第一卷)(第7版)(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454.0
《
什么是思想史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 售價:NT$
286.0
編輯推薦:
素有“英国文坛教父”的马丁艾米斯的作品在我国属于首次出版,该作系列共有10部,几乎网罗了艾米斯的各大经典之作。译文出版社已经推出这10部作品中的四部,分别为《时间箭——罪行的本质》《夜车》以及《金钱——绝命书》《伦敦场地》,出生于文学世家的艾米斯在国外,尤其在英国拥有很高的传阅度和众多粉丝,常与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被并称为英国“文坛三巨头”。艾米斯在英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全球众多文学评论家的研究首选对象,也是国外很多热门文学大奖——布克奖,普利策文学奖等著名奖项的常客,更被视为有望拿下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匹黑马。在《莱昂内尔阿斯博——英格兰现状》中,马丁·艾米斯将人性刻画得滴水不露,更将整个人性抛掷在一个风云莫测的大环境中悉心观察并打磨,语言革新尖锐,内容荒蛮怪趣,在缔造一个传奇的同时,艾米斯也在向世人展示着他的预言,本书更是当代英国人真实生活的写照。
內容簡介:
故事发生在伦敦迪斯顿市镇。莱昂内尔·阿斯博是一个臭名昭著、十恶不做的流氓恶棍,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关怀着已是孤儿的外甥德斯蒙德 o 佩珀代因,并对其谆谆告诫:男子汉必须刀不离身,与女朋友约会还不如色情挑逗管用……但一心想过正常生活的德斯蒙德却在无意间与外婆有了私情,这一秘密让德斯蒙德如履薄冰,为了守住这一秘密,德斯蒙德尽量迎合自己的舅舅,即将出狱的莱昂内尔意外中奖一亿四千万英镑,在金钱面前,莱昂内尔的贪得无厌和吝啬不堪显露无疑,金钱让莱昂内尔变得更加残暴无仁,也让这甥舅俩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關於作者:
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英国当代著名作家,1949年生于牛津文学世家,著名小说家金斯利艾米斯之子。马丁艾米斯素有英国“文坛教父”之称,与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1974年,艾米斯凭其处女作《雷切尔文件》摘得毛姆文学奖,并被誉为“文学天才”。此后艾米斯借其一系列风格多变的作品步入文坛巅峰:《金钱——绝命书》(1984)入选《时代》杂志“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列;《时间箭——罪行的本质》(1991)和《黄狗》(2003)先后入围布克奖提名。虽然艾米斯屡次无缘该奖项,但却无损他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年轻作家”(GRANTA杂志)的头号人物。马丁艾米斯在创作上深受卡夫卡、纳博科夫、乔伊斯等大师的影响,在写实的手法上融入了意识流、黑色幽默及浓郁的魔幻主义风格;其先锋实验的文学品格、标新立异的创作形式、变幻莫测的情节铺陈以及惊世骇俗的语言天赋令其享尽世人瞩目,更被形容为是“蘸着迷药水书写的文坛大师”。
內容試閱
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