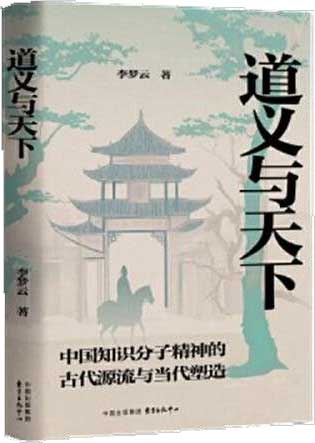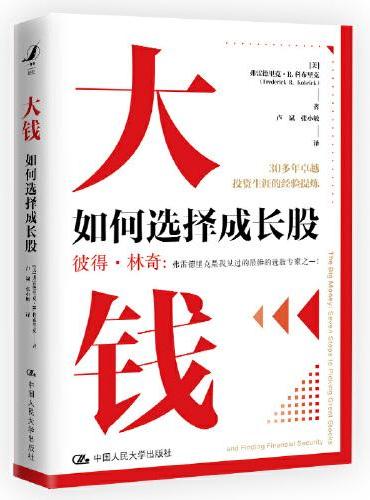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宋代将门百年兴衰史
》
售價:NT$
454.0

《
金钱的力量:财富流动、债务、与经济繁荣
》
售價:NT$
454.0

《
超越想象的ChatGPT教育: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教育 (土耳其)卡罗琳·费尔·库班 穆罕默德·萨欣
》
售價:NT$
352.0

《
应对百年变局Ⅲ:全球治理视野下的新发展格局
》
售價:NT$
398.0

《
前端工程化——体系架构与基础建设(微课视频版)
》
售價:NT$
454.0

《
《诗经》全注全译全本彩图 全书系列50万册焕新升级典藏纪念版
》
售價:NT$
25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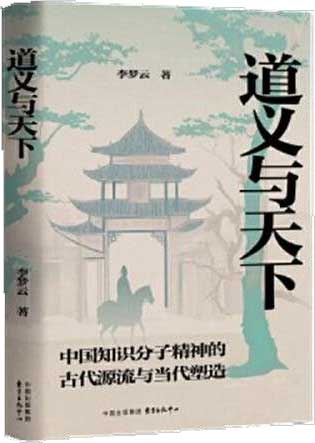
《
道义与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古代源流与当代塑造
》
售價:NT$
4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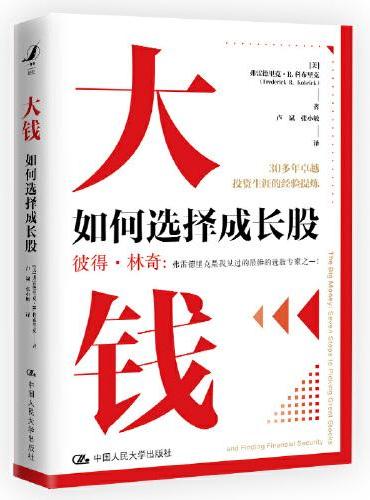
《
大钱:如何选择成长股
》
售價:NT$
505.0
|
| 編輯推薦: |
丛书特点:
【名家推荐】
著名教育家、知心姐姐卢勤,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鼎力推荐!
【著名作者+著名译者】
本丛书荟萃了世界文坛巨星的代表作品,罗曼·罗兰、马克·吐温、安徒生、泰戈尔,等等,都将与您相约《青少年课外必读经典》。而我们选择的译者,既有老一辈翻译家叶君健、鹿金、柳鸣九、陈筱卿、姚锦熔等,又有新一代资深翻译周露、姜希颖、杨海英等。
【全译+原版插图】
为让读者更好地感受经典的原貌,除个别版本外,我们都选择了全译本。许多图书我们还精心选取了国外原版插图,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增加了青少年的阅读兴趣。
【精装典藏】
国内一流设计师根据作品内容精心构图,设计独具匠心,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32开精装装帧,便于阅读,更适于收藏。
本书特点:
1.巴尔扎克的所有小说中最具可读性的一部著作
2.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幅”之一
3.讲述了金钱如何使人性毁灭,造就家庭悲剧的故事
4.使人们在被金钱遮蔽的黑暗世界里,看到一抹光亮
|
| 內容簡介: |
|
《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最出色的画幅之一”,是一幅法国19世纪前半期外省的色彩缤纷的社会风俗画。小说叙述了一个金钱毁灭人性和造成家庭悲剧的故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金钱对人的思想灵魂腐蚀和摧残。小说形象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金钱都充塞着“污秽和鲜血”,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冷酷的“现金交易”,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
|
| 關於作者: |
巴尔扎克(1799—1850)
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创作的《人间喜剧》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共91部小说,描写了2400多个人物,展示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生活画卷。
管筱明
1953年10月出生,原籍江苏常熟。资深法语翻译。主要译作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帕尔玛修道院》《吉尔布拉斯》《忏悔录》《狗与狼》《希望幸福的人》《情人的陵墓》《另类生活》《物类最新消息》《雨果传》《碧眼姑娘》《水晶瓶塞》《回浪湾》《钟敲八响》等。
|
| 目錄:
|
一001
二026
三041
四073
五109
六140
七158
|
| 內容試閱:
|
一
外省某些城市里,有些房子看上去有些凄凉,和见到最荒凉的旷野、最凄惨的废墟、最阴森的修道院时的感觉一样。修道院的静寂、旷野的枯燥和废墟的颓败,也许这些房子兼而有之。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平静,要不是听到陌生的脚步声,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面孔近似僧侣一动不动的人,朝生人射来暗淡冷漠的目光,外地人会以为那些房子没有住人。
苏缪城里有一所房子,外表就有这种凄凉的成分。一条高低不平的小街,这一头,是这所房子,那一头,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这条街,夏天热,冬天冷,好些地方黑森森的,已经不大有人来往,可是小石子铺的路面,走上去啪嗒直响,狭窄而弯曲的街面,总是那么清洁、干燥,街边的房子静幽幽的,坐落在城墙脚下,属于老城的一部分。这些,都使这条街引人注目。
在老城,上了三百年的房子,虽是木头造的,却还很坚固,那各不相同的外表,构成了苏缪城这一部分的独特之处,引起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注意。你从房前经过,很难不欣赏那些厚木板档头雕出的古怪图像。它们铺在大多数房子的底层上面,组成一幅黑黑的浮雕。
这里,有些房间横梁上铺着石板,不牢的墙上绘着蓝色的图案,木头桁架的屋顶,因为年深月久而往下弯沉,椽子经不起日晒雨淋,已经腐烂翘曲。那里,窗棂破旧发黑,精致的雕刻已经模糊不清,似乎承受不起某个穷女工放的种了康乃馨或玫瑰的棕瓦盆。再过去一点,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我们的祖先天赋聪明,刻上一些家族的古怪符号,其意义是永远捉摸不出的了:或许是一个新教徒在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许是一个旧教徒在诅咒亨利四世。有几个市民也刻上家徽,表示他们出于官绅世家,祖上也曾任过地方助理行政长官。这一切里面,就包含了法兰西的全部历史。有的地方,一边是摇摇晃晃的房子,那粗糙的墙壁上,木匠曾经卖弄过使刨子的手艺;一边则耸立着一座乡绅的公馆,半圆形石门拱上的家徽,受了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毁损,还依稀看得出痕迹。
在这条街上,底层的门面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生活的人可以在这里发现老辈们简陋的手工作坊。一间间低矮的房子,又大又深,黑森森的,没有橱窗,没有货架,没有玻璃门窗,里里外外都没有装修。实心大门粗糙地包了铁皮,分作上下两截,上截朝里打开,下截安装了弹簧门铃,不停地开开关关。这种潮湿的窑洞式的房子,就靠门的上部,或者地板屋顶和一堵齐腰高的矮墙之间的空间采光通风。矮墙上安着厚实的窗板,白天取下,晚上装上,再加上铁闩,用螺丝拧紧。货物就摆在矮墙上。那种哄骗顾客的花花玩意儿,在这里是见不到的。至于摆的是什么货,那要看铺子经营什么品种,或是两三桶盐和鳕鱼,或是几捆帆布和缆绳,或是挂在楼椽上的黄铜丝,或是靠墙放着的一溜桶箍,或是货架上放着的几段布。你要进去看看?那好,一个干干净净的漂亮姑娘,戴着白头巾,臂膀红红的,立刻放下手中的织物,叫她父亲或母亲来接待你,做一笔或是两个铜板或是两万法郎的生意。至于态度是冷淡是殷勤还是傲慢,那就全看老板的性格了。
你可见到一个卖桶材的商人,坐在门口,绕着大拇指和邻居聊天。表面上,他只有一些酒瓶搁板和两三捆桶材,可是码头上,他的货栈堆得满满的,向昂热地区的所有桶匠供料。如果葡萄收成好,他知道需要多少酒桶,估算得准确到一两块桶板上下。出一阵太阳可以让他发财,下一场雨也可叫他破产:一个上午,酒桶的价格可以涨到十一法郎,也可以跌到六法郎。
这个地区像都尔一样,天气的好坏决定着市场的行情。种葡萄的,有田产的,做木柴生意的,打酒桶的,开旅店的,驾船的,都盼着出太阳,晚上躺下时,就怕明天一早起来听说夜里结了冰。他们怕雨,怕风,怕干旱,可一时又要水,一时又要暖和一点,一时又要阴天多云。在上天与地上的利益之间,永远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只小小的晴雨表,能够叫人愁、叫人喜、叫人乐。
这条街从前是苏缪城的正街,从这一头到那一头,“这真是个黄金季节”这句话,被挨家挨户换算成数字。因此个个都会回答邻居说:“是啊,天上落金币了。”因为大家知道,一天的阳光、一场及时雨能带来多大利益。在黄金季节,到了星期六中午,在这些勤劳的工匠那里,你别想买到一个铜板的东西。各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小园圃,要到乡下去照应两天。在这条街上,买进,卖出,赚头,一切都是预先算计好了的,生意人可以花上大半天工夫,来开玩笑,来观察行人,评头论足,来打探人家的隐私。某家主妇买了一只山鹑,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到了火候。一个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绝不可能逃过三五成群的闲人的眼睛。因此那儿人的想法都是公开的,就是那些黑洞洞的、无声无息、外人难以进入的房子,也没有什么秘密。
这条街上的生活几乎永远处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个家庭坐在门口,吃午饭,吃晚饭,连吵架斗嘴也在那里进行。街上的行人,没有一个不被他们来一番观察研究,所以从前外地人到外省城市,总免不了挨家挨户给人家嘲笑。许多有趣的故事便是由此衍生而来。昂热居民“噱头鬼”的绰号也是这样来的,因为他们实在擅长开这一类的市井玩笑。
从前,这条街上住的是本地的乡绅。街的高头坐落着古城的世家老宅。如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这些世家老宅还可敬地保持着淳朴时代的遗风。发生本故事的那所凄凉房屋,就是其中之一。
走在这条景色别致的街上,连最细小的事件也足以唤起你的回忆,那古朴的气氛,使你不由自主地沉入遐想。顺着弯弯曲曲的街面走过去,你会看到一处阴森森的凹进去的地方,葛朗台先生公馆的大门,就开在这凹处当中。
在外省是不能随便把一个人的家称作公馆的,不把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交代清楚,读者就没法掂量这称呼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苏缪城名气不小,其前因后果,没有在外省或多或少住过几天的人,是难以完全理解的。葛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称他作葛朗台老爹,不过这些老人明显地越来越少了——在一七八九年还只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师傅,看书读报,写写算算都来得。共和政府在苏缪地区拍卖教产时,他正好四十岁,刚刚娶了一个做木板生意的富商的女儿。他把自己的现金和女人的陪嫁拿出来,凑成两千金路易,去了县城。监督拍卖的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共和党人,他把丈人给的四百路易往他那里一塞,就便便宜宜地把这一地区最好的葡萄园、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和几块分成制租种田买到了手,即便算不上违法,至少也是合法的。
苏缪城的居民很少有革命精神,在他们看来,葛朗台老爹是共和派、革命党,是个敢冲敢闯的新潮人物。其实箍桶匠一门心思只想着他的葡萄。他被任命为县里的行政委员,于是当地的政治和商业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
在政治上,他庇护从前的贵族,竭力阻止拍卖流亡贵族的财产。在商业上,他向共和军提供一两千件白葡萄酒,得到的回报,是把一家女修院的上等草场——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产业——弄到了手。
在执政府时期,老好人葛朗台当上了市长,不仅把地方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葡萄园的收成更好。到了帝政时期,他又变成了一介平民。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另派了一个贵族,一个大地主,一个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来顶替这位被认为戴过红帽子的人。葛朗台先生离开市长的宝座,毫不惋惜。他在任期内,已经为了本城的利益,修了几条出色的公路,通往他的产业。他的房子和地产在登记的时候,占了很大便宜,纳的税很少。
自从田产分类定级以来,他凭着精心耕种,使他的葡萄园和庄园成了当地的“头一份”,这个习惯术语指的是这里出产的葡萄能够酿出极品好酒。凭这一业绩,他本可以申请荣誉团的十字勋章。
葛朗台先生是在一八○六年免的职。那一年他五十七岁;他妻子约莫三十六岁;独生女儿,他们合法爱情的果实,刚满十岁。
或许是老天爷看见他官场失意,想安慰安慰他,在这一年里让他接连得了三笔遗产:先是岳母德·拉各蒂尼耶太太的,接着是妻子的外公德·拉伯特利埃老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先生的外婆尚蒂耶太太的。这些遗产究竟有多少,没有一个人知道。三个老人爱钱如命,一生一世积攒金钱,就图个关起门来看个痛快。德·拉伯特利埃老先生把投资叫作挥霍,觉得放高利贷获利,不如观赏金币来得实惠。所以,苏缪人只凭看得见的收入来估计他们的积蓄。
于是葛朗台先生得到了新的贵族头衔,那种身份,是我们讲求平等的怪癖永远也抹杀不了的:他成了本地区的“纳税大户”。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他还有十三处分成制租种田,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他把修道院的门窗全都从外面堵死,这样既保存了房子和里面的东西,又节省了修缮的费用。此外,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场,一七九三年种下的三千棵杨树,正在那里茁壮成长。最后,他住的房子也是他自己的房产。
这是他看得见的财产,大家都算得出的。至于他的资金有多少,只有两个人能大致说出个数目,一个是公证人克卢索,替葛朗台先生放高利贷的;另一个是代格拉森先生,苏缪城最有钱的钱庄老板,葛朗台先生同他暗中合作,私分利润。在外省要取得人家信任,挣一份家业,都要行事谨慎,守口如瓶。老克卢索和代格拉森自然谨慎透顶,可是在公开场合仍免不了对葛朗台表现出十二分的恭敬,旁观的人据此便可估算出前任市长的资本是多么雄厚。
苏缪城里人人都认为葛朗台先生家有一个特殊的宝库,一个堆满金路易的秘窟,说他只在半夜才去那里,享受注视那一大堆黄金的不可言喻的快乐。那些吝啬鬼看见老头子的眼睛,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因为他的眼睛都是黄澄澄的,染上了金子的色泽。一个惯于用资本赚厚利的人,必然像色鬼、赌棍,或者溜须拍马的人一样,眼神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总有躲躲闪闪、贪婪、诡秘的表情,这些都瞒不过他的同道。这种秘密的语言成了同道之间相互识别和联系的暗号。
葛朗台先生从不欠人家任何东西;作为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老手,什么时候要为自己的收成制作一千只桶,什么时候只要五百只,他计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精确;再说生意场上的投机从没踏过空,酒桶比酒贵的时候,他总有酒桶出卖;他可以把酒贮起来,等每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而那些小地主却早在一百法郎的时候就卖掉了。这样一个人物,理所当然地得到大家的敬重。一八一一年,他获得了了不起的好收成,他精明地贮藏在家里,慢慢地卖出去,赚了二十四万多法郎。若论理财,葛朗台先生像老虎,像蟒蛇,伏在那里,蹲在那里,把猎物打量半天,才一跃而起,扑上去,张开钱袋的血盆大口,吞进大量金钱,然后安安静静地躺下,像一条蛇吃饱了肚子,沉着冷静地躺着,不急不忙地消化。
看见葛朗台先生经过,没有一个人不生出一种交织着敬畏的钦佩。试问苏缪城中,有哪个人没有尝过他那光溜溜的钢爪的滋味?不是这个要买田,从克卢索先生那里借一笔款子,给要了百分之十一的利,就是那个拿了借票到代格拉森先生那里贴现,给先扣了一大笔利息。市场上,或是晚间闲谈中,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在有些人看来,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是本地的骄傲。不止一个生意人,也不止一个旅店老板得意扬扬地对外地客人说:
“嗬,先生呢,咱们这儿,上百万的有两三家,可是葛朗台先生哩,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
一八一六年的时候,苏缪城最精于计算的人,估计那老头子的地产大约值到四百万法郎;但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平均每年的地产收入大概在十万上下,由此推算,他手上的现金数额,大概与不动产的价值相当。因此,大家打完一盘牌,或是聊了一会儿葡萄,提到葛朗台先生的时候,那些自充里手的家伙就说:
“葛朗台老爹吗?……总有五六百万吧。”
要是克卢索先生或者代格拉森先生听见了,就会说:
“嗬!你比我还厉害,我都从不知道他的总数哩!”
有时,有的巴黎客人提到罗思柴尔德家族或拉斐特先生,苏缪人就会问,他们是否和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哑然一笑,轻蔑地说一声是的,他们便摇着头,面面相觑,满脸不相信的神气。
这样一笔财产给葛朗台的所有行为都镀了金。即使他早先的生活有什么异常之处,给人家当作笑柄加以嘲笑,那笑柄和嘲笑也早已过时了。他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最微小的动作,也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他的话语、衣服、手势,甚至眨眼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大家都要仔细观察、研究,就像自然学家在动物身上研究本能的作用那样,终于发现他最琐细的动作,也有高深的不露声色的智慧。于是,大家便说:
“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葛朗台老爹已经戴起皮手套了,该收葡萄了。”
或者说:
“葛朗台老爹买了不少桶材,今年一定能出不少酒。”
葛朗台先生从不买肉,从不买面包。每个星期,那些佃户给他送来阉鸡、子鸡、鸡蛋、牛油、麦子,这些抵租的食品足够他一家人享用。他有一座磨坊,租给人家经营,租主除了缴付租金,还得为他服务,来他府上取了麦子,磨好后再把面粉和麦麸送回来。他只雇了一个女佣,叫作高子娜侬,年纪已经不轻了,可是每星期六还得动手做面包。有些租户是种菜的,葛朗台先生便派定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收获甚多,大部分出售。烤火用的柴火,砍自田地周围的树篱,或者坏死一半的老树,由佃户劈成小块,用小车送进城,还有心巴结,替他送进柴房,讨得几声谢谢。他的开销,大家所知道的,只有教堂的香火和座位钱,太太和女儿的服饰费,家里的灯火钱,高子娜侬的工钱,锅子的镀锡费,缴纳的税金,修理房屋和开发经营的费用。他新近买了六百阿尔邦的树林,请林子附近的一位住户照看,答应给些津贴。置下这份产业以后,他才吃起了野味。
这个人的举止仪容十分平凡,言语不多,发表什么看法总是柔声柔气,句子简短,像是格言。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年代起,每逢要长篇大论发表演说,或者要和人家来一番争论,他总是变得结结巴巴,搞得对方十分厌烦。人家以为,他之所以说话含糊不清,断断续续,啰啰唆唆,前言不搭后语,是因为没受过教育的缘故,其实他完全是假装的,其原因,看过本故事下面某些情节以后,我们便会恍然大悟。再说,他有四句口诀,像代数公式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生活和生意上出了什么难题,只要搬出这四句话,一切便会迎刃而解。这四句话是:
“我不知道。”“我做不到。”“我不愿意。”“以后再说吧。”
他从不说一声“行”或“不行”,也从不写下什么字据。你要跟他说话吗?那好,他右手托腮,肘子抵着左手背,冷冷地听着。可无论什么事,他一旦打定了主意,就绝不再改变。再小的生意,他也得盘算半天。经过一番巧妙的商谈,他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细,而对方还蒙在鼓里,这时他往往回答:
“这件事嘛,我得跟太太商量以后才能定。”
在家里,太太的地位完全像奴隶,可在生意场上,却成了他最方便的挡箭牌。他从不串门走人家,既不吃人家的,也不请人家吃。他从不弄出声响,似乎什么都要节省,包括动作在内。他时刻尊重产权,从不在别人家里乱摸乱动。
然而,他尽管声音柔和,态度稳重,仍不免露出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尤其是在家里,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受拘束。
至于体格,葛朗台先生身高五尺,矮矮墩墩,腿肚子有一尺的围,膝关节粗大,肩宽背阔;古铜色的脸盘圆溜溜的,长着麻子;下巴直直的,嘴唇平平的,一口牙齿雪白,两只眼睛不露声色,像是要吃人,像传说中蛇怪的眼睛;额上布满抬头纹,且有一块意味深长的隆凸;一头黄中带灰的头发,有几个年轻人不知轻重,竟敢开葛朗台先生的玩笑,说那是黄金中夹着白银;鼻头硕大,顶着一颗布满血丝的囊肿,一般人不无道理地说,那里面装满了花花点子。这副尊容显示出一种要占便宜的精明,一种勉强装出的诚实,显出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习惯于把全部感情都集中在聚财攒钱的快乐以及他唯一真正关心的人、他的继承人、他的独生女儿欧也妮身上。此外,他的姿态、举止、走路的架势,总之,身上的一切,都无不显露出生意场上处处成功所养成的自信。因此,表面上,葛朗台先生性格温柔,一团和气,其实是外圆内方,铁石心肠。
他的装束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