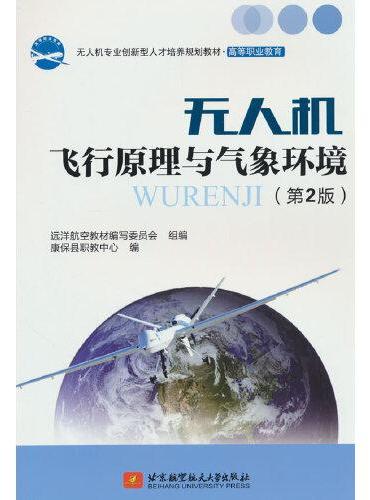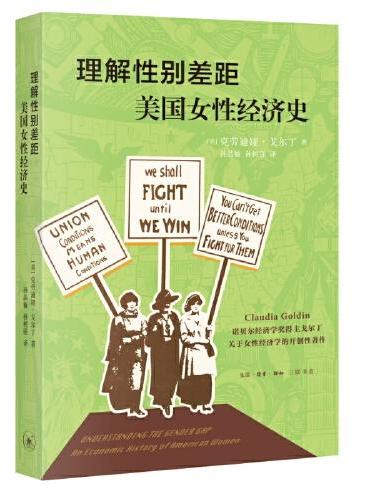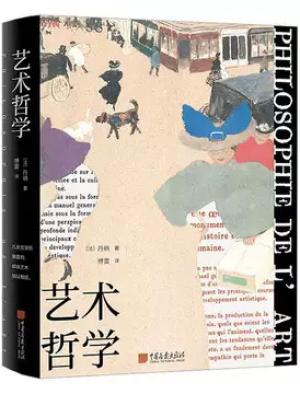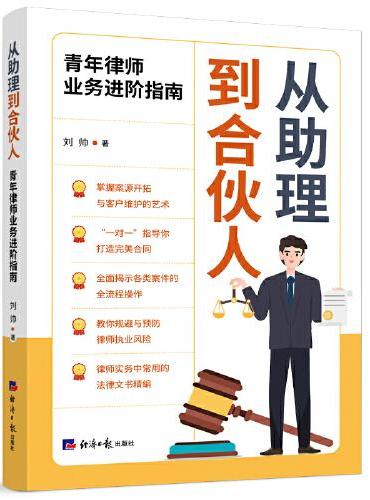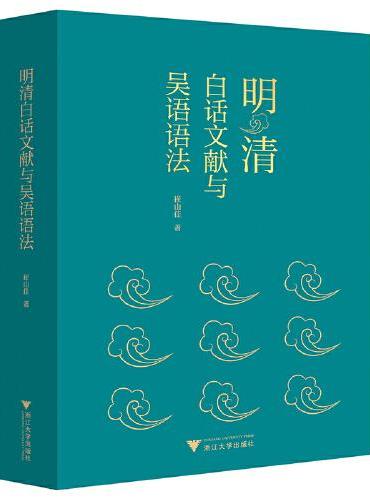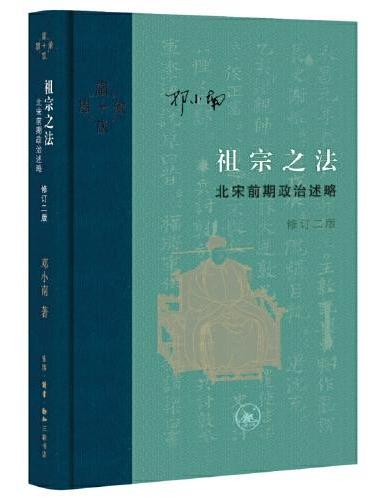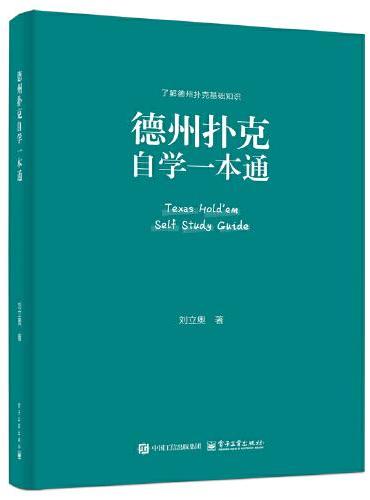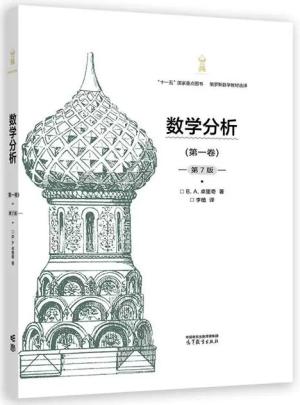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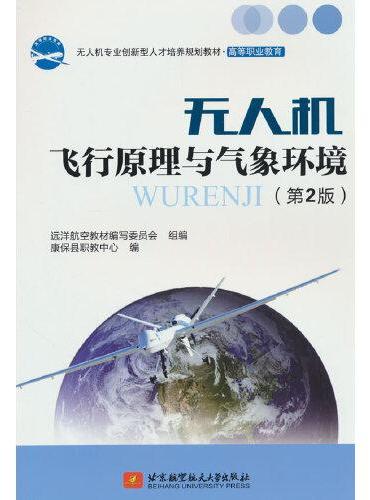
《
无人机飞行原理与气象环境(第2版)
》
售價:NT$
1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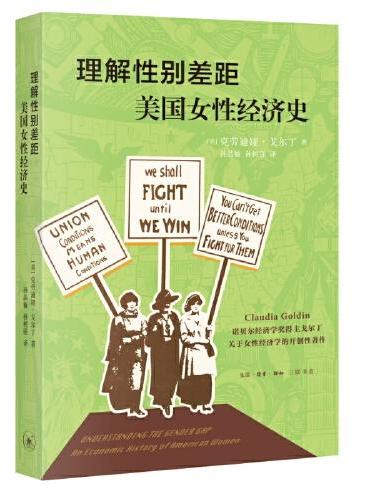
《
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
》
售價:NT$
4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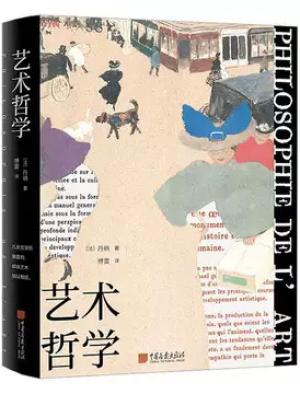
《
艺术哲学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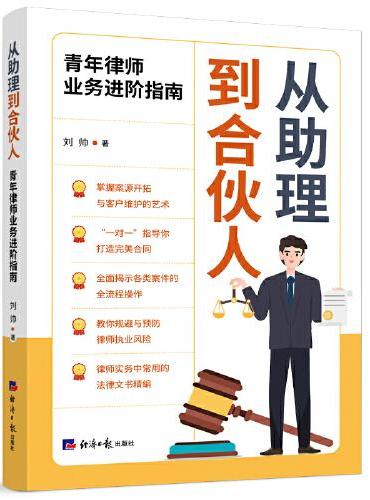
《
从助理到合伙人-青年律师业务进阶指南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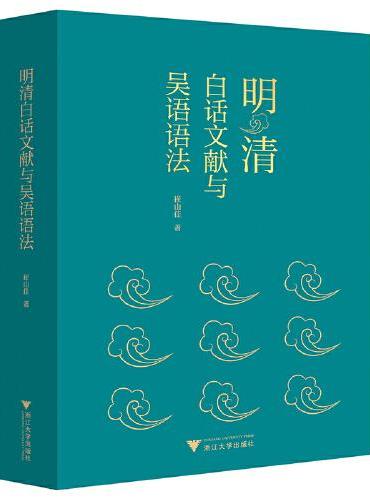
《
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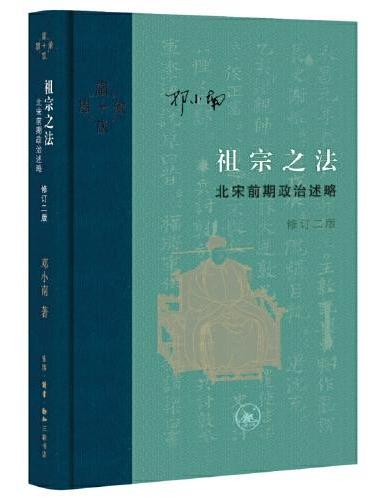
《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二版)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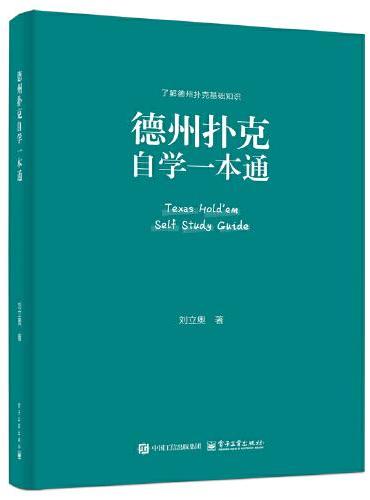
《
德州扑克自学一本通
》
售價:NT$
2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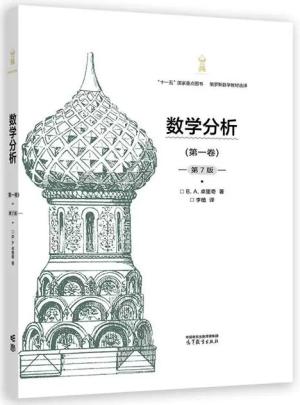
《
数学分析(第一卷)(第7版)(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454.0
|
| 編輯推薦: |
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让目中无人的喜欢和旁若无人的努力,成为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最适合、最优雅的姿态。当遇到足以让自己放弃的困难,或者极度的孤独之时,这个姿态将会支持自己,让自己依然能够坚持梦想。
依靠这个姿态、依靠自己的日益强健的内心,优雅的承受痛苦,最终成为无可替代。
|
| 內容簡介: |
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用自己目中无人的喜欢和旁若无人的努力,成为世界的无可替代。
从小,许芳宜就对念书没有兴趣,父亲最担心的就是她只能到工厂做女工;从小,她就在喧闹的人群中沉默娴静,无法让人关注。
但是,就是这个一个小孩,当接触到了跳舞,接触到了最接近她生命意义的东西,她就成了一个“目中无人”的、闪闪发光的小孩,专注于拼命,专注于自己内心的最好,拼命舞动,仿佛有了翅膀。她踩着自己的汗水和青春时光,一步步前行。
如今,她是美国最权威的玛莎·葛兰姆舞团的首席舞者,被誉为现代舞之母玛莎葛兰姆的传人。她用别人眼中的任性妄为,用自己旁若无人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成为无可替代。
|
| 關於作者: |
许芳宜
许芳宜,国际知名舞蹈家,出生于台湾宜兰县,现旅居美国纽约市。
许芳宜为前玛莎葛兰姆舞团的首席舞者,被誉为“美国现代舞之母玛莎葛兰姆的传人”。美国《舞蹈杂志》(Dance Magazine)将许芳宜列为当年“最受瞩目的25位舞者”之一,并且成为封面人物。并获包括台湾颁赠“五等景星勋章”等许多著名奖项。
近几年活跃于国际间,也积极与国际级的艺术家与编舞家交流,被李安称之为台湾地区的门面。曾受邀在TED演讲。
|
| 目錄:
|
序 这位是“许芳宜的爸爸”
简体字版序 我要成为太阳
自序 深深一鞠躬
Part 1 芳宜说芳宜
前头有光,有我最爱的舞台
“我爱瓦斯!我爱瓦斯!”
我的芭蕾考三分
罗斯老师教我的
菜鸟闯舞者圣地——纽约
把自己打碎,重新开始
葛兰姆的震撼教育
自己教自己
舞里舞外(一)
舞里舞外(二)
我知道你在看我
快乐三分钟,难过三分钟
受伤的滋味
做给他看!
另一个半圆
舞蹈与爱情相撞
云门经验
曼菲老师留给我的
我行,为什么你不行?
不打不相识
纽约高级住宅里的黄皮肤客人
相信自己的感觉
拉芳承载的梦想
舞蹈,我的生命态度
Part II 他们说芳宜
连喝一杯柳橙汁都是为了跳舞 林荫庭
采访后记 一场“文字人”与“身体人”的交会 林荫庭
|
| 內容試閱:
|
快乐三分钟,难过三分钟
多年下来,我慢慢习惯了在媒体曝光,接受外界品评长短;
同时,我也学会了“快乐三分钟,难过三分钟”的哲学——
无论毁誉,无论悲喜,
都不能长久耽溺,都要快快回复平常心。
掌声响起
葛兰姆舞团2000年因作品版权纠纷暂停运作,2003年2月卷土重来,自然是全球舞坛关注的大事。我在复团公演中担纲演出“迷宫行”和“编年史”,《纽约时报》舞蹈版做了大篇幅报道,我的独舞相片占据了整版的四分之一;文中称我是“当今葛兰姆技巧和传统的化身”,还形容我扫除了葛兰姆风格陈旧的蜘蛛网,为它注入新生命。
2004年,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制作“新移民”专辑(Destination America),报道我为了追求舞蹈天地而远赴美利坚合众国的心路历程,并且来台湾地区拍摄我的生长背景;与我在同一集出现的还有早年移民美国的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以及当代的俄国艺术家卡巴可夫夫妇(Ilya and Emilia Kabakov)。
2005年元月,美国舞蹈界最具影响力的《舞蹈》杂志选出了当年最受瞩目的二十五位舞蹈工作者(25 to Watch),我身穿一袭蓝紫色的舞衣登上了封面;同时获选的还有纽约市立芭蕾舞团的特雷莎·瑞克兰(Teresa Reichlen)、美国芭蕾舞团的克莉丝蒂·布恩(Kristi Boone)等杰出现代舞者、芭蕾舞者和编舞家。
经过许多年默默地埋首耕耘,猛抬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镁光灯对我闪起。纽约媒体给我很高的评价,认为我赋予作品新的诠释方式,很有自己的特色,甚至超越了玛莎当年。
葛兰姆舞团创立八十周年演出后,有媒体指出:“如何想办法把许芳宜留在舞团里,是现任艺术总监最大的课题。”如果有人说我已经成为葛兰姆舞团的“明星”,我必须说,媒体的加持是很重要的原因。
一般舞评家注意的主要是作品本身,所以评论里出现的大多是编舞者的名字,真正的明星是编舞者。舞蹈明星多数出现在芭蕾舞团,只有少数现代舞团受注目的是舞者,葛兰姆舞团就是其中一个,因为玛莎·葛兰姆已经不在人世了,评论仍然推崇葛兰姆大师的才华,但表演者如何呈现经典作品成了主要的评鉴焦点。尤其葛兰姆的舞作里,领衔舞者的角色鲜明,爱恨情仇非常强烈,如果诠释得好,会让观众觉得很过瘾,很容易就成为目光焦点。
多年下来,我慢慢习惯了在媒体曝光,接受外界品评长短;但在此同时,我也学会了“快乐三分钟,难过三分钟”的哲学——无论毁誉,无论悲喜,都不能长久耽溺,都要快快回复平常心。
这一切要回溯到1995年我首度遇到评论的经验。
来自《明报》与杂志编辑的冲击
那一年我刚进葛兰姆舞团,还是个实习舞者,第一次随团来亚洲巡回表演。舞台上,实习团员和群舞者只是舞团的一员,永远的大群舞,舞评人也永远不会单一提及的对象。想不到的是,在香港演出后,我居然上了《明报》。作者写道,一看我的名字就像是个中国人,再看到我的五短身材也像是中国人,“她应该是中国人吧!”
当时我真的被吓到了,不可能有人认识我吧?我在台上看起来真的很丑吗?他从一个最负面的角度来猜想我是中国人,实在让人很不舒服。我心里起了个大疙瘩,很不想让人家看到这篇文章,但藏得起来吗?报纸每天可是几百万份在发行的。
那次巡回表演,香港演出之后,我在日本演出时脚伤骨折,拄着拐杖回家养伤三个月。之后再回到纽约时,我收到了一封信,是香港一位杂志编辑寄来的,是个西方人,他竟然说,他去看了我们在香港的那场演出,从头到尾目光无法从我身上移开,一直跟着我转。他翻看节目单,寻找我的名字,猜想应该是Fang-Yi Sheu。但他不敢相信我只是个实习团员,因为我在舞台上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光芒,相信很快我将不只是一个实习团员,一定会是somebody(大人物)。
前后两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与学习。我先是害怕别人看到《明报》的报道,觉得自己很丢脸;后来收到那位杂志编辑的信,冲击更大,哇!这两个人说的是同一场演出啊,我要听谁的?我愿意接受谁的评价?我要相信别人的批评或赞扬?该为哪个开心、哪个难过?谁说的才对?好像都对也都不对,都只是某一个人的意见——主观、却是他们自认为客观的意见。
真正的尺掌握在自己手上
接下来这些年,一次又一次演出,一次又一次接受媒体评鉴。舞评人很多是资深观众,甚至看过早年玛莎·葛兰姆的演出,他们提供的观点或数据经常很有历史感,颇值得我参考;而且,平心而论,媒体的确给过我很多肯定,让更多人认识我的舞蹈,对于我在舞蹈界的发展帮助很大。
然而另一方面我也学会,不要因为别人给我很好的评论就飞上天;也不要因为拿到很糟的评论就要下地狱。今天选择走这条路,我认为自己的价值不应该只操纵在别人的一支笔上,不能让几个字就决定了我的成败及未来,难道我的存在只为别人?主客观评论我都接受,但是作为一个基本的“人”,这些仅供参考。我可以开心,也可以难过,但维持三分钟就好了,这些绝不是我生命的全部。
假设说,今天有篇评论指出,许芳宜这辈子没用了,我就真的没用了吗?这时候我该如何看待自己?相反地,有时报纸说我表现得很好,我自己却很不满意,因为自知没有达到该有的水平,发生了不该发生的错误,不可原谅。那把真正的尺握在自己手上;自己这关过不去,就是过不去。
不沉溺于光环
1995年秋天,我在纽约City Center第一次参与葛兰姆舞团“纽约季”的演出,那时我刚从实习舞者升为新舞者,老板就给了我独舞的角色,在“天使的嬉戏”里演红衣女子。当时《纽约时报》的评论大意是,“新团员许芳宜加入舞团,技巧非常干净利落”。很简单的几句话,我还问同事:“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好的评论吗?”同事说:“是啊,是好的,而且他还说你刚进来,他是喜欢你的。”像这样,尽管舞评中只提到了两三个字,已属难能可贵,只要自己希望,这个光环可以戴很久,但当时我只说:“哦,好,谢谢。”继续我的排练。
2003年2月16日《纽约时报》第一次大篇幅报道我,还记得那天我和朋友出去吃早餐,边吃边翻报纸,“喂,看,大张的呢!”然后去多买了几份报纸,回宜兰时要带给爸爸看。当时我也非常开心,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后来我很少看舞评,当时几乎每篇报道都给我许多赞许及肯定,却对其他团员评价不高,我不想在脑子里装太多好话,就怕自己太过沉溺,松懈了继续努力的心。那些文章看多了,真的会误以为自己是神,成天戴着那顶皇冠就好了。当然,别人赞美我时,我还是很开心,问题是,这顶皇冠要在我头上戴多久?世界这么大,光是纽约就有这么多这么多舞者,我绝对不能无限膨胀自己。
倘若有一天,我碰到当年那位揶揄我的《明报》记者,一定会大步走到他面前自我介绍:“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五短身材的中国人!我仍在舞台上!”至于那位鼓励我的杂志编辑,我也会向他致上最诚挚的谢意。
自己教自己
舞蹈给我的不只是舞蹈,
而是认真看待自己、看待生命的学习,
也让我对所有的感觉更深刻。
从1995年到2006年,我大部分的跳舞时光都在葛兰姆舞团度过,虽然曾经几度进出,但“Fang-Yi Sheu”这个名字与葛兰姆舞团越来越牵系在一起了。
我1995年2月进入葛兰姆舞团后,同年7月即由实习舞者升为新舞者,1996年升为群舞者;1997年晋级为独舞者;1999年成为首席舞者。许多舞者可能必须耗费十年时间才能走完的历程,我很幸运地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完成了。逐渐地,越来越多的媒体为我冠上了“明星”的称号。
但是,在这些表面的顺遂和光环背后,我修习了一门顶重要的功课:自己教自己。
自己找答案
刚进舞团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照顾自己的舞作学习,几乎没有余力观察环境或别人;在我心目中,这些世界知名的大舞团应该都是很完美的,我一定要管好自己,不能出错,不能连累别人。一段时间后,我开始观察别人排练,在技巧和表演方面发现了很多问题,当时我心想,“连我都看到的问题,为什么大家看不到?还是看到了没说?”也许他们觉得没有关系,这是每个人的标准不同;但我认为,在教室若排练粗糙,上了台绝对不可能有质感可言。于是我警觉到,相同的状况可能也发生在我身上,必须照顾自己更多、观察自己更多、自觉性要更强。
玛莎·葛兰姆所编的舞作,许多都取材自希腊神话或美国民俗故事,交织着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究,每接到一个角色,对我都是一次跨越文化和心理藩篱的挑战。有一回我为了一出极为抽象又充满内心戏的作品“赫洛蒂雅德”(Herodiade)头疼不已,向艺术总监求助:“这种呈现手法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她给我的答复是:“芳宜,我觉得你很聪明,一定可以自己找到答案!”
艺术总监或许是想留给我自由探索的空间,所以没有直接给答案,但当时我有点错愕,好像一扇门“砰”的一声在我眼前关上,是一种回绝。之后,我告诉自己:“从今而后,我必须找方法学,自己教自己,自己跟自己学,求人不如求己,非自立自强不可!”有书可以翻吗?有录像带可以看吗?也许这些作品不过就是人类共同的本性而已?神话故事描述的人生幽暗面与人性弱点,也许都可以从自己心底去找答案?
就像今天教授给了我一个论文题目,没有人教我,没有课本可依循,我要自己上天入地去找线索、找答案,这是我自己的功课。我进入了这个水域,不知会摸到蛤仔还是贝壳里的珍珠,只能先把脚放进去,才能学习游泳。
加上这段时间我大多是独自在纽约生活,也养成了自己与自己对话的习惯,无论白昼黑夜都在进行。
养成与自我对话的习惯
早晨好不容易把自己叫起床,全身又酸又痛,眼睛几乎睁不开来,我就对自己说:“加油!一定要加油!一定要醒过来!今天又是新的开始,不可以放弃!”我发现“加油”是这时候给自己最好的一句话。
晚上练完舞回到家,我也会不断思索当天排的舞作,比如:为什么“心灵洞穴”里的美狄亚会嫉妒?为什么女人永远嫉妒男人有外遇?她天生就如此心狠手辣,还是她其实只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为什么人们要说她很坏?男人背叛就不坏吗?或者,女人因为爱得太深、伤得太重,才会疯狂到丧失天良?当她为爱去杀人时,那种痛苦怨恨有多深?
这种自我对话最常发生在搭地铁时。我的住处通常离舞团都很远,每天搭四五十分钟的地铁是家常便饭,也成了自我修炼的最好机会。
我发现戴上耳机是与外界隔绝最好的方法,有时甚至不必放音乐。如果当天排练过程不顺,心里不舒服,身体又疼痛,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我为什么要接受不合理的对待?别人对我不客气时,为什么我回不了嘴?为什么我不掉头就走?
我就这样不断抛出问题,也不断回答自己,到后来甚至假想有一个人在与我对话。没有人教我,翻书也找不到答案,那种思维是自己的,我要消化、要说服的对象都是自己。
之后发现,这种与自己的对话能力很重要,因为许多事情我想要答案,有时问了十个人,就有十个不同的答案,此时的我就需要安静沉淀一下,听听自己的声音。刚好我在纽约独处的时间很多,除了跳舞不须操心其他事情,让我能完全专注在自己身上,每天修炼自己的思维。
即使没能到宗教圣地朝圣,在这个繁华的大千世界里,我也能悟出自己听得懂的道理。
把逆境转变为优势
当初艺术总监没给我答案,让我自己摸索,这种“反动力”成了我最大的“动力”,所以我一点都不怪她,甚至心存感谢,这应该是她帮助我最好的方式吧!她让我没有后路,反而给了我一条出路。
倘若当时艺术总监立刻给了解答,我不可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思路。当然,这需要有正面思考的态度,才能把一个恶劣的处境扭转为优势,也就是佛家所说的“逆增上缘”吧。
懂得把逆境转成优势的人,才会有活路可以继续往前走。当对方说“我觉得你很聪明,一定可以自己找到答案”时,我曾经沮丧难过,但很快就化解,可能因为一路走来碰过太多这种情况了,我若一次次都禁不起打击,可能哪里都去不了。
反过来讲,如果我很幸运,拥有丰富的资源,时时有人在旁帮助我、照顾我,绝对不可能有这些成长。正因为花了很多时间和自己工作,磨炼出敏锐的自觉能力,不论在舞台上或平常生活里,蛮容易看到自己的。譬如,练舞时我可以很快就察觉哪里出了问题,马上调整,当别人还没纠正时,自己已经在进行修正,如此自然省下许多改错的时间。
前辈舞者雪中送炭
我在寂寞中独自摸索学习,但并不是绝对孤单,当时曾有一双温暖的手向我伸来,令我感动,那是资深舞者蓝珍珠(Pearl Lang)。
蓝女士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是葛兰姆舞团的舞者,曾经与玛莎共事,也是玛莎传承角色的第一人,德高望重;我进入舞团时,她已经七十多高龄了,仍在葛兰姆学校教学。当我正在为如何诠释“赫洛蒂雅德”伤脑筋时,蓝女士打听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主动约我私下在葛兰姆学校会面,很慷慨地与我分享她早年演出这角色的经验,指点我的动作,尤其是一些录像带上看不清楚的地方。
经由蓝女士的点拨,我才了解,“赫洛蒂雅德”里女主角在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挣扎,不只是葛兰姆的挣扎,也是很多艺术工作者共同的写照;当每个舞者选择呈现葛兰姆时,我选择呈现自己。
后来蓝女士去看葛兰姆舞团的公演,总要先问清楚哪场有我的演出,她才会去看;甚至对别人说:“这个舞团如果没有芳宜,就不必看了。我就是来看她的。”
在我“自己教自己、自己跟自己学”的日子里,蓝女士这位前辈舞者的雪中送炭,好似一股暖流,纽约的冬天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寒冷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