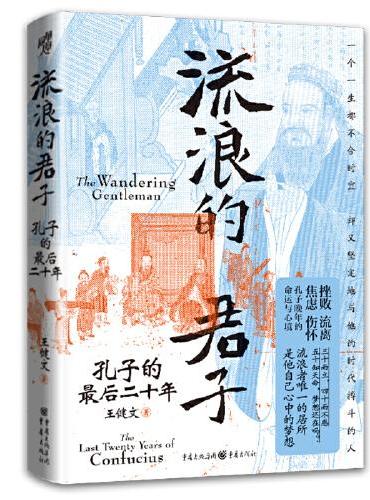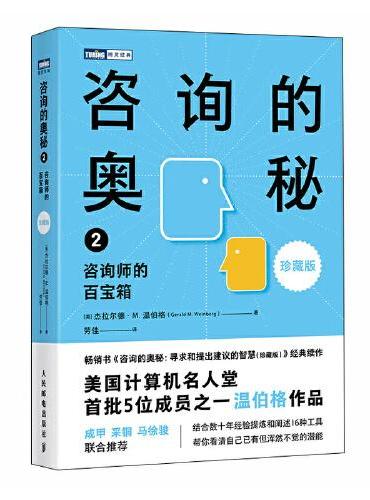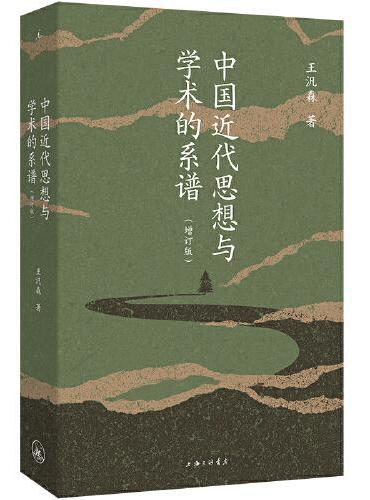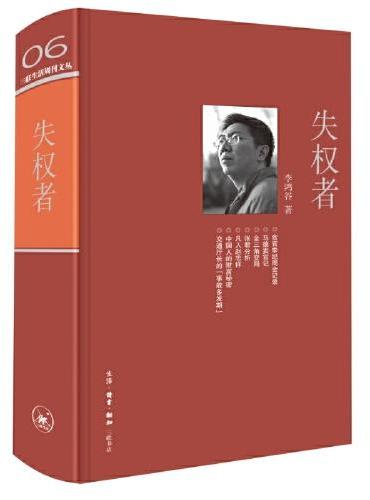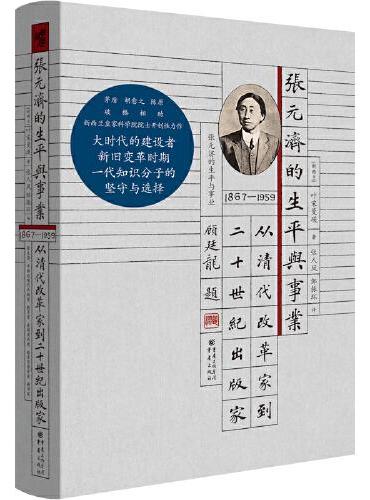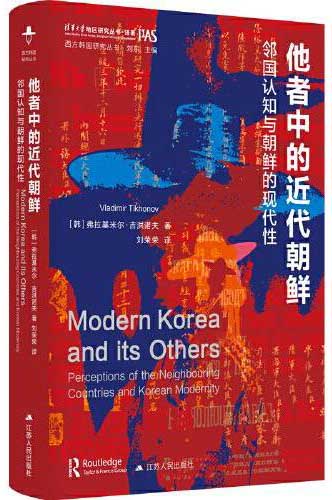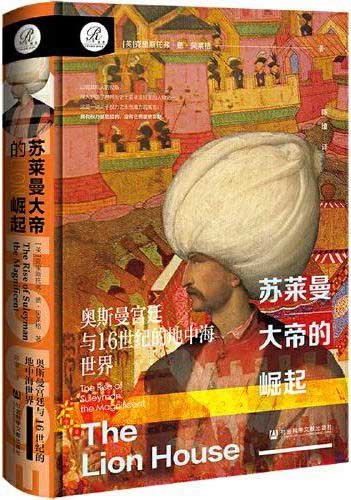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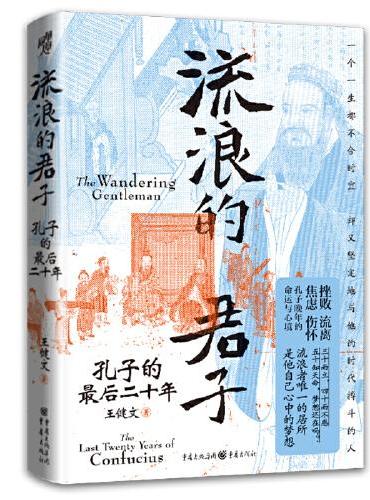
《
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 王健文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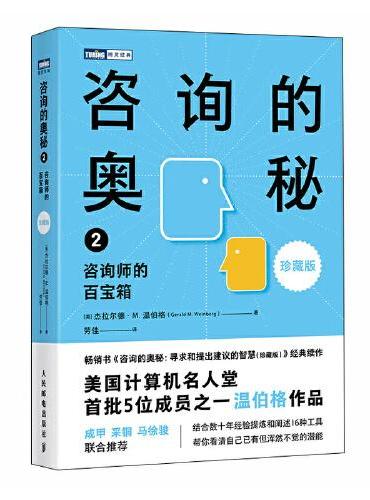
《
咨询的奥秘2:咨询师的百宝箱(珍藏版)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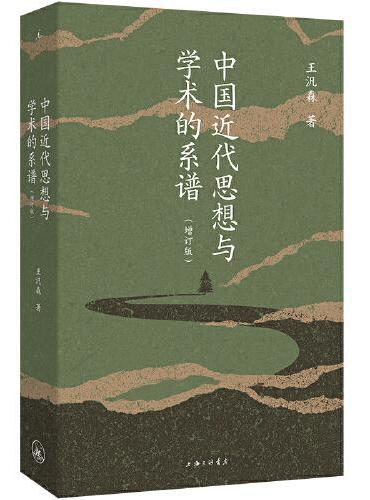
《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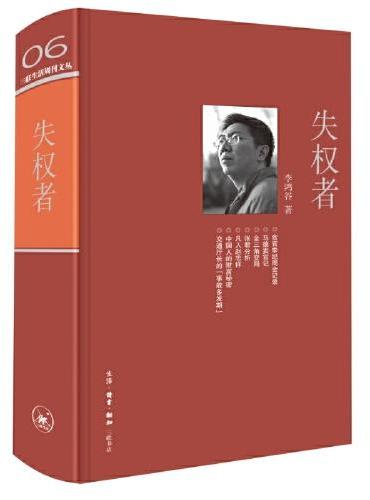
《
失权者(三联生活周刊文丛)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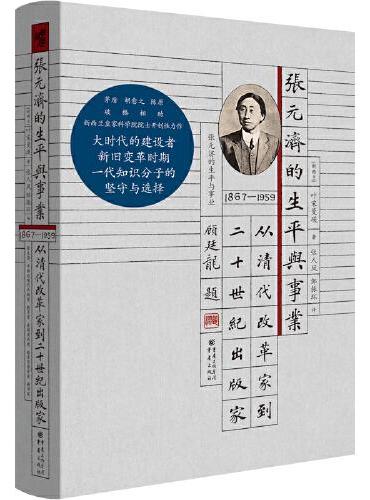
《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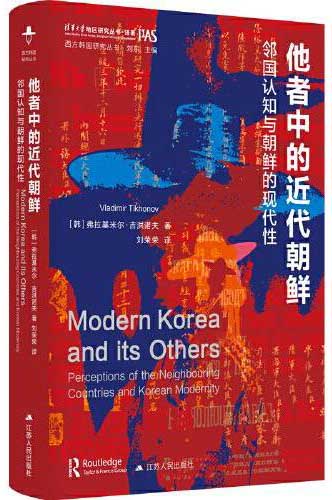
《
他者中的近代朝鲜(西方韩国研究丛书)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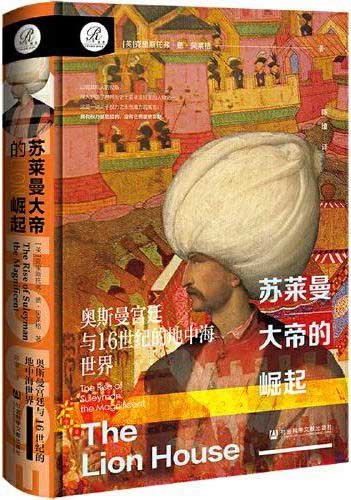
《
索恩丛书·苏莱曼大帝的崛起:奥斯曼宫廷与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
》
售價:NT$
403.0

《
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宋代将门百年兴衰史
》
售價:NT$
454.0
|
| 編輯推薦: |
|
蒋蓝对动物的观察和凝视,却是诗人生命热力的奔流和散射,是人类的智识和精神在动物物象中的浪漫灌注。在诗和科学的结合上,诗人的理性作了一次漫长而近乎完美的探险。当思想的火苗燃烧的时候,他始终克制着激情,尽量以最优雅的姿态对客体进行全方位细微的洞察和判断,俨然又是一位长期生活在从林和峡谷中的博物学家……
|
| 內容簡介: |
|
我看到太多的动物,它们或者用爪子,或者用尖利的喙和羽翅,或者用钩镰枪一般的尾巴,在哲学大师的指缝里施展绝技。它们麋集起来的身影宛如锈刀,剁开了人们完全锈死的思维之门。它们从偶然的缝隙间穿过,替哲人们完成了一篇篇直指人心的文字。动物们以自己的身影展示了“泼墨技法”——在人类智力的试纸上,人们看到了那些隐匿在表象背后的骨头和尖刺。哲学告诉人们的一个常识是:理性思维企图把整个世界化为精神的世界,如果现实世界是一个镜像世界的话,那:么把握世界本质的基本手段就是思想。与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一样,要达到对精神镜像的体认,就必须把握其思想特质。也就是说,思想是精神的动词,是精神得以成立的“第一推动力”。
|
| 關於作者: |
|
蒋蓝,诗人,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崇尚独立言路,喜欢特立独行者。人民文学奖、中国西部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布老虎散文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倒读与反写》、《梼杌之书》、《媚骨之书》《爱与欲望》等文学、文化专著。散文、随笔、诗歌、评论入选上百部当代选集。曾任《青年作家》月刊主笔、主编,现供职《成都日报》报业集团。近年在江苏、山西、新疆、吉林、山东以及金沙讲坛、成都故事讲坛等举办过多次文化、学术讲座。
|
| 目錄:
|
自序:动物的诗学镜像
驴上沉思录
蚕马与蚕神
梼杌的考古学
照亮黑暗的乌鸦
塞壬唱的什么歌
哲学狗儿
庄周的蝴蝶
蜗牛的慢性迷宫
宽体动物
鸭子的阶级性
天鹅让银子变暗
居住于陷阱的狐狸
鸡鸣与时间管理学
利维坦与贝希摩斯
纯粹的苦行
黑夜里的黑牛
鸵鸟
鬣狗
鲶鱼
鸭嘴兽
战马的尊严
独角兽
潜伏在体内的豹
快乐并痛苦的牛虻
豪猪的困境
猫头鹰之思
蚁王如花
老鹰
布里丹的驴子
极乐鸟与蝶翅间的魔术
孔雀的灵魂
啄木鸟
黠鼠
蚂蚁
斯芬克斯的意义
蜘蛛丝
老虎的仆从
羊、虎皮以及盐
替罪羊及其他
蛙语
葛上亭长放飞的西班牙苍蝇
后记
豹子的精神之旅——蒋蓝随笔印象
|
| 內容試閱:
|
蚕马与蚕神
一霎时风雨都停住,
皓月收束了雷和电;
马皮裹住了她的身体,
月光中变成了雪白的蚕茧!
——冯至《蚕马》
在古文化谱系下,似乎异端的叙事,总是比按部就班的“正统叙事”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这就是说,人们对与于碰断天柱的共工氏充满联想,但对于创世之前的“混沌”则漠然视之;人们对于教民养蚕、推进缫丝的黄帝正妃嫘祖并不感兴趣,尽管她有“先蚕”的光荣称号,但对于充满乱伦意味的“马头娘”则是常怀不止——按理说,西陵之女嫘祖才应该是桑蚕的始祖啊。但很多事情就这么颠而倒之。
荀子曾写下过一篇《蚕赋》,其中描写蚕的形态时有一句“此夫身女子而头马首”,是说蚕的身体柔软婉转,似女性躯体;头则似马之首。这一隐喻似暗示了某种男权视野下的“性取向”。
后来有人看出了其中端倪。唐时,四川盐亭的“鹅溪绢”称誉于世,被作为唐王室画院专用品,女皇武则天曾题诗《赴鹅溪》赞扬:“丝绸龟手富,贝锦鹅溪绢;功比马头娘,映月水三潭。”我至今不明“龟手富”为何意,但“马头娘”很明显,指的是广泛流传在川西的“蜀女化蚕”“蚕女马头娘”的传说。
清朝翟灏所编纂的《通俗编》,为历代关于俗语出处最著名、搜罗最广的一本典籍,其《神鬼》里引《原化传拾遗》记载说:帝喾高辛氏时,蜀中一个男人在野外征战被掠去,所骑白马独自回家。妻子伤心不已,发了毒誓:谁能将其夫救得生还,就把女儿嫁给他!白马闻言仰天长啸,挣脱缰绳疾驰而去。几天后,白马载着其父返回家中。其母见此反悔,不再提及嫁女之事,从此白马整日嘶鸣不止,不思饮食。其父见状,心中为女着急,取箭将马射杀,并残忍地把马皮剥下晾在院子里。某天,那马皮突然飞起,它像青蛙射出了红舌那样将姑娘卷走,不知去向……数日后,家人在一棵树上找到了姑娘,马皮还紧紧包裹着她,无人知道这奇异的爱情是否幸福,反正女儿的头已经变成了马首,正
伏在树枝上吐丝缠绕自己。
家人将其从树上取回饲养,养蚕吐丝结茧缫丝的历史从此开始。这个故事在《蜀图经》《太古蚕马记》《搜神记》《神女记》《太平广记》等古籍中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述。古代军人杀死自己战马的事绝无仅有,何况还是一匹通灵的救命之马。不但杀死它,还要剥皮抽筋,由此足见受战马刺激的父亲的狂怒程度,事情发展到彻底失控。这不但是对古侠义精神“践诺”的反讽,也是对爱情的背叛。
诗人冯至显然就不满足于这样结局的“人兽之恋”。1925 年他据此写出了叙事诗《蚕马》,以青年对美好爱情的追求。“白马”乃是“男青年”的面具,由此展开了汉语版的“白马王子”叙事。这一“故事新编”的写作被朱自清先生誉为五四新诗中“堪称独步的四首叙事长诗中有代表性的一首”,由此成为冯至叙事诗的杰作。
梼杌的考古学
事实上很难让人们跳出现在的思维模式,恶怎么做都不对,善做什么都有理。”
——【危地马拉】奥古斯托蒙特罗索《黑羊和其他的寓言》
伟人的遗传基因并不总是稳定的,何况伟人殚精力竭,总在人、神、兽之间异形、异位,忙得找不着北,加之消耗巨大,颇有一代不如一代之况。想想看,既然杂交水稻也可能出现变异,高粱秆儿也会变成矮冬瓜,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
黄帝巡游南方,见西陵氏女可人,娶为正妃,她据说叫“嫘祖”,后世也封之为“先蚕”。其实,“累”字本就是指东西一层又一层堆积起来,形状是堆起来虫子,这分明是指蚕茧。加上女旁,暗示了桑蚕缫丝来自一个女人。这就是说,这应是一个民间性职业封号,在汉朝开始才构成了黄帝正妃的名字。当时西陵之国大约在现在四川、湖北、湖南三省交界一带,与周时楚国疆域相邻,但当地却未以养蚕著名。文史学者邓少琴认为西陵就是蚕陵,黄帝所娶西陵氏女当为蚕陵氏女,蚕陵就是今天的四川茂州之叠溪。(《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136页)1933年发生叠溪大地震,彻底毁灭了那里的古文明遗址。
《说文》解释蜀字,就是“葵桑中虫”的意思,以蚕作为族名,说明古代蜀人很早就发明和驯养桑蚕。正因如此,蜀山氏又被称为蚕丛氏。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中》进一步认为,蜀山氏是最早“拾野蚕茧制锦与抽丝”的部族,到了“西陵氏女嫘祖为黄帝妃,始传蚕丝于华夏”,这也可以看做是中原文明文明与古蜀文明的第一次联姻。
梼杌的来历既有兽系,也有人传,更有神谱。
嫘祖生玄嚣、昌意二子。玄嚣之子蟜极,其之孙为五帝之一的帝喾;昌意又娶蜀山氏女为妻,生高阳,继承天下,这就五帝之一的颛顼,他被封为“北方天帝”。这几个女性,均出自蜀地区域。根据冯广宏先生考证,这是公元前23世纪前后的事情。颛顼固然是人中之龙,但颛顼的儿子梼杌却剑走偏锋,成为了“人子”的反词。
《山海经》说,梼杌实为一种猛兽,状如虎而大,毛长两尺,人面虎足,口牙,尾长一丈八尺,由于凶狠狂暴,扰乱荒中,梼杌也被称为“难训”或“傲狠”,还说梼杌喜好在荒野中拔足狂奔,发泄其汹涌的力比多。梼杌是从里到外的极端无政府主义,没有人能够使其归顺于制度和伦理的麾下。颛顼徒为神仙大帝,可惜的是,他的4个儿子均为邪神,前三个生出后不久就夭折了。第一个死后住在江水中,变做“虐鬼”,散布瘟疫疾病;第二个死后住于若水,叫“魍魉”,以使人生疮害病或者惊吓小孩为使命;第三个死在正月三十,最喜穿破衣喝稀粥,人称“送穷鬼”。只是他们恶的级别不够,比不上恶兽梼杌的名头。
在我看来,这口口相传的历史具有阴谋论和血统论性质。颛顼为黄帝后裔、昌意之子,生于若水(今雅砻江四川境内的雅安一带),有学者指出,“蜀”在古羌语呼复辅音“颛顼”,其义言鱼,高阳氏之鱼王,即蜀王,也就是禹王;颛顼是禹的羌语名。颛顼二字很奇怪,字书上解释有愚昧、谨貌等义项。颛顼二字均从“页”,《说文》云:“页,头也”,足见颛顼的命名与头有关。《说文》言颛顼是“谨貌”,就是“木头木脑”,川语“木脑壳”是也。所以,它被引申为“愚昧”。如果我们把颛顼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相联系,那些青铜头像就有些木脑壳意味。这幽暗地昭示后人:有其父,必有其子。
换言之,梼杌脑袋进水了,成了不会说话的弱智儿。
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凶兽”——贪得无厌的饕餮、穷凶极恶的浑沌、背信弃义的穷奇、沉默而好斗不已的梼杌。据说来历是:浑沌是驩兜死后的怨气所化,穷奇是共工死后的怨气所化,梼杌是鲧死后的怨气所化,饕餮是三苗死后的怨气所化。富有深意的在于,驩兜、鲧、三苗与共工,他们都因为反抗最高权力者而被杀,死后精神不灭,被当权者侮为“邪魔”,可见反抗独裁权力的异端之火从未断绝,地火一直运行。鉴于附有鲧的怒气,梼杌的长相十足凶恶,头脑不灵,这种对反抗者的刻意妖魔化,看起来起源甚早。我估计被权力口红妖魔化之后的梼杌,这一造型比起玛丽雪莱笔下的佛兰肯斯坦,也难望其项背。后来梼杌被主流社会定义为顽固不化态度凶恶之人,《左传文公十八年》有云:“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通过史书的铁板钉钉,就进一步把反抗者的后代与痴呆愚笨归为同类。
可以说,梼杌回到人形,为鲧;赋形于兽,为虎形兽。
需要注意的是,蒙文通先生经过缜密考证后,认为《山海经》是古代巴蜀的典籍,代表的是巴蜀文化地区的说法。鲧、禹本是古代巴蜀地区的传说,鲧、禹亦当原本是活动于这一地区范围。鲧采用“堵塞”的治水法,失败于岷江及其周邻的江河被杀后,他的滚滚怒气,是巴山蜀水的瘴气凝聚的一把利刃。
他赋予梼杌的,恰是来自古蜀地的红壤之血,染就了他的斑斓虎纹。
梼杌另有一说是神名,《国语周语上》:“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梼杌现身在河南丕山一带,不过是借此说明朝代兴起都是明神之志。另外一部战国时的书简名叫《梼杌》,是专门记载楚史的史书。我估计写作者是着眼于断木的木纹,取其年轮与史记的吻合。所谓“纪恶以为戒”,这至少说明,那个时代的梼杌恶名已经闻名遐迩,以此来命名煌煌史书,一定具有深意。也许,史书就是记恶戒杀之书。
美籍历史学者朱学渊指出:“为什么‘梼杌’是历史?翻阅一本《英蒙词典》,却不经意地解决了这个疑惑。原来,蒙古语的‘历史’是‘屠兀何’(tuuh),楚国历史‘梼杌’显然是用蒙古语的这个字来命名的。”他的证据是利用诸如“虎”字等几个词语蒙古语与楚方言近似读音的推论——这样的方式,当代彝族学者就在广泛使用,用彝语把古蜀历史逐一“通读”,就成为“夷史”了。朱学渊先生的结论是:人名“梼杌”可能是古代族名“屠何”或现代族名“达斡尔”。把它记为“梼杌”,只是巧合。(《以“梼杌”一词,为中华民族寻根》,《文史知识》2005年5期)
宋代大文士苏洵,为弱智的“梼杌”之所以是“历史”做了一个富有创建的圆通,他在《嘉佑集史论》中说:“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他认为历史是为忧世而作,以“梼杌”命名历史,是以恶人的名字来惩戒后人。这种将弱智儿说成恶人、并用来惩戒后人的说法,深得事物的中元。
还有学者推测,梼杌可能是指某一支好战的强悍部落。但这个与人伦格格不入的怪兽为什么从木呢?我的推测是,在冶炼青铜尚未出现之前,木器不但是最常见的工具,也应该是武器。《说文解字》:“梼,断木也,从木,寿声”。在《汉语大字典》当中,“杌”字有一个义项是:“砍树剩余的桩子”。因此,“梼”和“杌”放在一起,意思就是:树木横断之后剩下的树桩。焦循1763-1820在《孟子正义》中解释说:“惟梼杌皆从木,纵破为析,横断为梼杌。断而未折其头则名顽。是梼杌则顽之名,因其顽,假断木之名,以名之为梼杌,亦戒恶之意也。”
四川与梼杌有关的,在神、人之外,还有一本书。《蜀梼杌》一名《外史梼杌》,是北宋蜀州新津人张唐英早年的著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载记类》称:“其书本《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荀悦《汉纪》体,编年排次,于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由于来源于西蜀官方史籍,其立场与北宋官方史籍有异乃至对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晖先生指出,古蜀人用表示圆木桩的“梼杌”(梼梼)来称呼先辈祖先。“梼杌”(梼梼)应是中性词,是没有褒贬之义的。所谓的恶名应是中原诸侯方国强加给的。这就像“混沌(浑沌、浑敦)”一词,最初也是中性词,所以《庄子应帝王》中用来称呼“中央之帝”──黄帝及其后人的,显然是褒义性的。因此,《梼杌春秋》其义实际上就是“先祖们的历史”。(见《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
我很赞同这一判断。这就进一步逼近了事情的真相:梼杌具有兽、人、神、器物、历史等指称,堪称“五位一体”。
我在此引述了一些古事,并非有暗含高标鄙人出身之义,因为我等不过是尘土。只是想说,这梼杌一般的性格,一直就横行在人性的天桥上,稍不留意,他就会冲垮天桥,秀都懒得走了,只以血淋淋的断壁残垣来满足内心的嗜血——而不论结局是伤害对手,还是自伤。我的青少年时代,在搏杀之余,偶尔也会阅读家里不多的闲书,也许这个习惯最终改变了我的命运,没能以拳脚为生。记得那时读《世说新语》,王敦和周处卓然独行的故事很是吸引我,以至于我被邻居视为周处时,自己竟然还以周处后来的除害之举聊以自慰。但这种幻觉终究将彻底消散,以至后来在《水浒全传》里,这种痒意的疮,终于得到了全面爆裂。
所以啊,“金疮迸裂”不一定就是亡命之兆,也有大释放的快意。
成年以后,我读到明代的禁毁小说《梼杌闲评》,发现其命名颇有深意,既可理解为大恶人魏忠贤评传,又可解释为史事小语。小说确为“大嚼疗饥奸贼脑,横吞解渴残臣血”的泄愤之作,又岂是清风明月的“闲评”?!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历史与怪兽》一书,围绕现代性和怪兽性的辩证、历史和“再现历史”的两难来展开历史、暴力和叙事之间的互动。梼杌历经了怪兽、魔头、恶人、史书和小说的转变,说明中国文明对历史、暴力和叙事想象之一端,它引发人们思考:历史是对怪兽的暴力记录,还是本身就是暴力体现?王德威指出,“历史只能以负面形式展现其功能:亦即只能以恶为书写前提,借此投射人性向善的憧憬。扬善是历史书写的预设及终点,但填充文本的历史经验却反证了善的有效或可行性。历史的本然存在,甚至吊诡地成为集恶之大成的见证。”这是说的大历史,我想这并不一定包括个人的小历史。但就我而言,却觉得这当中蕴含了难以言传的诡变和危机……
这就是说,善与恶固然是有标准的,但历史并不掌握这个标尺。“秉笔直书”的人俨然拥有这个标尺,读史的后人则人人胸怀真理。我难以做到,只是希望在复原往事的过程里,不但相信“上帝即在细节中”,更坚信要反着阅读和理解梼杌以及冬烘的正人君子们书写的“梼杌史”。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在《黑羊和其他的寓言》里,借“恶”的口吻独白道:“事实上很难让人们跳出现在的思维模式,恶怎么做都不对,善做什么都有理。”正因为“恶”有这样的想法,“善”又一次幸免于难。
这些善与恶的争论与梼杌无关,反而与秉笔直书的冬烘先生有关。是想成为“木头木脑”的梼杌,还是表情诡谲的冬烘?自己掂量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