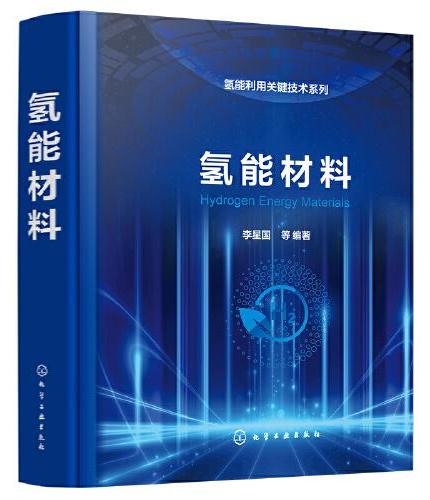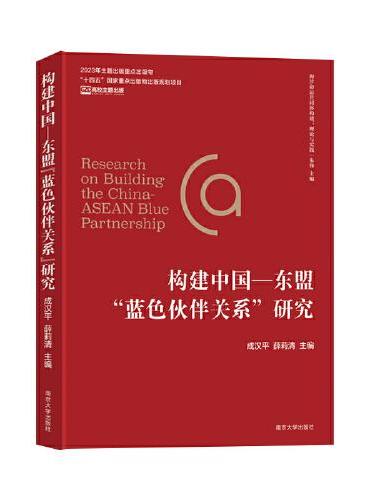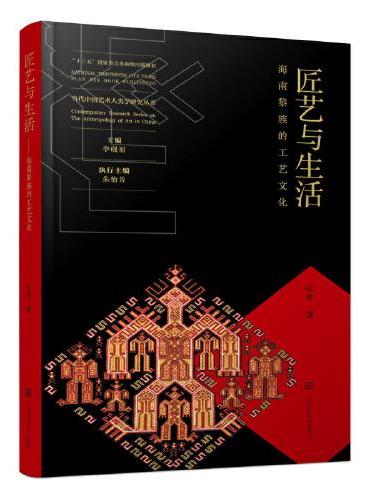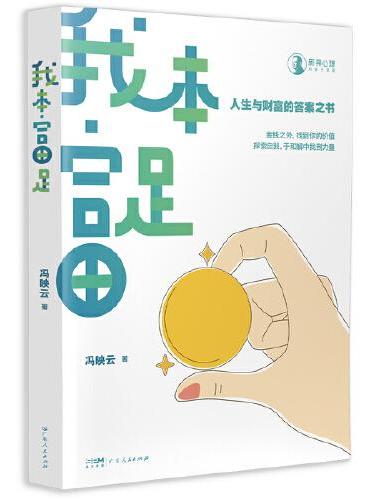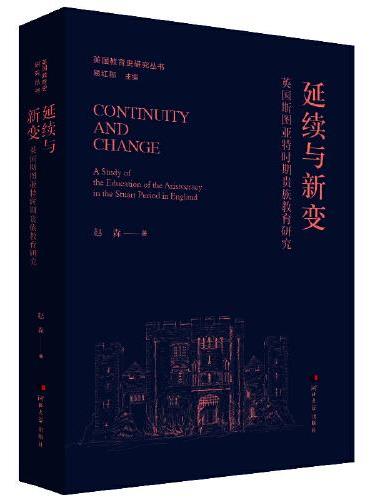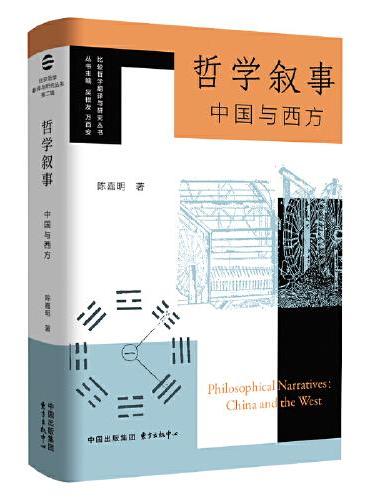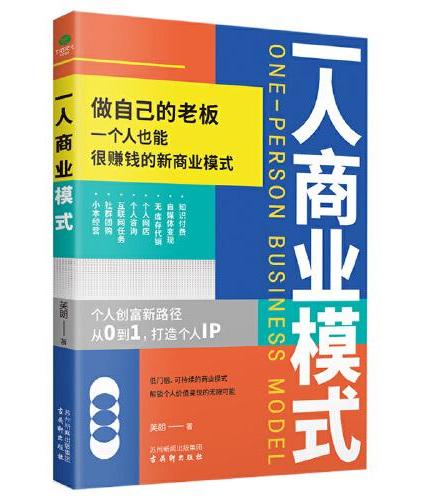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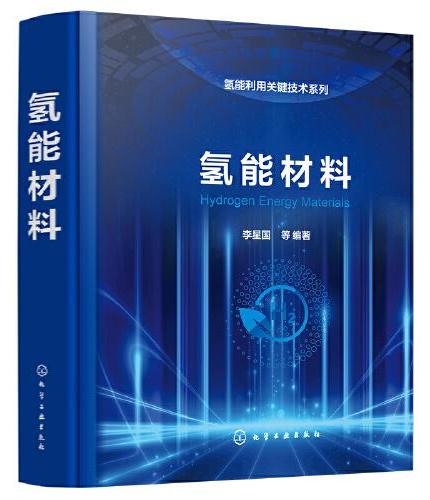
《
氢能利用关键技术系列--氢能材料
》
售價:NT$
18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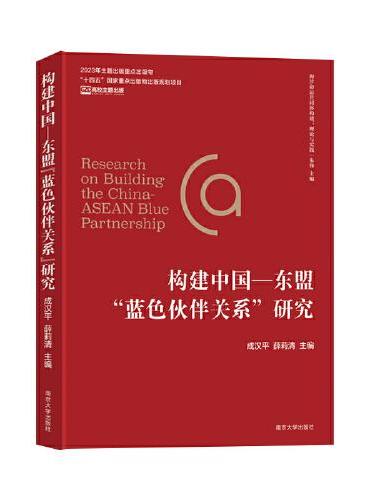
《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 理论与实践)构建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研究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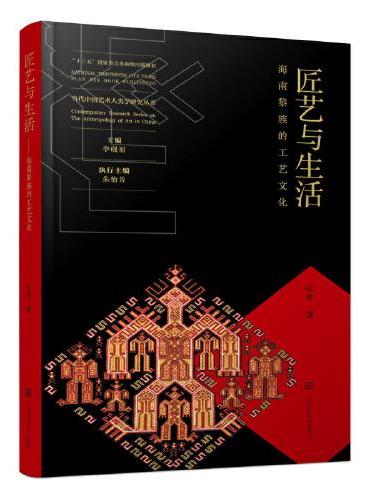
《
匠艺与生活:海南黎族的工艺文化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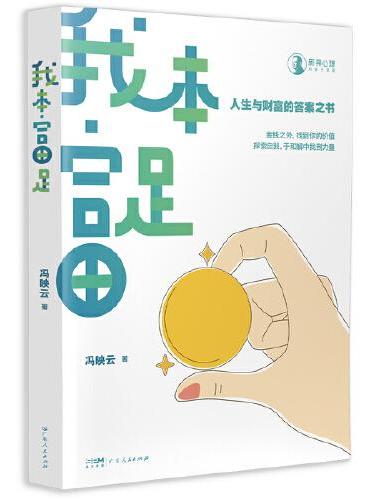
《
我本富足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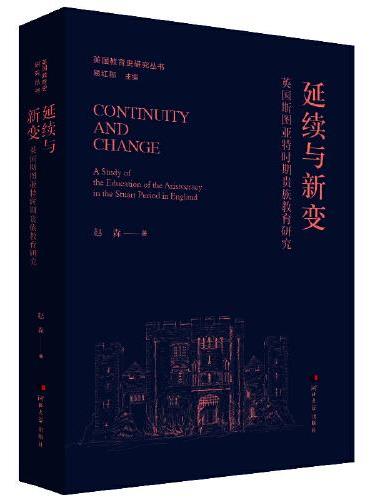
《
英国教育史研究丛书——延续与新变:英国斯图亚特时期贵族教育研究
》
售價:NT$
505.0

《
更易上手!钢琴弹唱经典老歌(五线谱版)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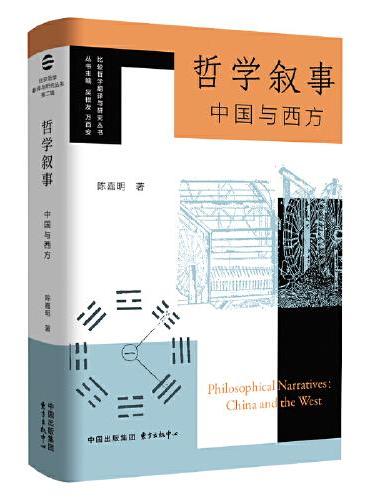
《
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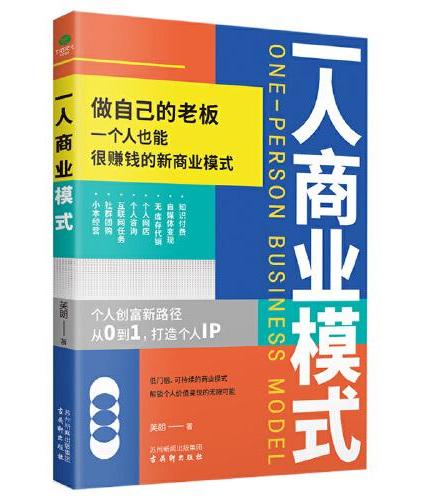
《
一人商业模式 创富新路径个人经济自由创业变现方法书
》
售價:NT$
254.0
|
| 編輯推薦: |
犹太教圣书《哈加达》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长河中颠沛流离
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书的书,更是一部人的信仰史诗。
|
| 內容簡介: |
《书之人》是一部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小说,有一定的畅销潜力。小说主要讲述了犹太教圣书萨拉热窝《哈加达》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长河中如何颠沛流离,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不同宗教的个人和家庭中,被创造,被毁损,被藏匿,被保护,被修复的故事。《哈加达》是犹太世界最受欢迎的典籍,也是史上版本最多的犹太经典,而1894年在萨拉热窝城被发现的这一本《哈加达》,是第一本被重新发现的,带有人像的中世纪希伯来语插图手稿!——人像艺术在中世纪犹太人中已被灭绝。萨拉热窝《哈加达》从此被视为稀世珍宝。
故事采取双线索的讲述方式。主线是主人公、古籍维护专家汉娜希斯博士的经历,她受联合国委托,去萨拉热窝修复一本战争中被抢救出来的奇书,即萨拉热窝的《哈加达》。从战火中抢救了此书的是萨拉热窝图书馆馆长奥兹仁卡拉曼。他们在共同工作中很快相爱,但是在之后有关此书的一系列离奇事件后,他们之间产生了误会,于是汉娜离开萨拉热窝、去每一个能够帮助她解开谜团的专家、老师、朋友那里寻找有关此书的线索,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发现并解开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并且,原来她本人就是半个犹太人。在不同领域的奇人的帮助下,她终于明白了一片虫翅、一根羽毛、一块酒痕、一滴盐水、一丝白毛所蕴含的意义……故事的另一条线索就此展开……
小说的结尾,奥兹仁说:“我觉得这一本《哈加达》来到这里是有理由的,它是来考验我们的,看这儿有没有人能够明白一个道理:让我们团结的东西要多于让我们分裂的东西:是一个人,要比是个犹太人还是穆斯林,是个天主教徒还是个正教徒更为重要。
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书的书,更是一部信仰之书。
|
| 關於作者: |
|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1955- ,出生于悉尼,拥有美国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1990年因报道海湾战争获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的哈波以尔奖。2001年出版的《奇迹之年》是澳大利亚政府推荐全民阅读的年度佳作。2006年因小说《马奇》获普利策奖。
|
| 目錄:
|
目录
汉娜(一九九六年春,萨拉热窝) ........1
虫翅(一九四○年,萨拉热窝) ........49
汉娜(一九九六年春,维也纳) ........95
羽毛和玫瑰(一八九四年,维也纳) ........111
汉娜(一九九六年春,维也纳) ........135
酒痕(一六○九年,威尼斯) ........153
汉娜(一九九六年春, 波士顿) ........201
盐水(一四九二年,塔拉戈纳) ........227
汉娜(一九九六年春,伦敦) ........271
白毛(一四八○年,塞维利亚) ........285
汉娜(一九九六年春,萨拉热窝) ........329
萝拉(二○○二年,耶路撒冷) ........341
汉娜(二○○二年,阿纳姆地,古努美伦季) ........351
后记 ........384
译后记 ........389
|
| 內容試閱:
|
汉娜一九九六年春,萨拉热窝
一
我还是一开始就说清楚吧: 那不是我的日常工作。
我喜欢在自己清洁、宁静、明亮的实验室里一个人工作。温度能控制,需要的一切都在手边。可不得已时我也做点实验室外的工作,也确实赢得过不错的名声。那是在博物馆不愿为藏品的运输付保险费的时候,在私人收藏家不愿让外人确切知道他们有什么藏品的时候。而且,为了完成有趣的工作,我也曾飞越半个地球。但是我还从没到过这种地方: 这座城市停止互相射击才五分钟,我已来到城市正中一家银行的会议厅里。
首先,若是在我家里,是不会有保安在我实验室里晃来晃去的。我是说,我那博物馆里虽有几位专业保安人员巡逻,他们都是一声不响的,做梦也不会想到闯进我的工作空间里来。这里的几位跟他们可是不同。这儿一共有六位,两位是银行警卫;两位是来监视银行警卫的波斯尼亚警察;还有两位则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来监视波斯尼亚警察。他们都在哔啵乱响的手机上大声交谈,说的是波斯尼亚话或丹麦话。这样的人群似乎还不够,还来了位联合国观察员哈密什萨冉。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位苏格兰血统的锡克教徒,一身苏格兰呢服装,缠着靛青色大头巾,非常精干。只有联合国有这样的人。我只好请他去向波斯尼亚人指出: 抽烟这件事不要发生在暂时放置一份十五世纪手稿的房间里。那之后他们就更加无聊了。
我也开始无聊了。我们已经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尽力消磨着时间。为了利用光线,几位警卫已帮助我把会议桌搬到窗户附近。我已安装好立体摄像显微镜,也摆出了工具: 文件编制摄像头和手术刀。白明胶已在大口杯里的加热垫上融化。小麦糨糊,亚麻线和金箔也全都摆好了。还有几个玻璃纸信封,是准备在有幸发现装订碎屑时使用的——从研究面包皮的化学你所能得到的知识有时可能很惊人。我还摆出了各种不同的小牛皮样品,一卷卷色调、质地各不相同的手工纸,还有放在“摇篮”里的泡沫塑形,为放古卷做好准备——如果他们真带来了古卷的话。
“我们还得等多久,你有数吗?”我问萨冉,萨冉只耸了耸肩。
“我估计是从国家图书馆来的代表耽误了,因为那书是博物馆的财产,代表不到,银行是不能进圆穹地窖取书的。”
我心里烦躁,来到窗户面前。我们是在银行的顶楼。这是一座婚礼蛋糕式的奥匈帝国建筑,跟城里其他建筑一样,灰泥门面都已被迫击炮轰了个千疮百孔。我的手一触到玻璃,寒冷就透了进来。据说已是春天,下面银行大门边的小花园里番红花已经开放。那天上午早些时还下过雪,一盏盏小花上覆盖着蓬松的雪花,仿佛是一小杯一小杯的热牛奶咖啡。白雪至少使房里的光线均匀明亮,形成了最佳的工作光线。要是能工作就好了。
就为找点事做,我打开了几个纸卷——法国制作的亚麻纸。我用金属镇尺碾过每张纸,把它压平。镇尺擦过大幅亚麻纸的声音像是我在悉尼家里听到的海涛。我注意到自己的手在发抖。干我这种工作,手抖可不是好事。
你不会认为这手是我较好看的部分。手背皲裂,松弛,简直不像手腕的延伸部分——我可以满意地说,我的手腕倒是纤小光润,跟我其他部分一致的。上次跟妈妈吵架时,妈妈就说我这手是“老妈子手”。从那以后,我跟妈妈非得在“大都会”见面喝咖啡不可时——对,时间很短,我俩都像冰凌柱一样易碎——我就戴上一副从“救世军”商店买来的手套,算是给自己解解嘲。当然,在悉尼,也只有在“大都会”人们才不会意识到其中的自嘲意味。我妈妈就意识不到,她还说要给我买顶帽子,跟手套匹配呢。
在明亮的雪光里我这手显得比平时更难看了。因为用浮石从牛肠上磨去脂肪,我的手全红了,而且蜕皮。你在悉尼生活,却想弄到一米牛犊肠,那可是世界上最不简单的事。自从屠宰场因为要给二年奥运会提供场地而被迁出霍姆布什起,你就得开了车去买——你的车基本上是在呜呜地叫,却不动弹,终于到达目的地时,却又遇到那么多保卫措施因为动物解放者众多,你几乎就进不了门。他们觉得我有点古怪,我倒不责备他们。为什么会有人需要一米牛犊的盲肠?人家一时也确实难以明白。但是,你既然是在五百年前的古物上工作,你就得知道那类东西五百年前是怎么做的。这是我的老师沃纳亨利希深信的道理。他说关于研磨颜料混合石膏粉的道理你可以愿怎么读书就怎么读,但是要想真弄懂它,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亲手做过。如果我想弄懂像cutch和schoder这类词语所描述的东西,我就得自己打造金箔: 敲打,叠过来再敲打,放在它不会黏附的东西上再敲打——比如洗干净的柔软的牛犊肠上。到最后,你才能得到一小包金箔。每一片的厚度不足千分之一毫米,而你那双手就狰狞得可怕了。
我把手捏成了拳头,想让老太婆般松弛的手光滑起来,也想看看能不能控制住颤抖。从前一天在维也纳换飞机起就一直紧张。我常常旅行。既然你生活在澳大利亚,想在这中世纪手稿维护领域得到一份最有趣的工作,基本上就只好四处奔波了。但是我一般都不去战地记者能发出划时代的重大报道的地点——我知道有人搞那类活动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我估计他们有一种“不会落到我身上”的乐观主义情绪,而造就了他们的正是那情绪。可我呢,我却完全是个悲观主义者。如果我去的国家在什么地方有个狙击手,那么,进了他的瞄准镜的准会是我,我充分肯定。
飞机还没降落,你已经见到了战争。我们穿出灰蒙蒙的云幕它似乎是欧洲天空亘古不变的状态,起初,环抱亚得里亚海的赤褐色小瓦房似乎成了我所熟悉的景观: 远处,悉尼城的红色房顶就在下面,靠近邦迪海滩的深蓝色的弧线。但在眼前这景色里,一半的房屋已经不存在了,只留下一排排断垣残壁,参差不齐地耸立着,俨然是一排排腐败的牙齿。
越过高山时,空中出现了湍流,到波斯尼亚时我不愿让自己看窗外,于是拉下了遮光板。我身边那年轻人,从他那柬埔寨围巾和瘦削的害疟疾的形象看,估计是位工作助理。他显然想往窗外看,我却没理会他那肢体语言,反倒提出了问题,想分散他的注意力。
“来这里有什么贵干?”
“排雷。”
我想说点真正接近问题的话,比如“业务多么”之类的,却终于违背性格,闭了嘴。然后,我们就降落了。他跟机上的每个人一样,站了起来,在甬道里挤来挤去,在头顶的行李柜里寻找。他扛上了一个庞大的帆布背包,一走动几乎撞破了挤在他身后的人的鼻子——他挎背包那动作真要命,一晃九十度。这情景那时你在邦迪的公共汽车上也能见到。
机舱门终于开了,旅客们仿佛粘到了一起,往外渗透。我是唯一仍然坐着的人。我感觉像是吞下了一块大石头,把我固定在座位上了。
“是西斯博士么?”航班空姐在空出的甬道上跑来跑去。
我正想说“不,那是我妈在英语里博士和医生是一个词: doctor。“我”的母亲是医生,而“我”是博士,所以引起了这场误会。”,却意识到她指的就是我。在澳大利亚只有傻瓜才拿博士头衔招摇。我除了“女士”从没填写过其他的头衔。
“您的联合国陪护人员在停机坪等您。”谜底揭晓了。在为这份工作办手续时我就注意到,联合国喜欢给人加上最闪光的头衔。
“陪护人员?”我傻呵呵地重复,“停机坪?”他们倒是说过有人来接我,但我以为不过是个懒洋洋的出租车司机,举着牌子,而且拼错了我的名字。航班空姐给了我一个快活而完美的德国式微笑,对我躬下身来,掀起拉下的遮光板。我往外一望,三辆深色窗户的装甲车懒洋洋地停在飞机翅膀尖下,也就是把美国总统拉来拉去的那种。这场面本该叫我放心,却让我肚子里的石头加重了一吨。装甲车外的深草里插着牌子,用几种文字标明: 小心地雷。我可以见到一部庞大的货运飞机的机身,已经生了锈。它一定是闯到跑道外遭遇了不愉快的事故。我望了望那位“笑靥小姐”。
“我还以为他们遵守了停战协议呢。”我说。
“确实遵守的,”她灿烂地说,“大部分日子都遵守的。您的手提行李要人拿么?”
我摇摇头,弯下身子想拽出那紧塞在前面座位下的沉重的箱子。一般情况下,航
班都不愿接受带金属尖角的行李登机,但是德国人非常敬业,我解释了不愿托运我的工具的理由: 怕它们到欧洲旅游去了,扔下我一个人傻坐着无法工作。检查人员倒真谅解了我。
我是个世界水平的胆小鬼,可我同意了干这样的工作,那是因为我爱好它。确实如此。说实在的,我从来就没想到过放弃。有机会在一份世界上最珍稀最神秘的文卷上工作,你是不会说“不”的。电话是凌晨两点来的。你要是住在悉尼,许多电话常常就在这时打来。连最聪明的人,管理着全球驰名机构的博物馆馆长,能告诉你某一天的恒生指数准确到分的首席执行官,也都会忘记一个最简单的事实: 悉尼比伦敦一般要早九个小时,比纽约早十四个小时。这骚扰有时让我恼火。阿密泰扬托夫是个精明人,也许还是这个领域里最精明的人,可他怎么就算不出耶路撒冷和悉尼之间的时差呢?
“你好,占娜,”他说。跟往常一样,他那浓重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口音照例改变了我名字的一个音,把汉娜叫做了占娜,“我没吵醒你吧?”
“没有,阿密泰,”我说,“我一向就是凌晨两点起床的——一天里的最好时刻。”
“啊,好吧,对不起,但是我以为你知道了会感兴趣: 萨拉热窝《哈加达》出现了。”
“啊!”我猛然彻底清醒了,说,“倒真是,啊,了不起的消息。”确实是的。不过那了不起的消息也可以在文明点的时间让我在电子邮件里读到的,我真想不出阿密泰干吗非吵醒我不可。
阿密泰跟所有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一样,属于自我克制型,但这个消息却让他忘乎所以了。“我可是一直认为这书能‘活’下来的,能逃脱炮弹的轰击。”
这个萨拉热窝《哈加达》,是有名的稀世古卷,一部有大量插图的希伯来文手稿,创作于中世纪的西班牙,那还是犹太信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插图的时代。一般人认为,《出埃及记》里的诫命“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也不可敬拜”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34章,第14、17节。,已使中世纪犹太人禁绝了人像艺术。可那书一八九四年在萨拉热窝重见阳光时,那一页一页的彩色微型人像插图却把压在它头顶的这个说法推翻了,艺术史也随之改写了。
从一九九二年萨拉热窝围城开始,博物馆和图书馆就成了战斗攻击的靶子,这部古代手稿也随之遗失。有谣言说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政府已把它卖掉,买了武器。不,摩萨德Mossad, 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the Institute for Intelligence and Special Operations,以色列政府的主要情报组织之一。的特务已通过萨拉热窝机场的隧道把它偷运出去。这两个“电影脚本”我都不信。我认为这本美丽的书大有可能已随燃烧弹的烈焰卷进了烧毁的书页的旋风,跟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文契、《古兰经》的古卷、斯拉夫人的卷轴一起,化作了热烘烘的雪花,飘落到城市各地。
“但是,阿密泰,这四年里它在什么地方?是怎样发现的?”
“你知道佩萨赫Pesach, 犹太人的逾越节。,对吧?”
事实上我知道。一个朋友曾招待我们在沙滩上野餐,让我过了一个很不正统的喧嚣的逾越节,到现在还在调理喝了红酒后很不舒服的余醉。在希伯来文里,那个逾越节家宴叫做塞德尔,原意是“秩序”,可那却是我近年的经历里很没有秩序的夜晚之一。
“对,昨天晚上萨拉热窝的犹太社区举行了塞德尔,非常戏剧性的是,在家宴进行时他们竟把那份《哈加达》捧了出来。社区首脑还发表了一篇演说,说这本书之大难不毁正象征了萨拉热窝多民族理想的大难不毁。你知道那文卷是谁抢救出来的么?那个人名叫奥兹仁卡拉曼,博物馆下属图书馆的馆长。是冒着猛烈的炮火钻进屋里去的,”阿密泰的声音似乎突然嘶哑了,“你能想象么,占娜?一个穆斯林,为了抢救一本犹太人的书,拿自己的脖子去冒险。”
为了某种英勇行为而感动似乎不是阿密泰的性格。有位不大谨慎的同事曾经透露过,阿密泰服义务兵役时是被分在突击队的。那是个超级保密的部队,以色列人只叫它“单位”。虽然已是很久前的事,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身板和神情仍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有举重运动员般结实的肌肉,还有一种超级的机警。他跟你说话时正眼望着你,其他时候却似乎都在分析着周围的事物,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我问起他关于“单位”的事时,他似乎真生气了。“我从没对你说过那是什么好玩意儿。”他狠狠地说。我觉得他那回答相当惊人。像那样爱护书籍的退伍突击队员,你肯定没见过几个。
“那么,那老家伙把书拿到手之后又怎么办了?”我问。
“他把它存进了中央银行的地下圆穹保险库的箱子里。你可以想象那情况对羊皮纸所起的作用……萨拉热窝的保险库至少从前两个冬季起就没有送过暖气了……还有那金属的现金箱——偏偏是金属的……现在那书又回到箱子里去了……一想起那情况我心里就难受。总之,联合国需要派人去检查情况了。他们愿意拨款做一切必要的维护工作——他们想用它尽快举行一次展览会,为了提高城市的民心,你知道。于是我在他们下个月打算在泰特美术馆召开的会议程序里见到了你的名字。我觉得既然你愿意来北半球,说不定让你来干这份工作倒合适?”
“我?”事实上我的声音变成了尖叫。我决不假惺惺地谦逊,我的工作确实做得很棒。但这样一份一辈子只能遇见一回的、能叫你一鸣惊人的工作,在欧洲至少有二十个人可以做,他们资格都比我老,关系都比我好。“他们为什么不找你干?”我问。
阿密泰比任何活着的人都懂得这份萨拉热窝《哈加达》,他写过好多篇关于它的论文。我知道他若有机会办这份古代抄本的事一定会非常高兴。但是他却发出了一声深沉的叹息。“塞尔维亚人三年来一直在说波斯尼亚人是狂热的穆斯林,这说法终于使一些波斯尼亚人相信了。现在那儿的捐款大户似乎都是沙特人,有人就反对把这工作交给以色列人做。”
“啊,阿密泰,很抱歉……”
“没事,占娜。我的朋友很多。他们也不愿让德国人干。当然,我首先推荐的是沃纳——你别生气……”沃纳马瑞亚亨利希博士先生不但是我的老师,而且除了阿密泰本人,他也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希伯来文手稿专家。我是根本不会生气的。但是,阿密泰解释说: 波斯尼亚人对德国人也不满意,因为正是德国人承认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从而引发了战争。“而联合国又不愿意让美国人来干,因为美国国会老是苛刻地攻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我觉得倒是你最合适,因为,谁会对澳大利亚人有多大意见呢?我还告诉过他们,你在技术上很可靠。”
“谢谢你的大力支持,”我说,然后更真诚地讲下去,“阿密泰,这事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谢谢你,真的。”
“你可以用整理好资料来感谢我的。那我们就至少能印出一份美丽的复印件了。你还可以把你画出的图也给我,对,还附上一份你的报告稿,尽可能快,好吧?”
他的口气带了那样的向往,我为自己的高兴感到了内疚。但是有个问题我还非问不可。
“阿密泰,对于这书的真伪是否还存在争论呢?你知道那些谣言的,打仗时流传过的……”
“不,对那类问题我们根本不理会。既然图书馆馆长卡拉曼和他的上级博物馆馆长都鉴定是真的,就不会有问题。在这方面你的工作只是技术性的。”
技术性的!我们就看看吧,我心想。我的大量工作都是技术性的。科学和技术,凡是有相当的聪明和精细的运动神经技术的人,都可以通过培训学会。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对历史的直感。研究还得与想象相结合,有时我可以钻进书卷制作人的头脑里去。我可以想象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是怎样进行工作的。那就是我能为人类知识的沙箱增加一两粒细沙的原因,也是我所进行的工作最让我着迷的部分。而萨拉热窝《哈加达》的问题又那么多,我哪怕能解决掉一个……
我再也睡不着了。我披上运动套装出了大门,走过了夜晚的街道。那里依稀还有点酸味,混合了呕出的啤酒和油煎脂肪的臭气。我来到海滩边,那里有从覆盖了半个星球的浩瀚无涯的大洋上刮来的海风,清爽,带点咸味。因为是秋天,又是在一周正中的夜晚,除了几个醉汉在冲浪俱乐部的墙根趔趄,一对情侣在海滩的浴巾上拥抱之外,周围几乎阒寂无人,没有人会注意我的。我沿着浪花走了起来。黑暗的沙滩闪着漆光,浪花在沙滩边闪烁。我还没意识到,却已像孩子一样奔跑起来。我跳跃着,闪避着浪花。这一切已是一周前的事。在随后的日子里,欢快的心情逐渐被申请签证、购买两个航班的机票、办理联合国的例行手续和一大堆焦虑和紧张埋葬掉了。在我承受着包裹的重压摇晃着走下舷梯来到停机坪时,我只好不断提醒自己,这正是我这一辈子为之活着的任务。
我只打量了一眼像大碗边缘一样卷起在周围的山峦,一个戴蓝色头盔的士兵斯堪的纳维亚型的高个儿已从中间那辆车跳了出来,抓过我的包裹,扔进了装甲汽车的后厢。
“稳着点!”我说,“里面有精密仪器!”那士兵的唯一回答是抓住我的手臂,把我塞进了后座,砰一声关上门,跳到前面的司机身边坐下。自动锁断然地喀哒一响,司机开大了油门。
“好呀,这倒是我头一回,”我说,想表现得活跃一点,“古籍保护人员是没有多少必要坐装甲汽车的。”那士兵和躬在庞大的装甲车驾驶盘边的老百姓都没回答。那司机瘦削,紧张,脑袋像乌龟缩在肩胛里。被摧毁的城市从有色玻璃窗外闪过,依稀可见,是一幢幢被开花弹炸碎的建筑物。几辆装甲车急速地开着,绕着一个一个迫击炮弹狰狞的弹坑,在装甲车掘起的沥青块上颠簸。街上车辆稀少,大部分人都步行,看去全都高瘦、憔悴,拉紧了外衣,顶着还没完全到临的春天的寒气。我们经过了一个公寓街区。那里简直就像我小姑娘时代的玩具房屋,前面的墙壁全炸掉了,露出了后面的房间。在这个街区,墙壁被爆炸剥掉,露出的房子内部却像玩具房屋一样还有家具。经过时我才意识到,有人还在那里设法过日子。他们仅有的保护就是几块飘动在寒风里的塑料布。他们还洗了衣服,衣服飘荡在绳索上,绳索牵在被炸碎的水泥里扭曲的钢筋之间。
我还以为他们会立即送我去看古卷呢,可那一天却是在没完没了的沉闷会晤里消磨掉的。首先是跟考虑过文化问题的每一位联合国官员见面,然后是跟波斯尼亚博物馆馆长见面,跟一群政府官员见面。一想到即将开始的工作,我担心自己不会有多少觉睡了,可就连那天给我送来的十一二杯土耳其浓咖啡也没有用,我还是昏沉了好一会儿——那也许是我的手仍然发抖的原因。
警察的无线电发出静电的噪声,所有的人都突然站了起来: 警察、保卫人员、萨冉。银行官员抽开了门闩,又是一群警卫人员排成楔形,飞跑着进来了。正中是一位瘦弱的青年,一身败了色的牛仔装,很可能就是那位让我们等了许久的博物馆懒虫。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跟他生气了,因为他捧着一个金属箱子。等到他把它放在长椅上时,我才看见箱子上还有好几处盖了印章的蜡封和胶纸密封。我把我的解剖刀递给他。他破掉封印,揭开盖子,打开了几层丝绢,然后把书交给了我。
|
|